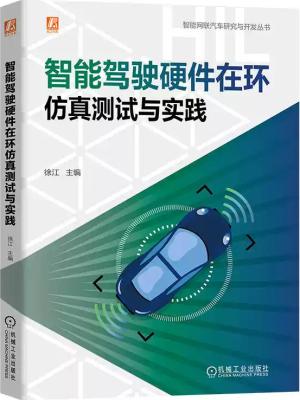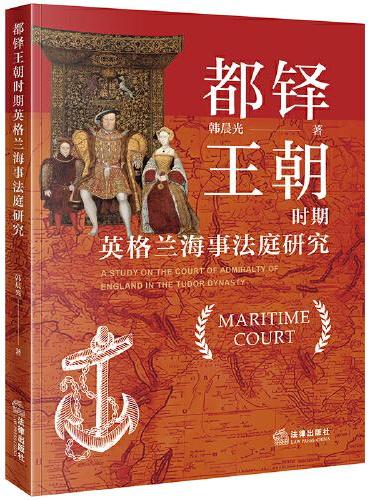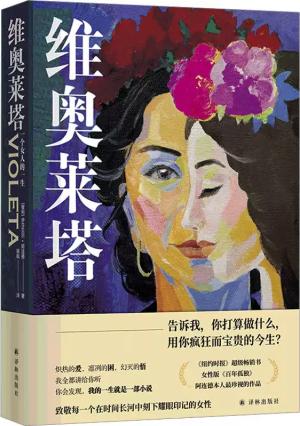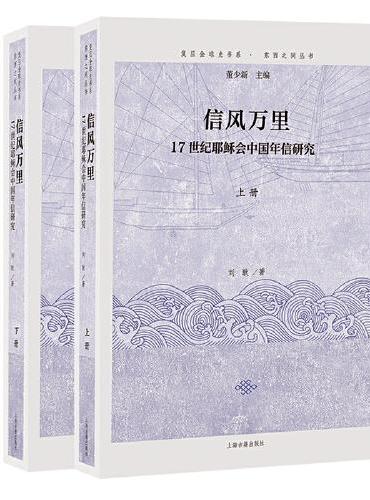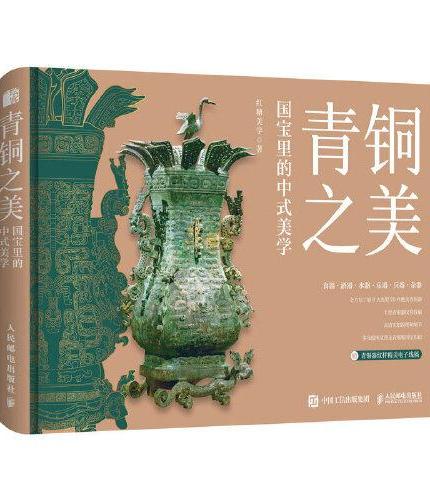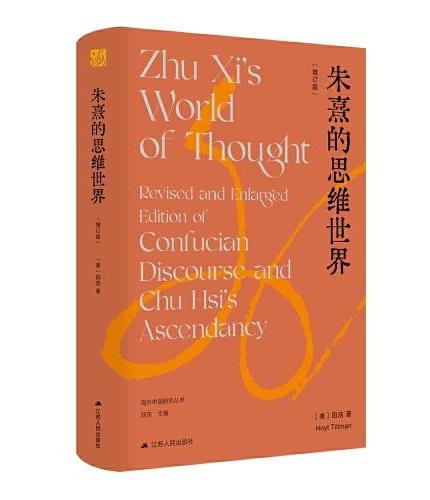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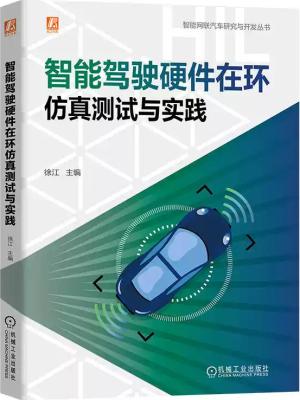
《
智能驾驶硬件在环仿真测试与实践
》
售價:NT$
70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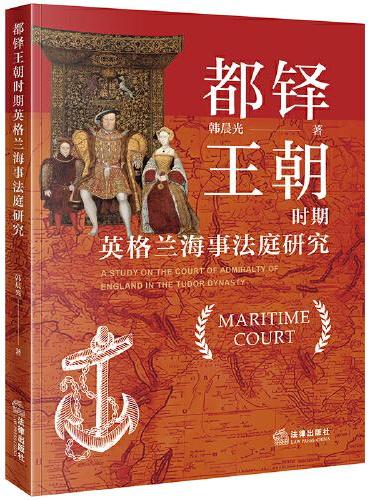
《
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海事法庭研究
》
售價:NT$
398.0

《
中年成长:突破人生瓶颈的心理自助方案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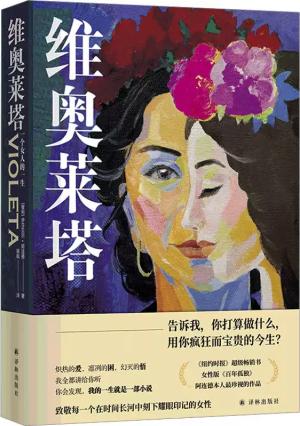
《
维奥莱塔:一个女人的一生
》
售價:NT$
347.0

《
商业银行担保管理实务全指引
》
售價:NT$
6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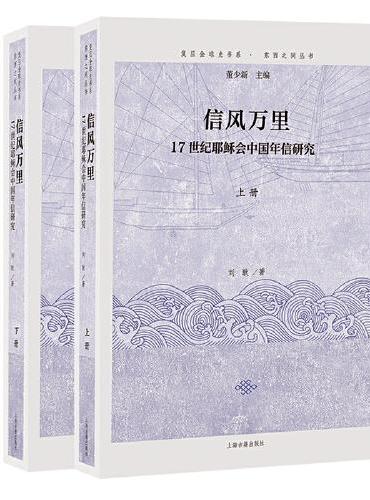
《
信风万里:17世纪耶稣会中国年信研究(全二册)
》
售價:NT$
8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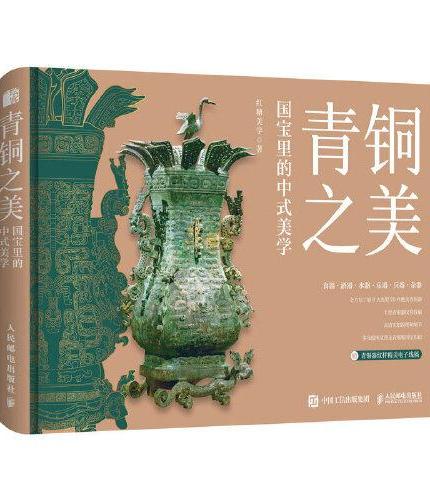
《
青铜之美 国宝里的中式美学
》
售價:NT$
8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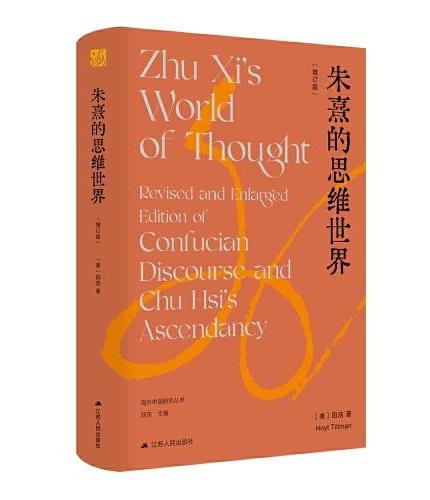
《
海外中国研究·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
》
售價:NT$
653.0
|
| 內容簡介: |
汪晖代表作,也是21世纪中国思想领域的扛鼎之作,出版二十年来在国内国际人文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迄今已有英文、韩文(全译本),及日文、意大利文等多语种译本。
作者以“现代中国的形成”为核心关切,以“知识考古”为方法,从观念史与社会史互动的双重视野中,追索现代中国认同的思想脉络与形成机制。全书两卷四部,每部分别以“理与物”、“帝国与国家”、“公理与反公理”和“科学话语共同体”等为论题,试图追问:宋明时代儒学的天理世界观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历史动力是什么?清代帝国建设与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晚清思想对于现代性的复杂态度能够提供给我们哪些思想的资源?现代中国的知识体制是如何构筑起来的?现代公理世界观与天理世界观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的是关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的现代”,以及中国思想的现代意义的历史理解。
|
| 關於作者: |
|
汪晖,1959年生,江苏扬州人。曾就学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和社会理论等。
|
| 目錄:
|
二十周年纪念版前言
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 (重印本前言)1
前言1
导论1
第一节 两种中国叙事及其衍生形式2
第二节 帝国/国家二元论与欧洲“世界历史”23
第三节 天理/公理与历史47
第四节 中国的现代认同与帝国的转化71
上卷 第一部 理与物103
第一章 天理与时势105
第一节 天理与儒学道德评价方式的转变105
第二节 礼乐共同体及其道德评价方式125
第三节 汉唐混合制度及其道德理想155
第四节 理的系谱及其政治性187
第五节 天理与郡县制国家212
第六节 天理与“自然之理势”254
第二章 物的转变:理学与心学260
第一节 “物”范畴的转化260
第二节 格物致知论的内在逻辑与知识问题270
第三节 “性即理”与物之自然279
第四节 乡约、宗法与朱子学284
第五节 朱子学的转变与心学291
第六节 此物与物298
第七节 无、有与经世310
第八节 新制度论、物的世界与理学的终结324
第三章 经与史(一)345
第一节 新礼乐论与经学之成立345
第二节 经学之转变382
第四章 经与史(二)411
第一节 辟宋与清代朱学的兴衰411
第二节 经学、理学与反理学429
第三节 六经皆史与经学考古学458
上卷 第二帝国与国家487
第五章 内与外(一):礼仪中国的观念与帝国489
第一节 礼仪、法律与经学489
第二节 今文经学与清王朝的法律/制度多元主义519
第三节 今文经学与清王朝的合法性问题551
第四节 大一统与帝国:从礼仪的视野到舆地学的视野579
第六章 内与外(二):帝国与民族国家609
第一节 “海洋时代”及其对内陆关系的重构609
第二节 作为兵书的《海国图志》与结构性危机619
第三节 朝贡体系、中西关系与新夷夏之辨643
第四节 主权问题:朝贡体系的礼仪关系与国际法679
第七章 帝国的自我转化与儒学普遍主义737
第一节 经学诠释学与儒学“万世法”737
第二节 克服国家的大同与向大同过渡的国家744
第三节 《大同书》的成书年代与早期康有为的公理观753
第四节 作为世界之治的“大同”765
第五节 经学、孔教与国家782
第六节 从帝国到主权国家:“中国”的自我转变821◎
下卷 第一部 公理与反公理831
第八章 宇宙秩序的重构与自然的公理833
第一节 严复的三个世界833
第二节 “易的世界”:天演概念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方案844
第三节 “群的世界”:实证的知识谱系与社会的建构882
第四节 “名的世界”:归纳法与格物的程序897
第五节 现代性方案的“科学”构想920
第九章 道德实践的向度与公理的内在化924
第一节 梁启超的调和论及其对现代性的否定与确认924
第二节 “三代之制”与“诸科之学”(1896—1901)929
第三节 科学的领域与信仰的领域(1902—1917)956
第四节 科学与以人为中心的世界(1918—1929)995
第十章 无我之我与公理的解构1011
第一节 章太炎的个体、自性及其对“公理”的批判1011
第二节 临时性的个体观念及其对“公理”的解构
——反现代性的个体概念为什么又以普遍性为归宿?1021
第三节 民族—国家与章太炎政治思想中的个体观念
——在个体/国家的二元论式中为什么省略了社会?1047
第四节 个体观念、建立宗教论与“齐物论”世界观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
——在无神的现代语境中,什么是道德的起源?1078
下卷 第二部 科学话语共同体1105
第十一章 话语的共同体与科学的分类谱系1107
第一节 “两种文化”与科学话语共同体1107
第二节 中国科学社的早期活动与科学家的政治1125
第三节 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科学话语与“国语”的创制1134
第四节 胡明复与实证主义科学观1145
第五节 作为“公理”的科学及其社会展开1169
第六节 现代世界观与自然一元论的知识分类1200
第十二章 作为科学话语共同体的新文化运动1206
第一节 “五四”启蒙运动的“态度的同一性”1206
第二节 作为价值领域的科学领域1208
第三节 作为科学领域的人文领域1225
第四节 作为反理学的“新理学”1247
第十三章 东西文化论战与知识/道德二元论的起源1280
第一节 文化现代性的分化1280
第二节 东西文化论战的两种叙事模式1289
第三节 东/西二元论及其变体1292
第四节 新旧调和论的产生与时间叙事1296
第五节 总体历史叙事中的东/西二元论及其消解1309
第六节 总体历史中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314
第七节 从文化观的转变到主体性转向1327
第十四章 知识的分化、教育改制与心性之学1330
第一节 知识问题中被遮蔽的文化1330
第二节 张君劢与知识分化中的主体性问题1343
第三节 知识谱系的分化与社会文化的“合理化”设计1370
第十五章 总论: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1395
第一节 作为普遍理性的科学与现代社会1395
第二节 科学世界观的蜕化1403
第三节 现代性问题与晚清思想的意义1410
第四节 作为思想史命题的“科学主义”及其限度1424
第五节 哈耶克的科学主义概念1438
第六节 作为社会关系的科学1454
第七节 技术统治与启蒙意识形态1486
附录一
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1493
第一节 作为“民族形式”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政治与文学问题1495
第二节 “地方形式”概念的提出及其背景
——战争对乡村与都市关系的重构1499
第三节 “地方性”与“全国性”问题1503
第四节 方言问题与现代语言运动1507
第五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否定之否定1526
附录二
亚洲想像的谱系1531
第一节 “新亚洲想像”的背景条件1531
第二节 亚洲的衍生性:帝国与国家、农耕与市场1539
第三节 亚洲概念与民族运动的两种形式1552
第四节 民主革命的逻辑与“大亚洲主义”1565
第五节 多个历史世界中的亚洲与东亚文明圈1574
第六节 互动的历史世界中的亚洲1592
第七节 一个“世界历史”问题:亚洲、帝国、民族国家1603
参考文献1609
人名索引1666
|
| 內容試閱:
|
二十周年纪念版前言
本书初版于2004年,2008年和2014年重印时曾分别做过一点修改,但没有做全面校订。这一版的校订始于英文版的翻译过程。2020至2022年,正值新冠疫情期间,译者们每完成一章的工作,都会将翻译中遇到的疑问汇集到韩嵩文(Michael Gibbs Hill)教授那里,由他与我共同商量和确认。我邀请接受过系统的历史学和政治学训练的邓欢娜与我一起处理这些问题。在这一时期的合作中,欢娜承担了主要的查核工作。
2023年,在三联书店的督促之下,本书20周年纪念版的出版工作提上了日程。由于邓欢娜参与了英译本的释疑和查核工作,由她负责此书的校订工作最为合适。她独立完成了上卷第一、二部和下卷第一部的校订,黄清源和李立敏共同完成了下卷第二部的校订。此外,本书出版以后,一些认真的读者不时来信分享他们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并指出一些文字上的讹误,这些意见也在甄别后吸纳到这一版中。这是作者的幸运:因着这一共同努力,这部作品经过较为全面的校订终于再度面世。我在此向欢娜、立敏、清源、各位译者和读者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汪晖, 2024年7月22日于清华园
文摘二
历史叙述中的国家与帝国
(节选自2008年重印本前言)
既然从中国历史内部展开了郡县与封建的问题,为什么又要讨论帝国和国家的问题?很显然,这个问题是与全书的叙述主线——即对“早期现代性”问题的追问——密切相关的。我追问的是:理学的形成是否显示了宋代以来的社会、国家和思想已经开始了某种重要的、可以被称之为“早期现代”的转变?正是在这个问题的压迫之下,我重新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由日本学者提出的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假设上来。“唐宋转变”是内藤湖南在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的概念,其后宫崎市定等京都学派的学者发展了“东洋的近世”、“宋朝资本主义”的论题。他们从贵族制度的衰败、郡县制国家的成熟、长途贸易的发展、科举制度的正规化等方面讨论这个“早期现代”问题,宫崎市定还将理学明确地视为“国民主义”——即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关于京都学派与帝国政治之间的关系,我没有能力在这里做出详细的讨论,但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至今值得讨论的议题,其中唐宋转变及宋代作为东亚近世历史的开端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的讨论主要从“天理的成立与郡县制国家”的关系着眼,分析儒学形态的转变,其中包含了与京都学派所讨论的问题的某种对话和回应。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对早期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会与帝国—国家问题发生关联?京都学派的问题与此又有何种关系?
霍布斯鲍姆曾说,假定19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有一个什么中心主题的话,那就是民族国家;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它的另一个更为基本的叙述则是资本主义。在19世纪以降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叙述中,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述是通过和其他叙述的对立构造出来的,所谓帝国和国家的叙述,就直接地表现了这个对抗。历史的观念在19世纪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所谓历史就是主体的历史,而这个主体就是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国家就没有历史。因此,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或者说,中国是一个帝国,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历史、无法构成一个真正的历史主体。正是为了与西方现代性叙述相抗衡,京都学派提出了“东洋的近世”、“宋朝资本主义”等论题,在“东洋史”的构架下,重建了中国历史内部的现代动力。关于这个学派与日本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之间的政治性关系,在这里暂略过不谈。我在这里关注的是它的叙述方式:它在建立与西方现代性平行的东洋的近世的叙述时,叙述的出发点同样建立在国家这一核心问题上。如果没有这个国家中心的叙事,就不存在所谓近世的叙事。京都学派也谈到理学或道学,但它是把道学或理学视为新的国民主义意识形态来理解的,在这个解释背后是有关作为早期民族国家或原型民族国家(protonation state)的郡县制国家的历史阐释。总之,当京都学派以“东洋的近世”对抗西方叙述的时候,它的确构造了一个以国家和资本主义关系为中心的叙述。这个叙述跟西方主流的叙述是倒过来的,即西方中心的叙述认为中国是一个帝国、一个大陆或者一个文明,潜在的意思是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京都学派刚好相反。通过诉诸“成熟的郡县制国家”或“国民主义”等范畴,京都学派建立了有关“东洋的近世”的历史假说。
在上述意义上,我与京都学派的对话与区别也包含着对这个19世纪欧洲“世界历史”的批评。简要地说,我和京都学派——尤其是其代表人物——对于宋代特殊性的讨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这样几点上:第一,与宫崎市定将理学视为一种与他描述的宋代社会转变相互匹配的“近代的哲学”或“国民主义”意识形态不同,我认为理学及其天理观恰恰体现了与这个过程的内在紧张和对立,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是通过这种对立而历史地展开的。从方法论上说,京都学派带有强烈的社会史倾向,他们使用的范畴主要是从欧洲19世纪以降逐渐形成的知识体系中产生的,从而缺乏一个观察历史变化的内在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京都学派的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历史叙述是欧洲现代性的衍生物。如果宋代真的像他们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更为中国的中国,那么从儒学的视野来看,这一转化应该如何表述呢?如果“东洋的近世”的实质内容是早期的资本主义和类似于民族—国家的郡县制,那么,宋代儒者据以观察历史演变的那种以“三代礼乐与后世制度”的尖锐对比为特征的历史观难道不是既包含了对历史演变的体认,又体现了对于郡县体制和“早期的资本主义”(如果这个概念的确可用的话)的抗拒吗?
与这一点密切相关,第二,京都学派在近代西方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的知识框架下描述宋代社会及其思想的“近世”特征,而我的描述——例如对“帝国—国家二元论”的分析——则试图打破这种单线进化的目的论叙述。京都学派通过将宋朝描述为一个成熟的郡县制国家而展开“东洋的近世”的论题,其基本的前提是欧洲现代性与民族—国家体制之间的历史关系,从而民族—国家构成了他们的现代性叙述的一个内在的尺度。京都学派有关“东洋的近世”的叙述明显地带有这一倾向。然而,如何描述元朝的社会构造,尤其是如何理解清代的社会体制?我所以加以限定地使用了“帝国”这一概念,目的就是打破那种将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相互重叠的历史叙述——毕竟,与被放置在“帝国”这一范畴内的漫长历史相比,民族—国家只是一个短暂的存在。从明到清的转变显然不能放置在类似于“唐宋转变”的模式之中,将清与民国的关系界定为从帝国到国家的转变也存在问题——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民国在人口、族群构成、地域和一些制度性设置上与清代的明显联系?
因此,当我们说宋代包含了某种“早期现代”的因素时,我们需要在一个不同于京都学派的、摆脱现代性的时间目的论的和超越民族主义知识的框架中来重新表述这个问题。曾有朋友向我问及书的标题问题。“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什么是“现代”?什么是“中国”?什么是“思想”?什么是“兴起”?“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看起来是一个平易的叙述,但从导论起到最后的结论,我的每一个部分都在挑战我们常识中的“现代”、“中国”、“思想”和“兴起”这些概念。我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不是写一部现代中国思想史的起源;什么是“兴起”?你也可以把它解释为《易经》所谓“生生之谓易”意义上的“生生”——一个充满了新的变化和生长的过程。假定宋代是“近世”的开端,蒙元到底是延续还是中断?假如明末是早期启蒙思想的滥觞,那么,清代思想是反动还是再起,我们怎么解释这个时代及其思想与现代中国之关系?我注重的是历史中一些要素的反复呈现,而不是绝对的起源。在历史的持续变化中,不同王朝以各自的方式建构自身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性,这一过程不能用直线式的历史叙述加以表达。正是基于这一历史理解,我没有把所谓“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看成一个类似京都学派的那种以宋代为开端直到现代的一条线。我对“时势”、“理势”等概念的解释就是要提供一个不同于时间目的论的历史认识框架,而这个框架同时也是内在于那个时代的儒学世界观和知识论的。如果我们参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对时间概念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时势范畴在王朝历史及其更替中的意义也许会得到更为充分的理解。
正是从这一视野出发,我批评了关于“中国”的各种论述。例如,我一方面对传统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然后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这一套自明的谱系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不赞成简单地从少数民族史的角度挑战(否定)中国认同的方式。如果儒学、特别是理学的兴起包含了对于历史中断的思考和接续传统的意志,那么,连续性就必须被放置在断裂性的前提下思考,放置在一种历史主动性的视野中思考——从政治的角度说,也是放置在合法性的不断建构过程中来进行理解。所谓以断裂性为前提思考连续性,即不是把延续性理解为一个自然过程,而是将延续性视为历史中的主体的意志和行动的产物。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中国”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存在,也不是一个外在于特定的历史主体的客体。“中国”是和特定时代的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密切相关的。当我把“天理的成立”与郡县制国家、宗法封建问题、土地制度、税法制度、两宋时代的夷夏之辨等问题关联起来的时候,也就是表明这一新型世界观的构成与一个社会重构认同和价值的过程密切相关;当我把儒学的经学形态与清朝国家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多元法律制度问题、满汉关系问题、由朝贡和国际关系为中轴的内外问题等等关联起来的时候,同样也表明这一相对于理学或新学的不同的儒学形态的出现是和一个社会重构认同和价值的过程密切相关的;当我把公理世界观与民族—国家、社会体制、权利问题与文化运动等等关联起来的时候,也正是讨论一种新型的认同及其内在的矛盾和困境。我从不同角度、方面探讨了“中国”这一范畴的不同的含义,力图将这一概念从一种单纯的欧洲民族主义模式中的“民族认同”中解放出来;“中国”是一个较之民族范畴更为丰富、更具弹性、更能包容多样性的范畴,在重建少数民族王朝的合法性、重构王朝内部不同族群间的平等关系,以及塑造不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朝贡或外交关系等方面,这一范畴都曾展现出独特的弹性和适应性。
伴随着对于民族—国家体系的检讨和所谓全球化的研究,早期帝国历史中的一些经验,以及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化的动力等问题,重新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人们据此重新检讨那些被限制在现代化的目的论叙述中的早期帝国的国家结构、经济制度和跨区域交往。当代有关帝国的讨论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对所谓“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问题的思考,奈格瑞(Antonio Negri)和哈特(Michael Hardt)的《帝国》(Empire)一书是这方面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另一个则是从对民族—国家体制的不满或反思出发而重新展开的“帝国研究”,它直接地表现在许多历史学者对各大前现代帝国历史的重新挖掘,以及对迄今为止仍然在历史研究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以民族—国家及其尺度为中心的叙述方式的超越。这两个方面我说的是对当代危机的回应与对历史的研究——当然是有联系的,但又不宜混淆,《帝国与国家》一册与后一方向关系更紧密一些。因此,重提帝国问题的目的不是加强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而是超越这个叙述。在帝国遗产的总结中,除了我已经提到过的跨区域的交往之外,帝国的多民族共存的政治结构和文化认同、帝国内部发生的殖民和权力集中趋势,以及帝国时代与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的复杂关系,都是学者们关心的课题。
但是,这一对于帝国与早期现代性问题的关心如果落入帝国—国家二元论的窠臼,就很容易陷入或反证19世纪的欧洲的历史观,即认为中国没有真实的政治主体。在这里,真正关键的问题不是承认还是否认中国的历史中是否存在“国家”,而在于重新澄清不同的政治体的概念、不同的政治体的类型,而不至让国家概念完全被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历史所笼罩。近代国家有不同的政治文化,比如社会主义国家或资产阶级国家,它们各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如果连讨论近代国家也离不开不同的政治文化或政治传统问题,那么,仅仅在抽象的意义上讨论前20世纪的国家及其主体性就显然是不够的了。京都学派强调到了宋代,中国变成了一个成熟的郡县制国家,而所谓成熟的郡县制国家也就是一种准民族国家。当这个学派把这个郡县制国家与早期现代性关联起来的时候,又在另一方向上确证了帝国—国家二元论。帝国—国家二元论可以表现为截然相反的叙述方式,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宫崎市定那样的论述就是一个例证。在这个框架下,我们不大可能再去探讨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了。
正由于上述多重考虑,我特别注重所谓帝国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的重叠关系,而不是在帝国—国家二元论内部纠缠。19世纪以降,对于所谓前现代历史的研究都被放置在帝国历史的范畴内,我们可以举出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即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的《帝国的政治体制》(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mpires)一书做一点说明。这部影响广泛的著作在一种韦伯主义的框架内,综合了世界各大文明的历史研究,将所谓前现代历史放置在“帝国的政治体制”的概念之下。这一概念是在19世纪欧洲政治经济学的“帝国—国家二元论”中孕育出来的。正是在这一二元论中,“帝国”构成了一切与现代性相反的特征,即或承认帝国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也总是被放置在一种特殊的追溯关系之中,例如:现代国家的专制和集权特性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现代国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暴力性质?所有现代性危机的表征都被追溯到现代世界与帝国之间的历史联系之中。《帝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例证,它说明在20世纪几乎所有“前现代的历史”均以不同的方式被纳入了“帝国”这一范畴之内。
在《帝国与国家》一册中,我主要讨论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儒学对清朝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性论证是如何构成的?帝国体制内的多元认同、多元政治/法律体制是如何构成的?清代统治者利用儒学巩固自身的统治,其中的一个环节是通过儒学将自身界定为一个“中国王朝”;而另一方面,士大夫也同样利用儒学这一合法化的知识对王朝体制内部的族群等级制提出批评,从而对于儒学的某些命题和原则的解释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平等问题产生了关联。第二,19世纪以降的许多重要著作一直将帝国作为国家的对立面,那么,帝国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历史关系究竟如何?例如在讨论清代经学、特别是公羊学的时候,我强调了包括朝贡体系的扩张在内的帝国建设与清朝的国家建设是同一进程的不同方面。实际上,那些被归纳为经典的民族—国家的标记的东西早在17世纪的清朝就已经存在或开始发展,像边界、边界内的行政管辖权等等。
然而,发生在17、18世纪清朝的这些现象是另一种政治文化和历史关系的产物,它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民族国家的雏形,诸如朝贡、和藩以及其他交往形态,均必须置于王朝时代的政治文化的框架中给予解释。但没有这个过程,我们很难理解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乃至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与清朝的地域、人口和某些行政区划之间,存在着如此明显的重叠关系。在书中,我分析了朝贡体制与条约体系的重叠与区分,以及儒学典籍如何被挪用于现代国际关系的具体过程。我的问题是:在殖民主义的浪潮中,这些“帝国知识”如何与一种新型的“儒学普遍主义”结合起来?从儒学研究的角度说,这一研究也是对那种将儒学单纯地放置在哲学的、观念的、伦理的或学术史的框架内的研究方法的修正。儒学在政治历史中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合法化的知识,它的不同形态与王朝体制及其合法性的建构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离开这个视野,我们不能全面地理解儒学的历史意义。
有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不是使用“天下”这一更为“本土的”或“儒学的”概念,而继续使用“帝国”一词?《庄子·天下》对“天下”概念做出的解释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例子,而后代学者对这一概念的运用也极为丰富。“天下”的确是一个富于魅力也蕴含着许多值得探究的历史内涵和理论内涵的概念。事实上,已经有学者为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也为了回应这一对于民族国家的质疑,而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毋宁是“天下”——这个“天下”的概念虽然与帝国概念有所区别,但共同之处都是在帝国—国家二元论之中解释中国历史——通过“天下”这一范畴,人们要做的无非是将中国与国家——即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内核的国家范畴——区分开来。这一论述忽略了中国历史中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是从战国时代的“国”这一制度形式中发展而来,也没有探讨“国”的不同历史类型和含义,在历史观上实际上不是又回到了19世纪欧洲“世界历史”的核心观点——中国没有历史或东方没有历史——之上了吗?我想对我在涉及“天下”概念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帝国”概念做几点限定。
首先,帝国这个词并不是我们的发明,中国古代典籍中也有帝国一词,但这些典籍中的帝国概念与近代从日本和西方输入的帝国范畴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帝国一词在晚清时代被重新发明,并进入现代汉语之中,已经是现代中国历史传统的一个部分,是所谓“翻译的现代性”的表征之一。在19世纪末期的民族主义浪潮中,这一词汇逐渐成为中国思想和知识谱系中的概念,从而这一概念是经过翻译过程而内在于现代中国思想的范畴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概念视为一个外在于中国历史的外来语汇。当然,如果能够找到更合适的概念,我完全乐意更换,但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想出一个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讨论相关问题的中心概念。
其次,“天下”概念是和中国思想有关宇宙自然和礼乐世界的思考密切相关的,有着极其古老的根源。但是,如果不是简单地将这个概念与欧洲民族—国家概念进行对比,而是将这一概念与其他的历史文明进行比较,我们也会在其他的文明和宗教世界观中找到相似的表述;在这个意义上,认为只有这一概念才代表了中国的“独特性”毋宁是从民族—国家的基本知识出发而展开的一种有关中国的特殊主义叙述,说不上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从政治分析的角度说,“天下”概念与作为特定的政治体的中国之间不能划等号,正如顾炎武力图在“亡天下”与“亡国”之间做出的区分所表明的,这一概念包含了特定的理想和价值,从而与“国”这一概念应该给予区分。如果将“天下”直接沿用于描述特定的王朝和政治实体,反而会丧失顾炎武等儒者所赋予这一概念的特定含义。
第三,很多学者曾经使用天朝国家、王朝国家等等概念描述中国的政治历史,这自然是可以的。但是,这两个概念不足以解释中国王朝之间的区别,尤其难以表示我在书中提出的宋、明王朝与元、清王朝之间的区别:它们都是天朝国家或王朝国家,但很明显,蒙古和满洲王朝的幅员、周边关系和内部政治架构与宋、明王朝——也就是宫崎市定称之为成熟的郡县制国家或准民族—国家的王朝——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京都学派强调宋代的郡县制国家是近世的开端,但他们怎么来解释元朝和清朝在中国历史当中的位置问题?他们把宋明理学解释成“国民主义”或近代思想的发端,但他们怎么解释清代的经学和史学的作用与清王朝的政治合法性的关系?在上述两个问题上,京都学派的解释都是跛足的。中国学者也常常把清朝看作是某种历史的中断,比如在有关明末资本主义的讨论或早期现代性的讨论中,满清入主中原同时也就被解释为资本主义或早期现代性的中断,这样一来,清朝就被排除在所谓现代性叙述之外了。
在讨论清代公羊学时,我使用了礼仪中国的概念,并把中国疆域的改变、政治构架的转化和内外关系的新模式都放到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之中。在我看来,不是重新确证中国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帝国,而是充分讨论中国的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及其转化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蒙古王朝、满清王朝与通常我们所谓帝国有着某种相似性,但我并没有把这个帝国叙述放置在帝国—国家的二元论中进行解释,而是着重地阐明了为什么清朝能够被合法地纳入中国王朝谱系之中的内部根据。以清代为例,统治者通过变更王朝名称、祭祀元明两朝的法宝、贡奉两朝皇室后裔、恢复汉文科举、尊奉程朱理学、继承明朝法律等方式将自己确认为中国王朝的合法继承者,在这个意义上,清朝皇帝也即中国皇帝。与此同时,清朝皇帝也以特殊的制度(蒙古八旗、西藏噶厦制度、西南土司制度及多样性的朝贡体制等等)对蒙古、回部、西藏及西南地区实行统治,从而就中亚、西亚地区而言,清朝皇帝也继承了蒙古大汗的法统。不仅如此,清朝皇帝还同时是满族的族长,承担着保持满族认同及统治地位的重任。因此,清朝皇帝是皇帝、大汗和族长三重身份的综合,而清代政治的复杂性——如皇权与满洲贵族和蒙古贵族的矛盾以及汉人在朝廷中的地位的升降等等——也与皇权本身的综合与演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单纯地从满人及其皇室为保持满洲认同的角度论证满洲的自足性以致后来形成满洲国的必然性,即使从皇权本身的多重性的角度看,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只是从满汉关系的角度讨论清代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如何解释清代前期历史中反复出现的清朝皇帝与满蒙贵族的冲突呢?在我看来,这些冲突本身正是王朝合法性建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多重性的皇权本身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化过程的产物。礼仪中国的概念也正是在这多重关系中被反复重构的。
如果说帝国—国家二元论无法揭示出中国的政治文化的特征,那么,中国的传统概念如天下或王朝等也无法说明不同王朝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方面的特点。事实上,在近代历史观的框架内,这些概念恰好构成了近代历史叙事的内在要素。与这种历史解释框架密切相关的,是中西二元论的叙述方式,即强调中国的特点是天下、王朝、朝贡体系,而西方的特点则是国家及其形式平等的主权概念。事实上,帝国与国家的二元论在近代也常常被殖民主义者所运用,他们用所谓“主权国家”的文化贬低传统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模式。例如,1874年日本第一次入侵台湾时,借口就是台湾原住民与琉球人之间的冲突。日本统治者利用清朝官员的说法,以台湾原住民(所谓“生番”)是中国的“化外之民”,亦即不在郡县制度内部或在大清法律管辖内部为由,强辩说对台湾“生番”及其地区的侵犯,不算对大清的侵犯。在这个时代,欧洲国际法已经传入东亚,日本统治者正是根据欧洲国际法,把清代所谓“从俗从宜”的多样性的制度和帝国内部的内外分别放置在主权国家间关系的范畴内,从而为侵略寻找借口。在这一事件中,我们不仅应该注意日本与清朝之间的冲突,而且还应该注意日本据以入侵的原则与清代多元性的社会体制及其原则之间的冲突,尤其是这两种原则在区分内外问题时的不同的尺度及其应用范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