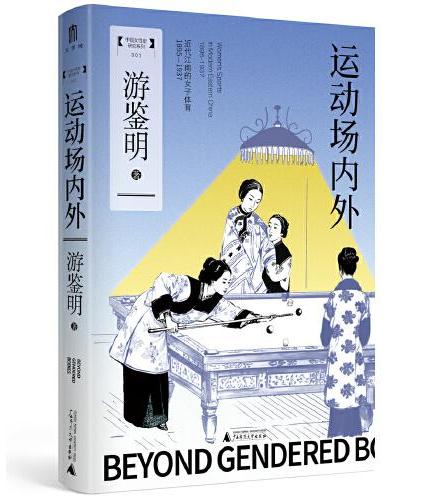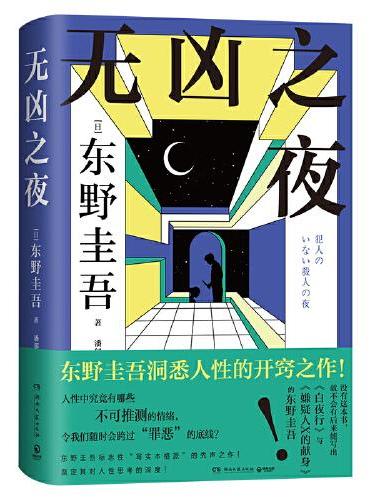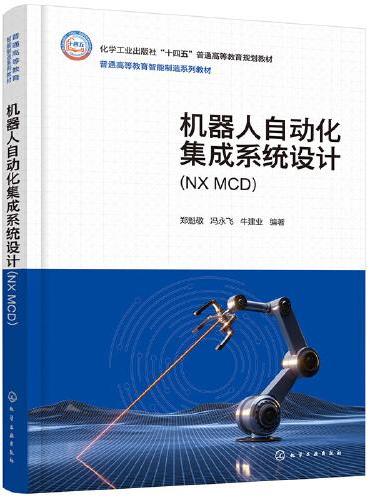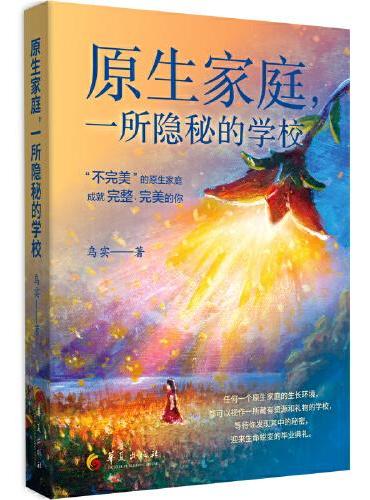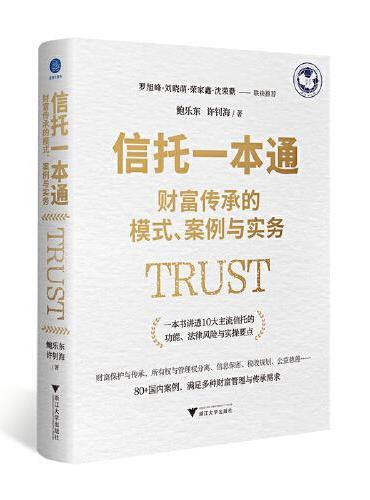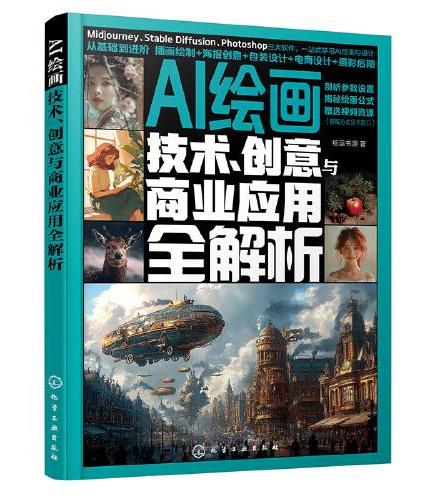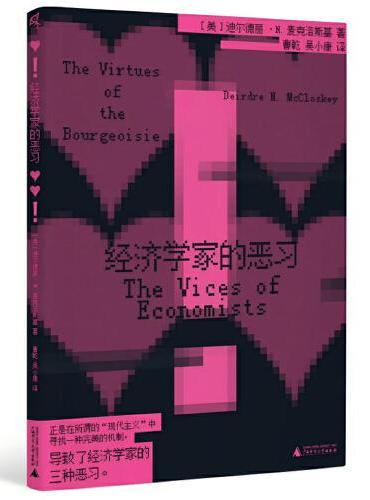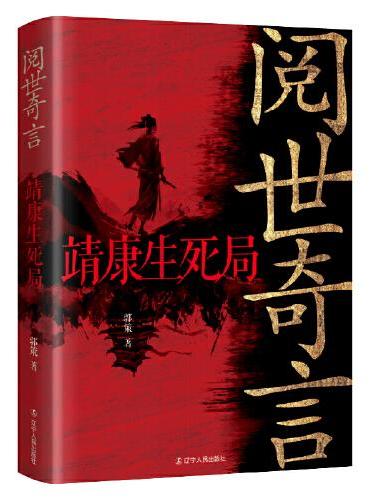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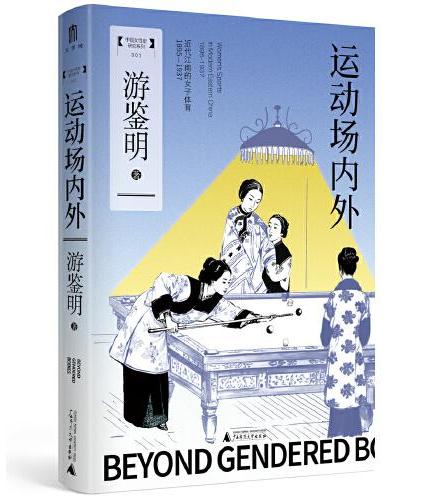
《
大学问·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1937)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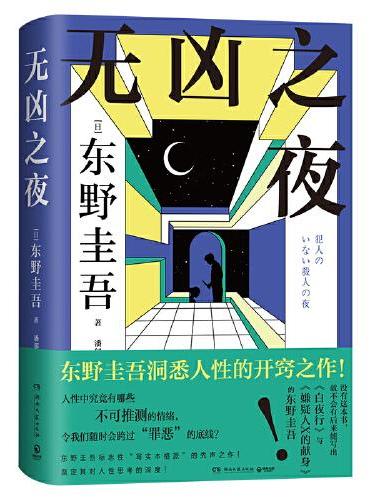
《
无凶之夜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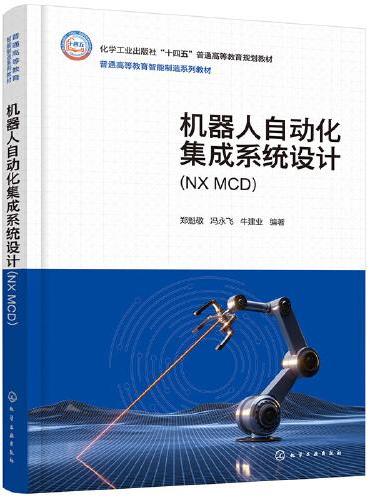
《
机器人自动化集成系统设计(NX MCD)
》
售價:NT$
2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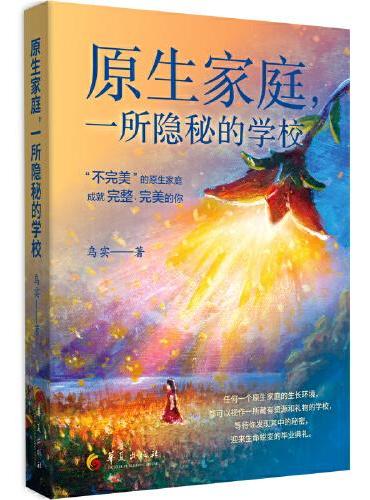
《
原生家庭,一所隐秘的学校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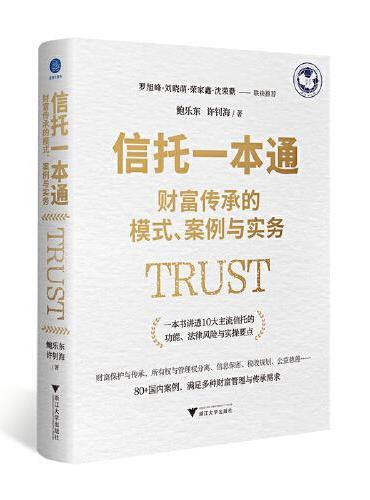
《
信托一本通:财富传承的模式、案例与实务(丰富案例+专业解读,讲透10大信托业务功能、法律风险与实操)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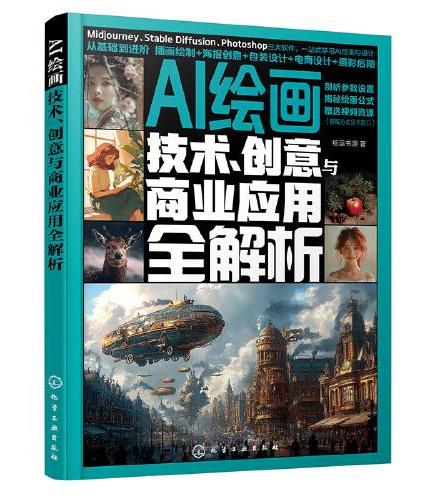
《
AI绘画:技术、创意与商业应用全解析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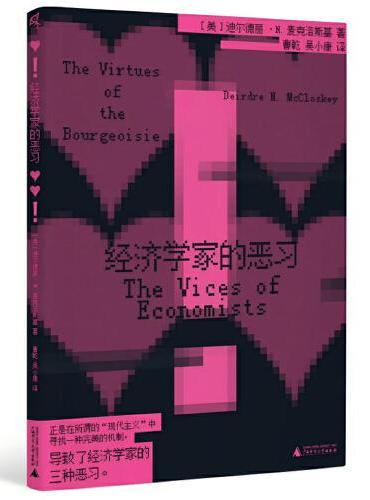
《
新民说·经济学家的恶习
》
售價:NT$
2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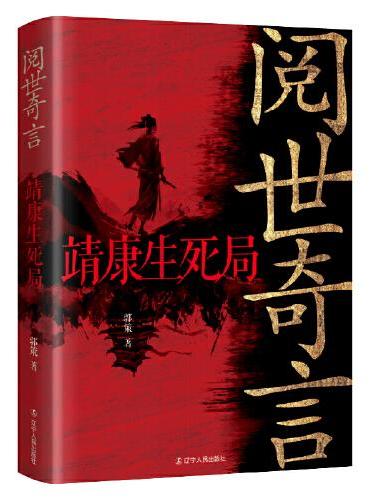
《
阅世奇言:靖康生死局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
“山系人文水满川”,是今人对“徽州”二字形态的形象解析。与此同时,“山系人文”亦包含着自然与人文的两层意蕴,与历史地理学关涉的两个重要分支密切相关。近数十年来,民间历史文献的大批发现,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具体说来,对徽州文书的广泛收集、整理和研究,亦有助于历史地理与徽学这两个学科领域的深入拓展。本书以来自田野的第一手民间文献为中心,从诸多侧面探讨生态、村落、城镇、商业以及相关史志。
|
| 關於作者: |
|
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1998年起任该校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现兼任安徽大学讲席教授。2003-2004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并曾赴日本东京大学、法国远东学院、荷兰莱顿大学等海外汉学机构学术交流。主要从事历史地理、明清以来中国史、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研究,出版有《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社会历史与人文地理:王振忠自选集》等著作十数种,主编及合作主编有《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30册、《长江与莱茵河》等五种,并有《从黄山白岳到东亚海域》《日出而作》等数种学术随笔。
|
| 目錄:
|
001 /
前言
001 / 生态、村落与城镇、商业
003 / “里至源头,外至水口”: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空间的建构
004 / 一、“ 里至源头,外至水口”:对生人、死鬼与神
明空间的界定
009 / 二、“源头”与“水口”:观念、类型
025 / 三、“源头——水口”的禁忌与保护
033 / 四、“源头——水口”的意义及其相关仪式
045 / 五、结语
051 / 生态与生计:清代深山开发与水土流失引发的纷争
053 / 一、19 世纪50 年代的官桥、寨山诉讼案
071 / 二、对诉讼两造背景的分析
082 / 三、余论
085 / 附录:实地田野考察报告
091 / 清代一个徽州村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重订潭滨杂志》
为中心
091 / 一、作为村落变迁史料的《重订潭滨杂志》
094 / 二、潭渡的村落、宗族及会社组织
111 / 三、潭渡村落文化与社会变迁
131 / 明清黄河三角洲环境变迁与苏北新安镇之盛衰递嬗
132 / 一、15 世纪前后苏北河湖环境的变迁
139 / 二、硕项湖与东、西鱼场口
143 / 三、新安镇的出现
147 / 四、新安镇的发展、繁荣
164 / 五、河湖环境变迁与新安镇之衰落
171 / 六、余论
177 / 商帮、产业分布与城市空间:17 世纪以来景德镇徽州会馆
之管理与运作研究
178 / 一、景德镇城市史研究的新史料
185 / 二、景德镇城市空间中徽帮产业的地理分布
213 / 三、徽州会馆的管理与运作
254 / 四、余论
271 / 方志及相关史志研究
273 / 从万历《歙志》看明代商人、商业与徽州社会
274 / 一、万历《歙志》的作者及其编纂
278 / 二、徽商与徽州的商业
290 / 三、明代的徽州社会
331 / 四、余论
338 / 日常与非常:康熙《上溪源志》抄本所见15 至17 世纪
的徽州社会
339 / 一、《上溪源志》所见婺东北村落社会
362 / 二、非常之变与社会应对
373 / 三、余论
376 / 论晚清《绩溪地理图说》的学术价值
376 / 一、《绩溪地理图说》的两种抄本
378 / 二、《绩溪地理图说》的史料价值
401 / 三、余论
409 / 从《歙县修志私议》到民国《歙县志》:有关徽州方志
史家许承尧的新史料之研究
410 / 一、新发现的《歙县修志私议》
413 / 二、《歙县修志私议》与民国《歙县志》
418 / 三、民国《歙县志》的编纂
428 / 20 世纪初以来的村落调查及其学术价值:以社会学家吴景超
的《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为例
428 / 一、吴景超与《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
434 / 二、从《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看传统徽州社会
465 / 三、结语
471 / 后 记
|
| 內容試閱:
|
前言
(一)
民间文献亦称“民间历史文献”,是指有别于正史、文集等传世典籍的文献,它来源于田野乡间,包括契约文书散件、未刊稿本或抄本,以及少量流传范围有限的刊本。国内目前已知明清以来的民间文献,比较著名的主要有徽州文书、福建闽北契约文书、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土地文书和贵州锦屏等地的苗族山林契约(目前多统称为“清水江文书”)等。近年来,各地的民间文献仍时有发现,有的地区还呈层出叠现之势。如浙江石仓文书、闽东文书和福州永泰文书等,亦日渐受到学界愈来愈多的关注。仍以徽州为例,近20 多年来,一些学术机构和个人持续不断地搜藏为数可观的民间文献。据估计,目前各公藏机构和私人收藏的徽州文书已达一百万件(册),这批民间历史文献,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对于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亦极有助益。
徽州是个著名的商贾之乡,“人家十户九为商”,在徽商极盛时期,经商所得利润源源不断地输回本土,促进了“小徽州”(徽州一府六县)区域社会的发展与繁荣。于是,自明代中叶以来,徽州社会的聚落景观和社会风貌都有了重要的改观,特别是村落社会的发展,尤其引人瞩目。“祠堂社屋旧人家,竹树亭台水口遮,世阀门楣重变改,遥遥华胄每相夸”,当时的诸多文献(如乡镇志,特别是其中的村志等),都对徽州村落社会作了不少概括性的描述。而民间文献的大批发现,尤其是众多的村落文书(包括相关的水利文书和可以自成一体的村社文书等),对于村落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具体而微的绝佳史料。村落社会史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前沿领域,而村落作为乡土中国的地理景观、广土众民的生活方式,也必将引起历史地理学界更多的关注。在这方面,丰富的徽州文书,可以极大程度上复原历史时期村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为村落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区域研究的重要视角。
明清以来,商业之发达与频繁的社会流动,使得徽州人滋生出强烈的契约意识,再加上民间敬惜字纸的传统,使得黄山白岳之间保留下极其丰富的民间文献。从南宋以来一直到1949 年之后,徽州遗存有国内目前所知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契约散件和簿册文书可谓汗牛充栋。其中,黄册、鱼鳞图册和保簿等各类文书的数量皆相当可观。这些资料,提供了大量徽州各地无微不至的地名史料,透过细致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南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代)皖南的土地利用状况,并从地名演化的轨迹探寻区域社会中纷繁复杂的诸多事象之嬗变。在徽州文书中,都图地名方面的资料相当不少,鉴于地名史料的巨量蕴藏,有关徽州地名学的研究,无疑是尚待发掘的宝库,具有颇为广阔的学术前景。
自明代起,“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在当时,“黄白游”成为一种空前的时尚b,由此,黄山白岳之间成了许多文人士大夫竞逐游历的胜地,明代地理学家徐弘祖在其名著《徐霞客游记》中,即留有《游白岳山日记》和两篇《游黄山日记》。在当时及以后,类似于此搜奇访胜的著作颇为不少。与此同时,徽州是社会流动极为频繁的地区,不仅有大批人外出科举仕宦、务工经商,而且,侨寓异地的商人还定期回乡省亲、展墓,他们写下的日记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地理学研究价值。譬如,歙县岑山渡程氏迁居扬州经营盐业,康熙年间程庭在返乡之后撰有《春帆纪程》,生动描述了他眼中的山乡乐趣、如画风景,对于徽州的村落景观、妇女生活和人文风气等,都作了形象的揭示。道光年间的《新安纪程》抄本,作者由陆路前往徽州,他详细记录了自苏北盐城至歙县西溪南的沿途所见,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歙县大阜潘氏迁居苏州虽然已历数世,但与祖籍地缘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大阜潘氏支谱》中保留有多篇晚清时期的展墓日记,对于新安江沿岸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都有着精彩的描述。此外,还有一些在籍乡绅的记录,如康熙年间婺源县庆源村生员詹元相的《畏斋日记》,亦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些日记,对于徽州的自然景观、天气年成、灾害信仰和民情风俗等诸多方面都留下了不少珍贵的描摹,对于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利用价值。
明清徽州是个宗族社会,除了遗存至今的大批各姓家谱外,还有《新安大族志》《新安名族志》和《休宁名族志》等涉及一府一邑的综述性总谱。这些谱牒资料独具特色,是深入研究徽州家族人口和移民以及社会文化地理分异的重要史料。另外,清代学者汪士铎曾认为,徽州的土产是“买卖人”,虽然“徽商”之总称闻名遐迩,但在事实上,徽州一府六县的商人仍是各具特色。大致说来,歙县以盐商最为著名,休宁人专擅典当,婺源人精于木业,而绩溪人则多从事徽馆(徽菜馆和徽面馆)业……有关这几个县域商人的各类文书之发现,对于历史社会地理区域人群的研究,尤其是徽商研究的深入,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徽州民间文献不仅在本土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方面极具价值,而且还为长江中下游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在“无徽不成镇”的明清时代,徽州人在各地建立会馆,甚至形成徽州社区,如扬州、淮安、汉口以及苏北新安镇等地,皆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徽人社区。在这方面,不仅有《淮安河下志》《新安镇志》《紫堤小志》那样的村镇志,而且反映当年徽商活动实态的各类征信录仍然保留有不少(如上海《徽宁思恭堂征信录》、杭州《新安惟善堂征信录》《新安太仓怀梓堂征信录》和嘉兴《翳荫堂征信录》等),这些独特的文献,对于研究徽州人在江南各地的迁徙、营生,分析徽州商业地理格局和慈善事业网络之拓展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徽州还保留有大批的民间日用类书,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诸多民事惯例,倘若将之与苏北海门、浙江绍兴、上海及江南其他地区的日用类书加以比较,更不难看出各地人群的地域特征及其相互差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徽州的商书(商人书和商业书)为数可观,此类文献主要包括路程图记、反映经营规范和商业道德的著作,对于各地的物产、交通线路以及风俗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详细的记录。以往,中外学界也有不少人从商业史角度关注类似的商书,但他们所利用的多为散落海外(尤其是日本)的刊本。而在新发现的徽州民间文献中,有多达数十种的商业书和商人书,有的为以往所未见,有的则提供了一种文献的不同版本,这对于廓清传统商书的源流脉络,探讨明清交通地理变迁和商业地理格局,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
从内容上看,本书分成两大部分,一是“生态、村落与城镇、商业”,二是“方志及相关史志研究”。
第一部分的首节“‘里至源头,外至水口’: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空间的建构”,通过爬梳文书、族谱、方志以及其他历史文献,并结合实地田野考察,探讨了“源头”“水口”的意义以及围绕着源头、水口之禁忌、仪式等,指出:“里至源头,外到水口”是传统时代徽州村落空间范围的一种重要表述。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源头——水口是一种依山傍水的村落地理空间,这与皖南低山丘陵之地貌颇相吻合。若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观察,就世俗生活而言,水口是区隔自我(里)与他者(外)的重要界限;而自神圣空间视之,在民间信仰相关的各类仪式中,此处又是阴、阳之分界,源头与水口分别对应的是“内神”与“外神”。与此同时,水口亦是观察村落、宗族变迁的一个窗口。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异军突起,并以群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徽州本土亦逐渐形成为宗族社会。在此背景下,“源头”(山、来龙)、“水口”(水、去脉)亦与宗族血缘、商业兴盛相互关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徽州是江南堪舆学的中心之一,风水观念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村落空间之建构具有重要的影响。至迟自16 世纪的明代中后期开始,青山绿水映衬下的粉墙黛瓦之徽派民居,与“里至源头,外至水口”的村落空间相映成趣,无论是单体建筑还是整体环境都形成了颇为固定的模式,从而塑造了徽州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特征。
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明代以来山区开发与棚民经济、水土流失,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学界对此的关注由来已久,相关成果亦颇为丰硕。而就皖南的山区开发而言,此前的研究多聚焦于外来棚民与水土流失的相关问题上,而徽州本土民众对邻近深山的开发,实际上是山区开发的另外一种类型,迄今为止的探讨仍然相当有限。“生态与生计:清代深山开发与水土流失引发的纷争”一节,以婺源官桥、寨山诉讼文书为中心,颇为细致地分析了清代深山开发与水土流失引发的纷争,指出:由此一偶发的洪灾引起的纠纷,诉讼一方认定此乃深山开发引发的生态灾难,这在部分程度上应当是事实,但揆情度理,却亦颇有强化灾难因果关系以及人为夸大化的倾向。此类情形,我们在以往所见的棚民垦山案例中也时常可见。例如,在棚民与土著的冲突中,棚民往往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土著方之攻讦也更易获得当地政府的共鸣。此一诉讼案例提醒我们,在传统时代的山区开发中,无论开山的主体是谁,其中涉及的生态问题与各色人等之生计利益纠葛,其实是颇值得仔细斟酌的问题。另外,文末所附的调查报告,亦涉及徽州水口建设的相关问题,反映了传统与现实的纠结。
与上述的村落研究主题相关,“清代一个徽州村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重订潭滨杂志》为中心”一节,聚焦于村落相关志书,指出:村镇志及其相关文书是研究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史料。历史时期,徽州民间素有自发性编纂村镇志、保存村落文书档案的传统,而且,此种传统迄至今日仍未中断。不过,尽管这些村镇志史料曾部分地为府、县史志所采辑,但遗存迄今并得以刊行的村镇志数量并不可观,这使得我们对于传统时代村镇等基层社会的实态,所知仍然相当有限。因此,广泛收集、发掘徽州村镇志等乡土史料,无疑将有助于区域人文地理及社会文化史的拓展与深入。该节结合在歙西平原的数度考察所见,聚焦于《重订潭滨杂志》一书,较为详细地探讨了清代潭渡村的村落、宗族、会社、民情风俗和自然灾害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分析村落文化及其社会变迁,以期从一些方面反映“小徽州”与“大徽州”(徽人在一府六县之外活动的广大地区)之依存与互动。
明清以来,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他们在全国各地开廛设市,许多人贸迁既久,留下了一些对侨寓地的深度描摹,这些文献记录,成了观察“大徽州”各地人文与自然地理变迁的珍贵史料。明代万历年间徽商方承训之《复初集》和清乾隆时代的《新安镇志》等,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献。由此,我们可以研究移民、市镇发展和环境变迁的相关问题。从中可见,15 世纪晚期黄河河势加快南趋,因其全流夺淮入海,下游三角洲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城镇受到洪水威胁,河水挟带的大量泥沙掩埋了道路。与此同时,也引发了此一区域湖泊环境的变化。明代中叶以后,苏北硕项湖之水域面积大为扩展,鱼类资源愈益丰富,这吸引了大批徽州人前往该处从事渔业贸易,他们在当地陆续购置田产,直接促成了早期聚落(鱼场口)的发展以及其后新安镇之形成。此后,随着河湖环境的变迁,徽州移民除了从事渔业经营之外,也在当地努力改善自然条件,仿照江南的圩田之制,筑堤从事农业生产。及至清初,随着硕项湖之淤垫成陆,当地粮食作物的种植也发生了变化,最主要的就是番薯之引进。与此同时,硕项湖周遭的城乡景观、民间信仰等也因此呈现出新的面貌。
与方志、文集一样,会馆保留下来的文献亦值得特别关注。在传统时代,徽州人呼朋引类外出务工经商。早在明代,无论是繁华都会还是山陬海隅、孤村僻壤,处处都留下徽商的足迹。在景德镇,整个城区范围内都有大批徽州人活跃其间,徽州会馆的相关产业也遍布于城市的各个街区。十多年前发现的《景德镇新安书院契录》一书,从徽州会馆管理的角度,较为系统地反映了20 世纪中叶徽帮产业在景德镇的空间分布,展示了极为生动的移民、定居以及产业变动不居的画面。此一文献,对于历史地理、城市史和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利用这批契约文书,我对景德镇新安书院(徽州会馆)、关帝庙等重要建筑之形成与发展作了一些新的考证。从中可见,前来景德镇谋生的人群来自各个阶层,会、社组织纷繁复杂,其组合方式亦各具特色。除了覆盖一府六县人群的同乡及慈善组织之外,还有一些县份单独兴建了会馆,并有名目繁多的会、社等组织活跃其间,藉以照顾到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群的利益诉求。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会、社组织的活动,对于徽州会馆之依附性显得愈来愈强。此种内附趋势,应当与景德镇徽、都、杂三帮之间激烈的竞争乃至冲突密切相关。
(三)
全书的第二部分,是对方志及相关史志的研究。
在明清方志中,万历《歙志》是极为重要的一部文献,自从明末清初以来,就一直受到包括思想家顾炎武在内的诸多学者之关注,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以万历《歙志》为切入点,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明代中叶以还徽州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脉动。本书第二部分的首篇,就结合其他明人文集、族谱等资料,较为系统地研究《歙志》所见的明代商人、商业与徽州社会。从中可见,就15—16 世纪的徽州社会而言,徽州与徽商各侨寓地的互动尤其值得关注。从万历《歙志》的记载来看,总体而言,明代中后期的徽州,是个在各个方面皆努力向着江南核心地带靠拢的地区。
除了府县方志之外,徽州也是村落志编纂最多的一个地区。除了此前已收录在“乡镇志集成”中的几部村镇志之外,在民间尚有不少尚待发掘的村落志,其中,康熙《上溪源志》就是一部颇为重要的文献。根据我的研究,《上溪源志》抄本是与现存的两种《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相关的珍稀文献,从内容上看,《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相当于是《上溪源志》的资料长编,而后者则以编年体的方式,辑录了上溪源一带的历史文献。此书虽题作“上溪源志”,但同时也标注为“即《乡局记》”,可见它显然脱胎于《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虽然编者可能最后是希望将之编纂而为该处村落的志书,但从现有的体例来看,它仍然与《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并没有多少差别,也仍旧是杂抄或史料长编的性质,离村落志成书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不过,也正因为它的原始性,提供了有明一代及清朝前期的生动资料,更成为我们了解明清时代婺东北区域基层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
与康熙《上溪源志》相同,《绩溪地理图说》也是近年来新发掘出的民间历史文献。该书系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 年)为编绘绩溪县全图所撰的文字说明,亦作《绩溪全图表说》,是迄今所见有关绩溪地理状况最为详尽的调查资料,其中对县以下村都之描述相当细致,是我们了解绩溪一域自然地理和基层社会人文状况的重要史料。该书虽然未经刊刻,但对于民国时期的一些相关著述仍有一定影响。尤其是书中有关都界之明确记录,对于未来编绘徽州历史地图,特别是厘清传统时代绩溪县以下的都图区划,具有难以取代的学术价值。
除了方志本身之外,在最近一些年的田野调查中,还发现了少量当年修志的珍贵档案。本书中的“从《歙县修志私议》到民国《歙县志》:有关徽州方志史家许承尧的新史料之研究”一节,即聚焦于新见的《歙县修志私议》,以此考察方志史家许承尧的方志编纂理论及其相关实践。
民国《歙县志》之编修,与许承尧长期的资料准备与通盘思考密切相关。与此类似,《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一文之形成,亦与吴景超早年的经历有关。该文属“风土志”的范畴,其写法可以追溯到久远的《禹贡》《职方》。及至民国时期,“风土志”之撰写,逐渐由传统方志学的描述转向具有一定近代社会调查意义的资料,其部分撰写者也由传统士绅转向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这使得“风土志”的内涵更为丰富和细致。吴景超是20 世纪前期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在1919 年撰述的《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迄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笔者首度发掘、表彰该文的学术价值,指出:《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是一篇有关其人桑梓故里、基于实地调查的民族志类型之资料,它从位置、沿革、物产、宗法、生活(含职业、衣食住、娱乐)、教育、风俗(婚嫁、丧葬、岁时、迷信)和胜景八个方面,对徽州的一个传统村落作了多角度的细致描述,其中不乏精彩的刻画和珍贵的史料记录。此一成果独具特色,对于我们理解吴景超的生活经历及其社会学实践,了解晚清民国时期的徽州社会,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此基础上,笔者还通过梳理较长时段的村落调查之学术史,指出:与民国时期其他的一些社会调查一样,该文对于当代的村落文化记忆和古村落之保护,亦颇具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本书主要是以来自田野的第一手民间文献为中心,从诸多方面探讨传统时代的生态、村落、城镇、商业以及相关史志。这些研究,始终关注新发掘的一手史料,藉以探索一些新的学术问题,以期有助于历史地理与徽学两个学术领域的深入拓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