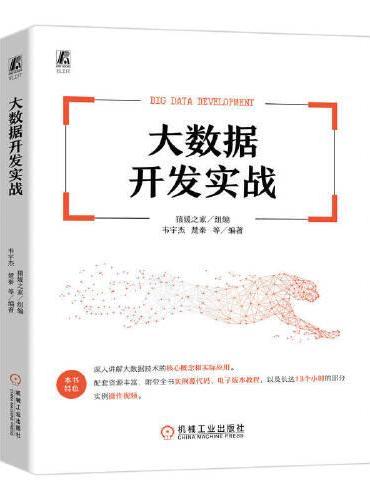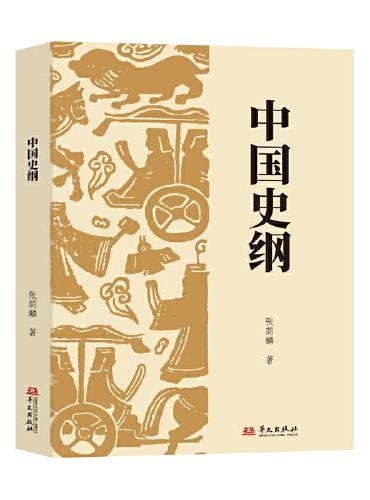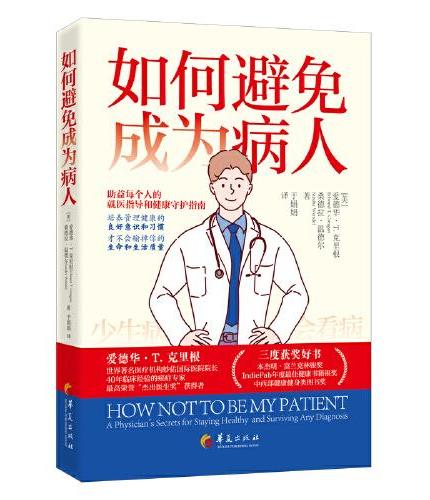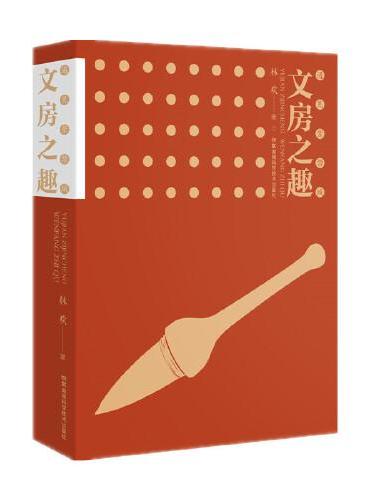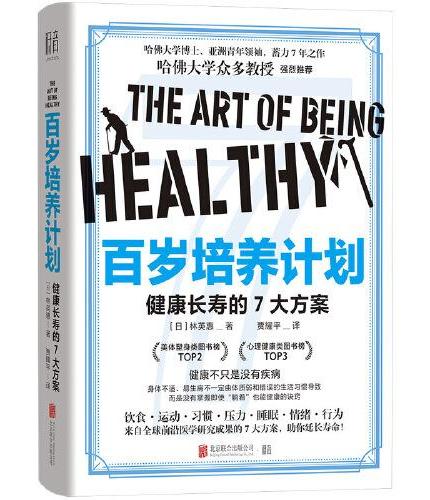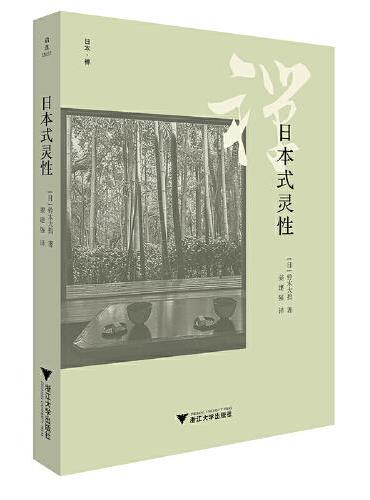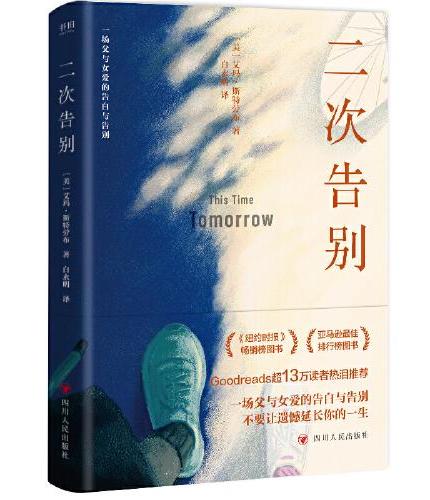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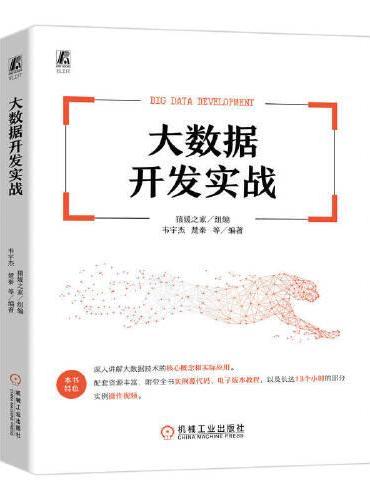
《
大数据开发实战
》
售價:NT$
6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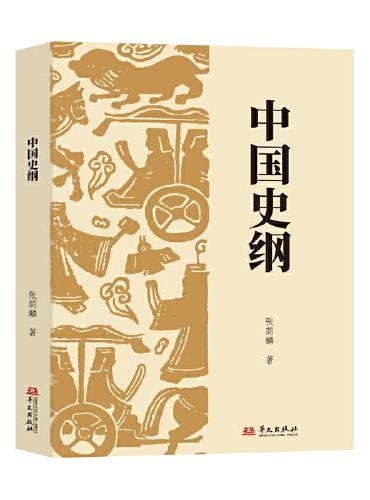
《
中国史纲(张荫麟先生带你学历史!)
》
售價:NT$
2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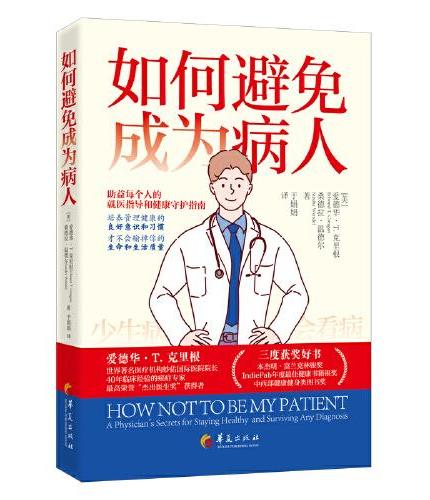
《
如何避免成为病人:世界著名医疗机构院长三度获奖的就医指导和健康守护指南
》
售價:NT$
3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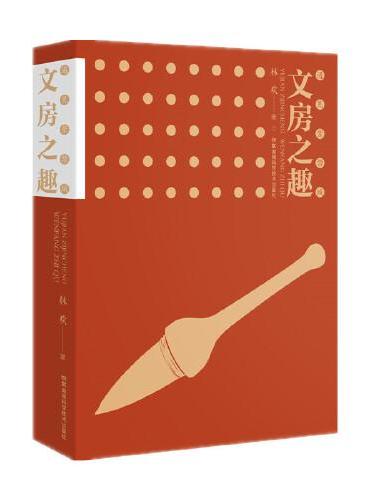
《
遇见紫禁城:文房之趣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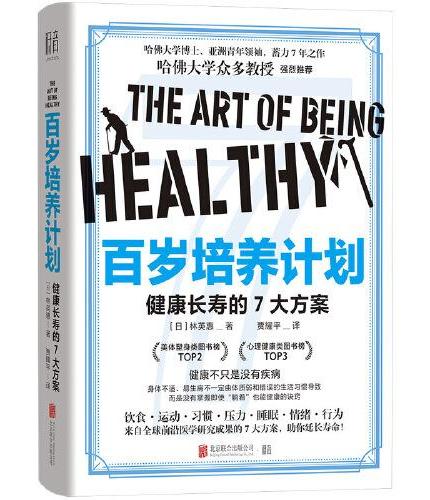
《
百岁培养计划:健康长寿的7大方案
》
售價:NT$
398.0

《
古代人的一天(第3辑):朝代的七天
》
售價:NT$
7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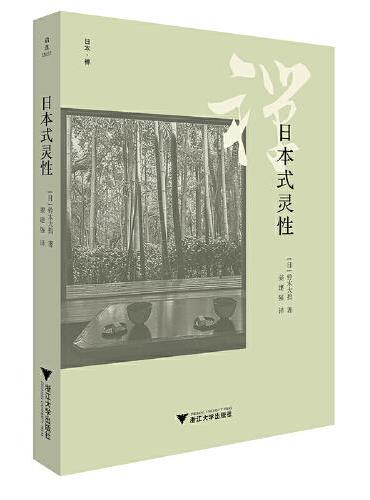
《
日本式灵性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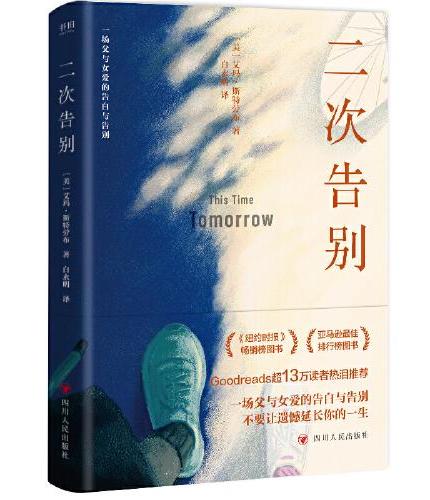
《
二次告别(一场父与女爱的告白与告别。不要让遗憾延长你的一生。)
》
售價:NT$
265.0
|
| 編輯推薦: |
|
本书收录了五则与爱有关的故事,每个故事独立成篇,互不关联,但都发生在一个叫风头岛的小岛上。五个浦斯,五个朱莉,分别代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境遇。作者用诗一样的语言把他们的现今与往昔错综交叠起来,使当下与过去互为因果,让他们的命运变得时而既定,时而充满未知。本书既讲述了原生家庭是生命的底色与塑造,也描绘了爱情是灵魂的相遇与升华。书中人物对亲情与爱情的追求,犹如书中所言:“仰望夜空,以光速穿越茫茫宇宙来到地球的星光,还会抵达其他星球。它们是自由的,无论如何,它们都不会停下脚步。除非死亡。”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一部小说集,收录了5则以“我”为讲述者的中短篇小说。小说中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叫风头岛的地方,讲述了一个叫浦斯的人在岛上经历的爱与恨。小说模糊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边界,融合了现实与梦境,以不确定性叙述,把5个边缘人的少年、青年、中年、暮年串联在一起,深情再现了故事中的主人公追求亲情、爱情的一生。
|
| 關於作者: |
|
周健平,1984年生于广东,早年习诗,后习小说,从事过杂志编辑工作。著有《星光来自从前》等系列小说。
|
| 目錄:
|
目录
001 星光来自从前
099 回不去的风头岛
205 我有一面镜子
277 无声告白
323 葬礼上的波斯猫
|
| 內容試閱:
|
序?言
宇宙是未知的,但似乎又一切皆有定数。仰望夜空,星光皆来自从前。对观测者而言,宇宙的往昔即我们的当下,而我们憧憬的未来,在远方观测者的视野中,也仅是宇宙的旧影。倘若时空可以交织,互为因果,那么人与人之间,是否也会存在这种奇妙联系?试想,世间同名同姓者何其多,倘若他们齐聚一堂,各自的人生轨迹交织重叠,那将会勾勒出一个怎样的世界?如若我们从他们的人生中剥离出这些交织与相似之处,又能拼凑出一幅怎样的人生图景呢?
这样的设想,影响了小说集《星光来自从前》的创作。书中五篇小说虽然各自独立,却以同名同姓的浦斯与朱莉为线索,编织出一个充满追问与情感纠葛的纷繁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个浦斯之间,每个朱莉与朱莉,尽管互无实际联系,但同名同姓的奇妙纽带使得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似乎都在互相映射,仿佛透过时空的棱镜,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彼此的影子。这种交织,使得他们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命运的共同体。从《星光来自从前》开始的童年追忆,到《回不去的风头岛》的海岛之旅和荒诞派对,再到《我有一面镜子》的爱情与迷茫,以及《无声告白》讲述的责任与失落,每一篇小说都在尝试透过浦斯与朱莉的经历与抉择,去探讨爱的真谛、人性的复杂以及命运的无常。最后,在《葬礼上的波斯猫》中,朱莉真假难辨的叙述,又为故事增添了一个全新视角,让一切如真似幻,充满了不确定。
这些故事,如同人生的不同切面,既展现了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挣扎与困惑,也讲述了他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所经历的爱与恨、后悔与期待。在一次又一次的追忆中,他们的现今与往昔错综交叠,现实与虚幻真假难分,自我与他人的边界渐渐模糊,而命运也变得时而既定,时而充满了未知。他们不懈地探寻着存在的意义,试图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回那份缺失的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领悟,并向我们传递:爱和后悔会同时发生,爱与恨也会相互依存,有时候,爱还会以我们不愿意触及的方式存在。
他们既在扣问自己,也在追问我们,人的一生是否真的充满未知,抑或一切都是已知的?选择了爱,是否就意味着同时选择了恨?
星光来自从前
我杀了马林,十年后他将成为我的父亲。如果朱莉没有听信梅娜的邀请搬去风头岛,或许他不会成为我的父亲。一开始,风头岛并不在我们的选择里。我们没有目的地。我们在老皮卡里抽烟,听广播音乐,睡着了也在开车。朱莉跟着广播唱歌,声音轻柔得像一个吻。离开海拉镇后,她从旅行袋里找出钢制的随身酒壶,喝里面的威士忌。我记得她穿着黑色半身裙和白色灯笼袖衬衫,眼神舒服得就像在重读一封爱人的信。
我们开上永风公路,阳光白晃晃,只剩下本能的鳄笛蒲荒原既不阻拦野草疯狂生长,也不在乎沙砾是否渴望重见天日。我们从一阵风闯进另一阵风,死去的黄牛还在用气味宣示它的存在。长空里飞出一只灰雀,栖落时路边的野生蓖麻恍然大悟地颤了颤。乌云飘过大路,阴影如同一群蚂蚁。我想该堵车了。没人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许多汽车在鸣笛。有人驱使发动机喊出对命运的不满,但时间继续向前,而人们只能暂停。有人转动方向盘,慢慢开下大路,驶进鳄笛蒲荒原的野蛮中。我不反对。每个人都有重新选择方向的权利,维持秩序也不是我的职责。
我打开转向灯。我知道,她将建议我们也开进去。我辗过一丛蒺藜,来不及向生命忏悔,鳄笛蒲荒原便以原谅一切的姿态任由我们驰骋。我们在车中颠簸,大喊大叫,相信自己已经无拘无束,可我们依然不知去往哪里。她说,管它呢,我们又不是非到某地不可。她摇下车窗,风的吹拂既有顺从之悲,亦有逆世之美。风不经许可闯进来,秘密无处可藏。喝酒吧,忘记秘密,给自己一个快乐的理由。她把喝空的随身酒壶扔到后排座椅,从旅行袋里又翻出一瓶红酒,重新唱起歌,一副凯旋的模样。一辆越野车从我们旁边飞驰而过,扬起漫天沙尘,我们呼吸困难,连吐出来的咒骂都不再是词语,而是硬邦邦的沙子。我关上车窗,秘密重新滋生。我知道再开下去会发生什么,可她不在乎。我也希望她不在乎。乌云把阳光还给世界,荒原亮得像突然恢复记忆一样。我们从剧烈的撞击感中缓过神来,推开车门,踩到鳄笛蒲荒原的地锦草上,车前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保险杠沾着一摊血迹。四周也不见任何动物的踪迹,一切祥和得如同心智不全,除了风呼呼吹着,声音比受伤的兽鸣还苍凉。远处荒林斜向一侧,就像一群列队做操的少女,由于身高不等,侧弯中各有深浅,风吹过后,直起来的姿势也参差不一。可怜的荒林,竟将排练多年的舞蹈首演给我们观赏,而忘了我们属于过去,给不出与未来有关的赞美。
她喝下一口酒,说道:“快到秋天了。”
“它应该没死。”我摸了摸血迹,热的。可能是阳光的温度。
“这不是我们的错。”
“可能吧。”我不再关心是否有一只动物正在经受死亡的考验,环顾周围,不得不承认自己正处在风景之中。四周草长虫鸣,藿香蓟与青葙争妍斗艳,就连猪毛蒿也不忘迎风招展。唯一的遗憾是一切仍在规则之内,即便阳光也安分守己,全然忘了自己生来便要对抗季节,抵御世界。
“要不我们去风头岛?”她摘了一株藿香蓟。
我知道我们终将到那里。我从后备厢找来一块抹布,擦掉保险杠上的血迹。我们开回永风公路,藿香蓟继续在车里开放,但这不是生命的延续,而是死亡的倒计时。车流已经不再拥堵,所有人紧踩油门,纵情享受秩序带来的自由与畅快。我们忘记过去,重新跟着广播放声歌唱。我们把命运交给老皮卡,把方向交给方向盘,视鳄笛蒲荒原如人生必经之路,义无反顾地往前冲。她歪着头打瞌睡,长发垂下来,遮住了半边脸。我承认,我一直无法从整体上熟知她,像冰山一样,我只看到了她愿意呈现出来的一面,隐藏在水面下的,或许连她自己也不清楚。老皮卡钻出乌云的阴影,阳光吵醒了她。
“到哪了?”她打了个呵欠。
“还没过鳄笛蒲荒原。”我又打开广播。
她点燃一根烟,拿起酒瓶,小口喝酒。久坐已经瓦解了她对终点的向往,掉落的烟灰,以及散发出难闻气味的皮革座椅、让空间变得更逼仄的广播音乐、发动机的絮絮叨叨、车轮与道路的争吵,还有午后暴躁的阳光,都叫她烦闷无比。她揉碎藿香蓟,打开车窗让风吹走。她关上窗,用手指卷着头发,又往窗玻璃上吹气,乱写乱画。她会尖叫的。她尖叫起来像我在尖叫。她的声音唤来一片乌云,阴影笼罩,像法官宣判我们无罪释放。我们在阴影里与无聊和解,为旅行袋里还有一瓶珍藏已久的奥比昂红酒开怀大笑。我们抽烟,吃紫菜包饭团,跟着广播摇头晃脑,大唱别人要我们听的歌。
该下雨了。荒原飞沙走石,乌云掉下来,雨在呐喊。我无法避开一场早已下过的滂沱大雨,哪怕我与每一滴雨都说同样的语言。雨埋住我们。她把手伸出车窗,如同探出墓穴。这种联想使我全身颤抖,此时此刻,我似乎已经失去她,但又无比真实地拥有着。我分不清现实与虚幻,道不明痛苦与幸福为何存在界限。车灯被打开,不是因为黑夜,而是由于雨太大。我们继续沉默。雨刮起起落落,始终无法在挡风玻璃上刮出真相。可什么是真相呢?不确定的回忆,抑或永远来不了的未来?我不回答,她也不愿意揭示。
人皆有秘密。世事艰难,全拜秘密所赐。我一路上都在剥着秘密的壳,就像把爱字拆解,又把所有笔画重新组合在一起,它是我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与秘密,而她也极力否认。我们把它关进广播里,拒绝接收无线电波发来的信号,我们在沉默中用呼吸与心跳交谈,否定该否定的,确认该确认的,连同身份也拿来探讨并被诘问。我愿意忘记我是谁,但她却时刻提醒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罔顾一切。是的,这世界,最奇怪的就是,爱自己所爱的就会犯错。她打破沉默,提醒我不要走错。车灯照见前方指示牌,永风公路会在两千米后分出岔口,一边继续沿主路伸延,一边拐向81号高速公路,通往风头岛。
我不能否认,不管我们要去哪里,都是他们说了算。他们给了我们一条新路,大雨在这里突然销声匿迹,夕阳西下,山如人立。
“鳄笛蒲荒原已成为回忆。”她说。
我不在乎。回忆有何不好?回忆永远不背叛我们。就我所知,回忆决定我们成为何种人,而追求决定我们能走到何处。81号高速公路不允许我们低速前行,如同不允许我们沉浸在回忆中。可加快速度,只会让未来加速成为回忆。这是个悖论。她呼出一口烟,让这个悖论变得更加不真实。我把车速控制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努力平衡回忆与未来的转换。不可否认,若未来足够精彩,回忆必然更加动人。可81号高速公路不是我们的未来,风头岛也不是。
我们不可避免地走进夜色。山隐如兽,月如悬心。我知道月亮曾经照过我们,现在也在见证,毫无疑问,未来它依然会在那里,见它所见。它知晓我的秘密吗?也许。我不担心。它是个好伙伴,只睁着眼,从不说话。我把车停在加油站前。趁油箱补充体力之际,我们各自走进洗手间。想到终有一日我们会像现在这样分别,我两头都在放水。这又是我的一个秘密。我害怕失去她,而她深知我从不曾拥有。我回到车上,她走过来,身上换了一条无袖小黑裙。她坐回自己的位置,把装着衬衫与短裙的单肩包扔向后排座椅,重新拿起酒瓶小口喝酒。
“我听到有人在哭。”她说。
“你喝多了。”
“也许吧,我忘了穿内衣。”
我不断超车。我知道过不了多久,发生在永风公路上的事情,就会在前方出现。车流会稠密,高速公路会重新拥堵。一辆救护车从应急车道呼啸而过,我们迷失在警笛与闪灯交织的混乱中,感觉就像自己躺在急救担架上。轿车侧翻在地,四处都是碎片,开车的男人陷在安全气囊里,血顺着扭曲的手臂流下。副驾驶门敞开着,两名急救护士正抬着一个女人往急救车走。她的白衬衫一片殷红。有交通警察挥舞荧光棒,指挥来往车辆避开隔离带。停在原地等待通行的车辆,探出一个个脑袋,感慨生死无常,庆幸厄运只降临在他人身上。
“还能救吗?”她问。
“但愿吧。”
“我不该喝酒的。”
“跟我们没关系。”
“也许是个错误,去风头岛。”
“反正已经这样,要不再挑个地方?”
“可是去哪里呢?”
“我们可以一直开在路上。”
“还是去吧,去看看梅娜。”
“跟梅娜没关系,对不对?”
“重要吗?”
我捶响广播,用音乐驱赶发动机的轰鸣声。她放低椅背,闭上眼睛,拒绝继续旁观灾难。我看着她,试图说点什么,脑海里又一片空白。指挥交通的警察过来敲响我的车窗,喊道:“该走了,别停下来。”
该走了,该继续上路。我驶进更深的黑夜,闪动的车流就像一条大河。后视镜里,警车还在闪烁,很快道路清障车就会赶来清空一切,道路恢复原样,如同事故不曾发生。
她调回椅背,取出一个眼镜盒,把垂在耳畔的秀发捋向脑后,漫不经心地打开盒子,戴上墨镜,转头看向窗外,声音似乎酝酿了许多年,“应该有十年了吧?当初马林死的时候,我就想告诉你,其实……”
“我知道。”我粗暴地打断她,踩紧油门,加速向夜色深处驰去。一直以来,我都知道,我们并不是天生就懂得人生不需要答案,只有问题接踵而至,一个比一个困难,我们才会相信,有些问题可以视而不见,即便拖到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它也不需要一个结果。但有些问题,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它就死死缠住我们,逼我们解答,当我们爬起床,当我们走进一家酒馆,当我们打开灯望向窗外的雨夜,当我们在泳池边踩死一只蚂蚁,它都会跳出来,指着我们的鼻子,要我们坦诚交代一切,解决该解决的。但并非所有交代都具有意义,有些事情,必须得到当事人的确认,才能成为真正的答案。只有到了那一刻,问题才会尘埃落定,随风飘散,它关联的过去也才会成为真正的过去。也只有那一刻,我们才会发现,所有事物都在以远离我们而去的姿势存在,包括宇宙中的天体,抬头仰望夜空,看到的不是未来,而是死亡与历史。
“你爱他,对不对?”
“已经不重要了。”
“那我呢?”
“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
有一瞬间,我突然希望我们永远到不了风头岛。在路上,在奋力前行的老皮卡里,我们的世界极其简单,每一条路都有自己独属的终点,每一个方向都有它自己的出口,生活不再具有评判性,它在后视镜里,永远跳不到我们面前说三道四,高声谴责。我看见夜空星河璀璨,但每一束星光都来自从前。飘过来的乌云吞下月亮,四周一片阴暗,耸立在夜色中的电子广告牌亮着系统错误的弹窗,瞬时间我恍如走进了虚拟世界,我们就像游戏里的角色,没有现在与未来。我们只有过去,而它完全来自杜撰。
“有没有可能,这一切都是假的?”我问。
“所以我们需要酒啊。”她说。
我突然明白她为何爱喝酒了。我也应该喝一杯。我们置身于陌生的车流中,目视前方,默念人生就是不断接受告别的过程,最后,我们也要和自己告别。只有风头岛还在远方的夜色中闪闪烁烁,就像月光下的海洋。我们历尽艰辛奔赴过去,不是向往自由,而是决心成为岛屿。我们隔海相望,以为回避过去,便能将无法言说的秘密永藏水底。然而,海风常常在我们心里拂起波澜,海水也在不知不觉间腐蚀着我们的防线,随着时间的流逝,秘密终将浮出水面,我们也终究要直面过往,如同直面风暴。我非常清楚我们究竟是谁,我是浦斯,我叫她朱莉,而不是妈妈。我无法面对过去,而她早已原谅。
当时我们还住在海拉镇,生活捉襟见肘,朱莉在酒馆当服务生的工作也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夜晚时光。她夜出晨归,那些我们在晚饭后一起洗澡的欢乐全部化成了遥远记忆中的泡沫,我们熄灯后相拥入眠的幸福也全都消散在浓浓夜色中。我一次又一次在她化完妆准备出门时,紧紧抱住她,央求她换回一份可以见到阳光的工作,就像当初在五金店当售货员一样只需要上白班的。我编了一个非常正义的理由,我怕黑,我害怕独自一人一边留意钥匙孔是否发出转动声,一边看着天花板等她。朱莉对我的央求无动于衷,也许因为可以免费喝酒,也许是她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曾经在蒙加德家里留宿过多次。我不怪她,人总会对付出过代价的事物保持一种食之无味又弃之可惜的态度,就像她始终没有放弃我一样。我只恨所有海拉镇人,他们称赞朱莉美艳绝伦,背后又骂她是一辆公交车,他们口是心非,道貌岸然,我无时无刻不在诅咒他们,甚至将书包装满石子,每当夜里辗转难眠,就偷偷溜上大街,一块又一块,投向他们虚伪的窗户。
后来,梅娜打来电话。她说,来吧,朱莉,带小浦斯一起过来,风头岛多得是机会。朱莉陷进留与去的挣扎中,到了开工时间,仍然没有出门的迹象。她站在窗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呛鼻的烟味与屋内沉滞的空气混为一体,使整间屋子变成了烟雾缭绕的石灰池。
“我们洗澡睡觉吧。”她突然扔掉香烟,回过头说。
从客厅到盥洗室,是我走过最幸福的一段路。我不敢像往常一样将泡沫拂向朱莉,太危险了,它们就像我的心跳,我不能暴露,不能被她发现,在她烦恼时,我正兴高采烈。可是,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灯光在泡沫上闪闪发亮,我们也在水声中熠熠生辉。朱莉又点了一根烟,似乎心中暴走的猛兽需要用烟气熏走。她一只手抱在胸前,沉默的样子俨然一座冰山,只要我敢靠近,就会撞得船翻人亡。这不是我想要的幸福,也不是我记忆中的欢乐时光。我将泡沫堆在下巴上,决心帮她把烦恼的猛兽赶跑。
“我是一个无所不能的魔法师。”我喊道。
朱莉将香烟移到嘴边,默不作声地抽了一口。我喜欢她抽烟的样子,就像在约定的地点等待梦中情人。
“真好吃的棉花糖啊。”我掬起一团泡沫塞进嘴巴,呛得浑身打战。
“你傻了吧?”朱莉终于开口说话。她把我拉到怀里,用花洒冲去我脸上的泡沫。
肌肤相触的温暖又一次融掉了我的童年。我抱住朱莉,把脸埋进她温润柔软的胸口。我想起蒙加德,想到许许多多海拉镇人,他们喜欢背地里嚼舌根,又常常装出一副关心的模样,他们讨厌朱莉,不是因为她穷,也不是因为她是个单亲母亲,而仅仅是因为她过于年轻美丽。
“别担心,长大以后我会保护你的。”
“那可还要等十多年哟。”
“我去把日历撕掉就快了。还有,客厅的挂钟也要调快。”
朱莉发出酒精一样的笑声,欢乐的颤动透过胸口,如同海浪拍打着我,使我以为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海边度假。我还记得她戴着宽檐帽在沙滩上看我玩水的模样,严肃又饶有兴趣,午后的阳光将她的身影投射在层层涌过来的海浪上,粼粼而动。我跑过去,挡在她的影子前喊道:“走开,快走开,我不许你们过来,她是我的妈妈,只能是我的妈妈。”
还有什么能比朱莉的怀抱更温暖呢?我惬意而贪婪地吸嗅着她的气息,就像一棵树苗在汲取成长的养分。是的,她是我一个人的母亲,她只能是我一个人的母亲,这个让我兴奋又使我忧愁的信念,以超出我能承受的速度生长着,终有一天它会破心而出,遮天蔽日。
她占据着我的眼睛,说道:“帮我揉揉吧。”
我的存在又有了被需要的价值。我卖力地揉捏她的肩膀,唯恐她的心重新被烦恼侵占。
“我们搬去风头岛怎样?梅娜姨母有一栋大房子,还有个花园,她一定会非常喜欢你的。”
“那你还去酒馆上班吗?”
“梅娜有个面包店,也许我可以当个面包师。”
“我喜欢吃面包。”
朱莉拍了拍我的脑袋,笑声如烟。我开始遐想搬去风头岛的生活,明亮的房子,五彩缤纷的花园,朱莉再也不用去上夜班,每当夜幕降临,她将重新属于我一个人。没有蒙加德,没有海拉镇人,她的世界会干净得像一面镜子,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在上面投下身影。我沉浸在独自一人拥有朱莉的幸福中,渐渐发酵的醉意使我眼皮沉重,我似乎睡着了,似乎又无比清醒,我恍惚记得朱莉抱着我回到卧室,在海拉镇人趁着夜色出去寻欢作乐时,我们一如往常地相拥而眠。我依稀记得朱莉在我的额间亲吻了一下,温暖而湿润,就像她胸口上的汗珠。
直到风头岛的热风迎面吹来,我才被陌生环境里的危险气息彻底惊醒。沿街而建的楼房和鳞次栉比的窗户,无不表明它是一个换了名字的海拉镇。唯一不同的是,我的敌人不再站在阳光下,他们成了潜伏的鬣狗。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们会出现在何时何地。
朱莉拉着一个巨大无比的铜绿色复古皮箱,里面塞着我们从海拉镇带来的所有家当,换洗的衣裳,高跟鞋,还有她最喜欢的化妆品。她身着一套曾经陪蒙加德出去过夜的宝石红及膝裙,还戴着去海边度假时才派得上用场的黄色宽檐帽,口红抹得香甜滑腻,让我总想猴上去吃一口。她慢悠悠地走着,手里拿着梅娜的地址条和一副墨镜,随风摇曳的长发撩得阳光也燥热起来。我恨死了身上的背带牛仔短裤,它把我瘦小的双腿暴露在阳光下,就像吃奶小孩的两抹鼻涕。幸好朱莉同意我把相片抱在胸前,印在衣服上的唐老鸭才没有呱呱乱叫。相片是我们在海边度假时请人拍的,也是我们迄今为止唯一一张合照。我问朱莉为什么我们不经常拍照,她总是抚摸着我的脑袋说照片是奢侈品,她的收入还不足以供我们用照片去记录生活,“不过我们还有记忆,它可是最厉害的相机”,我喜欢她说这句话时的语气,带着一丝俏皮和满足,仿佛一个睡前吻。
她在一个挤满孩子的门廊前停下,声音悦耳:“打扰了,请问梅娜住哪里呢?”
我不明白她拿着地址条为什么还要找人问路,而且还是一群小男孩。他们什么也不懂,连流出来的鼻涕不能吸回去如此简单的道理都一窍不通,又如何能简单明了地指路呢。我用海拉镇男人警告我的目光敌视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不要以为我们是异乡人就可以出言不逊,还有,朱莉不会喜欢你们的。
“就在街对面,往左走,带花园和泳池的那栋白房子就是她家。”一个虬髯男人从孩子堆中站起来,手里拿着一只刚刚系好线的风筝。他空出一只手抓了一下头发,又抻平身上的棒球服,两只大脚由于太慌乱穿反了拖鞋,毛茸茸的拇趾想缩回鞋里却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位置。
“谢谢啊。天可真热,要是有一杯加冰的朗姆酒,那就完美了。”
“去吧,罗奕,记得多倒一杯果汁。”
一个戴着棒球帽的男孩飞奔进屋,很快就端着一个托盘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朱莉接过平口玻璃杯,浅抿一口,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接着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她把玻璃杯放回托盘,伸手摸了摸他的帽子,然后甜甜地道了声谢谢。
罗奕,万恶的罗奕,瘦如鼻毛一样的罗奕。我看着他的脸,看着他鼻梁上的雀斑,一把抓住朱莉的手,扬起下巴,用鼻孔警告他,朱莉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可是,他直勾勾地盯着朱莉,完全无视我的存在,仿佛我只是他的影子,是他忘记吸回去的一口气。
“罗奕,别忘了还有一个人啊。”一个鼻子塌塌的女孩喊道。
“笨蛋罗妮,我用得着你提醒吗?”罗奕把托盘送到我面前,目光坚定,仿佛他才是这间屋子的主人。
“我不要。”我挡住托盘,用力推了回去。若不是朱莉抚摸他的脑袋,我不会拒绝他的好意。现在他已经成为我在风头岛的第一个敌人,我会像恨蒙加德一样怨恨他,并诅咒他永远长不大。
“我的小浦斯有点小脾气,抱歉。”朱莉一边说,一边用拿着墨镜的手搂住我。
“小孩子嘛,都喜欢这样。大家都叫我罗文。”虬髯男人说道。
“我的爸爸叫大胡子罗文。”罗妮摇了摇自己的裙摆。
“你可以叫我朱莉。我们今天刚到风头岛,往后还请多多关照。”朱莉道完谢,拉着我,款款走向梅娜的房子。罗奕和罗妮带上那群小孩,一声不吭地跟在我们后面,罗文的风筝已经失去魔力。这不能怨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小孩更容易被吸引和左右的呢?更何况他们的好奇心本就如同流水,随时都在变化。可是,他们真的只是因为我们是陌生人而好奇吗?
门铃响到第五声时,门开了。一个胡须修剪得如同剪彩仪式的男人滑出来,眼睛如同探雷犬,充满警戒地打量了一遍朱莉。他一定想在记忆中找到与她有关的第一印象,但记忆太深,岔路纷繁复杂,忆及往昔带来的迷惘,促使他紧皱眉头,满脸蚂蟥。他把目光投向我,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梅娜,看谁来了。”这个在家里也打领带的高瘦男人向屋内的阴暗喊道。
“也许我该叫你马林?”朱莉问。
“除了这个名字,我可想不出我还能叫什么。对了,你们的梅娜姨母喜欢叫我老马。”马林弯下腰,试图摸我的脑袋,“那么,这个帅气的小伙子一定是我们的小浦斯咯?”
我快速闪到一边,除了朱莉,我讨厌任何人在我的脑袋上摸来摸去。凭什么呢?我既不渴求怜悯,也不需要主人,我把头发整理得比仪仗队还工整,可不是为了继续当小孩。我要越过无知的童年直接进入成年,做一个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大男人。我要保护朱莉,赶跑围在她四周的鬣狗与狐狸。
“是朱莉吗?我们的小浦斯是不是也来了?天啊,我的蔓越莓饼干还没烤好呢,老马,亲爱的老马,我昨天买的彩虹棒棒糖是不是被你偷吃了?”
“她太想你们了。”马林苦笑道。
梅娜出现在门口,肥胖的身体撑得蓝白相间的碎花裙奄奄一息。可怜的裙子,至死都不会明白为什么朱莉不是它的主人,为什么同样是裙子,它却只能与庸俗相伴。梅娜油腻腻的笑容和穿透力极强的体味加重了它生而为裙的悲哀,也许不用别人,它便已自称为抹布,一条穿在身上的抹布。
“你就是我们的小浦斯?”她抓住我的肩膀,在我头上像剃头一样摸了一阵。
“梅娜,你打算让我们在门前晒一整天吗?”朱莉说。
梅娜笑得像一张随风摇曳的蜘蛛网。她抓着我们的手,走进屋内,并回头挥手驱赶门外的小孩。马林从朱莉手中接过皮箱,放进廊道尽头的房间。他走过来,在远离朱莉的沙发一端坐下,视线越过摆满水果的茶几,落在我身上。梅娜依然搂着我,仿佛我是她丢失多年的孩子。她絮絮叨叨,鼻息喷在我的脖子上,热乎乎的,像一条舔来舔去的狗舌头。我瞪着马林,他毫不在意朱莉的美丽,对她修饰过的海拉镇生活也毫无兴趣,就连她说到他的名字时,也无动于衷,他只是微笑着,仿佛只要看着我就已经心满意足。
“老马,朱莉问你话呢。”梅娜喊道。
“怎么了?”马林说。
“你去过海拉镇?”朱莉问。
“他去过的地方可多了,在他还是一名红酒推销商时,他就跑遍了大江南北,不过海拉镇我敢肯定他没去过,除非他忘了写日记。”
“日记?”
“对啊,就是日记,他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现在他还在坚持写呢。如果你能读到它们,哪怕短短的几句话,一定会为他不当作家而扼腕叹息的。真的,老马,你应该听我的,把你的日记投给出版社,书名就叫《马林的生活》,我相信它会成为一本人人都爱不释手的杰作。你放心,我不会和别人争风吃醋的,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不眷恋唯一的读者这个身份。”
“我只要有你就够了。”
“看来我是没有机会了。”
“所以你要赶紧找到一个愿意为你写日记的人啊。”
“谁叫我还带着浦斯呢。”
我挣脱梅娜的搂抱,跑到朱莉身边,紧紧抱住她的左腿,问道:“朱莉,你不要我了吗?”我仰头看着她,希望她用一个温暖而甜蜜的吻融化我心中的恐惧。朱莉双眉紧蹙,脸上浮出一丝锋利的笑容,我开始怀疑,搬来风头岛也许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在海拉镇的时候,每当她不愿意带我去参加全都是男人的派对而我又不可理喻地非要跟着去的时候,她就会露出这样的笑容,刀子一样,坚硬,冰冷,透着要砍断一切烦恼和阻碍的决绝和锋利。
“我的小浦斯,你是不是想家了?”马林问。
“老马,你胡说什么呢,这里就是他的家啊。”梅娜伸手过来想抱我,可是我避开了。她转头盯着朱莉问道:“浦斯为什么不叫你妈妈?”
“我定的。”
“为什么?”
“我还没准备好。”
“因为孩子的爸爸?”
“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哎,我们女人总是离不开男人,但他们却老是伤害我们。”梅娜若有所思地说道:“老马,你可千万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马林没有搭话,他只是看着我,脸上的微笑就像一根燃亮的火柴。
“那你要准备到什么时候?”
“也许等到我不后悔的时候吧。”
“换成我一定不会后悔。我和马林努力了这么多年,就是想要个孩子。”梅娜突然哭了起来。
马林像打开折叠刀一样站起来:“我的傻瓜,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他抱住梅娜,声音里闪耀着金属的光芒,“朱莉和浦斯在呢,他们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人了。”
朱莉抿紧双唇,脸色尴尬。她轻轻拍着梅娜的脊背,一边搂住我,在更大的尴尬冲涌而来时,我是她最好的防御。
“大人是不允许哭的。”我说。
梅娜破涕为笑。她离开马林的怀抱,双手抱着我的脸,黏糊糊的双唇在我额间重重地啜了一口。
“让我们来看一看浦斯的小王国吧。”她说。
梅娜一定不知道我的王国一直在朱莉身上,她自作主张把朱莉的卧室指定在一楼,又理所当然地把我安排在二楼,正对面就是他们贴着紫粉色花纹墙纸的卧室。我对拥有自己的房间这件事情毫无兴趣,我只希望能够和朱莉时时刻刻待在一起,有时候,我甚至希望成为她的衣裳,不仅仅是希望,我还嫉妒它们,可以穿在她身上,为她驱寒保暖,随她去往任何一个她想去的地方。现在,我只能困在摆满玩具的儿童房里,坐在一张樱桃木床上,对着另一张庸俗至极的婴儿床思念朱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