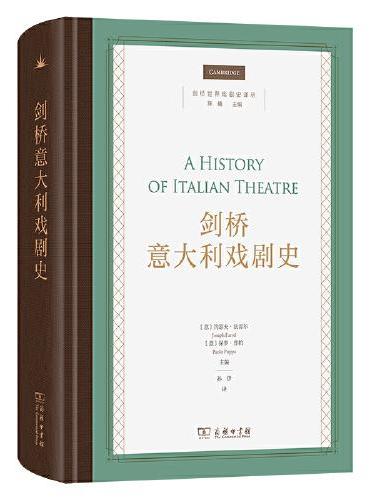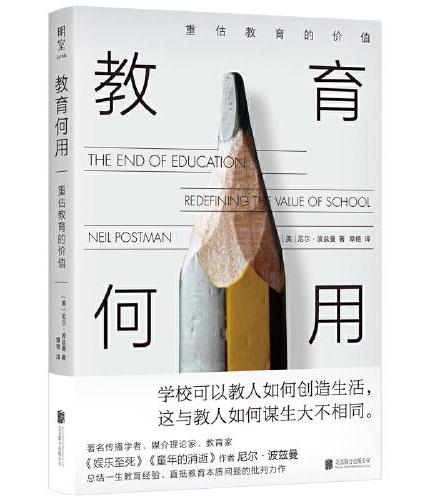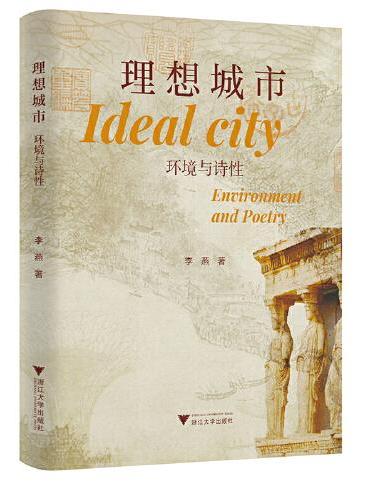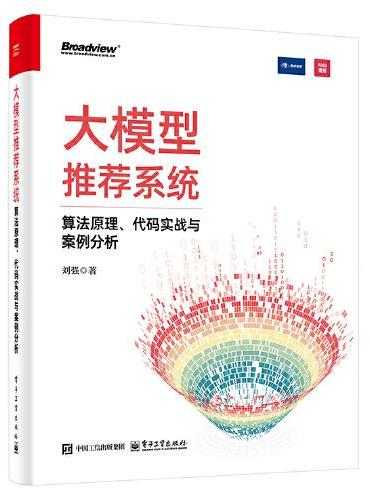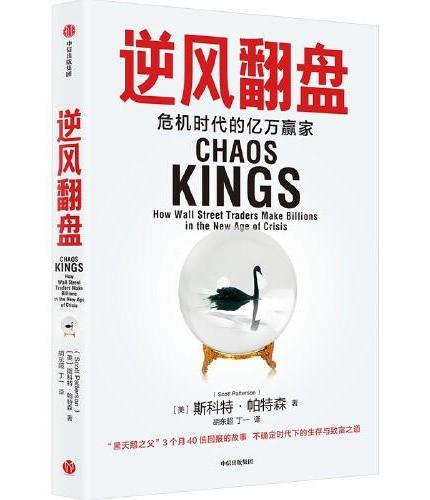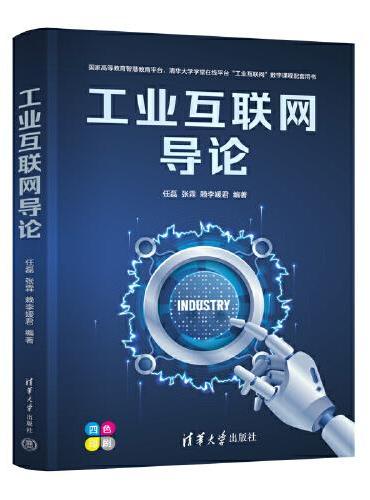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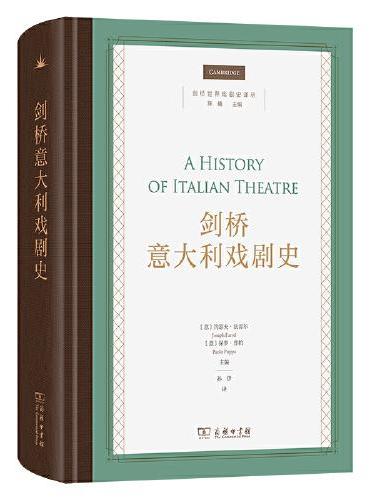
《
剑桥意大利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NT$
7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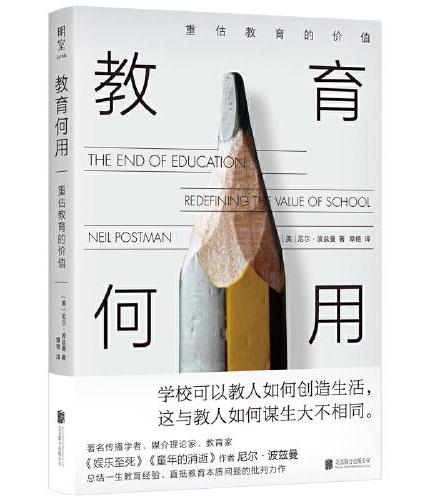
《
教育何用:重估教育的价值
》
售價:NT$
2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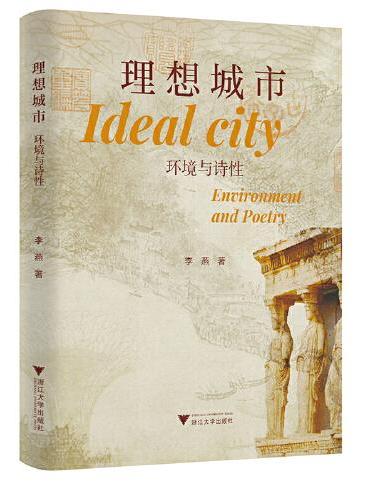
《
理想城市:环境与诗性
》
售價:NT$
3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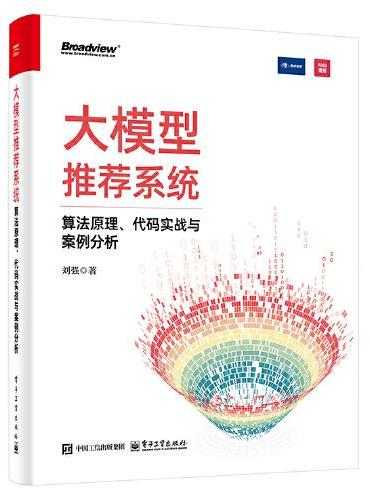
《
大模型推荐系统:算法原理、代码实战与案例分析
》
售價:NT$
4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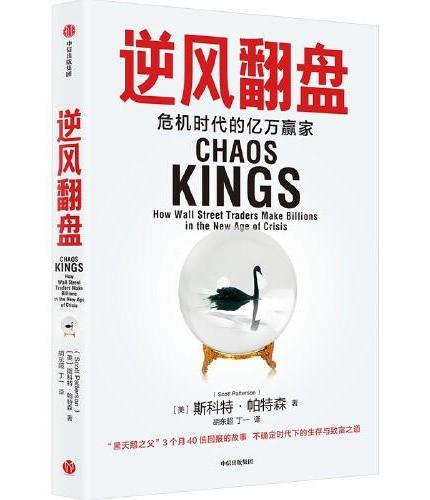
《
逆风翻盘 危机时代的亿万赢家 在充满危机与风险的世界里,学会与之共舞并找到致富与生存之道
》
售價:NT$
6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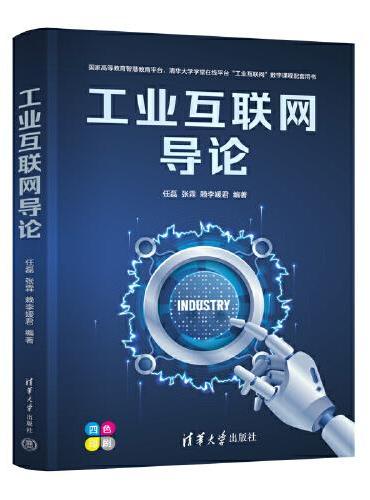
《
工业互联网导论
》
售價:NT$
445.0

《
木偶的恨意(法国悬念大师米歇尔普西悬疑新作)
》
售價:NT$
295.0

《
孤独传:一种现代情感的历史
》
售價:NT$
390.0
|
| 編輯推薦: |
活动说明:
12月10日至12月31日,所有购买《替补:哈里王子自传》的读者,均有机会参与抽奖活动,奖品为译者陈鲁豫、李尧老师的亲签本,限10个名额哦~
一部不可多得的王室文献。
一场窥见英国王室隐秘的皇家大戏。
一个王室“备胎“的“吐槽大会”。
一本充满情感纠葛与自我救赎的成长之书。
一份见证哈里王子从王室束缚走向自我解放的心路历程档案。
一次对传统王室规范与现代个人追求激烈碰撞的深度呈现。
|
| 內容簡介: |
|
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王室回忆录,由查尔斯三世和戴安娜王妃的次子哈里王子亲述。哈里王子以罕见的勇气和坦诚,讲述了他身为王室替补继承人的人生轨迹: 幼年丧母带来一生无法消解的痛,少年时在王室光环下的孤独与迷茫,成长过程中被媒体审视的压抑,面对家庭内部微妙复杂关系的纠结,对王室传统规范的困惑与抗争,爱情降临时在王室责任与个人幸福间的艰难选择,以及为爱脱离王室远走他乡后对往昔的重新审视……呈现了哈里王子身为王室继承人的“备胎”,突破身份的束缚、追寻自我价值的心灵成长历程。
|
| 關於作者: |
哈里王子,英国苏塞克斯公爵,一位丈夫、父亲、人道主义者、退伍军人、精神健康倡导者及环保主义者。他和家人及三只狗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塔芭芭拉。
译者简介
李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深翻译家,2024年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悉尼大学荣誉文学博士、西悉尼大学荣誉文学博士。1968年起从事文学创作,迄今为止翻译英美澳大利亚文学、历史、文化著作六十余部。
陈鲁豫,媒体人、中英双语主持人。从事主持专业三十年,累计采访政界、商界、文化界等各界精英一万多人次。她主持的人物访谈节目《鲁豫有约》,迄今已经完成了四千余集节目制作,堪称中国焦点人物影像志。
|
| 目錄:
|
楔子
第一部 走出笼罩我的暗夜
第二部 浴血,但我不屈服
第三部 我的灵魂导师
尾声
|
| 內容試閱:
|
我们约好在葬礼结束几个小时后见面。在弗罗格莫尔花园,古老的哥特式废墟旁。我先到了,环顾四周,连个人影儿也没有看到。
我看了看手机,没有短信,也没有语音留言。
他们一定是迟到了,我靠在石墙上想。
我收起手机,告诉自己保持冷静。
典型的四月天,冬已去,春未至。树木光秃秃的,但风儿柔和。灰蒙蒙的天空下,郁金香已经绽开。天光暗淡,花园里,靛蓝色的湖水亮光闪闪。
多美呀,我想,但又多么悲凉。
曾经,我以为这里将是永远的家。到头来,却只是又一次短暂的停留。
我和妻子出于对自身精神和人身安全的担忧而逃离这个地方时,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那是2020年1月。现在,十五个月后,我又来到这里。几个小时前,我一觉醒来发现三十二个未接电话,随后和奶奶进行了简短的、让人心跳加速的通话。“哈里,爷爷走了……”
风愈刮愈猛,天愈来愈冷。我端着肩膀,揉着胳膊,为白衬衫的单薄懊恼,后悔不该换掉丧服,后悔没带件外套。我背对着风,看见身后隐隐约约的哥特式废墟。事实上,它并不比千禧之轮更哥特式。那是聪明的建筑师的杰作,是舞台的艺术,和周围许多景物别无二致。
我从石墙旁挪到一个小木凳上。坐在那儿再次查看手机,在花园小径上来回张望。
他们在哪儿呢?
又一阵风扑面而来。有趣的是,那冷风竟让我想起爷爷。也许因为他举手投足的冷峻,也许因为他的“冷幽默”。我不由得想起几年前的一个周末。那天,一位朋友和爷爷聊天,问他如何看待我刚留的胡子。我留胡子这件事已经引起家人的担忧和媒体的争议。“女王会强迫哈里王子剃掉胡子吗?”爷爷看看我的同伴,又看看我的下巴,露出调皮的微笑:“那压根儿就不算胡子!”
大家都笑了。留胡子还是不留胡子,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爷爷却要求留更多的胡子:“让我们长出血腥维京人那样的华丽须毛吧!”
我想起爷爷的固执,想起他对赶马车、烧烤、射击、美食和啤酒的诸多爱好,他拥抱生活的方式。他和我母亲有许多共同点。也许这就是他也成为她的“粉丝”的原因。早在她成为戴安娜王妃之前,当她还是戴安娜·斯宾塞、幼儿园教师、查尔斯王子秘密女友的时候,爷爷就是她最坚定的支持者。有人说他实际上促成了我父母的婚姻。如果真是这样,爷爷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最主要的原因。要不是他,我不会在这里。
我哥哥也不会。
但是,也许我们的妈妈会还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她没有嫁给爸爸……
我想起最近的一次聊天,只有我和爷爷,就在他刚刚九十七岁的时候。他在想自己人生的结局,他说,他再也无法激情满怀,他最想念的还是工作。他说,没有工作,一切就都崩溃了。他看起来并不悲伤,只是做好了准备。“你得知道什么时候该走,哈里。”
我向远处瞥了一眼,望着弗罗格莫尔旁边由墓穴和墓碑构成的微型天际线。那里是皇家墓地,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在内的许多人最后的安息之地。这里有臭名昭著的沃利斯·辛普森,还有她同样臭名昭著的丈夫——前国王爱德华八世,也就是我的曾伯祖父。在爱德华为沃利斯放弃王位,离开英国之后,两人都曾为最终的归属之地焦虑,都希望归天之后能埋葬在这里。女王,也就是我的祖母,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但她把他们安葬在一棵弯曲的梧桐树下,与其他人保持了一定距离。也许是最后一次指责,也许是最后一次“流放”。我想知道,沃利斯和爱德华现在对他们昔日的焦虑有何感想?这一切最终对他们还重要吗?我想知道,他们是否想过这些?他们是漂浮在某个虚幻之境,仍在思考自己的选择,还是无处可去,什么都不想?生命完结之后真的什么都没有吗?意识是否和时间一样,也有一个终结点?或者,我想,只是也许,他们现在就在这里,就在伪哥特式废墟旁边,甚至就在我身边,偷听我的想法。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妈妈也在?
像往常一样,一想到她,我就充满了希望和活力,还有悲伤。
我每天都想念母亲,但那天,在弗罗格莫尔焦急不安地等待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她的渴望,却又无法说出其中的原因。个中滋味,很难用语言表达。虽然母亲是一位王妃,以女神的名字命名,但这两个称谓总让人觉得太过柔弱,并不恰如其分。人们经常将她比作偶像和圣人,从纳尔逊·曼德拉到特蕾莎修女,再到圣女贞德。但每一次这样的比较,虽然崇高且充满爱意,但也让人觉得不太恰当。我的母亲,作为这个星球上最有名、最受人爱戴的女人之一,无法用言语形容。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一个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人,怎么会如此真实?怎么会如此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怎么能看见她的身影,犹如靛蓝色湖面上向我飞来的天鹅?我怎么能听到她的笑声,像光秃秃的树上黄莺婉转的歌声?有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因为她去世的时候我年龄尚小。但宛如奇迹,我仿佛还记得一切:她那令人销魂的微笑,她那目光温柔的眼睛,她对电影、音乐、衣服、糖果如孩子般的热爱。还有对我们的爱。噢,她多么爱我和我的哥哥。她曾向一位采访者坦言,她对我们的爱是“如此执着”。
嗯,妈妈。我们对你的爱亦然。
也许她无处不在的原因和她无法被形容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她是光,纯净而光芒四射。你怎么能描述光呢?就连爱因斯坦也曾为这个问题纠结。最近,天文学家重新安放了最大的望远镜,将它对准宇宙中的一道裂缝,成功瞥见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球体,将其命名为厄伦德尔(Earendel)——来自古英语,意为“晨星”。它距离我们有数十亿英里之远,可能已经消失很久了,它比我们的银河系更接近宇宙大爆炸,也就是宇宙创造的那一刻。然而,人类的眼睛仍然可以看到它,因为它如此明亮和闪耀。
那是我妈妈。
这就是我总能看到她、感觉到她的原因。尤其在这个4月的下午,在弗罗格莫尔。
还有,我高举着她的旗帜,来弗罗格莫尔花园,是为了安宁。我追求安宁胜过一切,为了我的家庭,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她。
人们忘记了我母亲为世界的安宁所做的努力。她多次绕地球飞行,穿越雷区,拥抱艾滋病患者,安慰战争孤儿,总是努力为某个地方的人带来安宁。我知道她是多么迫切地希望——是真的希望——她的儿子之间,我们俩和爸爸之间,以及整个家族之间,都和睦安宁。
几个月来,温莎家族一直争论不休。上溯几个世纪,我们这个家族便纷争不断,延续至今。但这次不同。这次是全面的、公开的破裂,而且很可能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所以,我专程飞回家参加爷爷的葬礼,在葬礼上,我请求与哥哥威利和父亲秘密会面,谈谈现在的情况。
我想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又看了看手机,又在花园的小路上来回看了看,心想,也许他们改变主意,不会来了。
有那么一瞬,我想一走了之,去花园散步,或者回到那幢房子里去,在那里,家族中的兄弟姐妹正一起喝酒,讲爷爷的故事。
后来,我终于看到了他们,两个人肩并肩,大步流星向我走来,神情严肃,咄咄逼人。而且,他们看起来似乎已经达成某种共识。我的心一沉。通常他们总会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争论不休,但现在似乎步调一致——一副已然结盟的架势。
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等一会儿我们见面后,是一起散步,还是决斗?
我从木凳上站起来,试探性地向前走了一步,露出勉强的微笑。他们没有朝我微笑,我的心立刻怦怦地跳了起来。深呼吸!我告诉自己。
除了恐惧,我还感受到了自己的高度敏感,以及一种极度紧张的脆弱感。这种感觉我在其他关键时刻也曾经历过。
走在母亲的棺材后面的时候。
第一次投入战斗的时候。
“恐慌症”发作的情况下发表演讲的时候。
那同样是一种开始挑战的感觉,不知道是否能如愿以偿,却知道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命运掌握了主动权。
好吧,妈妈。我这么想着,加快脚步。开始了,祝我好运吧。
我们在路中间相遇。
“威利?爸爸?你们好。”
“哈罗德。”
彼此都不冷不热。
我们回转身,排成一行,沿着砾石小道出发,走过爬满常春藤的小石桥。
三个人低着头,一言不发,迈着同样的步伐,向前走着。不远处就是一座座坟墓,我不由得想起妈妈的葬礼。我一再告诉自己不要去想那些往事,而是去想我们悦耳的、嘎吱嘎吱的脚步声,去想我们的话语宛如一阵烟雾随风飘散的样子。
作为英国人,作为温莎家族的人,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天气,谈论爷爷的葬礼,我们苦笑着说,葬礼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策划的,包括最微小的细节。
闲聊。聊那些最没意思的话题,都是不咸不淡的事儿。我一直等待他们转入正题,不知道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闲扯,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和哥哥表现得如此冷静。
环顾四周。我们已经走了一段路,现在正好在皇家墓地的中央,这里周遭埋葬的尸体比哈姆雷特王子脚踝边的还要多。仔细想想……我不是也曾打算葬在这里吗?在我奔赴战场的几个小时前,私人秘书说我应该选择一个埋葬遗体的地方。“以防万一。殿下……战争是一件很难预测的事情……”
有几种选择。选择圣乔治教堂?选择温莎的皇家墓地——爷爷此刻安息的地方?
可我选择了这个地方,因为花园很可爱,而且看起来很宁静。
我们的脚几乎踩在沃利斯·辛普森的脸上时,爸爸开始给我们做一场“小型训话”。埋葬在这边的是什么人物,埋葬在那边的是哪个王室表亲,以及目前长眠在草坪下的所有曾经显赫的公爵和公爵夫人、勋爵和贵妇。作为一名毕生学习历史的学生,他有大量的信息可以分享。我心里想,这下子我们可得在这儿待上几个小时,最后还可能被他考问一番。幸运的是,他停止了说教,我们沿着湖边的草地继续前行,来到一小片美丽的水仙花前。
在那里,我们终于开始谈正事了。
我试图解释我的观点,但不在最佳状态。首先,我仍然很紧张,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想做到言简意赅、表达准确。更重要的是,我发誓决不让这次相聚演变成另一场争吵。但我很快发现,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爸爸和威利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他们准备好了战斗。每次我尝试一个新的解释,开始一个新的思路,他们中的一个或两个就会打断我。尤其是威利,他什么也不想听。在他三番五次拒绝我的善意之后,我们俩互相攻击起来,又把几个月甚至几年来一直在说的那些话搬了出来。场面非常激烈,爸爸举起手,大声说:“够了!”
他站在我俩中间,抬起头看着我们通红的脸:“求求你们,孩子们——不要让我的晚年变得痛苦。”
他的声音沙哑而虚弱,说实话,听起来非常苍老。
我想起了爷爷。
突然,我的内心发生了变化。我看着威利,认真地看着他。也许从小到大第一次这样直直地盯着他。一切的一切“尽收眼底”:他那熟悉的怒容,是和我打交道时惯有的表情;他那惊人的头顶,比我秃得还要厉害;他和妈妈众所周知的相似之处也逐渐消失。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某些方面,他是我的镜像;在某些方面,却是我的对立面。亲爱的哥哥,我的宿敌,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我觉得非常疲倦。我想回家,但意识到家已经变成一个复杂的概念。或许一直都是这样。
我指了指花园,指了指远处的城市,指了指这个国家,说道:“威利,这里本该是我们
的家。我们打算在这里度过余生的家。”
“可你走了,哈罗德。”
“是的,你知道原因。”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向后靠了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于往事的是非曲直、孰是孰非,观点不同是一回事,但他声称完全不知为何我要逃离我的出生地——我曾经为之战斗并准备为之牺牲的土地——我的祖国。这种说法让人心寒。难道你不知道我和妻子为什么会采取极端的行动,抱起孩子,抛下一切——房子、朋友、家具,拼命逃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抬头看着树说:“你不知道!”
“哈罗德……我真的不知道。”
我转过脸,望着爸爸。他盯着我,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我也不知道。”
哦,我想,也许他们真的不知道。
虽然难以置信,但也许是真的。
如果他们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我。或者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了解过我。
说句公道话,我也不了解他们。
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寒意袭人,内心深处非常孤独。
但这也点燃了我的激情。我想,必须告诉他们。
可该怎么告诉他们呢?我没法做到,那需要花很多时间。
而且,他们显然没有心情听我倾诉。至少现在没有,今天没有。
于是我写下这本书,给爸爸、威利,还有这个世界。
我要让你们知道这一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