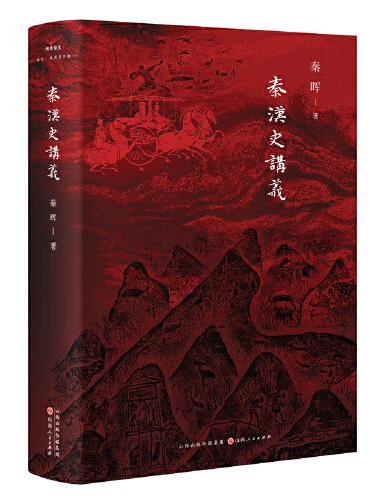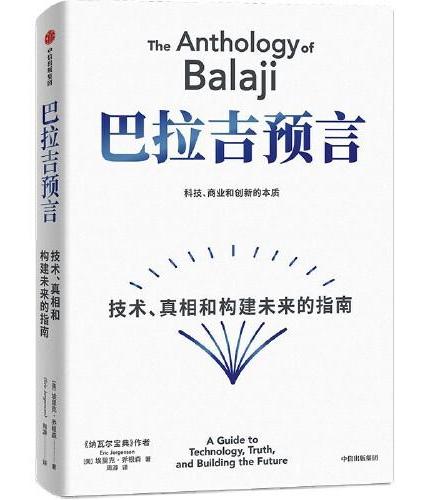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失败:1891—1900 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
》
售價:NT$
390.0

《
送你一匹马(“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看三毛如何拒绝内耗,为自己而活)
》
售價:NT$
2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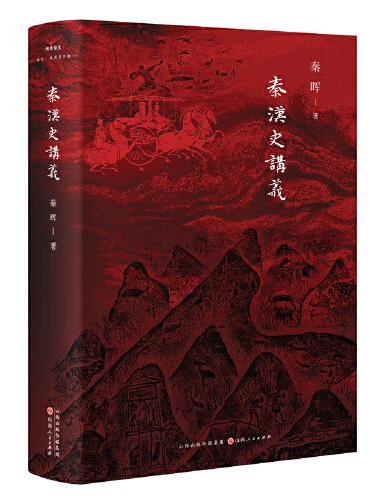
《
秦汉史讲义
》
售價:NT$
690.0

《
万千心理·我的精神分析之道:复杂的俄狄浦斯及其他议题
》
售價:NT$
475.0

《
荷马:伊利亚特(英文)-西方人文经典影印21
》
售價:NT$
490.0

《
我的心理医生是只猫
》
售價:NT$
2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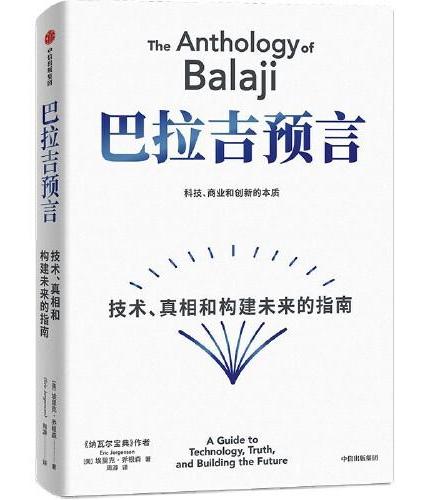
《
巴拉吉预言
》
售價:NT$
340.0

《
股权控制战略:如何实现公司控制和有效激励(第2版)
》
售價:NT$
449.0
|
| 編輯推薦: |
导游版《南京传》,六朝古都的文化地图
旧地故人的前世今生,深宅残垣中的温热余情
读过这本书,才懂得只属于南都金陵的华贵、落寞、温情与放肆
十月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汪曾祺文学奖得主深情诉说金陵往事
|
| 內容簡介: |
|
贾梦玮对包括大报恩寺、1865创业园、拉贝故居在内的诸多南京历史文化地标进行了实地探访,结合细致严谨的考据,追随张爱玲、赛珍珠、周氏兄弟、徐悲鸿等名人在南京的印记,讲述了这些建筑的前世今生,通过展现这些与南京息息相关的历史建筑、历史人物的历程和命运,勾勒出南京这座旧都华贵又落魄,端庄又沉郁的独特气质;借助南京这个小切口,作者寄思往昔,着眼未来,尝试用这些让人唏嘘的故事来标记历史与时代万变又不变的奔流方向。
|
| 關於作者: |
|
贾梦玮,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钟山》主编、《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散文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有散文随笔、文学评论若干见于报刊,结集出版的散文随笔集有《往日情感》《红颜》《南都》等。获在场主义散文奖、十月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汪曾祺文学奖以及其他多种文学编辑、文学评论奖项。
|
| 目錄:
|
1. 张爱玲:根在南京
2. 战争与菩提:1865 往事
3. 出入栖霞
4. 南京:两座洋楼的延续
5. 南京的赛珍珠
6. 南京的教堂
7. 文德桥:半个月亮和半个月亮
8. 金陵啊,秦淮啊
9. 回想朱偰
10. 姚鼐与南京
11. 新大陆:南京与周氏兄弟
12. 废都斜阳
13. 宁海路5 号
14. 憩庐 ? 美龄宫
15. 拉贝故居
16. 桂林石屋
17. 陈立夫、陈果夫公馆
18. 斗鸡闸
19. 陈布雷的公馆政治
20. 北极阁的“茅草屋”
21. 雍园1 号
22. 西流湾8 号
23. “ 无枫堂”
|
| 內容試閱:
|
“无枫堂”
在民国首都南京,除了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外国驻华使节外,只有极少数人有自己的公馆,大画家徐悲鸿是其中之一。
徐悲鸿在南京的时间不长,他在南京傅厚岗4 号的公馆“无枫堂”称得上是他的伤心之地。
因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徐悲鸿于1928 年举家由上海迁来南京,先是住在石婆婆巷,后来又搬到丹凤街52 号中央大学宿舍。当时徐悲鸿和夫人蒋碧微还没什么钱,盖不起自己的公馆。他们的宿舍在一幢老式的两层楼房里,里面还住有中央大学的另外三位教授。徐悲鸿分得其中的四间,蒋碧微的父母当时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因此显得特别拥挤。没有画室,无法进行大幅创作,徐悲鸿只好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为他准备的两间房子里作画,地点在中大靠东北角的围墙内,墙外就是成贤街北口,这两间房子一间开了大玻璃天窗作为画室,一间作为他的藏书室。好在从丹凤街去中大的这两间房子并不远,途中想必要经过北极阁和鸡鸣寺,这条路,徐悲鸿走了四年。当时的中大艺术系集中了一批造诣高深的教授,除了徐悲鸿外,还有吕凤子、汪采白、张书旗、潘玉良、陈之佛,后来又来了吕斯百、傅抱石等,艺术气氛好,在那间简陋的画室里,徐悲鸿还创作出了特大油画《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等名作。
徐悲鸿太需要自己的带大画室的公馆了。所幸当时他已是颇有名气的天才艺术家,人们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较为尊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肯出资3 000 块现大洋为徐悲鸿买宅基地,客观上也能说明这一点。民国之前的南京人习惯住在城南,鼓楼一带在民国之后才发展起来,吴稚晖出资买下的这块地皮在南京鼓楼坡的北面。这里本是大片的坟地,相当荒凉,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随着“建设新首都”计划的启动,房地产业火爆,地价飞涨,3 000 块大洋的巨款当时只买到两亩的坟地。特别的是,这块坟地上有两棵巨大的白杨树,据说当时全南京城这样的大白杨树只有三棵,另外一棵在城南。两棵白杨树身高达数丈,京沪路的火车驶近南京将到下关的时候,因为当时还没有高楼大厦,人们在火车上就可以远远地看见它们。
地皮买下了,没钱房子还是盖不起来。蒋碧微曾回忆其时她多次带着孩子和女佣到这块地皮上徘徊,憧憬着起于这片土地上的庭院楼阁。后来到了1932 年,还是由吴稚晖发起,许多人捐资凑起一笔钱,徐悲鸿公馆才终于动工。设计者姓卞,夫人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系,是徐悲鸿的学生,卞氏的设计想必是尽力的。房子终于在1932 年12 月建成了,徐悲鸿、蒋碧微一家子从拥挤的中大宿舍搬进了新居。
傅厚岗4号徐悲鸿公馆,是一座精巧别致的西式两层小楼,客厅、餐厅、卧室、浴室、卫生间齐全,徐悲鸿的画室更是气派,高1.6 丈,长3 丈,宽2 丈。那两棵白杨已经被围在院子里,周围是篱笆筑成的围墙,徐悲鸿的大画室正在两棵白杨的树荫之下。一进大门就是碧草如茵的前院,女主人当年在公馆落成之后就在院子里植上了草皮,点缀了花木,梅竹扶疏,桃柳掩映。
房子内部的陈设是法国风格,雍容典雅。女主人还在院中的草地上安上了两把大的遮阳伞,伞下放上圆桌和藤椅,可以在草地上乘凉消闲。蒋碧微游历欧洲多年,也有较好的艺术修养,她的公馆布置想来是不俗的。
但是,舒适的住房、美丽的庭院无法使心绪不好的人心旷神怡,良辰美景、香车宝马也只能给幸福的人带来幸福。徐悲鸿一家搬进新居之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年有余,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徐悲鸿将新公馆名为“危巢”,取居安思危之意。正如他在《危巢小记》中所说:“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意也。”但蒋碧微认为“危巢”之名不吉利,“危巢”也就未能叫响。在《危巢小记》中,徐悲鸿还以被置于庭院的黄山松自况:“黄山之松生危崖之上,营养不足,而生命力极强,与风霜战,奇态百出。好事者命石工凿之,置于庭园,长垣缭绕,灌溉以时,曲者日伸,瘦者日肥,奇态尽失,与常松等,悲鸿有居,毋乃类是。”看来,徐悲鸿对精致的公馆生活并不满意。在客厅的墙上,是一副对联:“独特偏见,一意孤行”,横批是“应毋庸议”,字如斗大,是泰山经石峪刻注的墨拓本大字。画家黄苗子第一次见徐悲鸿就是在傅厚岗公馆,他当时也被“这副气魄雄健、出语惊人的大对联怔住了”。这副对子与徐悲鸿所坚持的“一个艺术家要诚实、要自信”、“人不可有傲态,但不可无傲骨”、“不要为名誉和金钱创作,不要为阿谀世上创作”等是一致的。《蒋碧微回忆录》曾多次提到这副对子,她对徐悲鸿的这种脾气是比较恼火的。
精致的公馆对艺术家徐悲鸿确实并不合适。歌德就说过,奢侈的房间布置“终归是一种化装,从长远观点看,不会使人感到舒适”,这种布置“产生于一种空虚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方法,所以它只会加强这种空虚的思想境界”(艾克曼:《 歌德谈话录》,洪天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 年,第152 页)。他甚至认为:“摆着舒适而美观的家具的环境抵消我的思想,置我于舒适的被动的状态之中。除非从年轻时就习惯了,华丽的房间和精美的家具只适合没有思想或不想有思想的人使用。”(第404页)这种“华丽的房间和精美的家具”对从小过惯了贫寒和动荡生活的徐悲鸿反而是一种挤压。“危巢”是真正的“危巢”,“危巢”之“危”不仅指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也不幸言中了徐悲鸿和蒋碧微的情感婚姻。
他俩的结合曾是当时的一段佳话。蒋碧微生于宜兴的望族,宜兴南门大人巷里的蒋宅高墙巍峨,连绵数进,据说是当时宜兴城里最大的房子。蒋碧微是蒋家的次女,本名棠珍,1916年其父蒋梅笙在上海复旦大学当教授,蒋碧微随父在上海读书。当时徐悲鸿从家乡宜兴到上海发展,经人介绍去拜访这位前辈乡贤,徐悲鸿的人品才貌不但深得这位前辈的赏识,也赢得了蒋碧微的芳心。可惜的是,蒋碧微在13岁时就由其堂姐做主,许配给了苏州的查紫含。但生长在传统大家庭的蒋碧微却有勇气与出身寒微而且是丧妻的徐悲鸿悄悄恋爱起来。后来徐悲鸿得到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的一笔资助去日本留学,这位蒋二小姐跟着偷偷到了日本。在去日本的大海上,徐悲鸿将刻有“碧微”二字的水晶戒戴到她的手指上,“蒋棠珍”由此成了“蒋碧微”,时年18 岁。女儿和人私奔,对名门望族的蒋家来说是件很不体面的事,况且也不好向已经定亲的查家交代。蒋家无奈之下,只得宣称蒋棠珍已因疾病身亡,并在宜兴家中设了灵堂。出殡时,为免起疑心,棺材里放进了石头。多少年后,宜兴城里对此事还是津津乐道。在日本,在欧洲,蒋碧微和徐悲鸿度过了一段同甘共苦的日子,徐悲鸿作于法国的油画《箫声》中吹箫的女子不知倾倒了多少人,而这女子的原型就是蒋碧微。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徐悲鸿在美术界建立起了他的赫赫声名。
生活安定之后,特别是住进了傅厚岗的公馆后,他们之间的矛盾才渐渐显露出来。他们两个不但性情不和,生活态度也迥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对他们这样的两个人来说,能“共苦”而不能“同甘”有其必然性,往往与忘恩负义无关。“苦”时,为了改变生活状况,为了一段时期内共同的生活目标,双方的矛盾被掩盖;一旦一方功成名就,苦尽甘来,差异凸现,磨擦、冲突也就不可避免。2001 年9 月14日,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播出徐悲鸿专题,徐悲鸿和蒋碧微的女儿谈起她对父母的印象,态度非常诚恳。她谈话的大意是:父亲生活非常简朴,基本上是棉衫外加长衫,皮鞋实在不能再穿了,就到旧货摊上去买,而对艺术却是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花再多的钱也在所不惜。而母亲的穿着却超过了讲究的层次;喜欢请客,一请就是很多桌,她是把沙龙夫人的一套搬到家中来了。徐悲鸿和蒋碧微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活态度的巨大反差,他们之间的龃龉和情感危机主要发生在傅厚岗4 号的公馆中。清官难断家务事,徐、蒋孰是孰非外人恐难评说,大概也只有公馆知道了,傅厚岗4号目睹、见证了一切。所谓“家人”,“家”和“人”是连在一块儿的,人不和,再美的房子也是徒然。不和之人即使住在宫殿里,也避免不了家庭事件的发生。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授时,对女学生孙多慈的艺术才能颇为欣赏,师生感情甚笃。蒋碧微认为徐悲鸿移情于孙,背叛了她的感情,自然是不能容忍,大吵大闹,弄得满城风雨。公馆落成时,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来枫苗百棵,以作点缀新居庭院之用,本也无可厚非,用心也颇为不俗。蒋碧微得知此事,无法容忍,大发雷霆,竟令用人折苗为薪。作为艺术家的徐悲鸿面对这种事,自然是痛心不已,遂将公馆称为“无枫堂”,称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下“无枫堂”印章一枚作为纪念。这是艺术家徐悲鸿的纪念方式,也是他的反抗方式。于公,他将公馆命名为“危巢”;于私,他又称之为“无枫堂”,可见傅厚岗这座公馆在他心上留下的伤痛。
两人在政治上也有分歧。蒋碧微和张道藩曾劝徐悲鸿为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蒋介石画像,徐悲鸿就是不肯。不但如此,徐悲鸿还到处奔走,把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的田汉营救出狱,安排住在自己的公馆中。田汉出狱后继续进行抗日戏剧运动,徐悲鸿政治上又受到流言蜚语的中伤,离家出走,在广西等地游览、创作,组织义卖,为抗战筹集资金。他在广西不但为当时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画像,还在《广西日报》上撰文,指责蒋无礼、无义、无廉、无耻。蒋碧微在张道藩的影响下,希望徐改变反蒋态度,并亲赴桂林游说徐悲鸿,遭拒绝后,两人又大吵一场,不欢而散。
1938 年,徐悲鸿又曾与孙多慈相聚,但因孙的父亲反对,二人无奈地分手,孙后来经人撮合嫁给了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徐、孙从此天各一方,偶尔有书信来往,再以后连音信也断了。“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徐悲鸿在这首诗中表达了自己与孙多慈分手后的苦楚。孙多慈在赠徐悲鸿的诗中有这样两首:“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寒江沉落日,黄叶下深秋。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不知大地外,更有几人愁。”“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树。伤心家园无穷恨,红树青山总不知。”幽怨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1953 年9 月26 日,徐悲鸿在北京英年早逝,当时在台湾师大艺术系任教的孙多慈得知这一消息,悲痛万分,为恩师守了三年孝。
抗战期间,徐悲鸿多次努力和蒋碧微和好,甚至满面流泪地乞求,但因为蒋碧微正与张道藩爱得如火如荼,对徐悲鸿有的只是嫌恶,和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蒋碧微将她在重庆的住室命名为“宗荫室”,“宗”是张道藩给蒋碧微写情书时专用的名字,“宗荫室”怎么能接纳徐悲鸿呢?后来二人终于在重庆协议离婚,做证律师是大名鼎鼎的沈钧儒,蒋碧微从徐悲鸿那儿得到了一百万的赡养费和一百幅画。徐悲鸿后来还将油画《琴课》送给了蒋碧微,此画亦作于法国,画的是蒋碧微在巴黎练习小提琴的情景,是蒋碧微特别喜欢的一幅画。
抗战胜利后,徐悲鸿连到公馆凭吊往事的机会都没有了。傅厚岗公馆的房子和地皮当时都是用儿子伯阳的名义在市政府登记的,二人离婚时并未提到房子的事,蒋碧微是儿子的监护人,自认为“有权处理这幢房子”,徐悲鸿也一直没有提出房子问题,公馆因此实际上成了蒋碧微一个人的房产。抗战胜利后,张道藩先回南京,曾特地为蒋碧微到傅厚岗去查看房子,并将情况写信告诉了蒋碧薇。蒋碧微从重庆回到南京,与女儿两人住在公馆里,蒋碧微在回忆录中说:“……两母女住在那么大的一幢房子里,不免感到相当的冷清。尤其回忆前尘往事,当年筹建新屋时的兴奋欢欣,一家团聚的和乐融融,仿佛都在眼前,又仿佛距离已远。如今华屋依旧,人事全非……”蒋碧微后来将公馆略加修缮,高价出租给了法国新闻处,自己则在院内的空地上另盖了一座新楼,与她出双入对的已经换成了国民党要员、中宣部部长张道藩。
我曾从电视上看到徐悲鸿和蒋碧微在傅厚岗公馆门前的合影,想想徐悲鸿和蒋碧微之间的欢悲合离,心中不由得隐隐作痛。蒋碧微写《蒋碧微回忆录》时说:“我以‘真实’为出发点,怀着虔诚之心,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我半生的际遇,我一心坦荡,只有衷诚感恩之念,毫无睚眦必报之心,我在我的回忆录中抒写我所敬、我所爱、我所感、我所念的一切人与事,我深信我不会损害到任何一位与我相关的人。”睚眦必报,蒋碧微倒是没有,但“感恩”却也谈不上。蒋碧微总结她与徐悲鸿一起走过的岁月,说:“如此我从18 岁跟他浪迹天涯海角,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但不曾得到他一点照顾,反而受到无穷的痛苦和厄难……”(《蒋碧微回忆录》)这哪还有对人世的“感恩”?
仅从徐悲鸿以蒋碧薇为模特所作的画像中(大概有七幅,除了上面提到的《箫声》《琴课》外,还有《凭桌》《裸裎》《慵》《静读》《传真》),我就能读到徐悲鸿对蒋碧微的脉脉深情,或者说是曾经有过的脉脉深情。男女感情一旦破裂,心中难免怨恨,但就此否定以往的一切,心未免太狠了一点。从中国古代的怨妇诗一直到如今女作者回忆自己消失了的爱情的散文,我读到的只有怨恨,没有感恩。好在从男性作者的同类文章中,我还时常能读到忏悔和感激,我因此对人世间的男女之情不至于太失望。
1946 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蒋碧微以社会贤达身份当上国大代表,这可能与张道藩的举荐有关。据说每次开会她都要换不同的新装,而且色彩艳丽,虽然她已是半老徐娘。与张道藩过从甚密,也是许多报纸的花絮新闻。有家报纸在花絮里还写到她在休息室里和别人唱和,其中有这样两联:一是“秋水长天同碧色,落霞孤鹜逐微风”,一是“天黏芳草碧,山抹暮云微”。两联都嵌入了“碧微”二字,前者化王勃《滕王阁序》里的名句,后者化秦观词《满庭芳》。这个蒋碧微实在不是等闲女子。在傅厚岗公馆,蒋碧微还是免不了时常要大宴宾客,除了张道藩外,胡小石、宗白华、陈之佛、潘公展、傅抱石等都是她家的座上客,这些也都是徐悲鸿的朋友或学生,但是这样的聚会原来的男主人徐悲鸿是没法参加了,所谓“围炉共话少一人”!
徐悲鸿和蒋碧微生有一子一女,离婚后随蒋碧微生活,但由于家庭变故,蒋碧微又与张道藩相恋,儿子伯阳和女儿丽丽先后离家出走,1949 年都留在了大陆。解放军攻克南京时,女儿徐静斐(丽丽)由共产党派到南京参加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傅厚岗公馆已经人去楼空,蒋碧微只身去了台湾,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也从未与徐悲鸿和一双儿女有过联系。去台后,张道藩对她也逐渐冷淡,蒋碧微在孤寂中去世。我们可以不赞同蒋碧微的生活方式,但实在也不能苛责于她。徐悲鸿与蒋碧微离异后,对他们之间的事避而不谈,大概是怕揭自己心中的那块伤疤。徐悲鸿后来的夫人廖静文女士在《徐悲鸿的一生》中,谈到蒋碧微的时候,每出溢恶之词,我觉得也是不够厚道的。廖和蒋连情敌都算不上—徐悲鸿与廖静文相识时,早已与蒋碧微分居,廖连见到蒋的机会估计都没有,更不要说有多少直接的了解了。
傅厚岗原徐公馆至今仍在。潘孑农先生在《金陵拾梦(之三)》(《南京史志》1988 年第2期)一文中诉说过“傅厚岗前的怀念”:最近到南京小住,从玄武饭店出来散步,不知不觉地走近傅厚岗,顿时想起老画师徐悲鸿先生当年自建的寓所,就在这里上坡的小路边。很想寻找旧址,凭吊这位可亲可敬的忘年交,但徘徊良久,找不到一点痕迹。怀念的思绪,竟被默默地抽长了,抽长了!
1929 年田汉先生率领南国话剧团到南京公演,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我认识了悲鸿先生。后来我迁往四牌楼,靠近中央大学,和他见面的机会较多,更由他而拜识了宗白华、胡小石教授。徐先生非常关心话剧,偶有演出,只要送座券去,他总和夫人蒋碧微准时到场,有时还坦率地提点意见。因此,我也不时去徐先生寓所拜访,无所拘束地任意闲谈,徐先生和颜悦色,使我如坐春风,得益匪浅。
回忆那两座两底的西式楼房,隐围于精编的竹篱之中。一进门,碧草如茵的前院,点缀着疏淡的花朵,两大株白杨树荫下,是徐先生的画室,楼下客厅,楼上是卧室。春禽夏蝉,偶尔划破静寂的庭院,充满了诗情画意。然而就在这恬美的家庭里,徐悲鸿与蒋碧微的夫妻感情,正潜伏着破裂的危机,终于在抗日烽火中凶终隙末,分道扬镳于重庆。如今双方均已逝世,共栖的旧巢即使尚存,也是不堪回首了。
潘先生的感慨我也是有的,虽然徐悲鸿、蒋碧微以及他们在傅厚岗的公馆与我并无直接的关系。那么多年过去了,傅厚岗所在的鼓楼也是南京变化最大的地区之一,但潘先生没有找到的旧址我还是找到了。现在编为傅厚岗4 号的原徐悲鸿公馆据说为南京师范大学所有,大概是因为徐悲鸿原来是中央大学的人,解放后院系调整时中大的艺术系被划到南京师范学院(后来改为南京师范大学)的缘故。我找到这里时,原来这里的住户已搬走,从院门的门缝里可以看到它一楼的墙上挂着“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的铜牌,估计不是每天都有人上班,敲了半天也没人来开门。它的右前方原是傅抱石公馆,傅抱石先生当年由徐悲鸿介绍来中大艺术系任教,两家还做了邻居。两位艺术家如今都到了另一个世界,不知是否依然比邻而居。我敲开了傅家的门,傅家的后人也不常住在这里,看门的人告诉我,从傅家的院子也是没法进到4 号的院子里的。我只好又折回来,站在自行车的后座,从围墙上勉强摄下了原徐悲鸿公馆的照片。院内有高大的广玉兰,估计是当年所栽;那两棵高大的白杨据说早在抗战期间就被人伐去了。大概是没人居住的缘故,院内荒草萋萋,一只猫从草丛中钻出来,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
再后来路过那里,见“无枫堂”已装修一新,为南京徐悲鸿纪念馆。
“无枫堂”
在民国首都南京,除了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外国驻华使节外,只有极少数人有自己的公馆,大画家徐悲鸿是其中之一。
徐悲鸿在南京的时间不长,他在南京傅厚岗4 号的公馆“无枫堂”称得上是他的伤心之地。
因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徐悲鸿于1928 年举家由上海迁来南京,先是住在石婆婆巷,后来又搬到丹凤街52 号中央大学宿舍。当时徐悲鸿和夫人蒋碧微还没什么钱,盖不起自己的公馆。他们的宿舍在一幢老式的两层楼房里,里面还住有中央大学的另外三位教授。徐悲鸿分得其中的四间,蒋碧微的父母当时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因此显得特别拥挤。没有画室,无法进行大幅创作,徐悲鸿只好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为他准备的两间房子里作画,地点在中大靠东北角的围墙内,墙外就是成贤街北口,这两间房子一间开了大玻璃天窗作为画室,一间作为他的藏书室。好在从丹凤街去中大的这两间房子并不远,途中想必要经过北极阁和鸡鸣寺,这条路,徐悲鸿走了四年。当时的中大艺术系集中了一批造诣高深的教授,除了徐悲鸿外,还有吕凤子、汪采白、张书旗、潘玉良、陈之佛,后来又来了吕斯百、傅抱石等,艺术气氛好,在那间简陋的画室里,徐悲鸿还创作出了特大油画《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等名作。
徐悲鸿太需要自己的带大画室的公馆了。所幸当时他已是颇有名气的天才艺术家,人们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较为尊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肯出资3 000 块现大洋为徐悲鸿买宅基地,客观上也能说明这一点。民国之前的南京人习惯住在城南,鼓楼一带在民国之后才发展起来,吴稚晖出资买下的这块地皮在南京鼓楼坡的北面。这里本是大片的坟地,相当荒凉,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随着“建设新首都”计划的启动,房地产业火爆,地价飞涨,3 000 块大洋的巨款当时只买到两亩的坟地。特别的是,这块坟地上有两棵巨大的白杨树,据说当时全南京城这样的大白杨树只有三棵,另外一棵在城南。两棵白杨树身高达数丈,京沪路的火车驶近南京将到下关的时候,因为当时还没有高楼大厦,人们在火车上就可以远远地看见它们。
地皮买下了,没钱房子还是盖不起来。蒋碧微曾回忆其时她多次带着孩子和女佣到这块地皮上徘徊,憧憬着起于这片土地上的庭院楼阁。后来到了1932 年,还是由吴稚晖发起,许多人捐资凑起一笔钱,徐悲鸿公馆才终于动工。设计者姓卞,夫人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系,是徐悲鸿的学生,卞氏的设计想必是尽力的。房子终于在1932 年12 月建成了,徐悲鸿、蒋碧微一家子从拥挤的中大宿舍搬进了新居。
傅厚岗4号徐悲鸿公馆,是一座精巧别致的西式两层小楼,客厅、餐厅、卧室、浴室、卫生间齐全,徐悲鸿的画室更是气派,高1.6 丈,长3 丈,宽2 丈。那两棵白杨已经被围在院子里,周围是篱笆筑成的围墙,徐悲鸿的大画室正在两棵白杨的树荫之下。一进大门就是碧草如茵的前院,女主人当年在公馆落成之后就在院子里植上了草皮,点缀了花木,梅竹扶疏,桃柳掩映。
房子内部的陈设是法国风格,雍容典雅。女主人还在院中的草地上安上了两把大的遮阳伞,伞下放上圆桌和藤椅,可以在草地上乘凉消闲。蒋碧微游历欧洲多年,也有较好的艺术修养,她的公馆布置想来是不俗的。
但是,舒适的住房、美丽的庭院无法使心绪不好的人心旷神怡,良辰美景、香车宝马也只能给幸福的人带来幸福。徐悲鸿一家搬进新居之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年有余,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徐悲鸿将新公馆名为“危巢”,取居安思危之意。正如他在《危巢小记》中所说:“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意也。”但蒋碧微认为“危巢”之名不吉利,“危巢”也就未能叫响。在《危巢小记》中,徐悲鸿还以被置于庭院的黄山松自况:“黄山之松生危崖之上,营养不足,而生命力极强,与风霜战,奇态百出。好事者命石工凿之,置于庭园,长垣缭绕,灌溉以时,曲者日伸,瘦者日肥,奇态尽失,与常松等,悲鸿有居,毋乃类是。”看来,徐悲鸿对精致的公馆生活并不满意。在客厅的墙上,是一副对联:“独特偏见,一意孤行”,横批是“应毋庸议”,字如斗大,是泰山经石峪刻注的墨拓本大字。画家黄苗子第一次见徐悲鸿就是在傅厚岗公馆,他当时也被“这副气魄雄健、出语惊人的大对联怔住了”。这副对子与徐悲鸿所坚持的“一个艺术家要诚实、要自信”、“人不可有傲态,但不可无傲骨”、“不要为名誉和金钱创作,不要为阿谀世上创作”等是一致的。《蒋碧微回忆录》曾多次提到这副对子,她对徐悲鸿的这种脾气是比较恼火的。
精致的公馆对艺术家徐悲鸿确实并不合适。歌德就说过,奢侈的房间布置“终归是一种化装,从长远观点看,不会使人感到舒适”,这种布置“产生于一种空虚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方法,所以它只会加强这种空虚的思想境界”(艾克曼:《 歌德谈话录》,洪天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 年,第152 页)。他甚至认为:“摆着舒适而美观的家具的环境抵消我的思想,置我于舒适的被动的状态之中。除非从年轻时就习惯了,华丽的房间和精美的家具只适合没有思想或不想有思想的人使用。”(第404页)这种“华丽的房间和精美的家具”对从小过惯了贫寒和动荡生活的徐悲鸿反而是一种挤压。“危巢”是真正的“危巢”,“危巢”之“危”不仅指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也不幸言中了徐悲鸿和蒋碧微的情感婚姻。
他俩的结合曾是当时的一段佳话。蒋碧微生于宜兴的望族,宜兴南门大人巷里的蒋宅高墙巍峨,连绵数进,据说是当时宜兴城里最大的房子。蒋碧微是蒋家的次女,本名棠珍,1916年其父蒋梅笙在上海复旦大学当教授,蒋碧微随父在上海读书。当时徐悲鸿从家乡宜兴到上海发展,经人介绍去拜访这位前辈乡贤,徐悲鸿的人品才貌不但深得这位前辈的赏识,也赢得了蒋碧微的芳心。可惜的是,蒋碧微在13岁时就由其堂姐做主,许配给了苏州的查紫含。但生长在传统大家庭的蒋碧微却有勇气与出身寒微而且是丧妻的徐悲鸿悄悄恋爱起来。后来徐悲鸿得到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的一笔资助去日本留学,这位蒋二小姐跟着偷偷到了日本。在去日本的大海上,徐悲鸿将刻有“碧微”二字的水晶戒戴到她的手指上,“蒋棠珍”由此成了“蒋碧微”,时年18 岁。女儿和人私奔,对名门望族的蒋家来说是件很不体面的事,况且也不好向已经定亲的查家交代。蒋家无奈之下,只得宣称蒋棠珍已因疾病身亡,并在宜兴家中设了灵堂。出殡时,为免起疑心,棺材里放进了石头。多少年后,宜兴城里对此事还是津津乐道。在日本,在欧洲,蒋碧微和徐悲鸿度过了一段同甘共苦的日子,徐悲鸿作于法国的油画《箫声》中吹箫的女子不知倾倒了多少人,而这女子的原型就是蒋碧微。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徐悲鸿在美术界建立起了他的赫赫声名。
生活安定之后,特别是住进了傅厚岗的公馆后,他们之间的矛盾才渐渐显露出来。他们两个不但性情不和,生活态度也迥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对他们这样的两个人来说,能“共苦”而不能“同甘”有其必然性,往往与忘恩负义无关。“苦”时,为了改变生活状况,为了一段时期内共同的生活目标,双方的矛盾被掩盖;一旦一方功成名就,苦尽甘来,差异凸现,磨擦、冲突也就不可避免。2001 年9 月14日,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播出徐悲鸿专题,徐悲鸿和蒋碧微的女儿谈起她对父母的印象,态度非常诚恳。她谈话的大意是:父亲生活非常简朴,基本上是棉衫外加长衫,皮鞋实在不能再穿了,就到旧货摊上去买,而对艺术却是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花再多的钱也在所不惜。而母亲的穿着却超过了讲究的层次;喜欢请客,一请就是很多桌,她是把沙龙夫人的一套搬到家中来了。徐悲鸿和蒋碧微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活态度的巨大反差,他们之间的龃龉和情感危机主要发生在傅厚岗4 号的公馆中。清官难断家务事,徐、蒋孰是孰非外人恐难评说,大概也只有公馆知道了,傅厚岗4号目睹、见证了一切。所谓“家人”,“家”和“人”是连在一块儿的,人不和,再美的房子也是徒然。不和之人即使住在宫殿里,也避免不了家庭事件的发生。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授时,对女学生孙多慈的艺术才能颇为欣赏,师生感情甚笃。蒋碧微认为徐悲鸿移情于孙,背叛了她的感情,自然是不能容忍,大吵大闹,弄得满城风雨。公馆落成时,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来枫苗百棵,以作点缀新居庭院之用,本也无可厚非,用心也颇为不俗。蒋碧微得知此事,无法容忍,大发雷霆,竟令用人折苗为薪。作为艺术家的徐悲鸿面对这种事,自然是痛心不已,遂将公馆称为“无枫堂”,称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下“无枫堂”印章一枚作为纪念。这是艺术家徐悲鸿的纪念方式,也是他的反抗方式。于公,他将公馆命名为“危巢”;于私,他又称之为“无枫堂”,可见傅厚岗这座公馆在他心上留下的伤痛。
两人在政治上也有分歧。蒋碧微和张道藩曾劝徐悲鸿为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蒋介石画像,徐悲鸿就是不肯。不但如此,徐悲鸿还到处奔走,把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的田汉营救出狱,安排住在自己的公馆中。田汉出狱后继续进行抗日戏剧运动,徐悲鸿政治上又受到流言蜚语的中伤,离家出走,在广西等地游览、创作,组织义卖,为抗战筹集资金。他在广西不但为当时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画像,还在《广西日报》上撰文,指责蒋无礼、无义、无廉、无耻。蒋碧微在张道藩的影响下,希望徐改变反蒋态度,并亲赴桂林游说徐悲鸿,遭拒绝后,两人又大吵一场,不欢而散。
1938 年,徐悲鸿又曾与孙多慈相聚,但因孙的父亲反对,二人无奈地分手,孙后来经人撮合嫁给了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徐、孙从此天各一方,偶尔有书信来往,再以后连音信也断了。“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徐悲鸿在这首诗中表达了自己与孙多慈分手后的苦楚。孙多慈在赠徐悲鸿的诗中有这样两首:“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寒江沉落日,黄叶下深秋。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不知大地外,更有几人愁。”“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树。伤心家园无穷恨,红树青山总不知。”幽怨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1953 年9 月26 日,徐悲鸿在北京英年早逝,当时在台湾师大艺术系任教的孙多慈得知这一消息,悲痛万分,为恩师守了三年孝。
抗战期间,徐悲鸿多次努力和蒋碧微和好,甚至满面流泪地乞求,但因为蒋碧微正与张道藩爱得如火如荼,对徐悲鸿有的只是嫌恶,和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蒋碧微将她在重庆的住室命名为“宗荫室”,“宗”是张道藩给蒋碧微写情书时专用的名字,“宗荫室”怎么能接纳徐悲鸿呢?后来二人终于在重庆协议离婚,做证律师是大名鼎鼎的沈钧儒,蒋碧微从徐悲鸿那儿得到了一百万的赡养费和一百幅画。徐悲鸿后来还将油画《琴课》送给了蒋碧微,此画亦作于法国,画的是蒋碧微在巴黎练习小提琴的情景,是蒋碧微特别喜欢的一幅画。
抗战胜利后,徐悲鸿连到公馆凭吊往事的机会都没有了。傅厚岗公馆的房子和地皮当时都是用儿子伯阳的名义在市政府登记的,二人离婚时并未提到房子的事,蒋碧微是儿子的监护人,自认为“有权处理这幢房子”,徐悲鸿也一直没有提出房子问题,公馆因此实际上成了蒋碧微一个人的房产。抗战胜利后,张道藩先回南京,曾特地为蒋碧微到傅厚岗去查看房子,并将情况写信告诉了蒋碧薇。蒋碧微从重庆回到南京,与女儿两人住在公馆里,蒋碧微在回忆录中说:“……两母女住在那么大的一幢房子里,不免感到相当的冷清。尤其回忆前尘往事,当年筹建新屋时的兴奋欢欣,一家团聚的和乐融融,仿佛都在眼前,又仿佛距离已远。如今华屋依旧,人事全非……”蒋碧微后来将公馆略加修缮,高价出租给了法国新闻处,自己则在院内的空地上另盖了一座新楼,与她出双入对的已经换成了国民党要员、中宣部部长张道藩。
我曾从电视上看到徐悲鸿和蒋碧微在傅厚岗公馆门前的合影,想想徐悲鸿和蒋碧微之间的欢悲合离,心中不由得隐隐作痛。蒋碧微写《蒋碧微回忆录》时说:“我以‘真实’为出发点,怀着虔诚之心,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我半生的际遇,我一心坦荡,只有衷诚感恩之念,毫无睚眦必报之心,我在我的回忆录中抒写我所敬、我所爱、我所感、我所念的一切人与事,我深信我不会损害到任何一位与我相关的人。”睚眦必报,蒋碧微倒是没有,但“感恩”却也谈不上。蒋碧微总结她与徐悲鸿一起走过的岁月,说:“如此我从18 岁跟他浪迹天涯海角,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但不曾得到他一点照顾,反而受到无穷的痛苦和厄难……”(《蒋碧微回忆录》)这哪还有对人世的“感恩”?
仅从徐悲鸿以蒋碧薇为模特所作的画像中(大概有七幅,除了上面提到的《箫声》《琴课》外,还有《凭桌》《裸裎》《慵》《静读》《传真》),我就能读到徐悲鸿对蒋碧微的脉脉深情,或者说是曾经有过的脉脉深情。男女感情一旦破裂,心中难免怨恨,但就此否定以往的一切,心未免太狠了一点。从中国古代的怨妇诗一直到如今女作者回忆自己消失了的爱情的散文,我读到的只有怨恨,没有感恩。好在从男性作者的同类文章中,我还时常能读到忏悔和感激,我因此对人世间的男女之情不至于太失望。
1946 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蒋碧微以社会贤达身份当上国大代表,这可能与张道藩的举荐有关。据说每次开会她都要换不同的新装,而且色彩艳丽,虽然她已是半老徐娘。与张道藩过从甚密,也是许多报纸的花絮新闻。有家报纸在花絮里还写到她在休息室里和别人唱和,其中有这样两联:一是“秋水长天同碧色,落霞孤鹜逐微风”,一是“天黏芳草碧,山抹暮云微”。两联都嵌入了“碧微”二字,前者化王勃《滕王阁序》里的名句,后者化秦观词《满庭芳》。这个蒋碧微实在不是等闲女子。在傅厚岗公馆,蒋碧微还是免不了时常要大宴宾客,除了张道藩外,胡小石、宗白华、陈之佛、潘公展、傅抱石等都是她家的座上客,这些也都是徐悲鸿的朋友或学生,但是这样的聚会原来的男主人徐悲鸿是没法参加了,所谓“围炉共话少一人”!
徐悲鸿和蒋碧微生有一子一女,离婚后随蒋碧微生活,但由于家庭变故,蒋碧微又与张道藩相恋,儿子伯阳和女儿丽丽先后离家出走,1949 年都留在了大陆。解放军攻克南京时,女儿徐静斐(丽丽)由共产党派到南京参加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傅厚岗公馆已经人去楼空,蒋碧微只身去了台湾,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也从未与徐悲鸿和一双儿女有过联系。去台后,张道藩对她也逐渐冷淡,蒋碧微在孤寂中去世。我们可以不赞同蒋碧微的生活方式,但实在也不能苛责于她。徐悲鸿与蒋碧微离异后,对他们之间的事避而不谈,大概是怕揭自己心中的那块伤疤。徐悲鸿后来的夫人廖静文女士在《徐悲鸿的一生》中,谈到蒋碧微的时候,每出溢恶之词,我觉得也是不够厚道的。廖和蒋连情敌都算不上—徐悲鸿与廖静文相识时,早已与蒋碧微分居,廖连见到蒋的机会估计都没有,更不要说有多少直接的了解了。
傅厚岗原徐公馆至今仍在。潘孑农先生在《金陵拾梦(之三)》(《南京史志》1988 年第2期)一文中诉说过“傅厚岗前的怀念”:最近到南京小住,从玄武饭店出来散步,不知不觉地走近傅厚岗,顿时想起老画师徐悲鸿先生当年自建的寓所,就在这里上坡的小路边。很想寻找旧址,凭吊这位可亲可敬的忘年交,但徘徊良久,找不到一点痕迹。怀念的思绪,竟被默默地抽长了,抽长了!
1929 年田汉先生率领南国话剧团到南京公演,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我认识了悲鸿先生。后来我迁往四牌楼,靠近中央大学,和他见面的机会较多,更由他而拜识了宗白华、胡小石教授。徐先生非常关心话剧,偶有演出,只要送座券去,他总和夫人蒋碧微准时到场,有时还坦率地提点意见。因此,我也不时去徐先生寓所拜访,无所拘束地任意闲谈,徐先生和颜悦色,使我如坐春风,得益匪浅。
回忆那两座两底的西式楼房,隐围于精编的竹篱之中。一进门,碧草如茵的前院,点缀着疏淡的花朵,两大株白杨树荫下,是徐先生的画室,楼下客厅,楼上是卧室。春禽夏蝉,偶尔划破静寂的庭院,充满了诗情画意。然而就在这恬美的家庭里,徐悲鸿与蒋碧微的夫妻感情,正潜伏着破裂的危机,终于在抗日烽火中凶终隙末,分道扬镳于重庆。如今双方均已逝世,共栖的旧巢即使尚存,也是不堪回首了。
潘先生的感慨我也是有的,虽然徐悲鸿、蒋碧微以及他们在傅厚岗的公馆与我并无直接的关系。那么多年过去了,傅厚岗所在的鼓楼也是南京变化最大的地区之一,但潘先生没有找到的旧址我还是找到了。现在编为傅厚岗4 号的原徐悲鸿公馆据说为南京师范大学所有,大概是因为徐悲鸿原来是中央大学的人,解放后院系调整时中大的艺术系被划到南京师范学院(后来改为南京师范大学)的缘故。我找到这里时,原来这里的住户已搬走,从院门的门缝里可以看到它一楼的墙上挂着“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的铜牌,估计不是每天都有人上班,敲了半天也没人来开门。它的右前方原是傅抱石公馆,傅抱石先生当年由徐悲鸿介绍来中大艺术系任教,两家还做了邻居。两位艺术家如今都到了另一个世界,不知是否依然比邻而居。我敲开了傅家的门,傅家的后人也不常住在这里,看门的人告诉我,从傅家的院子也是没法进到4 号的院子里的。我只好又折回来,站在自行车的后座,从围墙上勉强摄下了原徐悲鸿公馆的照片。院内有高大的广玉兰,估计是当年所栽;那两棵高大的白杨据说早在抗战期间就被人伐去了。大概是没人居住的缘故,院内荒草萋萋,一只猫从草丛中钻出来,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
再后来路过那里,见“无枫堂”已装修一新,为南京徐悲鸿纪念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