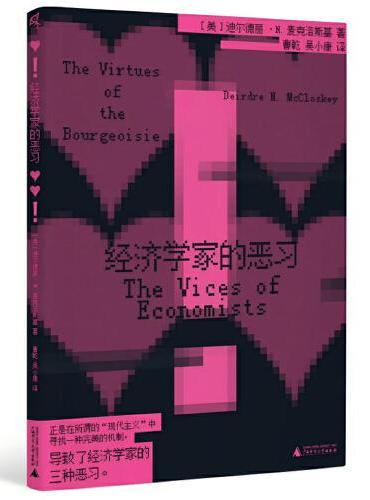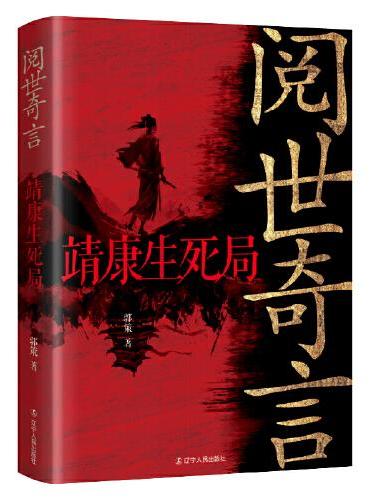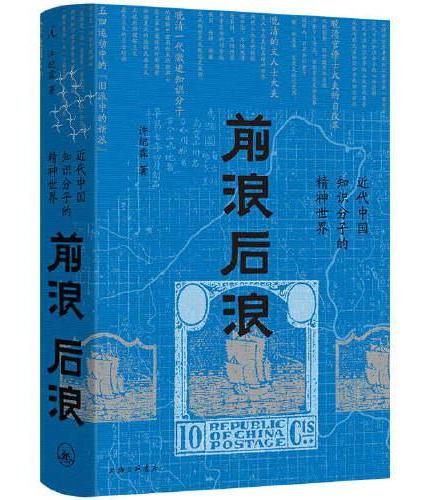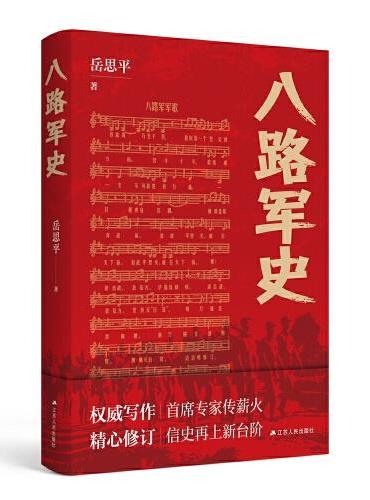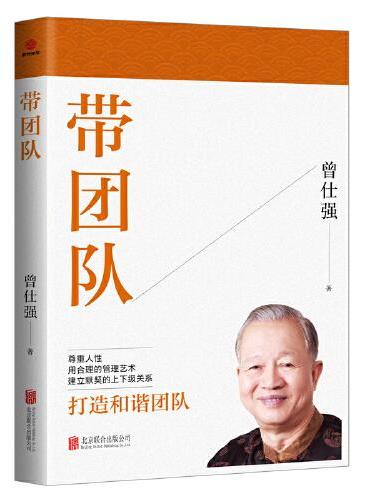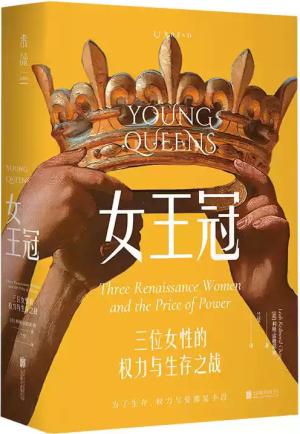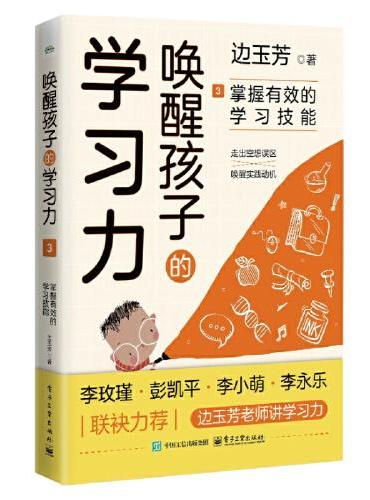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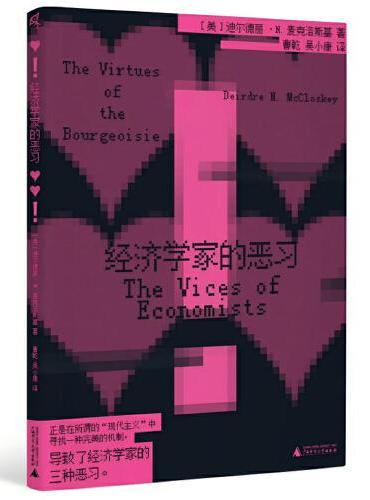
《
新民说·经济学家的恶习
》
售價:NT$
2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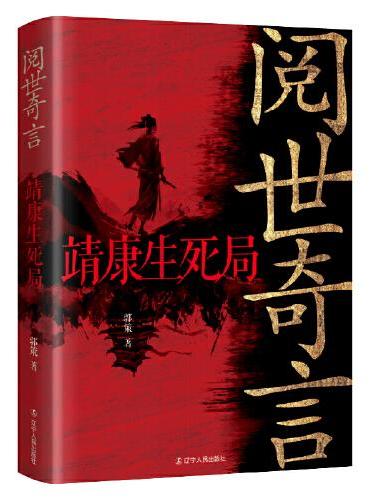
《
阅世奇言:靖康生死局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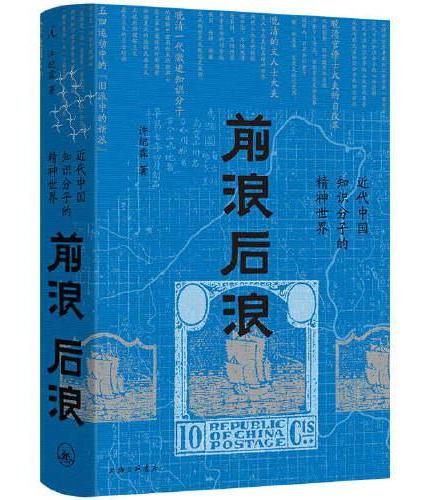
《
前浪后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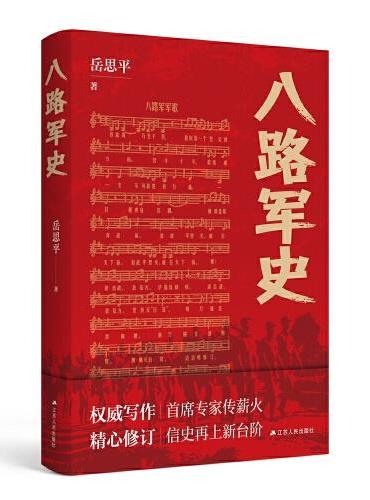
《
八路军史
》
售價:NT$
500.0

《
美味简史
》
售價:NT$
2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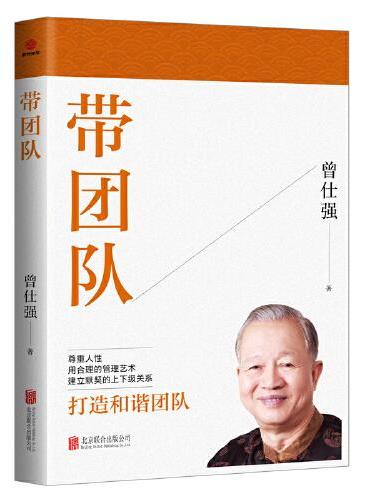
《
带团队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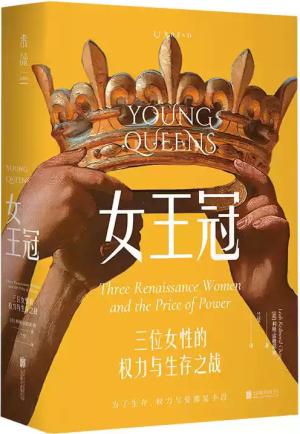
《
女王冠:三位女性的权力与生存之战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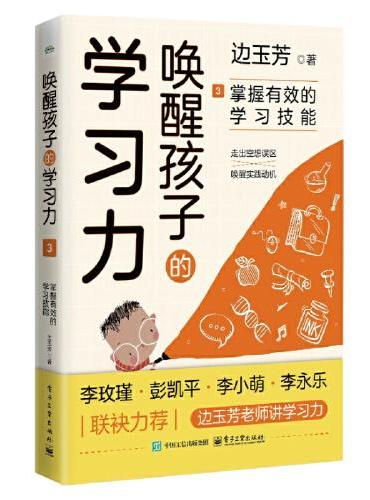
《
唤醒孩子的学习力3:掌握有效的学习技能
》
售價:NT$
332.0
|
| 內容簡介: |
这是一册有关童年少年生活的散记,每篇都独立成文,精心驾驭。没有虚构,或有美化,因为岁月的淘洗,沉淀下来的只有真善美。
少年比的是才气,中年比的是学问,老年比的是人格。如今白首回眸,三者都已在这薄薄的小册中,雕光铸影,毕现无遗。
|
| 關於作者: |
|
卞毓方,中国文促会国学艺术委员会顾问,聊城大学季羡林学院名誉院长,著名学者,作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系,长期供职于人民日报。中年皈依文学,有《长歌当啸》《季羡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寻找大师》《北大与时间之外》《日本人的“真面目”》《天马行地》等书问世。作品或如天马行空、大气游虹,或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其风格如黄钟大吕,熔神奇、瑰丽、嶙峋于一炉,长歌当啸,独树一帜。
|
| 目錄:
|
目录
代序:张謇是一方风水 001
A
生命的序幕 003
末代私塾生 010
青青园中葵 018
门缝里看戏 026
风筝还在天上飞 032
“耷钱堆”与“ 铜板” 036
上帝预先关上三扇门 042
一条手缝的红领巾 049
我是怎样当上小英雄的 054
月轮加冕图 059
的萌萌哒 066
历书上的英雄豪杰 070
八竿子打不着的施耐庵 075
天塌下来,自有不周山撑着 082
一桩无头案的始终 090
我成了李逵的伯乐 097
B
掠过我头顶的两朵雨云 105
停学停出来的转折 111
咒语也可以这么念 121
孤本记忆 125
蝴蝶打掌心飞过 134
这也是诗 142
有师如此,不亦快哉 150
眼前多少绿意 156
人有命运,书也有命运 163
“阿婆还是初笄女” 183
七拐八拐就拐向了北大 188
C
本庄人与本庄话 195
祖父眼中的风水 202
祖父的上中下三策 209
祖父的救命树 214
沪上归去来记 220
扁担那头的父亲 225
母子夜话三国 231
张四维先生小记 238
登览独成章 255
在暖黄的光晕中安享憬悟 263
莎士比亚长什么模样? 269
今夜,南侠北侠倒挂于谁家的屋檐? 274
D
梦考 295
古山兄弟 301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 307
“难得相看尽白头” 313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331
“人间万事细如毛” 340
母校,永远的大本营 353
也是不亦快哉 356
附 录
“宁静默默致远” 365
代跋:日月岛放飞 370
|
| 內容試閱:
|
生命的序幕
我一直说不清我出生在哪儿。这事从侧面证明,我的降生平淡无奇,既没有府第烘托,也没有名医院名产科大夫背书,就像大地上多了一粒灰尘,任谁,都懒得去理会。连最亲密的家人,也绝口不提。只有我本人不甘埋没,曾撰文钩玄索隐。首先确定,我老家是阜宁县陈良乡,这是板上钉钉的。其次,陈良乡在划归阜宁县之前,隶属于建湖县,这也确切无误。我小学时填表格,起初籍贯写的建湖,而后改成阜宁。但是,近来翻阅盐阜地方史,愕然发现:射阳县创立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它早期的辖境,包括了陈良。两年后我出生时,陈良仍然归于射阳。就是说,我是地道的射阳人,是它的第一批新生代土著。
确定我和射阳的“血缘关系”,并不等于就能确定我具体的出生地。选项依旧有两个:陈良与合德。陈良是祖居的老家,合德是祖父创建的新家。这两处地方,一在射阳之西,一在射阳之东,相距一百多里。我出生时,究竟是在陈良,还是在合德,始终是个谜。
我也说不清我是出生在船上,还是岸上。因为老家也好,新家也好,似乎都没有父母的房子,他们住在船上。这么说,我是肯定出生在船上的了。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合逻辑。老家,是曾祖父创下的基业。曾祖父过世,祖父接手。祖父迁走,父亲是长子,理应有所继承。再说,一条小船,来来回回在苏北和上海之间跑单帮,哪里还能容得下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岸上必然有房子,我当时太小,没记住。
母亲有次提到我出生后的“闹腾”,透露了可能的信息。母亲说:“你生下来后,总是哭,总是哭,白天黑夜哭个不停。迷信认为是前世阴魂作乱,不愿转世投胎。那天,你爸爸拿了一个畚箕,把你装进去,撂到屋后的垃圾堆。你一下子不哭了,从此变得很乖。”
母亲这里提到的“屋后”,究竟是谁家的屋后呢,难道不应是父母的吗?
我啰嗦这些并非出于矫情,实在是,一个人出生的地点,关乎他未来的命运。
我最早记得的事,是一岁多一点时的。这话说出来,恐怕谁也不信。大家知道,三岁以前的事,是记不住的,仅有极少数例外。我的一则记忆,恰恰就属于例外:那是大热天,那是一处旷地,地上有一堆火,火上烤着小猪,一帮穿黄衣服的男人,围着火堆忙碌……猪烤熟了,众人用刺刀挑着,大口撕咬……面目狰狞,火舌四窜。
我说不出自己当时是多大,也不晓得那是什么地方,什么人。若干年后,二姐告诉我:“那是日本鬼子,地点在爹爹(祖父)家西边闸口旁的河湾,猪是从陈爹爹家抢来的,毛都没刮,就搁在火上烧。大人远远地站着望,小孩子胆大的,走近了看。我十岁,你两岁,我驮着你,也凑过去瞧热闹。突然,不知哪儿飞来一团烂泥巴,正好砸着一个鬼子的鼻子,吓得他把嘴里的猪肉都喷了出来。跟着又飞来一块碎砖头。鬼子慌忙集合,排成两队,端着枪,四面张望。我怕出事,驮着你离开,你舞着手,不肯走。吃晚饭时,听爸爸和大哥讲,鬼子已经撤出合德,朝盐城方向移动,看形势要垮台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与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竟然在这么小的年纪照面,那狰狞而又狼狈的形状,就此在脑海定格。我也没想到,我后来大学的专业是日语,每逢和日本人打交道,眼底总会浮现那张“老照片”。日本侵略军溃败前的一幕被一个婴儿记住了,记住了而且终生不忘,这是天意。
二姐说我两岁,是虚岁。查射阳县志,日本侵略军是一九三九年冬天进驻合德,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仓皇撤退(半个月后,日本天皇就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的我,满打满算,仅一岁零三个月半。
两岁的事我说不出,缺少特别的参照物。也许哪一天我会忽然抽出一根线头,一扯一大串,这会儿还不行。三岁,四岁,五岁,那印象就多了,密密麻麻,重重叠叠。重叠得最多因而也记得最牢的,是回老家。一条水路,从合德到陈良,途经中兴镇、陈洋、小关子、老屋基、沟墩。射阳是老区,一九四六年实行土改,我家是贫农,分得十一亩水田。父母那时已移住合德,田给三叔父代管,每年栽秧、割稻,都要回去。平时我是跟着祖父祖母过,趁着这机会,父母也会带我回老家玩一趟。
老家建在高墩,南临马泥沟河,传说唐王李世民东征,在此留下御马的蹄印。西傍一条小河,无名。放眼四处俱是河道,密织如网。墩子上一排草房,坐西朝东,北边住的是三叔父家,南边住的是三祖父家。门前长着两棵老槐树,那真是高,在幼小的我看来,简直钻入云霄,我曾经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地想过,要把多少棵老槐树连接起来,就能爬到天上。
老槐树予我最早的美学诱导,来自它的整体长势。有一天我偶然观察到,老槐树是长在墩子东边的,枝枝丫丫都朝东南倾斜,大人说,那是跟着太阳跑的,但是它的根须,没有向东南延伸——东边悬空,南边还有余地——而是向西北蜿蜒,一路挺进到三叔父家的墙脚,有一截露出地面,三叔父把它深埋进土,顺便给拐了个方向,朝东北,免得拱坏屋基。瞧,枝枝丫丫向东南发展,根根须须却朝西北爬伸,树木天生就懂得生存哲学,越是高大,越讲究平衡。
屋后是一片竹林,细瘦,茂密,挺秀,砍下来可以作篱笆、竹帘、钓竿、风筝、竹蜻蜓——最后一项是我的手工课,我是笨,制出来的玩意儿总是飞不过别人。
父亲有项绝技,把细竹竿竖在右手拇指外侧,来回大幅度晃悠,竹竿就像被拇指吸牢,中途绝不会落下。父亲甚至能将扁担搁在右小臂内侧,如是表演。我让父亲教我,怎么教也学不会。父亲说,这要用巧劲、趁劲。啥叫趁劲?不懂。长大后才豁然:一切高超的表演都是艺术。
高墩北边是牛棚,牛棚北边是水车。牛是农家的坦克,当它犁田,我跟在后面吆喝,恍若有坦克大兵的洋洋得意。踩水车是大人的游戏,一般四人一组,双臂担在横杠上,双脚踩动脚拐,说说笑笑,快活郎当。小孩子无份,每想尝试,大人总说:去,去!等再吃十年饭。
十年饭是多少碗啊?好想赶快把它扒拉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