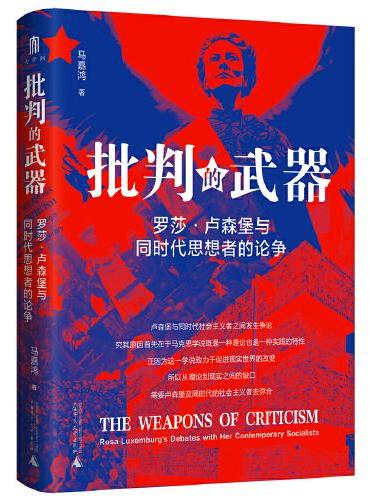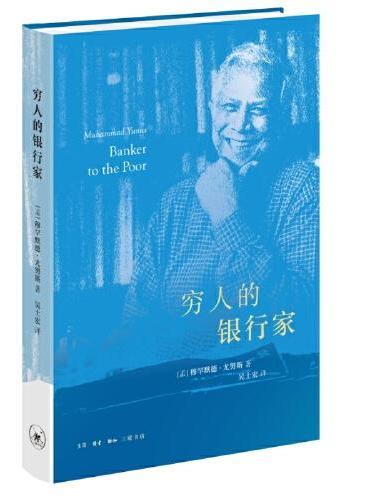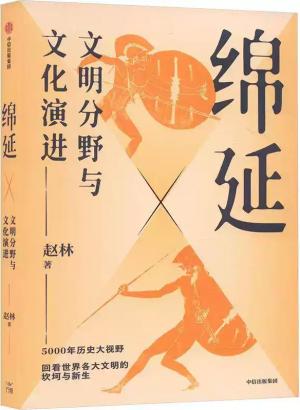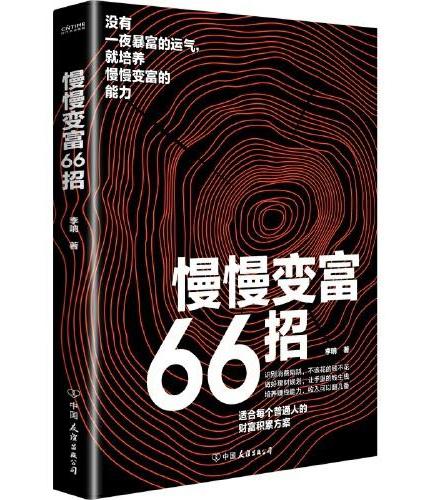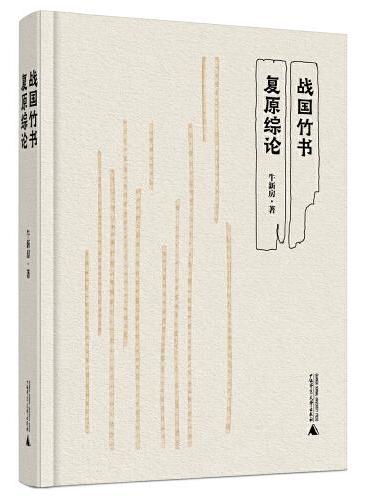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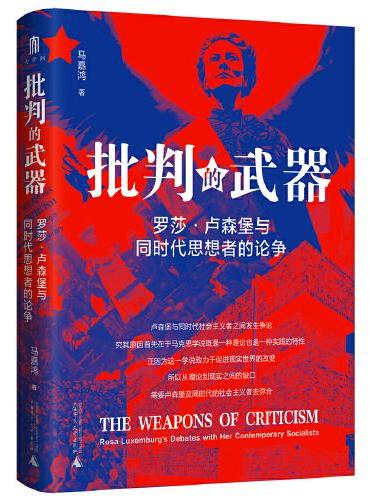
《
大学问·批判的武器:罗莎·卢森堡与同时代思想者的论争
》
售價:NT$
449.0

《
低薪困境:剖析日本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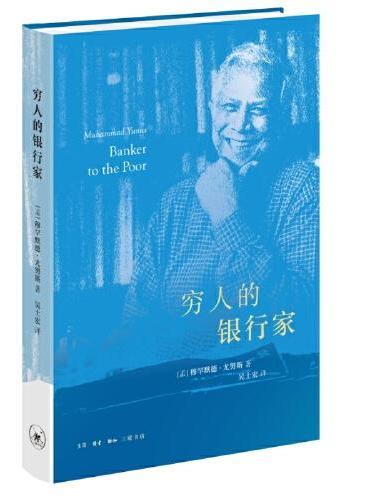
《
穷人的银行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自传)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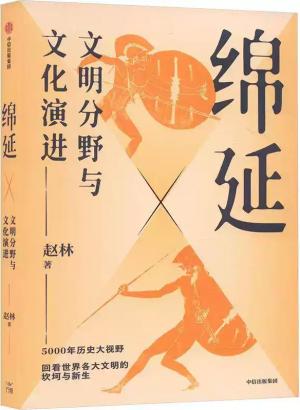
《
绵延:文明分野与文化演进
》
售價:NT$
301.0

《
三神之战:罗马,波斯与阿拉伯帝国的崛起
》
售價:NT$
367.0

《
法国通史(全六卷)
》
售價:NT$
44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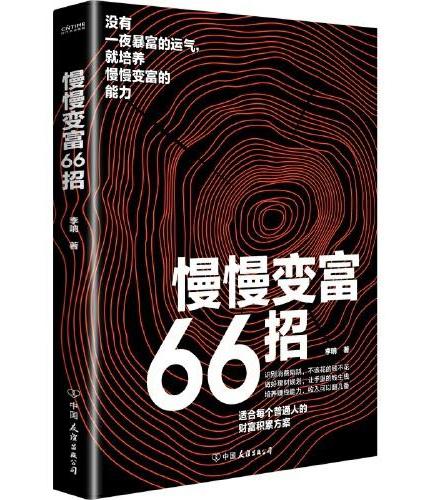
《
慢慢变富66招
》
售價:NT$
2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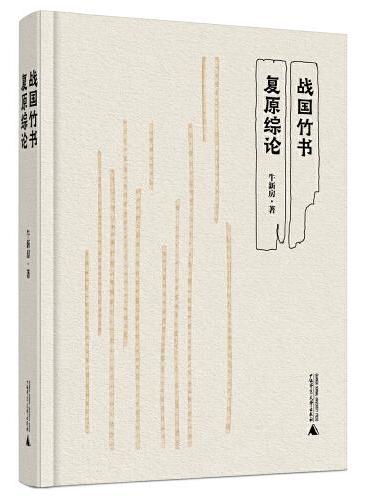
《
战国竹书复原综论
》
售價:NT$
449.0
|
| 編輯推薦: |
“我在精神科从医十多年,你有什么想问?”
真是执业医生,不会读心术。讲的都是真事,不搞猎奇,只有唏嘘。
我的世界,一边是“耶稣”、狼人、活死人、疫苗先知等患者(但他们通常并没有醉鬼危险);另一边是统计上更易自杀和罹患精神障碍的同行,证据薄弱的理论和带有权宜色彩的疗法,资源越配越少、加班和检查却越来越多的体制,更有着爹家暴、妈酗酒、奶奶失智、叔叔精神病的我自己……可我还是坚持了这么多年,还要继续坚持……
★ 是荒诞处境凝结为段子,还是精神疾病是喜剧的本质?
入职第一天学格斗,年终科室聚餐时欢谈如何自杀;上峰检查,最在意是陈列消防说明……没有吐槽和自我吐槽,何以在此间安身?
精神困扰和喜剧似乎有很深的联系。喜剧人六兽说:“我们都是带病上岗。”作者的咨询师说:”我来访里的几个喜剧演员是我最抑郁的病人。可能只比精神科医生低一点儿。“巧了,作者既是精神科医生,又是脱口秀演员……
NHS的医生写出了《打开一颗心》《脑子不会好好睡》《救命啊》(及本书)等众多佳作;而它引起中国人的关注,竟是因为“NHS面临有史以来最大危机”“NHS越来越崩溃”?真的是文章憎命达?读罢本书,你会
|
| 內容簡介: |
借着二十多桩遭遇,作者从内行视角呈现了精神医学行业,更隐隐勾勒出自己三十多年的人生。
重症精神病患者的苦楚,外人往往难以理解:温和的园丁因精神病史而遭社会排斥,终日请脑内的声音和自己作伴;妄想的儿子不知自己发病时要杀了妈妈;男子先跳桥后趴轨四肢尽断却依然活着;对分裂症管用的药让猛男胸部淌奶……另一方面,精神医学研究并不成熟,对患者的帮助依然有限甚至有时适得其反;精神科在医院各科室中又是资源少风险高,科内医生往往有更高的精神问题风险乃至患病率,连某位主任也不得不因重度焦虑而休长假——留下在岗者继续7*24运转。此时,遑论救人,精神科医生又如何自救?
作者自己,则是家族有酗酒、暴力、失智、精神病等多种精神、神经障碍史,于他常是阴暗的记忆,也阻挠着他建立、维护亲密关系。抱着帮助家人和自己的心愿选择了精神科的他,只是越发无助地发现众生皆苦,万事皆难。
尽管如此,作者依然选择在这个行业中坚持和奋进,凭着信念、人性和苦中作乐讲地狱笑话的喜剧精神,“救一只海星是一只”。
|
| 關於作者: |
著者:
本吉·沃特豪斯(Benji Waterhouse),英国精神科医生,供职于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下,从业十余年,亦就精神病学问题为公共媒体供稿或接受访谈。同时还是获奖的单口喜剧演员。
译者:
高天羽,笔名“红猪”,长期任《环球科学》杂志与果壳网翻译,出版译作数十种,如《打开一颗心》《神经的逻辑》《五感之谜》《开颅》《世界之门》等。
|
| 目錄:
|
前 言 1
序 章 7
第一部? 前驱症状
01 欢迎会(先学柔道) 15
02 格利克大夫(再学狠心) 29
03 芭芭拉(“我来和明星结婚的”) 46
04 格拉迪丝(“我是死人,不吃东西”) 59
05 安 东(“药我没吃”) 74
06 贝 琪(我奶奶) 84
07 贾迈勒(“你们迫害黑人”) 91
08 格雷恩(“有一阵子没来耶稣了”) 103
09 约瑟夫(精神分析师) 115
10 圣诞节(说好的救世主降生呢) 121
11 利 昂(手和脚都从身上断开了) 134
第二部? 疾?病
12 科顿大夫(“我是在你前一天生的”) 151
13 黛 西(32 卷锡纸) 166
14 马尔坎(“他安全吗”) 177
15 埃丝特(“你样子还蛮可爱的”) 193
16 佩 姬(“你已经是老油条了”) 198
17 塔里克(“为了这家伙我也得活下去”) 212
18 塞巴斯添(金融城职场人) 227
19 罗 宾(“吃的全是金属味”) 246
20 托马斯(“如果是你的家人”) 260
21 本 吉(好像知道为什么想做精神科医生了) 275
22 出岔子了(平常只在白天见到的病人) 281
第三部? 恢?复
23 新冠病毒(这家里有个医生) 287
24 安格斯(我双脚腾空) 300
25 费 米(“把你们全杀了”) 308
26 海 星(不逃避) 321
27 逃离精神科(“应该办一场乒乓球赛”) 326
28 家 人(痛快地哭) 337
29 新开始(谢谢你) 354
致 谢 367
资料来源 371
译名对照表 373
|
| 內容試閱:
|
我有一次坐飞机时,听到广播里说机舱内有紧急医疗状况。从医学院毕业后,我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这个大放光彩的机会不能放过。
“让我过去,我是医生。”我边说边从聚集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像个电影中的英雄。
过道上,一位脸色发红、眼镜起雾的大好人已经对一具人体做起了心肺复苏,他冲我上下打量一番,问道 :“你是哪一种医生?”
看来竞争之激烈超出我的预料。
我告诉他我是精神科医生。
他挑了挑一边的眉毛,视线转回病人,咕哝了一句:“我嘛,是急诊医生。好吧,如果我让他恢复了心跳,你就来问问他的童年经历好了。”
诚然,以当时的情形,不能为病人恢复脉搏,一切全都免谈。不过这次事件也反映了至今仍很普遍的一种心态 :精神健康不像身体健康那么重要。
经过报纸、电台、电视、播客、推特和TikTok的宣传,公众对精神健康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然而目前大家关注的仍只是精神问题中较为温和、较易接受的那一端 :焦虑、抑郁、强迫障碍(OCD)、孤独谱系障碍(ASD)或是确诊者越来越多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
至于那些带着慢性、重症标签的障碍,则被认为更加糟糕、丑陋乃至可怖,得到的关注也比较少,比如精神分裂、双相、人格障碍或者物质滥用障碍。
这本书写的是有后一类问题的人。对他们来说,在冷水中游泳和正念填色多半不会奏效。我希望做个潜伏者,记述我在这个医学中最神秘也最具争议的领域执业十年的经历,也希望纠正一些对于精神科的病人、医生和医疗活动的错误认识(就比如,诊室里其实没有软包墙)。
许多人依然相信,抑郁是“化学失衡”引起的,或者双相会使人成为创意勃发的天才,要么精神分裂患者都是挥着斧子的杀人犯,因为他们“脑子分裂了”。
你知不知道,精神科医生(psychiatrist)、心理咨询师(psycho logist)和大神儿(psychic)有什么分别?因为电视的误导,大多数人认为我要么会读心术(那是大神儿的营生),要么能对付吃人的连环杀手(那是精神法医干的事),要么向躺椅上那些富裕的神经症患者询问他们母亲的情况(那是精神分析师,psychoanalyst)。实际上,作为一名普通成人精神科医生,我平日(经常还有平“夜”)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帮助,至少是尝试帮
助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
常有人说,精神疾病和断一条腿没有什么两样。我自己在医学院攻读六年之后又做了两年的低年资医生 ?,那段时间里我治过许多条断腿,主要在急诊部,往往还是在急诊部的过道里。
当时我看过的断腿,要么是一处歪斜的变形,要么运气较好,是有一截方便诊断的骨头戳了出来。给伤者查体时,我能用手摸出骨折的地方(虽然伤者可能更想我别摸);如果摸了还是不能确切诊断,我还可以用验血来排除引起骨头疼痛的其他严重原因,比如骨髓炎 ;或者我也可以要病人拍个X光片,当场把伤情确认得黑是黑、白是白。断腿的有效疗法也是现成的 :我会将伤者转给骨科医生,他们会用螺丝修复断骨,再敷上石膏固定,要不了多久,伤者就又能玩撑竿跳了。
可是精神科就不一样了。你看不见妄想障碍,摸不出双相,抑郁靠验血验不出来, X 光片也拍不出精神崩溃的人心中的参差裂缝。你也不可能把听诊器贴到某人头上,去听他幻听到的说话声。
那么从哲学上说,我们如何在所谓“正常”和“障碍”之间划出这些武断的界线?毕竟“正常”和“障碍”都会随时空而变动。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同性恋都还被认作精神疾病,要用厌恶疗法“治疗”。对于那些冒险走到我们的“正常”观念之外的人,又该如何治疗他们?而当一个人自认是耶稣,试图在当地泳池的水面上行走时(见第08章),真的还有时间留给我们思索这个问题吗?
另一处复杂在于,那些与现实脱节的病人,往往认识不到自己病了,因而自然也不愿意接受治疗。和他们相比,一个脚掌扭向身后的男子至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实际层面的隐患。从统计上说,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会在一生某个时刻遭遇精神健康问题,虽然精神疾病在英国的全部疾病负担中占比达 28%之多,它收到的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拨款却只有 13%。更糟的是,虽然对精神健康支持的需求不断增加,但由于精神卫生“去机构化”(社区康复)变革以及近来的财政紧缩趋势,英格兰的精神科病床数从1988年的6.7万张降到了今天的1.8万张。
于是,紧急病房的月平均入住率超过了100%,满员的医院在病房的沙发上开辟简易“病床”,在杂物间、禁闭室乃至医生办公室里摆放行军床。有时病人要被送到近 500 公里之外才有最近的医院病床。 2019 年,精神科病人为了躺上“区域外”病床而旅行的路程,相当于环绕地球 22 圈 3—你能想象让某个拄拐杖的人这样奔波吗?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治疗病人的—和伍迪·艾伦电影中那些静谧的曼哈顿治疗室判若两个世界。
NHS的许多员工都用苦中作乐来对付这类窘境,所以我偶尔也会在书中说几个阴间笑话,希望你别介意。我认为喜剧是一件宝贵的工具,它能帮人应对艰难的课题。况且,如果在为精神健康争取与身体健康平等待遇的斗争中,我们因为在人体的孔洞中发现了五花八门的东西而开怀大笑,那我们偶尔也必须承认人心的黑暗与荒谬。比如有人要过量服药,服99片扑热息痛——因为他买了100片却掉了一片在地板上,又怕弄坏了肚子所以没有捡起来吃掉。
除了可耻的经费不足、人员短缺、粗疏的药物治疗、病人等候医治等得比医院网络加载用时还久以外,我希望你也能在本书中找到一些乐观的种子。
最后,这本书也是在写我自己,写为什么竟有神智正常的人选择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希望它能使你们明白,在医生那一袭白大褂下面,或者就我来说是那件手肘打了补丁的外套下面,同样是一个人。并且在所谓“理智清醒”和“精神疾病”之间的那条模糊界线,并不总能由医生清晰地划定。
序章
凌晨4点。员工电水壶的开关轻轻弹起。我在杯子里放了两个茶包,搞个双倍浓度,再倒入滚水,还有一大股标明属于“安琪拉”的脱脂奶,我知道这时间此地就我一人。
在顶楼,我在磨破的地毯上拖着沉重的步子,经过空荡荡的医生办公室继续朝里走。我年资还低,办公室只能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橱柜间,其实就是一只大柜子。我试过在办公桌上放一盆植物来增添一点个性化,多一点生气。可那是一盆仙人掌,一种沙漠植物,只靠最少的水分勉强生存,用来比喻NHS再合适不过。我们的团队秘书谢丽尔是个园艺迷,她总是把我的仙人掌移到过道里,说它需要自然光。而我每周五天一直待在这个没自然光的角落,倒似乎没人关心了。
手上的茶杯传来的温暖是一份小小的慰藉。我吸溜几口茶水,坐进椅子开始这一班的工作,之前干了七个小时,之后还要再干六个。我已经接待了八个病人,隔离了其中五个,病历记录还一条没写。
……
我对休眠的电脑感到一阵妒忌,伸手把它唤醒,接着揉揉眼睛,开始记录方才接待的患者 ……我才打了几个字,传呼机就响了,又一次。
“真他妈的!能不能……别……呼我了”我朝着那只小黑盒哀求。幸好在拿起电话前的几秒钟里,你说什么对方也听不见。
我在办公桌的电话上狠狠摁下呼机屏幕上发亮的四个数字,接着变戏法似的换了一种人格。
“你好,精神科,有什么可以帮你?”
电话彼端,一位直率而烦躁的急诊部女护士长给我转了个病人过来。“有个人给你。”她说。
或许我当初应该做外科医生。从来没人这样对他们说话。
“嗯?有个什么?”
“一个精神病人,亲爱的。你是今晚值班的精神科主治吧?”
“嗯,是我。能再说详细点吗?”
电话中,我听见一声恼怒的叹气。接着是一阵翻记录的沙沙声,背景里有脚步声、轮床的吱吱声,以及安慰医护人员病人还活着的机器哔哔声。
“……34 岁,跳自杀桥的。”护士长说。
我那缺乏睡眠的大脑开始游弋。
市政是不是该给“自杀桥”重新取个名?更振奋一点,像是“别想不开高架”或者“会好的天桥”?
“沃特豪斯大夫?”
“抱歉,我在。”我感觉这个病人或许能打发走,那样我就能处理一些文件,甚至喝掉这杯茶了,“这类病人不该由急救人员处理吗?人应该……还活着吧?”
“哦,因为你空着啊。病人运气好,掉在了一片荆棘丛里。
表皮有好多划伤,都叫整形科缝好了。一只手腕骨折,骨科也打好石膏了。就等往你那儿送了。”
我看了一眼堆积如山的文书。还有一张牌可以打,一个把这位病人推给别人的机会。
“人是从自杀桥哪一侧跳下去的?”
“啥?”
“是北边对着教堂的一侧,还是南边对着购物中心的一侧?
因为这座桥是南区和北区应急小组的分界。我们是北区的。”
“老天爷……”她不屑地嘟囔了一声。
我告诉自己,这不是冷血地置人命于不顾,而是NHS就是这么组织的。我自己已经忙得上气不接下气,为什么还要接收可能属于另一支团队的病例?这就像是飞机即将坠毁,你永远要先自己戴好氧气面罩,然后再去帮别人,对吧。
我听见护士长在翻救护车记录,于是决定抽空看看我的手机……
“好,找到救护车报告了。”护士长宣布,“报告说病人身上酒气强烈……说只想死……最好的朋友昨天死了……哦,就在这儿。病人是被一个遛狗的人发现的,地点在圣马丁教堂的停车场。所以就是你的!”
我×。
我打开全国网上数据库 Carenotes(“诊疗记录”),它好比精神病人的脸书。
“病人的NHS号是多少?”她报出编号,我敲进系统,点下“搜索”,趁老掉牙的电脑载入的时间喝了一大口茶。
屏幕上显示出了名字。是我认识的人。
如果生活是一部电影,此刻我的杯子就该失手掉下,碎瓷片以慢动作在地板上四散溅出。我多半还要发出哀号,尖叫着扯几把自己的头发。但眼下的气氛一点也不电影。我早已学会了用机器人般的职业态度吸收最极端的情绪,管它是震惊、恐惧还是悲伤。感情迟钝了,工作就容易了。
“马上过去。”我不假思索地说,然后匆匆向急诊部赶去,将那杯冒着热气的茶水留在了办公桌上,周围是其他喝了一半的茶水堆成的坟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