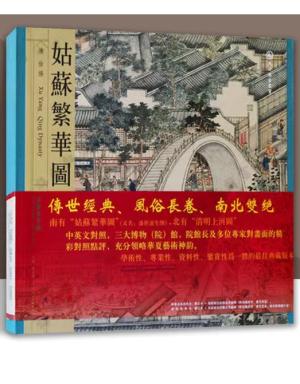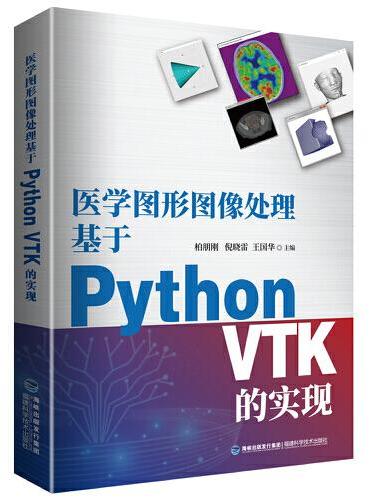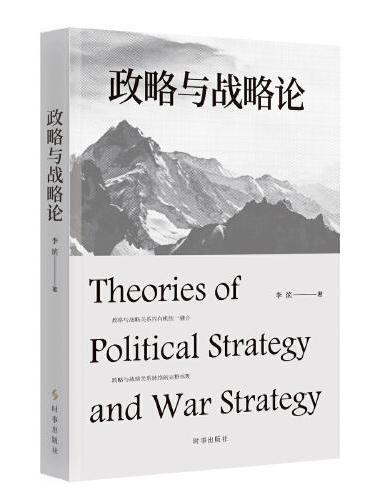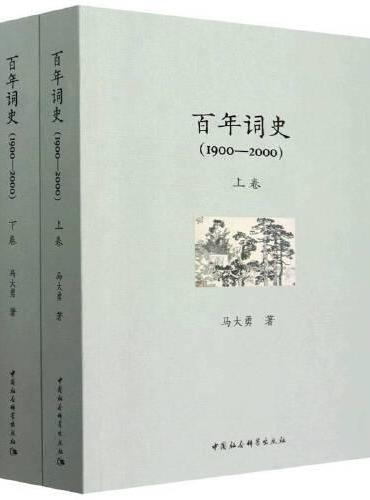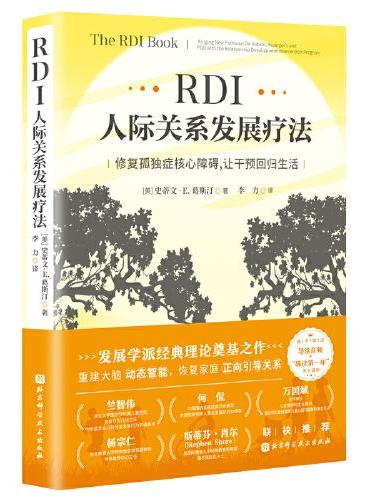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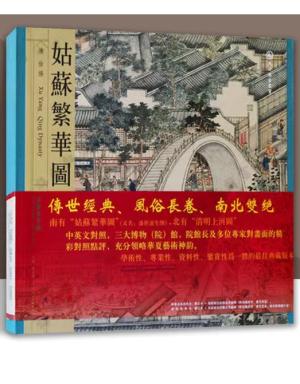
《
姑苏繁华图
》
售價:NT$
3190.0

《
人的消逝:从原子弹、互联网到人工智能
》
售價:NT$
484.0

《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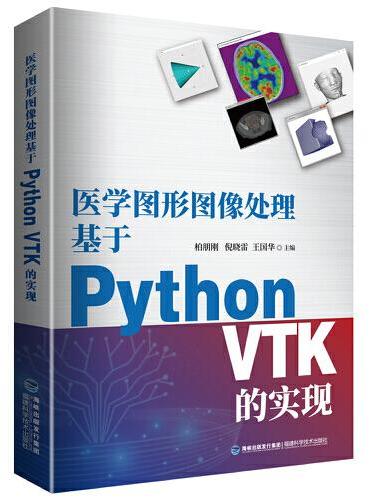
《
医学图形图像处理基于Python VTK的实现
》
售價:NT$
760.0

《
山家清供:小楷插图珍藏本 谦德国学文库系列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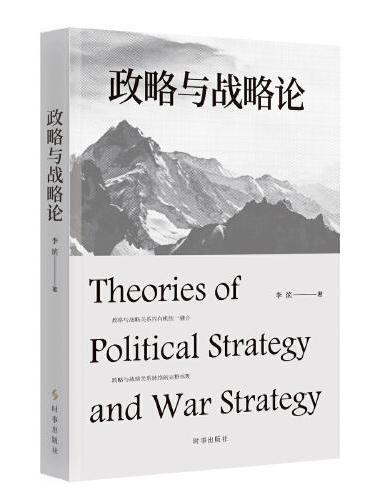
《
政略与战略论
》
售價:NT$
6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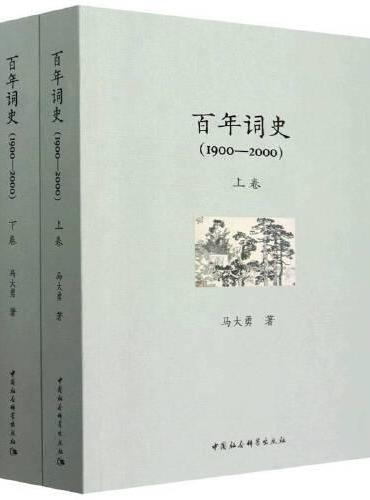
《
百年词史-(1900-2000(全二册))
》
售價:NT$
15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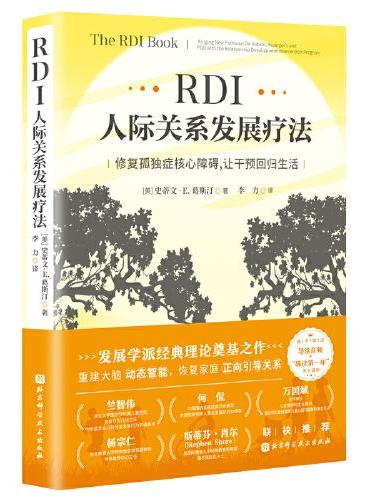
《
RDI人际关系发展疗法:修复孤独症核心障碍,让干预回归生活
》
售價:NT$
454.0
|
| 編輯推薦: |
消失,会是真的消失吗?消失或许是另一种生长。
降泽从树洞里消失了,凹村人往土里挖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植物时在地底下消失了,一个刚出生的娃在阿妈的眼睛里白白消失了,一座从水上漂下来的村庄在满是星辰的夜色中消失了,一位骑着瘦马的男人从俄色花的花香中追着一群向北走的蚂蚁消失了,贡布像坠落在黄昏里的一只大鸟消失了……
他站起身,不紧不慢地从怀中取出古铜色的驼铃,用额头虔诚地触碰手柄上的羊羔皮,接着举起驼铃,在风中有节奏地摇摆起来,哐当,哐当,哐当……他离我越来越远,远处的羊群看见他的离开,河流一样朝他涌去,那是一条可以流向任何地方的河流,那是一条柔软得如达乌里秦艽花瓣一样的河流。
|
| 內容簡介: |
|
散文集《消失的故事》,是以一座朴素的小山村凹村为写作背景,旨在结合实际,书写藏地人们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山乡巨变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思想带来的改变。此本散文集,共收录凹村故事三十个,故事中的人物相互牵扯,又各自独立,丰茂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座村庄的各种面向,当各个面向汇集到一起时,山乡巨变下一座朴素村庄的变化,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感觉到,这是一座不一样的村庄,但同时又让我们觉得这座村庄似乎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近到可以是任何一个人的故乡。《消失的故事》中的“消失”,并不是表面意义上的消失,而是一种新的生长和重生,是一个新的起点和开始,是一种希望和期许。
|
| 關於作者: |
|
雍措,藏族,四川康定人,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在全国公开刊物发表散文、小说作品一百多万字,作品散见于《十月》《花城》《中国作家》《民族文学》等期刊,出版散文集《凹村》《风过凹村》,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四川文学奖“特别奖”、三毛散文奖、孙犁散文奖、《花城》文学奖散文奖、《收获》无界漫游计划入画散文奖等奖项。作品翻译成朝鲜文、蒙古文、藏文等。有文字收入各种选本。
|
| 目錄:
|
孤独与疼痛的絮语 次仁罗布 /1
第一辑 光把他陷了下去
在还没有大亮起来的夜里 /3
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植物 /11
从一个人的心里消失 /16
是谁拖住了春天的脚步 /32
光把他陷了下去 /42
水上村庄 /47
越来越深的黑 /58
一条可以流向任何地方的河流 /63
第二辑 草带歪了一群羊
还你一个最好的秋天 /73
躲在很大的白里 /78
追踪 /84
暗中站起来的东西 /98
降泽 /106
一点一点消失的措姆 /110
草带歪了一群羊 /114
月光铺就的阴影 /118
第三辑 坠落在黄昏里的大鸟
坠落在黄昏里的大鸟 /133
荒芜中缓缓升起的炊烟 /137
大雪里归来的人 /141
天上有个洞 /149
村子越来越轻了 /155
寡淡的村子 /164
被风吹乱的旺堆 /171
第四辑 响在身体里的垮塌声
寒冬落日 /189
最大的黑 /198
响在身体里的垮塌声 /204
带着重量地垂向大地 /216
大树里的声音 /221
今天的太阳 /231
有事发生 /244
最后一种消失 /258
|
| 內容試閱:
|
孤独与疼痛的絮语
次仁罗布
我喜欢上雍措的作品,是在她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时。那时,作为《西藏文学》的编辑,恰在那段时间收到了一篇题为《凹村》的小说。初读这篇小说,我被那种冷厉、硬朗、剔透的文字所折服,暗暗惊叹作家的文采,同时也在佩服那些富有哲理的句子。这是雍措作品留给我的最初印象。说实话,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男是女,光读作品我心里一直认为是个男的。好在没多久,西藏作协跟甘孜州文联,在拉萨为两地获奖作家开了个座谈会,第一次见到了雍措。让我难以接受的是,雍措竟是一名柔软的女性,这跟我阅读中的那种风风火火,深邃的哲理思考,刀刃般的凌厉文字,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自那次拉萨的相见之后,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如今。每次我跑到康定,都要跟甘孜州的作家们酩酊大醉几次,每每不胜酒力的雍措,都会陪着我们。在更多的接触过程中,雍措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个开朗的人,可她在愣神的刹那间,我又从她的眼神里捕捉到了忧郁,从她的豪爽中,也能嗅出一丝无奈与柔弱。也许这些都是我的一种错觉,但我对雍措的文学创作一直持一种观点:雍措会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只是现在还没有被主流界所关注到。也许会有人说,我的这句话是诳语,但是我在2016年读到发表在《西藏文学》上的《凹村》时,就说过这类的话,至今我都没有改变过这种观点。一切让时间来检验吧!
藏族文学史上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独独雍措是跟她们完全不同的一位,甚至我想用独树一帜来形容她。与一些藏族女性作家相比,她在作品里是在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而其他作家是在描摹和呈现;她的世界荒诞却真实,而其他作家的世界现实却缺乏诗意。从这一点来讲,雍措的未来更加地辽阔,雍措的世界更加地绚烂。
散文集《消失的故事》,再一次让我感到震撼。虽然依旧以“凹村”为根据地,展现那里的日常生活,乡土风情,可与以往的凹村抒写表达不同的是,这是一组群雕之像,掺杂了魔幻现实主义叙述,是众多凡夫俗子的孤独与疼痛。在这本散文集中,雍措借用一种模糊化的时代背景,讲述凹村里发生的那些变化,很多篇章我们都可以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里来解读。偏偏有几个故事,却让我们分明感受到时代的气息,譬如,散文集的第一篇《在还没有大亮起来的夜里》,讲的是从凹村到城市里去打工的一群人,这些人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到各大城市去挣钱,这种情况只有改革开放后才能出现,但作品里没有只言片语来交代这个时代,明眼人却能在文字的底下触摸到这个时代;《水上村庄》以牛配种起始,这种引进优良种牛,对当地牛进行改良,也是上世纪末才有的一种现象;《躲在很大的白里》讲述的是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国家把目光从城市建设,投入到乡村振兴,为农村实现富裕而修建公路,村村通路在这篇作品里被表现了出来。作家有意把时间节点淡化,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界限,在阅读时会有意无意地框定在那个时限里。这种欲擒故纵的手法,为她的想象给予了合理性和真实性,要不我们无法接受和理解《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植物》《越来越深的黑》《坠落在黄昏里的大鸟》等。雍措营造的这种荒诞、怪异,比写实更能牵动人心,更能令人惊诧,更能让我们对现实感到震惊。《从一个人的心里消失》写的是“我”和“阿妈”之间的故事,我的出生没有给阿妈带来快乐,反而让她不快乐起来。我与羊群相伴,是羊喂养大了我,我也不知道阿爸是谁,阿妈对我来讲是个陌生又冰冷的人。在缺失母爱中羊群把我带大,直到有一天阿妈再次生娃,当得知是个男娃时,她终于笑出了声。读到这里让我感到震惊,雍措虽然写得很隐晦,但我读到了在凹村作为女人的命运,直到阿妈二胎生出一个男娃,她才觉得生出了一个人。足见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一个小村庄里的卑微,足见偏僻山村里固有的男尊女卑思想有多么严重。这是一个有关孤独,但又有些许温度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似乎都没有对错,每个人的内心都隐藏着一片荒漠。故事荒诞中让我们看清了现实,看到了本真的乡村。
阅读雍措的作品时,我的脑海里一直映现着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虽然两位作家都在讲一些不可理喻的荒诞事情,但奈保尔给我们留下了幽默与些许的光亮,雍措却用一种决绝和冷酷,让我们感受到了凹村的孤独和每个人的疼痛,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对这个世界重新审视。雍措的精明之处在于她向福克纳致敬,永远耕耘那片邮票大小的村庄,给读者构建了一个叫凹村的地方、凹村的社会组织、凹村的一群众生,重构了一个文学地理意义上的村庄,但我们始终确信有这么一个村庄,因为所谓的这个凹村,熔铸了当下中国藏区许多乡村正在发生的深刻
变化。
雍措的语言也是极具特色的,这部作品里有许多令人记忆深刻的文字,比如:它们站着做梦,走着做梦,叫着做梦,梦被它们的身体和叫声举得高高的,拉得长长的,只要它们经过的地方,都有一只羊留下的梦。站着做梦,走着做梦,叫着做梦的羊,把一场自己的梦,从家门口铺向山顶,铺向草原,它们在梦里早早修建了一条通向凹村,通向草原的路……我在这里不再赘述,请读者自己去阅读。
最后,我用雍措今年在《花城》获得的花城文学奖散文奖的授奖词来结束我的这篇序言:雍措的写作入乎凹村之内又出乎凹村之外,体现了尤为开阔的散文精神,将个体经验升华为集体记忆,探求存在之思,观照现实命运。文体探索与思想深度相融合,民族表达与共通体验兼顾,更新了读者对康巴文学的期待。
第一辑
光把他陷了下去
在还没有大亮起来的夜里
我忘记那是什么日子了,凹村走出去很多年的人,都在那段阴雨绵绵的日子回到了凹村。
一条很久没有热闹起来的土路热闹起来了,一个很久没有点儿说话声的村子活泛起来了,一座座很久没有人住过的泥巴房夜里到处亮着灯,灯光从每家每户的木窗户里透出来,忽闪忽闪的,仿佛灯在夜里也不敢相信自己还会亮似的。
其他村子跑得快一点儿的家畜像马呀,牛呀,狗呀,都从自己的村子跑到凹村来凑热闹,他们想来看看一个突然热闹起来的村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从自己的村子偷偷跑出来时,尽量不让村子里的人看见自己正火急火燎、兴头十足地往另外一个村子赶,他们怕村子里的人看见自己对另外一个村子那么感兴趣,会彻底对他们灰心丧气。人一旦对自己养了几年或十几年的家畜灰心丧气了,整个村子都会有一种灰心丧气的气味飘在空中。空气会受到影响,土地会受到影响,树木会受到影响,村子里的风会把这种灰心丧气的气味,刮得到处都是,让别个村子的人都知道有一个村子现在已经灰心丧气了。
为了更好地隐藏自己,那些从自己村子里跑出来的家畜,把平时常走的一条出村路,绕着走,逆着走,歪着走,把留在地上的脚印走得不像一个脚印,他们想让人误以为,那不是自己养了几年或十几年家畜的脚印。不是自己的脚印,人就放心了,人想自己养了几年或十几年的马呀,牛呀,狗呀,可能只是一时偷懒或调皮,睡在了哪棵俄色树下或哪片虫草山上,谁都在自己的一生里,有过一次或几次谁都不想见,谁都不想理的时候。人理解这一点,就不会去怪罪自己养的马呀,牛呀,狗呀了。
人不怪罪他们,有些跑不出村子的同类,会怪罪从自己眼皮底下跑出去的他们。这些同类跑不出去的原因有很多,腿短、力气不够、眼睛看不见、被束缚、怕主人发现等等,他们对着那些一心想去凹村凑热闹的同类发出恼怒、不甘心、指责的叫声,他们不想眼巴巴地待在原地而什么事情也不做,那样把他们显得太懦弱和无能了。
那几日除了凹村,其他村子也显得不同寻常,只是其他村子的不同寻常在家畜身上发生,而凹村的不同寻常是在回来的人身上发生。
那些从自己村子赶到凹村来凑热闹的家畜,躲在凹村附近的山坡上、树林里,虽然他们费尽心思、想尽办法来到凹村,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凹村是别人的村子,在别人的村子里,他们不敢大口喘气,不敢想走歪一条路就去走歪一条路,别人的村子始终是别人的村子。
那几日,凹村的四周到处弥漫着一种陌生的气味和一声声诡异的喘息声。那些出去多年再回来的人,感觉不到这种陌生的东西,他们早在一个曾经熟悉的村子里,把自己陌生了。
那些回来的人,好像是从四面八方回来的,他们说话的口音都带着四面八方的口音。每个不同的口音混在一起,凹村显得奇奇怪怪,仿佛凹村不是凹村,凹村成了别人的村子。
我一晚上睡不好觉,我的觉被说不清楚的什么东西抢走了。我早早就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木床被我翻来覆去的身体弄得“咯吱咯吱”地响。木床的响声在那几日也响得不同寻常。
我从床上爬起来,在堂屋里走了一圈,在睡觉的屋子里走了一圈,在放粮食的黑房子里走了一圈,在做饭的灶房里走了一圈,走完这些地方,我在自己的泥巴房里再没有可去的地方了。我在这座泥巴房里住了几十年,闭着眼睛也能走上好几十圈。有的时候,我真不想在这个屋子里再走下去了,就像今天这样。我问自己,在这样一个天还没有大亮起来的夜里,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出门走走吧,一个声音告诉我。
我打开院门,木门的“吱呀”声响在倒亮不亮的夜里,像给夜撕开了一道口子。我没再关上那扇木门,我家的门哪怕是在夜里整整开上一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屋里除了有点去年生虫的粮食,再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让别人心动的了。不过我知道,外面回来的人吃惯了外面的好粮食,他们嘴吃大了,味吃重了,再吃不惯生了小虫的凹村粮食,我可以放心地走。
我把自己跨出门的第一个脚步放得轻轻的,我不想让人知道,刚才是我把一个平静的夜打扰了。
不过我又安慰自己,即使有人在夜里听见我刚才的开门声,也没几个人会猜出是我,在还没有大亮的夜里走出了自己的家门。他们走后,我天天一个人生活在村子里,该走的路都被我走尽了,该看的风景都被我看完了,像我这样一个人,绝不会还对这个村子再感兴趣。有人即使听见我刚才的开门声,也在夜里分辨不出那声音来的方向。在一片夜里,声音会拐弯,会变着花样地糊弄人。那些听见我刚才开门声的人,他们想肯定是像他们一样从四面八方回来的一个人,想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走进一片夜里,找寻一些自己曾经丢失在黑夜的东西。
无论怎样,他们都怀疑不到我的头上。
而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在夜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真正的原因是那几天我突然住不惯自己的村子了,仿佛我才是一个真正出去很久,从四面八方回来的人。
拐过两道弯,走过三堵废弃的老墙,我站在天还没有大亮的夜里,累得不行。夜里的累来得比白天要快些,夜自身带着重量。我把手扶在老墙上,我需要一堵老墙支撑我的累。我的手刚放上去,老墙上的土就“稀里哗啦”地往下掉,我想一堵老墙也是在白天强撑着自己,一到晚上那股强撑劲儿过了,真的累和老就出来了。我把手从老墙上缩回来,手僵硬地垂在我的身体旁边,我突然觉得我的手在那一刻离我很远,一种近距离的远,莫名地让我恐慌。
我不想把自己直直地站在天还没有大亮的夜里了。直直地站着,我感觉自己正在夜里丢失自己。那种缓慢地丢失,那种你无法控制的丢失,那种知道自己在丢失自己的丢失,让我无奈和害怕。
我慢慢向有人住着的房子走。那几日,凹村所有的房子里都住着从四面八方回来的人,不会有一座空房子像以前一样空在夜里。我轻轻地走,生怕吵醒那些从四面八方回来的人。吵醒他们,就相当于吵醒了四面八方。当四面八方的声音响在天还没有大亮的夜里,凹村的夜又不是凹村的夜了,凹村的夜成了四面八方的夜。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路走下来,每座房子里都有低低的说话声响在还没有大亮起来的夜里。那些声音很小,是故意不想让人听见的,但还是被我听见了。那些人不知道,我在凹村一个人待得时间太久了,一个人待得太久,眼力和听力都会特别地好。
在还没有大亮的夜里,那些人说着凹村的土话,摆着凹村陈旧的龙门阵,说到高兴时,他们还在夜里偷偷地笑。那笑是凹村人一贯的笑法,我即使没看见他们的笑脸,也知道他们笑的动作,嘴皮上翻,舌头顶着门牙,只有这样的动作才能发出凹村人一贯的笑声。
在夜里,凹村突然回到了很多年前的凹村。很多年前,凹村没有一个向外走出去的人,所有人都待在村子里,所有人都说自己死也不出去,即使死也要死在一座自己熟悉的村子里。
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在还没有大亮起来的夜里,那些回凹村来的人说话声和笑声都很谨慎。他们说几句,马上停下来,笑几声,马上就不笑了。他们在屋里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声音,他们怕外面有像我这样的人,听见他们说着凹村的土话,笑着凹村一贯的笑。自从他们当年从凹村走出去,又从四面八方走回来,他们想自己总该有点变化。如果一点变化没有,他们怕别人说自己在外面白待了那么几年或十几年。如果没有一点变化,这些年走出去,就像荒废了自己一样。他们不喜欢这种荒废自己的感觉。
其实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哪怕他们在外面生活几年还是十几年,外面永远是外面,外面永远活不进他们的骨头里。他们在外面生活,过着外面人的日子,身体看似融进了外面的世界,但外面的世界是否真的让他们融进,自己是否真的能融进外面的世界,只有他们在外面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受到嘲笑,一次次在夜里唉声叹气的时候,他们才最清楚。
他们在外面生活,只是选择了一种背着凹村在活。这种背着,有种逃不脱的宿命感。他们在外面一心想回来,他们住不惯别人的城市。他们早就在外面为回来做打算,他们一天天计划回来的日子,一次次告诉外面认识的人说,自己要回来了。他们在说自己要回来时,说得趾高气扬的,说得洋洋得意的,好像外面的世界还没有自己的村子大,外面还没有自己的村子好。
但一旦定好了回来的日子,他们又开始担心。他们怕有人问自己为什么从外面回来了。他们不知道这个问的人,是从外面回来的还是一直没有离开过凹村。他们要提前想好,如果有人问他们这种话该怎么回答别人。他们不能告诉别人自己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才回来,也不能告诉别人自己融不进外面的世界才选择回来的,他们要脸面,都说人活着是为一张脸。
从外面回来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一种办法,他们用外面的口音说话,说些四面八方的话,说些别人听不懂自己也听不懂的话给遇见的人听。他们在问话的人面前装。装久了,嘴巴就痒,嘴巴痒了也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痒,他们就偷偷在夜里说凹村的土话,凹村的土话能治愈他们嘴巴痒的毛病。一家人凑在一起说,一个人偷偷地说,对着一堵老墙说,面对一片暗说。
我的脚步声很轻,那些从外面回来的人耳朵里装着很多嘈杂的声音,即使他们把要讲的话停在那里,要笑的声音空在那里,他们也听不见我的脚步声。他们在好一会儿之后,又接着上半句说,接着上半声笑。停了好一会儿的话和笑重新接上去,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话和笑,要有多别扭,就有多别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