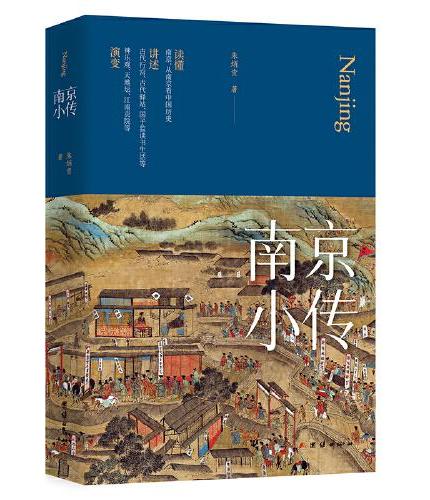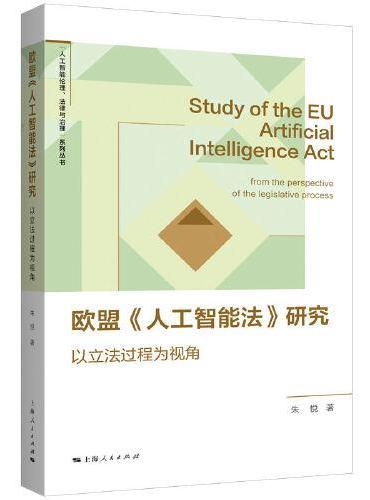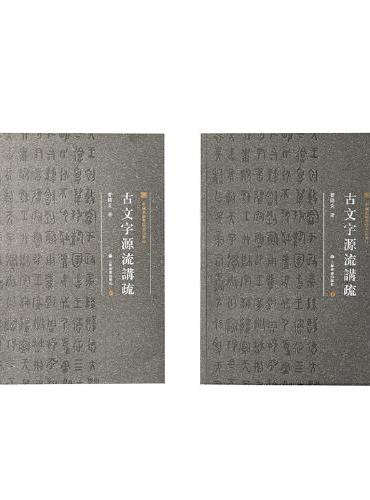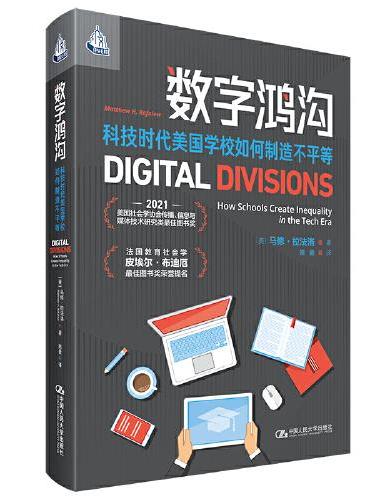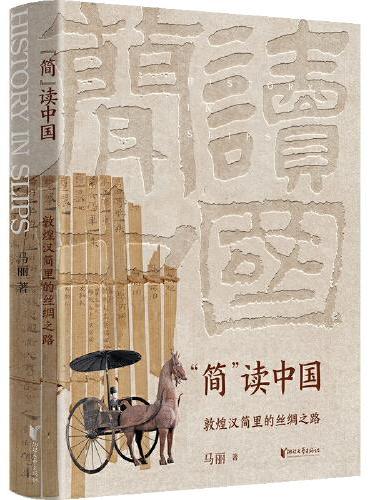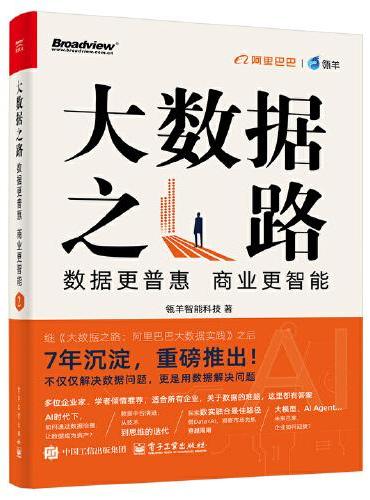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南京小传
》 售價:NT$
250.0
《
风雪唐古拉
》 售價:NT$
179.0
《
欧盟《人工智能法》研究——以立法过程为视角(“人工智能伦理、法律与治理”系列丛书)
》 售價:NT$
663.0
《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教材:古文字源流讲疏 (上、下册)
》 售價:NT$
1163.0
《
数字鸿沟:科技时代美国学校如何制造不平等
》 售價:NT$
352.0
《
“简”读中国:敦煌汉简里的丝绸之路
》 售價:NT$
398.0
《
我最好的朋友
》 售價:NT$
230.0
《
大数据之路2:数据更普惠,商业更智能
》 售價:NT$
500.0
編輯推薦:
本书介绍并分析了当代日本社会中一系列边缘性、非主流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如“JK散步”、女仆咖啡店、“神待少女”、虚拟主播等。透过这些现象,作者试图揭示当代日本社会、文化和思想的“零度”,探索重新想象未来的基本条件。全书一方面细致剖析了诸多微观细节,借此解剖日本社会不可忽视的“肌理”,另一方面与日本当代亚文化的有关理论论述展开对话,这些分析不仅可以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当代日本,也可以为读者了解当代中国、了解我们自身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
內容簡介:
《“零度”日本——陷入“关系性贫困”的年轻一代》介绍并分析了当代日本社会中一系列边缘性、非主流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如“JK散步”、女仆咖啡店、“神待少女”、虚拟主播等。透过这些现象,作者试图揭示当代日本社会、文化和思想的“零度”,探索重新想象未来的基本条件。全书一方面细致剖析了诸多微观细节,借此解剖日本社会不可忽视的“肌理”,另一方面与日本当代亚文化的有关理论论述展开对话,这些分析不仅可以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当代日本,也可以为读者了解当代中国、了解我们自身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
關於作者:
王钦,1986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为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等。著有『魯迅を?iもう:〈他者〉を求めて』、Configurations of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等;译有柄谷行人《探究(一)》《探究(二)》、中岛隆博《作为思想的语言》、雅克·德里达《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雅克·德里达《赠予死亡》、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等。
目錄
引言
內容試閱
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