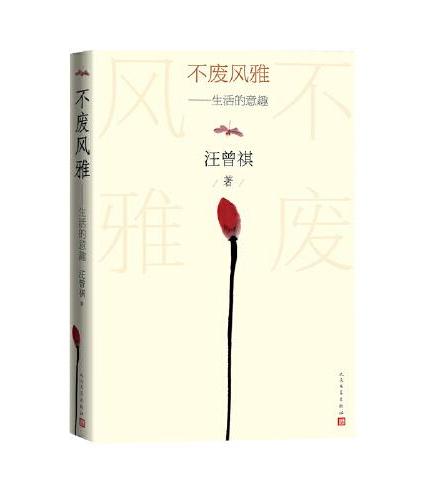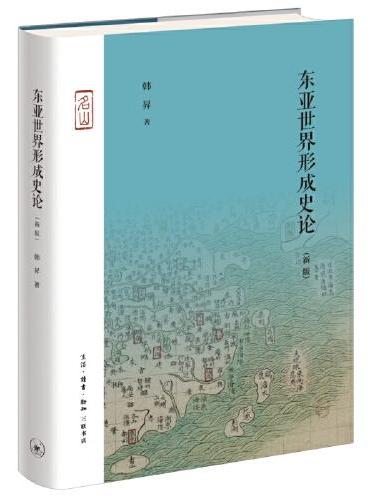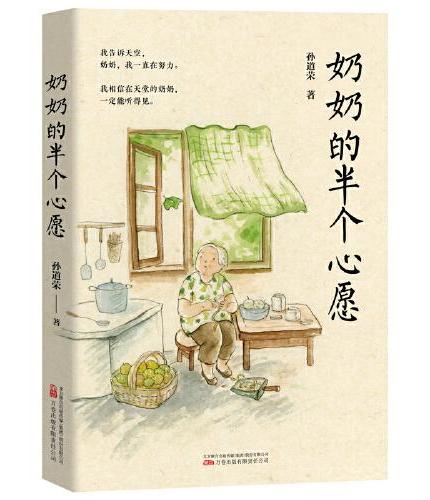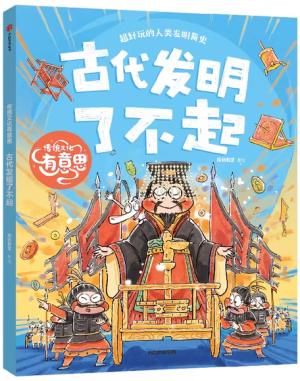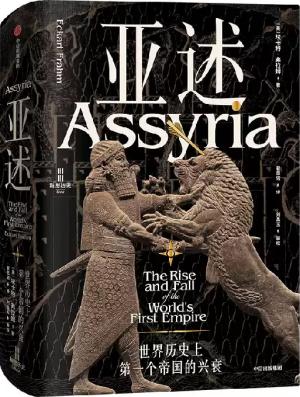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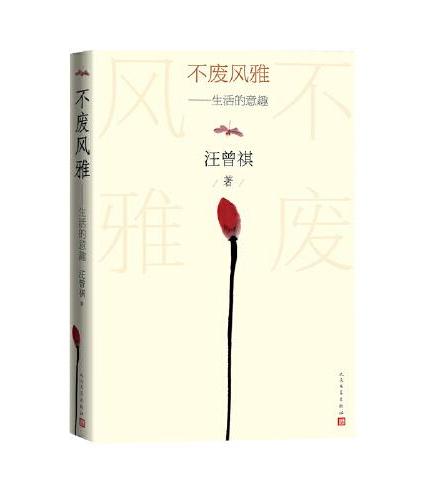
《
不废风雅 生活的意趣(汪曾祺风雅意趣妙文)
》
售價:NT$
2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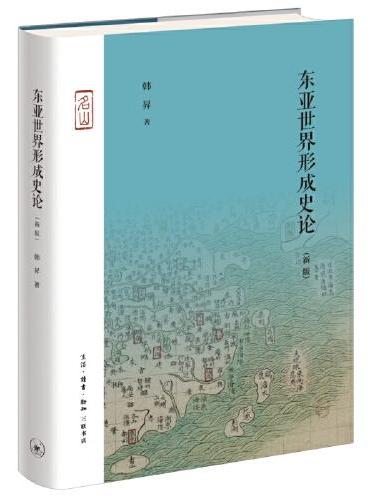
《
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新版)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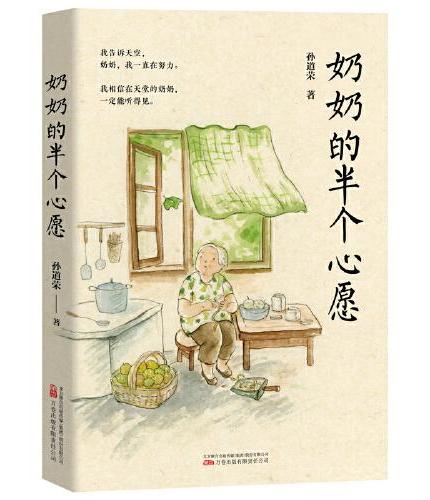
《
奶奶的半个心愿 “课本里的作家” 中考热点作家孙道荣2024年全新散文集
》
售價:NT$
190.0

《
天生坏种:罪犯与犯罪心理分析
》
售價:NT$
445.0

《
新能源材料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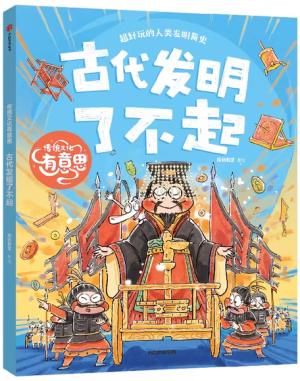
《
传统文化有意思:古代发明了不起
》
售價:NT$
199.0

《
无法从容的人生:路遥传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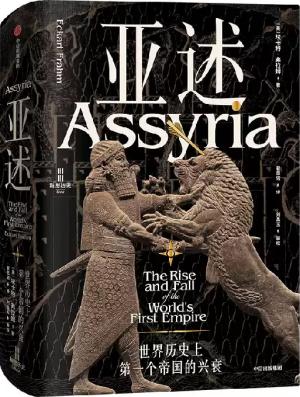
《
亚述: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的兴衰
》
售價:NT$
490.0
|
| 編輯推薦: |
?甄选最具实力女作家 最经典作品,主打少而精 轻阅读
精选对中国女性文学进程有影响力的中国女作家:铁凝、迟子建、王安忆、池莉、张洁、徐小斌,以“少而精”的方式将她们最具代表的作品呈现给广大读者,有极强的欣赏性和阅读价值。
?当代中国女性经典作品的一次整体亮相,兼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
作为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这些女性作家的创作洋溢着时代女性独立坚强的精神,也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深深吸引着一批又一批读者,经得起时间与口碑的考验。
?徐小斌创作生涯各时期代表作品,走近徐小斌神秘与瑰丽的叙事迷宫
收录《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双鱼星座》《银盾》《女觋》等4篇经典小说,每篇故事都有出人意料之处,徐小斌像个巫女般为我们装扮了一个属于她自己和所有读者的“迷幻花园”。
?隐喻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尴尬处境,揭示现代社会中变质的男女关系
她在这些故事中精心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形态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她们或耀眼或平凡,或隐忍或张扬,但都张力十足,以遗世孤立的姿态绝决地走向生活的绝境,又能用反抗的姿态逃离。
?只有明暗的对照才有意义,美丽是因灰暗的存在才
|
| 內容簡介: |
|
《双鱼星座》系女性短经典丛书之一种,收录徐小斌创作生涯各时期创作的极具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共计4篇,分别为《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双鱼星座》《银盾》《女觋》。这些作品是数年来经过时间考验的最为读者们青睐的中短篇,徐小斌的小说故事奇幻,把语言之美发挥到极致,独具风情。徐小斌的创作特立独行于一切文学潮流之外,主题关于现代女性、女性生存与文化困境的寓言,以独特的视角揭示女性生活的独特精神内涵。她的作品不仅仅关于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关乎于整个现代社会与现代生存。她的作品中那浓郁神秘的女性意识弥漫在所有的作品中,有着非常深刻的宗教意识,其造诣远非许多畅销书作家可比。
|
| 關於作者: |
|
徐小斌,著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画家,刻纸艺术家。自1981年始发表文学作品,当年即获《十月》首届文学奖。主要作品有《羽蛇》《敦煌遗梦》《德龄公主》《双鱼星座》等。曾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第三届女性文学奖,第八届全国图书奖,加拿大第二届华语文学奖·小说奖首奖,英国笔会文学奖,2023年度人民文学奖等。代表作《羽蛇》成为首次列入世界著名出版社Simmon&Schuster国际出版计划的中国作品。部分作品译成英、意、日、西班牙、葡萄牙、巴西、希腊等十余国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在美国国家图书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均有其藏书。
|
| 目錄:
|
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001
双鱼星座097
银盾207
女觋223
|
| 內容試閱:
|
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
这口小湖上结的冰仿佛又加厚了,在溶溶月色中泛着蓝幽幽的光。
上次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这灌木丛的叶子还没落光。微风拂来,那几片零落的叶子还会沙沙作响。她整个儿缩进那件褐色和暗红色条子的老式棉袄里。那棉袄是那么大,那么臃肿,她缩在里面像个小孩儿。发黄的柔软的发丝覆盖着她半个额头,双颊在月夜里呈现着病态的青白。尖尖的下颏儿倒是挺富于表情地向上翘着,使人能想象出她儿时的俏皮劲儿,淘气劲儿。
“真的,不骗你。我一点儿也不骗你。”她说。她这样说了多少次了。每当她这样说的时候,她眼神儿里就流露出那么一种可怜巴巴的神色。好像此刻我的一句话,一个反应都会成为她的判决书。
“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我这样说。笑笑。我也这样说了多少次,笑了多少次了。以至已经不想再笑了。我把疑问埋在心里。我想说,我相信你说的一切,但我觉得那很荒唐。是的,荒唐,但为什么要说出来呢?或许整个世界都是由荒唐构成的呢!难道我和她的相识、相爱不是很荒唐,很莫名其妙的么?
我始终怀疑她有一种穿透力,有一种非凡的心灵感应,我疑心她读出了潜台词。要不,她干嘛反复进行这种无益的表白呢?要不,就是她身上还有一种没被发现的偏执狂。我的天!被害妄想型已经够了,再加上个偏执狂,她还活不活,我还活不活?!
“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和我梦里一模一样。”她紧紧地怕冷似地偎着我。眼睛里现出一种迷离的神色。这眼神使她的眼睛显得很美。我轻轻地吻吻她的睫毛。我知道,她又要讲她的梦了。第一百二十回地讲她的梦,那个奇怪的、神秘的梦。对正常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梦。这种梦也许只能产生于天才或者精神病患者的意识之中。
“那口蓝色的结了冰的小湖,就是这么被朦朦胧胧的月光笼罩着。周围,就是这样低矮的灌木丛。风,轻轻地吹,灌木丛沙沙地响。”她睁大眼睛,盯着湖对岸的一片白色的光斑,“我一个人来到这里。是的,只有我一个人。我走到湖面上,轻轻地滑起来。我不会滑冰,也从来没滑过。可是……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就那么旋转了几下之后,我就轻轻易易地滑起来。那是一片朦朦胧胧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你会忘了一切,甚至忘了你自己。你忘了你自己,才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真的,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身心放松之后的自由。我飞速地旋转着。头顶上是漆黑的夜空和一片泛着微红色的月亮。冰面上泛着一层幽蓝的寒光。我越滑越快,听见耳边呼呼的风响,在拐弯的时候,我仿佛有一种被悠起来的感觉。我想起童年时荡秋千的情景。可那时是在碧蓝的晴空里。空中飘荡着伙伴们的欢声笑语。现在呢,是在暮色深浓的夜里,周围是死一般的静寂……我就那么飞着,飞着,月光渐渐变得明亮起来了。突然,我发现湖面上的一个大字——哦,是的,那湖面上有字——”她突然顿住,声调变得恐惧起来了。
我默默地望着她。第一次听她讲这个梦,听到这里还真有点毛骨悚然。——不得不承认,她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可是现在,这故事我听了不知有多少遍了。它的开头,结尾,内容,……我完全可以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岂止是背下来,我还可以编成小说,拿到一家三流杂志上去发表。
但我不愿打断她。不仅不打断,而且每逢听到这里,便条件反射似的集中起全部注意力,一动不动地看着她,我知道她愿意我做出这样的神情,她希望我看着她的眼睛,听她讲。
“那是一个大大的‘8’字。这‘8’字在蓝幽幽的冰面上银光闪闪的……哦,我这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按照这条银光闪闪的轨迹在滑行,不曾越雷池一步。而且我发现,这‘8’字已经深深地嵌入冰层——这证明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上面滑过了。
“我想摆脱这个硕大无朋的‘8’字,于是有意识地按别的路线滑行。可是,我的双脚却被一种无形的引力牢牢钉死在这个‘8’字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如愿。我惊奇极了。我感到这是一块被施了魔法的冰面——”
突然,她顿住了。在这刹那间,一切似乎都突然静止了。连风也不再吹。她伸出一个手指头按在嘴巴上,眼睛里充满了恐怖的光。
“怎么了?”我问。我不知道这个疯姑娘又在玩什么花样。然而不能不承认,她的确富于感染力。
“看,看那!你看那冰上——”
她声音里的恐惧感是那么强,以致我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感到后背发麻,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只见那平展展的蓝色冰面上,写着一个硕大无朋的‘8’字。
我感到自己是被裹胁到一桩荒唐的事情中去了。常常听人说,逻辑和常规不适用于女人,这次我可是深有体会了。我的女朋友谢霓平时可谓是个明智决断、不让须眉的姑娘,可这回却干出了一件荒谬绝伦的事。更加荒谬的是,她还硬要我充当这一荒唐事件的牺牲品。我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断然拒绝。然而,女人的韧性和“磨性”又是一桩法宝。我终于屈从了。
我和谢霓是同班同学。五月份我们开始毕业实习。我们这些“文革”后的第一届心理系毕业生备受优待,被安排在北京最大、也是全国闻名的一所精神病院里实习。说实话,我对病理心理并不很感兴趣。如果将来有机会读研究生,我倒是宁愿选择教育心理或实验心理。
可是谢霓不。她考入北大心理系之前似乎就对精神病学很感兴趣。入学后,常常看到她捧着弗洛依德、肯农等人的著作。有人说,研究病理心理、变态人格的人容易把自己也“折”进去。可她坚信自己神经的强度和韧性。
这回到J医院实习,她订了一套雄心勃勃的计划,我看着都眼晕。她挺怪。平时处理事情颇具大将风度,连班里很多男士都对她的冷静务实深表钦佩,认为她是女性中少有的务实派。可她骨子里却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一点,恐怕只有本人知道。你看,就说她这个计划吧,从微观角度看来,倒还像那么回事,似乎可行;可是从整个宏观角度和计划后面藏着的“潜计划”看来,她不仅是个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个带有点狂气和危险性的理想主义者了。
实习的头一天我们来得很早。病人们还没有结束早餐。谢霓悄悄扯扯我的袖子。我这才发现,病人们捧着的白色粗陶碗里,只有灰糊糊的粥和几根棒槌似的老咸菜。那粥,一看就是头天的剩饭煮的。
不知是不是缺乏阳光的缘故,病房里显得很暗淡。墙早已不那么白了。上面布满了斑斑点点。病人们倒是挺安静,对我们的到来漠然置之,甚至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
“东面第二张病床是躁狂抑郁症,王守志,部队来的;第六张病床是强迫性精神分裂症,乔德轩,教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跟他们聊聊。”郑大夫向我们介绍。
郑大夫是全国著名的病理心理学专家。是他在全国首创了心理咨询门诊。我们不少同学都读过他写的东西。没想到他还很年轻,四十岁出头,皮肤白净,一双眼睛十分精明,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另一位刘大夫是他的学生,二十多岁,身材颀长,足有一米八五以上,可脸还是个娃娃脸儿,满脸稚气。紧跟在老师后面大步流星地走着,白大褂像鸽子尾巴似的晃来晃去。
几个同学留在男病房。多数同学跟着郑大夫来到女病房。一进去,劈面便遇见两个青春妄想型病人,向我们频频飞来一些莫名其妙的眼神。谢霓立即向我投来一个意味深长的、诡谲的微笑,我装作没看见,把头转了过去。
“西面那个角落是个重病号。景焕。原来是个街道工厂的出纳员。”郑大夫的声调依然不带任何色彩,但目光里却掠过一丝忧郁,“被害妄想型,这已经是二进宫了。”
这就是她,那个景焕。名字就有些与众不同。她缩在角落里,成很小的一团。肥大的病衣把她全身所有的部位都掩住了,看不出她的体型。她长着一张很小的鹅蛋脸。脸色灰白,头发稀而黄,梳成一根蓬蓬松松的辫子——这种发型已经太过时了,但对她来说,却有着一种特殊的韵味。这使她看起来更像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她是那样年轻,真想象不出她老了是什么样子。她的眼睛和长长的睫毛像一扇门,遮蔽了她的心灵。可是,她的嘴巴却暴露了她内心世界的一角。是的,她的嘴长得很美,丰满、生动而富于表情。我想,假如她再胖些,眼睛再有神些,肤色再鲜润些,那么一定是很好看的。现在呢,当然不能说是漂亮了。
“景焕,这些都是来我们医院实习的大夫,”郑大夫俯下身,口气温和地说,“他们都跟你年纪差不多,你不用怕。怎么样,这两天好些吗?”
她抬起眼帘。她的眼睛不大,却是秀丽细长的那一种,很像绢画上的古代仕女。她的目光看上去很温和,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你叫景焕?这名字挺好听呀!”谢霓靠近她床边。看到景焕之后,我认定她便是谢霓需要的“模特儿”。果真如此。
“是《红楼梦》里的‘警幻’仙姑么?”谢霓故意跟她开玩笑。
“这名字是我妈妈给起的。”突然,景焕开口了。她说话的声音很低很柔,像是害怕别人听见似的。
“哦?那我猜,你一定有个好妈妈,是吗?”谢霓笑眯眯地看着她。
景焕的眼睛又垂下去了。
我看了谢霓一眼。我们早就看过景焕的病历,了解到她有着一个极不和睦的、终日吵闹的家庭。她本人也犯过错误。她之所以被街道工厂开除,据说是由于和以前的男朋友伙同贪污。
我不明白谢霓的用意。
谢霓的家坐落在市中心。是那种独门独院的老式厢房。全算起来得有十来间。门口还有个不小的院子,栽着各式花草果木。在现在住房拥挤的情况下,这儿可真算是神仙住的世外桃源了。
我头一次走进这间客厅还是在三年前,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当班长。为了应付“五四”青年节的文艺节目,我不得不低头踏上这座高门坎——尽管早有耳闻,她家的庭院之整洁,客厅之堂皇,陈设之高雅还是令我吃了一惊。
那是五月,艳阳当空,庭院里的竹篱笆上爬满了金银花,靠墙的地方栽着几株凤尾竹。窗台上,齐刷刷地摆着一排紫砂陶小花盆,栽着各色鲜花。倚窗台的一根较粗壮的葡萄藤上,还挂着一个相当精美的鸟笼,里面是只画眉,笼中挂着四个极精巧的小磁杯,分别装着肉松、蛋黄、小米和芝麻。
一进门儿,正面墙上挂着一副民族风格很浓郁的壁毯。那是两个造型别致的“飞天”,用一色的青铜色线织成,很美丽。壁毯下面是一张古色古香的琥珀石长桌,上面放着盆景和金鱼缸——都很新鲜:盆景的盆是个造型怪异的根雕,从一棵古树上伸出一枝枯枝,上面栖着只长尾鸟。布满苔藓的假山石长在古树洞里,假山石的洞穴里还长出几片飘飘逸逸的文竹。金鱼缸不是玻璃的,而是石头的,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石头,透明程度像是毛玻璃,迷迷朦朦的,闪着变幻的光。几色金鱼像是在厚厚的丝绸里面游来游去,更增添了一种迷离的色彩。
家具不多,都是桃花心木的。清一色的暗栗色腰果漆,显得庄重高雅。地板上铺着厚厚的俄式地毯,花纹图案都和室内陈设十分谐调,连花瓶、茶具甚至痰盂都是用的同一色调的陶瓷。
看到这份排场,我心里多少有点紧张。没注意到放在门口的拖鞋,于是一脚踏在地毯上,盖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章。谢霓的母亲,一位五十多岁、服饰高雅、颇有教养的女人,十分和气地安慰我说没有关系。这时拖着厚底拖鞋的谢霓走出来了。
“没想到今天大班长光临寒舍,”她嘴角上挂着讥讽的微笑,“……有什么招待你的呢?……我看看,哦,这儿有酒心糖……喏,”她打开小柜子,把糖盒子、饼干筒、水果盘子……统统拿出来,“喜欢什么就吃什么。不过我可以推荐一下,这种饼干挺不错,柠檬味儿的,平均半小时我可以吃一听。”
对谢霓的“吃”,班里同学早有领教。班里有几位老高中的男生都是美食家,但是绝“吃不过”谢霓。她在烹调方面颇有一套。当然,这也是实践出真知。据她自己说,她从小就爱吃,也会吃,能吃出食品的“个中三昧”。那次全班在香山聚餐,每人做两个拿手好菜,属她做的蘑菇馅饼和奶油酥卷最受欢迎。那天她高兴,又趁着点儿酒劲儿,话格外多。她大讲了一通中国烹调。从红案白案讲到各个菜系,最后颇带权威性地得出结论:“我国的烹调艺术是整个东方文明的一面镜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会吃,就不懂得文明。”
这句话后来在学校广为传播,成为老饕们的护身符。大家在餐桌上言必称“文明”,后来心理系成为全校闻名的“美食家俱乐部”,谢霓的功劳当推第一。
但有时她又不是那么讲究的。比如说吧,上生理课的时候,我的位子在她的斜后方,常常看到她漫不经心地从书包里掏出半块干得掉渣儿的烧饼,一小口一小口津津有味地啃着,不知那味同嚼蜡的东西究竟有什么品尝的价值。但她那副啃烧饼的样子实在令人好笑,我对她的兴趣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徐小斌”,”
“我今天是代表全班同学请你出山的。”我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听说你过去在工厂一直是团支部文体委员……”
“哦。是为‘五四’吧?现在可是只差一个星期了。”她嘴上又挂起那种讥讽的微笑。
“是啊。不然的话,不敢有劳尊驾。这次全校还要评奖,要是咱们剃了光头就寒碜了!”
“我这个人讲实惠,事成之后,拿什么谢我?”她诡谲地一笑。
“这个……”我略加思索,便痛快地说道:“请你吃一顿,怎么样?……当然,如果你不拒绝的话。”
“干嘛还要找补一句?你们这些男士呐!哈哈哈……”她开怀大笑起来。她笑起来很好看,一口整洁的牙齿闪着光,使人感到她的爽利和明朗,“好,阁下这顿饭我算敲定了!这样吧,明天午休时间我们就开始。我坚信,用优质蛋白武装起来的心理二班,音乐秉赋绝不会差!”
果然如她所说,那天我们班虽是仓促上阵,但还是获了奖。大家反应不错,凭良心说,这和她出色的组织能力是分不开的。
那是个晴朗的夜晚。我们吃罢饭,从前门外的一家餐厅走出来,她兴致很高,不断地转换话题。我知道,每逢她吃了一顿美味佳肴之后总是心情很好。那天她点的三个菜味道都不错。她吃牡蛎的本事简直令人惊叹,不是一个个地吃,而是舀起满满的一小勺,还来不及看清她的牙齿和舌头是怎样运动的,那吃得干干净净的半透明的壳便一个个从她薄薄的嘴唇里吐了出来,简直就像鹦鹉吃瓜子那样灵巧。我突然感到:她是那种善于发现和欣赏日常事物的人,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是不会乏味的。我喜欢从抽象的思维中寻找乐趣,而她的快乐永远只从生活本身去寻找。她直面生活,懂得生活,更会生活。我们这个时代造就了一大批重理性、重思维的青年知识女性,而谢霓却属于另一种人。
这顿佳肴成了我们进一步交往的媒介。
现在,我已是这里的常客了,但对这里始终保持着一种新鲜感。每次来这儿,室内的陈设都有些新的、小小的变动。例如:古董柜里又添了个唐三彩,放在茶几上的青铜色古瓶里插上了几根长长的孔雀翎,而茶几上的尼龙缕花台布又换成镶着茜色缨络的亚麻布了。我知道这都是谢霓的作品,她喜欢别出心裁的特点表现在各个方面。我相信,即使是一间简陋的小屋,她也会利用手头上能找到的东西,尽量把它布置得“有味儿”。记得那次下乡劳动,在只有一个西红柿、几分钱“辣丝儿”和两毛钱肉末的情况下,她竟利用这些东西做了一顿美味的面条,吃得我们班的这帮老饕们纷纷赞不绝口。好事者还起美名曰:“琥珀面”。说是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出访时,曾吃到一种美味的鱼,回来便大加赞赏,鱼便身价百倍,成为御前食品。照此推导,琥珀面亦应称为中国烹调之又一奇葩了。
也许这种新鲜感就来自她本人。她容貌并不出众。梳得很自然的短发。大大的额头和顾盼流眄、带点调皮的眼睛显得很聪明。鼻子略嫌宽大,但整个看上去却显得端庄大方。她身材很漂亮,是当代西方最崇尚的那一种女性体形:骨骼宽大,细腰长腿。她喜欢穿舒适、随便的衣服。今天,她穿了件米色真丝双绉的连衣裙,这是她按照一家杂志上介绍的国际流行的式样,自己做的。式样很简单,宽松的裙子,腰间系上一条细细的本色绦带,走起路来,那薄薄的透明的裙翼在苗条修长的双腿上飘飘颤颤,有一种飘逸感。这便是典型的谢霓风格。
我从她递过来的饼干筒里拿了两块饼干,她便自己抱着筒子吃起来,一边津津有味地翻着她的实习笔记。
“你知道,我一见到她,就知道,买卖来啦!”她俏皮地向我挤挤眼,“可是,这笔买卖咱们得合伙做,这就是今天我叫你来的目的。”
“我?跟你合伙?……”
“对。而且起重要作用。懂吗?好啦,从今天起,咱们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算是成立了,我当总经理,可董事长嘛……得由你来当罗!”
“可我无资可投嘛!”
“你有。你的‘资’,就是你本身,懂吗?”她诡秘地一笑,把她的实习笔记递给我,“你瞧,这是她的病历和我对她的临床精神检查。后面是我对她过去情况的一个初步调查。根据这些情况,特别是我对她的直接印象……我作了个初步诊断,”她顿了一下,两眼奕奕放光,“我敢说,她不是精神病患者。她是个正常人。”
“……?!”我惊住了。
“是的,她是个正常人。不过是个被扭曲的正常人罢了。”
“不,不,”我连连摇头,“过分相信直觉和那些表面化的东西,这是你们女人的通病。你要知道,她入院是要经过各种检查的。这里的大夫临床经验很丰富,郑大夫又是全国著名的病理心理专家,绝不会把一般的心理功能性紊乱当作器质性病变来治疗的。她的病历上不是讲得很清楚么?”
“你们就是过分相信病历!”她两道眉毛高挑起来,“这就是懦夫和懒蛋的逻辑!病历,病历不是人写的吗?再说,病历上也讲了她的神经科检查始终没有阳性反应,服用了大量氟奋乃静、泰尔登……疗效甚微。哼,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又自以为是,这是你们男人的通病!”
我的天!她可真是寸土必争。
我只好缄口不言。开始慢慢翻着那份厚厚的“病案”。
患者:景焕 女 21岁 宣武区小桥胡同街道工厂出纳员
精神状况检查:
1一般表现:
意识清醒,定向力完整,接触被动,对医疗、护理等合作不够。
衣着较齐整,年貌相符,日常生活能够自理,入院后饮食、睡眠均不好。
2认识活动:
〈1〉无感知觉障碍
〈2〉思维
对所问问题回答被动,语句不连贯,意念飘忽。
反应一般。临床诊断主要为被害妄想兼有关系妄想。
患者一直坚持有人害她这一说法,但对具体问题避而不答。患者病历中记载:患者在街道工厂当出纳员期间,曾贪污现款,后被该厂除名。此后她的神志开始不清醒。第一次犯病时,曾把十元一张的人民币撕碎,并说它是“印着咒语的小纸片”,是“巫婆用的”。被其母及弟送来住院治疗。治疗期间,常常不进食,夜间噩梦纷扰,常哭醒。只能靠安眠药才能维持起码的睡眠。患者自述常心悸,但拒绝说出恐惧的对象。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略有好转。患者不经医护人员同意,私自出院,后被送回。患者情绪低落,抑郁寡欢,仍不愿进食,身体非常虚弱,治疗过程中,曾两次虚脱。医护人员对其采取特殊措施进食。尽管院方看管严格,患者仍两次出逃,但似无自杀意向。
3情感:
表情淡漠。情感反应不鲜明。无明显低落与高涨。
4意志、行为:
至今仍不安于住院。适应力极差。对医疗护理等均合作不够。无任何主动要求。常有些特殊举动。如:夜半常独自坐在床边,沉思默想。一次,护理人员忘记锁门,她当夜便跑到阳台上,望着天空发呆,直到凌晨时才被护理人员发现,经劝说回到病房。
5记忆,智能:
患者从不愿回忆往事,对住院前的事,特别是贪污现款一事缄口不言。记忆似乎已丧失。对于问话,回答时语量少,不主动,态度不自然。多疑。承认脑子乱。
注意力不集中,有时似听不见别人问话。
智能方面尚未发现明显异常。
我合上“病案”夹子。
“一会儿,我再仔细看。告诉我,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我想让你……”她望着我,笑容可掬,“我想让你和她谈恋爱。”
“什么?你再说一遍——”我以为她疯了。
“是的。我想让你和她谈恋爱,交朋友,你不懂吗?”
她的眼睛突然变得无法穿透,像是垂下了一片神秘的漆黑的帐幕。
夜晚,我家中。一片沉寂,只有我翻着这本“调查材料”的声。勿宁说,它更像一篇不成熟的文学作品:
小桥胡同坐落在闹市区的中心,却显得异乎寻常的宁静。北面的出口处有一家新建的“红枫旅馆”,出去便是一个中等规模的菜市场,南面是“小桥街道服务社”。景焕家住小桥胡同2号,紧挨着“红枫旅馆”。
这是个小院。看来像她家的私房。但除了西厢房还算完整之外,其它几间房都显得破旧不堪。敲门时,使大点劲儿,门框便晃悠起来。上面的白灰也直往下掉。这里像是“聊斋”里描写的无人住的“鬼屋”。
这是一个很普通但又很特殊的四口之家(包括景焕)。按照景焕父亲景宏存的职称看,这应当算是高知家庭。但是给我的印象却是:这个家庭像一座临时拼凑起来的质料不同的建筑,根基十分薄弱,拼凑的裂缝很深,仿佛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
景宏存是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年轻时曾名噪一时,发表过不少有相当价值的论文,三十一岁时便被破格提升为副研究员。后来不知为什么,他在物理学界销声匿迹了。我万没想到他会是这样子:瘦骨嶙峋,面色憔悴,嘴唇发紫,像个晚期癌症患者。
无论是他的在家待业已久的儿子,还是一直没参加工作的妻子,都是靠他的工资养活的。然而给我的感觉却是,他在家里的地位很低。从他的面部表情和说话的语调看来,他是个有脾气的人。但在这个家里却似乎不得不时时压抑着自己的怒气,他重重地叹气。他不时地伸出一双枯瘦的手去搔头发。他的表情烦恼、愧疚甚至带着一丝羞赧。就像是那些自尊心很强的人感受到自己给别人带来麻烦似的那种神情。我注意到他那磨破了的发黄的衬衣领子和袖口,以及那双早该淘汰了的断裂了几处的古铜色塑料凉鞋。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隐秘。家庭可以是避风港,也可以是囚笼,是监狱。而这个家庭中的窒息气氛在十分钟之内就能被人嗅出来。仿佛每个成员之间都有着夙怨,而每个人又都以一种病态的敏感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那个说话慢声慢气的矮小女人是景宏存的夫人,景焕的母亲。她过去曾是景宏存的同窗,只是毕业后一直没有工作,该算个“家庭知识妇女”吧。她的内心却不像她的表面那样,她很难识破。在我拜访的这一个小时之内,有关她,我心里大约已经做出了若干种判断,而这些判断又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她表面上看去很胆小,懦弱,就像那些长期患神经官能症、夜夜失眠的人那么敏感。她待人一团和气,无论你说什么,她总是顺着你,不作任何异议。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她并没有认真地听着你说,她心不在焉,只有当她心爱的小儿子景致开口说话的时候,她才真正地在听。而且,她跟儿子讲话时,露出一种和母亲身份不符的谦卑,简直可以说是卑躬屈膝,这与她对丈夫所持有的那种带着愠怒的不耐烦的态度恰成对比。
景焕的弟弟景致倒是个一眼望得见底的人。一看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二十郎当岁,受阶级斗争教育长大的,所以战斗性也就格外强。边说话边抽烟,标准京腔儿。不像个高知的儿子,倒像是成天上老酒馆吃泡花生米的出身。谈起景焕,他直言不讳地说和姐姐的关系不好。“我打过她,也骂过她。”他俨然一家之主的样子,就像是被打骂的对象不是自己的姐姐,而是自己的奴隶似的,“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我。她那人,太个色,招气。三天不打,她就痒痒。她呀,天生就是神经病的脑袋,早晚得得神经病!”
我对这番话简直反感透了。第一,他那么随随便便地就把“精神病”说成“神经病”(这在我们学心理的人看来是不可原谅的概念错误),这暴露了他的无知和自以为是。第二,作为弟弟,对姐姐毫无悯念之情,这也使我感到他的狭隘和冷漠。毫无疑问他不是个男子汉。但是他很直爽,也容易感情用事,这点我可以利用。
我了解到景焕过去的男朋友叫夏宗华,是青年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副导演。他们从红领巾时代就认识了,可算作是青梅竹马。据景致说,景焕很爱他,但不知为什么每次和他见面回来,都是愁眉不展。在她被揭发贪污现款前后的那段时间里,景致曾发现她久久地发呆。后来,就拒绝进食了。在她被街道工厂除名之后,他们断绝了来往。
关于夏宗华的情况,我只了解到这么一点点,至于这个人本身,他们全家在交换了一下眼色之后,由景致说出三个字:“不了解。”
大约是弗洛依德定律的作用吧,在送我走出胡同口的时候,景致塞给了我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夏宗华的电话和地址。
一个新鲜的念头突然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
她这个新鲜念头大约就是迫我去和景焕“谈恋爱”,而她自己则在找夏宗华“交朋友”吧。还美其名曰是按“弗洛依德定律”办事,让这个鬼定律见鬼去吧!我对这件事可提不起兴趣。
屋里月光很浓。我睡不着,索性下床把窗帘拉开,出人意料地,并不是满月,而是一钩亮闪闪的新月。我奇怪今天的月光为什么这么明亮。小时候,自然课老师曾教给我们识别新月和残月的办法。他说,很多影剧布景往往爱犯这样的错误:剧本上明明写着“新月高悬”,而背景上出现的都是一钩残月,“残”的汉语拼音字头是“C”,而“C”就是残月的形象。反之,则是新月了。这个办法我至今记得很清楚,真是“儿时所学,终生难忘”。
其实儿时的一切都令人难忘。岂止是难忘,儿时的经历就是一把刻刀,一个人一生的雏形就是由那把刻刀雕琢出来的。这两天在J医院实习,发现那么多患强迫症、反应性精神病的人都在童年时代有过不同程度的精神创伤。从这个意义来讲,我真想对着那些不幸的家庭,对着那些不称职的、还没学会做人就有了孩子的父母们,对着那些压抑人、窒息人、扭曲人的社会弊病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在这方面,我总是感到庆幸。我的家境并不宽裕,父母都是小人物。兄弟姐妹一大群。但我却有着一个和谐、温暖、幸福的家。记得小时候,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妈妈为了让我们吃好,真是千方百计啊!她工作之余,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出去采野苋菜、摘榆钱、挖蘑菇,她蒸的棒子面裹白面的发糕“金裹银”,包的马齿苋馅的饺子,蒸的榆钱饭,煨的蘑菇汤,我们吃起来都是又香又甜,回想起来,比现在饭馆里的西餐大菜还有味。妈妈凭着一颗慈母心和一双巧手为我们全家度过了难关。四个男孩子都长得结结实实,爸爸多年的肺病竟也慢慢地好起来。回想起这一切,我总是由衷地感激妈妈。
是的,我发现一个家庭主妇对家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母爱下长大的孩子都有着一颗仁慈、博大的同情心,一种对人宽容的善行。相反,无爱的家庭却往往造就畸形、病态的孩子。我当然不了解景焕家庭内部的真正情况,但是仅从她住院半年,竟无一个家庭成员来看她这一点推断,她是患了爱的饥渴症(而且是重症)的女孩子。
这种女孩子往往对爱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渴望,但同时又具有同样强的排斥力。
我要小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