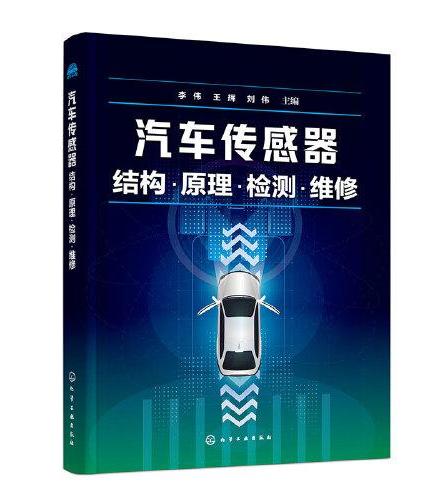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精品教材大系:材料的时尚表达??服装创意设计
》
售價:NT$
347.0

《
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
》
售價:NT$
653.0

《
国家豁免法的域外借鉴与实践建议
》
售價:NT$
857.0

《
大单元教学设计20讲
》
售價:NT$
347.0

《
儿童自我关怀练习册:做自己最好的朋友
》
售價:NT$
316.0

《
高敏感女性的力量(意大利心理学家FSP博士重磅力作。高敏感是优势,更是力量)
》
售價:NT$
286.0

《
元好问与他的时代(中华学术译丛)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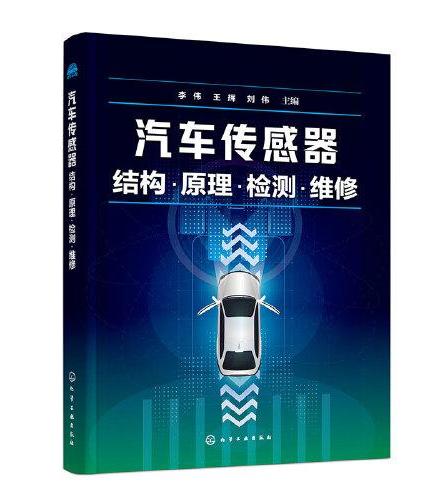
《
汽车传感器结构·原理·检测·维修
》
售價:NT$
500.0
|
| 編輯推薦: |
◆ 一部躁郁症患者康复手记,一场绝望与希望交织的生命之旅。“可是,天好蓝花好美今天的风格外温柔,好吧,我要活下去。”
◆ 真实细腻、直接客观地呈现病发、病中、到康复的完整过程,“让更多人直面负面情绪,了解躁郁,避免躁郁,不害怕躁郁”。
◆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负责人陈祉妍倾情作序,在充满压力的现代社会,呼吁更多人关注年轻人心理健康:“这本书会让关心抑郁症和躁郁症患者的家人、朋友、助人者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患者,会让患者们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和希望,还可能让全社会对于患者的偏见稍稍减少一点。”
◆ 如果你也身处黑暗,这本书能带来理解、共鸣和希望,你不是在孤军奋战。
◆ 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人撑伞。饱受躁郁症折磨的“过来人”真诚剖白内心,传达出对同行者深刻的理解、支持和鼓励,即便曾经堕入黑暗,依然可以追寻和实现自己想要的人生。“你也知道的,天亮之后,会很好看。”
◆ 哪怕身处无边无际的黑暗,哪怕被消沉悲伤的情绪困住了,但也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人间水火。
◆ 封面插图来自一位6岁的小朋友,想传达给你的是:哪怕你患了躁郁
|
| 內容簡介: |
《我是个年轻人,我得了躁郁症》是一本带有自传性质的心理自助类图书。
23岁、研究生毕业的年轻人阿杰正要展开新的人生,却在此时确诊了躁郁症,跌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像被困住了。
作者以躁郁症亲历者视角真实记录一场绝望与希望交织的生命之旅。他经历了困惑、怨恨,克服了如“木柴在火堆里烧得噼里啪啦”的痛苦后,终于走出黑暗,迎来清晨,并鼓励人们,躁郁症康复后,人还是那个人,日子还是那些日子,但生命开始有了坐标轴,我们拥有了托起自己的底气。
全书分为“确诊以后的日子”“凭什么要好起来?”“开始治疗了……”“让头浮出水面”“ 康复的那一刻”五个章节,作为一个“过来人”,作者用直白平实的语言科普了在患病的每个阶段会遇到的困惑,同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诚恳、细腻地描述了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诉我们,哪怕身处无边无际的黑暗,哪怕被消沉悲伤的情绪困住了,但也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人间水火。因为黑暗中的路无论有多远,都会有结束的那一刻,第二天的清晨也都会如约来临,而你也知道的,天亮之后,会很好看。
|
| 關於作者: |
李俊杰
1995年生,双子座。
在没确诊为躁郁症之前,是和我们大家一样在生活中浮沉的普通人,做着一份新媒体编辑的工作,在网络上记述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也不知道躁郁是怎么来临的,他也困惑过、怨恨过、痛苦过,但是最终,他努力让自己浮出水面,走过了最黑暗的时刻,迎来了清晨。人最矜贵的品质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替别人撑把伞”,作者阿杰也如是。目前已经康复的他,在大学里做心理健康志愿者工作,帮助大学生预防情绪亚健康状态。
|
| 目錄:
|
序言1:文字的背后,是一种温暖的关怀(陈祉妍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
序言2: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种子(李健敏 作者阿杰的姐姐)
CHAPTER 1确诊了,可为什么是我?
确诊的前一天
告知家人
医生说确诊了
如何判断自己该去看医生了?
为什么是我?
我的失败清单
写给未来的一封信01
来自现在的回信01
CHAPTER 2凭什么要好起来?
得了抑郁症是什么感觉?
躁郁就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起起伏伏
世界不公平……吗?
凭什么要好起来?
站在天台上的人
活下去的理由
写给未来的一封信02
来自现在的回信02
CHAPTER 3 开始治疗了……
刚开始治疗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
如何争取家人的理解、支持?
关于吃药这件事
那,需要去做心理咨询吗?
面对伤痕
每天只动100米
有空的话,什么书可以看看?
我抑郁的时候听什么?
去书店、菜市场和老人院
那一天,我选择公开
写给未来的一封信03
来自现在的回信03
CHAPTER 4 渡过自己的海底
试着就地躺下
让头浮出水面
我们是可以不放下的
我们是可以害怕的
带着抑郁去毕业
决定给100 人发新年祝福
写给未来的一封信04
来自现在的回信04
CHAPTER 5康复的那一刻
找份工作干
这个奇怪的公司,奇怪的同事
想辞职的念头来得很快
我去徒步了,可是……
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
决定开始停药
开始巡回分享
康复的那一刻
最后,我想对大家说
最后一封:来自现在的回信
|
| 內容試閱:
|
确诊的前一天
2018年8月14日。
印象中,那天天气特别晴。
那段时间,刚在香港完成研究生学业的我,回到大学实习过的公司做新媒体副主编已经一个多月了。公司离我家有40分钟的车程,工作是我喜欢的,也是自己选的,老板和同事都对我很好――读到这里,也许你会对我的生活背景有个初步印象:物质条件不错,留得起学,有交情不错的人脉,是过得比较顺利的那种人。
是的,一切都很好。
只有我感觉很不好。
事实上那段时间,我没有一天睡得好。
公司的公众号,每天都要发文章。明明那是我最擅长的事情,却变成了每天最恐怖的时刻,因为当时,我已经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奇怪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脑子里好像装了一个放大器,它可以放大一切可能引起消极的声音。
比如说,我的老板问:“阿杰,还好吗?今天需要支持吗?”
脑子里听到的是:“你怎么还不好?今天的文章呢?”
我的同事看我脸色不对,问:“你还好吧?”
到了脑子里,则是:装的吧,你哪里不好了?
更扯淡的是,这些声音一旦形成,就跑不掉了。走路也好,工作也好,休息也好,这些声音都在我的脑海里回荡,像是要炸掉整个头,甚至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真的能炸掉,就好了。当时的感觉,就像是自己被捆在一张剧场的凳子上,周围是所有你想象出来的,任何人指责你的声音。你无法捂上耳朵,也无路可逃。
慢慢的,脑子就成了堵住的下水道。紧接而来的,就是工作能力的迅速消退――先是记忆能力,然后是反应能力,最后是输出能力。无论原来多么擅长的工作,多么熟悉的事情,慢慢的,都变得无比困难。
比如2018年8月14日这天,我的工作是给一篇需要转载的文章想一个新的标题。对于任何一个专业的新媒体编辑来说,完成这个工作只需要15分钟。这很正常,也许你取不出特别好的标题,但是取3~5个能用的、合格的标题,是基础的业务能力。
但那天,我花了5个小时,依然没有想到1个能用的标题。事实上,我只是在绝望地散步,公司周围逛了十几圈,把一杯又一杯咖啡灌下去,直到心脏像被人揪着一样疼。
我回到公司,打开手提电脑,看了一会儿空白的文档,又关上。再趴到桌子上,又一会儿,抬起头来,我像刚从地府回来一般,朝对面的主编张了张嘴:
“我不行了。”
主编抬起身体,从座位挡板上冒出半个头,露出关切的眼神:
“吃错东西了?还是没睡好?”
“都不是,脑子快炸了。现在,我连一个字都想不出来。”
“没事,今天的文章给我,你先回去吧。”主编的头又缩回去了。
那一刻我是真心地感激:她不仅帮了我,还没让我解释自己的状况。当然,事实是我也解释不清楚,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抑郁到底是个啥呢(拜电视剧所赐,编剧想象的抑郁症患者,要不就是个病恹恹的美女,要不就是个天天哭闹吵架的长辈,让人看着只能往神经病方向联想)。更别说我还是个男的,抑郁?这能跟我有啥关系……
我斜挎着每天都背的包――电脑包,感觉它比往日都重一些。然后,走出公司大门,玻璃门展开的时候,关系很好的同事向我打招呼,我麻木地点了点头(或者是没点,谁记得呢),走到园区的夕阳下。若从旁人的视角看,应该是挺美的画面。而且,作为常常加班的新媒体编辑,我也很久没有看着夕阳下班了。这种种,能令人开心的理由真的很多。
但,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
从公司大门到地铁站,平时走路只需要5分钟。但是那天,我应该用了两倍的时间,也许更久。那根本不能算走,只是一只脚拖着另一只脚在挪动。就像战争电影里那种伤兵败军的撤退画面――大概比那还要慢一些。
在公司与地铁站中间,有一条小马路,延伸到远处的工地,往来都是运货的小货车和挖掘机,它们的速度很慢很慢。所以小马路上不需要信号灯。
每个人都走得很快,除了正在蠕动的我,还有我那停不下来的脑子:
“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脑子是废了吗?”
“以后连标题都想不出了吗?”
“明天怎么办?”
“这份工作怎么办?”
“回家怎么跟父母说?”
“他们会怎么看我?”
……
远处有一辆面包车,司机把半只手臂放在窗外,大声打电话,像是个危险的驾驶行为,但它开得特别慢。
而此刻我的脑子转得特别快,不一会儿,就从“连个标题都想不到”跑到了“连个标题都想不到,还混个屁”。过了很久,我才明白:积极的想法需要日积月累,而消极的想法就像一列不断加速的火车,越想操纵就越是失控。
“撞上去吧。”
本来行动缓慢的身体,忽然不自觉地往前,向着面包车的车头靠过去。事实上,那并不是我最痛苦的一刻,却是我最接近死亡的一刻。因为,那一刻我的情绪与痛苦,掌控了我的身体。一只“看不见的手”从我的身后出现,正在送我前往深渊。
等反应过来,我已经跌坐在地上。司机刹住了车,并用各种脏话问候我,不过没关系,我的脑子一句都没听进去。我身上穿着一件短袖,里面的汗是凉的,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打了个踉跄。身旁的人们绕着我走,应该是怕染上某种神经病(我不怪他们,后来更是对这种态度习以为常)。
我终于想明白了那天唯一能想明白的事:
我需要找个医生了,心理的,精神的,都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