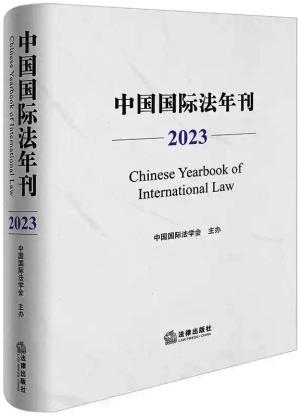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大学问·明清经济史讲稿
》
售價:NT$
3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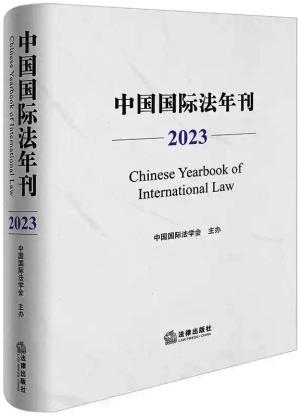
《
中国国际法年刊(2023)
》
售價:NT$
539.0

《
早点知道会幸福的那些事
》
售價:NT$
295.0

《
迈尔斯普通心理学
》
售價:NT$
760.0

《
古典的回響:溪客舊廬藏明清文人繪畫
》
售價:NT$
1990.0

《
孤独传:一种现代情感的历史
》
售價:NT$
390.0

《
家、金钱和孩子
》
售價:NT$
295.0

《
量价关系——透视股票涨跌脉络
》
售價:NT$
340.0
|
| 編輯推薦: |
★一部写给所有女性的励志之书与自我保护指南。
14起属于所有女性的诉讼,她们摊开自己的人生,告诉每一位女性:无论何时,只要你想,人生就可以重启。
★14起热血沸腾的女性诉讼,14个关乎“底层”女性的真实故事,14次对不公命运的奋起反击!
被亲生母亲当作商品售卖的女儿;长期遭受家暴的妻子;被性侵的视频遭到恶意传播的女初中生;因为离婚无家可归的女人;意外卷入命案的失足女……重现她们的诉讼之路,看她们如何重获新生!
★一位手捧法律温度的资深律师,用善良捍卫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取证、起诉、法律援助、无罪辩护……执业10年,律师蔡寞琰因法律与上百位女性当事人交织,热心帮助她们用法律武器挣脱命运的束缚。因为出身农村,他对“底层”女性有着更为真挚的共情,他说:愿法治更加公正、细致、温暖地呵护她们。
★直面底层女性的生活与维权困境,聆听她们遥远的呐喊。
留守、性别歧视、贫穷、家暴、性侵、生育困境、无性婚姻……
掀开女性主义被忽视的一角,触摸“底层”女性的真实困境。她们的个体命运中,流淌着女性共有的伤痛。
|
| 內容簡介: |
资深律师蔡寞琰亲历的14起关于“底层”女性的真实诉讼。
母亲强迫女儿跟6个男人结婚,生下7个孩子,只为给儿子赚彩礼钱。
离婚后的女人失去了自己花钱盖的房子,只因宅基地属于前夫。
留守女孩被两个堂哥性侵7年,却始终不敢告诉父母。
……
她们深陷不同的人生困境,
曾经被环境、观念等所束缚,面对苦难懵懂、胆怯、忍气吞声,
直到遇到蔡律师,在他的温暖帮助下,她们勇敢地走上法庭,用法律的力量挣脱自己的命运,重获新生!
|
| 關於作者: |
蔡寞琰,执业律师。
已发表作品百万余字,其中多篇售出影视版权。
作品具有强烈的悲悯心,文笔细腻且有力量。
|
| 目錄:
|
01 前言
001 七刀之后,她终于逃离那个家
019 在农村,离婚的女人无家可归
041 没有强奸的强奸犯,演不好父亲的父亲
059 坚决和“模范”丈夫离婚的女人
081 十三岁的他,何以为家
101 “十五元按摩店”杀人事件
119 弑父之后,母亲要他去死
137 盗窃罪掩盖下的七年性侵案
157 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最后四十八小时
177 三次诉讼,她的离婚之路走了六年多
197 病到最后,家人想要拖死她
215 不敢离婚的女人,杀了自己的丈夫
231 她最疼爱的儿子,因母爱丧命
249 离过四次婚的女人,守着永恒的爱
275 后记
|
| 內容試閱:
|
稿件即将成书时,编辑告诉我选篇都为女性故事,我不免诧异,是吗?执业多年,我不在意当事人的身份、年龄、性别,任何人来,都认真做好分内的事。就算是写稿,也没有刻意注意到这一点,却没想到,不知不觉就写出了女性的故事,那就当是一种特别的缘分吧。
我是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出来的人,早早便学会了感同身受,只因成长环境恶劣。一个地方如果落后、闭塞,女性和孩童必定首当其冲,遭受最深的伤害,难以解脱。
我见过被丈夫打得头破血流,没等大夫赶到,就踉踉跄跄走进灶屋,自己用草木灰草草止血,赶着生火煮饭的女人,她坐在灶前喃喃自语:“到点了,孩子们要放学回来了,我得做饭。”我见过因为产后抑郁喝农药自杀的女人,死后被人评头论足,说是“做傻事”,最后成了“短命鬼”。即便同为过来人的女性也不过是轻描淡写:“她就是想多了,过去我们生孩子,死活不论,天天要干活,哪有时间去胡思乱想?有谁没坏(夭折)过几个小孩?”我见过在家中“隐形”的小女孩,父母想要生儿子,对她很是嫌弃。最后一次见到她,她抱着弟弟对我说:“我很怕爸爸,也不对,他都不准我叫爸爸了。”后来,小女孩为了捡弟弟被风吹走的帽子,死在了车轮下。她的父亲到达现场后,只是抱起儿子说:“苍天有眼,还好没事。”
还有很多女性,她们习惯把身体当作武器,却不知法律才是真正的武器。
我受过女性的恩惠,尽管同样苦难深重,但她们还不忘给我拥抱。有一位阿姨,生了好几个女儿,因而被婆家看不起,经常挨打,但她从未哭过,有次我碰到她边跑边喊,“你们莫打了,我当下没空挨打,地里还有几担红薯没有挖”。有人说她是傻的,“女人生孩子最疼了,尤其是过去,可她生那么多孩子都没有喊过一声,后来被摩托车撞得骨头都露出来了,也没哭”。但我见她哭过一次,我祖父去世那年,家里只剩我一个人了,她给我送来了几个鸡蛋,看着我就哭:“我的满崽,你以后怎么办啊,哪有你这么多灾多难的人,怎么办?”我问她:“您不是不哭的吗?”她抱着我说:“我天生不怕痛,但我有心,我疼我的满崽啊。”
被家暴的女人,给我补过扣子;喝农药的女人,给过我几个透红的柿子;出车祸的小女孩,给我抓过虱子;那个不知道痛的阿姨,疼每一个她见过的孩子,包括她的女儿们,“来了就好好活”。
这些女人,有的不在了,但不代表她们没有存在过,她们的爱在我的心头,不会消散;有的还在,一见到我总会满心欢喜。我常常想,除了提着礼品探望,我还能做点什么呢?
我到底没有“烂”在村里,长了她们从未长过的见识,赚了她们这辈子都赚不到的钱,勉强算是村里功成名就的人,可以走得远远的。但她们呢?
执业以后,有次我去看望那个为我哭过的阿姨,刚好碰到她丈夫因一件小事对其大声呵斥,阿姨先是躲在我身后,而后挽着我的手挺直了胸膛回道:“你想怎么样?打了我半辈子了,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天我走到哪里都是笑着的,尽管她可能还会挨打,但总算有底气回击了。
我能做的就是接过她们身上的爱与韧性,踏出去、走回来,与更多的当事人相遇。
我大致盘点了这些年接手的案件,原来女性当事人已多达上百位。时至今日,我仍清晰地记得她们每一个人的眼泪与无助。她们之中,有差点被丈夫打死却仍旧困在婚姻中犹豫不决的人,我虽恨铁不成钢,却还是愿意等等她;有被亲生母亲卖掉几次依旧心怀善意的人,我愿意护送她一程;有被男友拍裸照后奋力一搏逃出生天的人,我愿意站在最前面声援她……她们最终因法律与我交织,有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能给的,只有那一丝温度,让她们有可以相信的东西。
与其说我是律师,不如说是船夫,送当事人去想抵达的地方,然后返回最初的地方继续出发,划过泥泞,拨开迷雾,见证人生。
这本书也如一艘船,我不经意间一看,满船都是流泪的女人。有些眼泪滴在了水里,被淹没了,有些滴在我心里,被记住了,即便下船,还想远远地望一眼她们。
进入大学的第一天,法理学老师曾对我们说:“法是狭窄的,狭窄到只需容纳公正就足够,同时它又是宽泛的,宽泛到与宗教、哲学乃至主义都相互依存,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宽泛到要负责每一个人的经历,不应该有任何的疏忽。法律的制定不是为了大多数人,而是为了所有人,所以,法绝不能是冰冷的机器。”
后来,我常告诫自己,无论看过多少悲凉,经历过多少失望,身为一名法律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温度。
我不想将此书单纯地定义为女性书籍,女性的痛,即为男性的疼,我们共同承受这个世界的好与不好。我不愿意打着任何旗号为自己谋利,我的当事人,她们眼里只有生活,很少为自己发声,但我会告诉她们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厌其烦地说。或许道阻且长,但作为船夫,我尚有逆流而上的勇气。
我无意美化自己的职业,手捧法的温度,是我的追求,也是我想看到的美好未来。
……
从匡腊英离婚到她回娘家,近一年过去了,却仍未有个好的结局,就连我一个律师都有点力不从心了。2021 年 5 月,我又着手帮匡腊英处理她娘家的侵权纠纷。
匡腊英叔叔说的话,与陈勇昆没什么两样:“哪里来的狗屁律师,还想管我们的家事。你随便找个人问一下,哪有嫁出去的女人找外人来娘家闹事的。”
我提醒他,按照法律规定,女儿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怎样都轮不到兄弟和侄儿,就算村集体要收回土地,也要有正式手续。何况匡腊英结束了婚姻,户口迁回来,就属于本地村民,理应继承父母的全部遗产。匡腊英叔叔拍着桌子道:“前后两边都想要,法院不是判了她前夫那边的房子有一半属于她的吗?怎么就见不得自家人好,母女俩回来打劫。”
我让匡腊英叔叔替自己侄女想一下,她在那边毕竟是个外人,孤立无援。匡腊英叔叔扬起脑袋,问:“她有替她的两个堂弟想吗?村里寸土寸金的,你让我们住哪里?”
匡腊英的两个堂弟更过分,抄起扁担威胁我:“房子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只是暂时分给大伯而已,自古男丁负责守祖产,谁敢抢我们的房子,我们就拿刀来劈。”
匡腊英担心我的安全,将我拉开,问我接下来怎么办。我问她:“你还想回来吗?”
匡腊英回:“当然想。虽然人心难测,但这里终究是我的家。我和父母美好的回忆在这里,他们没有重男轻女,只生了我一个,也没说要领养男孩。我自个儿也喜欢这脚下的土地。你看这儿视野开阔,外面稻田从不缺水,池塘里的鱼肥,土里的油菜花看不厌。不是所有女人都有能力去职场的,她们就是一辈子土里土气、住在农村。”
我理解匡腊英。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受限于经历,看着缺少智慧、耿直倔强、不讨人喜,但他们只是想守好自己本来有的东西。我想护送他们一程,恶劣的环境和人性桎梏人,那就试着改变环境,凿一汪清水涤荡人心。
我让匡腊英尽快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不料镇上办理户籍的工作人员告知匡腊英,要迁回村里,得村委会开具接收证明。
而村委会收了匡腊英叔叔的好处,故意刁难匡腊英,说必须经过她所在村民小组三分之二的村民签字同意,他们才能签字盖章。村民小组开出的条件则是,匡腊英要放弃继承她父母除金钱外的所有遗产。
在当地农村,之前十年左右是按户籍人口分配田地,后来由于很多人家占用农田建房子,田地没法进行继续分配,当地村民便默认原占有土地为固定的家庭土地承包。也就是说,增人不增田地,减人不减田地。
匡腊英若放弃继承,在村里就只空有一个户口。我去村委会告诉村支书,只要能证明匡腊英的娘家在这儿,他们就无权干涉。若他们一意孤行,我便向上面反映情况。
村支书勉强同意出具证明,但又说公章被妇女主任拿去公干了,要过两天才回来,他承诺一周之内一定把证明给搞定。匡腊英想着缓几天也不碍事,便回了镇上,让我也先回去。
谁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周后,匡腊英在电话里焦急地告诉我,因为房子的事,霞霞一气之下喝了农药,被送到了医院。匡腊英说自己“恨不得把所有人都剁了”。
原来,匡腊英和霞霞回村要证明的时候,发现自家的老屋屋顶没了一大半。前天晚上确实下了雨,但房屋不至于损毁成这样,匡腊英气得大喊:“我那混账前夫都没这么恶心我的,就因为我是个女人,碍着你们了?”
就在匡腊英要报警时,组里的人将她团团围住,说她的房子是危房,差点砸伤路人,要按照村相关规定拆除。说着就当着匡腊英的面拆起木板。这时,霞霞从书包里翻出一瓶农药,毫不犹豫地拧开盖子喝了一口,边喝边哭喊:“妈妈,我真没用,让他们这么欺负我们娘俩……”
万幸的是,霞霞喝的不是百草枯,送医院救治后,没有生命危险。农药是霞霞偷拿的,按照她后来的说法:“我没有能力保护妈妈,只能拿农药来吓唬爸爸家和妈妈家的坏人。”
……
——《在农村,离婚的女人无家可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