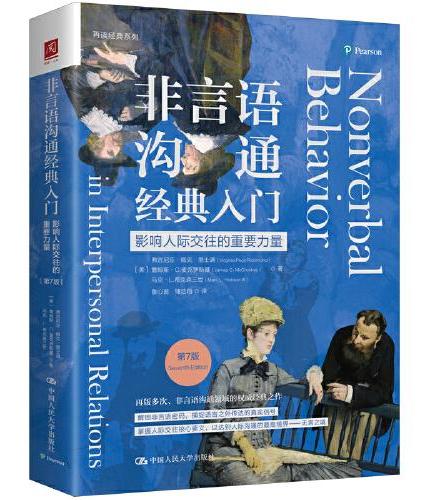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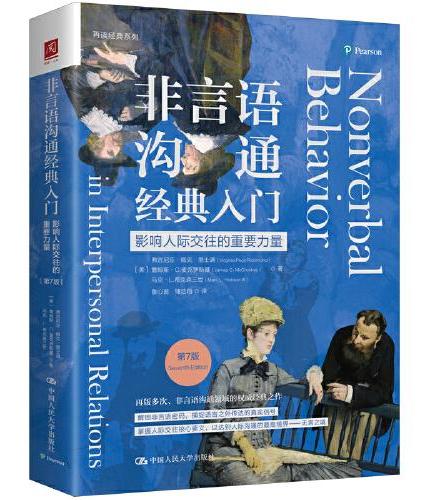
《
非言语沟通经典入门: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力量(第7版)
》
售價:NT$
560.0

《
山西寺观艺术壁画精编卷
》
售價:NT$
7650.0

《
中国摄影 中式摄影的独特魅力
》
售價:NT$
4998.0

《
山西寺观艺术彩塑精编卷
》
售價:NT$
7650.0

《
积极心理学
》
售價:NT$
254.0

《
自由,不是放纵
》
售價:NT$
250.0

《
甲骨文丛书·消逝的光明:欧洲国际史,1919—1933年(套装全2册)
》
售價:NT$
1265.0

《
剑桥日本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NT$
918.0
|
| 編輯推薦: |
?笔记中的科学史。
?那些曾经被忽视、遗忘,甚至已经消失的伟大的笔记,见证了现代早期科学思想的诞生。
?一部如散文般生动活泼的科学史著作,促使我们对记录、处理信息进行反思。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部科学史著作,深入探讨了“笔记”在17世纪英国科学领域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深入分析当时英国科学、思想名家制作的形式各异的“笔记”,揭示了他们在记录、搜集和检索信息方面的独特见解和实践,为理解现代早期的“科学革命”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书的主要研究时段为17世纪,英国科学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涌现了弗兰西斯·培根、罗伯特·玻意耳、威廉·哈雷、罗伯特·胡克等科学哲学家、科学家,诞生了全球首家社会化科研机构——英国皇家学会,经验主义兴起——科学家开始重视实验和观察,丰硕的科研成果——英国科学成果约占全球的40%,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天才的世纪”。作者理查德?约对科学史中这一重要时期的研究可谓另辟蹊径,他选择了较少被人关注的事物——笔记,展示了当时的科学先驱如何通过笔记来处理和分析信息,以及他们如何将笔记作为科学探究和实验的辅助工具。作者还探讨了如何通过笔记来记录和传播科学发现,以及笔记在形成科学共识和学术网络中的重要作用。
在整体结构上,作者首先概述了笔记在现代早期科学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信息与经验对知识积累的影响,从第四章开始,每一章介绍一位科学名家的笔记实践,让读者有机会走进科学大家的思想世界。此外,作者设置的编者按、前言、注释、手稿来源等部分,为读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信息和解释,有助于提升阅读体验。
在史料运用方面,除了书信、笔记等科学家的个人档案,作者还利用了英国皇家学会、大英图书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收藏的珍贵文献,确保了研究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
| 關於作者: |
理查德?约(Richard Yeo),现任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研究员。
译者简介:
李天蛟,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已出版译著《王莽》《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食物小传:派》《金钱、奇珍异品与造物术:荷兰黄金时代的科学与贸易》。
|
| 目錄:
|
编者按
前 言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广袤的记忆与浩瀚的笔记
第三章 信息与经验感性
第四章 塞缪尔·哈特利布社交圈的笔记
第五章 记忆力竞赛 :约翰·比尔与罗伯特·玻意耳论经验信息
第六章 罗伯特·玻意耳的松散笔记
第七章 笔记大师约翰·洛克
第八章 集体笔记与罗伯特·胡克的动态档案
第九章 结语
致 谢
手稿来源
|
| 內容試閱:
|
前 言
笔记可以用来记录书中的段落,记载人们对世界的观察,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想法。我们可以把笔记写进手稿,也可以通过印刷书籍、纸片、索引卡片、袖珍型或各种尺寸的大型对开装订笔记本保存笔记内容。可以按照日期、主题对内容进行分类,或者对事件、问题及愿望清单进行粗略地编号排序。笔记内容可以是未来作品的草稿,也可以是对已发表文章所作的注释。笔记还可以成为一种发挥撒手锏作用的工具,部分原因是偶然性与有意为之的结合。比如达·芬奇的小张折叠的镜面书写,莱布尼茨煞费苦心重新想象出的笛卡尔那遗失的笔记,牛顿年轻时那写满了自身罪恶的随身笔记本,达尔文那记录了自然选择进化论第一幅树形图的“红色笔记本”。再比如 19 世纪的艺术家和旅行者青睐的“魔力斯奇那笔记本”(Moleskine),布莱恩·塞兹尼克(Brian Selznic)作品中年轻的雨果·卡布里特(Hugo Cabret)珍爱的机械素描本,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笔记可以构成整部遗失作品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内容,还可以体现从未真正落笔的作品精华。笔记可以唤起记录者的记忆,同样可以为其他人或者后世提供有关信息。
我将在这本书里向读者展示现代早期科学领域的一些英国领军人物的笔记方法,以及他们在记录笔记以及收集并检索信息方面的观点。罗伯特·玻意耳(Robert Boyle)、约翰·奥
布里(John Aubrey)、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约翰·洛克(John Locke)、马丁·利斯特(Martin Lister)、 约 翰· 雷(John Ray)以及罗伯特· 胡
克(Robert Hooke)在与自己的欧洲好友和联络人通信的过程 中,践行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从文本中摘录内容的做法,在自己的个人笔记中积累了大量谚语、格言、引语以及其他内容。这种笔记叫作“札记”,根据主题或者标题对相关内容进行分类整理。这里的问题在于,“札记”在教学和学术领域是一种传统的文本模式,常常被那些信奉科学的“现代人”贬为一种陈腐且不适合研究自然世界的方法。17 世纪早期,伽利略(Galileo Galilei)曾在写给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信中,讽刺了那些坚持认为可以通过研究书籍作品来理解大自然的学者 :
这种人把哲学当作一种类似于《埃涅伊德》(Aeneid)或者《奥德赛》(Odyssey)的书籍,认为真理并非来源于世界或者大自然,(用他们的话来说)而是存在于文献整
理之中。我希望能够和你就这件事一起欢笑,度过愉快的时光。
在这里,伽利略用开玩笑的口吻提出了一种观点,这种观 点很快就被解读为文献学与针对自然世界的实证(包括实验)研究之间的内在冲突。
英国哲学家、大法官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同样贬低过那些过度依赖书籍的现象,认为这种现象在他的时代构成了自然知识停滞不前的一种主要诱因。培根的观点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于 1660 年)成员的支持。这些学会成员在辩论中,将前几代自然哲学家使用的书籍与自己的观察方法、实验方法对立起来。本书所提到的人物大多数是皇家学会成员以及培根的仰慕者。他们认为,培根对“具有文献学特征的一切事物”的批评与收集博物学信息的呼吁具有共存关系,而想要获得博物学信息,就需要坚持不懈地制作大量笔记。今天的我们对于那些通过实验室、实地考察或者机械化自动记录的详细笔记逐步积累的大量数据早已司空见惯。早在 17 世纪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浩瀚的知识海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纳入人的记忆进行储存和操作。科学革命期间出现了一种相反的观点,它认为,想要在自然知识领域取得进步,就要重新对记忆和其他信息储存手段进行平衡。人们普遍认为,经验科学需要大量详细信息,这些信息需要通过精确且持久的记录进行保存,进而供分享与交流使用。英国科学名家针对记忆、笔记以及其他形式的记录在收集和分析经验信息时的最佳使用方法进行了思考,并对这些信息载体进行了重新评估。他们通过制作大量笔记来应对印刷书籍数量激增的现象,与此同时,通过笔记收集并记录了图书无法提供的各类信息。他们超越了培根和诸多人文主义者,对历史进行了探索,在古老的希波克拉底医学传统中寻求长期研究项目所面临的挑战和必要性。在此过程中,他们把笔记和信息管理转化为现代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内容涉及现代早期欧洲的科学史、书籍史、信息文化史方面的相关研究。第一,正如伽利略和培根所提到的,本书同样提出了“两种文化”的问题。本书研究了人文主义学者与
科学人士之间的密切关联,认为不应该将“书卷气”与经验主义、独立研究与集体研究置于严重对立的位置。其实,诸如玻意耳、洛克等科学名家在提到自己的广泛阅读或者朋友时,认
为自己充满了“书卷气”。在他们看来,争议的焦点不是书籍的价值,而是如何使用书籍。因此,洛克曾批评那些“投身于某种学派、具有书卷气的饱学人士”,认为他们无法与他人进行
理性地对话。洛克还曾嘲讽那些严重地依赖札记的人,认为这些人针对各类问题堆积了正、反观点,自身却没有进行适当地思考。他提到,这些人“只能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侃侃而谈,无法坚定地作出独立判断”。我对英国名家笔记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发现了全新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个人层面的研究工作造就了日后的文献学研究与实证科学研究领域。
第二,本书将针对印刷文化与手稿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展开探讨。伊丽莎白·埃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曾提出,印刷与科学革命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此后,相关领域再次重申了手稿交换在现代早期知识生活中持续发挥的作用。哈罗德·洛夫(Harold Love)曾论证了手稿交换在政治和音乐领域中的运行方式。后来的研究表明,手稿交换同样存在于知识群体网络与科学群体网络之中。现代早期欧洲的医学、化学、植物学、实验以及古文物领域的相关最新研究表明,印刷品包含的信息曾通过笔记和通信转化为洛夫所谓的“抄写交流” (scribal communication)。人们认为这些笔记比印刷品更灵活、更易于思考,且非常适合用于自我定义的小群体的快速交流。这种观点并非出于对手稿文化的怀旧情怀。相反,这种观点认为,印刷品的固定属性发挥最大作用的阶段是科学研究的结束阶段,而非初始阶段。不过为了进行更广泛地传播,人们也曾用到印刷形式的调查问卷。不过这些问卷通常会邀请他人提出其他问题,因此手稿形式的问卷更为常见。
第三,我的关注点是个人记忆与储存和处理信息的外部记录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关主题在当代认知心理学领域中属于热门话题。通过分析科学名家的笔记和思想,我对相关历史维度展开了思考。这些科学名家在实证研究中往往需要处理大量信息。想要理解他们的思想,就需要密切关注记忆、回忆以及信息记录之间的区别。17 世纪晚期曾出现一种转变——人们起初非常看重记忆,特别是记忆训练所具有的价值,后来开始更多地依赖手写资料和印刷资料。不过,由于我们现阶段所处的历史理解水平,所以很难对相关内容作出明确陈述。我的研究材料主要包括 17 世纪英国知识领域重要人物保存在各类文件中的笔记和信件等。通过这些材料可以得出这样一种推论 :各类群体和个人面对各种知识问题时,通过各种方式在记忆(无论有没有笔记的辅助)与外部记录之间作出了权衡,并得到了各种结果。培根及其在皇家学会的追随者曾告诫人们,记忆无法对细节进行妥善处理,与此同时,他们在材料整理方面提出了一些新方法,利用这些方法辅助记忆,进而辅助思考。另外,他们希望能够找到质量较好的文献档案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石,不过他们仍然坚信个人的深刻记忆和生活经历同样是促进知识进步的重要因素。
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学者,也是心理测量研究领域的先驱。他在作品《旅行的艺术》(The Art of Travel,1855 年)中,针对笔记的记录和保存方法提出了极具实用性的建议,探讨了质量最好的纸张、铅笔、墨水、各类袖珍笔记本,还提到了信息在各种工具之间的转移。高尔顿强调,必须在记忆清晰的情况下及时记录笔记,作笔记的方式需要能够为他人提供帮助,“很久之后,即便陌生人看到这部笔记也能理解其中的内容,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类建议在 17 世纪屡见不鲜,因此我们必须发掘收集与储存信息的工具和技术方面的历史。英国名家借鉴了他们经常抨击的传统教学法,同时进行了一些他们自认为的创新。不过有时他们没有意识到,此前的一些学者也采取过类似的举措。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通常是,这些学者对早期笔记的理解主要依赖于那些公开发表的建议和规则,特别是人文主义学者与耶稣会士提到的内容,而没有密切关注个人层面的各种私人笔记。比如,这些英国名家没有注意到,图宾根大学的希腊语教授马丁·克鲁修斯(Martin Crusius,1526—1607 年)曾经在自己手中的荷马著作中添加了大量日记、松散笔记以及通信内容等注释,展示了抄写、日期测定、交叉引用等复杂的方法,还对大量资料来源与信息中的材料进行了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讲,马丁·克鲁修斯是这一代欧洲学者的典型代表,这些学者在印刷信息的压缩、组织、检索方面开创了各类技术,相关技术得到了流传和
应用。
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17 世纪 40 年代,流落他乡的普鲁士人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曾在为英国伦敦和欧洲地区学术界与科学界协调信息的过程中,针对类似的实践进
行了调查研究。他对托马斯·哈里森(Thomas Harrison)设计的一种新奇装置(由他人制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种装置主要用来检索松散纸片上的笔记,不过这项发明后来逐
渐无人问津。20 世纪,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 年 ) 开 发 了 一 种“ 卡 片 盒 笔 记 法 ” (Zettelk?sten)。这种方法使用一组盒子对卡片笔记进行编号、归档和关联。尼克拉斯·卢曼很可能没有注意到,托马斯·哈里森曾在现代早期发明了类似的装置。高尔顿重提古老建议针对的是包括冒险者和探险家在内的新受众,不过他的这种做法似乎构成了笔记历史的一个特征——在不同的时代,在某一种情境之中早已风靡的各类技术和技巧,在另一种情境中需要重新发明创造。18 在探讨现代早期笔记记录者的过程中,我无意主张这些人创造了全新的方法或技术。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如何对一种既定的实践活动进行开发,满足自己认为与新科学的进步有关的全新需求。
英国名家把笔记看作科学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们看来,笔记产生于博物学、实验化学以及实验生理学在观察方面的要求,因此笔记完全适用于伊夫林有关园艺学的研究,玻意耳针对空气重量和人体血液的开创性研究,洛克关于气象和疾病病因的研究,以及胡克关于化石和地震的研究,等等。英国名家认为,这些内容构成了培根所定义的“博物学” 的部分内容。19 有人认为,这些研究的动力来自对稀有、奇异和奇妙现象的好奇心。在不具备重大资质的情况下,这种由好奇心和热情产生的驱动力不适用于顶尖学者。20 这些英国名家一致认为,新科学的重点不能局限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共同”经验。他们采纳了培根的观点,认为新科学还必须包含“偏离性实例,也就是大自然的失误、多变以及奇异现象。大自然会在这些实例中偏离自身的正常轨迹”。此外,英国名家同样采纳了培根对于更详细的信息所提出的要求,根据这类要求,那些看似平平无奇的日常现象同样应该被纳入为归纳建立基准线的工作。玻意耳认为,新科学的研究工作需要的是对所有信息均持开放态度的知识分子。他指出,想要“成为名家”,就需要具备“温顺”(“均匀”)的特质,22 温顺的姿态可以规避修辞方面的修饰和理论方面的预设,有利于进行第一手观察和撰写实验报告。
上述内容可以产生一种推论——认真记录笔记可以为所有信息提供保障。第一,奇特的物品和人为现象可能在脑海中留下持久的印象,但各类证言、观察和实验仍然需要记录,以便进行适当地评估和对比,评估和对比的时间往往很长。第二,在缺乏概括性理论或系统的情况下,无法通过记忆记录具体细节,其中包括时间、地点等。第三,与记忆相比,书面形式更适合对碎片化数据进行移动和整合。在提出以上三点的同时,英国名家的知识立场与做笔记,以及有关记忆与外部记录之间信息分配流程的思考,紧密关联。
对于那些参与培根式科学研究的人而言,可能无法必然在一生之中享受发现和理解的满足感。因此英国名家希望个人笔记能够为合作研究以及流传后世的科学档案作出贡献。这里的一个问题在于,个人笔记处于所有者的掌控之中,所有者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和观念来决定笔记的记录和编排方式。这一类个人倾向为笔记赋予了提醒与提示的功能。想有效地开展长期的科学研究活动,研究人员需要对收集、展示和交流材料的标准方法达成共识。在理想的情况下,这种共识可以延续几代人之久。另外,通过各类网络——比如商业贸易、宗教使团、“书信共和国”等途径——获取的经验信息必须得到过滤和审查。早期的皇家学会主要依赖这一类网络获取信息,因此必须通过信用、可信度、质疑等方面的标准对信息进行监控。皇家学会的主要成员经常在与勤勉的学会秘书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的通信中表示,希望能减少相关意外事件的发生。他们认为笔记的形式和功能是一种基本变量,把笔记作为收集、记录和传播信息的一部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终提升了日常信息收集工作的有效性。19 世纪 40 年代,《笨拙》(Punch) 杂志讽刺了当时的科学研究普遍具有的一种特征,“在过去的一年里,索夫汀维茨先生(Softinwitz)受任在伦敦摄政街记录
地震震级。最终,他根据自己的观察结果提交了四令空白的大页纸”。
本书第一章介绍了英国名家以及他们对于阅读、学习和科学持有的态度,现代早期欧洲使用的笔记和笔记本类型,记忆、笔记、思考三者之间的关系等内容。第二章探讨了人文主义学者与耶稣会在笔记和记忆训练方面的传统,并考察了约翰·伊夫林和罗伯特·索思韦尔(Robert Southwell)的笔记。第三章阐述了实证信息的全新必要性,培根曾对这里的内容进行过预测,相关内容得到了皇家学会成员的拥护。有关笔记的思考解释了新兴经验科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接下来的四章内容涉及一些关键人物,描述了他们关于笔记的方法与目的、深层个人记忆、信息的系统展示、检索书面记录等内容的观点。每一章都将为读者呈现大量的个人档案资料。第四章展示了伦敦情报人士塞缪尔·哈特利布收集的大量现存资料,其中包括哈特利布本人的日记,以及哈特利布打造的通信网络所产生的信件和文件,相关人士包括约翰·比尔(John Beale)、威廉·佩蒂、约翰·佩尔(John Pell)、托马斯·哈里森等。第五章结合玻意耳与哈特利布、比尔等人的关系,探讨了玻意耳有关记忆和笔记的观点。第六章引用了玻意耳论文的部分内容,描述了玻意耳的笔记模式以及他对于笔记、记忆、科学信息传播三者之间关系的看法。第七章介绍了洛克终其一生勤勉记录笔记采用的方法和基本原理,附加洛克个人笔记的内容。这一章同样提到了如何使用洛克的方法进行大规模研究。第八章探讨了集体笔记在合作项目中(如约翰·雷和马丁·利斯特的合作项目)面临的挑战,以及奥尔登堡身为皇家学会信息管理人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章涉及的主要人物是罗伯特·胡克,他对笔记的观点与他针对机构档案的看法紧密交织。第九章为结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