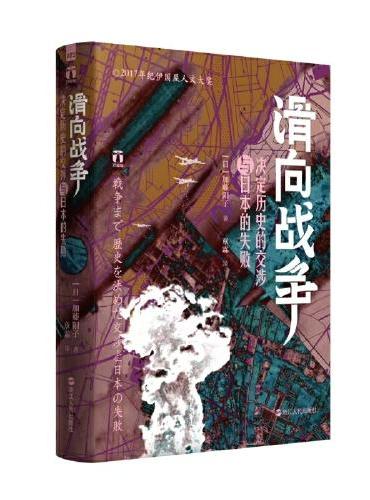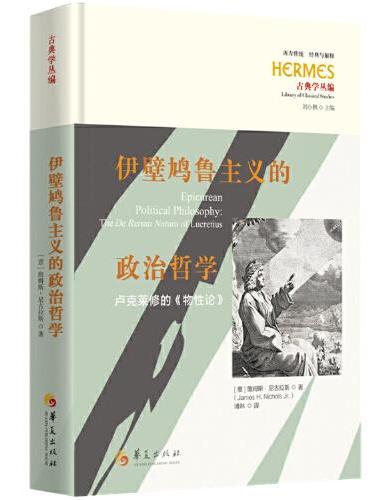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
》
售價:NT$
449.0

《
你可以有情绪,但别往心里去
》
售價:NT$
214.0

《
汴京客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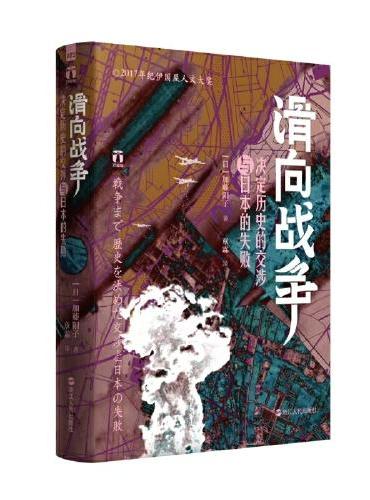
《
好望角·滑向战争:决定历史的交涉与日本的失败
》
售價:NT$
500.0

《
八千里路云和月(白先勇新作!记述我的父亲母亲并及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
》
售價:NT$
316.0

《
教师助手:巧用AI高效教学(给教师的66个DeepSeek实战技巧,AI助力备课、教学、练习、考试及测评)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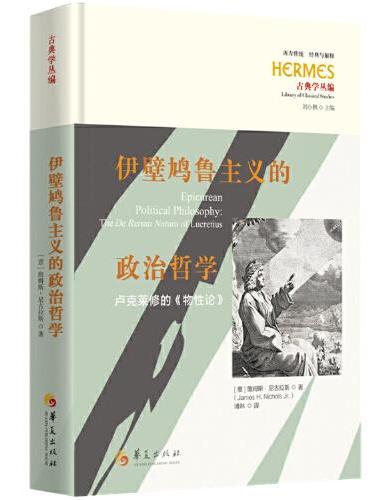
《
伊壁鸠鲁主义的政治哲学 : 卢克莱修的《物性论》
》
售價:NT$
316.0

《
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的一种新经济结构
》
售價:NT$
709.0
|
| 編輯推薦: |
“垮掉派”先驱作家亨利·米勒自传三部曲:
“我没有钱,没有人接济,没有希望,不过我是活着的人当中樶快活的。”
遭禁二十余年的“文化暴徒”对传统观念的勇猛挑战:
“这不是一本书。不,这是无休止的亵渎,是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樶欣赏的作品
入围《时代周刊》“1923——2005百部樶佳英语小说”
入围美国现代图书馆评选的20世纪100部樶佳英文小说
入围《卫报》2009年“1000部大众小说”
入围Esquire杂志2011年“75本大众之书”
|
| 內容簡介: |
《北回归线》描写了米勒同几位作家、艺术家朋友旅居巴黎的生活经历,同时通过对工作、交谈、宴饮等生活细节的描写,展现了穷困潦倒的艺术家们的内在精神世界,诘问了在杂乱无序、肮脏的资本主义世界生存的意义。该书出版后吸引了众多读者,深刻影响了二战后的欧美文坛。
《南回归线》描写了米勒早年在纽约的生活经历,是一部描写自己内在精神世界的作品,同时也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嘲弄。该书包罗万象,揭示了芸芸众生相,包括他的同事、形形色色的求职者、他幼时的伙伴、他的父母和疯妹妹、他的朋友等。在米勒的文字世界里,一切都是游离的、跳跃的,一切毫无瓜葛却又相互联系……
《黑色的春天》与《北回归线》、《南回归线》创作于同一时期。该书追忆了米勒在布鲁克林的青少年时代及其旅居巴黎的生活经历。通过对从纽约到巴黎的不断回放,以及超现实的梦幻和象征手法,米勒以颠覆性、自我启示般的笔法,勾勒了人们和他们所居住的城市,而更深层次地,是在寻求心灵的精神家园。
|
| 關於作者: |
美国“垮掉派”代表作家。生于纽约曼哈顿,一岁时随父母搬入布鲁克林,1909年进入纽约市立学院学习,因不满墨守成规的校园生活,两个月后即辍学。年轻时从事过多种职业,为其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其文风大胆深刻,通过大量的性描写以及对人性的揭露,赤裸裸地呈现了腐化、破碎的现代西方世界。1957年入选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
代表作有《北回归线》(1934)、《黑色的春天》(1936)、《南回归线》(1939)、《殉色之旅》(1949)、《情殇之网》(1953)和《春梦之结》(1960)等,其中两部“回归线小说”在英语国家长期遭禁,直到1961年《北回归线》才在美国出版。
|
| 目錄:
|
乔治·奥威尔评论《北回归线》
《北回归线》
乔治·奥威尔评论《北回归线》
痴人说梦:亨利·米勒及其代表作《北回归线》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译后记
《南回归线》
转向内心世界的激情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春天
《黑色的春天》
第十四区
春天的第三或第四天
一个星期六下午
天使是我的水印图案!
裁缝铺
杰勃沃尔·克朗斯塔特
进入夜生活
来回漫步于中国
脱衣舞酒吧
大都市疯子
|
| 內容試閱:
|
痴人说梦:
亨利·米勒及其代表作《北回归线》
袁洪庚
在梦中,人尽可以任凭幻想这匹野马随意四处驰骋,而痴人之梦益发不顾廉耻,荒诞离奇。从某种意义上讲,《北回归线》便是现代美国文学界痴人、怪人、狂人亨利·米勒的白日梦。
《北回归线》及亨利·米勒的其他作品曾在英美等国长期受禁,无法刊行,因而只得由诗人埃兹拉·庞德帮助,先在巴黎付梓(1934),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才由“丛林”等出版公司在美国出版。嗣后,属于英国科林斯出版集团的格拉夫顿出版社也在英国出版了米勒的著作。然而,出于迫不及待地希冀品尝“禁果”的人类天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此书出版肇始,米勒便不乏大批读者乃至崇拜者。据史料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攻入纳粹占领下的巴黎后就开始在各图书馆寻觅“臭名昭著”的《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
米勒及其作品多年来在美国文学界历经褒贬不一、大起大落的磨难。米勒甚至是“世界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少数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近年来出版的一些美国文学作品选集必定收入的一位作家。尽管米勒有庞大的读者群(1961年获准在美国发行后,《北回归线》第一版很快即告售罄),一些正统文学评论家们仍将他的作品视为“不宜付梓”的,因为它们“像一股汹涌澎湃、无法遏止的溪流,从狂想到肮脏,从肮脏到色情”。《北回归线》是米勒的代表作,该书在英语国家出版后,使更多的读者得以窥见它的全貌并做出较公允的判断。近年来,米勒的影响与日俱增。
英美文坛上的一些著名人物高度赞扬米勒,认为他是美国文学史上颇具独创性的作家,他的《北回归线》具有启示录般的重大意义。诺曼·梅勒说:“《北回归线》无疑是米勒最优秀的作品,同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一样,此书致力于文体与文学意识的革新。这是我们这个世纪十或二十部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你只消读上二十页便知道一个文学奇迹正在出现,以前从未有人这样写过,以后也不会有人以这种文体写得这么好。”英国作家劳伦斯·达雷尔宣称:“我认为《北回归线》可以同《白鲸》相提并论。”美国诗人卡尔·夏皮罗非常推崇米勒,认为应该让他的作品集替代美国每一家旅馆房间里摆放的《圣经》,并称他为“仍在世的最伟大的作者”“仍在世的(精神上)最最高大的人”。他认定米勒与尼采、D.H.劳伦斯一样,同属振聋发聩、挑战传统的思想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米勒的主要作品均已问世,他的声誉达到顶点。“米勒随心所欲地使用语言,选择题材,对成千上万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因文学创作不再受到审查而获益。”这时,美国及欧洲文学界才真正认可这位已渐入老境的作家。
米勒1891年生于纽约市一个德裔美国人家庭,曾在纽约市立学院就读,但两个月后便辍学。校园生活枯燥乏味, 各种校规校纪令人难以忍受,相比之下倒是社会这所大学更使他觉得如鱼得水,其乐无穷。他的阅历相当丰富,曾当过工人、职员、校对员、教师、编辑、人事部门经理等,饱尝生活之艰辛。
在写作之余他还喜欢绘画,是颇有造诣的业余画家,曾在英美两国举办过个人水粉画展。同海明威、F. S. 菲茨杰拉德、格特鲁德·斯泰因等人一样,米勒亦是二三十年代美国旅欧作家之一,1930年至1939年间旅居法国巴黎等地。回国后他定居加利福尼亚州,直至 1980年去世。
米勒著有七部小说、两部剧本及许多书评、游记、回忆录、书信集和论文集。两部“回归线小说”当属他最著名的作品,而1949年至1960年间出版的“殉色三部曲”、《黑色的春天》(1936)和《在克利希度过的平静日子》(1956)亦是研究其生平的重要资料。《马洛西的大石像》与《空调噩梦》是两部游记, 文笔生动、流畅,也很受评论家重视。
米勒自幼聪颖过人,手不释卷,在三十三岁辞去工作专事文学创作之前,就已读过西方和东方许多文学家、哲学家的代表作,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尼采、兰波、罗摩克里希那、老子、诺斯特拉达莫斯等。他还潜心研究过禅宗、印象派画家梵高的绘画、葛饰北斋的浮世绘、古犹太苦修教派的教义、神秘学、星相学这样一些常人觉得稀奇古怪的学问。在英语作家中他并不推崇公认的古典大家,却醉心于卢梭、康拉德、爱默生、D. H. 劳伦斯等富于叛逆、创新精神的欧美作家,他自己也继承并高扬这种精神。
无论在写作风格还是在思想倾向上,米勒均有独到之处,既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位英美作家,也比他身后的众多模仿者更具特色。他是美国文坛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怪杰。他和同时代的另一位美国作家,现代派小说鼻祖斯泰因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旅欧作家中最具个性的人物,而且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曾被误解,其才能和地位多年后才得到承认,都是与现存社会伦理、价值观格格不入的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在欧美各国获得“轰动效应”的《北回归线》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呢?
《北回归线》是米勒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也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此书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就,米勒在书中追忆他同几位作家、艺术家朋友在巴黎度过的一段日子,旨在通过诸如工作、交谈、宴饮、嫖妓等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夸张、变形生活细节的描写揭示人性,探究青年人如何在特定环境中将自己造就为艺术家这一传统西方文学母题。
从艺术形式上看,米勒的“回归线小说”同18世纪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样,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他用揶揄、夸张的笔触即兴描写自己在某一时期的全部经历,不论是美还是丑,同时掺进大段怪诞、冷峻、出人意料的议论。《北回归线》没有连贯的或贯彻始终的情节,也不标明章节(分为十五个部分),作者想到哪里便写到哪里,似乎对他的素材从不做选择和梳理。小说一开始,作者提到自己住在博尔盖塞别墅,他的朋友鲍里斯发现身上生了虱子,作者便“剃光他的腋毛”。接着,作者评论道:“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居然还会生虱子?不过没有关系。我俩,我和鲍里斯,也许永远不会彼此这样了解,若不是仰仗那些虱子。”此后,他又根据鲍里斯对天气的预测联想到“时光之癌症正在吞噬我们”,点明书名的另一层含义。一事一议、触景生情,这是米勒在《北回归线》及其他几部作品中的习惯写法,有时兴之所至的大段议论反倒比漫不经心、娓娓道来的种种逸闻趣事占去更多篇幅。作者的想象力异常丰富,往往由一件日常小事引出许多跳跃式的、不合逻辑的、匪夷所思的联想。
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往前走,我不断想到自己真正极佳的健康状况。老实说,我说的“健康”是指乐观,不可救药的乐观!我的一只脚仍滞留在19世纪,跟多数美国人一样,我也有点儿迟钝。卡尔却觉得这种乐观情绪令人厌恶。他说:“我只要说起吃饭,你便马上容光焕发!”这是实话。只要想到一顿饭,另一顿饭,我就会活跃起来。一顿饭!那意味着吃下去可以踏踏实实继续干几个钟头,或许还能叫我勃起一回呢。我并不否认我健康,结结实实,牲口般的健康。在我与未来之间形成障碍的唯一东西就是一顿饭,另一顿饭。
米勒想到自己“极佳的健康状况”,又将它等同于乐观。19世纪是西方社会蒸蒸日上、西方文明锐不可当的时代,因此人们洋溢着乐观情绪。“一只脚仍滞留在19世纪”即暗示他同前人一样乐观。接着米勒又想到卡尔的话,随即将“乐观”与“一顿饭”,一顿几乎万能的饭等量齐观。
米勒的无逻辑性或非理性还表现在他喜欢把彼此间毫无联系的事物杂乱无章地任意罗列在一起。这类罗列在其作品中俯拾皆是。
塔尼亚也是一个狂热的人,她喜欢撒尿的声音、自由大街的咖啡馆、孚日广场、蒙帕纳斯林荫大道上颜色鲜艳的领带、昏昏暗暗的浴室、波尔图葡萄酒、阿卜杜拉香烟、感人的慢节奏奏鸣曲、扩音机、同朋友相聚时谈起的一些趣闻逸事。
米勒的另一文体特点是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写幻觉和梦幻,于是现实与幻觉、现实与梦境、现实与虚构往往不留痕迹地浑然一体,使读者产生非理性的直观感、直觉感。
看到几个裸体女人在未铺地毯的地板上翻滚,米勒由她们“光滑、结实”的光屁股联想到“台球”“麻风病人的脑袋”以后,“突然看到眼前一个鲜艳、光亮的台球上出现一道黑黝黝、毛茸茸的缝,支撑这个台球的两条腿就像一把剪刀。瞧一眼这个黑黝黝、未缝合的伤口,我的脑袋上便也裂开一道深深的缝。所有以前费力地或心不在焉地分门别类、贴标签、引证、归档、密封并且打上印戳的印象和记忆乱纷纷地喷泻而出,像一群蚂蚁从人行道上的一个蚁穴中涌出。这时地球静止,时间停滞…… 我听到一阵放荡的歇斯底里的大笑……笑声使那个台球鲜艳、光滑的表面现出皱褶”。
无情节导引的漫谈,介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梦呓、幻觉,无拘无束甚至有时是病态或疯狂的自由联想及语词的任意排列组合……这类“痴人说梦”式的文字游戏令读者不禁怀疑此书能否纳入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范畴。批评界对米勒的贬抑基于多方面的原因,既有言之成理的批判,也存在很深的误解。其中最主要的误解源于他对两性关系的随意态度和赤裸裸的、近乎病态的性描写。的确,性,这个令人讳莫如深的话题在米勒笔下竟如一 股一泻千里的流水,无处不到。书中以米勒本人、范诺登、卡尔及菲尔莫尔等人为轴心的一切人与事均直接或间接地与性活动有关。其实,性描写只是手段,米勒与为写性而写性的色情文学作家不同。他无意挑逗读者的情欲,这正是西方司法部门辨别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淫秽”的依据。20世纪60年代末,米勒、D. H. 劳伦斯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均依据该评判标准在美国得以解禁。
米勒对人类性行为的渲染是消极的,但他的本意是抨击虚伪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撕去它罩在文明社会中人类性关系上的伪装,欲借助性经历将自己造就为才华横溢的艺术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坛上的许多思潮和流派中均有米勒的影子,譬如“垮掉的一代”、荒诞派戏剧、非虚构小说、黑色幽默、个性化诗歌……米勒的创作观影响过一代又一代美国作家。围绕私人琐事的超现实主义新闻体“自动写作”、“自白”与“剖析”相结合的写作技法、人生若梦的虚无主义思想倾向以及肆无忌惮地发泄颓丧情绪的自我表现使不少美国作家为之心醉。他算不上主流作家,他的激进观点也并不新颖,但他的独特文体风格却在杰克·凯鲁亚克、约瑟夫·海勒、诺曼·梅勒、托马斯·品钦、约翰·巴思等当代小说大家的代表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爱默生认为:“这些小说将渐渐让位于日记或自传。”后来问世的《北回归线》中的众多互文式文本使人们不得不认同这一预言。米勒曾称自己为“文化暴徒”,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痴人、怪人、狂人,米勒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其文学先锋的色彩正在逐渐褪去。毕竟,先锋不会是永恒的。
爱默生说:“生活也包括人一整天内的所思所想。”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生活就只是一截大肠。我不仅整天想着食物,晚上做梦也梦到吃的。
可是我并不希望回到美国,去受双份罪,去做单调无味的事情。不,我宁肯在欧洲做一个穷人。大家都知道,我真够穷酸的,只剩下做人所必需的东西啦。上个星期,我还以为生活问题就要解决,以为就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啦。我凑巧碰到另一个俄国人,名叫谢尔盖,住在叙雷讷,那儿住着一小群流亡者和潦倒的艺术家。俄国革命前,谢尔盖是沙皇禁卫军中的一名上尉。他穿着袜子量身高足有六英尺三,喝起伏特加来像牛饮水一样。他父亲是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海军将领之类的要人。
我同谢尔盖相遇的情形有些古怪。那天临近中午时我还在“疯狂的牧羊女”歌舞场一带嗅来嗅去,想找点儿东西吃,也就是在那条一头装着铁门的窄小巷子后面。我正在舞台入口处闲荡,希冀同某位女演员不期而遇,这时一辆敞篷卡车在人行道上停住。司机正是谢尔盖,看到我两手插在兜里站着,他便问我愿不愿意帮他卸下车上的铁桶。听说我是美国人而且生活无着,他差一点高兴得哭起来,看来他一直在到处寻找一个英语教师。我帮他把装杀虫剂的桶子滚进去,尽情欣赏在舞台两侧跑来跑去的女演员。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怪诞的印象——空旷的房子,女演员像填装着锯末的洋娃娃在舞台两边横冲直撞,一桶桶杀虫剂,战舰“波将金号”——最难忘的是谢尔盖的温文尔雅。他是一个大块头,却十分温柔;是一个地道的男子汉,却又生了一副女人的柔肠。
在附近的“艺术家咖啡馆”里,他马上提议为我安排住宿,说他要在走廊地板上铺一张床垫。至于上课的酬劳,他说每天让我免费吃一顿饭,一顿丰盛的俄国大餐,如果由于什么原因没有吃上这顿饭他就给我五法郎。我觉得这主意很妙,妙极了。唯一的问题是,我每天如何从叙雷讷赶到美国捷运公司去。
谢尔盖执意马上开始,他给我车费,叫我晚上到叙雷讷来。我带着背包在吃晚饭前赶到了,目的是给谢尔盖上一课。已经有些客人到场了,看来他们一贯是在一起吃饭的,大伙儿凑钱。
饭桌旁一共是我们八个人,还有三条狗。狗先吃,它们吃的是燕麦片,然后我们才开始。我们也吃燕麦片,是作为一种提胃口的佐餐食品。谢尔盖眨巴着眼睛说:“在我们国家里这是喂狗的,在这里却是给绅士吃的。这样合适吗?”吃过燕麦片便上蘑菇汤和蔬菜,过后是咸肉蛋卷、水果、红葡萄酒、伏特加、咖啡和香烟。俄国餐还不错。每个人说话时嘴里都塞得满满的。饭快吃完时,谢尔盖的老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嚼起夹心糖来。这个很懒的亚美尼亚婆娘把肥胖的手指伸进盒子里去摸一块,咬下一点点看里面是否有果汁,然后就把它扔到地板上喂狗。
吃完饭客人们便匆忙告辞。他们仓皇逃走,仿佛怕瘟疫降临。最后只剩下谢尔盖、我和狗,他老婆已经在长沙发上睡着了。他满不在乎地走来走去,替狗收集残汤剩饭。他用英语说:“狗很喜欢(吃这些东西)。(拿它们)喂狗好得很。那条小狗它有虫子……它还太小。”他弯腰仔细察看狗两只爪子之间的地毯上爬的一些白虫子,试图用英语描述这些虫子,但是他的词汇不够用。最后他查了查词典,欣喜地抬头望着我道:“哈,是绦虫!”我的反应显然不那么明显。谢尔盖有些迷惑不解,于是便跪在地上,双手撑地更仔细地察看它们,还捉起一条放在桌上的水果旁。“嗬,它不太大,”他用蹩脚的英语嘟哝道,“下一课你教我各种虫子(的词汇),行吗?你是个好老师,我跟你学了不少东西呢……”
躺在走廊里的床垫上,杀虫剂的气味叫我喘不过气来,这种刺鼻的辣味似乎已钻进我身上每一个毛孔。刚才吃过的东西又在口中散发出气味——廉价燕麦片、蘑菇、咸肉和煎苹果。我又看到躺在水果旁的那条小绦虫和谢尔盖向我解释狗出了什么毛病时摆在桌布上的各式各样的虫子。我看到“疯狂的牧羊女”歌舞场的空乐池,每一条裂缝里都藏着蟑螂、虱子和臭虫。我看到人们发疯似的挠自己的身子,不停地挠,直到挠出血来。我看到这些虫子像一支红色蚂蚁大军,在布景上到处爬,吞下它们看见的一切。我看到合唱队的姑娘扔掉薄纱外衣,光着身子跑过走道。我还看到正厅后排的观众也脱掉衣服互相挠痒痒,活像一群猴子。
我试图让自己心平气和。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我找到的一个家,每天有一顿现成饭吃,而且谢尔盖无疑是一个热心人。可是我无法入睡,这简直如同在陈尸所里睡觉一样。床垫已被散发出香气的液体浸透,已成为虱子、臭虫、蟑螂和绦虫的陈尸所。我忍受不了。我不愿忍受!毕竟我还是一个人,不是一只虱子。
早晨,我等谢尔盖装车,叫他把我带到巴黎去,却不忍心告诉他我就要走了。我把背包留下,还有他给我的几件东西。到佩雷尔广场时我跳下来,在这儿溜掉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任何事情都没有特殊原因。我是自由的,这才是最要紧的……
像小鸟一样,我轻松地由一条街飞奔到另一条街,仿佛刚从牢里放出来。我用全新的目光看世界,万物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甚至包括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布尔索尼尔街,我停在一家体育用品商店的橱窗前,里面有一些照片展示“史前及史后”人类的标本。全是法国佬,有些人光着身子,只戴一副夹鼻眼镜,留一绺胡子。真不明白这些怪鸟怎么会爱上双杠和哑铃。一个法国佬应该有一个微微腆起的大肚子,像夏吕斯男爵那样。他应该蓄胡须,戴夹鼻眼镜,不过不应该光着身子让人拍照。他应该穿一双闪闪发光的漆皮靴,短便衣口袋上应该插一条白手帕,露出一英寸的四分之三。如果有条件,他还应该在上衣翻领上系一条红绶带,穿过纽扣眼儿,上床睡觉时还要换睡衣。
傍晚我走近克利希广场,从那个装着一条假腿的小婊子面前经过,她日复一日站在戈蒙宫对面。看起来她还不到十八岁,可我想她已有固定的客人。午夜过后她用黑假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身后是一条小胡同,里面像一座地狱一样灯火通明。如今我心情轻松地从她身边经过,不知怎么搞的,她使我联想起一只拴在桩上的鹅,一只肝上患病的鹅,这样世人才得以享用鹅肝馅饼。带着那条木腿去跟人睡觉一定很古怪,人们会联想到各种各样的事儿,木刺啦等等。得啦,各人对自己的口味就行!
沿着圣母街往前走,我碰到佩克奥弗,另一个在报社工作的穷鬼。他抱怨说每夜只能睡三四个钟头,因为早上八点就得起身到一家牙医诊所干活。他干这个活并不是为了钱,他解释道,这只是为了替自己买一副假牙。他说:“困得直打瞌睡时看清样可不容易,可我老婆还以为这差事像吃饭一样容易呢。她说,我若丢了工作咱们该咋办呀?”可是佩克奥弗对这个工作根本不感兴趣,这个工作甚至不允许他花钱。他只好存起香烟蒂,把它们填进烟斗里再抽一回。他的外套是用别针别在一起的。他有口臭,手上总出汗,可是一夜只能睡三个钟头。“不该这样对待一个人,”他说,“还有我的那位老板,若是我丢掉一个分号他便会把我骂得尿裤子。”说起他老婆,他又补充道:“我的那个女人,我告诉你,她他妈的一点儿都不知道感激我!”
分手时我设法从他那儿骗到一个半法郎,我想再榨出五十生丁,可是办不到。不过我弄到手的已足够喝一杯咖啡,吃几块新月形面包。圣拉扎尔车站附近有一家供应降价食品的酒吧。
恰巧,我在盥洗室里找到一张音乐会的票,于是便像一只轻松愉快的鸟一样奔夏沃音乐厅去了。引座员脸色难看极了,因为我竟没有给他一点小费。每次从我身边经过,他都要征询似的看看我,希望我会突然想起小费的事儿。
我已很久没有同穿着考究的人物坐在一起,心里不免有几分忐忑不安。我仍闻得到那股甲醛味。或许谢尔盖也往这儿送货,不过谢天谢地,这儿没有人挠痒。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儿……非常淡。音乐会尚未开始众人脸上便显出百无聊赖的神情,这音乐会真是一种礼貌的自我折磨。指挥短短的指挥棒敲响后大家紧张地全神贯注一阵,随即便是寂静,一种单调沉闷,被管弦乐队奏出的沉着、不间断的轻微乐声反衬出的寂静。我的头脑出乎意料地清醒,好像脑壳里镶着一千面镜子。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十分激动,音符像玻璃球在一百万股水流上跳跃。以前我从不曾饿着肚子去听音乐会,没有一种声响能逃过我的耳朵,甚至最细小的别针落地的声音我也听得见。好像我没有穿衣服,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是一扇窗户,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光亮穿透我的内脏。我可以感觉到这光线就蜷曲在我肋骨的穹隆下,我的肋骨垂在一个空空如也的肚子上,响声使它颤抖。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持续多久,我早已失去时间和地点的概念。仿佛经过很久很久以后出现了一阵半自觉的状态,与之相抵的是一种平静感。我感到身体内有一个大湖泊,一个发出彩虹色光辉的湖泊,冷峻得像果冻。这个湖泊上突然形成一个个巨大的螺旋,成群候鸟出现了,腿细长,羽毛漂亮,它们一群群地从清凉静谧的湖面上腾空飞起,从我的锁骨下飞过,消逝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间里。然后,缓慢,异常缓慢地,这些窗子关上了,我的器官也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犹如一位戴白帽子的老妇在我身体内漫游。突然,剧院里的灯全亮了,我发现白色包厢里的那个男人原来竟是一个头上顶着花盆似的东西的女人,起初我还以为那是一位土耳其军官呢。
一阵骚动,所有想咳嗽的人都尽情咳嗽开了。传来脚在地板上踢蹬发出的声响,竖起椅子的声响,人们漫无目的四处游逛发出的没完没了的嘈杂声,还有人们展开节目单时发出的窸窸窣窣声。他们装模作样地看看便又丢开,把它胡乱塞在座位底下。最小的事变亦值得谢天谢地,因为它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扪心自问在想什么。若是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曾想过,他们准会发疯。在刺眼的灯光照射下,他们呆呆地互相望着,而且他们逼视对方的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紧张感。一听到指挥轻轻敲台子预备再开始,他们便回到原先的自我强迫状态之中,他们不由自主地挠痒,或是突然回忆起一个摆着围巾或帽子的橱窗。他们仍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个橱窗里的所有细节,却想不起这个橱窗到底在哪儿,这使他们大伤脑筋,极度清醒而又不安。于是他们打起双倍的精神听音乐,因为他们十分清醒,无论乐曲多么美妙也不能忘怀那个橱窗和挂在那儿的围巾或是帽子。
这种聚精会神的气氛感染了会场,连乐队似乎也受到激励,变得格外精力充沛。第二个节目像最好的压轴戏似的结束了,十分迅捷,音乐戛然而止。灯亮时,有些人像胡萝卜一样瘫在座位上,下巴抽搐着。假如你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喊“勃拉姆斯,贝多芬,门捷列夫,黑塞哥维那”,他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4967289。
演奏德彪西的曲子时,场内的气氛已完全毒化。这时我在想,女人性交时究竟有何感觉,会不会对欢悦更敏感一些,等等。我在想象一件东西穿透我两腿间那个地方的情形,不过只有一点隐隐约约的痛感。我企图集中注意力,但是音乐太难把握,我只能想着一只花瓶慢慢翻转过去,音符散入空中的情形。 最后我只注意到开灯关灯,我便问自己灯是如何开关的。我旁边的人在呼呼大睡,他像一个掮客,大肚子,蜡黄的小胡子。我就喜欢他这样,我尤其喜欢他的大肚子和所有吃出这样一个大肚子的食物。为什么他不该呼呼大睡?若想听,无论何时他都可以搞到买一张票的钱。我注意到那些衣着较好的人睡得更踏实一些,这些有钱人问心无愧。若是一个穷汉打瞌睡,哪怕只是几秒钟,他也会觉得很丢脸,他会认为自己是对那位作曲家犯罪。
演奏那支西班牙曲子时整个音乐厅都轰动起来,大家都笔直地坐起来,他们是被鼓声惊醒的。我以为鼓点一旦敲响便会一直响下去,我期望看到人们从包厢里跳下来,或是把帽子扔掉。这支曲子蕴含一种英雄气概,拉威尔,他本可以使我们彻底发疯的,只要他想这么做。不过,这不是拉威尔的曲子。突然一切都静寂下来,仿佛拉威尔在开玩笑,突然想起自己还穿着一件剪破的衣服,便及时抑制住自己。依愚见,这酿成了大错。艺术即意味着有始有终,假如你以鼓点声开始,就要用爆炸声或TNT炸药告终。为了形式拉威尔牺牲了一些东西,为的是人们睡觉前必须消化掉的一棵菜。
我的思绪发散开来,约束不住。既然鼓声已停,音乐便也离我远去。无论何处,人们生来就是指挥别人的。出口的灯光下坐着一位郁郁寡欢的维特,他双肘支撑着身子,目光呆滞。门口站着一个西班牙人,裹着一件大斗篷,手里拿着一顶阔边帽,那副架势像是正在摆姿势让罗丹塑“巴尔扎克”似的。他的脖子以上部分很像水牛比尔。我对面的顶层楼座前排坐着一个女人,她两腿叉得很开,脖子向后拗去,错位了,看上去像是得了破伤风。还有那个戴红帽子的女人,她正趴在栏杆上打盹儿呢。她若是来一回脑出血就太妙了!设想她流出一桶血,全倒在楼下那些浆洗得硬硬的衬衫上。设想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衬衫上沾着血迹走出音乐厅回家的情景!
睡觉是基调。没有人再听音乐,无法再思考,再倾听,也无法去梦想,即使音乐本身也成为一场梦。一个戴白手套的女人把一只天鹅放在膝上。传说勒达怀孕后生下一对双胞胎。人人都在生出某种东西,除了上面那排座位上那个搞同性恋的女人之外。她高昂着头,大张着嘴,注意力十分集中。这曲交响乐像镭一样放射出一阵阵火花,使她激动不已。朱庇特在穿透她的耳朵。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片言只字,长着大鳍的鲸鱼,桑给巴尔,城堡。瓜达尔基维尔河沿岸上千座闪闪发光的清真寺。冰山深处的时光全是淡紫色的。蒙尼大街上立着两根拴马的白柱子。滴水嘴……宣传贾沃斯基谬论的男人…… 河边的灯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