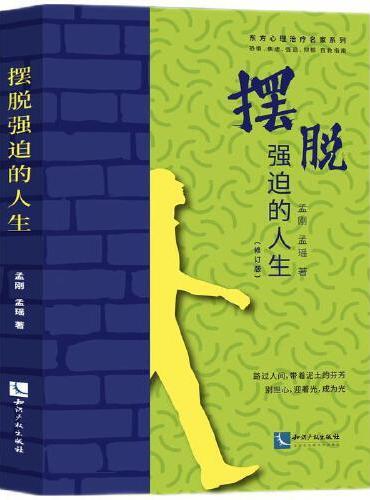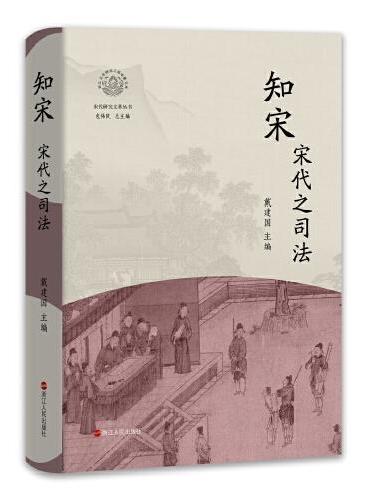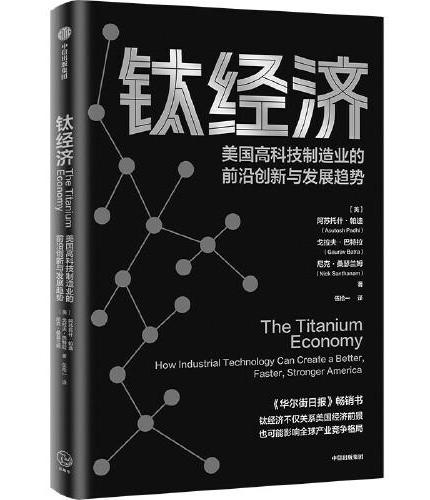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艺术图像学研究(第一辑)
》
售價:NT$
8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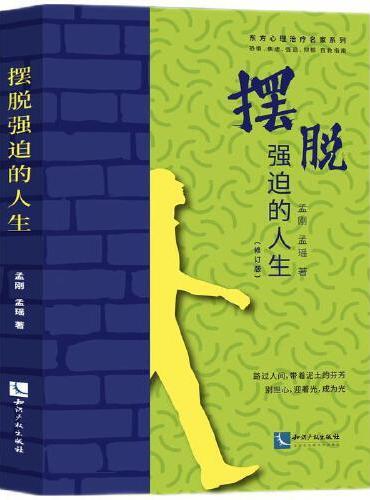
《
摆脱强迫的人生(修订版)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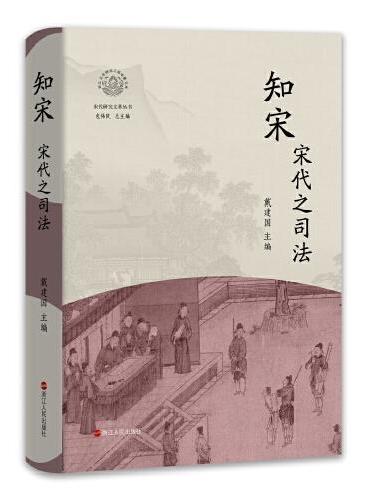
《
知宋·宋代之司法
》
售價:NT$
454.0

《
空间与政治
》
售價:NT$
398.0

《
少年读三国(全套12册)
》
售價:NT$
2234.0

《
不完美之美:日本茶陶的审美变革(知名茶人李启彰老师器物美学经典代表作 饮一口茶,长一分体悟与智慧 制一件器,生一曲手与陶土的旋律 不借由任何美学架构来觉知美)
》
售價:NT$
398.0

《
现代化的迷途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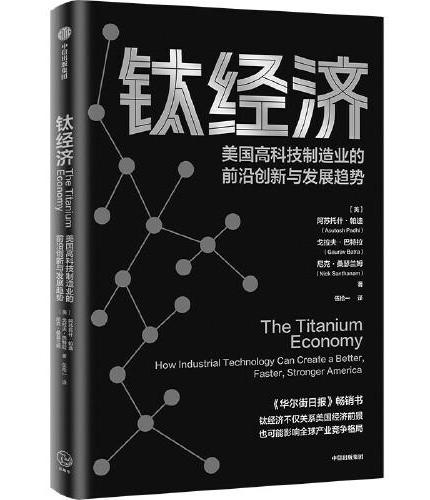
《
钛经济
》
售價:NT$
352.0
|
| 編輯推薦: |
★大山的作品是一方净土……是作家一片慈悲心向他的信男信女施洒甘霖。
——孙犁
★大山的创意是精致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精品。
——徐光耀
★“简洁”曾是短篇创作中备受推崇的品格,可是现在的短篇创作中却有一种繁缛和冗长之风。贾大山因“简洁”而独树一帜,他的短篇,超过万言的极少,这在今天尤显难能可贵。
——雷达
★贾大山为文淡而有味,为人淡泊名利。
—— 白烨
|
| 內容簡介: |
本书收录了贾大山代表性的作品,如《取经》《花市》《梦庄纪事》《莲池老人》等一批短篇佳作。其中《取经》荣获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他的作品扎根中国农村,直面现实,关注底层小人物的笑与泪、歌与哭,传递出积极的道德秩序和优雅的文化价值,具有持久的文学价值和独特的阅读魅力。
他的故事造就了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乐观的辛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愚钝的聪慧、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他的作品中寄寓的人民性是朴实而深刻的,从而能成为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
|
| 關於作者: |
|
贾大山(1942—1997),河北正定县人。历任正定县文化局局长、政协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河北文学》《上海文学》等多家刊物发表小说。短篇小说《取经》获得首届全国优秀小说奖,《花市》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小戏屡屡获奖。在80年代的文学界,他与贾平凹并称短篇小说“二贾”。
|
| 目錄:
|
目 录
1/天籁之声,隐于大山(代序) 铁 凝
1/取经
12/花市
19/劳姐
29/年头岁尾
36/中秋节
45/小果
52/赵三勤
60/拴虎
69/鼾声
74/友情
80/午休
90/村戏
100/花生
105/老路
110/干姐
117/定婚
123/离婚
131/俊姑娘
138/丑大嫂
144/杏花
151/坏分子
155/孔爷
161/飞机场上
169/会上树的姑娘
173/写对子
176/妙光塔下
183/林掌柜
191/钱掌柜
200/王掌柜
208/西街三怪
223/“容膝”
229/书橱
232/门铃
237/老底
241/莲池老人
245/老曹
248/担水的
252/卖小吃的
257/腊会
262/智县委
268/游戏
273/童言
277/傅老师
282/老拙
|
| 內容試閱:
|
天籁之声,隐于大山(代序)
铁凝
贾大山是河北省新时期第一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一九八○年,他在短篇小说《取经》获奖之后到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正在文坛惹人注目。那时还听说日本有个“二贾研究会”,专门研究贾平凹和贾大山的创作。消息是否准确我不曾核实,但已足见贾大山当时的热闹景象。
当时我正在保定地区的一个文学杂志任小说编辑,很自然地想到找贾大山约稿。好像是一九八一年的早春,我乘长途汽车来到正定县,在他工作的县文化馆见到了他。已近中午,贾大山跟我没说几句话就领我回家吃饭。我没有推辞,尽管我与他并不熟。
我被他领着来到他家,那是一座安静的狭长小院,屋内的家具不多,就像我见过的许多县城里的居民家庭一样,但处处整洁。特别令我感兴趣的是窗前一张做工精巧的半圆形硬木小桌,与四周的粗木桌椅比较很是醒目。论气质,显然它是这群家具中的“精英”。贾大山说他的小说都是在这张桌子上写的,我一面注意这张硬木小桌,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什么出身。贾大山却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家好几代都是贫下中农。然后他就亲自为我操持午饭,烧鸡和油炸馃子都是现成的,他只上灶做了一个菠菜鸡蛋汤。这道汤所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因为大山做汤时程序的严格和那成色的精美。做时,他先将打好的鸡蛋泼入滚开的锅内,再把菠菜撒进锅,待汤稍沸锅即离火。这样菠菜翠绿,蛋花散得地道。至今我还记得他站在炉前打蛋、撒菜时那潇洒、细致的手势。后来他的温和娴静的妻子下班回来了,儿子们也放学回来了。贾大山陪我在里屋用餐,妻儿吃饭却在外屋。这使我忽然想起曾经有人告诉我,贾大山是家中的绝对权威,还告诉我妻儿与这“权威”配合得是如何的默契。甚至有人把这默契加些演义,说贾大山召唤妻儿时就在里屋敲墙,上茶、送烟、添饭都有特定的敲法。我和贾大山在里屋吃饭没有看见他敲墙,似乎还觉出几分缺欠。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贾大山有一个稳定、安宁的家庭,妻子与他同心同德。
那一次我没有组到贾大山的稿子,但这并不妨碍贾大山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这是一个宽厚、善良,又藏有智慧的狡黠和谋略,与乡村有着难以分割的气质的知识分子,他嘴阔眉黑,面若重枣,神情的持重多于活跃。
他的外貌也许无法使你相信他有过特别得宠的少年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他不仅是历选不败的少先队中队长,他的作文永远是课堂上的范文,而且办墙报、演戏他也是不可少的人物。原来他自幼与戏园子为邻,早就在迷恋京剧中的须生了。有一回贾大山说起京剧忍不住站起来很帅地踢了一下腿,脚尖正好踢到鼻梁上,那便是风华少年时的童子功了。他的文学生涯也要追溯到中学时代在地区报纸上发表小说时。如果不是一九五八年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首寓言诗,很难预料这个多才多艺的男孩子会有怎样的发展。那本是一首慷慨激昂批判右派的小诗,不料这诗一经出现,全校上自校长下至教师却一致认为那是为右派鸣冤叫屈、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寓言。十六岁的贾大山蒙了,校长命他在办公室门口的小榆树下反省错误,那天下了一夜的雪,他站了一夜。接着便是无穷尽的检查、自我批判、挖反动根源等等,最后学校以警告处分了结了此案。贾大山告诉我,从那时起他便懂得了“敌人”这个概念,用他的话说:“三五个人凑在一块儿一捏鼓你就成了阶级敌人。”
他辉煌的少年时代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因病辍学,自卑,孤独,以及为了生计的劳作,在砖瓦厂的石灰窑上当临时工,直到一九六四年响应号召作为知青去农村。也许他是打算终生做一名地道的正定农民的,但农民却很快发现了他有配合各种运动的“歪才”。于是贾大山在顶着太阳下地的业余时间里演起了“乐观的悲剧”。在大队俱乐部里他的快板能出口成章:“南风吹,麦子黄,贫下中农收割忙……”后来沿着这个“快板阶梯”他竟然不用下地了,他成为村里的民办教师,接着又成为入党的培养对象。这次贾大山被吓着了——使他受到惊吓的是当时的“极左”路线:入党则意味着被反复地、一丝不苟地调查,说不定他十六岁那点陈年旧账也得被翻腾出来。他的自尊与自卑强烈主宰着他不愿被人去翻腾。那时的贾大山一边做着民办教师,一边用他的编写才华编写着那个时代,还编出了“好处”。他曾经很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我是怎么由知识青年变成县文化馆的干部么?就因为我们县的粮食‘过了江’。”
据当时报载,正定县是中国北方第一个粮食“过江”的县。为了庆祝粮食“过江”,县里让贾大山创作大型剧本,他写的剧本参加了全省的汇演,于是他被县文化馆“挖”了上来。“所以,”贾大山停顿片刻告诉我,“你可不能说文艺为政治服务不好,我在这上边是沾了大光的。”说这话时他的眼睛超乎寻常的亮,他那两只狭长的眼睛有时会出现这种超常的光亮的,那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眼中的流动,这便是人们形容的犀利吧。犀利的目光、严肃的神情使你觉得你是在听一个明白人认真地讲着糊涂话。这个讲着糊涂话的明白人说:“干部们就愿意指挥种树,站在你身边一个劲儿叮嘱:‘注意啊注意啊,要根朝下尖朝上,不要尖朝下根朝上啊!’”贾大山的糊涂话讲得庄重透彻而不浮躁,有时你觉得天昏地暗,有时你觉得唯有天昏地暗才是大彻大悟。
一九八六年秋天我又去了正定,这次不是向大山约稿,是应大山之邀。此时他已是县文化局局长——这似乎是我早已料到的,他有被重新发现、重新“挖”的苗头。
正定是河北省著名的古城,千余年来始终是河北重镇之一。曾经,它虽以粮食“过江”而大出过风头,但最为实在的还是它留给当今社会的古代文化。面对城内这“檐牙高啄”“钩心斗角”的古建筑群,这禅院寺庙,做一名文化局局长也并非易事。局长不是导游,也不是只把解说词背得滚瓜烂熟就能胜任的讲解员,至少你得是一名熟悉古代文化的专门家。贾大山自如地做着这专门家,他一面在心中完整着使这些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重放光彩的计划,一面接应各路来宾。即使面对再大的学者,专家贾大山也不会露“怯”,因为他的起点不是只了解那些静穆着的砖头瓦块,而是佛家、道家各派的学说和枝蔓。这时我作为贾大山的客人观察着他,感觉他在正定这片古文化的群落里生活得越来越稳当妥帖,举止行动如鱼得水。那些古寺古塔仿佛他的心爱之物般被他摩挲着,而谈到他和那些僧人、住持的交往,你在夏日习习的晚风中进一趟临济寺便一目了然了,那时十有八九他正与寺内住持焦师父躺在澄灵塔下谈天说地,或听焦师父演讲禅宗祖师的“棒喝”。
几年后大山又任县政协副主席。他当局长当得内行、自如,当主席当得庄重、称职。然而贾大山仍旧是个作家,可能还是当代中国文坛唯一只写短篇小说的作家,且对自己的小说篇篇皆能背诵。在和大山的交往中,他给我讲了许多农村和农民的故事,那些故事与他的获奖小说《取经》已有绝大的不同。如果说《取经》这篇力作由于受着当时文风的羁绊,或许仍有几分图解政策的痕迹,那么这时贾大山的许多故事你再不会漫不经心地去体味了。虽然他的变化是徐缓的、不动声色的,但他已把目光伸向了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灵魂的深处,于是他的故事便构成了一个贾大山造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乐观的辛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愚钝的聪慧,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
贾大山讲给我的故事陆续地变成了小说。比如一位穷了多半辈子终于致富的老汉率领家人进京旅游,当从未坐过火车的他发现慢车票比快车票便宜时居然不可思议地惊叹:“慢车坐的时候长,怎么倒便宜?”比如“社教”运动中,某村在阶级教育展览室抓了一个小偷,原来这小偷是在偷自己的破棉袄,白天他的棉袄被作为展品在那里展览,星夜他还得跳进展览室将这棉袄(他爷爷讨饭时的破袄)偷出御寒。再比如他讲的花生的故事:贾大山当知青时花生是中国的稀有珍品,那些终年不见油星的百姓趁队里播种花生的时机,发了疯似的带着孩子去地里偷花生种子解馋。生产队长恪守着职责搜查每一个从花生地里出来的社员,当他发现他八岁的女儿嘴里也在嚅动时,便一个耳光打了过去。一粒花生正卡在女儿气管里,女儿死了。死后被抹了一脸锅底黑,又让人在脸上砍了一斧子。抹黑和砍脸是为了吓唬鬼,让这孩子在阴间不被鬼缠身。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读贾大山小说的时候,眼前总有一张被抹了黑又被砍了一斧子的女孩子的脸。我想,许多小说家的成功,大约不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孩子因为偷吃花生种子被卡死了,而在于她死后又被亲人抹的那一脸锅底黑和那一斧子。并不是所有小说家都能注意到那锅底黑和那一斧子的。后来我读大山一篇简短的《我的简历》,写到“一九八六年秋天,铁凝同志到正定,闲谈的时候,我给她讲了几个农村故事。她听了很感兴趣,鼓励我写下来,这才有了几篇‘梦庄记事’”。今天想来,其实当年他给我讲述那些故事时,对“梦庄记事系列”已是胸有成竹了。而让我永远怀念的,是与这样的文坛兄长那些不可再现的清正、有趣、纯粹、自然的文学“闲谈”。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这尤其难得。
一些文学同行也曾感慨为什么贾大山的小说没能引起持续的应有的注意,可贾大山仿佛不太看重文坛对他的注意与否。河北省曾经专门为他召开过作品讨论会,但是他却没参加。问他为什么,他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小说发表时他也不在乎大报名刊,写了小说压在褥子底下,谁要就由谁拿去。他告诉我说:“这褥子底下经常压着几篇,高兴了就隔着褥子想想,想好了抽出来再改。”在贾大山看来,似乎隔着褥子比面对稿纸更能引发他的思路。隔着褥子好像他的生活能够沉淀得更久远、更凝练、更明晰。隔着褥子去思想还能使他把小说越改越短。这让我想起了不知是谁的名句:“请原谅我把信写得这么冗长,因为我没有时间写得简短。”
写得短的确需要时间需要功夫,需要世故到极点的天真,需要死不改悔地守住你的褥子底下(独守寂寞),需要坦然面对长久的不被注意。贾大山发表过五十多篇小说,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小说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不能说是当红作家。但他却不断被外省文友们打听询问。在“各领风骚数十天”的当今文坛,这种不断地被打听已经证明了贾大山作品留给人的印象之深。他一直住在正定城内,一生只去过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一九九三年到北戴河开会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了海。北戴河之后的两年里,我没有再见贾大山。
一九九五年秋天,得知大山生了重病,我去正定看他。路上想着,大山不会有太重的病。他家庭幸福,生活规律,深居简出,善以待人,他这样的人何以会生重病?当我在这个秋天见到他时,他已是食道癌(前期)手术后的大山了。他形容憔悴,白发很长,蜷缩在床上,声音喑哑且不停地咳嗽。疾病改变了他的形象,他这时的样子会使任何一个熟识从前的他的人难过。只有他的眼睛依然如故,那是一双能洞察世事的眼:狭长的,明亮的。正是这双闪着超常光亮的眼使贾大山不同于一般的重病者,它鼓舞大山自己,也让他的朋友们看到一些希望。那天我的不期而至使大山感到高兴,他尽可能显得轻快地从床上坐起来跟我说话,并掀开夹被让我看他那骤然消瘦的小腿——“跟狗腿一样啊”,他说,他到这时也没忘幽默。我说了些鼓励他安心养病的话,他也流露了许多对健康的渴望。看得出这种渴望非常强烈,致使我觉得自己的劝慰是如此苍白,因为我没有像大山这样痛苦地病过,我其实不知道什么叫健康。
一九九六年夏天,蒋子龙应邀来石家庄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当我问及他想看望哪些朋友时,蒋子龙希望我能陪他去看贾大山,他们是中国作协文讲所的同学。是个雨天,我又一次来到正定。蒋子龙的到来使大山显得兴奋,他们聊文讲所的同学,也聊文坛近事。我从旁观察贾大山,感觉他形容依然憔悴,身体更加瘦弱。但我却真心实意地说着假话,说着看上去他比上次好得多。病人是需要鼓励的,这一日,大山不仅下床踱步,竟然还唱了一段京剧给蒋子龙。他强打着精神谈笑风生,他说到对自己所在单位县政协的种种满意——我用多贵的药人家也不吝惜,什么时候要上医院,一个电话打过去,小车就开到楼门口来等。他很知足,言语中又暗暗透着过意不去。他不忍耽误我们的时间,似又怕我们立刻离去。他说你们一来我就能忘记一会儿肚子疼;你们一走,这肚子就疼起来没完了。如果那时癌细胞已经在他体内扩散,我们该能猜出他要用多大毅力才能忍住那难以言表的疼痛。我们告辞时他坚持下楼送我们。他显然力不从心,却又分明靠了不容置疑的信念使步态得以轻捷。他仿佛以此告诉人们,放心吧,我能熬过去。
贾大山是自尊的,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当着外人他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尊严和分寸。小梅嫂子(大山夫人)告诉我,只有背着人,他才会为自己这迟迟不好的病体焦急万分地打自己的耳光,也擂床。
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贾大山。经过石家庄和北京两所医院的确诊,癌细胞已扩散至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山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像每次一样,见到我们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这时的大山已瘦得不成样子,他的病态使我失去了再劝他安心养病的勇气。以大山审时度势的聪慧,对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于是我们不再说病,只不着边际地说世态和人情。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件是大山讲起某位他认识的官员晚上出去打麻将,说是两里地的路程也要乘小车去。打一整夜,就让司机在门口等一整夜。大山说:“你就是骑着个驴去打麻将,也得喂驴吃几口草吧,何况司机是个人呢!”说这话时他挥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指着一个什么地方,义愤非常。我未曾想到,一个病到如此的人,还能对一件与他无关的事如此认真。可谁又敢说这事真的与他无关呢?作为作家的贾大山,正是这种充满着正义感和人性尊严的情感不断成就着他的创作。他的疾恶如仇和清正廉洁,在生他养他的正定城有口皆碑。我不禁想起几年前那个健康、幽默、出口成章的贾大山,他曾经告诉我们,有一回,大约在他当县文化局局长的时候,局里的话务员接到电话通知他去开一个会,还问他开那么多会真有用的有多少,有些会就是花国家的钱吃吃喝喝。贾大山回答说这叫“酒肉穿肠过,工农留心中”。他是在告诫自己酒肉穿肠过的时候别忘了心中留住百姓呢,还是讥讽自己酒肉穿肠过的时候百姓怎还会在心中留呢?也许告诫、讥讽兼而有之,不经意间透着沉重,正好比他的有些小说。
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与大山的最后一次见面,还听他讲起另一件事:几个陌生的中学生曾经在病房门口探望他。他说他们本是来医院看同学的,他们的同学做了阑尾炎手术,住在贾大山隔壁。那住院的同学问他们,你们知道我隔壁住着谁吗?住着作家贾大山。几个同学都在语文课本上读过贾大山的小说,就问我们能不能去看看他。这同学说他病得重,你们别打扰,就站在门口,从门上的小窗户往里看看吧。于是几个同学轮流凑到贾大山病房门前,隔着玻璃看望了他。这使大山心情很不平静,当他讲述这件事时,他的嗓音忽然不再喑哑,他的语气十分柔和。他不掩饰他的自豪和对此事的在意,他说:“几个陌生的中学生能想到来看看我,这说明我的作品对人们还是有意义的,你说是不是?”他的这种自豪和在意使我忽然觉得,自一九九五年他生病以来,虽有远近不少同好亲友前来看望,但似乎没有谁能抵得上几个陌生的中学生那一次短暂的隔窗相望。寂寞多年的贾大山,仿佛只有从这几个陌生的孩子身上,才真信了他确有读者,他的作品的确没被遗忘。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日(正月十四)大山离开了我们,他同疾病抗争到最后一刻。小梅嫂子说,他正是在最绝望的时候生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希望,他甚至决心在春节过后再去北京治病。他的渴望其实不多,我想那该是倚仗健康的身体,用明净的心,写好的东西。如他自己所期望的:“我不想再用文学图解政策,也不想用文学图解弗洛伊德或别的什么。我只想在我所熟悉的土地上,寻找一点天籁之声、自然之趣,以娱悦读者,充实自己。”虽然他已不再有这样的可能。但是观其一生,他其实一贯是这样做的。他这种难能可贵的“一贯”,使他留给文坛、留给读者的就不仅是独具气韵的小说,还有他那令人钦佩的品性:善意的,自尊的,谨慎的,正直的。他曾在一篇小说中借着主人公,一个鞋店掌柜的嘴说过:“人也有字号,不能倒了字号。”文章至此,我想说,大山的作品不倒,他人品的字号也不倒。
贾大山作品所传递出的积极的道德秩序和优雅的文化价值,相信能让并不熟知他的读者心生欢悦,让始终惦念他的文学同好们长存敬意。
智县委(P262)
小时候,我是很淘气的。一到晚上,我和我的伙伴们就欢了,打蝙蝠、掏麻雀、捉迷藏,古老的府前街就变成了我们的天下。
因为淘气,认识了县委书记。他姓智,那时人们不叫他智书记,而是叫他智县委。打戏院门口的电灯泡玩儿,看谁能打中。我正瞄准,忽然有人揪住我脑后的小辫儿,伙伴们立即就跑散了。扭头一看,揪我小辫儿的是个生人,中等个儿,白净脸,穿一身灰军装,戴一副眼镜。我挣脱他的手,撒腿就跑,他一把又揪住我的小辫儿,揪得好疼。我骂他的娘,他也不理睬,终于把我揪到父亲面前去了。
“这是你的小孩?”生硬的外地口音。
“噢,是我的孩子。”父亲是个买卖人,开着一个杂货铺,一向胆小怕事。一见那人,赶忙捻亮罩子灯,显得很惊慌:
“智县委,请坐……”
我也一惊,他就是智县委!
智县委没有坐,眼睛忽然盯住桌上的一片字纸。那是我写的一篇大楷: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哪个写的?”他问。
“他写的。”父亲指指我说,“瞎画。”
他立刻瞅定我,脸上竟然有了喜色,眼镜也显得明亮了:
“几岁了?”
“十岁了。”
“十岁了还留小辫儿?”
父亲赶忙解释:当地的风俗孩子们留小辫儿,要留到十二岁,成人。智县委听了哈哈大笑说:
“好哇,那就留着吧!”
智县委夸了一番我的毛笔字,就和父亲说起话来。他问父亲的年龄、籍贯,又问这个小铺多大资本,生意如何,拿多少税。我站在他的背后,并不注意他们的谈话,眼睛一直注视着他的衣襟下面露出的那块红布——那是一把盒子,真家伙!
他和父亲谈着话,忽然仰着头,望着货架子说:
“怎么,连个字号也没有?”
“没有。”父亲笑着说,“小本买卖,还值得立字号?”
“怎么不值得?”智县委好像生气了,脸色红红的,说,“城里买卖家,哪个没字号?‘亨茂号’‘文兴成’‘荣泰昌’‘广顺正’,都有字号嘛!你也赶快立个字号!”
父亲想了一下,说:“叫‘贾家小铺’?”
“不好,小气!”
“叫‘万宝店’?”
“也不好,俗气!”
父亲就笑了:“智县委赏个名儿吧!”
“‘复兴成’,怎么样?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一切都要复兴的,你也要复兴嘛!”
父亲说好,行,不错。
智县委走了。父亲茫然如做梦,问我做了什么事,怎么把他引来了?我把我们打戏院门口电灯泡的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摇摇头,叹口气,大惊小怪地说:
“哎呀,你这个孩子,今天是沾了那几个毛笔字的光了!”
父亲说,那座戏院,是智县委心上一朵花儿,谁也碍妨不得。每天一散戏,他就出来了,朝戏台上一站,眼镜子亮闪闪地望着观众散去,谁在座位上踩一下,都不行,你们敢打他的电灯泡儿?
我笑着打断父亲的话:“什么叫立字号呀?”
“立字号,就是挂一块匾。”
“咱家挂不挂?”
“不挂还行?不挂交代不了智大炮……”
“智大炮?”
“小孩子家,少打听。”父亲笑了笑,什么也不说了。
不多几日,父亲便请人书写了一块匾额,挂匾那天,还在“小南楼”饭庄请了客。
后来我才知道,智县委对买卖家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脾气也很暴躁。他不但要求买卖人做到“秤平斗满,童叟无欺”,而且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夏天不搭凉棚不行,门口不设“太平水缸”不行,没有字号也不行……谁家不按他的要求去做,就把掌柜的叫到街上,当众呲一通。买卖人都很怕他,暗地里叫他“智大炮”。
买卖人怕他,心里又很敬重他。有一天,我看见一个胖胖的、歪戴着帽子的醉人,从周家烟摊上拿了一盒“大婴孩”香烟,说是“赊账”。周掌柜不认识他,刚刚说了一声“不赊账”,醉人口里便冒出一句惊人的话:
“老子打过游击!”
话音刚落,智县委刚好走到这里,啪啪就是两个耳光!醉人急了,拍着胸脯大叫:
“好哇,你敢打……”
认清是智县委,放下香烟,赶紧走了。买卖人哈哈笑着,故意说:
“智县委,你们八路军,可是不兴打人呀!”
“这种东西不是人!”
“他喝醉了……”
“我也喝醉了!”他说。
智县委虽然脾气暴躁,但我一点儿也不怕他,心里很喜欢他。自从他到了一次我家铺子里,我总觉得他好像是我家的一个什么亲戚。上学放学的路上,我总是注意着穿灰军装的人,希望天天碰到他。偶尔见他推着车子从街上走过,我就赶上前去,亲切地叫一声:
“智县委!”
“啊,一去二三里!”他不晓得我的名字,总是喊我“一去二三里”。
但是,这个“亲戚”,后来再也没有到过我家铺子里,我也很少听到他的消息。
寒假里,刚刚下了一场雪,街上冷清清的,没有人买东西。我正趴在柜台上写大楷,一个青年来买松花,买二十个。父亲看看玻璃缸里,只有十来个松花了,便说:“买那么多?”
“有多少要多少吧!”青年笑着说,“前天晚上,智县委来买松花,没有敲开你家的门。今天我想多买几个,给他预备着。”
“你是……”
“我是他的通信员,叫小马。”小马说,“智县委睡觉前爱喝两口酒,最喜欢吃松花。”
我想起来了,正是下雪的那天晚上,父亲正在灯下“碰账”,外面有人啪啪地敲门,父亲没有理睬。又敲,父亲便一口吹灭了灯……
“那是智县委?”父亲吃惊地望着小马。
小马笑着点点头。
“我不信。”父亲摇摇头,也笑了,“半夜里,那么大雪,他来买松花,你干什么?”
小马说:
“黑夜里买东西,他总是自己去,从不使唤我们。买到就买,买不到就回去。他怕我们狐假虎威,打扰睡下了的买卖人。”
从那以后,不管天多晚了,只要听到敲门的声音,父亲就赶紧起来去开,但是哪一次也不是智县委——智县委调走了。
他走了,好像是在一个春天,满街古槐吐新芽儿的时候。
他走了,多少年后,这里的百姓们还时常提念他。有人说他是山西人,有人说他是陕西人;有人说他没有上过学,从小放羊;也有人说他是大学毕业,伺候过薄一波。至于他的政绩,百姓们看到的自然都是小事,不是大事。无非是说,智县委在时,夏天街里有凉棚,冬天路上无积雪,到处都干净,买卖人都和气,卷子蒸得个大,烧饼上的芝麻也稠。就连菜摊上的小葱、黄瓜、水萝卜,也一堆是一堆、一把是一把,红的红绿的绿,洗得鲜亮放得整齐。只有我父亲,在公私合营的时候,短不了皱着眉头埋怨他两句:
“你说老智非让立个字号干吗?‘小南楼’请客,白花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