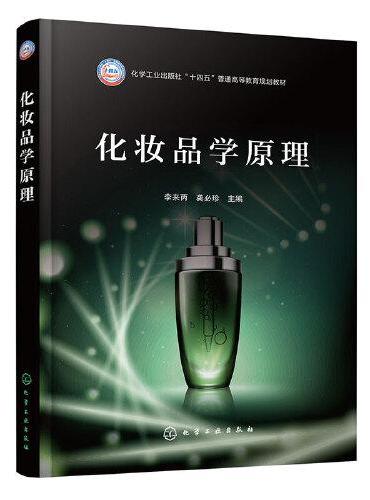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拯救免疫失衡
》
售價:NT$
254.0

《
收尸人
》
售價:NT$
332.0

《
大模型应用开发:RAG入门与实战
》
售價:NT$
407.0

《
不挨饿快速瘦的减脂餐
》
售價:NT$
305.0

《
形而上学与存在论之间:费希特知识学研究(守望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译丛)
》
售價:NT$
504.0

《
卫宫家今天的饭9 附画集特装版(含漫画1本+画集1本+卫宫士郎购物清单2张+特制相卡1张)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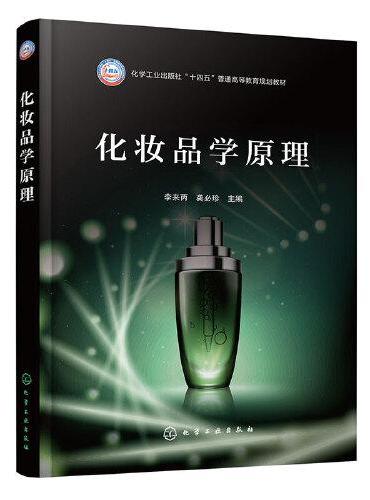
《
化妆品学原理
》
售價:NT$
254.0

《
万千教育学前·与幼儿一起解决问题:捕捉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教育契机
》
售價:NT$
214.0
|
| 編輯推薦: |
|
《在伊犁》作为新中国文学中一个独特而精湛的存在,共收入《哦,穆罕默德· 阿麦德》等九篇作品,于1984年8月由作家出版社首次结集出版。此次重新出版的《在伊犁》,对该版本进行了重新编辑修订,特别恢复了后续版本没有使用的代序——《故乡行——重返巴彦岱》一文。该文是王蒙1981年在离开新疆近两年以后重返新疆巴彦岱,和他的维吾尔族农民兄弟把酒言欢,用深情的笔触写下的,既感人至深,又对《在伊犁》的人物和故事原型有重要交代。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希望此次出版的《在伊犁》能够以最完整的、本真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也成为探索王蒙文学艺术价值的一个重要范本。
|
| 內容簡介: |
|
一九六五年,王蒙来到伊犁,在伊宁市巴彦岱镇(原红旗人民公社)劳动。 他吃住于农民家中,抡起坎土曼,学习维吾尔族语言,爱上奶茶泡馕……这六年的经历,成为他后来创作 “新疆叙事” 系列作品的宝贵源泉。写作于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间的《在伊犁》系列作品,正是以他的这段经历为背景。在这部作品中,王蒙有意回避了职业的文学技巧,通过散文化的日常生活叙事,塑造出让人哭笑不得的穆罕默德 · 阿麦德、野心勃勃的依斯麻尔、智慧老者穆敏老爹、热烈淳朴的爱弥拉姑娘等众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视角别致,意蕴丰富,成为其作品中一个独特而精湛的存在。
|
| 關於作者: |
王蒙:
一九三四年出生在北京,一岁到四岁在老家河北南皮农村,小学上了五年,跳班上了中学,差五天满十四岁时加入了还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高中一年级辍学,当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共产主义青年团)干部。一九五三年开始写《青春万岁》,一九五六年发表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了大响动。一九六三年到新疆,曾任伊宁县红旗人民公社副大队长。后来还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等。
二〇一九年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出版五十卷文集。此前获得过茅盾文学奖、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荣誉博士、澳门大学博士、日本樱美林大学博士、约旦作家协会名誉会员等称号。
出访过境外五大洲七十多个国家与地区。
屡拔先筹,屡有曲折,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惭愧厚爱,自称要干的事太多,顾不上斤斤计较。人说高龄少年,嘛也没耽误。
|
| 目錄:
|
目录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016
淡灰色的眼珠/052
好汉子依斯麻尔/090
虚掩的土屋小院/132
葡萄的精灵/186
爱弥拉姑娘的爱情/196
逍遥游/220
边城华彩/294
鹰谷/322
后记/384
|
| 內容試閱:
|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
小说题目愈来愈长,加感叹词和标点符号,以至把标题变成“主谓宾定状”俱全的完整的句子,大约也是一种新潮流吧?于是我想来它个以毒攻毒,将此篇命名为:《哦,我的远在边疆的亲爱的可怜的维吾尔族兄弟穆罕默德·阿麦德哟,让我写一写你!》。后一想,如此创新,殊非正路,乃罢。
似乎自从日本电影《啊,海军》在我国放映以来,“啊”“哦”式标题就多起来了——来自东洋?电影《啊,摇篮》,小说《哦,香雪》《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哦,我歪歪的小杨树》——流韵所及?当我这次来上海给《小说界》改中篇的时候,有人建议我把中篇命名为《哦,我的爱》,您受得了么?
我看不惯“啊”“哦”。想不到,在这个短篇上竟向“啊”“哦”投降了。这只能说是穆罕默德·阿麦德的力量。 ,按惯例译作“买买提·艾买提”,同样的名字如果来自埃及、叙利亚或苏丹,就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似乎雅气了些也庄重了些。我几经推敲,决定从后一种译法,倒并非想冒充阿拉伯故事或炫耀博学以招揽读者,而是不如此译,便不能表达我对 的郑重的敬意。
一九六五年四月,我到达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的毛拉圩孜公社劳动锻炼,分配到三大队第五生产队。先是在队部附近干活,一个月以后,第一次去离住地四公里以外的伊犁河沿小庄子附近锄玉米。八点来钟出发,走到庄子,都快九点了,只见几个社员还坐在渠埂上说闲话,抽莫合烟。我由于诚惶诚恐,劳动上不敢怠慢,便问了一句:“还没上工么?”问完了才意识到,这里在场的是百分之百的维吾尔人,我的汉话没有人听得懂,问也白问。
但是马上从人群里站起一位机灵的小伙子,他身材适中,留着大分头,头发卷曲,眉浓目秀,目光流动活泼、忽暗忽亮,胡须楂子虽密却刮得很干净,上身穿一件翻领青年服,下身一件黄条绒的俄式短腰宽脚裤,神态俊雅,只是肤色似乎比这儿的一般社员还要黑一些。他用流利但仍然带有一种怪味儿的汉语对我说:“同志,你好。你是新来的社教干部吧?我们正在学习讨论《纪念白求恩》呢,来,坐下吧。”
我解释说,我不是社教干部,而是来劳动锻炼、改变思想的。他睁大了眼睛,把我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打量了几遍,突然一转头,哈哈大笑起来。
他笑的样子非常粗俗丑陋,与刚才问“你好”的文明样子颇不相称。我知道,在新疆,即使懂汉语的乡下人,见面问候时也是用“好着呢吗?”而不会说“你好”的。会问“你好”那是见过相当场面的标志。
笑完了,他指一指渠埂,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坐下,休息。”然后,他与同伴们继续说笑。他说话非常快,一套一套,表情也很夸张,好像在模仿着什么人。但是在这样的说笑中,他也时时照顾着我的存在,一会儿用简单的话语向我介绍他们谈话的内容,原来他们并没有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会儿又问问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婚姻状况、家庭成员、简历,干部登记表第一面和第四面上的几项,他都问到了,我很佩服他的一心二用的本领。
这时又来了几个穿得花花绿绿的女社员,坐在对面的一条渠埂上,不是正对男社员而是拉开十几米的距离,以示男女有别。他噌地站了起来,跑到女社员那边去,马上,那边传来了活跃的说笑声。
太阳烤得我已经满头是汗了,我已经怀疑这一天还干不干活了,一位留着圆圆的白胡子的组长才下令下地。干活的时候那个伶俐的小伙子主动和我结伴,不停地和我扯着闲话,不断地嘱咐我“忙啥,慢慢的,慢慢的”。对我提出的有关劳动工艺上的问题,他一概置之不理,同时热情地向我嘘寒问暖,向我介绍在这里生活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我叫穆罕默德·阿麦德,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好了。”
直到快收工的时候,我才直腰四处看了看,我发现,穆罕默德·阿麦德干的活比我还少。我是一个人锄四垄地,他一个人只锄两垄,但前进的速度一样。他锄漏的生地、野草,也绝不比我少。再一看,我确实吓了一跳,原来他拿着的是一柄那么小的坎土曼,别说是男人,就是未成年的女孩儿用的坎土曼,一般也比他的大。
他一边“干活”,一边说笑,肆无忌惮,最后还唱起歌来了,有滋有味,有腔有板,他的嗓子可真不错。
后来不知谁笑着说了一句什么话,他突然生起气来了,立在那里,噘着嘴像个孩子,不声不响也不干活。过了足足两分钟他对我说:“这人是不好人,这人人不是。”他停了一下,调整了盛怒中弄乱了的语法,告诉我说:“这些人不
是人。”
午饭时候,他不由分说把我拉到他家里去。本来庄子的住房水平低于队部附近的住房,他住的那个歪歪扭扭的用烂树条编在一起抹上泥就算墙的烂房,更可以说是倒数第一。他的父母都已老迈,两个小妹年龄很小,这四个人穿的都是破衣烂裳,只有他一个人穿得囫囵、整洁,还颇有式样。泥房外面是烂柴草搭的一个凉棚,凉棚下面砌起一个土台,土台上铺着一块布满烂洞、裂纹、粘成一绺绺的破羊毛毡子,毡子上放着一个四角包上铁皮仍然松松垮垮的炕桌,土台边连着锅灶,老太太正把一大把一大把发了霉的麦秸填到灶里,烟大火小,烧开那一大铁锅水显然是很难的。
我遵照礼仪向坐在室外土台上的二位老人问好。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父亲向我还礼和问候的时候,胸腔里发出一种奇怪的沙沙声,而且结结巴巴,口齿不清。他母亲正在害眼,红红的两只眼睛眼泪花花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却不耐烦地催我进屋,屋里摆设稍稍好一点,有半新的花毡,有条案,条案上有挑花桌布与大小瓷碗,还有一排维吾尔文旧文字的精装厚书,这是不多见的。墙角有镶着黄色条饰的木箱,墙上还有一张不大的镜框,奇怪的是镜框里摆着的全都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一个人的照片,有穿俄式多扣学生装的,很天真可爱,还有一张穿西服的,拙劣地涂上了颜色,照得却走了形。墙上除了挂着面罗、和面的木盆、两把未编完的糜秸扫把以外,还有一个大肚的庞然大物——那是一种乐器,叫作都塔尔,我在来伊犁以前已经去过吐鲁番和南疆,我是见识过的。
屋里空气潮湿憋闷,我其实宁愿出去到土台上坐,但是他正在认真地张罗着。先是在我面前铺上了饭单,然后打开黄条木箱,拿出两个小碟,一个碟里放着方块糖和葡萄干,一个碟里放着小馕与小饼干。然后,他从室外拿来一个搪瓷高桩茶壶,从案上取下两个小碗,给我和他自己各倒了一碗茶:“请,请,请……”他平摊着向我伸手,极为彬彬有礼。从茶色的淡薄上,我又一次体会到这一家人经济上的拮据。
茶虽淡,方块糖、葡萄干种种看来也是历史悠久,但他的招待却是一丝不苟,我也就非常感激地端起茶来啜饮,饮着饮着忽然想起了他的父母,维吾尔人是最讲敬老的,岂有把老人丢在室外之理。我眼睛看着门口要说话,他已明白,皱着眉对我说:“他们不喝茶,喝开水。”稍待,他又解释说:“在南疆,没有几户人家喝得起茶。”
喝了几口,这道程序结束,他拿起一个小碗出去了,一去好大一会儿也不回来,使我坐也不是走也不是。最后他拿着空碗气冲冲地进来了,他生气地说:“你是北京来的客人,我却要不来一碗奶皮子。这儿的人,太不好了,在我们南疆,一家做好吃的,一定把周围所有的人叫来。”
没有奶皮子,做不成奶茶,但还是一起喝了咸茶,并且吃的是白面馕。我本来中午是带了馕的,但那是包谷馕。在春天青黄不接的季节,中午是难得有白面馕吃的,看来,他已经全力对我进行规格最高的款待了。
从此,我结识了这位懂汉语的、殷勤亲切又有点神拉巴唧的年轻人。我那时初到维吾尔农村定居,言语不通,心情沉郁,穆罕默德·阿麦德的存在,使我感到了友谊的温暖。每逢到伊犁河边干活的时候,我就带上馕,到他家喝热茶,就是喝碗开水,也是暖的。我得知,他们全家是五年前从喀什噶尔老城步行半个月,从新源那边翻天山来到伊犁地区落户的。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好学,三年前考上了乌鲁木齐气象学校,但这个学校的食堂整天吃吐鲁番产的白高粱面,他吃不惯,加上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离了他日子没法过,他便退学回来了,回来后心情抑郁,整天胡打混闹。我也把我的大概情况介绍给他,他立即表示:“我听了心疼得很。”他的“很”字拉得很长,而且中间拐两个弯。后来,见我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他要说一次心疼,看我吃一次干包谷馕,他也要说一次心疼。有一次队里出义务工,到公社西面三公里远去修湟渠,中午回不来,周围又没有人家,只好就着西北风和泥沙吃硬馕,他又“心疼”起来,还掉了眼泪。我问:“你们不也都是这样吃的吗?”他说:“我们惯了,你可是北京来的呀。”
他正式请了我一次客,是伊犁人最爱吃的“大半斤”——抻条面。他自己和面,做剂儿,抻面。他做抻面的方法与伊犁的旁人不同,伊犁人是先把面剂儿做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一一拉细,像毛线绺一样地悬挂在桌角边,然后一锅一锅地煮。他呢,跪在毡子上,做了一个大面剂儿,裹上油,像盘香一样地盘成一座小山,等到锅开了,他飞快地拉起来,愈拉愈多,愈拉愈长,中间不断,直到拉满一锅的时候,他才把面从中间断开。他说:“这是喀什噶尔做拉面的方法。”说起喀什噶尔,他满脸的依恋之情。不但面是他做的,菜卤也是他做。“你的妈妈呢?”我问。“她做不好!”他粗暴地回答。面煮好以后,他倒是很仁义,不但给父、母、妹妹盛好送到手上,而且确实如他所说过的,他推开房门,谁从这儿过他就叫谁来吃。最后,他自己只剩了小半碗。这时来了一只邻居的黑白花小猫,向他喵喵地叫,他以惊人的慷慨从他的碗里用手捏出一半面条来,喂了猫。剩下的几根面条,他也不用筷子,就用手指捏着吃了。都拾掇完了以后,他自己又吃了一个包谷馕。
利用饭后的融洽气氛,我向他进了一言:能不能换个稍微大一点的坎土曼,干活时稍稍多卖点力气。他立刻板起了脸,恶狠狠地对我说:“我不爱劳动嘛!我不是国家干部嘛!我不是积极分子嘛!”
“那你爱什么呢?”我没生气,却笑着问。
“我爱玩,我爱看电影,我爱唱歌跳舞,我爱看书。”
“什么书?”
“爱情小说。我最喜欢爱情啦,我喜欢美,漂亮,我喜欢女孩子。”说着说着他转怒为喜,突然,他向我跪下,给我磕了一个头:“王大人,请不要肚子胀。”在我莫名其妙的时候,他又粗俗丑陋地笑开了。
笑得突然,停止得也突然,他突然停住了笑,问我:“你会跳‘坦萨’吗?”
“什么‘坦萨’?”
他抬起两手,做出一个交际舞的姿势。
我不快地哼了一声。
“我最爱跳‘坦萨’了。”他哼哼着歌噌地站了起来,一个人前后左右地迈着步子。我当时的心情与交际舞是格格不入的,连看也不看他,于是他改唱维吾尔歌曲和跳维吾尔舞。然后他气喘吁吁地从墙上摘下都塔尔,一通乱弹,然后把都塔尔砰地一扔,颓然叹道:“每天都抡坎土曼,每天都抡坎土曼,手指头都粗了,还怎么弹都塔尔呢?”人是不错,可是思想太差劲,我当时想。同时我想起,根据我的一段观察,人们对穆罕默德·阿麦德普遍抱着一种取笑和轻视的态度。当穆罕默德·阿麦德大说大笑或者出洋相的时候,特别是年轻的男社员,便会互相挤挤眼睛、撇撇嘴,老头儿们也忍俊不禁,有的还摇摇头,最无保留地欢迎他和欣赏他的倒是女社员,特别是中年女社员。有一次队里开会,有一项议题是改选妇女队长。那天穆罕默德·阿麦德不在,一位有名的健壮而泼辣、刚刚和丈夫打了离婚的女人阿细罕喊道:“我们选穆罕默德·阿麦德!”一句话全场就爆炸了,男女老幼,全都笑成了一团,我也笑了。
我又想起,有一天我从他家喝茶出来,大队的会计、一只眼睛的伊敏问我:“是到穆罕默德·阿麦德家里去了吗?”当我点头以后,他却大摇其头,并且连连叹气,“唉、唉、唉……”是一种不以为然的腔调。
这是怎么回事?
这次正式请吃“大半斤”,以欢快开始,以兴味索然而告终了。而且,在我告辞的时候,他把右腿别在左腿前,身子扭成了八道弯,上身晃动着,面红耳赤地说:“老王哥,夏天要到了,我的三片瓦帽子再也戴不住了,队上又困难……你能不能借我十块钱?”
我把十块钱给了他,但心情更加不快了,他借钱的时机和场合使我对他的友谊的纯洁性产生了一点点怀疑。至于帽子,我完全懂,维吾尔族人不论春夏秋冬、室内室外,都是必须戴帽子的。人前脱帽,是极为失礼的表现。而他的那顶三片瓦帽子,确实是不能再戴下去了。但用得了十块钱吗?我怀疑。
勿谓言之不预,真是忠言逆耳!就在第二天,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等一批干部到庄子地里参加劳动来了,他们立即发现了穆罕默德·阿麦德的超小坎土曼。中间休息时,他们集合了全体社员,然后拿起穆罕默德·阿麦德的坎土曼示众。维吾尔族副队长讲了一大套,我听不懂,但是口气严厉,这从其他社员屏息静气、鸦雀无声的状态中可以体会到。汉族队长拿起他的坎土曼来说了一句话:“这是坎土曼吗?不,这是耳挖勺!”他的话立刻被工作队的翻译翻成了维吾尔语,又是一阵大笑。
穆罕默德·阿麦德面红耳赤,像发了疯一样冲了过去。他口若悬河,与工作队干部辩论起来,还解开自己的腰带撩开衣服让工作队干部看伤口。翻译给汉族队长翻译的时候我也听见了几句,他不服,第一他说他有病开过刀,维吾尔语表达的方法是“吃过刀子”。第二他说批评表扬不能光看表面现象,不能不调查研究。他的坎土曼固然小一点,但他去年一年上工三百四十五天,今年半年出工一百七十天,属于全队前三名,为什么不表扬?而同一个队里的××××、 ××××……一贯不出工,为什么不提?为什么越是积极上工的好社员越是要听训,受批评,而从不上工的人却两耳清净、逍遥自在?再说,去年决算他结余七十多块,七十多块都被超支户用了,队上没钱给他开支,至今欠着他钱,工作队管不管?不是批评他的坎土曼小吗?拿钱来!他立刻买来两把特大号的,一把自己用,一把送给工作队长……
他的顶撞使所有的人捏着一把汗,因为那个年月,不仅在城市,即使在农村顶撞领导也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但显然他以凌厉的口舌在辩论中占了上风。工作队长们开始降低了自己的调子,倒是长着圆白胡须的作业组长非常照顾领导的面子,适时地站出来把他训斥了几句,宣布继续干活。
工作队干部有了台阶,离去了,大家一面干活一面议论纷纷。从人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一部分人拍手称快,更多的人认为穆罕默德·阿麦德是干了蠢事。又干了一个多小时,太阳还老高,组长宣布收工,但一律不得回家,以免给人以本组收工太早的不良印象。大家聚在地边抽烟,意思是如果碰到上面有人来检查,就重新下地比画比画;如果没有,等暮色昏黄时再起立各奔各家。这次照例的呆坐,穆罕默德·阿麦德非常沉闷,连阿细罕和他说笑他也不理。后来阿细罕过来拉他,与他动手动脚,别人笑起来了,他仍然面色阴沉,不理人。阿细罕无法,回头看见了我,向我求援,哇里哇啦,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叫我劝劝他。我刚走过去,穆罕默德·阿麦德转头说了句:“别理他们!”我说:“社员们都等着你说笑话呢!”他抬起头,对我说:“你看我这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啊!”我看到,他满眼是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