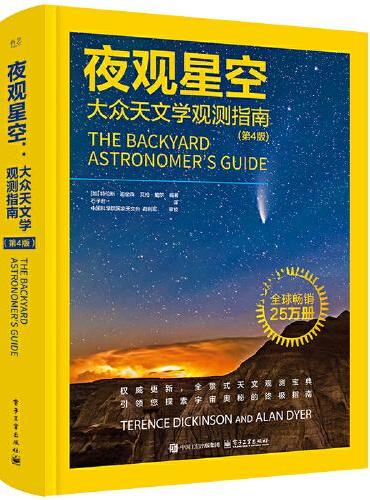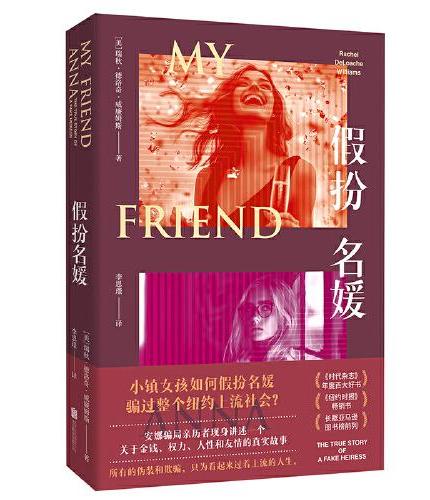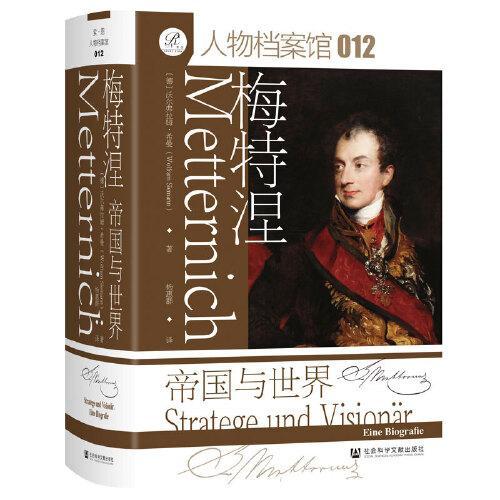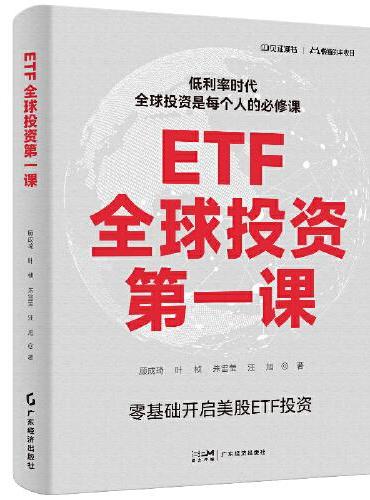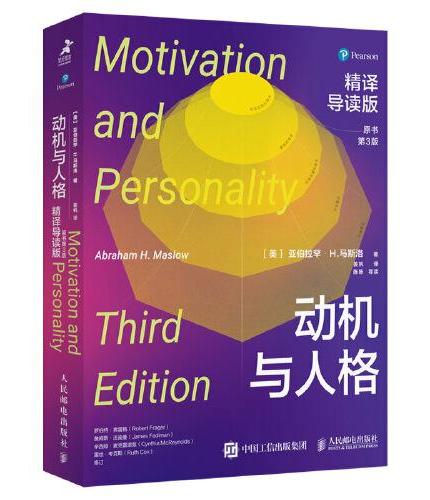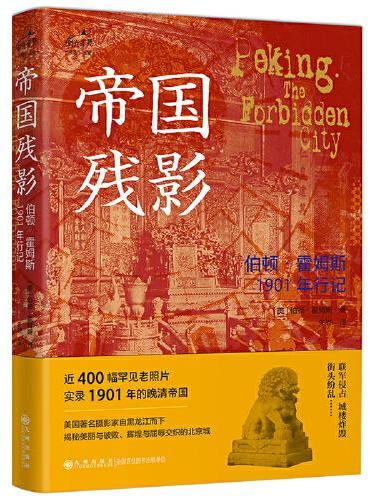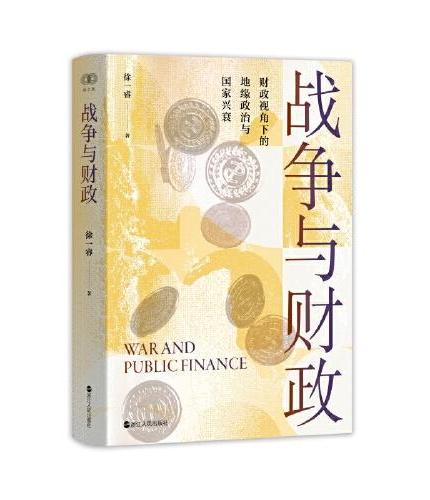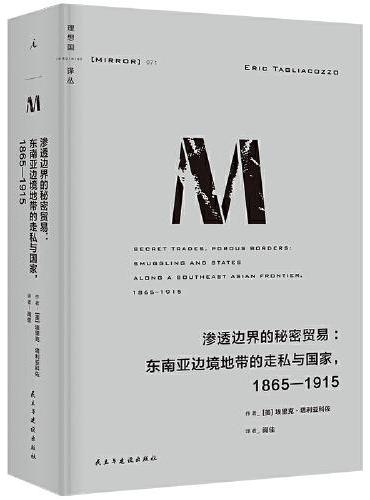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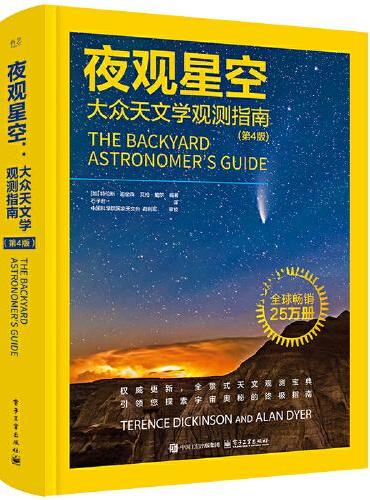
《
夜观星空:大众天文学观测指南(第4版)
》
售價:NT$
7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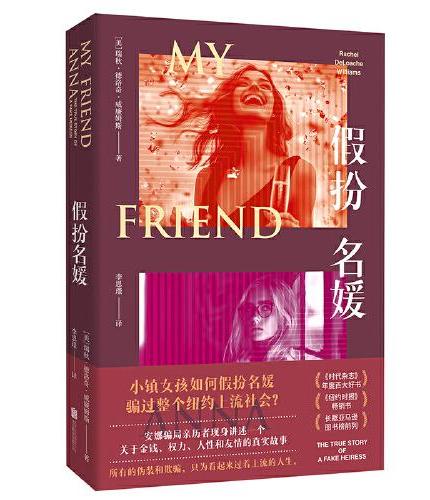
《
假扮名媛
》
售價:NT$
2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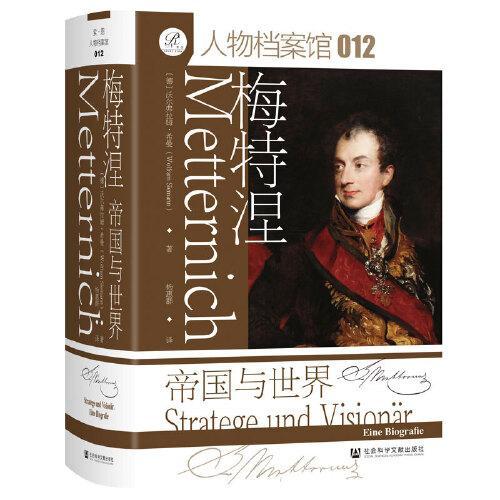
《
索恩丛书·梅特涅:帝国与世界
》
售價:NT$
9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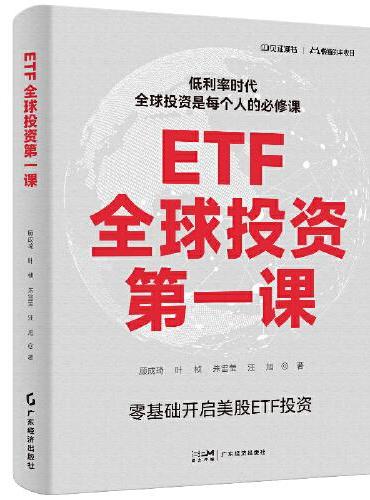
《
ETF全球投资第一课 顾成琦等著 体系化、全方位的ETF投资入门指南 帮助新手投资者一键入门全球资产配置 ETF投资、ETF基金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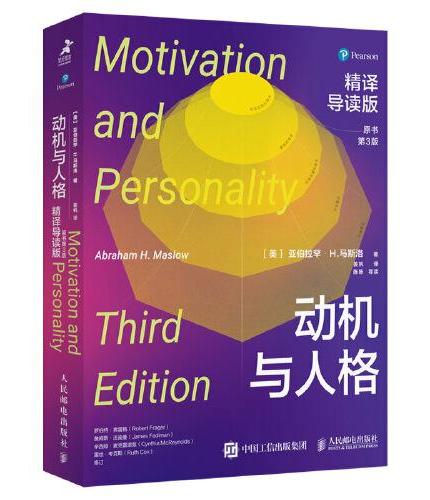
《
动机与人格:精译导读版(原书第3版)
》
售價:NT$
4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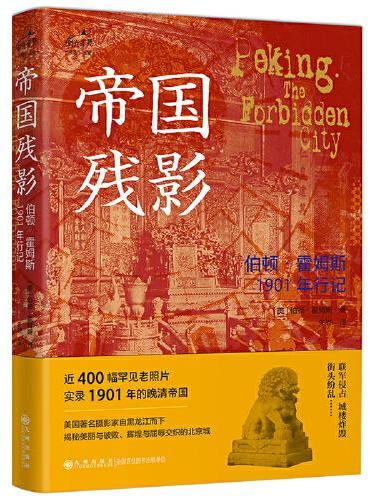
《
帝国残影:伯顿·霍姆斯1901年行记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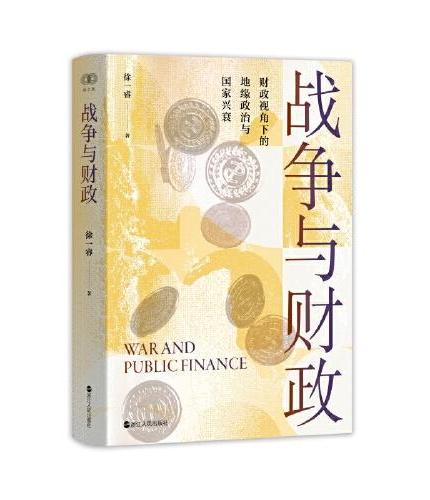
《
战争与财政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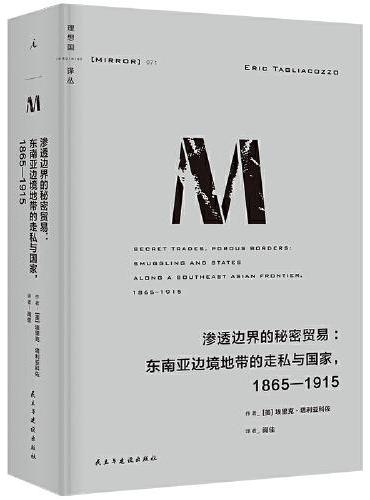
《
理想国译丛071:渗透边界的秘密贸易:东南亚边境地带的走私与国家,1865—1915
》
售價:NT$
602.0
|
| 編輯推薦: |
|
一本以《周官》为基础文献,以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国家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学术著作。书中围绕《周官》的考订、疆域国家的研究、周朝的制度等方面展开讨论,重新审视了东亚早期的疆域和中华文明的源头。首开先河,完整恢复《周官》原貌。本书剥离《周官》中历代窜入的注文,首次完整复原这部经典的原始面貌,溯清《周官》的出身、特点、历史位置,给予《周官》客观评价,是对《周官》研究的重大突破。深入解析周制,展现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细节。本书透彻描述了官制、赋役制度、城邑制度等周制的方方面面,展现了三代文明的诸多细节,例如王藉与王籍的区别、万民非庶民、周无五等诸侯制等。在考镜源流的史学基础方法上,开《周官》研究新进路。本书不仅运用“以他经解此经”的方法来考镜源流;并“以经注史”来复原和解析《周官》、周制;还通过考古发掘材料与文献交互论证,来辨别真伪;更引入了制度史的方法和理论框架,即法学的规范分析方法,来整合和阐发史料与文本。论述周圆,逻辑严密,表达流畅。书中全面而系统的框架论述,使得复杂的历史问题变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打开探索中国历史源头的新窗口。通过深入研究《周官》与周制,本书系统、翔实地揭示了中华文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一本以《周官》为基础文献,以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国家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学术著作。通过剥离窜入的注文,首次完整呈现《周官》职文的原貌,溯清《周官》的出身、特点、历史位置,给予《周官》客观评价。同时,结合考古资料,对先秦时期东亚疆域国家的发展变迁及其制度规范进行了考订,并系统、深入地描述了官制、赋役制度、城邑制度等周制的方方面面,展现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诸多细节。本书的研究成果,不仅挑战了传统关于《周官》的误解,更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东亚早期的疆域与华夏文明的起源,为中国历史的源头部分提供了新的视角。
|
| 關於作者: |
|
俞江,出版专著《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清代的合同》《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主编《徽州合同文书汇编》影印本、点校本。
|
| 目錄:
|
前言
序编:“第六经”之谜
——《周官》复原
第一章 经文与注文
第二章 《周官》出身辨
第三章 《周官》评价
上编 疆域国家
第四章 虞人与史前疆域国家
第五章 封国与中小型疆域国家
第六章 附庸与兆域
第七章 仆、庸与裔民
——兼论混淆附庸的身份
第八章 王畿(上):王畿非王土辨
第九章 王畿(下):周天子的疆域
下编 周制
第十章 中央官制(上):官等
第十一章 中央官制(中):公卿
第十二章 中央官制(下):大夫
第十三章 乡遂与都鄙(上):遂制
第十四章 乡遂与都鄙(中):县制
第十五章 乡遂与都鄙(下):州制
第十六章 庶民(一):民本思想
第十七章 庶民(二):籍田制
——兼论籍田非藉田
第十八章 庶民(三):赋役
结语:“七十子丧大义乖”
参考书目
全书图表名
附录:《周官》职文复原
后记
|
| 內容試閱:
|
本文是《〈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一书的前言,作者俞江阐述了研究周代历史与制度的重要性,指出周史的清晰对于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形态与特征至关重要。文章深入探讨了“疆域国家”的概念,分析了“疆”与“域”在古代中国的含义,以及它们如何与国家制度和鬼神信仰相结合。作者还讨论了“制度”一词的多重含义,以及它在周代社会中的作用。
——编者按
周制解码:《周官》与中国古代疆域国家(前言)
主旨与脉络
我们研究周史与周制,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抱着自审与自新的决心。
周史已亡,人物、事件俱成传说。近代以来,考古学昌明,又从地下挖出一些。然而,把这些加起来,对于全部的周史来说,仍像是碎缕之于衣裳,让人不禁废叹。周史不明,则华夏文明的起源、形态与特征俱不明。世人喜说文明复兴,原型不明,何来复兴?! 又不止于此,周史不明,读《左传》 就有隔膜。《左传》有隔膜,虽然殚精竭虑,春秋战国史终不明。春秋战国是华夏文明的大转型时期,春秋战国史不明,则理解此次转向必有窒碍。
人类世界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有形的器物、建筑等物质世界,另一部分是无形的制度等精神世界。无形的又何止是制度。观念、德性、美感、意境,凡能够定义人的属性和人类社会,往往是无形的。但凡是有形的,不过是人的创造物或生产物,为人所定义,而不能定
义人。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形的,人文社科却要同时研究有形与无形,而且无形的往往更重要。 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强加于人文社科,是自然科学家的狂妄。把自然科学的评价方式用到人文社科,是人文社科的沉沦。
制度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均致力于通过制度来解释世界。制度既是人创造的,又反向规定人,所以,它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制度还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系统性,二是稳定性。一种制度形成之后,可以数百上千年稳定运行。同时,一种制度绝不孤立,而是与其他制度组成系统,在系统中相互牵制,不允许轻易变化。一旦变化,又会引发其他制度随之改变,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转型、巨变、崩溃或重新平衡。制度的系统性,使制度史具有整全的性质。制度史之于历史就像恐龙的骨架化石。 若恐龙的血肉已无存,能得到整全的骨架,岂非幸事。制度的稳定性,则使其可以记录,可以执行,可以复述,可以科学研究。利用这个特征,只要有可靠的文献,不但可以辨别史之真伪,还可以顺藤摸瓜,恢复一个时代的制度全貌。
话虽如此,难就难在什么是“可靠的文献”。顺藤固然可以摸到瓜,却要知道藤在哪里。 若藤已不存,瓜也遥不可及。 幸好中国是历史文献的大国,有一部专门记录周制的书保留下来,这就是《周官经》(简称《周官》,俗称《周礼》)。《周官》 是“六经”之一,而且是“六经”中唯一的古文经(不算伪古文《尚书》)。古文经是西汉时期陆续发现的先秦文献,以《周官》为本,以《左传》和《尔雅》 为两翼。它们与今文经的区别,只在于今文经在西汉时尚有经师讲说,而古文经已失师说。 西汉以下两千余年,很多学者知道《周官》的重要,但有更多人不承认,这是莫大的遗憾。 知道它重要的学者,误以为今本《周官》就是入室管钥,不知道真正的钥匙封存于其中,这是更大的遗憾。
本书的任务分两步:第一步,把封存的钥匙取出来;第二步,找到锁孔,把钥匙放进去。 全书分为三编:1.序编;2.上编;3.下编。
序编专讲如何打破今本《周官》,把封存的钥匙找出来,所以它的副标题叫“《周官》复原”。全书还有一篇附录,题为《〈周官〉职文复原》。看名字就知道附录原是序编的一部分,为了查阅方便才放在末尾。我在书中会解释它的用途,阅读本书离不开它,请读者随
时查对。
上编的标题叫“疆域国家”。“疆域”一词不是随便用的,它呈现了古人对国家的理解角度,下文再详。 这里要说的是,疆域看上去好像归属于历史地理专业,怎么会成为本书的中心问题呢? 原因很简单,国家就是制度的集合体,所有的国家问题都离不开从制度方面解锁。一个国家的疆域,首先要看它的国境线,而国境线就是制度。其次要看国内的各种政治实体,而政治实体仍然无非是制度。搞不清这些制度,就无法定性各种疆界与区域。 定性尚且不准,这个国家的政治地理也不可得。我很喜欢老派史家常用的“名物制度”一词,四个字道尽了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遗憾的是,在一些人眼中,名物是名物,制度是制度,史学割裂成两个截然不相关的门类,一是名物考订,二是制度梳理。 学者们可以各据一门,老死不相往来。这在当今尤其突出。然而,任何东西只要进入人眼所及的范围,就不再是自然物,而且不可避免地被人类重新定义,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进一步,它一旦进入国家的视野,就不可避免地被国家重新定义,成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所有的自然物都被规定,甚至名字也是制度赋予的。鉴于此,我想大胆地说:山川名物,无非制度。
下编的标题叫“周制”。该编主要讨论王国的制度,诸如官制、城邑、万民等。从《周官》中得到的信息,已足以把周制从遮蔽和孤立状态中解救出来。这是因为,认识一个时代的制度,最好的方式是利用具有系统性的法典,而《周官》正是一部近似法典的文献。迄
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尚未发现周的法律简牍,估计永远也不会发现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对于商制研究是有效的。 因为没有商制的传世文献,更别说法典,研究商制只有依靠出土物。对于周制研究却不适用。《周官》的传世,使得周制研究必须以它为主心骨,考古资料只能处于辅助地位。说《周官》 是解锁周制的唯一钥匙,丝毫不为过。但需申明的是,《周官》 仅仅记载了官制,不及其他。先贤虽尊其为“周礼”,那只是想突出它在群经中的重要性。周制的范围非常广,比如与器物有关的制度,凡宫殿、玉器、兵器、车
马、符节、墓葬等,在《周官》 中虽有记载,但细节不详,对它们的研究,文献与出土实物具有同等重要性。又需指出,器物制度依附于国家制度,尤其依附于等级制与礼制,犹如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换言之,器物制度只是等级制和礼制的一部分,就像
枝叶是树干的一部分,若以为器物制度可以代替国家制度,无异于本末倒置。
疆域国家
疆域,是上古中国的特有概念,类似今天的国家领土。
疆
疆,泛指人工设置的各种边界,通常采用封、沟、树等办法。封是堆垒大型土堆,沟是人工挖掘界沟,封和沟结合称为“沟封”,通常用于国界或城池。树是立界石,又称树石。 沟和树结合称为“沟树”,用于较小的地域单元,如邻里、县鄙等。古人称周王的国土为王畿。畿是面积方千里的简称,也指国家的形体。但没有边界不成形体,《大司徒职》说“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表示王畿是疆界围出来的。封疆树界的王官叫封人,他不但负责在王国边境上设置疆界,还负责为诸侯国、城池等设立疆界。也就是说,疆界不只在王国的边境线上,而是密布于王畿内外。实际上,凡是人工的建筑物,如城郭、宫殿、坟墓、田亩、道途等,皆有疆界。 又凡是自然的地理地形,如原野、沼泽、山陵、河川等,也有疆界。周王命令官吏把订立疆界的事情办妥,叫“体国经野”。《周官》 现存五篇《叙官》,开篇都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可见体国经野是建立王国的首要任务。
体国经野是浩大的土木工程,这一工程完成之后,全国分出不同的地域层级。比如,最低层级的邑坐落在四井之中,井田是邑的次级单元。又如,最高层级是王都,周边方百里以内的城邑,均设为王都的附属单元。在每一层级中又分割出不同的地域单元,每个单元都被冠名,同时定义它们的用途,不但人工筑造的城池、宫殿、道路等如此,自然资源也不例外。 河流的某段用于灌溉,某段用于渔猎;森林,或用于狩猎,或用于伐采;山脉,或用于采矿,或用于祭祀,或用于设险防御等。国土的每一部分都被规划,再分界,再根据实际情况定义用途,以便随时利用。体国经野并不仅仅是设置一条条界线,而是规划与定义全部国土。古中国以农为本,土地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既然每一份土地都被定义,可以想象,与这些土地捆绑在一起的人也被定义。随着进一步开疆拓土,不断纳入的土地和人口又按相同办法规划与定义。“疆域国家”的第一层含义,指国家自建立之初就成了规划和定义的结果。在王国中,没有一块土地是自然的,也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土地和人都是资源。 疆界设立妥当之后,才把围出来的各种地域画在地图上,标注名称,这种地图叫做“土地之图”。 疆界和地图完成之后,国家就算造好了。在此意义上,疆域国家是统一规划和整体筑造的结果。
本文深入探讨了《周官》一书在中国古代经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以及围绕其真伪和地位的长期争议。作者首先指出,《周官》的真伪问题是讨论其地位的前提。通过《〈周官〉职文复原》的研究,作者认为真伪之争可以告一段落。文章接着对经籍的价值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并提出《周官》应列为六经中的第四位。
——编者按
《周官》评价:真伪之争与经籍地位的再审视
《周官》一书向来有两大争议,一是真伪,二是地位。真伪不明,不足以讨论其地位,故前者为主,后者为次。现在用《〈周官〉职文复原》呈现其经注关系,真伪之争,可以歇矣! 而此书的地位及其价值,牵扯仍多。不揣鄙陋,就教于方家。
“群经源本”
按照汉晋士大夫旧说,《周官》一直位列“六经”之一。且不论《艺文志》的排序,《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位列首位。再加孔壁所得古文,从此古文经学有了依凭。朝廷立《周官》《左氏春秋》博士,为古文经学正名。到此时,未闻名为“乐经”的经籍传世,也未闻立有“乐经”博士。最多有《乐记》,所谓《乐记》,是按《周官》所载的大司乐及其属官的诸篇职文编写。我疑就是《周官传》的一部分。 “乐经”为六经之说,不过是今文经师抵制《周官》的手段。
山东诸儒多从游于河间献王,这是儒学在山东复兴的一支源头。自刘德献书,《周官》分出两个版本,一藏秘府,是古文原本,也即司马迁、王莽、刘向、刘歆等人看到的,姑且称为秘府本 秘府本肯定有传抄本,但这个抄本系列在东汉时已亡。二是献王自留了抄本,姑且称为献王抄本。献王抄本在山东诸儒间传抄,添加注疏,形成独立的版本系列。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征天下通《周官》等经之人,前后至者以千数。其中专研《周官》的经师此前见不到秘府本,只能研习献王抄本。由此可知,献王抄本在民间流传,有经师精研,仅凭秘府本不能独擅其学。入东汉,秘府本和献王抄本的原版俱毁,只有某种源自献王抄本的俗本流传下来,也就是今本《周官》的祖本。
秘府本和献王抄本相当于《周官》加上原注和纂者注。有种说法,太史迁见到的《周官》只剩《大司乐职》。其实,武帝封禅,群臣不懂望祀之仪,找《周官》来研究。太史迁在《封禅书》中略引《周官》的文字,这些文字取材于《春官》,并非出自《大司乐职》。《春官》
载有望祀的职文,主要是《大宗伯职》 《小宗伯职》 《大祝职》 《男巫职》等四篇。同时,从今本《周官》中校出的注文,出身各不同,或有纂者注,或有《周官传》。这些注文在汉初是否已窜为职文,无法一一考订。但汉初群臣能看到它们,是可以肯定的,从中也能获得不少望祀的信息。总之,结合《周官》及其注文,约略可推知望祀礼。太史迁说汉儒据《周官》定封禅礼,不算夸大。元始五年(公元5年),西汉创立“九命之锡”制度,俗称“九锡”。 九锡以《大宗伯职》“九仪之命”为原型。此时《周官》已成显学,位列“六经”之一,又称“六艺”,立有博士官。王莽和曹操各自篡位之前,皆加九锡。后世提到九锡,就会想到两位著名的篡臣,《周官》的名声跟着坏了。其实,元始五年距新建国尚有三年,王莽篡位之迹未显,仍是公认的学术权威和有德之士,借《周官》为篡逆的大旗,说明《周官》是当时公认的经籍,有资格充当这杆大旗。若此书有伪造嫌疑,王莽岂非自找麻烦?! 总之,司马迁、王莽、刘向、歆等人看到的秘府本,除了《冬官》亡佚外,基本保留了原本的状态,只是职文原注和纂者注在西汉时已不能与经文区别,然而不伤大雅。
莽新以后,就有篡改经书的传言,为《周官》增添了一层疑云。所谓篡改文字不过是西汉经师留在经文中的注文。到了东汉,整理者不辨,将这些注文抄成了经文,并非东汉经师有意作伪。问题是,后世大大低估了两汉之际的文化断裂,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西汉与东汉之间的丧乱之日较短,可以视为一个朝代,则郑玄一系经师看到的《周官》必定与秘府本无异。事情可能复杂得多,秘府本及其抄本系列在东汉初年俱已毁尽,献王抄本的祖本也已不存,杜子春手中只有献王抄本的某个俗本,并无善本可资校订,又不能全文记诵《周官》,无法一一校出汉儒注文。从此,汉儒注文大量窜入《周官》,为非议留下了口实。
即便窜入了西汉经师的注文,自东汉、两晋至隋,《周官》仍是公认的“群经源本”,常列“五经”之一。如,东晋元帝太兴初年,置八经,《周官》列第五。刘宋置“十经”,《周官》列第五,在《仪礼》和《左传》之前。唐宋以降,去古愈远,对“经”的判断标准愈加宽泛,《周官》始终在经籍之中,不必细说。随着今古文的辩争在清代进入极盛,经学风气丕变。伪古文《尚书》辨明之后,古文经的地位一落千丈,几乎与伪作相等 一些儒生站在理学的立场,对《周官》肆意诋毁。如万斯大的《周官辨非》,列举了五十条伪制,只凭一句话:圣人不会如此。意气用事,莫过于斯! 近代,又以成书年代为标准判断五经。常听学者以贬抑口吻说,今本《周易》 的成书年代已入战国,或者《左传》是战国文字,似乎成书年代晚至战国已不配称为经。若按这种标准,只有《诗经》、今文《尚书》中出在西周春秋时期的篇章或段落,才配称为经。
何谓“经”?
只有辨明什么书有资格称为“ 经”,才能真正理解《 周官》 的地位。
经,是汉晋士大夫定义的。中国的经,指那些最能再现或阐明三代文明的篇章。从再现的角度,当然是时间越早越好。《诗经》中的诗篇,代表三代文明的原貌,自然没有争议。 但从阐明的角度,却是越权威越好。 所以,汉晋经师把祖述周礼的《礼记》也定为经,把
解释周人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公羊传》《穀梁传》等定为经。他们不知道记、传晚出吗? 当然知道。他们不知记、传之间多有抵牾吗?那也是常识。然而,经非史! 如果经必须符合今天史学的标准,只有《春秋》 是纯粹的史书,也就只有“一经”,不必谈“六经”。 实际
上,《春秋》 列在“六经” 中,也不因为是史,而是让“乱臣贼子惧”。大致说来,“文以载道”才是评判经的核心标准。今文《尚书》是公认的经,如果按今天的学科分类,它妥妥地算文学类,里面涉及的人物和事件,只能当传说或故事看。 如果非要一一证明今文《尚书》中的故事是真实的,那就掉进了经史不分的陷阱。进一步,经是文化的概念,没有著作年代的限制。比如,贴上“今文”的标签,并不保证著作年代在春秋以前。“今文”仅仅代表西汉时尚有儒生能讲,有师说可传,至于原文写在西周春秋,还是写在战国,是不能保证的。《禹贡》是今文,但著作时间必定已入战国。《金縢》是今文,但它的后半部分添加于战国。难道要在今文《尚书》中再做一番经与“非经”的区别? 那是笑话! 反过来说,写于西周春秋时期的著述未必有资格称为经。比如,若有一部西周的兵书传下来,班固不会把它放在“六经”中,至多放在礼类的记、传中,就像《司马法》。再如,《山海经》《水经》都自称“经”,即使它们是西周时的著作,也永远不会属于“六经”或“十三经”。
从经的定义就知道,重要的是阐述者的权威性,而非成书年代或事件真实性。当然,成书年代最好在秦火以前,否则也降低了权威性。只要成书于先秦,权威性就取决于人,而非年代。比如,孔子晚于管仲,孟子晚于商鞅,《管子》和《商君书》中或多或少地保留了管、商二人之学,然而,就算里面每个字都是管、商二人所作,这两本书也绝不会因此称为经。 真正的经,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没有一部是独著,全部是集体创作的结晶。《论语》和《孟子》在汉晋时只在子部,不可称为经。或许有人认为,《语》《孟》《管》《商》等在子部只是目录学意义的分类。不然! 它们不能称为经,是因为个人著作毕竟带有一人或一派的创见,不一定忠实地反映了三代文明。也就是说,称为经的著作要保证忠实于三代文明。 或者说,唯有忠实于三代文明或旨在解释三代文明,才有资格跻身于经之中。同时,经是优中选优的结果,以经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是知识精英群体共同创造与主导的。 它崇尚知识与智能,厌弃愚昧;崇尚明智与中道,拒绝极端。经的主旨是明理,这是汉语文化圈看待经的一贯态度。所谓载道,道是贯穿于文明中的规律性。以阐述道理为主旨,为世间树立模范,为后世立法度的著作,才可称为经。看待外来文化也是如此,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皆作如是解。
又需说明的是,汉晋士族子弟研读诸经是为了恢复旧制,也可以说是为了复兴三代文明。 翻看正史,《史记》以下直至新旧《唐书》,记载大夫士援引《周官》以创建、改造或增删制度的实例,目不暇接。唐以前的士族,无需为考取功名去作“八股文”,有见识、有能力者迟早要出仕,学习经籍是为了在出仕之后能引经据典,匡正政事,订定本朝体制。这一时期的经,与本朝大政方针是同义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宋以后,科举兴盛,平民由科举入仕,经籍看似捧得更高,其实已沦为田舍郎获取富贵的敲门砖,经籍中的道理渐渐视为陈词滥调,地位有所下降。不过,王安石尚能依托《周官》为改革大旗,可见经在北宋士大夫中还有极大的号召力。元朝,人们经历了杀人如麻的暴政,庆幸苟全性命于乱世,对经籍所载的王道深感绝望,经籍几乎变为废纸。 明朝恢复华夏,士大夫尚能议政,又稍稍重视。至清入主,忌讳深刻,兴文字狱,株连以万数,秦政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从此,读书人寻章摘句,以记诵为能事。经籍的地位再变,从引领改革的政治纲领,变为名物考据家的依据,古文经学几乎成了小学的代名词。用成书年代判断经籍的地位,此时也已显出端倪。兼之元、明、清三代,皇权专制变本加厉,有骨气之人尽遭屠戮。屠余之人心生畏惧,于是不敢务实,转而向内用力,渐渐以蹈虚为己任,发明出各种精致的心性之学,尽讲空疏的道德,拘束人
心有余,挽救糜烂则不足。发展到最后是自我欺骗,以为凭道德文章就能救世,进而相互比赛谁的调门更高。像万斯大的《周官辨非》,满嘴圣人如何,就是此类代表。现在看来,都不过是些争宠的心机,只能诛心、杀人与误国。近代说它们是“伪道学”,不可谓毫无道理! 至清覆亡,经籍的地位再一变,不再是改制的依据,不再有潜心经籍的读书人群体,从此经籍与故纸无异。既如此,如果我说今人已经丧失了评判经的资格,恐怕不会有人异议吧? 那么,经籍的地位,何妨存旧制,维持汉晋士大夫之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六经”之中是否还有地位高低之别? 当然有! 一言蔽之,“六经”的地位以出身为标准,出身越高,地位越高。具体说来,以出自周王室或王官为上,姬、姜等旧侯国次之,再往下则不入流。西周时期,王室的文化成果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周王
的礼乐是最精致和优雅的,王制是最完备先进的。这里用的“最”,都是相对于诸侯、诸臣与四方而言,在当时是不争的事实,不承认就不必谈上古史。因此,《周官》在经籍中的地位与《诗》《书》《易》并列,这四经集中反映周王室的文化与制度。若比喻成一个人,《书》
《易》是思考和决策的大脑,《诗》是说话的嘴,《周官》则是骨架躯干。若要系统了解三代的制度,又以《周官》为唯一门径,绝无他途。唐以前士大夫重视制度改良,把《周官》奉为“群经源本”,毫无过誉。四部之外,《仪礼》可比人的衣冠服饰,可惜士礼的等级较低。《春秋》可比人的血肉肌肤,可惜是侯国史书。
“六经”的合理排序是:1.《诗经》;2.《尚书》;3.《周易》;4.《周官》;5.《仪礼》;6.《春秋》。
——选自俞江《〈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