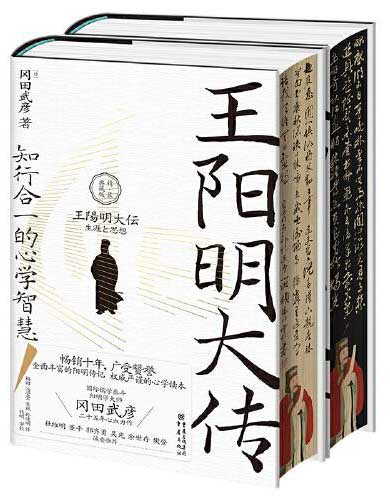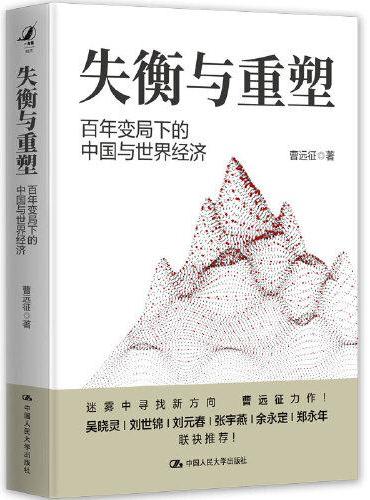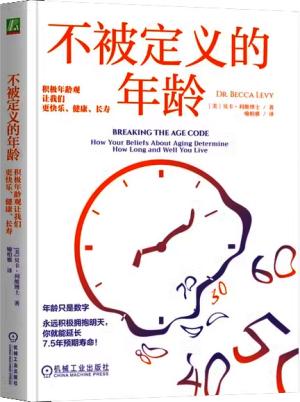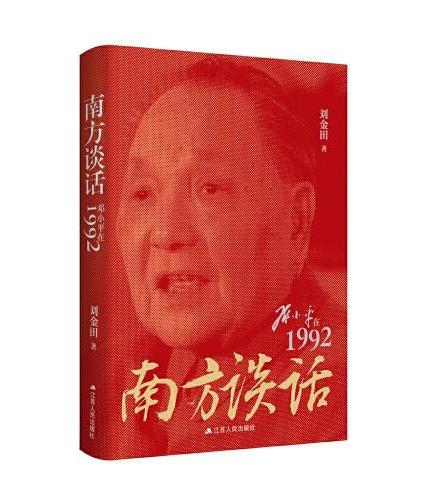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强者破局:资治通鉴成事之道
》
售價:NT$
367.0

《
鸣沙丛书·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
售價:NT$
551.0

《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兼论宗教哲学(英国观念论名著译丛)
》
售價:NT$
275.0

《
突破不可能:用特工思维提升领导力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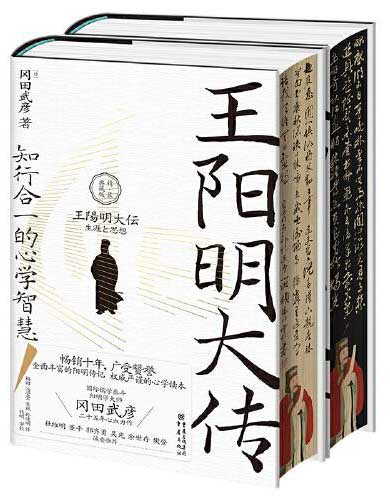
《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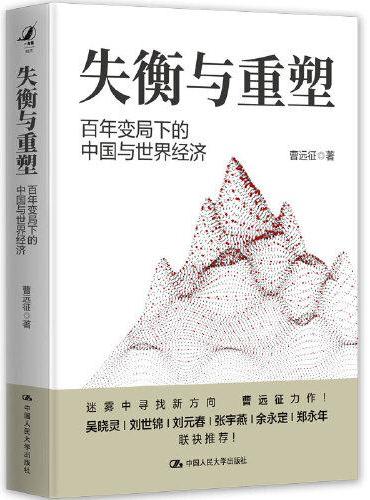
《
失衡与重塑——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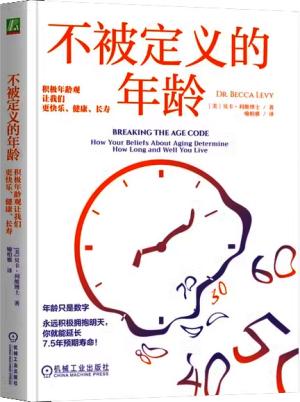
《
不被定义的年龄:积极年龄观让我们更快乐、健康、长寿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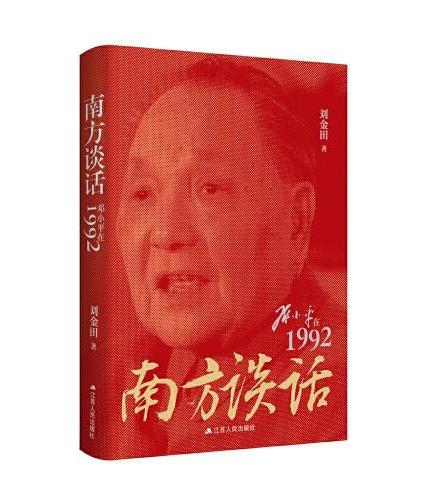
《
南方谈话:邓小平在1992
》
售價:NT$
367.0
|
| 編輯推薦: |
★ 比尔·克林顿(美国第42任总统)×凯博文(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系教授)×金墉(前世界银行行长)×特雷西·基德尔(普利策奖获得者)×潘天舒(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联袂推荐
★ 19篇振奋人心的全球健康倡议演讲,对医疗公平、医学的未来与愿景、社会团结与正义等主题的深刻思考
★ 写给每一位医学专业人士,也写给普通读者,尤其是正在思考未来人生道路的年轻人
★ 了解保罗·法默行医理念及其毕生志业的理想入口
★“贫困和不平等正是我们这个拥挤而美丽的星球所面临的两大问题——不是唯一的问题,但或许是最为严峻的问题”
★ 为贫困人群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是否真的 “不可能”“不可持续”“低性价比”?跟随保罗·法默一起,打破种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医疗公平的行动蓝图也由此清晰显现
★ 我们无需成为另一个保罗·法默,而是从他那里获得启发——“如何在不断变化且紧密联系的世界中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
|
| 內容簡介: |
“陪伴是他的方法,也是他的生活。”
------------
“谈到公共卫生,很多人说家庭、村庄、社区、城市、国家。但首先是病人,一个一个的病人,治疗病人的时候,你才会学到怎么治疗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也许整个世界。”
------------
保罗·法默是哈佛大学医学和人类学双料博士,曾任哈佛大学科隆科特隆斯校级教授、哈佛医学院全球健康和社会医学系主任。本书汇集了他在哈佛医学院、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及医学院毕业典礼或其他公开场合的一些令人难忘的演讲。这些演讲涵盖了一系列精彩主题,包括在资源极其匮乏的环境中提供医疗服务的挑战、对医学未来的思考、以医学为志业、让公共卫生变得重要、医疗保健权利、医生的勇气与同理心,等等。
法默曾写过许多学术著作,但通过这本演讲集,我们将能够在其轻盈又不失深刻的话语中,以一种全景式的视角轻松地了解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那些理念。他的事迹结合他的演讲,将对年轻人起到莫大的示范和鼓舞作用。
|
| 關於作者: |
★ 2020年博古睿奖获得者
★ 福布斯400社会企业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 国际应用人类学协会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奖和玛格丽特·米德奖获得者
★ 美国医学协会(AMA)杰出国际医师内森·戴维斯 (Nathan Davis) 奖获得者
保罗·法默(Paul Farmer)是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医学人类学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全球健康人物之一,曾任哈佛大学科隆科特隆斯校级教授、哈佛医学院全球健康和社会医学系主任。自1983年到海地开诊,法默就立志为生活在赤贫中的人们提供医疗服务,他创办的公益组织“健康伙伴”活跃在海地、卢旺达、秘鲁、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为贫困人群带去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终其一生,法默为“将现代医学带给最需要的人”而奋斗直至生命最后一刻。2022年2月21日,他因突发心脏病在卢旺达去世,享年62岁。
译者简介
张晶,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硕士。资深媒体人。曾任《第一财经周刊》驻纽约代表,其间创立播客“声东击西”。现任职于某科技公司。始终对世界保持本能的天真和好奇心。
|
| 目錄:
|
中文版代序1
序 言15
引 言25
第一部分 重新想象公平43
(年轻医生)灵魂的普遍麻木?
布朗大学医学院,2001年毕业典礼50
顿悟、转化和实践:由焦虑进入希望和行动的变革之路
波士顿学院,2005年毕业典礼72
三个故事、三个范式和对社会企业家的一种批判
牛津大学,2008年斯科尔世界论坛91
吸入器的故事
圣十字学院,2012年毕业典礼116
对抗想象力的失败
西北大学,2012年毕业典礼134
第二部分 医学的未来和愿景151
如果你服用了红色药丸:对医学未来的深思
哈佛大学医学院,2003年毕业班日157
以医学为志业
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2004年毕业典礼183
震后海地
哈佛大学医学院,2010年“正午”演讲系列204
关于破伤风的演讲
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2010年毕业典礼223
第三部分 健康、权利和非自然灾害239
全球健康公平和在大规模拯救中遗失的武器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04年毕业典礼248
让公共卫生变得重要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
2006年毕业典礼273
非自然灾害和医疗保健权利
杜兰大学医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295
探索相邻的可能
乔治城大学,2011年毕业典礼307
第四部分 服务、团结、社会正义327
谁在坚守阵地?
纽约协和神学院,2006年荣誉奖章授予典礼336
关塔那摩时代的勇气和同理心
埃默里大学,2007年毕业典礼350
灵性与正义
新教圣公会教堂(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
2008年灵性与正义奖授予仪式370
让希望与历史押韵
普林斯顿大学,2008年毕业典礼386
指挥家本能
波士顿大学,2009年马丁·路德·金日庆典403
作为政策的陪伴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2011年毕业典礼420
注 释443
致 谢471
|
| 內容試閱:
|
全球健康公平和在大规模拯救中遗失的武器(节选)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毕业典礼
2004 年6 月10 日
我也很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卫生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演讲。它比起在医学院做毕业演讲更有挑战性。其中有些常见的恼人规则:比如避免讨论党派政治。如果提到战争,也应该是发生在过去那些世纪的战争,包括布拉德?皮特出演过的电影里的那些。接下来还有公共卫生学院自己的准则,比如鼓励使用“患病率”和“发病率”这样的术语。“基于人群”和“疾病负担”这类术语也是被鼓励使用的。今天这种场合不需要生物统计学数据,但好的公共卫生方面的笑话和段子是需要的。
这的确是个问题。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听过公共卫生领域的笑话?我们这个领域可不是什么搞笑的领域。更糟糕的是,笑话必须能产生文化上的共鸣,因为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常平均每个班上都有来自64个国家或地区的学生,加起来可能说着147种不同语言,这还不包括你们现在可以流利运用的公共卫生语言。
这里有一个跨文化的公共卫生笑话,我最初是在隔壁餐厅听到的。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于1978年签署的《阿拉木图宣言》被认为是现代初级卫生保健运动的里程碑,宣言的崇高目标是“到2000年人人享有医疗保健”——其中提出的所有计划,无论是提升疫苗接种率,还是减少营养不良现象,都被签署国认为是可行的。然而,在大多数最需要它们的国家,这些目标并没能实现。一些最贫困国家的健康指数还在恶化。随着2000年临近,《阿拉木图宣言》的口号在国际卫生界也成为了笑柄。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口号有个错别字,应该是‘到3000年让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
你看,并没有出现捧腹大笑的场面。公共卫生领域的笑话,基本都是黑色幽默,因为代价太大了。既然代价很高,我们的标准也必须很高。但相反,我们看到,以实用主义的名义去解决穷人的健康问题时,人们的期望值在逐渐降低。这一直是一个重大问题:如今,在国际卫生领域,给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设定低标准成了一种“默认机制”。当你开始或继续你的职业生涯时,你将不得不应对一些所谓的传统智慧,正是它们造成了我们为世界底层的十亿人口所设定的低标准。
……
贫困国家的状况更加令人不安。在讨论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口时,你会听到我们这类人说:“不,我们不能专注于精神疾病,因为那样我们就不会对传染病足够重视了。”又或者:“资源匮乏的前提下是无法治疗艾滋病的,因为这样就没钱进行预防了。”我发誓我曾经目睹过有位专家责备另一位专家,因为前者专注于研究由烹饪时的灶火引发的哮喘——而真正的问题其实是烟草。这真是书呆子之战啊!
这些小冲突又是如何在贫困者的生活中发生的呢?
东非小旅行
让我通过最近的一次东非之行来告诉你答案。为了保护无辜者,我不会提到国家名字,但这次旅行期间我们住在马赛地和维多利亚湖畔附近(这就把范围就缩小到了两个国家)。我当时和“健康伙伴”的负责人一起旅行,该组织致力于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我们一起参观了几个艾滋病项目。马赛地的一个小型项目把预防和治疗结合起来,并为那些从未接受过这类服务的牧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我们从内罗毕飞往凯乌鲁山,一个世界上非常美丽的地方。乞力马扎罗山就像一座丰碑一样耸立着,很多大型哺乳动物在点缀着金合欢树的浅绿色草原上奔跑。我们和一名肯尼亚飞行员在一架小飞机上(等一下——我好像不该提到任何国家)。我坐在后座,右边是一堆仿制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飞机在草地停机坪上嗡嗡作响,赶走了正忙着在吃草的动物。
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我当时只问了飞行员一个问题。我指着啃着金合欢树的长颈有蹄类动物问道:“那些是长颈鹿吗?”飞行员不屑地答:“是的,医生,那些是长颈鹿。”但看着我的眼神好像在说:“不,先生,它们是法国贵宾犬。”我太惊讶了,以至于很快就不再感到尴尬。
第二天,我们拜访了在诊所和家中的患者。如你所知,马赛人往往又高又瘦。我还注意到,有些人少了下面一颗门牙,笑起来有一道黑色的缝隙。我问了一个在这个项目里工作的朋友这是为什么。她说,这颗牙齿是被预防性地拿掉的,这样一旦因破伤风出现“牙关紧闭症”的时候,他们的家人可以喂食牛奶,增加他们活下来的机会。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针对“当地情况”的一个巧妙甚至了不起的应对方式。当偶尔有住在医院附近的人感染破伤风(仅仅是一阵痉挛就可能导致脊柱骨折)的时候,我们会插入鼻胃管,通过它给病人喂药和食物。我想,牙关留有缝隙多少是一种类似的思路。
这些做法哪怕在20世纪真的算得上聪明或了不起吗?更不用说21世纪了。要知道,破伤风疫苗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推广了。看着这些可爱的马赛人,我有点想大喊:“为什么不给他们打疫苗,而要拔掉他们的牙?”但由于我们参观的这个项目的工作涵盖了从疫苗接种到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我只能默默祈祷,并感谢项目成员正在用有效的方式解决“结果差距”问题。
维多利亚湖之行更加令人不安。在那里——艾滋病一开始被发现的那个地方——HIV携带者在某些社区年轻人中占到30%。我们看到了很多孩子和老人,但是年轻人不多。看看你们周围的同学:那里缺失的正是和你们年龄一般大的人。消失的一代。想象一下。
我们去那里是为了评估孤儿项目,以及针对艾滋病患者的“家庭护理”项目。但由于家庭护理不包括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大多数接受这种护理方式的患者都没能活太久。负责运营这些项目的非洲同事感到非常沮丧。他们说,如果有合适的工具,就能让这套机制发挥作用。
当然,这些是我们在海地的经历。人们经常问我们,为什么海地中部的艾滋孤儿这么少?部分原因是,在那里,艾滋病晚期的年轻妈妈有理由要求获得和波士顿相同标准的护理条件。为什么在维多利亚湖沿岸,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没能得到更广泛的使用?很明显,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甚至连仿制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都买不起,而那些资助过我们拜访的项目的跨国机构呢?他们有能力负担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的费用,却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专家告诉他们这样做“不划算”。性价比不高。不可持续。不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优先事项。想象一下在维多利亚湖的岸边听到这种说法,那里有很多孩子当家的家庭(child-headed households)、拥挤的孤儿院和无人耕种的田地。但是话说回来,这些主张并不来源于这样的地方,而是在波士顿、日内瓦、华盛顿、伦敦或纽约。无论在海地、非洲或者这附近的某个角落,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穷人会说:“医生,别费心了,我认为治疗我不划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