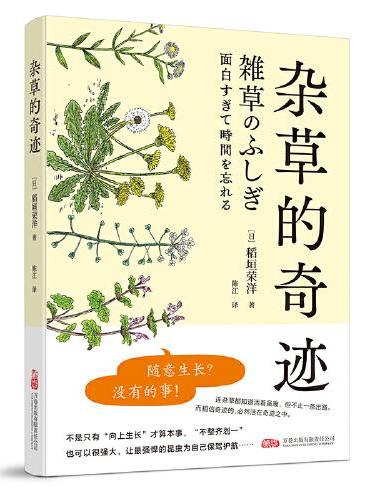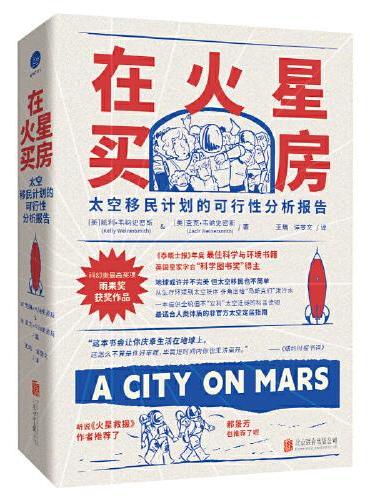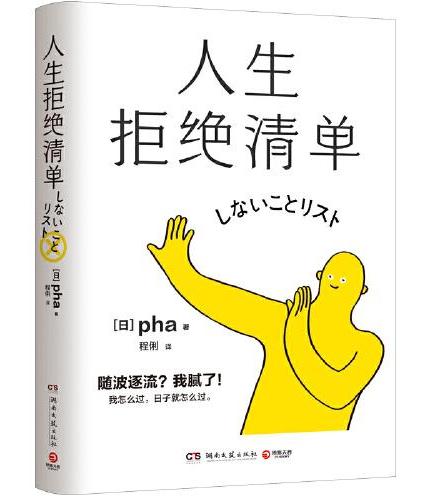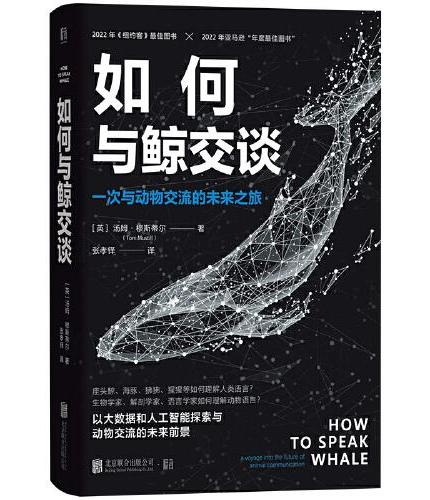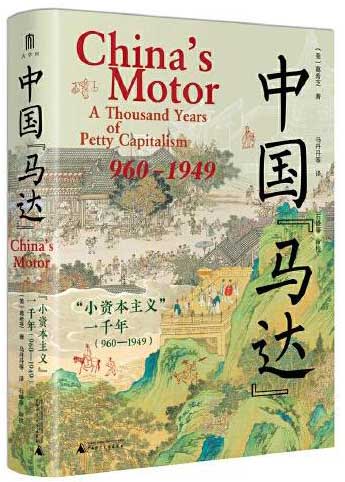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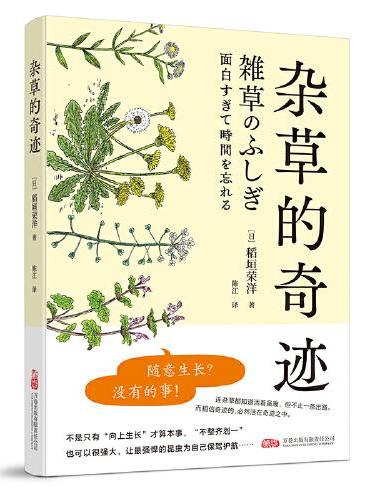
《
杂草的奇迹(杂草学家稻垣荣洋精心总结 脚下蔓延的杂草生存策略)
》
售價:NT$
2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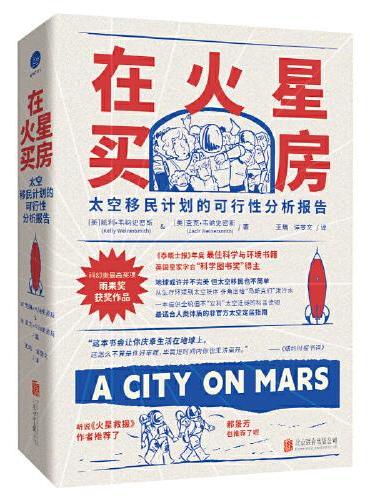
《
在火星买房:太空移民计划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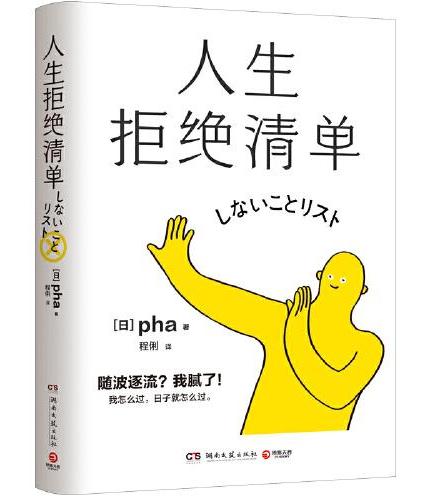
《
人生拒绝清单
》
售價:NT$
245.0

《
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
》
售價:NT$
281.0

《
哪吒之魔童闹海艺术设定集
》
售價:NT$
1010.0

《
混搭的承诺:现代政治观念史40讲
》
售價:NT$
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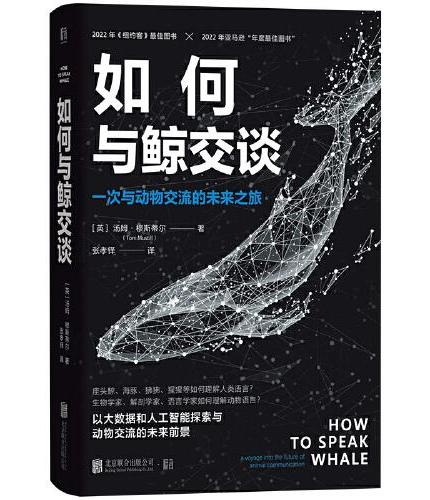
《
如何与鲸交谈:一次与动物交流的未来之旅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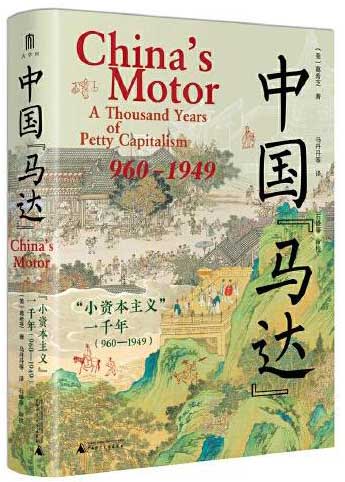
《
大学问·中国“马达”:“小资本主义”一千年(960—1949)
》
售價:NT$
359.0
|
| 編輯推薦: |
|
通观中国古代各体文学发展演进的种种实际情形,叙事与抒情经由共生、分化、消长、互渗的历程,两者边界是流动变化的,非一次划定而截然清晰。在原始宗教、远古神话、上古歌谣、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巫歌楚辞、《周礼》“六诗”之赋比兴等形式载体中,叙事与抒情是一体共生的;春秋以至两汉时期,随着 “六诗”的赋与比兴分开,“诗亡然后《春秋》作”,赋的手法与赋的体式分开,赋体文学与他体文学分开,叙事与抒情分化,其边界日益清晰;此后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类、以说部为代表的叙事文类分途发展,其抒情、叙事的份额与质性此消彼长,两者边界主要表征在文体分类上;及元明清时期, 叙事与抒情诸要素在此消彼长同时,竟在某些特定文类中出现 互渗现象,如人物诗传、长篇叙事诗 (咏剧诗、绝命诗、子弟诗、弹词等)、说部 (小说和戏曲)中嵌入诗词,以致有时模糊 了叙事与抒情的边界,因使诗歌叙事传统发生明显的新变。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丛书之一种,研究时段为元明清,内容包括“导论 中国古代诗歌叙事的边界、传统与新变”“上编 元代诗歌叙事传统”“中编 明代诗歌叙事传统”“下编 清代诗歌叙事传统”。
|
| 關於作者: |
饶龙隼,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级访问学者,现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制度、中国文学思想史、近现代巴蜀经史学脉。出版著作《上古文学制度述考》《元末明初大转变时期东南文坛格局及文学走向研究》等七部,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刘蓉蓉,上海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领域有元明清文学、宋明儒学。发表《从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探讨其对当前大学教育的启发》《明代心学家钱绪山的生死智慧》等学术论文多篇。
田玉龙,上海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枣庄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先秦文论及元明诗歌研究。发表《“微”字义解》《明诗制题之叙事》等学术论文多篇。
石超,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大学博士后,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戏曲。发表《明代戏曲插图本的叙事系统——基于文字叙事与图像叙事的考察》等系列论文。
|
| 目錄:
|
导论中国古代诗歌叙事的边界、传统与新变1
一上古诗歌抒情与叙事之同体共生及分化2
二早前诗歌叙事的发展演进及体制规定性18
三元明清诗歌叙事传统之因变及研治策略37
上编元代诗歌叙事传统
第一章元诗叙事的总体特征57
第一节时段分布特征57
第二节空间分布特征61
第三节学术群派属性65
第二章元诗单体文本之叙事特色68
第一节正文本之叙事特色68
第二节副文本之叙事特色87
第三章元诗复合文本之叙事特色113
第一节集咏之叙事特色113
第二节套数之叙事特色135
第三节组诗之叙事特色144
第四章元诗叙事之心理结构层次157
第一节和陶: 人格向往158
第二节咏史: 文化情结169
第三节记梦: 真实的幻象180
第四节纪游: 体验与想像190
第五章元诗叙事之地理空间拓展201
第一节安南纪行诗之叙事201
第二节海洋纪行诗之叙事212
第三节西域纪行诗之叙事222
第四节上京纪行诗之叙事236
第六章元诗叙事观念与理论批评250
第一节元诗叙事纪实观念250
第二节元诗叙事理论批评260
中编明代诗歌叙事传统
第七章明诗叙事的总体特征271
第一节时段分布特征271
第二节地域分布特征279
第三节流派分布特征289
第八章叙事型诗的体类形态301
第一节乐府与歌行301
第二节组诗与联章323
第三节人物传记诗332
第九章明诗叙事的体格风貌339
第一节诗歌叙事的题材类型339
第二节诗歌叙事之人物群像364
第三节人物诗传之叙事艺术416
第十章明诗叙事观念之更新433
第一节诗歌叙事趋势之认识433
第二节缘事感发的创作思想450
第三节“诗史”的理论构建459
第十一章羼入诗歌的叙事功能469
第一节小说中羼入诗歌的体制因变470
第二节小说中诗歌叙事的文本呈现482
第三节小说中诗歌叙事的功能拓展494
下编清代诗歌叙事传统
第十二章清诗叙事的总体特征511
第一节时段分布特征511
第二节地域分布特征521
第三节流派分布特征534
第十三章清诗叙事传统的发展544
第一节清诗制题的叙事艺术新变545
第二节组诗叙事的历史文化增溢556
第三节小说羼入诗歌之叙事创变571
第十四章清诗叙事的语言特色589
第一节事语兼情景591
第二节古今典契合606
第三节雅俗之调适618
第十五章清诗叙事体类之创变635
第一节同题集咏诗歌之叙事635
第二节清代词与散曲的叙事640
第三节题画诗辞的叙事艺术658
第十六章清诗叙事品类的创新681
第一节子弟书的叙事策略681
第二节咏剧诗的叙事艺术705
第三节女性绝命诗之叙事726
后记754
|
| 內容試閱:
|
复雅就俗: 元明清诗歌叙事传统研究导论中国古代诗歌叙事的边界、传统与新变导论
中国古代诗歌叙事的边界、传统与新变元明清时期诗歌叙事之传统,并非独立在外以自成一系;而是在因承早前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并出现若干新变。其拓展与新变固然重要,但并非诗歌叙事之主导;主导元明清时期诗歌叙事的,还是对诗歌叙事传统的因承。而要讨论中国古代诗歌的叙事传统,就无法回避诗歌抒情传统之另一面,且随着国际交流和跨文化对话的开展,又必然引发孰主孰次及二者边界问题。
近世以来随着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讨论的深入,中国古代文学叙事与抒情的边界问题日益凸显。它们究竟有无边界?若有边界则在哪里?其边界是模糊的,还是截然清晰的?其边界是一次划定,还是历史地生成的?这一系列问题,亟需得到解决。这些问题若获解决,且能付诸学术实验;则可为疏通中国文学抒叙传统提供理论依据,也能够更好地参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国际对话,以校正充实陈世骧提出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说陈世骧: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论中国抒情传统》,张晖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9页。,并证成中国文学叙事与抒情两大传统之双线并行论。
通观中国古代各体文学发展演进的种种实际情形,叙事与抒情经由共生、分化、消长、互渗的历程,两者边界是流动变化的,非一次划定而截然清晰。在原始宗教、远古神话、上古歌谣、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巫歌楚辞、《周礼》“六诗”之赋比兴等形式载体中,叙事与抒情是一体共生的;春秋以至两汉时期,随着“六诗”的赋与比兴分开,“诗亡然后《春秋》作”,赋的手法与赋的体式分开,赋体文学与他体文学分开,叙事与抒情分化,其边界日益清晰;此后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类、以说部为代表的叙事文类分途发展,其抒情、叙事的份额与质性此消彼长,两者边界主要表征在文体分类上;及元明清时期,叙事与抒情诸要素在此消彼长同时,竟在某些特定文类中出现互渗现象,如人物诗传、长篇叙事诗(咏剧诗、绝命诗、子弟诗、弹词等)、说部(小说和戏曲)中嵌入诗词,以致有时模糊了叙事与抒情的边界,因使诗歌叙事传统发生明显的新变。
一上古诗歌抒情与叙事之同体共生及分化
上古诗歌之抒情与叙事,是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它始于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殷周时期,而终于诗赋文各自成体的两汉时期。此时期,诗歌的抒情与叙事行为发生,并且彼此之间产生相互影响。这总体表征为两种情形,即同体共生与体制分化。(一) 殷周时期叙事与抒情之同体共生
文字表达的方式多样,叙事与抒情特其二义,此外还有议论与说明等,而前二者更适用于文学。从中国文学史的源头上说,叙事与抒情发生孰先孰后,是个难以考索的问题,今日恐只能任其茫昧。然据甲骨文和青铜文,及其相应的表达辞式,犹可探悉情、事性状,并考察抒、叙之何如。甲骨文出现“事”字162处,只出现“情”字1处;青铜文无“情”字,出现“事”字338处;甲骨文无“抒”“叙”字,《殷周金文集成》亦无之。甲骨文出现“事”字,分别见《甲骨文合集》115处、《甲骨文合集补编》41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6处;甲骨文出现“情”字仅见于《甲骨文合集补编》1处;青铜文以《殷周金文集成》为检索标本。这起码说明,在殷周之际,抒与情、叙与事不可能成辞,抒情与叙事的概念无从谈起。
然而这只是一种器物文字上的表象,并不排除当时有抒情、叙事之行为。此中抒情、叙事的实际状况与情形,可据从“心”字和“事”字来分析。
先看从“心”字。在甲骨文字中,从“心”者少,据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著录,从“心”的甲骨文字大略有15个,分别为心()、文()、吢()、()、()、沁()、惄()、懋()、悤()、寍()、()以及不可识读的、、、,这些字多为人、地、水名,看似没有明显的情感含义,其所出文句多为叙事,亦几乎没有抒情意味;据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从“心”的青铜文字大略有84个,其中带情感含义的字,有心()、志()、忍()、()、()、忑()、()、懽()、懼()、(),其所出文句多为叙事,且早期略无抒情意味。
如较早的周武王时器保卣铭文: 乙卯,王令保及殷东或五侯,兄六品,蔑历于保,易宾,用乍文父癸宗宝彝。遘于四方王大祀、于周,才二月既望。又如较晚的周宣王时器虢宣公子白鼎铭文: 虢宣公子白乍鼎,用追享于皇且考,用祈眉寿,子孙永用□宝。以上参见陈梦家: 《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上册,第7、330—331页。但也有学者指出个别特例,如西周前期作册嗌卣铭文: 乍册嗌乍父辛,氒名义曰:“子子孙宝。”不彔!嗌子,子延先尽死。亡子,子,引有孙!不敢忧。况彝,用乍大御于氒且匕、父母、多申。母哉!戈勿剥嗌鳏寡遗,石宗不刜。晁福林说:“《作册嗌卣》却是一个例外,它既没有称颂先祖之美,也没有走‘子子孙孙永宝’这样的‘明著之后世’的路径,而是彰显个人的失子之痛、失子之忧。就此而言,若谓此篇铭文是后世悼亡文字的滥觞,并不过分。此篇铭文没有直接写自己的苦痛心情,而是胸臆临铭而发,感触方现于笔端。”晁福林: 《〈作册嗌卣〉: 风格独特的周代彝铭》,《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4月29日第7版。据实而言,这番分析属援后例前,明显有夸大其词嫌疑。铭文中确实述及嗌亡子之事,但并非抒写器主的失子忧痛,而只是向祖神陈述其情,并明确说“不敢忧”。所以,该铭虽然表达很特殊,但仍属叙事而非抒情。
再看“事”字。甲骨文中,“事”字作、,从又持,为手执简书之象形,其在卜辞实例中,事、史、使无别,盖指执简策之职官,及其所掌管之职事于省吾说:“史字所从之,究属何物,实难索解。……王国维以为为盛简策之器,亦难令人信服。商代已有典册,但未见与有任何联系。晚周以后‘中’之形制尚难以说明商代事物。”(《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四册,第2961页。);青铜文中,“事”字作、,从又持,亦手执简书之象形,盖承甲骨文之笔势而来,然上作三歧乃周文特有,亦指执简以记录之职事。王国维说:“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引申而为大官及庶官之称,又引申而为职事之称。其后三者各需专字,于是史、吏、事三字于小篆中截然有别。持书者谓之使,治人者谓之吏,职事谓之事。”王国维: 《观林堂集·释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0页。由此可知,史为记事之类职官,事为史官所记之事;则甲骨、青铜文之叙事职能,乃殷周制度设施之固有节目。陈梦家曾通过综述西周铭文所载,将成、康以后史官演变分为三期: 参见陈梦家: 《尚书通论》(增订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7页。初期中期晚期乍册乍册尹、命尹内史内史、乍册内史、乍命内史内史尹尹氏、尹氏友尹氏史史史这三个时期都有史与内史之类职衔,恰合“大史、内史掌记言、记行”说。《礼记注疏》卷二十九《玉藻》,郑玄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74页上。后世传说、文籍载述,又有左史、右史之分。如刘勰称:“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刘勰: 《文心雕龙注》卷四《史传》,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3页。关于左史、右史之职分,史载有两种相反的说法。刘勰所记特其一种,同于《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然史志所载,正好反过来。《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隋书·经籍志》:“夏殷以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两说以何为正,今日难以稽考。不论“言”“事”如何,均为史官所叙之事无疑。
但甲骨、青铜文所反映的情况,并不能说明叙事就早出于抒情。这是因为,龟甲兽骨和青铜鼎彝作为器物,其贞卜、祀典功能是第一属性,其所铭刻的文字只是附属品,而不是独立自足的文本形式。若将甲骨青铜器物与所铭刻文字一同观察,就会发现其所含叙事与抒情是同体共生的。通常贞卜的对象是祖先或神灵,贞人和时王都满怀虔敬之心情,在这通灵的占问与刻辞活动中,情感表达和事件陈述是并行的;同样,铸铭隐含的对象是祖先和后代,器主人既敬慕祖德又冀望后人,在其家族铭功纪德的铸造活动中,情感表达和事件陈述也是并行的。
今所见保存较完整的甲骨卜辞,包含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各部分文辞不是连贯的,而是贞卜诸环节的记录。如:“(前辞)戊子卜。(命辞1)嘏贞: 帝及四夕令雨?(命辞2)贞: 帝弗其及今四夕雨?(占辞)王占曰: 丁雨,不辛。(验辞)旬丁酉,允雨。”胡厚宣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第1413页。这四部分要连缀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叙事;而其连缀所依凭的就是贞卜程式,以及贯注其中的对上帝虔敬之情。故知其事与情是一体二分的,则叙事与抒情行为实属共生。青铜器铭的情况与甲骨贞卜近同,而又有自身特点和后续发展变化。早期青铜器的铭文简朴,字数偏少甚或仅为族徽,其叙事的意味不甚明显,而铭功纪德的情意较强;以后铭文字数逐渐增多,所述祖德勋绩亦更详实,其叙事的功能日益凸显出来,而与器主人的情意共为一体。
以上通过甲骨文与青铜文这类器物文字,分析殷周之际叙事与抒情同体共生现象。这个现象在远古时期是普遍存在的,因而隐含了叙事与抒情共生之通例。以此推寻,远古歌谣,例皆情、事兼含,抒情与叙事共体:
例1《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赵煜: 《吴越春秋》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63册,第60页。传说此为黄帝时的歌舞,舞蹈是模仿狩猎的场景,歌词是呈现捕猎的过程,前者为激奋情绪之宣泄,后者为连续动作之描述。将这两相配合起来分析,即为抒情与叙事之共生。
例2《葛天氏歌》:“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吕不韦: 《吕氏春秋注疏》卷五《仲夏纪·古乐》,王利器注疏,巴蜀书社2002版,第536—538页。此为远古葛天氏族祀神庆功的歌舞,仪式为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这八阕实为八个歌舞段落,逐一演述氏族生活的场景,包括养育百姓、图腾崇拜、水土保护、五谷生产、敬奉天常、建立帝功、依顺地德、统领万物吕不韦: 《吕氏春秋注疏》卷五《仲夏纪·古乐》,王利器注疏,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538页。引毕沅校语:“旧本作‘总万物之极’。校云: 一作‘禽兽之极’。今案《初学记》卷十五、《史记·司马相如传》索引及《选》注皆作‘总禽兽之极’,今据改正。”毕氏所据诸校本均出自唐代,比东汉高诱的注本更晚产生。“禽兽”作“万物”,或另有所本,可并存不废,而于义无害。,这些实堪称宏大叙事,而多种崇高情感寓焉。
例3《伊耆氏祭歌》:“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正义》卷二十六《郊特牲》,郑玄注,孔颖达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454页上。这是伊耆氏蜡祭歌舞,为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而模仿天神威吓训斥的语气,命令水土昆虫草木各安其事。此将叙事隐含在神威之中,而呈现快意又庄严的情氛。
例4《抢亲歌》:“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周易正义》卷三《贲》,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8页上。这是远古氏族抢亲习俗及场景的描绘,其野性冲动和欢快喜庆之情溢于言表。
例5《潜龙歌》:“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见群龙无首。”《周易正义》卷一《乾》,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5页上。这是一首远古歌谣,描述龙的潜飞过程;但它不是意脉联贯的文辞表达,而分属于筮占操持程式诸步骤。其步骤有四: 一,用枚蓍筹算,以确定占问事类所随机配对的卦名《乾》;二,查阅占卜书,以给《乾》卦的每一爻位和整卦配对谣辞;三,依据卦象和《易》象对爻辞作出解说;四,结合谣辞和《易》象来占断吉凶祸福。在这颇为神秘的操持程式中,逐步灌注敬慎、刚健之志意;故神龙潜飞之事与君子自强之志,同演述于卜官的筮占诸步骤之中。
例6《佚女歌》:“燕燕往飞。”此为有娀氏二佚女所作歌,因其极简朴而为北音之始。其创作情形为:“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吕不韦: 《吕氏春秋注疏》卷六《季夏纪·音初》,王利器注疏,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627—631页。燕应该是某氏族的图腾,盖该氏族与有娀氏通婚,才发生男女恋情,而产生这首恋歌。像这种演生于原始宗教之鸟图腾崇拜中的爱情,其燕飞鸣逝之事与恋慕不舍之情是一体未分的,两相共生,见于音初。
例7《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是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一所录诗歌,大概是依据更晚出文籍所载《击壤歌》诸本校订的。该诗前四句为叙事,最末一句则属议论。其实,在王充《论衡·感虚》等篇中,载录有《击壤歌》更早版本:“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此本叙事性增强,议论的意味减弱。若再往上追溯,则知该诗本无。《庄子·让王》曰:“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乎,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后《淮南子·齐俗训》亦因承之,只是将主角善卷改为古童蒙民。由此可知,传说尧盛平时期的击壤歌,实为一种自娱的歌舞唱和,其文辞之有无、文本之歧异实不足深考,然其情绪的发泄与美善之追述必相伴生。以上参考饶龙隼: 《击壤歌小考》,《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2期。
例8《候人歌》:“候人兮猗。”此为涂山氏女所作歌,因其极简朴而为南音之始。其创作情形为:“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吕不韦: 《吕氏春秋注疏》卷六《季夏纪·音初》,王利器注疏,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616—619页。“候人”既为极短之叙事,“兮猗”又是深情的发抒,两相共生,亦出音初。
如上所示,原始宗教活动中的歌舞谣讴,其抒情与叙事是同体共生的;而作为原始宗教整合升级版的祖神崇拜,及其制度化产物的甲骨贞卜、青铜铸铭,其抒情与叙事也仍是同体共生的,故表征为抒情与叙事之早期状态。这状态为叙事主要由文辞承担,而抒情主要由器物或仪制承担。总之,从远古歌谣,到殷周甲金,例皆情、事并生,更兼抒、叙共体。(二) 晚周两汉叙事与抒情之体制分化
中国本土的原始宗教诸形式,如天帝高级神、巫术仪式、图腾崇拜、万物有灵、祖先崇拜、自然星辰神话、祖神崇拜,及其作为制度化产物的甲骨贞卜、青铜铸铭、《周易》占卜、礼乐仪制、《诗》篇演述等等参见饶龙隼: 《上古文学制度述考·原始崇信及其表象》,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0—92页。,都是抒情与叙事的原始载体。这些原始载体之功能发挥,其有效时间是极为漫长的,上可追溯至遥远的鸿蒙时代,下则临届春秋晚期礼崩乐坏。但从周公旦制礼作乐,到孔子所遭礼崩乐坏,这些原始载体也经历一个衰落失效的过程,就是在这过程中抒情与叙事发生体制分化。
这些原始载体的衰落,是个局部缓慢的过程: 一方面,甲骨贞卜、青铜铸铭、《周易》占卜、礼乐仪制、《诗》篇演述等还在流行,但同时它们的某些传载功能、操持程式与寓意内涵在逐渐流失、消退或变改;另一面,言语这种新媒质的传载功能在悄然生长,并逐步取代器物或仪制原来担当的职能。由于早前叙事主要由文辞承担,而抒情主要由器物或仪制承担;所以言语传载功能之增长,更明显体现在抒发情志上。
这可从《诗》篇所载,来考察情志抒发状况。大抵说,十五《国风》和《小雅》中的情志抒发频繁,而《大雅》和三《颂》中的志意活动却极少。这个分布性状表明两点: 一,《诗》篇的情志抒发主要发生在志意活动场景,而明显远离朝政、宴飨、祭祀等公共典礼场合;二,其志意活动不再依赖礼乐仪制,而是主要诉诸言语文辞之表达。此性状既见于《诗》篇,也还表征于《尚书》中。例如: 1 谑浪笑敖,中心是悼(《邶风·终风》);2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3 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小雅·白驹》);4 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小雅·节南山》);5 心之忧矣,云如之何(《小雅·小弁》);6 往来行言,心焉数之(《小雅·巧言》);7 啸歌伤怀,念彼硕人(《小雅·白华》);8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商书·太甲下》);9 尔惟训于朕志(《商书·说命下》);10 志以道宁,言以道接(《周书·旅獒》);11 有夏诞厥逸,不肯慼言于民(《周书·多方》)。例1至例7是《诗》篇中的语句,年代范围为西周初以至春秋中期;而从其情感色彩看,大多是忧伤的思绪,盖属变风、变雅之类,应出自平王东迁前后。这些语例反映了西周晚期人们对志意与言语沟通的朴素认知,其主要特征是志意与言语发生直接沟通而不需礼乐仪制传载,志意是抒情主体的,言语也属抒情主体,两相均由抒情主体来操控,而达成二者的无间隔胶合。
以此认知进度来反观更早《尚书》中的语例,就会发现《尚书》的志意与言语沟通更古朴。例8和例9中的言语和志意,明显分属施受两种身份的人。施言者发出言语,来干预受言者的志意;受言者怀有志意,来接受施言者的影响。此即造成这样的一种状态,志意与言语不是同出一人;故二者沟通是间接的,尚未达至直接之沟通。例8和例10中的志意与言语沟通还另有隐情,即志意与言语借助“道”的中介而发生关联。这样,不论志意与言语分属两人,还是统合在同一个人身上,它们均因“道”的间隔而发生间接沟通,却无法达成直接沟通。至于例11“不肯慼言于民”,虽关夏政而所言在西周早期,时序上更接近《诗》篇中的语例,故其志意与言语沟通与《诗》同。由此可知,尽管《尚书》有疑伪成分,但其语例所显示总体情态,仍然真实地反映了殷周之交人们对志意与言语沟通的认知,故《尚书》与《诗》篇的认知序列恰与上述示例顺序相反,即在该时段人们对志意与言语沟通之认知,经历一个由间接沟通趋向直接沟通的进程。若说志意与言语间接沟通,仍表明有器物仪制的痕迹;那么志意与言语直接沟通,就使抒情脱离了器物仪制,以此引发两相的体制分化,而与叙事同诉诸语言表达。参见饶龙隼: 《上古文学制度述考·前诸子时期言意关系的新变》,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6—51页。
至此可以说,抒情与叙事之传载体制及界面,已由器物仪制转接为语言媒介。正是得力于语言媒介的逐步深入地参与,抒情与叙事的边界才因体制分化而彰显。比如殷周青铜铭文,越往后其文字越多;并且随着长篇铭文大量出现,不仅其叙事性获得长足发展,而且其抒情因素也有所增长,终使器物的表情功能被弱化。尤其战国中山王鼎,作为巨幅的青铜载体,竟然铭刻有六百多字长文,而使述事与写情一体兼备。其文曰:“氏(是)以赐之厥命:‘隹(虽)又(有)死辠(罪),及参(世),亡不若(赦),以明其德,庸其工(功),(吾)老(贾)奔走不听命,寡人惧其忽然不可得,惮惮,(恐)陨社稷之光;氏(是)以寡人许之,(谋)(虑)皆从,皮(克)又(有)工(功),智旃,诒死辠(罪)之又(有)若(赦),智(知)为人臣之宜旃。于(乌)虖(乎),(念)之(哉),后人其庸庸之,毋忘尔邦。”张亚初: 《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编号52840,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6页。此一文例亦充分表明,青铜器之情、事共生,已由器物含情、铭文述事之一体二分,演变为铭文既述事又写情之一体兼备;则其抒情与叙事之边界,也就移置到语言媒介上。
与此类似的情形,也显明在易象上。前引《潜龙歌》之文辞,是依托占卜操持程式的,其神龙潜飞之事与君子自强之志,实分属于筮占的文辞与程式之中,虽一体二分,而以占为主。及至春秋晚期孔子研《易》时,占卜功能弱化而文辞功能增强。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所出帛书,其中《要》篇有一段文字曰: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赣曰: ]“……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陈松长、廖名春: 《帛书要篇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35页。孔子研习《周易》之取向,是“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安其用”即尚占,是指卜、筮、赞、数等要素;“乐其辞”即尚辞,是指遗言、辞、德义等要素。在尚占与尚辞之间,孔子显然更重文辞。如此就出现了尚辞不尚占的趋势,以至有伪托孔子“十翼”之创作,其文辞义理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不再依赖占卜之操持程式。后《焦氏易林》即依循其文辞义理,推演编撰出四千零九十六首卦变辞。这些卦变辞均为四言诗,其中既有叙事又有抒情。如卦辞:“黄鸟悲鸣,愁不见星,困于鸷鹯,使我心惊。”焦延寿: 《焦氏易林》卷一《屯之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08册,第279页。这是一首很纯粹的抒情诗,其情思乃因《说卦》而来。依据焦延寿的“卦自为变”之占法,《屯》之《丰》可演为七个单元卦: 《离》有“雉”象,可引申为鸟;《震》有“玄黄”之色,则“黄鸟”之象出。《兑》有“口舌”之象,《坎》有“忧愁”之义,则“悲鸣”之象可得。《坎》又为水,可引申为云;《坤》有“阴”“夜”之象,合而为阴云;《巽》为风,风吹阴云掩盖天空,则“不见星”之象出。《艮》有“黔喙之属”,为黑嘴鸟类之象;《兑》又有“困境”之象,则“困于鸷鹯”之象生。《震》又有“决躁”之象,则可引申为“心惊”。参见陈良运: 《焦氏易林诗学阐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349页。这样仅在文辞义理上推演,就奇妙地生成一首抒情诗。像用这种方式创作的诗歌,实已脱离占卜程式之共体,而单纯在语言媒介上,就可区分叙事、抒情。
其实上述情形,也可反过来看。语言媒介功能之逐步上升,挤占器物仪制的传载空间,因使铸铭或筮占承担的抒情职能退化,而需更纯粹的言语文辞形式来替代之。如在晚周诗教兴废和两汉辞赋兴盛的背景上,“赋”的功能变迁及体式生成就颇能说明之:
在《周礼·春官·大师》中,载有针对乐师瞽矇的六诗之教,即风、赋、比、兴、雅、颂;同书《春官·大司乐》中,又有针对国子生员的乐语之教,即兴、道、讽、诵、言、语。前者旨在培养能演述诗篇的音乐人才,后者旨在培养能行使专对的行政人才。在周代礼乐制度尚完好时,这两类教职都属史官系统,能并存不替而各施其责,共同承载礼乐言语行为。及平王东迁而天子衰微,更因春秋晚期礼崩乐坏;这种教学制度遭破坏,出现“诗亡”的局面,瞽矇采《诗》之官失散,新的《诗》篇不再产生参见孟轲《孟子注疏》卷八上《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赵歧注,孙奭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27页下。;已经整编好的《诗》篇虽留在官府,但其礼乐形式日渐流失而徒有文辞,成为“赋《诗》言志”的素材,用来修饰朝堂议政和外交辞令;后来孔门开设言语一科,并以《诗》篇作为教程,就是为应对这个变局,以教导弟子能适应之;至于孔子删定“《诗》三百”,则无奈只能以文献形式保存之。在这脱落仪制而徒有文辞的《诗》篇文献中,原来诗乐演述中的抒情与叙事行为无所附丽;其情志的发抒与人事的记述,就须转接到新的创作活动中。当时活跃的创作方式有两种: 一是作为士大夫素养的“登高能赋”参见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而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二十四史》缩印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55页。,一是制度化的史官之“《春秋》作”。前者主打抒情,是溢出《诗》篇外的讴歌啸咏参见饶龙隼: 《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上编第一章《讴歌啸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09页。;后者主打叙事,是为春秋时期的列国《史记》。两者内涵、语体和功用均不同,展示了抒情与叙事的首次分化。
像这样转接为新的创作形式,只是“诗亡”后的一条出路;同时还开辟另一条出路,即用《诗》方式的变革。原来“六诗”之风、赋、比、兴、雅、颂,本是礼制完好时诗乐演述的六道工序,各项目之间是逐步递进的,共同承载抒情与叙事功能;但随着《诗》篇以文献形式被编定,其风、雅、颂作为诗歌类名得落实,而赋、比、兴则因无法归类而没有着落,这反映在《诗大序》中便为“六义”说。《诗大序》对“六义”说,只解释了风、雅、颂三项,而于赋、比、兴不予解释,因使此三项有流失的错觉。其实赋、比、兴这三项并未流失,而是以说《诗》的方式继续流行,今存《鲁诗》残篇、《毛诗》郑注等文籍,多保留“赋也”“比也”“兴也”解说语。如: 《关雎》,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嫔御之职,而供祭祀宾客之事,故作是诗。首章,于六义中,为先比而后赋也;以下二章,皆赋其事,而寓比、兴之意。
《氓》,淫妇为人所弃,鄘人述其事以刺之。首二章皆赋也,三、四、五[章]皆兴也,五章赋也,六章赋中有比也。以上申培: 《诗说》,程荣纂辑《汉魏丛书》本,明万历新安程氏刊本,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上、24上页。这从功能角度对赋、比、兴作出解释,而与风、雅、颂之诗歌体类分列开来;并历经郑众、郑玄、刘勰、钟嵘的递相沿袭,至唐初孔颖达《毛诗正义》而有三体三用说。更在此“三用”之中,赋与比兴进一步区分,赋通常指向叙事,比兴多指向抒情。如: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正义》卷二三《春官·大师》,郑玄注,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96页上。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刘勰: 《文心雕龙》卷二《诠赋》、卷八《比兴》,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610页。
诗有六义焉: 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钟嵘: 《诗品集注》卷首《序》,曹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郑玄从政教功利解说赋、比、兴,指明其铺陈与比类、取喻之差别;刘勰从摛文写志解说赋、比、兴,指出其体物与附理、起情之不同;钟嵘从言意关系解说赋、比、兴,提出书写事物与隐喻情志需相待。两相辞采、对象和效用均不同,体现了抒情与叙事的二次分化。
二早前诗歌叙事的发展演进及体制规定性
此所谓早前是指元代以前,包含从上古以至两宋时期。如上所述,抒情与叙事在经历了体制分化之后,诗歌叙事就进入分途发展演进阶段。其具体历程大略分三段式演进: 首先是抒情与叙事之各体消长,其次是诗歌叙事之多体式分布,终至诗歌叙事传统之凝定成形。(一) 唐前诗歌叙事与抒情之各体消长
上述抒情与叙事的两度分化,导致赋的叙事功能急剧增强。随着赋的叙事功能增强,其所叙事容量也在增加;当叙事文字达到一定长度,就会提高其篇幅的独立性;而文辞篇章一旦相对独立,作为文体的赋就脱胎而出。如战国晚期荀况所作《赋》,本是由五篇咏物短赋构成的,分别题咏礼、知、云、蚕、箴,文末附有佹诗、小歌两小部件。此五篇短赋用问答形式展开叙事,所谓“君子设辞,请测意之”云,颇类谜语竞猜而又含讽喻意味,将《诗》的讽喻精神移入赋体。类似兼含讽喻意味的咏物赋,还有宋玉《风赋》《钓赋》。是知赋虽“自诗出”,然已“分歧异派”。刘勰: 《文心雕龙注》卷二《诠赋》,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6页。同是发挥《诗》的讽喻精神,汉代楚辞批评诸家依经立义,将屈原所作《离骚》诸篇及后学追摹之作,强行纳入辞赋范围而有“屈原赋”之名目;又因主客问答是战国策士的主流言语方式,而使服习纵横家语的“陆贾赋”独标一类;至于《客主赋》等十二种,大都是咏物写事夸诞之作,因无法归入前三个赋类,乃汇聚一起而称为杂赋。
对此情形,班固评曰:“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班固: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诗赋略后序》,《二十四史》缩印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56页。同出于周代“六诗”之赋演述源头,至汉代而分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赋体从此走向独立,因而“与诗画境”。刘勰: 《文心雕龙注》卷二《诠赋》,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页。前者“丽以则”,后者“丽以淫”;“丽”即语言修饰,是为诗、赋所共有;“则”为遵守法度,“风谕”之义存焉;“淫”为逾越法度,“风谕”之义没焉;赋体既然“没其风谕之义”,便只剩“侈俪闳衍之词”了。这就是汉代大赋的体貌性状,其辞气之铺张扬厉长于体物写事,而相应地短于言志舒情,故与诗分任叙事与抒情。以后诗、赋分途演进,各成体类而边界分明,以至有“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之断制。《六臣注文选》卷十七《文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与赋体叙事性增强同步,诗的抒情性也逐渐凸显。中国诗歌最早的源头,当可追寻到远古歌谣;然至晚周时期,则有三个近源。一是经删修的《诗》文本,即文献形态的“诗三百”;二是士大夫“登高”所赋,即散见于载籍的讴歌啸咏;三是楚地巫歌及文人拟作,即屈原师徒所创作的楚辞。这三宗诗歌资源都出自“诗亡”之后,是与《春秋》叙事并行的抒情之产物,其情感特质明显,并获得当下认知。《诗》篇章句的情感特质,是在用《诗》场景发掘的。春秋时期断章取义式的“赋《诗》言志”活动,是建立赋诵者与《诗》篇之间的情感对应关系;孔门创设“不学《诗》无以言”的言语教学科,是开启《诗》兴、观、群、怨的情感教育功能参见《论语注疏》卷一七《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何晏等注,邢昺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5页中。。这些情感认知不断培养积累增聚,终至《毛诗序》中获得理论表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正义》卷一之一《大序》,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9—270页。这是“诗言志”说最早的完整表述,标志着中国诗歌抒情传统正式确立。
春秋时人“登高能赋”,本为士大夫的素能修养。故班固追述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班固: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诗赋略后序》,《二十四史》缩印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55—1756页。不论是赋诵那些脱离乐舞体制的《诗》篇章句,还是像《大隧》《狐裘》那样的“词自己作”,它们都是“睹物兴情”,允能“原夫登高之旨”。由此可知,散见于载籍的讴歌啸咏,容涵士大夫的情感体认。
楚辞是屈原借用楚地民间祭祀歌曲形式而创作的,如《九歌》就是他根据旧曲《九歌》而翻作新声,有所因袭,又有创新。王逸、朱熹都肯定《九歌》是屈原在沅、湘流域民间祭歌基础上的创作,胡适《读楚辞》、陆侃如《屈原评传》则指出《九歌》为楚地宗教舞歌;闻一多《甚么是九歌》则认为是楚国郊祀的乐章,周勋初《九歌新考》肯定《九歌》为屈原的创作。屈原创作一系列作品,已有明确的抒情意识。如《惜诵》“惜诵以至愍兮,发愤以抒情”,《抽思》“兹历情以陈辞兮,荪详聋而不闻”。此创作风气一旦开启,宋玉《九辩》亦效曰:“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于素餐。”对此,刘勰虽从宗经角度强调其“取熔《经》旨”,亦从情辞表达方面肯定其“自铸伟辞”:“《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刘勰: 《文心雕龙注》卷一《辨骚》,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页。
以上三宗对诗歌情感特质的认知,不仅终结了情志抒写的自发状态,而且凸显了诗家对情感的节文作用,从而确立了抒情在诗歌中的主体性。早在孔门《诗》的教学中,孔子就告诫弟子“无邪”;“无邪”就是保守《诗》的性情之正,对郑、卫之音不要往淫邪的方向去想。参见《论语注疏》卷二《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何晏等注,邢昺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1页下。嗣后,《荀子·劝学》:“《诗》者,中声之所止也”;《毛诗序》:“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止”就是节止于某一点,这在语言表达上即为节文参见荀况《荀子集解》卷四《儒效》曰:“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王先谦集解,《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3—134页。。若将节文转释为汉魏六朝时期更趋华美的言语修饰,则“诗缘情而绮靡”之“绮靡”就是对抒情的节文。这样,一方面诗歌明显具有情感特质,另一面诗家对抒情又有所节止。对此,刘勰总括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刘勰: 《文心雕龙注》卷二《明诗》,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页。若将大赋与诗歌对照而言,则其叙事与抒情各有消长。赋长于写物叙事,而短于言志抒情;诗长于言志抒情,而短于写物叙事。正如刘勰所言:“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刘勰: 《文心雕龙注》卷七《情采》,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38页。这就确立了叙事在赋、抒情在诗中的主导地位,从此叙事与抒情便成为大赋和诗歌各自的专长;以后虽因文体的变迁与交叠,叙事与抒情的成分各有消长,但总体上不超出这个基本格局,直到中国文学古典形态的终结。
如果说大赋与诗歌分任叙事与抒情,作为“诗亡”后的一种代偿与分化,实现了集体创制向私人创作的转换参见饶龙隼: 《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2页。;那么“《春秋》作”局面的出现,作为周代职官制度化写作之留守,则使史官的集体叙事职能不至失坠。当时各国都有史记之编撰,正如《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事即指春秋争霸之史事,其文则指对争霸事之史述,这当然是一种历史叙事,只不过仍属制度化写作。对孟子的这个称述,唐刘知几有解释曰:“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刘知几: 《史通训故》内篇卷一《六家·春秋家》,王惟俭训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据明万历三十九年序刻本影印,第254页下。
但随着春秋晚期职官制度进一步废坏,史官的史书撰述职能从官府下移民间,以至出现国史日渐旷缺,而私家竞相著史的现象。刘知几《史通》首篇《六家》论史家流别,其中的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均属私家著史的范围,表征了史学发展趋势。《春秋》乃孔子依鲁国史记而作,《左氏春秋》传说为左丘明所作,都是私家著史的代表作,传载了史文叙事之功能。故刘知几评曰: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隐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刘知几: 《史通训故》内篇卷一《六家·春秋家》,王惟俭训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据明万历三十九年序刻本影印,第254页下。尽管孔子修《春秋》,还能够遵行旧法遗文;但其义例已有学派倾向,甚至加入了个人的意见。如他惊惧弑君、弑父之事频发,乃在史文中寄托“微言大义”,称“知我”“罪我”惟在《春秋》,这种自我认知当然有他的评判标准。以上参见孟轲: 《孟子注疏》卷六下《滕文公下》,赵歧注,孙奭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14页下。《左氏春秋》之史述,主要是记事而兼记言,因其行文多有夸饰成分,而被史家奉为叙事典范。如刘知几赞曰: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叱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论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风;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刘知几: 《史通训故》外篇卷十六《杂说上·左氏传二条》,王惟俭训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据明万历三十九年序刻本影印,第385页。这显然突破了史家实录规范,而流为后世小说之虚构夸诞。此体流荡以至于战国时期,出现仿史书之《战国策》,其实只是辑录纵横家语,已入诸子著述的范围了。至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严氏春秋》之类,更只是假“春秋”之名以著诸子学派一家一得之见;其著史的体例既失,叙事也就无所附丽。直待司马迁之《史记》出,史文的叙事性才得以振复。所谓:“《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刘勰: 《文心雕龙注》卷四《史传》,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4页。“述”“总”“铺”“谱”,是《史记》行文之“古式”;而称“得事序”,就是得叙事之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