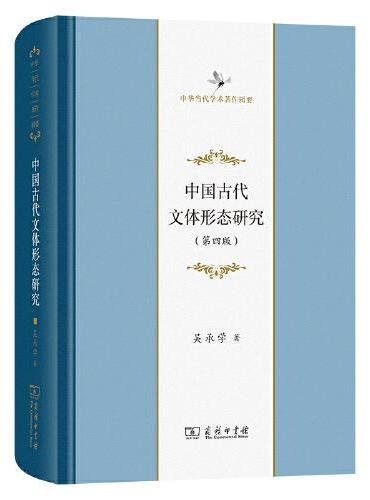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纷纭万端 :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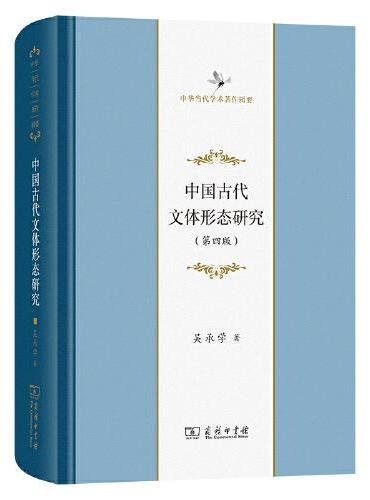
《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四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
售價:NT$
765.0

《
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大学问
》
售價:NT$
454.0

《
甲骨文丛书·波斯的中古时代(1040-1797年)
》
售價:NT$
403.0

《
以爱为名的支配
》
售價:NT$
286.0

《
台风天(大吴作品,每一种生活都有被看见的意义)
》
售價:NT$
245.0

《
打好你手里的牌(斯多葛主义+现代认知疗法,提升当代人的心理韧性!)
》
售價:NT$
301.0

《
新时代硬道理 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
》
售價:NT$
352.0
|
| 編輯推薦: |
★ 阅读汪曾祺应从文库本开始,它是第一套纯粹以读者视角编选的汪曾祺文集,来自资深读者几十年的阅读体验,是一个读者对另一个读者的口口相传。
★ 汪曾祺的作品非常适合做成文库本,不仅因为其篇幅短小,也因为文库本的形式更契合汪曾祺文字闲适、淡雅的气质。
★ 汪曾祺一生写下约250万字的作品,以散文、小说为主,“资深读者”杨早主编,经典甄选70万字,分10册,编为小说3册、散文5册、戏剧1册、书信1册,基本涵盖了所有体裁。了解汪曾祺及其作品,这10本小书足矣:《异秉》《受戒》《聊斋新义》《人间草木》《人间至味》《山河故人》《桃花源记》《自报家门》《沙家浜》《写信即是练笔》
★ 《汪曾祺文库本》以公认“经典”和大众“喜闻乐见”为编选标准,但对部分未被重视却有一定文学价值的作品亦特别收入。文库本不求面面俱到,不照顾研究需要,所愿者,是将汪先生最精彩的文本,最适合随时随处阅读的文字,以最适当的篇幅、形式呈现给读者。
★ 汪曾祺的小说共有162篇,约70万字。《异秉》收录的7部短篇写于1940―1962年,具有明显的现代派风格,如意识流的写法、对个人生存困境的关注等,是汪曾祺早期偏“诗化小说”
|
| 關於作者: |
|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著有短篇小说《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162篇,散文《昆明的雨》《故乡的食物》《人间草木》等550余篇,戏剧《范进中举》《沙家浜》等19部,以及诗歌、书信等共约250万字,有《汪曾祺全集》12卷、《汪曾祺别集》20卷。
|
| 內容試閱:
|
活着多好呀(代总序)
为什么要出这套10册的汪曾祺文库本?出版方在后面的《出版说明》中说得清清楚楚,用不着我再啰唆。至于每册收录的文章是何考虑、有何特色,选编者杨早先生在各册序言中也都有明确交代,轮不到我去当什么狗尾巴。杨早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员,对汪曾祺的作品颇有研究,搜罗了不少有关老头儿的趣闻,出过多部专著。他撰写的这些序言,旁征博引,娓娓而谈,对汪曾祺的为人为文都有精当评价,作为各册文章的导读十分合适,为这套书增色不少。
如此一来,我只能谈点儿零碎感想了。
文库本第7册《桃花源记》的序言中,杨早引用了汪曾祺在自编《旅食与文化》一书题记中的一段话,“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他还特地点明这篇题记是汪曾祺在距去世不到三个月时写成的,并评论说:“这是一位老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的慨叹,却是如此的‘人间送小温’。”对此,我们家里人也有同感。1997年5月老头儿逝世后,我们把这篇题记复印了一些,分送给送别他的朋友,算是他的最后赠言。
《旅食与文化》是《旅食集》再版时改的名字,原书刊行于1992年,书前有一篇百余字的短序:
“旅食”是他乡寄食的意思,见于杜甫诗。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本集取名“旅食”,并无杜甫的悲辛之感,只是说明这里的文章都是记旅游与吃食的而已。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五日
这是老头儿所写书序中最短的一篇,语气很平和。五年多后,他在《旅食集》再版时,添了七篇文章,改了书名,还将短序扩展为近千字的题记,最后部分,便是这段“活着多好呀!”
汪曾祺为什么会在暮年发出这样的感慨?说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人生总结”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这些年,老头儿作品中最受追捧的,就是写吃喝、写花草和记游之类的文章,相关的选集层出不穷、不知凡几。这套文库本,把老头儿所写的草木鱼虫、瓜果食物和山水游历的文章分别汇编,单独成册,大约也是想让读者更好地体验“活着多好呀”的滋味。
其实,汪曾祺的“活着观”,并非只存在于旅食之类的文章中。他的许多小说散文,都有这种气息弥漫其间。《受戒》《大淖记事》《羊舍一夕》《葡萄月令》《夏天》等固然如此,即便是《异秉》《七里茶坊》《随遇而安》这类略含苦涩甚至悲辛的篇什,如果细细品读,也会隐约听到“活着多好啊”的喟叹。应该说,这是汪曾祺作品的基调,也是他“人间送小温”创作主旨得以成立的基础。这套文库本的一个好处,便是将汪曾祺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中的精华集中展现出来,读者可以更加立体地了解其人其文,从多个角度体味“活着多好呀”的意蕴。
这套文库本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文本雅驯、少有错讹。这是李建新先生多年劳作的成果。建新校勘汪曾祺的文章堪称有瘾甚至有癖,往往为了一个字、一句话的正误,多方考证、反复斟酌,直到找到满意答案。例如,汪曾祺在散文《昆明的雨》中回忆,一次他和同学朱德熙在昆明莲花池游玩时遇到下雨:“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这段话读起来没毛病,而且老头儿自编的《蒲桥集》中文字就是如此。建新却认为,“半市斤酒”应为“半斤市酒”,因为汪曾祺自己写过,昆明市场上的白酒有升酒和市酒之分,市酒的档次较低,售价也更便宜。他在文章中特意点明“市酒”身份,多少反映出自己当时的穷酸。文章发表时,编辑大约不清楚什么是市酒,遂将“半斤市酒”改成了“半市斤酒”,这样的表述虽然说得过去,但失去了原文的本意。这样的考订,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阅读好文章若是有一个好文本,会让人倍感愉悦,就像吃上一碗热腾腾的新米饭,自始至终没有碰上一粒沙子。
一部文集,若是有几点可取之处,也就够了。
汪朗
2023年11月18日
1946年7年月,汪曾祺从昆明复员回上海。在香港等船的时候,有一天无所事事地逛街,汪曾祺居然在报摊的一张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青年作家汪曾祺近日抵达香港。”
汪曾祺是贯穿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作家。目前所发现他最早发表作品的时间,是1940年6月,他还是西南联大中文系大一新生。老师沈从文1941年2月3日致施蛰存的信里说:“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大有成就。”
文学史家将汪曾祺视为“京派”的殿军。“京派”涵括了从周作人、废名到林徽因、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一系列战前居于北京的作家,让他们形成流派的是思想与趣味的相似追求。用林徽因的话说,题材往往“趋向农村或少受教育分子或劳力者的生活描写”,对农人与劳力者“有浓重的同情和关心”,但更重要的是“诚实”。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散文,一起笔就带有这样的取向。本集中如《老鲁》《艺术家》《异秉》《鸡鸭名家》皆是如此,后两篇更是开启了后来成为汪曾祺标签之一的“高邮叙事”。
另一方面,西南联大的文学环境有着浓重的现代派氛围。联大出身的“新作家”,往往共同受到弗吉尼亚·伍尔夫、阿索林、纪德甚至萨特的影响。青年汪曾祺笔下的现代味儿也很足,甚至还在他展现出“京派”的文学特质之前。有一次走在校园里,汪曾祺听见前面有两个女生在聊天,提到汪曾祺这个名字,说是“就是那个写诗别人看不懂,他自己也看不懂的人”。像《小学校的钟声》虽然也是写高邮往事,使用的却是意识流的手法。汪曾祺后来回忆,当时就有很多人不同意这种写法,“说这有什么社会意义”。
《复仇》的现代派意味更是明显,是很典型的“诗化小说”。当然诗化这种方式,又与“京派”的某些作家如废名形成了传承。总之,20世纪40年代的青年汪曾祺小说里,有这样的“两种调子”。
1949年之后的汪曾祺当过教师、编辑、编剧,就是不写小说。1958年汪曾祺被补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劳动四年。这四年让汪曾祺真正深入了民间,“真正接触了中国的土地、农民,知道农村是怎么一回事”。他在1961年写出了反映张家口农场生活的儿童小说《羊舍一夕》。这篇小说深受沈从文先生好评。师母张兆和把这篇小说推荐到《人民文学》,同样也震动了编辑部,认为有屠格涅夫《白净草原》的风味。《羊舍一夕》充分证明,汪曾祺在十余年的时光里,是如何“有意识地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但是,汪曾祺认为的现实主义与民族传统,是“能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能吸收一切外来影响的民族传统”。
杨早
2023年3月
异秉
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就在保全堂药店廊檐下摆一个熏烧摊子。“熏烧”就是卤味。他下午来,上午在家里。
他家在后街濒河的高坡上,四面不挨人家。房子很旧了,碎砖墙,草顶泥地,倒是不仄逼,也很干净,夏天很凉快。一共三间。正中是堂屋,在“天地君亲师”的下面便是一具石磨。一边是厨房,也就是作坊。一边是卧房,住着王二的一家。他上无父母,嫡亲的只有四口人,一个媳妇,一儿一女。这家总是那么安静,从外面听不到什么声音。后街的人家总是吵吵闹闹的。男人揪着头发打老婆,女人拿火叉打孩子,老太婆用菜刀剁着砧板诅咒偷了她的下蛋鸡的贼。王家从来没有这些声音。他们家起得很早。天不亮王二就起来备料,然后就烧煮。他媳妇梳好头就推磨磨豆腐。——王二的熏烧摊每天要卖出很多回卤豆腐干,这豆腐干是自家做的。磨得了豆腐,就帮王二烧火。火光照得她的圆盘脸红红的。(附近的空气里弥漫着王二家飘出的五香味。)后来王二喂了一头小毛驴,她就不用围着磨盘转了,只要把小驴牵上磨,不时往磨眼里倒半碗豆子,注一点水就行了。省出时间,好做针线。一家四口,大裁小剪,很费工夫。两个孩子,大儿子长得像妈,圆乎乎的脸,两个眼睛笑起来一道缝。小女儿像父亲,瘦长脸,眼睛挺大。儿子念了几年私塾,能记账了,就不念了。他一天就是牵了小驴去饮,放它到草地上去打滚。到大了一点,就帮父亲洗料备料做生意,放驴的差事就归了妹妹了。
每天下午,在上学的孩子放学,人家淘晚饭米的时候,他就来摆他的摊子。他为什么选中保全堂来摆他的摊子呢?是因为这地点好,东街西街和附近几条巷子到这里都不远;因为保全堂的廊檐宽,柜台到铺门有相当的余地;还是因为这是一家药店,药店到晚上生意就比较清淡——很少人晚上上药铺抓药的,他摆个摊子碍不着人家的买卖,都说不清。当初还一定是请人向药店的东家说了好话,亲自登门叩谢过的。反正,有年头了。他的摊子的全副“生财”——这地方把做买卖的用具叫作“生财”,就寄放在药店店堂的后面过道里,挨墙放着,上面就是悬在二梁上的赵公元帅的神龛。这些“生财”包括两块长板,两条三条腿的高板凳(这种高凳一边两条腿,在两头;一边一条腿在当中),以及好几个一面装了玻璃的匣子。他把板凳支好,长板放平,玻璃匣子排开。这些玻璃匣子里装的是黑瓜子、白瓜子、盐炒豌豆、油炸豌豆、兰花豆、五香花生米。长板的一头摆开“熏烧”。“熏烧”除回卤豆腐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极少红烧、清炖,只是到熏烧摊子去买。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地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呈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猪头肉则分门别类地卖,拱嘴、耳朵、脸子——脸子有个专门名词,叫“大肥”。要什么,切什么。到了上灯以后,王二的生意就到了高潮。只见他拿了刀不停地切,一面还忙着收钱,包油炸的、盐炒的豌豆、瓜子,很少有歇一歇的时候。一直忙到九点多钟,在他的两盏高罩的煤油灯里煤油已经点去了一多半,装熏烧的盘子和装豌豆的匣子都已经见了底的时候,他媳妇给他送饭来了,他才用热水擦一把脸,吃晚饭。吃完晚饭,总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生意,他不忙收摊子,就端了一杯热茶,坐到保全堂店堂里的椅子上,听人聊天,一面拿眼睛瞟着他的摊子,见有人走来,就起身切一盘,包两包。他的主顾都是熟人,谁什么时候来,买什么,他心里都是有数的。
这一条街上的店铺、摆摊的,生意如何,彼此都很清楚。近几年,景况都不大好。有几家好一些,但也只是能维持。有的是逐渐地败落下来了。先是货架上的东西越来越空,只出不进,最后就出让“生财”,关门歇业。只有王二的生意却越做越兴旺。他的摊子越摆越大,装炒货的匣子、装熏烧的洋瓷盘子,越来越多。每天晚上到了买卖高潮的时候,摊子外面有时会拥着好些人。好天气还好,遇上下雨下雪(下雨下雪买他的东西的比平常更多),叫主顾在当街打伞站着,实在很不过意。于是经人说合,出了租钱,他就把他的摊子搬到隔壁源昌烟店的店堂里去了。
源昌烟店是个老字号,专卖旱烟,做门市,也做批发。一边是柜台,一边是刨烟的作坊。这一带抽的旱烟是刨成丝的。刨烟师傅把烟叶子一张一张立着叠在一个特制的木床子上,用皮绳木楔卡紧,两腿夹着床子,用一个刨刃有半尺宽的大刨子刨。烟是黄的。他们都穿了白布套裤。这套裤也都变黄了。下了工,脱了套裤,他们身上也到处是黄的。头发也是黄的。——手艺人都带着他那个行业特有的颜色。染坊师傅的指甲缝里都是蓝的,碾米师傅的眉毛总是白蒙蒙的。原来,源昌号每天有四个师傅、四副床子刨烟。每天总有一些大人孩子站在旁边看。后来减成三个,两个,一个。最后连这一个也辞了。这家的东家就靠卖一点纸烟、火柴、零包的茶叶维持生活,也还卖一点趸来的旱烟、皮丝烟。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挺敞亮的店堂变得黑暗了,牌匾上的金字也都无精打采了。那座柜台显得特别的大。大,而空。
王二来了,就占了半边店堂,就是原来刨烟师傅刨烟的地方。他的摊子原来在保全堂廊檐是东西向横放着的,迁到源昌,就改成南北向,直放了。所以,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摊子,而是半个店铺了。他在原有的板子之外增加了一块,摆成一个曲尺形,俨然就是一个柜台。他所卖的东西的品种也增加了。即以熏烧而论,除了原有的回卤豆腐干、牛肉、猪头肉、蒲包肉之外,春天,卖一种叫作“鵽”的野味——这是一种候鸟,长嘴长脚,因为是桃花开时来的,不知是哪位文人雅士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桃花鵽”;卖鹌鹑;入冬以后,他就挂起一个长条形的玻璃镜框,里面用大红蜡笺写了泥金字:“即日起新添美味羊羔五香兔肉”。这地方人没有自己家里做羊肉的,都是从熏烧摊上买。只有一种吃法:带皮白煮,冻实,切片,加青蒜、辣椒糊,还有一把必不可少的胡萝卜丝(据说这是最能解膻气的)。酱油、醋,买回来自己加。兔肉,也像牛肉似的加盐和五香煮,染了通红的红曲。
这条街上过年时的春联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特制嵌了字号的。比如保全堂,就是由该店拔贡出身的东家拟制的“保我黎民,全登寿域”;有些大字号,比如布店,口气很大,贴的是“生涯宗子贡,贸易效陶朱”,最常见的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小本经营的买卖的则很谦虚地写出:“生意三春草,财源雨后花。”这末一副春联,用于王二的超摊子准铺子,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虽然王二并没有想到贴这样一副春联——他也没处贴呀,这铺面的字号还是“源昌”。他的生意真是三春草、雨后花一样的起来了。“起来”最显眼的标志是他把长罩煤油灯撤掉,挂起一盏呼呼作响的汽灯。须知,汽灯这东西只有钱庄、绸缎庄才用,而王二,居然在一个熏烧摊子的上面,挂起来了。这白亮白亮的汽灯,越显得源昌柜台里的一盏煤油灯十分的暗淡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