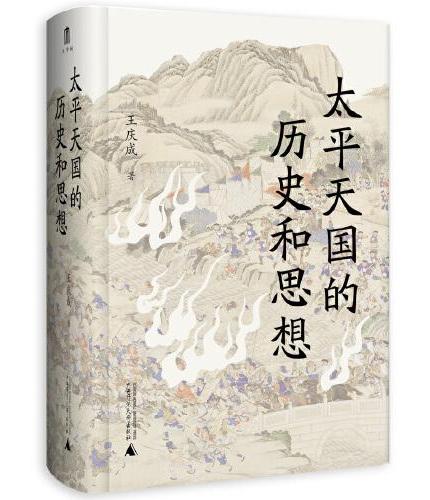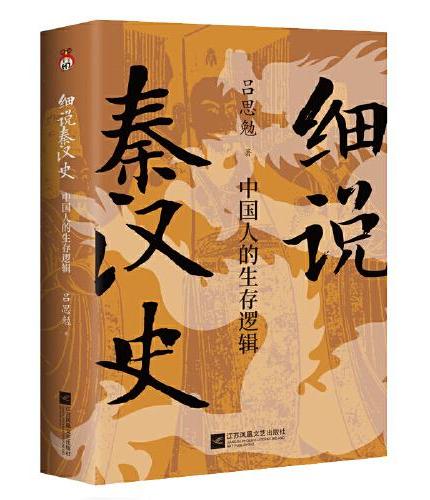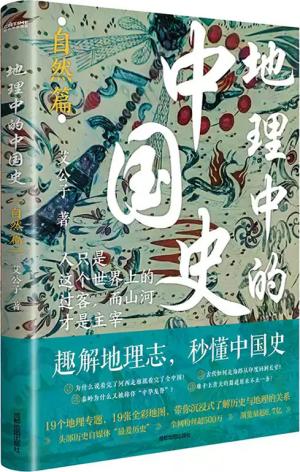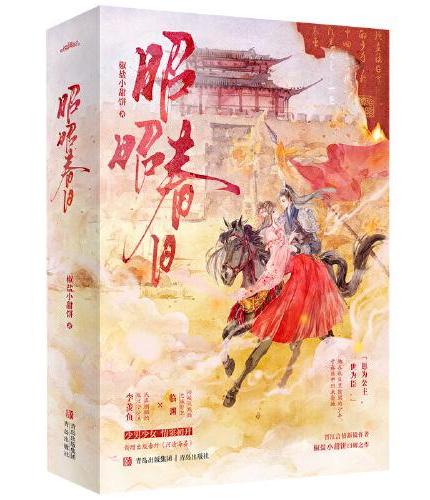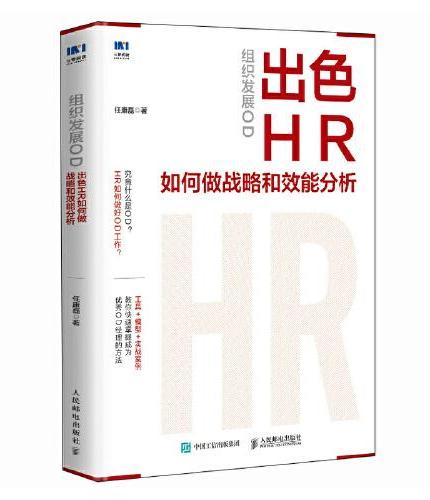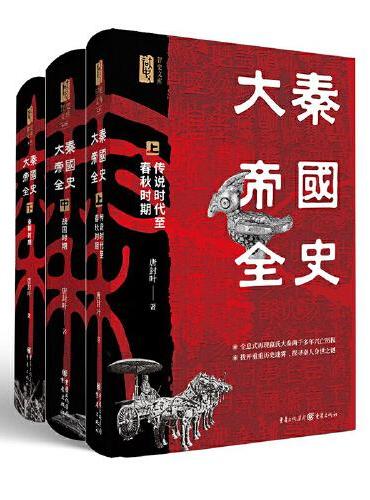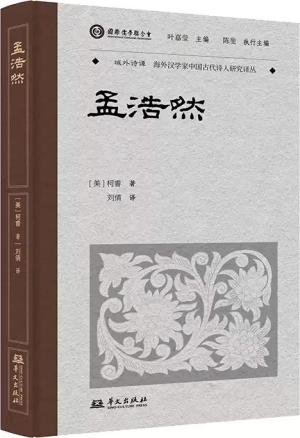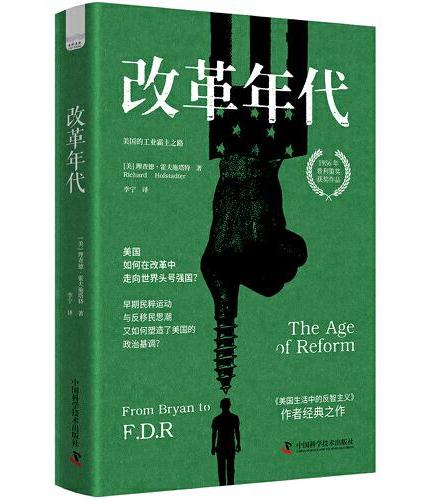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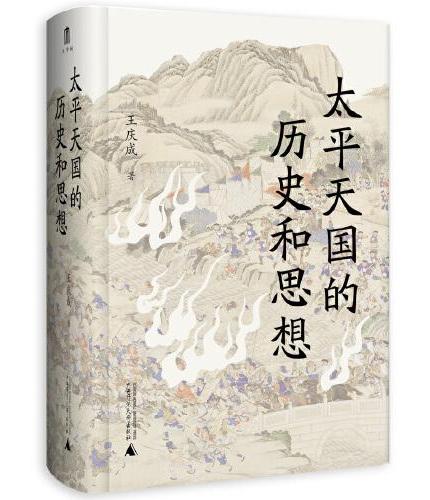
《
大学问·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部研究太平天国的经典著作)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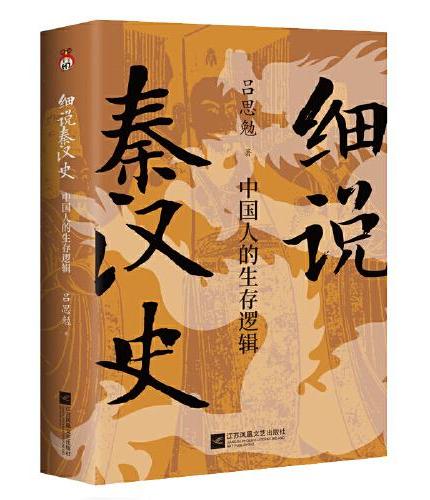
《
细说秦汉史:中国人的生存逻辑
》
售價:NT$
7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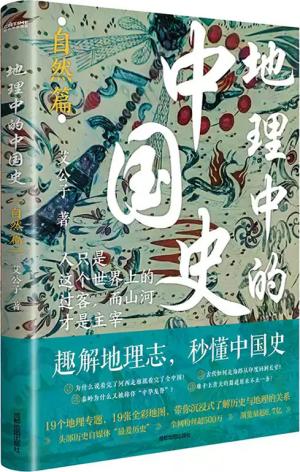
《
地理中的中国史(自然篇)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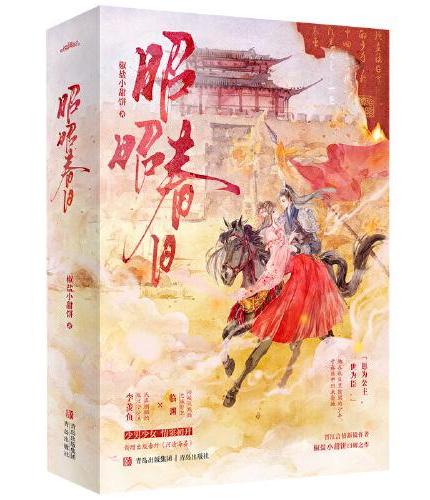
《
昭昭春日
》
售價:NT$
3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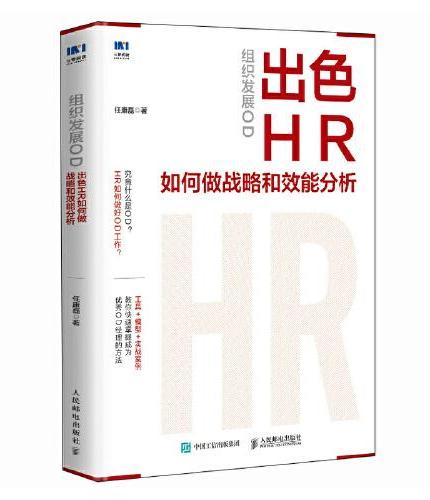
《
组织发展OD:出色HR如何做战略和效能分析
》
售價:NT$
3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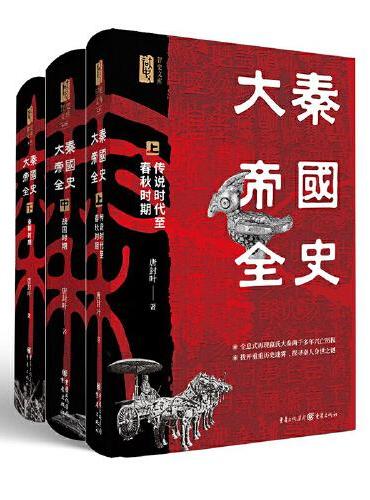
《
大秦帝国全史
》
售價:NT$
10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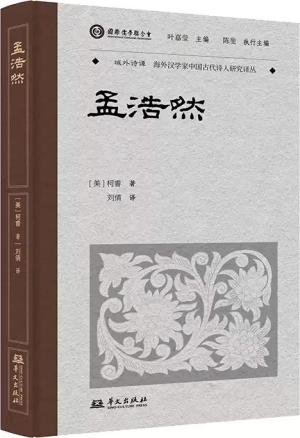
《
孟浩然(英语世界中的*一本孟浩然传记)
》
售價:NT$
3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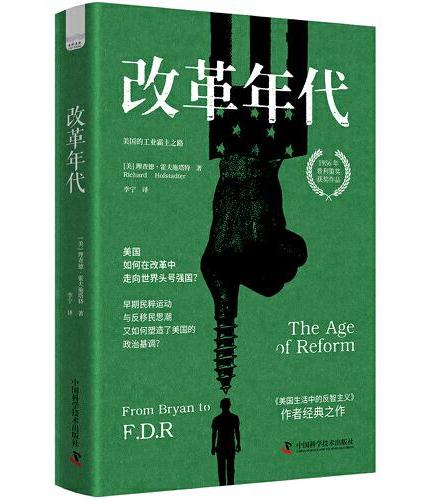
《
改革年代:美国的工业霸主之路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1、我必须离开,必须感觉到自己,我和自己必须到自由里去。
2、《再团圆》导演&编剧、《野马分鬃》编剧,鹿特丹、戛纳、平遥等国际影展荣誉获得者、90后实力派影人高临阳shou部小说集。
3、勾动记忆的高手,精确捕捉年轻一代的迷惘与珍视。有故事、有细节,有理解也有调皮。
4、用一本书的时间,等等心里那个来不及长大就被推入成人世界、落在身后的小孩子。
【真正属于年轻人的写作:反叛,一点中二,很多柔软】,主人公像每一个按部就班长大的我们,被推入成人世界,而成年人的所谓规则,却没有一样处理好——换言之,没有一样想去迎合。
【被无形框架笼罩的我们啊,这是我们共同的经历和故事】,有隐痛,有野心,有幻想,“我们都曾把沉重的吞下去,长成身体的一部分;直到遇到彼此,分担共有的伤口。”
5、7个故事,给不愿对自己重复失望的我们,给奋力逃离毫无想象力的生活、不甘庸常的心。
6、管虎、韩东、何平、弋舟推荐。
天生会讲故事的人,用天真的眼睛观察、感受,触碰读者心底那些来不及收拾的情感和遗憾,也勾动了我的私人记忆。
——导演 管虎
朴素而力图精确,不玩“花活”,更无“知识分子”的陈规陋习,
|
| 內容簡介: |
不自觉地,我喜欢跟在一些人身后:
偏僻小镇上如惊蛰降临的女吞剑者,叫松鼠蹿上肩头、一起跃入云层的婴儿囡囡,以尺规作图仗剑天涯的天才同桌,耳边回响心碎大象叫声的女孩,为了报答一个故事决心交出一切的男人,大雪冰封下湖底用力呼吸的我自己,上流第一流也很孤独的神。
活在框架外的他们,引诱着我。引诱我看清自己,继而试图看清这个世界。
我们都曾把沉重的吞下去,长成身体的一部分;直到遇到彼此,分担共有的伤口。
走吧。我或许沉默,或许迷失,或许弄丢钥匙,至少我睁着眼睛,我会看到自己平稳停落。
|
| 關於作者: |
高临阳
1991年生于山西太原,电影导演,编剧,作家。
长片首作《再团圆》获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老虎奖评委会特别奖及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
编剧作品《野马分鬃》入选戛纳国际电影节官方片单。
《把空气冲破一下》是他的shou部中短篇小说集。
|
| 目錄:
|
吞剑者
直视
把空气冲破一下
友人高元奇
爱情大象
生铁落饮
浪味仙
|
| 內容試閱:
|
吞剑者
镇上来了一个女吞剑者。
我从邮局出来,手拎一瓶酱油和一封信,看见一群人围在镇中心小广场上。
根据围的圈数,我判断出车祸了。一般来说,围一圈,是崔疯子在犯病;围两圈,是河南家耍猴的来了,有时猴也耍人;围三圈,是庄家大公子开豪车把人撞飞,尸体横地上。那次我赶到时,尸体已经被苫布盖上。高远命好,当时在附近目睹了全程。次日,他成为班上的英雄,因为他是我们初二一班第一个见过死人的活人。
我把信投进邮筒,快步向人群跑去。
我甚至忘了去吹一吹邮票。镇上邮局的胶水比奶奶熬的稀饭还稀,掺过水,出了名的偷工减料。我总担心邮票会从信上脱落。每次寄信前,我都鼓足腮帮子,像台鼓风机一样吹干水分,确保邮票焊在信封上。一周后,信将会抵达东部沿海一座城市,邮差会骑着自行车放进一所市重点中学的传达室,之后一个女孩会接走它。算上这封,我跟女孩靠通信神交有一年之久。生活里我话不多,常与人神交。在所有的神交对象中,我最珍惜她。我们都订一本叫《科学世界》的杂志,它是教育bu推荐的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十大杂志之一。但我认为,这本杂志之所以能在坊间经久不衰,很大原因在于页脚处开辟了一个交友专栏,免费发布中学生一句话交友感言,同时附发布者的通信地址。我从小到大,没出过山西,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省城太原。我的梦想是认识一位生活在海边的女孩儿,简称海的女儿。我拿出一张中国地图,在床上摊开过去一年订阅的所有《科学世界》,把交友专栏中所有异性所在的城市在地图上标注下来。我给所有生活在海边的女孩都去了信,内容只有一句话,能为我寄些海风吗?只有一个女孩回了信,但信封里是空的。从此,我们成为固定的笔友。我在班上订阅的《科学世界》很快换成了《科幻世界》,母亲问我科幻是什么,我说科幻是未来的科学。她很为我的超前而自得。我不敢让她知道,那本杂志主要刊登小说。
在信里,我无可救药地把自己塑造成本镇的流氓头子、气功爱好者兼流浪诗人。我还跟她吹嘘曾在镇上的木塔顶层放孔明灯,为她许愿。那座木塔始建于辽代,号称建筑史奇迹,没用一钉一铆,完全纯木搭建。它作为景点,是镇上支柱产业。母亲说它和比萨斜塔、埃菲尔铁塔并称世界三大奇观。母亲说这话的表情好像她去过托斯卡纳和巴黎。木塔早先允许登顶,后来政府担心游客过多,有损塔的健康,遂禁止。崔疯子平时不疯,夜里负责守塔,在塔底的院子边上有个砖房。我小学和高远上去过一次,当然没替她许过什么愿。我甚至连死人也没见过。除非在信里,而且是我们班第一个见的。
我已经忘记自己如何一步步对信里的自己深信不疑。关键是我从未穿帮。因为每次给她写信,我都会打一遍草稿,再重新誊写到新信纸上。每封信我都留有一份底稿,写下一封前随时重温。从回信中,我感到她同样珍惜我,我甚至能猜到,她会向闺蜜隐秘地炫耀有我这样一个小镇异性的存在。我的存在,毫不夸张地说,是她作为优等生的一种筹码。她是一个艰涩的术语,我是她的通俗脚注,通过我这个隐形而奇怪的异性,她在班上的地位能更加牢不可破。同样,对我来说,她也是。但今天,我居然忘了吹干邮票。我边想边飞速向人群跑去,我必须见一次死人,为了她。
我仗着年龄小,无赖般往人群里挤。透过人缝,我看到一个女人仰着头,口中含剑,剑把留在外面。很快,她举起双手,将一柄剑从喉咙里缓缓取出来,剑身有半米长。看上去她也就二十多岁,和我哥年龄相仿,头后扎一束马尾,表情漫不经心,似笑非笑。她一手持剑,一手揽向胸口,向观众鞠躬示意,马尾辫荡了起来。四面八方的掌声从观众手里冲出来。女吞剑者没有因掌声改变表情。她身边站着四个侏儒,他们张开手,脸朝外,把她围住,大概是担心有疯狂观众靠近她造出危险。侏儒们面无表情,既像炸弹又像拆弹专家。女人把直剑递给离她最近的侏儒,从他手里又接过一柄细弯刀。刀有一种抄袭来的蒙古风格,弧度造作,为弯而弯。她拿在手里,注视着刀,却用一种注视爱人般的目光。所有人都大致猜出她接下来的举动。身边一个胆小的姑娘捂住眼,从指缝瞄。高远不用看就知道,眼睛一定睁得比硬币还圆。女吞剑者偏过头,腰部随之向右侧微倾,让身体也造出一个弧度。接着,她缓缓将弯刀探进口中,直到身体吞没整把刀。刀如一滴水,坠入一片海绵,没发出一滴声音。
我感到,全场观众都在努力镇压即将造反的胃。我甚至听到,高远喉咙发出怪声,下肚的炸酱面炸了锅。
女人还没表演完。她含着刀,以右脚为圆心旋转。裙子跟着马尾辫荡起来。几个侏儒的手拉得很紧,表情更凶了。她转得我有些晕。我想起,女孩上封信提到她买了一条新裙子,在海边跟家人玩,她穿着新裙子也喜欢这么转。直到女吞剑者把刀取出来时,我还一直有些恍惚,仿佛刚结束一场梦。围观的人被震住,人已不止三圈。我感到小广场上的气温,比平时高出两三度。几秒后,比上轮多出三四倍的掌声从观众手里涌出。人潮把我推向侏儒。我稳住自己,观察女吞剑者的脸。她的五官让我想到一种节气——惊蛰。暗地里我一直用节气形容女人的脸。冷酷的脸,是大雪。甜蜜的脸,是芒种。惊蛰这个节气,我一直打算留给笔友,虽然我没见过她。但眼前这个吞剑者,把这个节气夺走了。她有惊蛰的眼,惊蛰的鼻,惊蛰的嘴,还有惊蛰的辫子。从她身体里来了去去了来的刀剑,像夜空中的一道闪电。我不觉得刀剑在她身体来去有什么突兀,就像我不会奇怪闪电劈开夜空,但这并不妨碍闪电对我造成的杀伤力。小镇偏僻,我当时还不会熟练使用艺术这个词,否则我一定坚信吞剑是一种艺术。
女吞剑者再次鞠躬,几个侏儒拿着帽子向观众讨钱。人们没像往常似的摸脑袋假装路过,而是发自内心地摸腰包,连崔疯子都放了五块。我被大家的热情弄得不好意思,因为我一分钱也没有。我后悔刚才买了带图案的高级信封,不然还能剩一块。高远把口袋翻遍,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一块。我凑上去,拉住高远,问他还有钱吗。他摇摇头。这时,端帽子的侏儒走到我们跟前,把帽子递过来。侏儒很低,物理意义上帽子离我有段距离,心理意义上简直近在鼻尖。
高远豪爽地把一块钱丢进帽子。他指着我俩对侏儒说,一人五毛,我请了。说完,他故作潇洒地拍拍我的肩,意思是别客气。
侏儒瞪我一眼,转身朝女吞剑者走去。我心虚地低下头,一肚子火。我认为高远不应该在这个严肃而神圣的场合,开这样的低级玩笑。我想揪住高远,但我快走两步到端帽子的侏儒旁。我说,你们住哪儿,我没带钱,下午给你们送去。侏儒不言语,指了指不远处一家国营招待所。
我转身朝家跑去,跑两步猛地停下,折了回去。女吞剑者已退出人群,圈子又围起来,一个浑身腱子肉的大力士准备表演上刀山。我走到女人身边,问,我能看一眼那把剑吗?女人看着我,不说话,仿佛在说总不能白看吧。我脸唰的红了,她似乎看出我刚才就没掏钱。我只是想确认那剑是真的。她还是不说话,我沮丧地转身要走。女人突然问我,你们镇上的木塔怎么走?我说,走到河边,沿着河岸走到一个小水泥厂,拐弯有个院子,有个疯子守着。女人问,晚上能上去吗?我说,塔封了。女人疑惑地看着我,说,他疯了?我说,对,很早就封了。女人问,谁疯了?我说,木塔啊,就你说的木塔啊。女人反应过来,我说的是封不是疯,笑了起来,辫子一晃一晃的,我自己也咧嘴笑。我觉得自己必须配合她,好像我的笑是她的笑的一部分,只有我笑,她的笑才足够完整。她笑完,打开旁边的一个袋子,把剑递给我。我伸手接剑,右手伸到一半,停在空中,左手追了上去,两只手把剑捧在胸口。这是一把货真价实的钢剑。我捧在手里,像一个处男面对一具成熟而鲜艳的女性胴体,满腔征服欲,但手足无措。我手上这柄剑,曾进入她体内探险。剑有些烫手,不知是被阳光晒得,还是因为曾窃走她体内的温度。它陌生,又很实在。我放心地把剑还给女人,往家走去。
我原本只是出来买一瓶酱油,结果时间耽搁得有些久。等我到家,午饭已经上桌。我家今天来了两位远房亲戚,祝贺我哥考上省城太原一所重点大学,同时祝贺去年我新生的妹妹满一周岁。父亲常年在太原做生意。家里还有个奶奶。我们家有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妻子。我进门后,母亲瞪我一眼,让我赶紧上桌,客人都在等着。奶奶给每个人面前的空杯满上水,这是我们家惯例,饭前一杯水。水不是一般的水,是奶奶发过功的水。奶奶退休后,开始练一门叫作香功的气功。水缸上悬着此功创始人的头像,一个脑袋后面有好几重影子的男人。每天早晨,她把水缸接满,就开始对水发功。她通常微扎马步,深扎她身体架不住,然后运气,双掌对着水缸,口中念念有词,传输着从宇宙间吸纳来的某种神秘能量。她总拿发过功的水问我们,甜不甜。所有人都说,甜,和从自来水里直接接出来的水味道不同,我也觉得确实如此。但有一次,我直接从水龙头接了一杯水,一时忘喝扔在桌上,过后再喝味道同发过功的水一样。我觉得,味道不同,估计是因为温度。但我不能戳穿奶奶,我也找不到什么其他事让她填补白天的空闲。再说,我答应过女孩,如果她有机会来我们镇,请她喝奶奶发过功的香水。由于没酱油,母亲为提味没少撒盐,她一直问亲戚菜咸不咸。奶奶最近则怀疑她功力变弱,一直问亲戚水甜不甜。亲戚一会甜一会咸,险些招架不住。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弄点钱给女吞剑者送去。去镇上电影院看电影都想方设法逃票的我,不知为什么把钱交给那个女人的冲动如此强烈。我甚至突发奇想,面对一件艺术品,金钱就是尊重的表达。从母亲那不太可能弄到钱。几个月前他们房间内的柜子钥匙丢了。柜子里放着我们家很重要的东西。母亲怕钥匙丢就把它放在厨房天花板上,结果还是丢了。他们起初怀疑我,但没证据,后来又怀疑家里有老鼠,钥匙被老鼠不知叼到什么角落。柜子是姥爷传下来的,是个文物,母亲不舍得用锤子砸,她天天在家里各种地方找钥匙,她怀疑钥匙可能出现在家里任何角落。
饭桌上,远房亲戚掏出一个红包,往哥哥手里塞,哥哥大义凛然拒绝,跟拿炸弹一样,红包险些掉碗里。母亲也义不容辞表示绝不能收。远房亲戚发动再一次进攻,母亲再次拦截,表示亲戚已经带了礼物。亲戚来前,母亲已经和哥哥彩排过这幕,而且母亲安排好,一会让我送亲戚坐公交,她判断这时亲戚会顺势把钱再塞给我,我年龄小,可以装不懂事把钱收下,然后交给她。母亲甚至推算出亲戚红包里钱的张数。她有一个红旗本,专门用来记录亲友间的账目往来,根据上次她给远房亲戚的回礼数,她判断这次哥哥读大学、妹妹满月远房亲戚给五张算比较得体。
果然,远房亲戚在上公车最后一刻,把红包塞进我口袋。我装出措手不及无招架之力的表情,目送他们两口子离开。等车从视线中快消失,我飞快地打开红包,数了起来。我数出八张。我想也没想,抽出三张,脱下鞋,塞进鞋垫下方。我骗自己说,红包里只有五张,红包里只有五张,然后飞快向家跑去。踩在钱上,像踩在棉花上。
我将红包递给母亲,母亲露出猎人那种不易察觉的微笑。她又看我一眼。我把空荡荡的裤兜翻出来,同时翻一个白眼送她。母亲对哥哥喊了一句,钱我给你留着啊,然后打开红包瞟了一眼。母亲说,五张,我说得没错吧。她走进厨房,又补一句,我什么时候错过。
我对她很失望。对无知的妹妹我也很失望,因为她生来有这样一个母亲,我甚至对考出小镇的哥哥也失望。他居然只考到省会太原,她从母亲身边考到父亲身边。他简直永远不会长大了。哥哥从小成绩好,他不是别人家的孩子,胜似别人家的孩子。毫无意外,他考上一个太原的重本。镇上的人都觉得去太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太原,从名字就能看出是一个毫无想象力的城市。太圆,圆是最没有想象力的图形,所有的圆都长一个样子。他随便去哪儿,只要出山西都会令我对他刮目相看,他为什么不去一个有海,有树,哪怕沙漠的地方。我怀疑他这辈子去过的地方也不会比女吞剑者现在走过的地方多。我准备把脚下的钱,献给勇敢的女吞剑者。我甚至突然有了一个更疯狂的念头:我要跟她学吞剑,去流浪表演。我要干一件我在信里从未提过的事。这个疯狂的念头折磨得我无法在家再待一秒。我害怕女吞剑者提前离开小镇。我幻想学成之日,我去那个沿海城市,表演给笔友看,让她知道,我的疯狂所言非虚。在信里我虚构的疯狂,都不及表演吞剑疯狂。这一个真疯狂,可以抵消过去所有假疯狂。此时,哥哥在床上预习大学英语教材,他看着看着昏睡过去。我骗母亲说要去高远家过夜。父母不在家他一个人害怕。母亲说,背上书包,把暑假作业写了。
我确实先去了高远家。交代他如果母亲问起来,帮我打好掩护。他问我,你要干什么。我说,去学吞剑。他说,我不信。我就知道他不信。他一直觉得我虚张声势,他最初甚至不信去我有一个海边的笔友。他觉得那些来信都是我自己写的,我编一个沿海地点,盖一个假邮戳。直到女孩有一次把她家里电话号码给我。在一个周末,我当着他的面拨通那个电话,听到女孩神迹般的声音,他彻底心服口服。那天我们聊了什么早忘记了,我只记得高远在我身边听得一愣一愣。他这张嘴,等开学后一定会把我学吞剑的消息散播出去,这样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就像拨通那个电话后,他让全校都知道我有一个听上去很美的笔友,就差逼我把信出版了。我其实根本不在乎他信不信,我只是借他的嘴。但他又加了一句,我不信吞剑,那玩意绝对是假的。我说,那你还给钱?高远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起来,虚无地说,人生不就是逢场作戏吗?我说,是真的,我摸过那剑。高远说,你看过电影吗?电影里剑插人身体没?我说插了。高远说,流血没?我说流了。高远说,对呀,但实际情况是没插,血也是假的,这不因为是电影吗,那剑是道具。我说,剑是真的,沉。高远说,你听说过司马南吗?我摇摇头,说,我听过司马光。高远说,他比司马光牛逼,司马光就知道砸缸,司马南什么都知道,不信你问他去。我心里说,去你的,等我以后学会吞剑,当面吞给你看。九月开学后我已经指不定在哪里演出了,可你们还得穿着校服,在操场上听国旗下的演讲。
从高远家出来,我在招待所附近一家面馆找到女吞剑者。她换了一身裙子,比演出那身素朴不少。四个侏儒在她旁边坐一桌,她一个人坐一桌。侏儒桌上有几瓶啤酒,他们都直接对嘴喝,由于瓶子很大,他们不得不两手捧着。店门外,我从鞋底把那三张百元钞票掏出来,往平捋了捋,攥在手里,向她走去。
进到店里,我有些紧张,不知道该干什么,顺势点了一碗面。我其实不饿,点了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我坐在女人对面。其中一个侏儒警惕似的看了我一眼,另一个侏儒跟他耳语一句,大概是说我刚才出现过,那个瞪我的侏儒眉头才熨平。
我小声说,那是把好剑。这像一句暗号,表明我们共同经历过什么阴谋似的。
她看了我一眼,低头继续吃面。
我说,我只听说过吞剑,我以为是假的。
她点点头,仍没打算看我。
我说,我想学。
女人抬头,仔细盯着我瞧。我在她眼睛中看见一个紧张的自己。
她说,你有什么特长?
我思来想去,想把我在信里向女孩吹嘘的特异功能一一复述。但我退缩了,在她面前我必须坦诚,我不能隐瞒自己,否则像是一种亵渎。至于亵渎什么,我也暂时说不上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