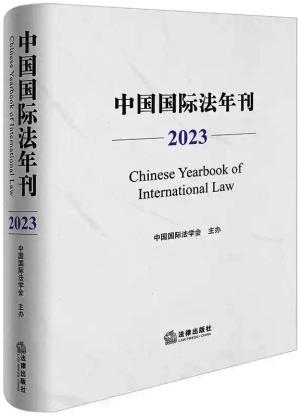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大学问·明清经济史讲稿
》
售價:NT$
3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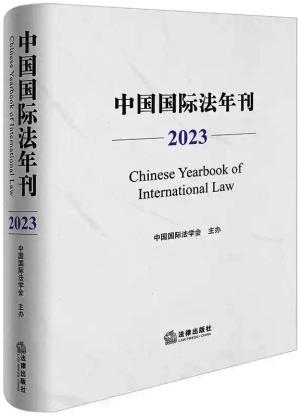
《
中国国际法年刊(2023)
》
售價:NT$
539.0

《
早点知道会幸福的那些事
》
售價:NT$
295.0

《
迈尔斯普通心理学
》
售價:NT$
760.0

《
古典的回響:溪客舊廬藏明清文人繪畫
》
售價:NT$
1990.0

《
掌故家的心事
》
售價:NT$
390.0

《
孤独传:一种现代情感的历史
》
售價:NT$
390.0

《
家、金钱和孩子
》
售價:NT$
295.0
|
| 編輯推薦: |
波兰“女辛德勒”艾琳娜·森德勒的真实事迹改编,她曾冒死从纳粹手中救下2500余名犹太儿童。
另一角度的“辛德勒名单”,那些纳粹手下幸存下来的受害者会经历怎样的一生?那些为了逃出去只能改换姓名身份信仰、失去所有亲人的孩子内心要承受多大的折磨?
一个关于爱与家庭、战争与伤痛的故事,对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来说,他们的过去将不仅仅是一种回忆,也是由血与肉、石头与水泥、痛苦与折磨重新筑就的现实。
一段计划外的旅程,一个隐瞒了80年的秘密,一对祖孙的互相救赎
一个因父母离婚而走向叛逆的青少年,一个背负沉重回忆的86岁战争幸存者,在这场意外旅程中,他们找回了直面伤痛的勇气。
随着尘封80年的秘密被揭开,两条平行的时间线相交,过去与现在交织,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被缓缓讲述。
战争中的幸存者用眼睛和记忆书写过去,他们永不遗忘的痛苦是不应被掩盖的历史。
一曲写满生与死、血与肉、战争与伤痛的悲歌
“有时候一个人死了,他自己也意识不到。”
“我们活下来的人要带着残缺的身躯生活。我们是不被人看见的截肢者。”
“人的离去,一旦被察觉到了,原来所占据的位置就会空出来,永远空着,没有什
|
| 內容簡介: |
15岁的马库斯因在学校的墙上写下针对犹太同学的侮辱言辞而被停学五天,甚至有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惩罚。
马库斯的妈妈约翰娜向曾任校长的老父亲鲁道夫·斯坦纳求助,请他帮忙跟现任校长沟通。86岁的鲁道夫对外孙的行为深感震惊,决定带他去一次波兰。在这次波兰之行中,鲁道夫第一次讲述了连自己女儿都不知道的秘密:他是艾琳娜·森德勒从纳粹手中救出的数千名犹太儿童之一,他的真实名字甚至不是鲁道夫……
|
| 關於作者: |
|
尼古拉·布鲁尼亚尔蒂,意大利作家、词曲作者、广告人。他是意大利诗人、作家和剧作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的后裔,曾在广告行业工作多年,自2009年开始担任流行电视节目编剧,已出版十多部儿童文学作品。
|
| 內容試閱:
|
《一个不属于我的名字》文摘
一
在母亲撒开他手的那一刻,雅努什明白那会是最后一次。他感到很揪心,小心脏有几秒钟停止了跳动。他与母亲的距离慢慢变得越来越远,但他希望自己的双臂可以无限延长,这样他仍然可以拥抱母亲。
他转头继续望着母亲,说不出一个字来,但护士推着他朝反方向走,希望没人看到他们。可他很固执,停下来注视母亲,他想记住自己正在经历的那一刻:母亲目送他离开,表情因为生不如死的离别十分痛苦。他想把那一刻变成一张照片,毫厘不差地保存下来。
每当他闭上眼睛,那幅画面就会浮现在眼前。自那以后,在整个余生中,他永远都能看见那个场景。
二
在学校栅栏门旁边的外墙中央,出现了一个清晰的、黑色的卐字符,画得有点歪。它过分向右倾斜,仿佛随时要转过去一样。卐 字 符 旁 边 有 一 句 话:HILDE BIERMANN JüDISCHE SCHLAMPE,意思是“希尔德·比尔曼犹太婊子”。这句话也是黑色的,笔迹连贯而潦草,JüDISCHE(犹太)一词的“I”显然是后来添的,起头的字母隔得很开,为了把整句话在墙上写全,收尾的字母就变得很挤。
拍视频的人手有些颤抖,那句话写完后,还对着它拍了几秒,背景里可以听到短促而得意的笑声,同时夹杂着汽车的噪声和远处传来的狗叫声。
随后,手机镜头忽然转向左边,在闪光灯的照耀下,黑暗中出现了三个孩子,他们的脸庞完全被面巾遮住,头上戴了卫衣帽子。其中一个孩子手里自豪地拿着一罐喷漆,刚用它写下了墙上的话,现在正得意地展示“作案工具”。
三个孩子看了拍摄他们的人一眼。然后,随着导演一声令下,他们变得严肃,齐声高呼:“希尔德·比尔曼犹太婊子。”他们重复喊了三遍,以明确表达他们如何看待可怜的希尔德。
接着,他们抬起一只手臂,敬了一个纳粹礼,高喊了一声“胜利”,声音有点慌张,这意味着有人过来了。的确,拍摄镜头突然转向了地面,三人发出一阵哄笑,就逃走了。视频就这样结束了。
乌尔里克·库尔兹太太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从来没查过儿子的手机,她承诺过,不会像儿子沃尔夫冈那些朋友的妈妈那样,她跟她们讨论过数十次隐私对孩子的成长有多么重要。要想让孩子做到自知自主和真正独立,远离成年人不断的监视和严格的管控,必须让他们拥有一个自己负责和管理的空间。
只有这样孩子才能真正长大,心理医生威默也这样告诉过她。六岁的沃尔夫冈突然开始尿床的时候,她咨询过威默医生,医生说,您和您丈夫的婚姻生活出现了一点小危机,这有些打乱了平静的家庭生活。而沃尔夫冈又是个敏感的孩子,很快就受到了影响。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一切都回归正常,他们家四墙之内一片祥和。
然而,那天下午,乌尔里克打消了自己所有的美好念头,背叛了她身为母亲十分笃信的所有教育原则。一时间,她要做一个“现代和解放的”母亲的决心都去见鬼了。
她是迫于无奈。前一天晚上,沃尔夫冈离开饭桌时显得有些不安,这样的举动在那个星期已经出现很多次了,当时她就跟丈夫悄悄说了这件事。她儿子从来没有那样沉默过,从前总是跟他们分享自己的不安和痛苦,甚至爱情方面的苦恼。他们就是这样把他养大的,在家里给予他绝对的信任,让他明白在家里他可以得到他想要的支持和安慰,如果他需要的话,还有理解。然而,最近这些天,他待在房间里的时间比平常多了,总是一头扎进手机里,以前他从不这样。
很明显,沃尔夫冈忧心忡忡。有什么事情在折磨他,让他睡不了安稳觉。起码有两次,乌尔里克深夜来到他房间,听见他在梦里喊叫,嘟囔着些没有意义的话,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也很难猜出来。但是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会一探究竟。这会不会跟某个小混混有关系?
她家孩子被学校那些浑小子盯上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些家伙喜欢让他陷入自卑,因为他身体不健壮(的确有些超重),还因为他发音有轻微的缺陷,发不好“s”音,虽然语言治疗师说这是“s音发音障碍”,但其他人还是叫他“咬舌儿”。
没错,乌尔里克想,肯定是这一类问题使她的沃尔夫冈不得安生。
她也试过直接跟儿子谈,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他心绪不宁,比如班上某个“有点活泼”的同学。乌尔里克有些冒昧,但没有说出“流氓”这个词,她担心情况要真是那样,会加深对孩子的伤害。然而,沃尔夫冈极力否认了母亲的猜测,他甚至说自己没有任何不顺心的事儿,她是瞎操心,然后又把自己关进了房间,不让母亲再问其他问题。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她决定查看儿子的手机。那个星期六早上,乌尔里克利用了沃尔夫冈洗澡的空当。她十分内疚,但那是帮助儿子的唯一办法。
她的心扑腾直跳,好像自己正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她静悄悄地走到走廊尽头,溜进沃尔夫冈的房间,在书桌上的几何课本和数学课本中间找到了手机。
为了不被逮个正着,她竖起耳朵听着浴室传来的声音。她在屏幕上画出图形,解锁了手机。前一天晚上,她仔细观察儿子手上的动作,记住了解锁的手势。然后,她开始逐个浏览手机里的页面,直到在 WhatsApp 上发现了一个叫“密室”的聊天群,名字跟哈利·波特系列的一本书相同,群里有 35 条未读信息,是最近几分钟才发出来的,而此时沃尔夫冈正在洗澡。
乌尔里克手指颤抖着点进了聊天群,她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里面有很多视频,多数是模仿热映的电影或电视剧的场景,大部分很枯燥,但也有一些视频很不寻常,尤其是色情视频,还是一些女孩上传的,这令她匪夷所思。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录下了卐字符和严重侮辱希尔德·比尔曼的那句话的视频。如果她没记错,希尔德·比尔曼是沃尔夫冈班上一个女同学的名字,那个女孩学习用功,很有教养,是犹太人。
乌尔里克跟希尔德的母亲交谈过几次,比如在家长会上,还有一次是在学年末的晚上聚餐,当时她们挨着坐的。她初次见到比尔曼太太时,就觉得比尔曼太太是个文雅的人,举止得体,能言会道。她记得比尔曼太太是心理学家,但她没见过比尔曼太太的丈夫。比尔曼先生是维也纳大学的德语文学教授,几个星期以前,乌尔里克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过他的照片,那篇文章讲的是比尔曼先生作序的一部新小说。
看了那个视频后,她想到了那个美好的家庭,现在她心里很痛苦。
婊子。谁也不该被人这样叫,何况一个十五岁的无辜女孩。但是她的犹太身份,可能令她受到的侮辱变得无以复加。还有卐字符、抬起的手臂、纳粹礼,一切都令乌尔里克作呕。
在她的成长和教育环境中,人们对纳粹主义恨之入骨,讳莫如深,在奥地利禁止销售任何涉及那个历史时期的物品,所有人都想忘记那段历史。“二战”后的奥地利儿童都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心里承受着一种已经厌倦了的愧疚感。
那些孩子现在又把一切摆在了面上,手段无耻之极,他们有什么权利那样做?
乌尔里克感到热血沸腾,怒不可遏,心里燃起一股滔天的怒火。视频不是她儿子拍摄的,但情况同样严重,她既然看到了视频,就不能假装无事发生。
从群里的聊天记录看,拍视频的那些孩子应该是沃尔夫冈学校的,甚至可能还是同班同学。没等儿子从浴室出来,问问是怎么回事,乌尔里克就从裤子的口袋里拿出手机,找到了班长的电话。所有人都应该知道在班上的孩子间传播的那个视频。当电话拨出去的时候,她想沃尔夫冈会原谅她的。也可能不会。但是现在这不重要。
现在重要的是希尔德·比尔曼,必须马上让人擦掉侮辱女孩的那句话。
三
狗,总是狗。鲁道夫·斯坦纳不断梦见那些可恶的畜生,已经近八十年了。一群血口大张、獠牙暴露的德国牧羊犬在追捕他,而他瘦骨嶙峋,赤身裸体,在一条空荡的街道上奔逃。街道是如此空荡,以致能听清他赤脚击打路面的声音。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呼吸也越来越急促。最后,狗包围了他,他祈求恶狗动静小点,以免那些人听见它们的号叫。快撕碎我吧,他无奈地说,撕碎我吧,但请小点声。
幸好前列腺救了他。像每天早晨一样,那天他也在迫切的尿意中醒来,六点半,准时。他该把钟调准了。
八十六岁的高龄当然有诸多不便:心脏跳动过缓,随时准备发动致命一击;血压急剧升高,仿佛火车头全速运行时喷出的蒸汽;关节病折磨他的膝盖,迫使他走路颤颤巍巍,步伐缓慢,像他年少时讥笑的那些老年人一样。
前列腺显然也有问题,但这些问题对他来说却一直是一种好处,近乎一份恩泽。这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只有这样才能打断那些有恶狗狂吠不止的噩梦。恩泽并不止眷顾一次,每天晚上他至少起三次夜,就像三个固定的点,三条逃跑路线,逃脱那些折磨了他一辈子的挥之不去的痛苦画面。
其实,被鲁道夫看作福分而非不幸的高龄还会带来另一个后果:如果不戴助听器,实际上他的耳朵什么也听不清,只有模糊的噪声,像雾里看花一样。
对他来说,这也是一条绝妙的逃生之路,但这次逃离的不是噩梦,而是现实,一个他越发难以理解的现实,他虽然置身其中,每天却越发感到格格不入。让他感到格格不入的是电视和收音机播放的音乐,所以他几乎不再打开电视和收音机了;让他感到格格不入的是他几个外孙、外孙女说的语言,里面夹杂了太多糟糕的英语和混合词,听到那些用语他心如刀绞,毕竟他在一所文科高中做了三十多年校长;但最让他感到格格不入的是科技创造的那些新玩意儿,手机、电脑、网购、信用卡和自动取款机,他觉得自己被拒之门外了。这些东西之于他,就如同猪之于他的父母,是一根手指都不会碰的东西。
可是,鲁道夫需要接触世界,需要用鼻子去嗅,用粗糙、消瘦、布满岁月磨痕、像迷彩服一样的双手去感受。他需要感受世界,包括人、物品和钞票。
两只招风耳如同翅膀从他憔悴的面容支出,眼睛乌黑,水汪汪的,鬈曲的头发稀疏、苍白,鼻子与脸不相称,身体瘦骨嶙峋,年岁赫然可见,所有人都看得出,他的脸是一幅日历,没有遗漏他漫长人生的任何一天。
此时他刚刚走过了第八十六个春天,觉得自己像保留地的最后一个印第安人,一位来自一个遥远时代的旅者,另一个地质时代的残余,一只厚颜无耻、还没有变成化石的恐龙。
他出生在 1934 年,是一个已经逝去的历史时代的活照片,维也纳这座城市收留了他。现在他感到很不自在——这是他走在市中心的街头,心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的感觉。他原来的那个由木头、皮革和毛料组成的旧世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现在的世界纷乱不堪,充斥着塑料、荧光、运动鞋和震耳欲聋的音乐,仿佛一个疯狂的游乐园,里面只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房子。即便是想逃离这样的现实,他也没有向过去寻求庇护。不是因为他遗忘了过去,而是因为,他铭记着过去,论恐怖,没有什么能够超越他的过去。
鲁道夫拖着缓慢的步伐走出了厕所。他来到厨房,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结婚之后,他马上去了意大利旅行,那时他学会了用摩卡壶煮咖啡,他很喜欢。奥地利人喝美式咖啡,但那种咖啡没有特点,依他的口味,就是索然无味的洗碗水,全然无法下咽。就算美式咖啡味道不错,他也永远没法真正喝下去,因为那勾起了他对战争年代咖啡替代品的深深记忆。更糟糕的是,奥地利人在晚饭后喝卡布奇诺,他完全无法理解这个习惯。这个接纳了他近八十年的民族很热情,缺点不多,但这算是一个。
鲁道夫抬头看了看,现在应该是六点五十分,因为门上的钟显示的时间比实际要快一个小时。很多年以来,他不再根据夏令时或冬令时把时针调前调后。他厌倦了追寻时间。要不了几个月,时间就会重新变正确,再耐心等等就好了。毕竟,现在他的耐心就像记忆,他有的是。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记忆怎么会每天变得越来越清晰呢?
有时候,童年的画面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声音、气味、颜色没有任何改变,这使他怀疑一切就在眼前。他回忆的都是微不足道的事物:一颗玻璃球,一个玩具小兵,一个圆形鞋油盒,柔软的橡皮,吸墨纸上的横格,祖母的气味,唯一不算太微不足道的是林格尔布鲁姆先生的驼背。
相反,“当下”从他的记忆迷宫中逃走了,他记不起晚饭吃了什么,下午做了什么,甚至应当按时吃的药也不记得。鲁道夫永远走不出这个困境。
迷宫有太多出口,最近的记忆像从屋檐滑下的水滴一样消逝了。然而,他和妻子阿加塔不想任何人帮助他们。两个人相依为命,虽然女儿约翰娜和埃莉卡总希望找个保姆照顾他们,哪怕只是半天也好。
鲁道夫看了一眼右手上新长的一块黑斑,说:“她们认为我们老糊涂了。”这时候,他注意到自己忘了开火。“可能她们说对了。”他又笑着说。
他开了火,站在那里等着,为了取暖,两只手在摩卡壶下面的小火焰旁边翻来翻去,大家都会这样做。一听到水开的声音,他就慢慢拿起盖子,享受咖啡刚刚煮沸时散发的香气。他闭上双眼,让充满香味的蒸汽真正唤醒他。
这个仪式持续很长时间了。他喜欢独自待在厨房,而妻子还要在他留下的温暖中再好好睡一会儿。跟往常一样,昨晚阿加塔吃了半片镇定片,晚上她有多么难睡着,早上就有多么难醒来。
咖啡完全烧开后,他会马上把妻子那杯送到床前,这和快速检查天气情况都是固定的习惯。鲁道夫离开了炉子一会儿,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看了看外面:风和日丽。收音机里说,这次入秋是自从欧洲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温和的一次。天气如此舒适宜人,完全无法让人联想到即将给他的生活带去第无数次波澜的暴风雨,毕竟此时他已坚信,人生的最后一次波澜会是尘世生活的落幕。
他最后看了一眼楼下的街道,路上开始变得拥挤,不断有学生、上班的人和起早的游民经过。随后,他从炉子上方的隔板上拿了糖罐,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勺子。
这时,他看见手机在震动。他感觉没有听到声音,因为助听器还放在床头柜上。
他戴上读写镜。是大女儿约翰娜打来的,她是美景宫美术馆的职员,也在维也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