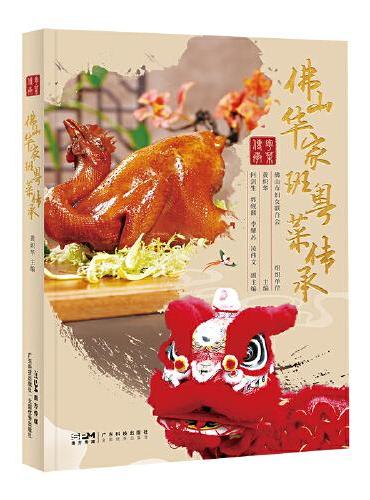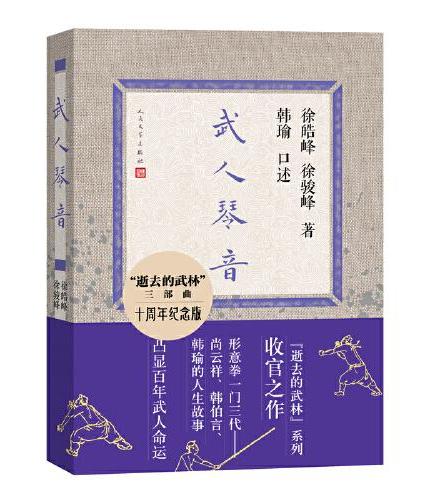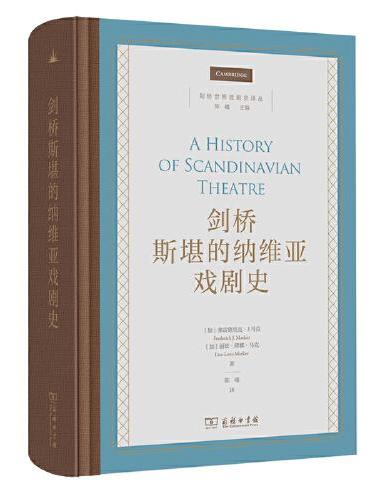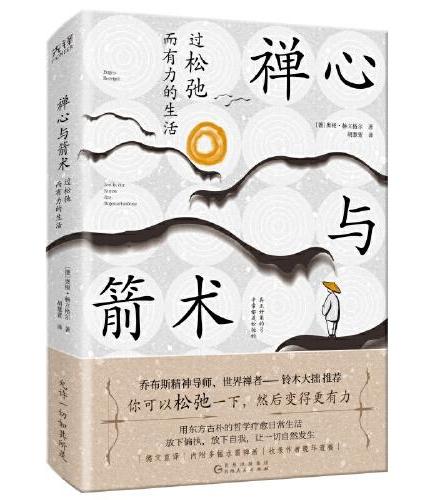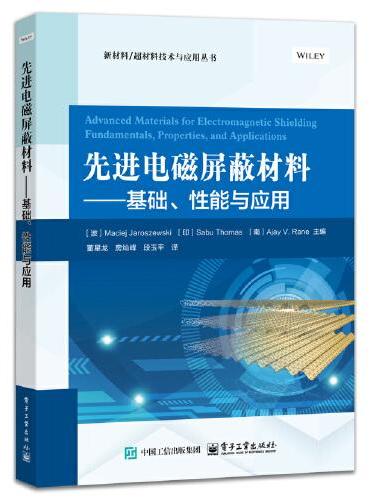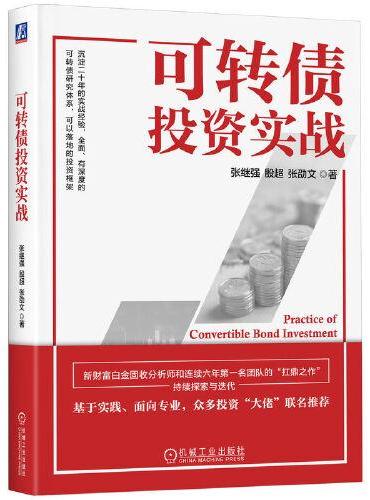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半导体纳米器件:物理、技术和应用
》
售價:NT$
806.0

《
创客精选项目设计与制作 第2版 刘笑笑 颜志勇 严国陶
》
售價:NT$
2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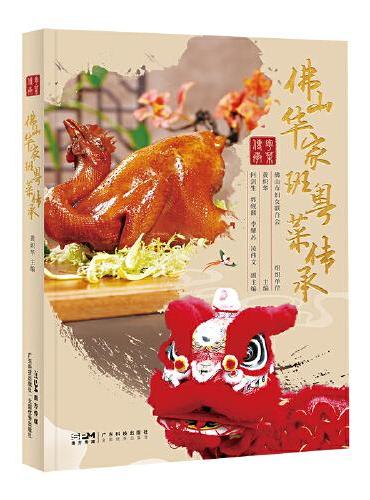
《
佛山华家班粤菜传承 华家班59位大厨 102道粤菜 图文并茂 菜式制作视频 粤菜故事技法 佛山传统文化 广东科技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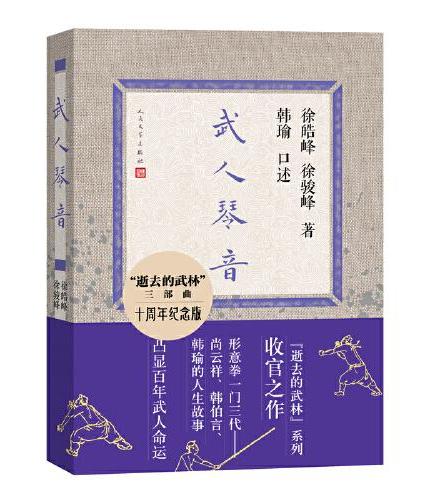
《
武人琴音(十周年纪念版 逝去的武林系列收官之作 形意拳一门三代:尚云祥、韩伯言、韩瑜的人生故事 凸显百年武人命运)
》
售價:NT$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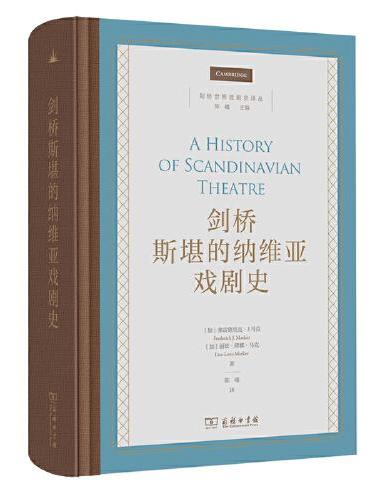
《
剑桥斯堪的纳维亚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NT$
7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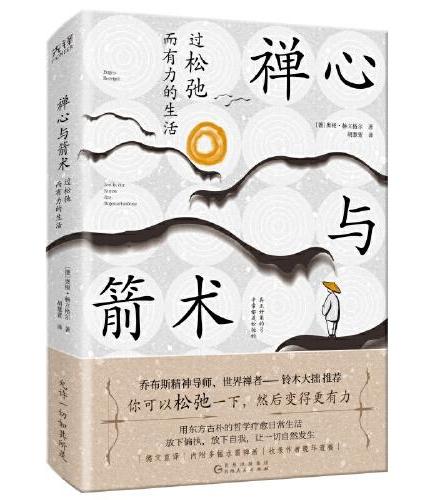
《
禅心与箭术:过松弛而有力的生活(乔布斯精神导师、世界禅者——铃木大拙荐)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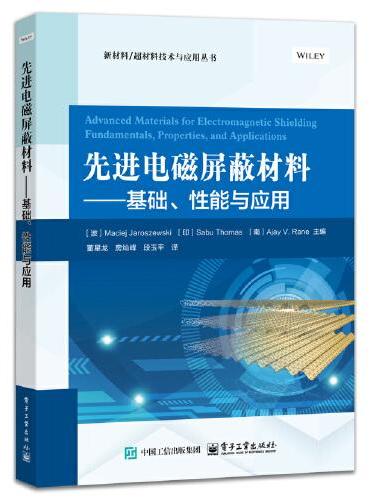
《
先进电磁屏蔽材料——基础、性能与应用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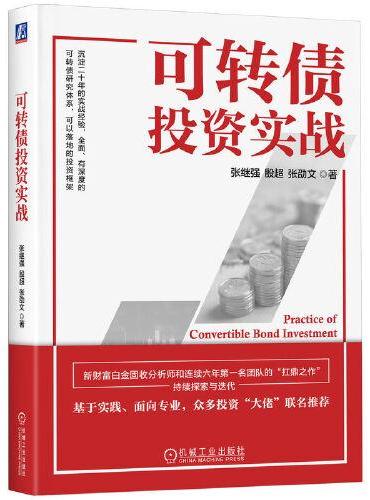
《
可转债投资实战
》
售價:NT$
454.0
|
| 編輯推薦: |
张宇著《没有孤独》为“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之一种。
一、该丛书是由当代著名评论家点评的涵括中国百年经典中篇小说、展示中国百年中篇小说创作实绩的大型文学丛书。
该丛书对“五四”以来中篇小说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读者可以通过本丛书确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中篇小说的阅读坐标。当代著名评论家何向阳、孟繁华、陈晓明、白烨、吴义勤对作品的文学价值以及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对文本进行了精彩点评,这对于读者欣赏把握这些经典作品起到了引导作用。
二、形式有突破。
丛书以作家分册,每册精选该作家最经典、读者认知度最高的作品。除经典作品以外,另附文学化的作家小传及作家图片若干幅。所附内容既可以为文学研究者、文科学生提供必要的资料,对普通读者深入理解作家作品同样大有裨益。
三、所选作家有较大影响力。
张宇,1952年生于河南洛宁。作家。曾任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活鬼》《乡村情感》《没有孤独》等,长篇小说《呼吸》《疼痛与抚摸》《软弱》《足球门》《晒太阳》等,长篇散文《对不起,南极》。作品获得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河南省政府奖、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小说优秀作
|
| 內容簡介: |
本书收录的是当代著名作家张宇的小说代表作《没有孤独》《乡村情感》《枯树的诞生》三篇。
《没有孤独》探析中国当代农民所走过的曲折坎坷的道路以及他们灵魂蜕变的心路历程。《乡村情感》展现作为一名科学家的主人公鲁杰,在蒙冤入狱后所经历的一生心灵跋涉的艰涩,不停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枯树的诞生》通过与一群玩盆景的朋友的相知相熟,作者从此跟树结下了不解之缘,突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通。
张宇以真诚的创作态度,创作了众多的典型的“软弱”小人物,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尤其是他们分析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传达给读者一种平等而又可贵的真诚,而这种对读者的真诚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张宇的特别之处及其作品的魅力所在。
|
| 關於作者: |
|
张宇,1952年生于河南洛宁。作家。曾任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活鬼》《乡村情感》《没有孤独》等,长篇小说《呼吸》《疼痛与抚摸》《软弱》《足球门》《晒太阳》等,长篇散文《对不起,南极》。作品获得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河南省政府奖、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奖、人民文学杂志社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电视剧飞天奖等十余种文学奖项,被评为“中国小说家50强”之一。长篇小说《疼痛与抚摸》《软弱》《呼吸》以及部分中短篇小说被译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西班牙、以色列、越南等多国语言,在海外出版。
|
| 目錄:
|
没有孤独
乡村情感
枯树的诞生
生存的?存在的!——张宇中篇小说“叙事”(何向阳)
|
| 內容試閱:
|
生存的?存在的!
——张宇中篇小说“叙事”
何向阳
《乡村情感》写虽死犹生,《没有孤独》写虽生犹死,《枯树的诞生》写对意味的死的战胜,枯荣是一种站着的死,也是一种越过死的生。有形的、无形的、具体实在的死,虚假的、乌有的、看不见的死。存在,跨过一般的灵、肉冲突,而以共居精神内部的生、死一步步向他逼近。
抚案惊异。冷,果真是保护的伪装?在他设置的叙述方法的重重障碍里,我们还能找到一个作家以精神标准反观世俗人生并绝望又执拗地追寻某种超越价值的作为人的不懈努力吗?!他总是把疾首痛心掩盖在冷漠平常的语言叙述背后,藏着,虽言死亡、存在,却无实验派笔下的末世图景;张宇的主体性还表现在他对文坛狂热的语言颠覆、结构实验的不为所动,在形式与内容之间,他并不选择纯粹性,他深知单凭纯粹的形式无法企及意义的高峰,甚至连传达文学的本意都勉为其难,但他也不主张形式纯粹为内容服务以达到某种绝对的化解或中庸的兼容。他要求的是一种历史与现实与艺术、人生的融会,而真正的融会便不再能够捡出单纯的形式或内容,这种观念使得他在膨胀的形式实验热浪中警惕自己的被卷入、淹没,而在另一番具体模仿的写实流向里又为保存他极珍视的艺术挣脱而出。对于写作,张宇是一个偏执的人。
设若1985年前后的张宇是被某种潮流裹挟推上文坛某种地位的话,那么,1988年以后的张宇则竭力逃避任何潮流,这不能不使他的作品在貌似跌落的表象中有内化的独语倾向,如《没有孤独》中夹杂的长篇议论,《枯树的诞生》中随意如笔记的漫谈,这种内化使他躲过了许多青年作家躲不过的狂潮,使他在咄咄逼人的“新就是一切”的势力面前还能保持相当的自信与老练,所以,当突起的狂飙衰微、新不免成了旧的时候,他的坦然便不是任何丢盔卸甲者所能享受和得到的。
艺术的独一无二性本质是反对任何潮流的,甚至以将自己被归入某种派别而感到羞辱,真正认识到这一层的人不多,张宇算是不多者中的一个。张宇可以把叙述设计为多个层面,但绝非意在增添阅读的屏障、摆弄噱头。他试图包好那个核心,但他拒斥曲径通幽。他总是把他最想说的话包裹得很深,这就使得那隐匿在重叠的文字背后的真正悲悯与时下流行中的软弱、感伤,与将艺术当作麻醉的虚妄、欺骗划开了界限。
如何走出问题对视,走向哲学俯视,是他自己的小说所面临的问题。幸而以后,张宇终于找到了“事实关系”与“意义关系”的不同,从而使他的创作由《乡村情感》《没有孤独》开始选择与前两种关系相对应的“媒介语言层”“思考语言层”,可以看出,张宇小说前期在事实关系即媒介语言层内展开得多,噪哗、火气;近期作品则倾斜于意义关系,即思考语言层,力图发展潜台词中的隽永意蕴。这个过程,在张宇,并不是跳跃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大的方向上,他常能把握住一个脉络与流向,而在具体方案与事情上,却并不显得特别机灵。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所渐渐意识到并感喟的那样,自己是一个夹在中间的人。
在通往巨著的路上,他有太多旁骛,这时常遮掩了远方真正的目标。而让人钦慕的是他的聪明,每次临到了迷失的时候,他都能抬起手臂挥去雾障。能够提供这一论点的论据便是那部《没有孤独》。完全冷峻的主题。但那种近乎禅境的入世方式和他对人生深得三昧的体察、了悟,更使他在超越与逃避之间,在独善与拯救之间,在入世与出世之间,逍遥不起来。张宇以此证明了他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他所承载的庄严、艰辛不时在他极现实的作品里刷上一层冷色。
理想还表现于对田园的复归倾向,《乡村情感》的第一句话是:
我是乡下放进城里来的一只风筝,飘来飘去已经二十年,线绳儿还系在老家的房梁上。
现实的失意使他愈加怀念故园,从而内心靠近温情主义,不自觉甚至下意识地寻求某种平衡,1990年前后的《乡村情感》题目取向便可说明这一点。
《乡村情感》作为张宇人格的投影,正如乡村作为张宇情感、血缘的空间投影,都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张宇的爱憎、批判与亲情使他清醒到能站在自己的外面看到自己的局限,然而却站不到这局限的外面。在《那牛群,那草庵》中,张宇说,我的家在豫西伏牛山里,那里有我的根,而在《乡村情感》中便很难再找到这种早期的单纯。张宇对他的局限看得很清楚,然而,无论他的自然血缘还是文明良心以及乡土经验、文化冲突所形成的孤立、隔膜与傲气都不允许他对这种情感有所背离。一方面是对“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在一个地方生下根……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子一般”的乡土的拳拳留恋,一方面是对温情脉脉的乡土文化竟包孕没落、残酷、腐朽等封建性因素的痛恨;一方面是对现实历史作为前进的无可挽回的陌生式人文关系扩散发展的认识;一方面是对“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费孝通:《乡土中国》,第6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的隐隐忧惧,理、情对峙,这是张宇乡土情结分裂的实质。以致在《乡村情感》中呈现出情节发展与情绪表现的不平衡,结尾的匆匆收束某种程度上是作者对自己逃避的完成,再深一步地探询很可能导致张宇否定自己。在一片苛责的清算传统的“寻根”中,张宇不愿加入自己的批判,他守住自己,不发一言。守,本身就是一种局限,然而,为了一种血缘的情感,他宁愿如此,哪怕局限就是血缘,哪怕这种守带来更大的局限。
最能表现他乡土情结的怕是张宇对树根的热爱,他可以为买一棵好的树桩早晨不到天明便骑车跑到几十里开外的交易场,他可以为培育一个自己喜爱的盆景而不惜费时地施肥、剪枝、浇灌、看护,他小心的神情像对婴孩一样,令人想到一种创造,想到一种使世界诗意化的劳动的沉浸,想到热爱绘画的丘吉尔:“……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在不精疲力尽消耗体力的情况下比绘画更使人全神贯注的了。不管面临何等样的目前的烦恼和未来的威胁,一旦画面开始展开,大脑屏幕上便没有它们的立足之地了。它们退隐到阴影黑暗中去了。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工作上面。”(丘吉尔《我与绘画的缘分》)寄托于树根与寄托于山水一样,是他“乡土情结”的肯定发展。但即使在这得鱼忘筌式的热爱里也藏有深刻的矛盾,将根扎在土地里,而做盆景的根却在不断扭曲,断线的风筝是无根的,盆景里的根又失去了它原有的土地,张宇面对一棵树时,很难说他面对的不是自己。那些扭曲却还在挣扎上升的树根,是否就是他性格的旗帜,是他的心灵那不断受伤的部分?是否正代表着一个外观上节节胜利、命运如此娇宠,而内心却已疤痕累累的人呢?《枯树的诞生》同样写扭曲、磨砺。张宇一直想把自己对树根的爱好对象化、物化,可是审美中主体的感受浸润使他无法无动于衷地面对自己。我时常想,为什么张宇对“养树”题材这样抓住不放,乐此不疲,原因即在于张宇自己被卡在了这里;而依他的个性,当未经解决的矛盾困扰折磨他时,他本能要紧紧咬住,而不会轻易放弃。
《枯树的诞生》表层,他极力要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和生活实质;内里,却极力抗拒这种接受,抗拒这种被城市容纳、消化和自己同化后的消逝。意识层的趋近,情感层的偏离甚至逃离,理智上要接受城市,情感上则背离城市,这种矛盾并不仅仅限于对城乡的态度差异,这似乎已奠定了张宇性格的悲剧性。所以,在张宇“乡土情结”较浓的篇什里,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自我的寻找,“还乡意识”,是他自己找自己的一种方式。而在寻找过程中,他时时感到浮士德式的分裂,“我”把“我”丢失在了哪里?
对乡村的回忆,使他选择了一条非但不能逃避反而是充满悖论的道路。在这里,他找到了与现实不同维的参照度,但时间的介入不仅为他带来安慰,同时也为他迎战人生打下更深的基础。福尔斯曾说:“您甚至并不认为您自己的过去是完全真实的,您将它装扮起来,您为它镀金,或将它抹黑,您欲言又止,掺假乱真……一句话,您将它虚构化,然后搁置上架——这就成了您这本书,一本充满罗曼司的您的自传。我们都在逃避那真正的真实。这就是智人的基本定义。”(《法国中尉的女人》)庄子的解脱法是,“把人的存在的时间性消融到川流不息、变化无穷、无始无终的壮观的时间之流中,把人的生死残全融会到一种具有必然性、宿命性的自然律动里,把自我融入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中去分享其中的永恒和宁静”,其结果,“时间=无时间性=无生死=没有分别的‘圣一’,存在与非存在并置而予以抵消,人的存在的短暂性的识别因与时间总汇的无限性并置而导致泯灭,充满欢乐和痛苦的生的丰富性因与死的一致性并置而给予否定”。(刘绍瑾:《庄子与中国美学》,第24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西方意识的时间里,在中国儒道过渡的精神流程里,张宇获得了暂时的休憩,但是果真逃避并解脱了自己么?回忆的微醺,使张宇在“乡土情结”作品中一直追求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于世、无为有为的道家境界,但又终因他不忍不舍的道德精神与责任心而无法企及。他钦慕庄子世俗之累摆脱之后的逍遥适己,他赞赏陶潜归田后“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心远地偏的悠闲旷远,甚至,“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感慨也与张宇此时此地的心境有着惊人的相近。然而,张宇也分裂成为两部分:一个庆幸自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并通过养树真的做到了“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另一个则摆脱不开“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理想纠缠。
对父亲或祖辈(文化象征)的感情,是张宇“乡土情结”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情感》中对父辈情感的难以割舍,张宇创作的确在培养一种性情,一种“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对审美的超实用性、艺术的非功利性的追求可视为他对纯朴心境的恢复,《枯树的诞生》是这种“心斋”的过程。在回到过去的背后,包含着他对人与自然和谐合一的程序的肯定,包含着对未遭异化、富有生命活力的诗意的肯定。这种肯定是矛盾的,《枯树的诞生》里的张宇极力想抛开虚假文人俯拾皆是的令人窒息的圈子(城市的象征物),找到与自己品性相近的一群,如养树根的未失质朴天真的工人们(乡土意象),但又由于思想文化的障碍而不能真正走近,成为他们中无隙的一员。他觉得找到了一种集合,姿态上也力图扎根,但又是一种过路的心态。写市井、玩盆景,艰涩的寓言包裹在游戏的形式与散漫的文笔中,吃力显出出世的不纯,和凡俗不能脱离,而找到的群体所具备的单纯天真则是张宇的心理指向:他们的自由、随意、友爱的生活使他长期在旋涡中颠簸的心灵得到抚慰;更深的意义是,他们对平常生活外另一番天地——养树的倾注,与张宇倾注写作——精神生活的心态相吻合,而写树被砍后扭曲又坚韧的成长又与自身屡经挫伤却又冷硬的性格合上了拍。正因为张宇将这错综复杂的情感微妙而不自觉地糅合在一起,却又在凡常中寻求超越,在冲突中寻求统一,所以,他自以为投入,而实际一直未把自己真正放进去,清傲、不甘的背后,则是更深的孤独。作品带出了能走出(逃离城市)不能走进(回归乡土)的苍凉,进不去、回不来的尴尬又为张宇作品投上一层老年的沧桑。此时,张宇已看出自己心造的这一寓所的虚伪性——正是它,影响了张宇创作本应有的恢宏气度。所以张宇力图清除字面上的感伤性和堆砌铺张,与一种肤面的技巧,力图抓住文字后面的容易被人放过与忽略的生命,做到洁净、干脆,这种语言追求正是张宇追求的由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到简单的心境流露。这使得张宇的《枯树的诞生》超越了“乡土情结”而具有普遍的存在意味,“我养树实际上是在为我自己早早营造坟墓”。
人类物质文明、理性精神的发展,与人的“天放”“素朴”之心,直观感悟二律背反的结果,使不断有人主张的“回归”之声汇成了人道主义强劲的合唱。张宇的自个人体验出发的“回归”与这股潮流不期而遇,从本质上讲,张宇对农业文明与自然生活方式的态度是双重的,在一方面化解痛苦、一方面又生长痛苦的土地上,张宇的“乡土情结”最终无可置放,这种困境,是我们与张宇一样或迟或早要遇到的,这是人类文明状态里生命必然承受的一个永恒悖论。
在对故事即生活本身的判断里,人们宁愿对更深的意义视而不见。这种现象本身流露出人类对存在追问的避讳,这怯弱、短视恰恰反衬出张宇的雄辩与天真,那种九死不悔的执着当然使他祛除了蒙在生活表面的一层虚幻的、哪怕是意念中的暖色,张宇的冷毅使他最终必然走出消耗自身才华的“桃花源”式的梦境。
所以有《没有孤独》。
鲁杰堪称文学史的“这一个”。张宇以精神分析概括出人的命运以及与命运起伏、跌宕相映衬的历史,手术解剖样的冷叙述直剥真实的残酷性。张宇第一次这样集中写人的失败,写大潮裹挟中人无可抗违的宿命和“运动”当中人力量的渺小与无奈;张宇第一次把时间切割开来,把鲁杰的一生分为几大段落,以冷写冷,以冷漠写冷酷,以无情写无情,张宇碾碎一切的冷冷的真实,足以与岁月那副冷静的面容对垒,这种冷酷的写法确实可以看成对生死置之度外的超越——如果说张宇一直在写人的生存状态,而《没有孤独》则第一次写人的存在,写对存在的况味。
鲁杰一生都在追求超越平庸,从乡间的求知心到留学的报国志,从三十岁的监狱到七十岁的研究院,他一直在挣脱未能挣脱的圈索,历史的逆流、失误可以挽回,而鲁杰的一生只能是三十年后在郊外踱步“站在自己的躯壳旁边”所悟到的虚无的胜利:“于是鲁杰浑浑感到,他这一生不可能对科学有所贡献有所建树了,他甚至觉得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他对科学的纯粹的态度。他对科学研究的态度,最终成为他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集成。从这里,我们终于发现,支撑鲁杰一生的命运大厦只有一根巨柱,那就是他对于科学研究的纯粹的态度。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全部精神的物质的财富,也只有他对于科学研究的纯粹态度。”惨烈、凄惶的人生,透着真实的可怕、可怖。鲁杰进一步体悟:“这就是别人说的鲁杰了,我在这里边曾经生活过七十五年。他望着这躯壳,像看着一座破旧的草屋或一辆破旧的汽车壳子,这才使他明白过来,人们几十年都把这老头儿叫自己,现在看它不过是自己的外壳。”这种“哲学评论”的引入使人步步陷入人对自身的追询,这追询的残酷性是对人存在实质的剥离,然而张宇还不罢休,又引入“外壳行为”“灵魂行为”加以穷究: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经常发生这样的现象,有时候外壳拖着灵魂行走,有时候灵魂冲动着外壳运转。在外壳主宰着这个单位时,行为是平庸的,在灵魂主宰着这个单位时,行为就发生杰出的表现。平庸的人生就是外壳行动,杰出的人生就是灵魂的运转了。原来人生是从这里来区别质量的……从此,他要开始最伟大的科学研究,那就是生命能源的研究。这个研究从探索生命的外壳和灵魂的关系开始,到任意更换或选择生命的外壳而告一阶段。通过这第一阶段的研究……可以叫作生命的外壳学……
鲁杰终于以传统的精神胜利超越了现实的悲剧人生,而这种所谓超越使他再度沦为非存在的生存状态,使他以存在陷入的孤独这种生存方式取得了与世人一致的、化解任何忧患的、没有孤独的众人皆醉境地。鲁杰的醉是半醒着的,鲁杰的醒只在他的头脑设计里,这就是这段文字后面渗出的血,所以,“鲁杰死了/我们这么说”,一种意味上的存在的死亡被写得淋漓尽致。结尾的钢琴声中,一面是岁月、时光奔涌的流畅、无情,一面是对生命存在的貌似漠然后藏有的难抑的激愤与平静,激愤的形式与内容都流为漠然。张宇的精神分析是与事件并行的,这种叙述为他的作品增添了厚度,这是一次灵魂解构的尝试。但与“以零度感情介入”的“还原生活”的新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新小说派不同,张宇貌似旁观的冷叙述中含有明确的意识选择性与情感倾向,所以,在对人物、事件、时间的不断解构中,他不惜插入大段大段的议论,以小说创作之大忌的作者介入来构成参照,并在鲁杰(人物)、“我”(叙述者)外加入中性评判者,使作品的空间充满弹性,将恒温的事件经叙述者“冷冻处理”后再以评判“加温”“速冻”。在此张宇第一次将反讽、佯谬的手法用到极致,以之写存在与生存的悖谬,“既是怀疑自我的结果,又是消解自我的有效手段”的反讽,与人物主观雄心不成而客观上一步步向随遇而安演变的过程取得了惊人的对应,从作为艺术感与科学精神的结合并体现为否定性的创造力的反讽中,可以看出它将生存及环境诗化的原则。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年代已远但已作为骨髓被承继下来的作为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之一的魏晋风度的潜影,其遗世独立、追寻精神超迈的实质确实与鲁杰持有的“纯粹的科学态度”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悲剧是深刻的,孤独不可避免。
张宇擅以冷静、肃穆、具有浓厚抽象色彩的数学眼光看待世界,普遍与永恒、框架与内核、心灵与现象的进入又使整部《没有孤独》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它的风格,在他许多过于实在具象的小说中,显然是别具一格的一例。张宇对创作语言的理解的形成是与理论界的“语言热”同时的,他说:“那种把语言仅仅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人,是可怕的。在使用的同时也在消灭和隔离着自己。”(张宇:《语码寻找》,载《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第4期。)所以他引进“具有灵性、直接沟通心灵”、闪烁“生命之光”的语码概念以区别于语言:“只要这种语码一启动,就赶起了我思维的疯狗,到处奔跑着咬叫着,没有了束缚和秩序,写作时就变成了一种宣泄,不再是一种吐咯的难受。”(张宇:《语码寻找》,载《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第4期。)这最后一句无意透出了张宇创作观念的更变,其越过法则与禁忌之上的蔑视并自信的态度,比起先锋派对作者议论介入拒斥而未能全部自由开合的创作观念来,张宇更具有先锋派所不及的思维先锋性。以理性写非理性,不仅需要与非理性的历史现实抗拒的勇敢,更需要与时代文坛理性受排挤的氛围作战,张宇再次把自己置身于两军对垒中间:“不是走向生命的最终拯救,与外部客体的理性认知,而是趋向生命现世的有限而持续的超越,与内部人格心性的锤炼。”张宇对自己的锤炼近乎严苛,他似乎在加码似的考验他自己对苦难的承受力,所以,无论是冷静的分析,还是严谨的推断,都无法掩饰他对悲剧的兴趣,和这兴趣后隐藏得很深的一种失望与悲观。以理性写非理性,是与悲剧分不开的,悲剧又与存在共在。生存与存在的分界,对张宇来讲是艰辛的跋涉,生存所考虑的只是物质层面的,包括扩大了的物质、方式与手段,诸如职、势、权、名等,存在则属于精神领域,是目的、意义的追问,诸如精、神、血、气等。
由写生存到写存在,是张宇创作的一次跃进;而带给文学的,则是一种更高价值的探询。二者都围绕悲剧展开,存在的实质要求人生解除“倒置”的痛苦,去掉物役的惶惑,不争逐名利,不陷入世俗观念,达到精神系于天然的境界,追求人与外界、人与主观精神的和谐。由此看来,“乡土”是由生存到存在的必经之路。然而张宇并不囿于田园,他进一步体验人生,标志他创作深化、成熟的《没有孤独》建立起的痛感意识,使他笔下的悲剧带有浓烈的正剧气息。“那些丢弃了常规生活,心怀悲壮,体验到人生、生命、存在的真谛,向着更阔大的意境升腾的人和事,那种不安、困惑、愤慨、超脱、孤独、凌驾于世俗生活之上的感情”,深深地烙进他的体验里,这种体验的刻骨铭心给他提供了一种悲剧的眼光,他确实做到了将人看作寻根究底的探索者,赤裸裸,无依无靠,孤零零,面对着他自己天性中和来自外界的各种神秘的和恶魔的势力,还面对着受难和死亡这些无可回避的事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