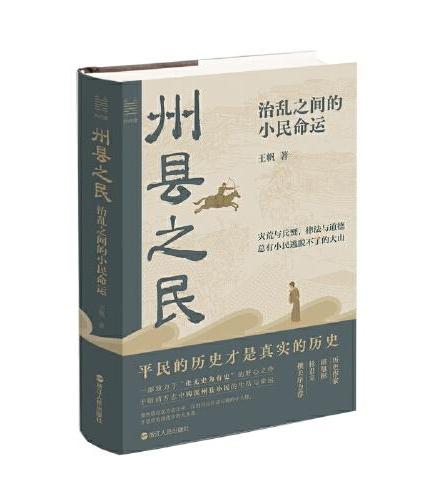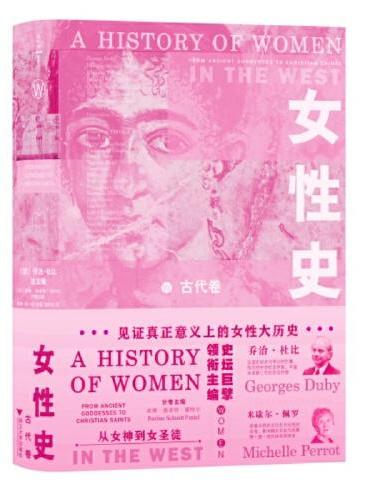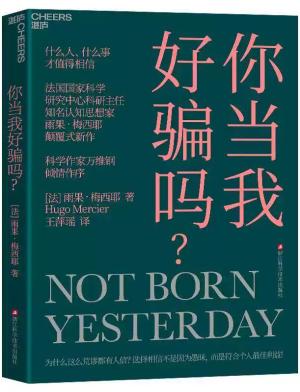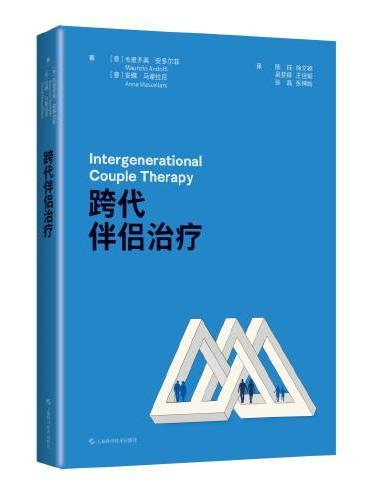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斯大林格勒:为了正义的事业(格罗斯曼“战争二部曲”的第一部,《生活与命运》前传)
》
售價:NT$
840.0

《
日内交易与波段交易的资金风险管理
》
售價:NT$
390.0

《
自然信息图:一目了然的万物奇观
》
售價:NT$
6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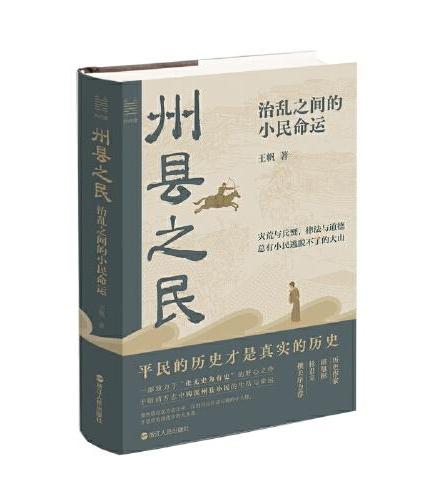
《
经纬度丛书·州县之民:治乱之间的小民命运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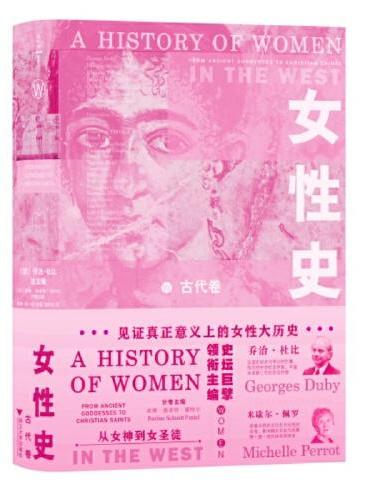
《
女性史:古代卷(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大历史)
》
售價:NT$
5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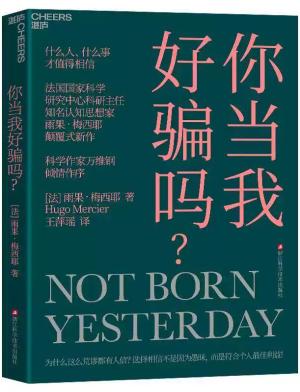
《
你当我好骗吗?
》
售價:NT$
5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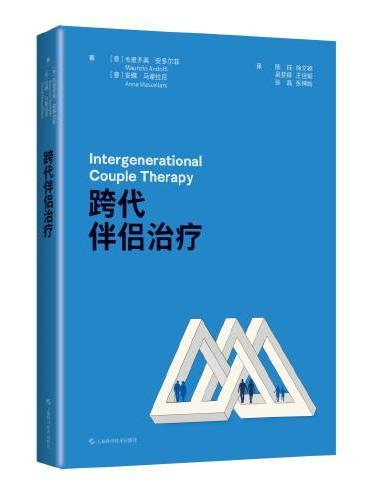
《
跨代伴侣治疗
》
售價:NT$
440.0

《
精华类化妆品配方与制备手册
》
售價:NT$
990.0
|
| 編輯推薦: |
★ 托特·克里斯蒂娜是匈牙利当代最负盛名的诗人、小说家,其作品已有超过二十种语言的译本,《像素》是托特的代表作,也是面对中文读者的shou部作品。
★ 手的故事、颈的故事、眼的故事……30个故事分别以身体器官命名,发生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身份各异的人迷失在现代世界里,却如构成完整躯体的器官一般彼此关联。
★ 《像素》如同一颗魔法师的水晶球,从中可以窥见欧洲近一个世纪的时空和身份各异的人,他们在破碎的现代世界里品尝着失败和苦涩的创伤。托特邀请读者从看似独立的故事中拼出人物关系的魔方,看见他们的命运共同体。
|
| 內容簡介: |
|
《像素》可以被看作一部由30个看似独立的短篇构成的中篇小说。华沙犹太区孩子的手、希腊移民的舌、布达佩斯检票员的脚踝……这些器官属于一个个普通的欧洲人,他们在近一个世纪的时空里时隐时现,有时以同样的名字上演着全然不同的故事。这些故事分别以身体器官命名,在黑色童话般的语言里,讲述着现代世界里的失落和苦涩。那些或平凡或边缘的人物,正如身体器官一样,彼此关联而不可替代。
|
| 關於作者: |
|
托特·克里斯蒂娜,匈牙利当代诗人、作家、译者。她的作品已有约二十种不同语言的译本,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鱼缸》、短篇小说集《像素》《条形码》等。曾获“尤若夫·阿蒂拉奖”、“匈牙利共和国花环桂冠奖”等十余个文学奖项。 青年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欧洲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研究方向为东欧文学与文学翻译。 青年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欧洲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研究方向为东欧文学与文学翻译。
|
| 目錄:
|
作者前言 文本的身体——致中国读者 托特·克里斯蒂娜
译者序 像素、拼图或色块——译者序 何溯 方萱妮
第一章 手的故事
第二章 颈的故事
第三章 眼的故事
第四章 腿的故事
第五章 头的故事
第六章 手掌的故事
第七章 肩的故事
第八章 耳的故事
第九章 指的故事
第十章 阴道的故事
第十一章 脚踝的故事
第十二章 头发的故事
第十三章 心脏的故事
第十四章 大腿的故事
第十五章 脐带的故事
第十六章 乳房的故事
第十七章 舌的故事
第十八章 肚子的故事
第十九章 阴茎的故事
第二十章 齿的故事
第二十一章 下巴的故事
第二十二章 脚掌的故事
第二十三章 嘴的故事
第二十四章 牙龈的故事
第二十五章 后颈的故事
第二十六章 脊背的故事
第二十七章 鼻子的故事
第二十八章 膝盖的故事
第二十九章 胎记的故事
第三十章 臀的故事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手的故事
这只手的手指短小又柔嫩,所有指甲都被啃得乱七八糟的。它属于一个六岁的小男孩,他掰着手指算数,也常常用手来揉眼睛。男孩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捏着裁缝粉笔在桌面上画着圆圈,有人提醒过他好几次别这样做,他可不管。他画着螺旋状的线条,线条组成一个个圆圈,他想,要是一直不停地画下去,线条就会根根相叠,然后从桌面升到半空,就像个立体弹簧。他曾试着跟别人讲过这个点子,但从没有人听他说完过,于是他现在歪着脑袋,独自在木板上忙活着,手臂遮着他的画作。大人们把裁缝粉笔藏在抽屉里,结果被他找着了。顺便一提,小男孩名叫达韦德,与妈妈鲍日娜和几个姨妈一起住在华沙犹太区。门从外面被撞开了,房间里的三个人立马缩进角落。塞丽娜猛地站起身来,她一眼就看到了那块裁缝粉笔,但还没来得及出声,一颗子弹就击中了她。粉笔掉在地上,摔成了两半。过了一会儿,入侵者一拥而入。他们在厨房抽屉里翻找刀叉和银器时,有人一脚踩在了粉笔上。可惜达韦德再也没有机会完成他的粉笔实验了,他没能在战争中活下来。他死在了特勒布林卡集中营。[ 纳粹德国于1942年建造的集中营,位于波兰境内。]
我搞错了,搞错了,达韦德不是在特雷布林卡死的,死掉的也不是一个小男孩,而是个小女孩。不过这些小孩子的手都那么相似,指甲全都啃光了,软乎乎的指头又粗又短。总之,这是一个小女孩的手,小女孩名叫伊莲娜,来自立陶宛维尔纽斯。我讲得颠三倒四,因为我想一次性把所有的故事全都讲完。她怎么会是立陶宛人!她的头发只在第一眼看上去是金色的。真是这样,那头秀发乍一看是金黄的,实际上却色深而卷曲。其实——这是真的——她名叫加芙里埃拉,出生于萨隆基[ 波兰中北部村庄。],1943年2月被关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她在战争中活了下来,但她失去了母亲和家园,只能流落他乡。后来,她会去巴黎,在那里安顿下来后,她会成为一名法国记账员。是的,这种事情也是有可能的。
她的丈夫是一位白领,为人友善,只是没什么头发。他在巴黎银行上班,但他本人同我们的故事完全无关。加芙里埃拉日常用法语思考,她已经忘了希腊语该怎么说。她妈妈的希腊名字,多姆娜,在她的耳中跟法语里的“诅咒”越来越相似。她同孩子们讲话时也说法语。实际上如今她只读译成法语的希腊文学作品。她的手确实不怎么好看,指头短短的,因此,她丈夫送她的那些饰品她从来也不戴,只把它们保存在一个皮质首饰盒里。加芙里埃拉过得并不快乐,毕竟,也没有多少人能在巴黎过得快乐,不过她也知足了。她还有一个好友,她们俩经常一起去购物。
好友和她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两人肩并肩坐在地铁上时,别人都会以为她俩是亲生姐妹。其实,好友有一半罗马尼亚血统,一半匈牙利血统,跟她一样,也长着一头鬈曲的灰褐色头发。我知道,这个故事越讲越复杂了。但我们没法让现实杂乱无章的线头变成闪着光泽的流苏,线索太杂了。好友的手也不好看,但美或丑,她已毫不在乎,毕竟,她已不再年轻。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人丢开了她的手。那时候,她的妈妈在克鲁日-纳波卡[ 罗马尼亚西北部一座城市。]有个情人。当时,清洗犹太区的消息满天飞,情人设法弄来了两张通行证。妈妈苦苦想了三天三夜,最后还是跟着情人跑了,将只有四岁的克斯米娜独自扔下。妈妈寻思,还是先保住自己的命要紧。她往女儿怀里塞了一个包裹,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那天是1944年5月13日,小女孩站在鸢尾花区[ 罗马尼亚克鲁日-纳波卡的北部地区。]看着妈妈离去的背影。巧合的是,后来,克斯米娜的儿子也在5月13号这一天出生,他的名字是达维德。当然,这跟那个死在华沙犹太区的小男孩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尽管两个小男孩同名,但已经没人记得达韦德了,而这个达维德却总会有人记得。他的曾祖父是匈牙利人,老爷子奇迹般地挺过了战争,但后来却没挺过齐奥塞斯库[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1918-1989),二十世纪下半叶罗马尼亚政治人物。]统治的天堂[ 二战后匈牙利一部分领土划归罗马尼亚],他离开人世前,刚刚得知达维德出生的喜讯。他觉得达维德这个名字不好,不过这又是另一码事了。达维德妈妈小时候被抛弃的事,不是曾祖父讲给他听的(幸好不是),而是砖厂犹太区的居民告诉他的。克斯米娜变成弃儿后,正是这些好心的居民出于愤怒与道义,担惊受怕地把她抚养长大。[ 作品中有些相同的名字,由于在不同国家发音和拼写有所不同,因此译成中文时也会有所区别。]
我刚刚说谎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事情本就是这样。实际上,达维德并不知道妈妈被抛弃过。毕竟没有人能活那么久,久到能跟达维德见上一面,久到可以告诉他,当时,妈妈的妈妈是怎样苦苦乞求情人把两张通行证都给她,而求生的欲望又是如何在她被爱情占据的混乱头脑里占了上风。加芙里埃拉也没听过这个故事,她所听到的故事里,一切都发生在遥远的立陶宛,维尔纽斯。故事中的小女孩名叫伊莲娜,是伊莲娜的手被丢开了,被妈妈扔下的小女孩其实是伊莲娜。加芙里埃拉多多少少也能猜得到,这对母女没有一个在战争中活了下来。
这一切当然都没法查证了。这么多名字,看得人眼花缭乱,很难搞清楚谁是谁。我们一般还是得靠推测。比如说,达韦德的粉笔实验在理论上是可以成功的,毕竟线条具有延展性。不难推测出,达韦德是对的。如果在同一个地方不停地用粉笔画圆圈,不受时间限制一直画下去,线条就会根根相叠,从桌面上升起来,变成一个圆柱体,我们甚至还能触摸到它的凸起,这可不像树上的瘤节。在纸上也可以做这个实验,不过在这个世界上,还没人有耐心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完成这项粉笔实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