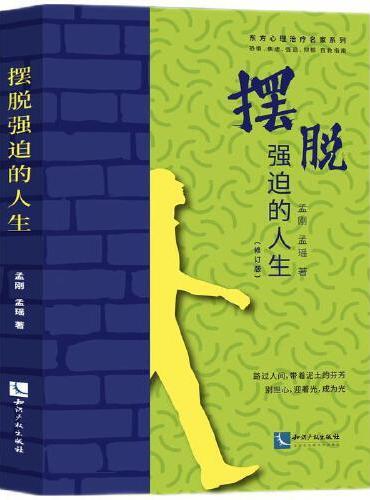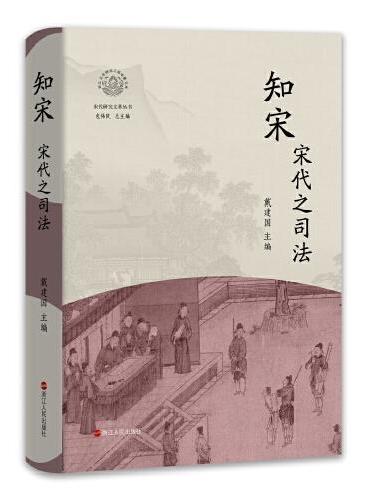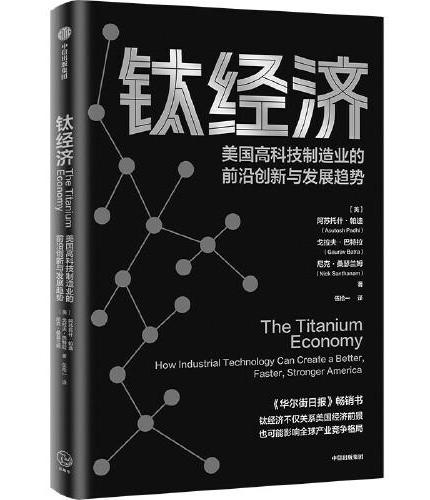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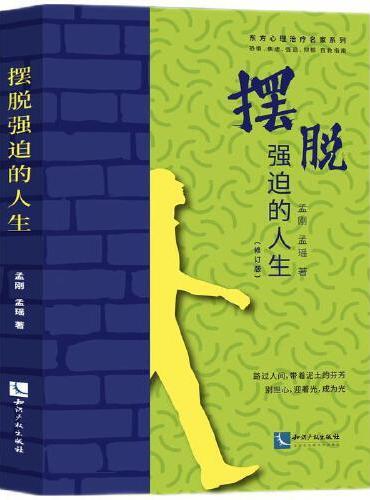
《
摆脱强迫的人生(修订版)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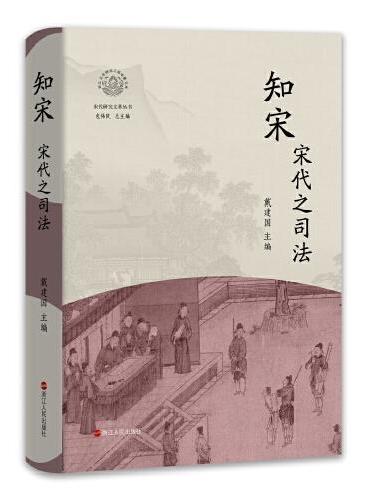
《
知宋·宋代之司法
》
售價:NT$
454.0

《
空间与政治
》
售價:NT$
398.0

《
少年读三国(全套12册)
》
售價:NT$
2234.0

《
不完美之美:日本茶陶的审美变革(知名茶人李启彰老师器物美学经典代表作 饮一口茶,长一分体悟与智慧 制一件器,生一曲手与陶土的旋律 不借由任何美学架构来觉知美)
》
售價:NT$
398.0

《
现代化的迷途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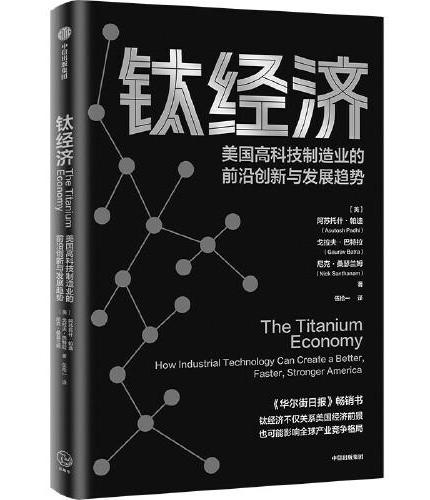
《
钛经济
》
售價:NT$
352.0

《
甲骨文丛书·无垠之海:世界大洋人类史(全2册)
》
售價:NT$
1469.0
|
| 編輯推薦: |
媲美《歌德谈话录》,无所不谈,指点人生,真情与智慧流露,前所未有地呈现一个真实而立体的卡夫卡!
1. 卡夫卡与忘年交的谈话记录,媲美《歌德谈话录》。
2. 从文学艺术到为人处世,从思想困境到社会现实……布拉格街道上和办公室里无所不谈的交流,真实记录下卡夫卡思想的闪光点和人生境况。
3. 北大德语系教授、资深翻译家赵登荣经典译本,著名学者、卡夫卡研究权威叶廷芳专文导读。
4. 特别收录卡夫卡罕见画作与详尽卡夫卡年表。
5. 赠送主题明信片,展示卡夫卡生活剖面。
6. 纪念卡夫卡去世百年,著名设计师廖韡倾情设计,再现卡夫卡精神。
|
| 內容簡介: |
1920年的一个春日,热爱文学的少年雅诺施被父亲引荐给一位同事,眼前这个身形高瘦、面带苦笑的中年男子便是《变形记》的作者卡夫卡。在此后的两年多中,两人结下深厚友谊,结伴而行的身影漫步于布拉格街头,他们的对话无所不包,文学艺术、为人处世、思想困境、人生难题……作家的生活有了难得的情绪和思想宣泄口,而少年的成长有了引路人。
这是一部足以媲美《歌德谈话录》的杰作,真实记录了卡夫卡晚年的生活状态,他的话语中直接体现着他对世间万事万物的真知灼见,一个情感饱满、形象立体的真实的卡夫卡立于眼前。
|
| 關於作者: |
|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作家。生于布拉格犹太商人家庭,与父亲关系始终不睦。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08年起任职于工伤保险公司,并开始发表作品。1924年病逝于维也纳。作品多呈现小人物在社会重压之下孤独、苦闷、恐惧而又不甘屈服于命运的生存状态,文字简练,风格冷峻,但因作家丰富而玄奥的思想,留下可供多样化解读的巨大空间。卡夫卡对后世影响深远,被奉为“现代主义文学之父”。代表作有《城堡》《审判》《变形记》等。
|
| 內容試閱:
|
译本序
叶廷芳
在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作家日常的言论由别人记录成书而成为名著者究竟有多少?恐怕很难说得准。但在提及这类书籍的时候,其中有一本大概谁都不会忽略,那就是由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歌德是德国文学史上的“诗中圣哲”,他的言论被人们视为至理名言是不难理解的。但无独有偶,同属于德语文学的另一部谈话录,即由古斯塔夫·雅诺施记述的《卡夫卡谈话录》,数十年来正随着谈话者的名字蜚声国际文坛,而且在《歌德谈话录》新译本(选编)在我国出版仅仅十三年之后的 1991年,其首译本也已在我国问世。如同《歌德谈话录》体现着作者在“阅尽人间春色”之后的晚年,亦即在他思想最成熟阶段的智慧的结晶一样,卡夫卡的这部《谈话录》也是在他的晚年,在他“纵览”了一遍世界,即思考了一辈子人生真谛后的产物,全面反映着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从中可以看到这位貌不惊人的“鬼才”的许多真知灼见或思想火花,人们现在经常引用的一些卡夫卡的著名观点,许多都出自这部书。可以说,如果没有卡夫卡的这部《谈话录》,则尽管有他那许多半自传性的长短篇小说和大量书信、日记,他的性格特征和思想风貌也不如现在这样全面而丰富。因此这部书的诞生和存在进一步加强着人们对德语作家的这一印象:作家兼哲人的品格。
或许有人会问:在谈论《卡夫卡谈话录》的时候,难道有必要与《歌德谈话录》相联系吗?难道前者的重要性堪与后者相提并论吗?这样的疑问如果出自一个对卡夫卡还不甚了解的读者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对卡夫卡是有所了解并对西方现代文学的要义有所领悟的话,那么你就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肯定性的回答。诚然,卡夫卡的年寿只有歌德的一半,而且作为业余作家,就知识之渊博、作品之丰富而言,他确实是不可与歌德同日而语的。但是,凡具备一定的文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作家存在的特殊价值,主要的并不取决于其知识积累的程度和作品的多寡,而取决于他对时代的独特贡献。而这种贡献,就看他对他的时代的某种潜精神的洞见,并通过文学手段对之做了预言性的、启示性的表达。无疑,歌德作为德国古典文学鼎盛时期的代表,在这方面的成就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他的作品不仅属于他的时代,而且也开启了未来,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还汲取不尽他那丰富文学遗产中的艺术养料。卡夫卡,这个不幸的犹太人,由于自己的血统而深深感受到是被排斥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无家可归的异乡人”,他仿佛站在世界之外,以“异乡人”的陌生眼光和惊讶神情观察人类社会,发现这个亲亲热热、熙来攘往的社会表面,掩盖着一种可怕的东西,一种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异己的东西,人人参与其中而又人人受其控制。于是他满怀恐惧,发出惊叫,一种凄厉的、大难临头似的绝望的喊叫。起初多数人对于这种声音不以为然,充耳不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人们变得清醒些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卡夫卡对那些异常现象的揭示,那种警报性的“喊叫”,日益领悟了,共鸣了,以至把卡夫卡的作品视为“现代启示录”。于是,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家,一跃而为现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并被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父”,从而获得了传奇性的色彩,成为20世纪国际文坛爆出的最大的冷门。有人甚至认为,“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堪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相提并论”。如果说这些评价不过是些专家、学者的看法,那么,1985年西欧五个文学大国英、法、德、意、西的诸家重要报纸联合举办的“已故十大欧洲作家”评选的结果,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上述看法的普遍性和群众性。根据那次评选揭晓的名单看,卡夫卡被排在“十大”的第五位,名列莎士比亚、歌德、但丁、塞万提斯之下,而在托马斯·曼、普鲁斯特、莫里哀、乔伊斯、狄更斯之上。当然,有时候时代是会错爱一个人的,那么,就由历史去下最后结论吧。但在历史下最后结论以前,我们把两者做这样的比较,该不会是无稽之谈吧。
在我们把德国文学史上这两位大师相联系的时候,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卡夫卡作为以“反传统”出名的“现代派之父”,不仅不反歌德这位最重要的德国古典作家,相反,他是歌德最热烈的崇拜者。在他大量的书信、日记中,被提及最多的就是歌德,在一篇日记里他写道:“一星期之久都沉浸在歌德的氛围里。”卡夫卡之所以推崇歌德,主要是因为他认为歌德的作品有一种“持久性的艺术”。应当指出的是,卡夫卡崇拜歌德并不是表现在把歌德单纯当作偶像加以顶礼膜拜,而是把歌德的杰出之处例如艺术的“持久性”切切实实贯彻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了,无怪乎他那些生前并未激起普遍反响的作品,具有那么大的“后劲”,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征服着越来越多的读者,越来越广大的地域。这一事实说明,卡夫卡是歌德艺术遗产最好的继承者。但歌德的艺术之所以具有“持久性”,关键性的一点是强调自己的创造。这一艺术要旨,卡夫卡也牢牢把握住了。在1912年2月8日的日记里,他单独记下歌德的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我对创造的兴趣是无止境的。”显然,卡夫卡对前人遗产的继承与其说停留在被动的接受上,毋宁说表现在对它的精神的把握上。如果说,卡夫卡不跳出前人的雷池,根据自己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关心当代人的根本命运,并善于相应地捕捉时代的新的审美信息,那么,卡夫卡的作品是不可能打动今天的读者的心灵的。可见,对于任何作家来说,创造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只懂得依样画葫芦地继承前人、仿效别人的作家是不会有前途的。卡夫卡在这方面与歌德是一脉相通的。
…………
1920年3月底的一天,我父亲在吃晚饭时要我第二天上午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我知道,你常常逃学,到市立图书馆去。”他说,“明天到我那儿去一趟。穿整齐像样点。我们去见个人。”
我问,我们一起到什么地方去。我觉得,我的好奇让他高兴,但他没有说到哪里去。“别问,”他说,“别好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快中午时,我来到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四楼我父亲的办公室。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我一番,打开写字台中间那个抽屉,拿出一个上面写着“古斯塔夫”几个美术字的绿色公文包,放在自己面前,然后又打量了我好久。
“你干吗站着?”他过了一会儿说,“坐下。”我脸上紧张的神情使他狡黠地微微皱了皱眉头。“别害怕,我不会责骂你的,”他和蔼地说,“我要像朋友对朋友那样和你说话。你要忘记我是你的父亲,好好听我讲。你在写诗,对吧?”他看着我,好像要给我一张账单似的。
“你怎么知道的?”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从哪儿听说的?”
“这很简单,”父亲说,“我们每月付一大笔电费。我研究了耗电量这么大的原因,于是发现你房间里的灯深夜还亮着。我想知道你都在干什么,就注意观察你。我发现你老是写呀画的,写了又撕,或者把它塞到钢琴下面。有一天你去上学时,我看了你的东西。”
“你发现什么了?”我咽下一口口水。
“没什么,”父亲说,“我发现了一个黑皮笔记本,上面写着‘经验集’。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兴趣。但当我发现这是你的日记时,我就把它放到了一边。我不想窥探你的灵魂。”
“可是诗你读了。”
“是的,诗我读了。那些诗放在一个黑色公文包里,取名为‘美好集’。好多地方我不懂。有些东西,我只能说挺傻的。”
“你为什么读我的诗?”我已经十七岁,碰我的东西就是对我的大不敬。
“我怎么不能读你的诗?我为什么不能了解你的诗作?有几首诗我甚至很喜欢。我很想听听行家们的评论。所以我抄下了你的诗,在办公室里用打字机打了下来。”
“你抄了哪些诗?”
“所有的诗,”父亲回答,“我不仅仅尊重我理解的东西。我让人判断的不是我的鉴赏力,而是你的诗。因此我抄了所有的诗,交给卡夫卡博士评价。”
“卡夫卡博士是什么人?你从来没有说过他。”
“他是马克斯·布罗德的好朋友,”父亲解释道,“马克斯·布罗德的书《第谷·布拉赫走向上帝的路》就是献给他的。”
“那他就是《变形记》的作者!”我高喊起来,“这篇小说妙极了!你认识他?”
父亲点点头。“他在我们的法务部工作。”
“他对我写的东西怎么说?”
“他称赞了你的诗。我原想,他只是这么说说而已,但后来
他请我把你介绍给他。我跟他说了,你今天去。”
“这就是你说的去见人的事,是吧?”
“是的,就是去见他。”
父亲带我走到三楼,来到一间布置得很好的大办公室。房间里两张办公桌并排放在一起,一张桌子后坐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他一头黑发向后梳着,大鼻子,窄窄的前额下长着一双漂亮的灰蓝色眼睛,微微苦笑着。
“这肯定就是那个孩子啦。”他说,连句问候也没有。
“就是他。”我父亲说。
卡夫卡博士向我伸过手来。“在我面前您不用害羞。我也交一大笔电费。”他笑起来,我的胆怯消失了。
他就是神秘的甲虫萨姆沙的作者,我心中想道。我看见面前站的是个简朴的普通人,不禁有些失望。
“您的诗里还有许多喧闹,”父亲走出办公室后,弗朗茨·卡夫卡说,“这是青年人的并发症,他们生命力过于旺盛。甚至这种喧闹也是美的,虽然它与艺术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喧闹妨碍表达。但我不是批评家。我不能很快变成什么,然后又很快回到我自身中,精确地测量距离。我已经说过,我不是批评家。我只是个被审判者,是观众。”
“不是法官?”我问。
卡夫卡尴尬地微微一笑。
“我虽然是法庭工作人员,但不熟悉法官。也许我只是个小小的法庭杂役。我没有什么明确固定的任务。”卡夫卡笑了。我跟他一起笑,虽然我不懂他的话。
“只有痛苦是确定的。”他严肃地说,“您在什么时候写作?”
我没有想到他提这样一个问题。我很快回答道:“晚上,夜里。白天很少写。白天我不能写。”
“白天是个大魔术师。”
“光亮妨碍我写,工厂、房子、对面的窗户都妨碍我。最主要的是光,光使我不能集中精力。”
“光亮也许把人从内心的黑暗中引开。如果光征服了人,那很好。如果没有这些可怕的不眠之夜,我根本不会写作。而在夜里,我总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单独监禁的处境。”
难道他自己不也是《变形记》中的不幸的甲虫吗?我心中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想法。
我很高兴,这时门开了,我父亲走了进来。
卡夫卡浓眉大眼,眼睛是灰色的。他褐色的脸生动活泼。他用表情传言。
只要能用脸部肌肉的运动代替话语,他就这样做。微笑,皱眉,蹙起前额,努嘴或撮尖嘴唇,这些都是他代替说话的动作。
弗朗茨·卡夫卡喜欢手势,因此他轻易不用手势。他的手不是伴随谈话的辅助手段,而仿佛是独立的动作语言的话语,是一种交际手段,绝不是被动的反射,而是有目的的意念表达。
十指交叉,或手掌摊开放在办公桌的桌面上,上身舒适而又紧张地后靠在椅子上,脑袋前倾,双肩微耸,把手放在胸口——这就是他有节制地使用的表达手段的一小部分。他在做这些动作时总露出请求原谅的微笑,仿佛他要说:“这是真的,我承认我在做游戏,不过我希望,我的游戏能让你们喜欢。而且—而且我这样做也只是为了争取你们片刻的理解。”
“卡夫卡博士很喜欢你,”我对父亲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因公事认识的。”父亲回答,“我设计了卡片柜以后,我们的来往就更多了。卡夫卡博士很喜欢我做的模型。于是我们就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下午下班后,会在卡林区波德布拉德街上的科恩霍伊泽木匠家‘干几个钟头’。从那时起我们就常谈
私事。后来我把你的诗给了他,我们就成了熟人。”
“为什么不是朋友?”
父亲摇摇头说:“要交朋友嘛,他太胆怯,太内向了。”
我第二次去看卡夫卡时问他:“您还到卡林的木匠家去吗?”
“这您知道?”
“我父亲告诉我的。”
“不去了,我早就不去了。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去。身体陛下不许。”
“这一点我能想象。在尘土飞扬的作坊里劳动不是什么舒服的事。”
“您这就错了。我喜欢作坊里的劳动。刨花的气味,锯子的吟唱,锤子的敲打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夜晚的到来总让我感到十分诧异。”
“晚上您一定很累。”
“我是累,但也幸福。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纯洁的、摸得着的、到处有用的手工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匠活,我也干过农活,莳弄过花草。那些活都比办公室的徭役美好、有价值。表面看来,办公室里的人要高贵一些,幸运一些,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人们更孤独,更不幸。事情就是这样,智力劳动把人推出了人的群体。相反,手工艺把人引向人群。可惜我不能到木匠铺或花圃里干活了。”
“您不会放弃这里的位置吧?”
“为什么不呢?我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工匠呢。”
“您把一切都留在这里?”
“为了到安全优美的地方找到有意义的生活,我愿把一切留在这里。您知道作家保罗·阿德勒吗?”
“我只知道他的《魔笛》一书。”
“他在布拉格,和妻子儿女在一起。”
“他的职业是什么?”
“他没有职业。他只有使命。他带着妻子儿女从一个朋友家到另一个朋友家。他是个自由人,自由作家。在他身边,我总感到良心不安,我就这样让我的生命在办公室里窒息而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