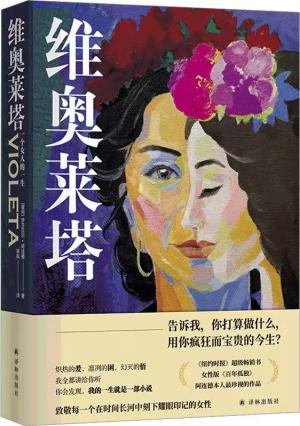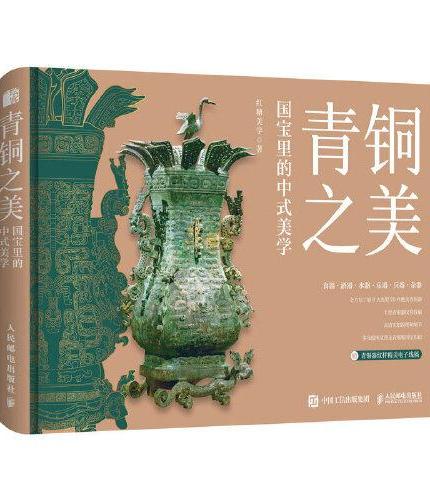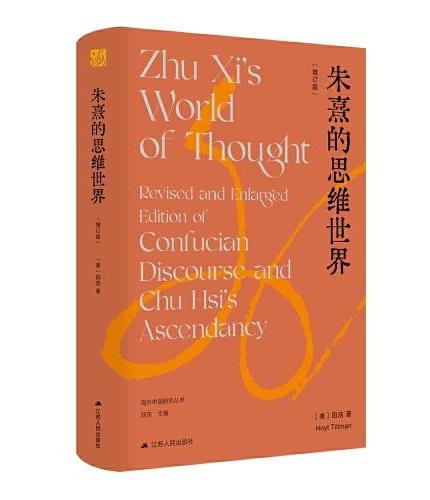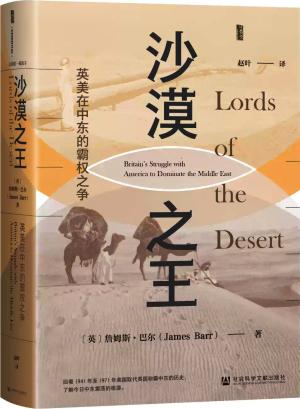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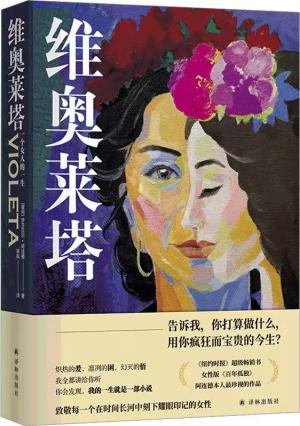
《
维奥莱塔:一个女人的一生
》
售價:NT$
347.0

《
商业银行担保管理实务全指引
》
售價:NT$
658.0

《
信风万里:17世纪耶稣会中国年信研究(全二册)
》
售價:NT$
8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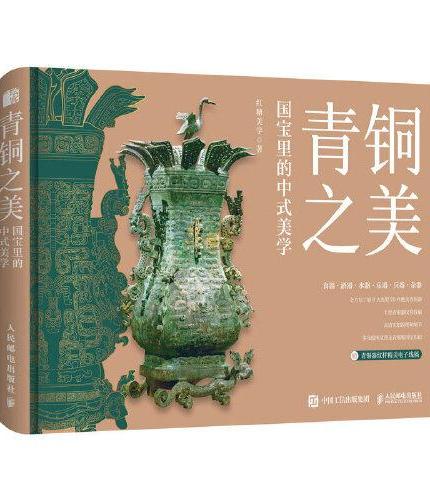
《
青铜之美 国宝里的中式美学
》
售價:NT$
8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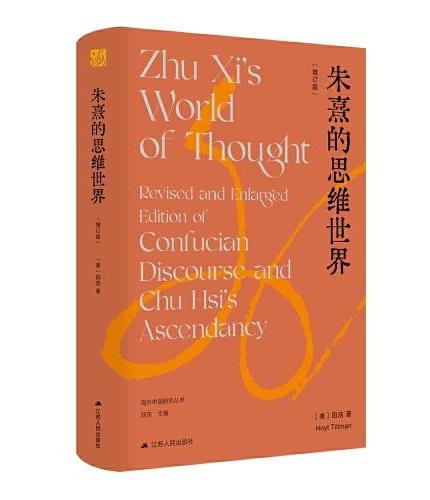
《
海外中国研究·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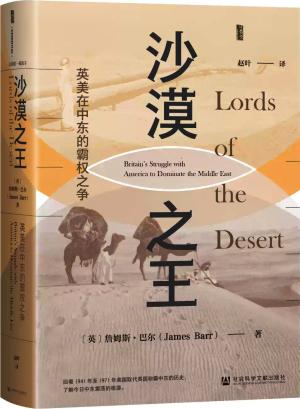
《
甲骨文丛书·沙漠之王:英美在中东的霸权之争
》
售價:NT$
505.0

《
汗青堂丛书147·光明时代:中世纪新史
》
售價:NT$
388.0

《
能成事的团队
》
售價:NT$
510.0
|
| 編輯推薦: |
★本书由海子先生好友孙理波先生创作,回忆与海子先生同在学校任教时的青春岁月、热烈友谊、为文学燃烧岁月的真挚之作。
★名家推荐:
这位海子生命岁月中最重要的朋友和同事,为我们提供了可信赖的能认识和了解海子的极为真实的讲述,我以为最可贵的是,他的讲述既有我们称之为口述史的故事逻辑,更让人感到亲切可信的是,他在还原当时的生活面貌时,并没有以推论甚至想象的方式来描述当时发生过的一切,尤其是他们在昌平的生活,让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那一代人的生活状况,那的确是一个让年轻人怀揣梦想并期待着发生变革的时代。
——当代著名诗人、文化学者 吉狄马加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作者理波是诗人海子的好友,本书为作者回忆与海子同在学校任教时的生活,披露海子很多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纪念曾经的青春岁月、热烈友谊、为文学燃烧的岁月。作者查阅了相关文字材料,并找出了当年的实物、照片,更重要的是仔细查阅了他写了十一年(1977-1988)的日记,并跟与他和海子都熟识的老友多次交谈,了解并唤起了更多记忆中的细节,进而对既有文字中的重要时间节点、人物、事件做了必要的调整与勘误。谨以此书纪念逝去的好友、人们喜爱的诗人——海子。
|
| 關於作者: |
|
理波,本名孙理波,1960年9月生于上海。1979年考入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1983年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讲授《西方法律思想史》,任副教授。2000年后在上海工作,担任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同时,从事现代艺术实验,曾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画展,作品被北京、上海、香港、美国等地收藏家收藏。
|
| 內容試閱:
|
相识在法大
孤独的东方人第一次感到月光遍地
月亮如轻盈的野兽
踩入林中
孤独的东方人第一次随我这月亮爬行
——《孤独的东方人》海子
1983年的春天,雨水尤其多,是那种江南特有的细雨,不打伞也没事,但时间一长,从头发上滑落下来的水珠就像一滴滴泪珠挂在脸上。
3月起,我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实习,带教老师是一位五十多岁、身材微胖的老法官——赵凤岱。之前,他曾是静安分局一个派出所的所长。
某天下午,窗外阴雨绵绵,老赵随手收拾了一下办公桌上的卷宗说:“你们今天就早点回学校吧。”我走出位于愚园路上的法院小洋楼,徒步到两公里外的中山公园,穿过宽大的草坪,公园的北门外,便是华东政法学院。
中山公园北门内的小路旁有块空地,靠墙处有一长溜报栏,我们平时路过时都习惯在那儿浏览一会儿报纸。
记不清是哪张报纸在版面的中间赫然印着一排黑体字,映入眼帘的便是“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成立”的字样。这下我知道了,原来的“北京政法学院”现在改名为“中国政法大学”了,特别是前面冠以的“中国”两字,使一个从未去过北京的青年学生,顿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向往。中国政法大学在公安部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时间是1983年的5月7日,我看到的应该是第二天的报道。
实习结束,回到学校。不久,我果然被分配到了北京,被分配到了法大。对未来,我内心充满一种懵懂的憧憬。“做一名教师仍然是很高尚的事”,记得海德格尔曾这样说过。
1983年8月12日,我们一同被分到政法大学的几个同学约好一起赴京。由于火车票不好买,辗转托人才搞到了几张早上八点四十五分发车,从福州开往北京的45次列车车票。
赤日炎炎、气温如蒸,匆匆上车,放好行李,浑身已被汗水浸湿。火车在嘈杂声中,徐徐离开站台。这趟45次列车是过路车,我们买的是无座票,只能站在拥挤的过道里。窗外的风在列车提速时才能刮到脸上,深深地吸一口气,方感到一丝凉意。直到列车驶过南京长江大桥,我们才陆续有了座,经过二十二个小时的燥热旅途,次日清晨六点,我们终于到达了北京站。
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那年,差一个月,我二十三岁。
毕业前夕的一段时间里,我所在年级的同学都在实习,有些在郊区实习的同学就住在了实习单位,因此学校宿舍楼里有不少房间有空的床位。
有一天,来了几个自称是北京政法学院1979级的学生,他们也在实习,抽空溜到上海玩几天,自行找到我们同学,说想在宿舍里借宿几晚,这样可以省掉一笔旅馆费。晚上,我们好奇地与他们攀谈,也想了解一点他们学校的情况。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一个劲儿地夸我们这个曾经被称为“东方哈佛”的校园,简直赞不绝口。说到他们的校园时,其中一个同学调侃道:“我们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围墙,但门不少;二是学生没人管,自由自在。”我有点儿蒙,想象不出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
有关中国政法大学的情况,除了他们说的,就是我在中山公园的报纸上看到的一些信息,知道了学校实行“一校三院”制,即校部下设本科生院、研究生院和进修生院三个学院,还知道了当时的校长是由司法部部长刘复之兼任,其余则一概不知。
直属司法部的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等五所院校,都是1952年所谓“院系调整”的产物。经历了“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后,这些院校都是几次关门几次复校,用“满目疮痍”来形容它们一点不为过。
“文革”后,北京政法学院恢复招生。1979年第一次招生时,1949年前的老教授们已靠边站了几十年,五十年代的青年教师们也都已人到中年,有的从京郊、有的从外地被陆续召回政法学院。
1989年主政法大的江平校长,当年被打成“右派”后,“文革”期间一直在北京延庆的一所中学里当老师。复校时,被请回学院担任民法教研室主任。1983年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时,江老师是本科生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
五十年代初,在学院路新建的“八大学院”里,法大校园原本就是最小的(也有说法认为“八大学院”中不包括法大),经过二十多年的折腾,校园支离破碎,全部加起来也就八九栋楼。尽管当时已复校四年,依然有多家单位占据其中的几栋,北门则常有外面的马车拐进来,校园的路上不时可以看到马粪,因为三环辅路到法大北门时断掉了,所以马车右拐借道,进入学校从东门出去。
在新盖食堂的边上是五号楼,由北京歌舞团、戏曲团等单位占用。清晨时分,经常能听到年轻学员吊嗓子的声音,崔健成大腕儿之后,大家发现就是当年曾在楼道里练歌、在食堂里挤着买饭的小伙子。
法大校园当时确实没有完整的围墙,学校的大铁门也关不上,斜着用一根木棍支撑着。东西南北,都有门可以自由进出。一号到四号楼是所谓的学生宿舍,我们几个从上海来的同学,到达法大的当天,两眼一抹黑,根本没人管。后来找到了先来的同学,与他们在二号楼的宿舍挤着住下。
我思忖等开学了,应该会安排我们,至少分一间宿舍吧。其实,学校压根儿就没有地方给我们这拨人住。
几天后,校人事处处长告诉我们,学校在北三环西路,大钟寺正对面一条小路(当时没有路名,现在叫四道口路)往南一百米的地方,租了一个小院,作为我们的临时宿舍。
小院是海淀区东升乡大钟寺大队为搞活经济,利用闲置空地新盖的三排东西走向的平房。红砖红瓦,每间十多平方米,南北各有一个窗户,放置了三张单人床,可以住两到三人。
我第一次见到室内朝北的窗户又高又小,有人告诉我,北京冬天风大,“针鼻儿大的窟窿,斗大的风”,所以朝北的窗户必须小,到时还要用纸把窗框糊上。
一扇双开的紫酱红大铁门,进门右侧是门卫、厕所,有一位村里的大爷做门卫,顺便照看院子、打扫卫生;左侧是水房,里面有一个烧水的小锅炉。
大铁门外正对的是大队的猪圈。正值夏天,那股味儿弥漫整个小院,屋里的苍蝇黑压压趴满半个天花板。开学后,学校给每间屋子安了一个纱门,但对面那味儿始终无法消除。
每一排房屋有十五间左右,我和查海生都住在左侧靠北的这排,我在第四间,他在往东朝里的第十间左右。
1982年秋天,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四学生查海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实习,协助法官审理了几个离婚案子,实习结束,回到北京。1983年8月底,他带着一个大木箱和生平第一本诗集《小站》,来到了位于海淀区学院路41号——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政法大学。
查海生从1979年到北大上学,已经在北京待了四年了,分配到法大工作的时候他才过十九岁。
拿到钥匙后,查海生直接把他的行李从北大搬了过来。行李中有一个醒目的大木箱,足有一米二长,本色,没有油漆。
查海生在我们这群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中,年龄最小,个头最矮,圆圆的脸上一脸稚气,留着简单朴实的发型,爱穿一件白衬衫,话也不多,似乎没过几天,在我们中就开始流传他会写诗。
大钟寺小院离学院路校区公交一站地,我们每天徒步沿着三环路往东,过一座铁路桥去上班。我在办公室打杂,没有太多事儿,一般四点左右就回去了,小查一般都会在五点后回来。
先回来的我,时常看见他穿着白衬衫、淡灰色长裤,低着头,一手拎着一个学校发的绿色铁皮暖壶从宿舍那头走出来,路过我的房门,到大门口的水房打开水。那时我们都初来乍到,碰上会打招呼,略微寒暄几句。
过了几个月,住在小院的年轻人便慢慢熟稔起来,有人提议周末聚在一起聊天,还给这种聚会取了一个雅号 “白取乐”,即英文单词bachelor的谐音,意指大家都是大学毕业,有学士学位,又都还是单身,聚在一起聊天消遣。
小查有时也会被邀来“白取乐”,从聊天中,我们对朦胧诗及当时全国各地的所谓“黑道”诗人,开始有了一些了解。大家也知道小查爱写诗,读了不少书。
“残云收夏暑,新雨带秋岚”。9月开学后,院里召集我们这批刚入职的年轻人开会,江平老师是我见到的第一位领导,五十开外,略发福,说话字正腔圆,嗓音浑厚清亮。
应该是因为“北政”变成了“法大”,学校亟须扩充教学、教辅人员。仅以华政就分来了二十多人,加上一起分来的其他院校的同学,共有七八十人之多,查海生、唐师曾都在其中。
《中国政法大学校刊》是一张只有四个版面的小报纸,编辑部原本有两名同事,查海生与另外一位文学爱好者的加入,让这份名不见经传的小报开始有了变化。大家会定期读到一些带有文学色彩的内容,由此校刊曾一度备受学生和青年教师的喜爱。编辑部有时还会组织一些诗歌活动,被邀请来作讲座的著名诗人有顾城、刘湛秋等。在校刊编辑的带动下,同学们成立了自己的诗社,查海生被聘为顾问。
编辑部在学校大门右侧七号楼的底层,我们教研室在二层。上班不久,我时不常地会去他们办公室聊会儿天,他们也需要联络老师和学生给他们投稿。喜欢摄影的唐师曾也经常过来串门,他摄影生涯中发表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刊登在这份不起眼的小报上。报纸还有一个不定期的栏目叫《青橄榄》,我还应约写过五六篇与读书相关的短文,发在这个栏目上。
小查曾用笔名“扎卡”在校刊上发过几首小诗,法大第一本诗集《青铜浮雕 狂欢节 我》中,刊登了他的长诗《北方》和《女孩子》。后来,校刊又编了一本校园诗集《草绿色的节日》,海子在诗集的第57页《双叶草》栏目中,刊登了《感觉》(九首)。我现在想不起来自己为何会用“黎波”之名在其中的《星星雨》栏目,刊登了一首题为《飞碟》(外一首)的诗。
这本诗集出来以后,有人给了我一本,我碰到海子对他说,《草绿色的节日》的这个“草”字,挺别扭的。他朝我看看,低头笑笑,这是他习惯性的表情。
这些年常有人问:“理波,你写诗吗?”
其实,我对这本诗集早已忘得精光。直到有一年在北京,一位当年的学生给我看这本集子的照片,我才想起有这档子事。当年在法大,有不少人写过诗,后来都因为有了海子,几乎再也没有人自认是诗人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诗人消灭了诗人”吧。
从那时起,小查开始使用“海子”这个笔名。从此,他多了一个名字。
现实中,他其实有三个名字,查海生、小查、海子。在法大工作关系中,年长者一般都连名带姓地叫他全名;年龄相仿者则一般叫他小查;知道他写诗而且关系比较熟的会喊他“海子”。
在我们认识的头两年中,我称呼其“小查”远多于叫“海子”,后来慢慢认同了他的诗人身份后,越来越多的时候会叫他“海子”,感觉他也很喜欢别人这样称呼他。
他不在场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聊天中提到他,还会称 “小查”。小查、海子,这两个名字似乎内涵有些不同,尤其是在不同人的嘴里。
称谓的变化也是人际关系的变化,其中会隐含某些微妙的感觉。那些年龄比他大几岁的法大人,很长时间都是认为这个“小查”就是一小屁孩儿,因为他不仅个子不高,年龄也确实小。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每次提到海子,还是叫他“小查”。直到近些年,我才发现他们慢慢改称“海子”了。
第二年的春天,我们住的大钟寺小院开始有传言,“小查有女朋友了”。大家没太当真,因为他年龄太小,小到甚至比同住一起的人小了近十岁。自从有了这个传闻,我发现有人见到他时会逗他,他则低头不语,抿嘴一笑。
也是从那以后,我开始知道,该女生1983年入学,是刚成立不久的经济法系的学生,他们是在那年寒假前的学生诗歌活动中认识的。转过年来,1984年上半年的春天里,两人渐渐进入“恋爱”季。就在此时,在校办工作的一个同学,在校园里碰上,笑呵呵地告诉我,“小查‘以文会友’,有女朋友了”。
那年,海子写了一首《爱情的故事》:
今天夜晚
语言秘密前行
直到完全沉默
临近暑假的时候,传言我们要搬到昌平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