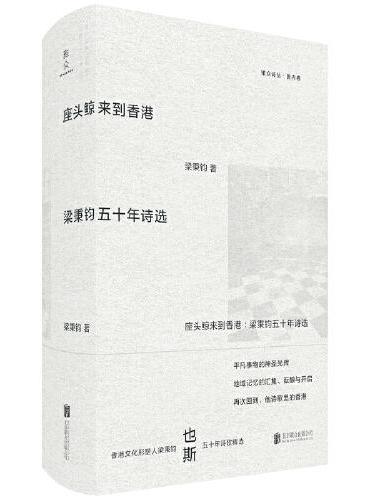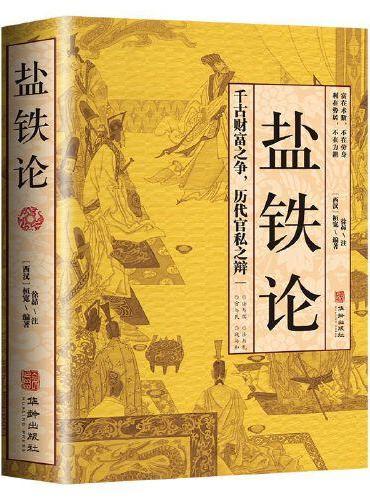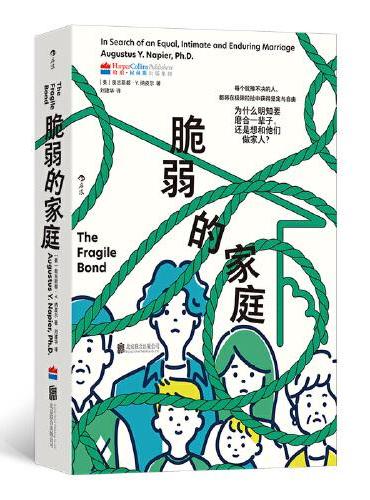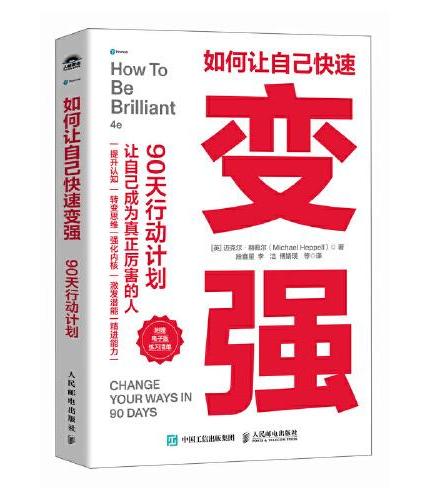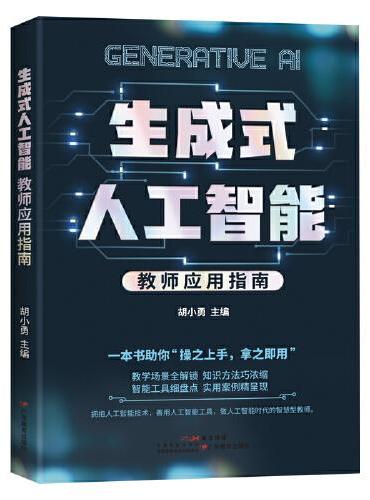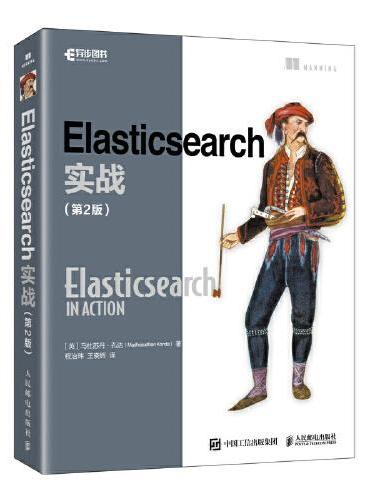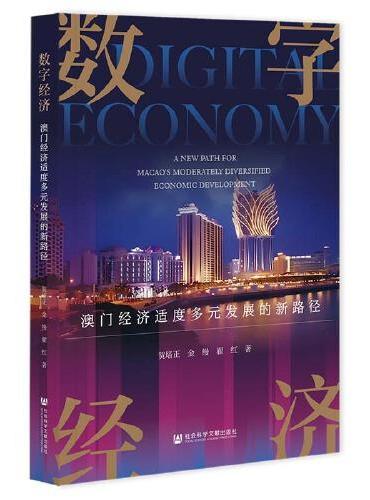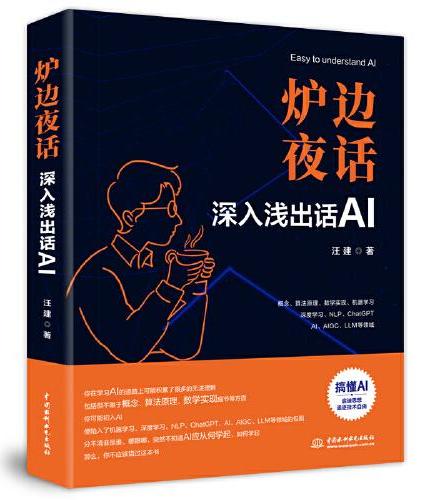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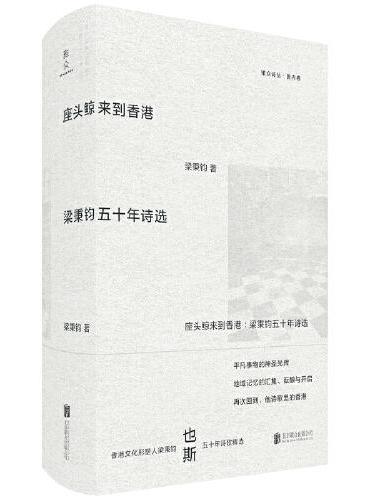
《
座头鲸来到香港:梁秉钧五十年诗选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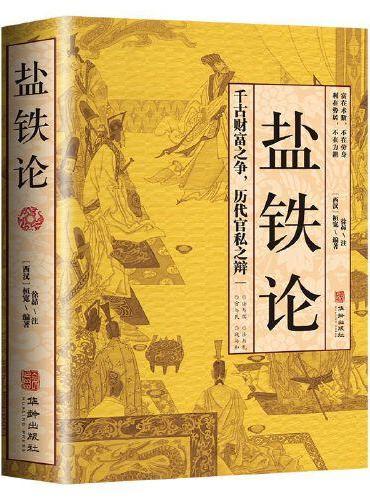
《
盐铁论 原文+注释+译文白话桓宽著 一场政治与经济的纠纷经济书籍经济理论中国古代官场政治制度经济学军事谋略辩论博弈智慧书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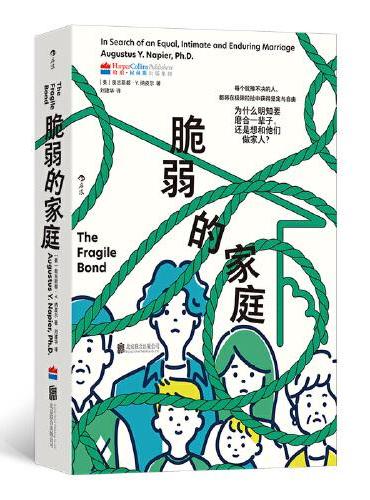
《
脆弱的家庭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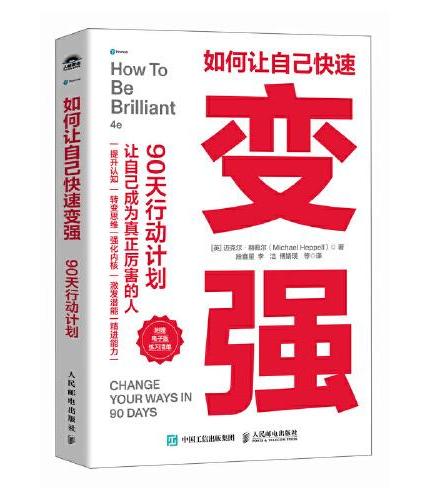
《
如何让自己快速变强90天行动计划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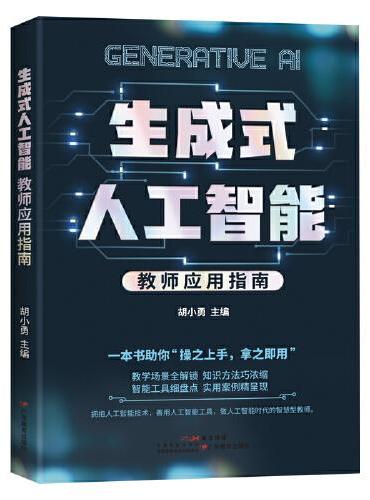
《
生成式人工智能:教师应用指南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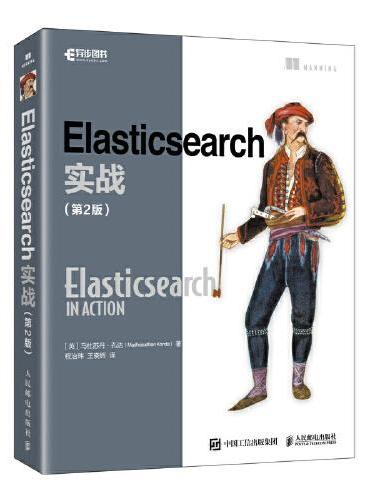
《
Elasticsearch实战(第2版)
》
售價:NT$
66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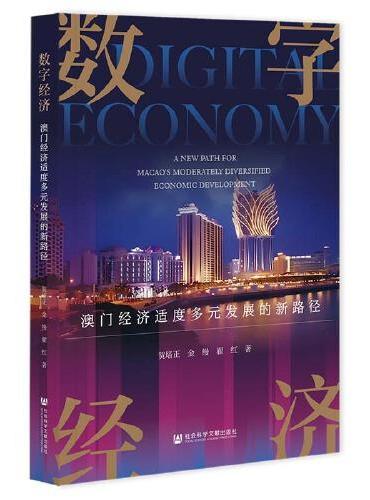
《
数字经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路径
》
售價:NT$
7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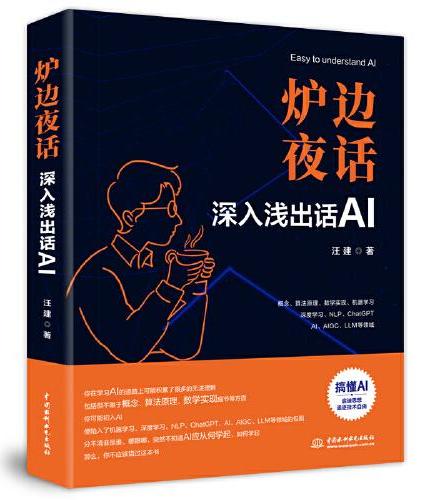
《
炉边夜话——深入浅出话AI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本书卖点
1.导演读文学、看电影的心得,艺术爱好者的掌中小书。《晶报》总编辑胡洪侠、巴塞尔艺术展策展人李振华、艺术批评家寒碧联合推荐!
2.作者兼具“作家”与“导演”双重身份,为《晶报·深港书评》2018年度十大好书得主,实验长片《满洲里来的人》被国际电影杂志《银幕》称为“中国电影新声”。
3.除了电影之外,作者还旁涉对文学、摄影等领域的思考,可见作者见识广博,文字信手拈来,阅读门槛较低,适合大众阅读。
4.开本小巧,设计精致,护封典雅清新,里封又极富电影质感,适合在睡前、在旅途中、在某个闲暇的日子随手翻开。
编辑推荐
1.《电影漫游症札记》的姊妹篇,是作者关于文学与电影、摄影、书法的感受。
《深港书评》十大好书得主、“中国电影新声”之作导演、《字花》杂志“电影书写”专栏撰稿人……作者身兼导演、影评人和写作者身份,如何给读者讲述他的私人记忆和感悟?旅行、记忆、孤独,又与怎样的人生处境相关?书桌前的你,面对塞巴尔德、贝尔纳·弗孔、罗伯特·卡帕等人的文学、电影作品,是否也有着同样的漫游感受?
2.文字明白晓畅,适合大众阅读。
3.设计富有电影质感,与内容相呼应,适合
|
| 內容簡介: |
唐棣,身兼导演、影评人和写作者身份,游走于文学、电影、艺术等众多领域,谈论旅行、记忆、孤独等多个文化主题,均与人生处境密切相关。作者每每将多个同类主题的文学、哲学与影像内容串联交织,使不同的思想和观点跨界对话,彼此振荡,从而引入对相关主题的深度思考。
关于旅行、想象、未来,关于虚构与真是、距离与焦点,关于摄影、书法,……在唐棣的世界,体裁只是外在的,他用心地生活,思考,一次又一次地穿行在关于想象和艺术的场景中。
|
| 關於作者: |
唐棣,1984 年 生 于 河 北 唐 山。 2003—2008 年 写 作;2008— 2015 年拍照片、短片;2015—
2018 年从事影视编导、新媒体艺术创作;2018—2023 年在《字花》(香港)、《天涯》杂志开设《电影书写》《法国电影新浪潮小史》专栏。
2009 年起摄影、影像作品开始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波兰文化中心及成都、重庆、香港等地艺术机构展出。
|
| 目錄:
|
目 录
4? 引言
1? 卷一
3 想象:旅行启示
35 过去:事实角度
48 承诺:词语之声
64 复现:回归想象
70 追寻:身份焦虑
82 形式:隐逸之谜
95 密度:记忆未来
107? 卷二
109 虚构:真实故事——贝尔纳·弗孔的图像世界
120 距离:焦点问题——罗伯特·卡帕的战地摄影
128 传奇:思想之眼——亨利·卡蒂埃 – 布列松的摄影与逃离
137 时间:艺术过程——罗兰·巴特论艺术
147 新事物:神秘摄影——慈禧与中国近代摄影技术
160 长镜头:视觉实况——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24 帧》拉片笔记
178? 结语
183? 附录? 书写的目的
|
| 內容試閱:
|
引言
2020 年 3 月,北京。我一个人走出小房间,来到街上。行人不多,车辆更少,每一个声音都显得比平时刺耳。我记得那种淡金色、有点刺眼的阳光,扎扎实实地把曾经拥挤的街道铺满。街道在阳光里,显得落寞而空旷。那也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在走路时留意到脚下的影子。艺术史教授维克多·斯托伊奇塔在《影子简史》里说:“当人的影子第一次被人用线条勾勒出来时,绘画诞生了。”故事的背景是男友要去打仗,很可能回不来了。临别时女孩用跳动的油灯光,把男友的侧脸投射到墙上,然后用画笔勾出形象,这样就可以对着墙壁上的轮廓表达思念。
艺术是什么,可能很难说清。但它具有保存、寄托人的情感的作用,这是肯定的,如同科学可以让人们认识自然界的原理一样重要。在我这里,影子还是影响的隐喻。创作者的工作就是在作品与现实之间(有时也是作品之间)找到这种既发生在自己身上,又能连接他人(阅读、观看、思考),既深藏不露,也象征变动,甚至很可能带来恐慌的关系。
这次外出的目的地是一家艺术书店。我到书店时,书店所在的那层一个人也没有。我拿起一本书坐下后,就被书里描述的一个空间吸引了:在高高的探照灯正下方,是一个没有窗户的空间,里面只有一张操作台、一把扶手椅、一部用来消遣的收音机和几本书,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本“值班日志”。每隔十五分钟,值班员要在上面记下当时的天气、海面状况、灯光装置的可见度、船只经过的情况、储备情况、养护工作、意外、事故、灯塔工介入处理的情况等。在这里做出的每个决定都是孤独的,却又都影响着航线的选择、航向的变化……不知不觉翻完这本《灯塔工的值班室》,抬起头,附近有了三两个人,阳光也已经褪下去了。
以前,我不知道如何描述那种谁都能接收到的,毫不特殊的,又能和看起来深刻的艺术相关的情绪。就在这时,我想到了“孤独”。普通人会把它当秘密,生怕外人知道。艺术家不这样,他们视孤独为宝藏,拼命折腾,享受揭开它的过程。我们在生活中并不常用这个词,但每个人一听就懂。现代世界,谁不孤独?这可能就是艺术存在的意义。所以,写艺术也是一种面对,如同意大利文学评论家卡斯特尔维特罗所说:“对艺术的欣赏,就是对克服了的困难的欣赏。”(《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诠释》)
追寻:身份焦虑
苏珊·桑塔格说:“小说的结局带给我们一种解脱,一种生活无论如何也不愿给予我们的解脱:一切都彻底结束了,但这个结束不是死亡。”这句话正好可以用在作家W.G.塞巴尔德身上。虽然摆在了开篇,但最早我并不是很理解这句话的深意,只是凭直觉抄写下来。后来,我对这份直觉的确认来自英国作家杰夫·戴尔,他在《塞巴尔德、轰炸和托马斯·伯恩哈德》一文的开头写到塞巴尔德的书,说“它们总是有一种死后的感觉”。
2001年12月中旬,东英吉利,大雪纷扬,一条乡下公路上,一辆疾驰的车在急转弯处失去控制,与一辆卡车迎面相撞,塞巴尔德因此丧生……两个月前,准确地说是2001年10月15日,塞巴尔德还在美国著名文化中心与桑塔格并肩而立,大谈自己的作品:《晕眩》《移民》《土星之环》《奥斯特利茨》塞巴尔德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成长于瑞士、英国、德国之间,属于二战幸存者后代。“二战”也是他在几本书中萦绕不去的主题。战争造成的伤害、针对族人的屠杀、犹太人背井离乡的悲惨场景,直接构成其处女
作《眩晕》的主题“战后父子关系”;《移民》里的“移民”也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概念,而是“移动的人民”的意思。可以说,塞巴尔德大部分作品的用意都在于描写人经历重大历史事件后精神上的转变。作为犹太裔作家,这种情绪与集体屠杀的历史密不可分。死亡气息伴随着他的成长,对“二战”这一历史文化记忆的反思,可以说是一种出于记取的本能,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问题。
“记取”这个词,来自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认取”。费孝通谈到语言的时间性时写道:“‘记’带有在当前为了将来有用而加以认取的意思,‘忆’是为了当前有关而回想到过去经验。事实上,在当前很难预测将来之用,大多是出于当前的需要而追忆过去。”“认取”有一部分非常私人。这体现出塞巴尔德写作的另一面,这一面让读者看到一种带有罪恶感的“局外人”风格。
同为犹太人的知识分子斯坦纳,在谈话录《漫长的星期六》里有一段专门谈到罪恶感、局外人的感觉:“我想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理解这件事。我们没法理解。我们唯一能感受到的东西就是,这里面有偶然性……非常神秘的偶然性。”局外人都活在一种“可耻的幸运”之中。身份焦虑问题,和我们这些现代读者又有什么关系?
首先,我确信这种关系出现了从文化层面到现实生活的变体,比如我在一部美国的青春电影《微型家具》里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刚大学毕业、找了一份餐馆服务生工作的女孩,和朋友聊到餐馆里很帅的一个男厨师。朋友告诉她,有一次自己看到他坐在一堆洋葱上面看《奥斯特利茨》。那一刻,我有些诧异。因为没想到,塞巴尔德文学的焦虑,和一个美国年轻人步入社会的焦虑如此相近——当然,我也知道它们不同。我是想说,身份转换给这个女孩带来迷惘,这个情节非常真实,也让这部电影变得好看。从一个大学生到一个社会人,电影里的女孩很明显找不到自信和节奏,这反映在两个女孩之间的对话上,真实的迷惘特别牵动人心。
身份问题从《眩晕》延续下来,贯穿了《奥斯特利茨》(写一名犹太男孩探寻自我身世,揭露一段悲恸的个人史、家族史和整个欧洲的黑暗岁月)全文。这已经不能算一个新问题。西方作家从来不想弄懂别人,一生都在为“我是谁”创作的人不在少数。例如,小说家莫迪亚诺的《暗店街》里,私人侦探于特的工作就是帮失忆的居伊寻找身份。到了塞巴尔德的笔下,追寻就是字面意思,他的书都是写旅行,或者寻亲的故事。
《奥斯特利茨》也不是一部很有名的小说——书名隐喻了一个典型的犹太人名和一场著名战役,还与尽人皆知的“奥斯维辛”发音有些相似……塞巴尔德的书里有太多对身份追问以及犹太文化的思考,对读者并不友好。我对那段历史没什么感觉,所以最初拿到这本书时,读了几页就放下了。
我看纪录片《奥斯特利茨》时注意到一个直观场景,可以说它是一个“纪念馆”式的呈现,因为历史的干扰过多,导演选择以一种近似“偷懒”的视角,不展示监狱里的任何场景,而是用1小时33分25秒的镜头,扫视年轻参观者——我不想称其为“游客”——的状态。导演的意图明确,就是在提醒我们:历史过去了,现在的人才是重点。一个地方因为“某种历史”的痕迹获得被观察的可能,电影里参观的年轻人,甚至脸上还带着微笑,启示很多。
人们认知里的那部分历史,可能只是一段公众历史(也可以称为大写历史,更多朝向过去,后代的历史研究者倾向于诉说它日渐消磨的历史价值。它像一段古老的记忆,被纪念、翻阅,用来警示当下)。纪录片里的参观者,无论为何种理由而来,是否都意味着一种“正视”?在监狱铁门上有一行字:“劳动创造自由。”这个镜头在纪录片的开端和结尾都出现了(开始是从监狱里向外,结尾是从外向内),与之一同出现的是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年轻人。自由,这个词语格外醒目。这种对比似乎也唤醒了在一个不自由的“历史想象”之中的“自由想象”(这个想象是当下的一个幻觉,其含义似乎还有待深刻挖掘)。
我和国内的出版人提过一个看法:“塞巴尔德的意义,在于他对新一代作者文体上的提醒。像1980年代先锋作家一代的回忆里,出现最多的一部作品是《百年孤独》,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到塞巴尔德的《移民》出版时,这种特征已经非常鲜明。可以说,塞巴尔德写作就没有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所以阅读也不会被体裁的枷锁和对大历史的排斥之心所束缚。
后来,我拿上“这把钥匙”重读《奥斯特利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有时候是为了去做研究,有时候也是出于连我自己都不太清楚的缘由,我从英国出发,多次前往比利时……
——《奥斯特利茨》
塞巴尔德是小说家、随笔家、哲学家,甚至是摄影家(他的书中有很多他拍摄的照片)。插入图片是塞巴尔德作品的一个标志,“所有的照片都是一种运输形式,也是一种对缺席的表示”。约翰·伯格的话,一方面指明了塞巴尔德对其描述的事物的一种心态,另一方面也说明照片为叙述提供了“真实感”。罗兰·巴特在某次访谈里说:“描述根本不能让人看到什么,描述属于纯粹的可理解性范畴,并因此与所有图像有所差异,因为图像只会妨碍描述、扭曲描述。”
这么做也让文本呈现出的东西变得暧昧。读者不得不从无可争辩的角度进入他的描述,比如“旅行”的寓意:无论从政治、文化,还是自身与周遭的疏离关系上看,大部分都始于逃离(离开某地)。最终,他通过对目的地景观的描述,追寻的还是对始发地的一种复杂情绪。
在《土星之环》结尾,他写道:“荷兰有种风俗,死者家中所有能够看见风景、人物或者田野里果实的镜子和图画都要盖上真丝黑纱,这样一来,离开肉体的灵魂在他们最后的旅途中就不会受到诱惑,无论是因为看到自己,还是因为看到即将永远失去的家乡。”
我们可以把“复杂情绪”理解成一种“现代人的乡愁”,包括厌倦、思念、质疑以及留恋。塞巴尔德文字的感染力,可能来自照片的确定性。很多张出现在书中的照片,都呈现出一种荒凉的场景:类似《小雅·我行其野》里的“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纠结着关于真实的想象。纳博科夫就说:“能讲述真相的只有虚构。”而塞巴尔德似乎又想抹掉虚构的标签,他写的都是人在旅行中收获的实在情感。情感可能就是他认为的真相吧,他的作品都是在下面这种行文基调上展开的:
一九八〇年十月,在英国一个总是灰云密布的郡居住了将近二十五年后,我来到维也纳,希望地点的变换能帮我度过那段特别困难的岁月。
——《眩晕》
一九七〇年九月底,在我于东英吉利城市诺里奇任职前不久,我同克拉拉一道出城去欣厄姆寻找
住所。
直到二十二岁时,我还从未去过离家超过五六个小时火车路程的地方,所以当我出于种种考虑,
于一九六六年秋天决定移居英国时,我对那儿是什么样子,对我只能靠自己挣钱过日子,在异国他乡
要怎样才能适应环境,几乎都没有充分想过。
——《移民》
一九九二年八月,当热得像狗一样的盛夏时节渐近尾声,我开始了徒步穿越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旅程,希望在一项较大的工作完成后,能够摆脱正在我体内蔓延的空虚。
——《土星之环》
如果说《眩晕》是一次“逃离之旅”,《奥斯特利茨》是一次“追忆之旅”,《移民》是一次“追悼之旅”,那么《土星之环》就是一次“修复之旅”,它的行文涌现了大量对记忆的反思,或者说是对“历史”的探讨——“我忙着回忆美好的自由自在,也忙着回忆令人麻痹的恐惧,它们以各种方式向我袭来,因为我看到即便在这一偏僻的地区,也有着可以向过去追溯很远的破坏痕迹。”对于经常着墨于同一主题,塞巴尔德曾借书里人物托马斯·布朗的嘴,简单解释了一下:“每一点知识都被不可琢磨的模糊包围着。我们所感知的,只是无知深渊中的、被深深阴影笼罩着的世界大厦里的数缕光芒。”塞巴尔德笔下的人物,通常带有鲜明的反思情绪,某种程度上可能都是一个不断出行,面对记忆,又被记忆把意识变得模糊,在深夜的床上产生幻觉的人。“不可琢磨的模糊”就像书中的情绪一样,不易界定,难以平息。“……叙述的可靠性越是减弱和降低,它的确会越是吸引人不断地去证实其可靠性。”(杰夫·戴尔《人类状况百科全书》)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不限于一种事物(当然基本的用字准确也是必需的),而是呈现一种事物
与另一种事物之间互相遮挡的部分,以此激起联想——西方现代派写作多是走这条路径。这些严肃的写作,除了跟作者的身份有关,还有一部分来自其语言系统。那种结合了片段(“段落感”)与长段落(“绵延的叙述”)的特殊文体,产生了某种效果。
我的说法是,叙述像打开了一道闸门,随着人物旅程的继续,回忆纷涌而来。其实,那些回忆都是碎片式的,以时间、地点,以及书籍、饰物等为转接道具。塞巴尔德的迷人之处在于,他对写作有一种让人很想去解释的信念:“如果写作过程过于艰难,完成的书对他而言就像是已被遗弃的孩童,如此一来,往事不免受个人的道德观所浸染。而作者们总是对手头的作品一筹莫展,害怕自己无力完成它们;也是出于此等恐惧,作者们才不愿意回忆那些作品,因为这难免会使他们产生一种本有能力早些将之完成,却力有不逮的想法。他又说,由于写作是件缓慢得令人感到痛苦的行当,所以他最珍爱的是那些少之又少的可以一挥而就的片段……”
《眩晕》的译者在同一篇文章继续写道:“塞巴尔德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如何一气呵成地写下了这个名为《归乡》的章节,彼时,他散漫地逗留在希腊的一座小岛上,既无书可读,也无报纸可看,陪伴他的只有手边的稿纸与铅笔。这个时刻,就是塞巴尔德现实的一刻,其实他很少描述现实。最后他讪然一笑,说这是他短暂写作生涯中最自由的时刻,此后他再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至福。”
塞巴尔德躺在椅子上,陷入回忆中。
我感到风拂过我的额头,地面在我的脚下晃动,我将自己委身于一条意念中的船,它正在离开洪水淹没的群山。然而,除了建筑变成木船,克鲁门巴赫圣堂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描绘苦路的画作,它必定是出自十八世纪中叶某只不甚灵巧的手,一半已遭霉斑覆盖、吞噬。我在高处看到的一切都是白垩色的,一种明亮耀眼的灰,无数石英碎片闪烁其中。这给我留下了奇异的印象,仿佛岩石也在放光。从我的位置看,
沿着这条路往下走,远处还有第二座至少与第一座一样高的山,我预感自己无论如何都攀越不了。我的左边有一道真正令人眩晕的深渊。
——《眩晕》
这样的引用让我意识到,眼前看不清的事物依然很多。《眩晕》在叙述上的问题,恰恰也出在这里。相对于后三部作品,他的处女作在叙述上的推进是盘旋式向上的,而非向前的。“眩晕”的命名,可能来自围绕一个点的不断描述(塞巴尔德娴熟地运用了各种文体,如书评、电影、论文等,将描述嵌入主故事线)。这样的问题在《移民》到《土星之环》的写作过程中都已经慢慢解决了。在后来的阅读中,可以看见塞巴尔德熟练地运用“记忆”写文章,但他还不是普鲁斯特。塞巴尔德的记忆具有更大范围的空间感(毕竟是在旅途中,而普鲁斯特大部分时间局限在床上、房间里)。不可否认,艺术家的工作顶多是在记忆的苍穹之下,寻找自己的星光而已,“那不是漆黑的暗夜,而是像一个有着星光的夜晚”(贡布里希《世界小史》)。带上这个想法,再进入塞巴尔德“隐喻与模拟泛滥,构造了迷宫般的、有时长达一两页的句子”(《土星之环》)中漫游,总有惊喜。
对他来说,记忆是一种能量,它能推动故事、情绪的发展,为读者营造一种静谧的氛围。《土星之环》里有一句说的就是我的感受:
夜晚,这令人惊异的、对于所有人而言的陌生者,在山顶上方哀伤而闪亮地流逝。
一个既现实又抽象的感受,“这形容的,分明是记忆”。我心想。此外,还有一段关于“星空”的描述,也是塞巴尔德躺在椅子上仰头望向天空时记下的,它出现在《眩晕》里:
在多年前的这一天,更确切地说,是这天夜晚,卡萨诺瓦嘴里说着“然后我们走出去,凝视群星”,
从那条鳄鱼的铅制盔甲中挣脱。而我自己,在十月三十一日的那个傍晚,吃过晚饭后又回到河边的酒吧,跟一个名叫玛拉基奥的威尼斯人聊天,他曾在剑桥大学学习天体物理。我很快发现,他看待一切事物,不止星星,都是从最遥远的距离外。
这个叫玛拉基奥的威尼斯人看待事物的角度,提醒我们留意塞巴尔德也并不是那么真实,他的写作与“真实”还是保持着一段有趣的距离。这里有个缺口,用以引入漂浮不定的意念。每一次,塞巴尔德似乎都是从具体出发:清晰的时间,明确的地点,确切的人物。唯独在文字洋溢出的情感上,表现出某种遥远的疏离感。“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日,卡夫卡博士曾独自躺在那里的湖畔绿地上,凝望着芦苇丛中的波浪,在其他时候总是悒悒不乐的他,心中充满着唯一的幸福:此刻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眩晕》这段关于卡夫卡的描述,让我想到,对于人类来说,未知是动力,是吸引,有可能产生创造的喜悦。
其实,我越读塞巴尔德,就越能从各种文本分析、评论的声音中走出来。那些都是他人的看法,自己看看身边不快乐的人吧,也许都在寻找“未知”的可能性。很多时候,主人公的逃离心态之于当下生活多么真切!在那一刻,塞巴尔德和当下有了联系。我开始回忆自己读塞巴尔德的顺序:《奥斯特利茨》——《土星之环》——《移民》——《晕眩》,与他创作这些作品的时间顺序正好相反。这个顺序造成了一种“从深海浮上水面”的感觉,就是说同一个主题在《眩晕》里已然确定。我曾看到读者就《奥斯特利茨》提出一个问题:“人到底需要多少记忆?当孤身穿过时间,我们真正需要记住什么,面对什么?”
《眩晕》里写道:“一个人记忆中的图像即便再逼真,也只能信其几分。”在后续作品中通过不同人物、不同旅途、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出行缘由等,不厌其烦地确认:“什么是真实,我们该相信什么?记忆可信吗?”我一直觉得塞巴尔德对细节、局部,还有叙述语调的强烈追求是一场“预谋”(记忆的准确度对应某种“真实”)。他写作,就是为了提醒自己和读者,某些不容忽视的事件背后,到底还发生过多少交错相生的事。具体表现,就是打开书,扑面而来的长句子,事物被卷进那股记忆的、历史的旋涡之中。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有个理论:在一个事件尚未结束时,另一个事件悄然开始。塞巴尔德的写作几乎就是这样。现在,我也不敢说懂得了塞巴尔德提出的问题,但知道他所说的记忆,有些方面可能倾向于归入一种不可捉摸的“知识”中,无关真假,趣味盎然。下面是《土星之环》里关于“五点梅花形纹样”的
段落,这明显超出了“记忆”的范畴:
它是由一个规则四边形四个角上的点及其对角线交叉点构成的。在活着的和死了的事物上,布朗到处都找到了这种结构,在某些结晶形状中,在海星和海胆身上,在哺乳动物的脊椎骨上,在鸟类和鱼类的脊柱上,在不少蛇的皮肤上,在以十字交叉方式前行的四足动物的足迹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