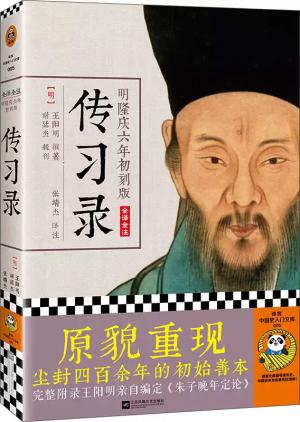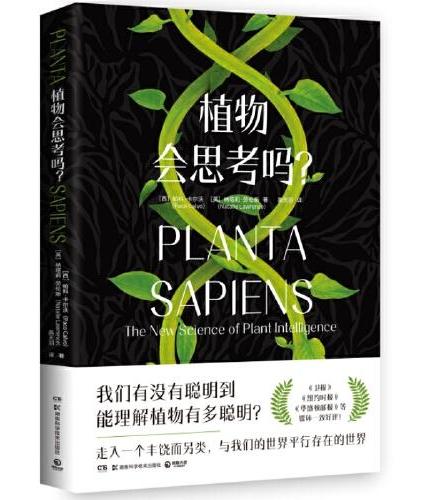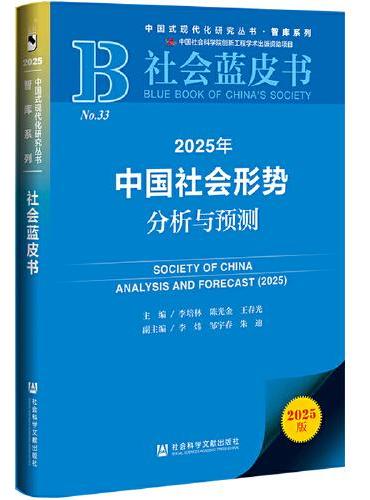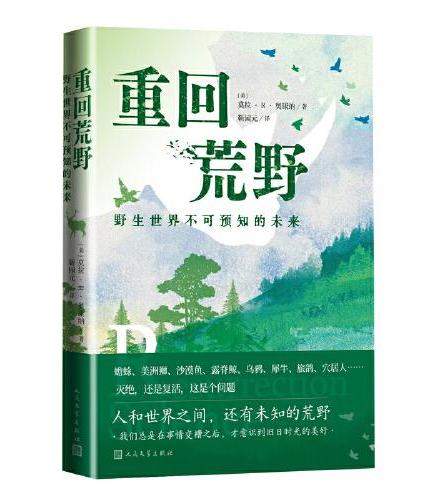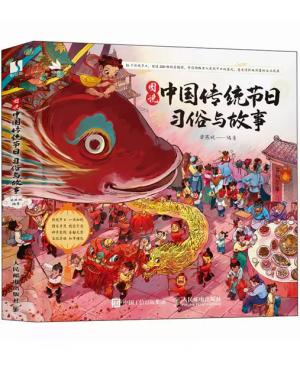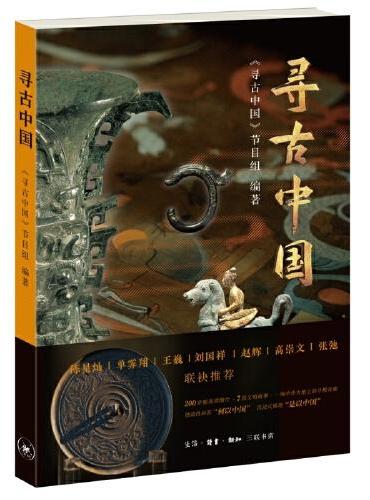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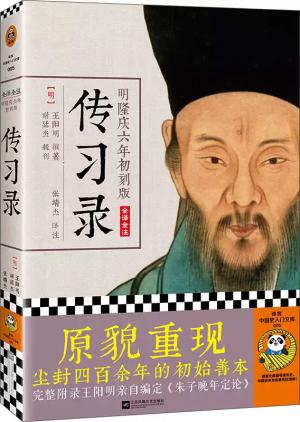
《
王阳明传习录 (全译全注)
》
售價:NT$
255.0

《
倾听疯狂的声音:被误解的精神分裂症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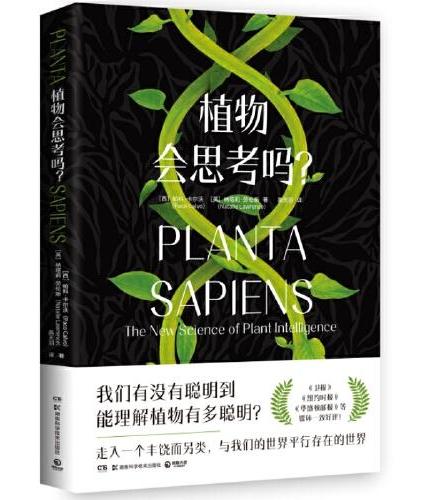
《
植物会思考吗?(揭晓你从未知道的植物智能,带你走入丰饶而另类的植物世界!)
》
售價:NT$
2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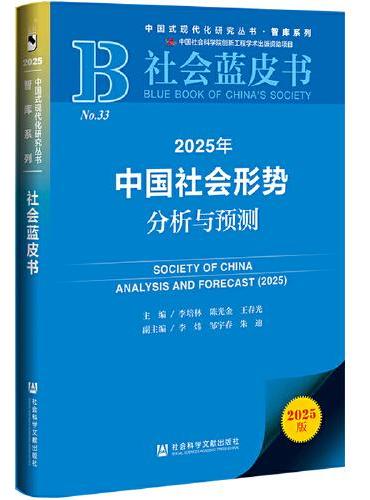
《
社会蓝皮书:202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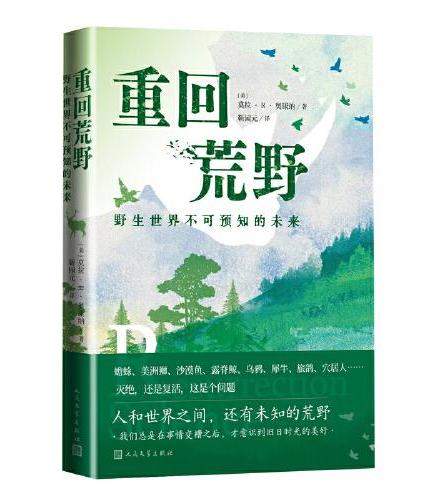
《
重回荒野 野生世界不可预知的未来
》
售價:NT$
2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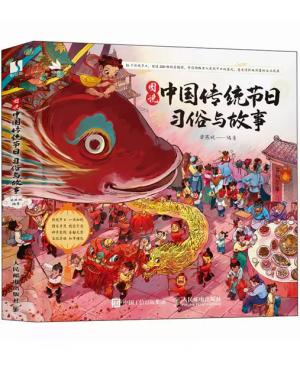
《
图说中国传统节日:习俗与故事
》
售價:NT$
662.0

《
发现你的职业性格——MBTI助你改善工作方式和人际关系(钻石版)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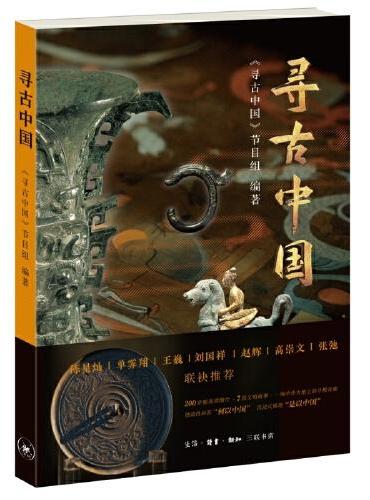
《
寻古中国
》
售價:NT$
505.0
|
| 編輯推薦: |
◆ 在一个冲突频现的世界,如何找寻不同文化、不同人群共同的声音,建立现实可行的政治秩序,成为至为重要的社会议题。全球化是否从道德上将我们吸引在一起?面对差异,我们究竟共享什么样的美德、原则和行为准则?这些问题正是叶礼庭在三年走访过程中试图回应的。
◆ 《平凡的美德》就世界秩序之问给出了一个新颖的答案。在叶礼庭看来,如果说国际主义是少数上层精英的专属语言,那么普通人在面对社会冲突和全球化浪潮时,他们所依赖的就是平凡的美德:一种从经验中获得的实践,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辨识出的语言。
◆ 作者调研足迹所至,不乏我们也熟知和关切的热点地区。在日本福岛,作者试图探寻当地居民、专家与官员在海啸与核事故处理中扮演的角色。而从经历爆炸性经济增长到腐败丛生的巴西,到陷入支离破碎的“彩虹之国”南非,再到缅甸与波斯尼亚,读者得以跟随作者的文字,一同走进这些差异巨大的国家,一同经历这场政治、经济、文化的探索之旅。
|
| 內容簡介: |
在如纽约市杰克逊高地这样高度多样化的移民世界里,对“共同生活”的强烈认同与现实实践中不同人群分开居住的景象相伴相生。从这里,叶礼庭辨认出一种有别于理论意义上的“全球伦理”的日常道德秩序,它不是自上而下的有关平等和多元的话语,而是一套基于信任、互惠、非暴力准则和合作倾向的运作体系。
经济的全球化是否带来了道德的全球化?如“人权”这样的世界性话语,究竟是代替了本土的道德规范,还是对其构成挑战?为调查21世纪道德全球化的景象,叶礼庭与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的研究者先后走访了洛杉矶贫穷的西班牙裔居住区、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比勒陀利亚郊外的非法定居点及曼德勒附近的贫穷村庄,尝试贴近冲突发生之地,研究伦理如何塑造人们的决策和行动。在长达三年、遍及四大洲的旅程中,作者发现,人类的共同之处在于一系列“平凡的美德”。平凡的美德是本土化、非意识形态、反理论的,是在道德行为和洞察之中获得的实践技艺。
作者进而着意探究了美德和公共机制之间的关系。平凡的美德有赖于公共的召唤和培育,理想的制度则可以激发纠错与更新的良性循环。一个良善社会的全部要义,就是创建法律和公共机制,让美德变得平凡。
“平凡的美德意味着,通过创造共同实践现实政治的空间,与文明和宗教冲突的全球性的陈词滥调做斗争。当普通的个体通过公共互动领会到,他们还有未被全球化论调俘获的利益,即和平或简单的平和与安宁时,现实政治就出现了。”
|
| 關於作者: |
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
加拿大作家、学者和政治家,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等校,也曾担任战地记者和政治评论员多年,出任多国政府顾问。其文章多见于《纽约书评》《金融时报》《新共和》等媒体,另著有《伯林传》《血缘与归属》《战士的荣耀》《火与烬》《痛苦的正当尺度》《陌生人的需要》《权利革命》等作品。2001年获乔治·奥威尔奖,2003年获汉娜·阿伦特奖, 2016—2021年担任匈牙利中欧大学校长。
译者介绍:
成起宏,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供职于上海,译著另有《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之旅》《战士的荣耀:种族战争与现代良知》《权利革命》等。
|
| 目錄:
|
导论:道德全球化及其不满
1 杰克逊高地,纽约:多样性广场
2 洛杉矶:全球化城市的道德运作体系
3 里约热内卢:秩序、腐败与公共信任
4 波黑:战争与和解
5 缅甸:道德叙事的政治
6 福岛:韧性与难以想象之事
7 南非:彩虹之后
结论:人权、全球伦理和平凡的美德
致谢
索引
注释
|
| 內容試閱:
|
1914年2月10日,世界首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在他位于曼哈顿第 91街的大厦里会见了一群教士,捐赠给他们200万美元,用于资助教会和平联盟(Church Peace Union)。卡内基的想法非常宏大:通过推动世界各种信仰之间的对话,促进世界和平。不是世上全部宗教教徒都参与会见,参加的有犹太教教徒、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但没有穆斯林、印度教教徒、佛教教徒和神道教教徒。不过一种理念已隐隐浮现:如果拥有信仰的男人们——他们都是男人——能够学会如何超越宗教神学之间的差异,超越绵延千年的宗教战争,那么全球冲突也许可以避免。教会和平联盟是卡内基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所建立的慈善事业的顶峰,这一事业包括矗立于海牙和日内瓦的世界和平宫,以及遍布全球的图书馆网络—致力于为各国的劳动者提供教育,教导他们作为公民该如何拒斥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蛊惑。卡内基对进步、知识和文化之间对话的信念,是全球化1.0版的成果。在这一阶段,身为苏格兰移民的卡内基,从19世纪50年代宾夕法尼亚的一名电报员,一跃成为19世纪80年代的钢铁大亨。如果说到现在,进步,尤其是道德进步被我们看成一种19世纪的理念,那么没有人比安德鲁·卡内基更狂热地信仰它。他的一生似乎都在为之身体力行。对于他,不言自明的是,让他成为亿万富翁的经济全球化也将整合全世界的信仰体系,而道德的全球化将带来和平,就算没有发生在他的时代,也将发生在我们的时代。2月的那一天,在他的书房里,他告诉这些聚集在一起的教士:“千真万确,先生们,你们正在创造历史,因为这是第一个倡导国际和平的教会联盟。我真挚地希望,坚定地相信,那一天肯定会加速到来。到了那一天,令人性蒙受耻辱的人们不会再像野兽那样互相杀戮。”卡内基的信念——跨越相互争斗的信仰进行伦理对话可以防止战争——今天顶多让我们觉得过于天真。就在他那次捐赠的几个月后的 8月,仿佛一道晴天霹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卡内基通过法律和对话实现世界和平的梦想就此破碎。这位老人那惊 的时候与世长辞。然而他的梦想并没有随着他的生命消逝。卡内基也许是道德天真那奇特而持久的生命力的一个例证。没有卡内基,是否会产生国际联盟?没有国际联盟,是否会诞生联合国?没有卡内基,是否会出现盖茨、巴菲特、*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巍峨庞然的慈善事业?甚至连教会和平联盟都得以存活下来,这得感谢复利计息的魔力。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它逐渐转变为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总部设在纽约东64大街一条林荫道上的褐石双子楼里。它是一个低调而深具关怀的组织,以“伦理最关键”为格言。这是一个信仰宣言,也是向我们的时代提出的问题。它为全球的研究员、研究项目和会议提供资助,关注伦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2013年,在这个组织获得安德鲁·卡内基的捐赠 100周年之际,其主席乔尔·罗森塔尔(Joel Rosenthal)和我探讨,他们应当如何纪念此事。记得当时我说:“你们需要走出纽约。”我建议,为了观察行动中的伦理,委员会应当带着伦理问题走出会议室,贴近冲突发生之地,研究伦理如何塑造人们的决策和行动。罗森塔尔抓住了这个一闪而逝的灵光,为它注入生命力。他说,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拥有遍布世界各学术机构的全球伦理研究人员,如果我们着手开展一项行动中的全球伦理研究,他们可以担任研究伙伴。这样,卡内基百年纪念计划诞生了,本书即成果:纪念卡内 查 21世纪的道德全球化是何种景象。2013年6月,一个小组得以成立,成员包括项目主管德文·斯图尔特( Devin Stewart)、一名翻译、一位研究员,还有我。我们与所到之地的负责人、驾驶员一起,开启一场道德发现之旅,这场旅行带领我们在随后的三年里抵达四个洲。我们的主题是全球化,但现实地说,我们不可能完全走遍全球。我们去的是可以获得卡内基的全球研究网络支持的地方,是我们已经拥有某些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地方。例如,我们去波黑 a和南非。对于我而言,这是旧地重游,过去 25年以来,这些国家的艰难和成就是我的写作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在其他国家,如缅甸和日本,我们都借鉴了我的同伴德文·斯图尔特的专业知识。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与专业人员开展对话,包括学者、法官、新闻从业人士和政治家。这些对话者本身就是行动中的全球化的例证:绝大多数人说英语,熟悉我们话题中的国际文献,是各种国际会议的常客。同时,这些本土的“世界主义者”跟我们一样,离他们自己的棚户区、贫民窟和贫穷社区中的现实非常遥远。当他们陪同我们造访这些地方的时候,跟我们一样,他们也进行了一场发现之旅。我们定点访问,去了洛杉矶贫穷的西班牙裔居住区、皇后区的移民社群、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比勒陀利亚郊外的非法定居点以及曼德勒附近的贫穷村庄。事实证明,这些访问对我们的项目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让我们提出问题:世界主义者通常使用的全球道德话语,对于居住在贫穷社区的人们的生活和思考而言,到底有没有“市场”?我们受委员会的委托,开展全球道德伦理对话,重点是与专家、学者、法学家和记者的讨论,对话只关注一个问题:全球化是否在道德上将我们吸引到一起?面对那些差异,我们要共享什么样的美德、原则和行为准则?为了避免针对价值观自身的对话—这有变得抽象和过度一般化的危险,我们决定聚焦于共同面对的实践问题。我们想找出,在面对诸如腐败和公共信任、多元文化城市中的宽容、战争和冲突之后的和解以及在不确定和危险时期的韧性等问题时,我们是否会操持同样的伦理话语。通过围绕这些主题展开的对话,我们希望对这样一种理念做出评估:随着经济、生活方式、技术和立场的全球化,伦理的论证也走向全球化。当我们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共享同样的产品、市场、生活方式和生活机会时,我们也逐渐走向共享相似的伦理论证模式。这一度是卡内基的希望:经济的进步将带来世界各宗教和价值体系的融合。一个世纪之后,这一希望仍旧在全球化的拥护者中生机勃发,但相比卡内基的时代,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相信宗教是道德全球化的一种动力,或者世界上的各宗教仍是道德行为指南的单一权威。我们发现,在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中,宗教仍然非常重要 —作为慰藉、激励和指南,但新的世俗信仰模式正在宣示它们吸引世界忠诚的力量。此类信仰之一 —对人权的信仰—出现在我们的集体思维之中,成为新的全球伦理的候选之一,但我们想知道:这一伦理已经传播得多广泛、多深入?它是真的已经代替了本土的道德规范,还是对其构成挑战?本土和世界、地方环境和全球化之间的战斗,在普通人的道德生活中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当我们着手思考怎样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全球化”主题时,这些是我们首先会遇到的问题。
全球伦理学家将全球伦理的失败归于自私的国家利益。然而问题还可以做更加深入的探讨。大多数民主国家的人们都相信,他们自己的利益是经过民主选择的,理当超越其他国家的民族利益。至少在拥有普选权的国家,这个观点是冲突的一种征兆,即民主和正义之间的冲突、我们附着于民族自决的那种价值观与附着于所有个体之抽象正义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很久以前就看到,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之中内在地存在一些冲突,正义和民主、正义和仁慈、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冲突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基于这些冲突,甚至连单一全球伦理的理念是否能在逻辑上自洽,也不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它绝不等同于各种道德价值彼此相容地排列座次。相反,最好将其理解为一个辩论场所,其中,某一社会的正义在全球的各种主张面前取得了为自己辩护的资格。不问出处的观点让强权者的自我辩护接受考验,强权者越是寝食难安,效果越好。
在那个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里,在那个人类的旅行范围只限 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不能享有道德封闭的奢望。我们会不断地被人追问,要我们解释自己。彼此对立的自我解释不可避免。不管在世界哪里,任何人离开家乡哪怕只有一段距离,就必然会捅破他们认为理所当然之道德世界的那层薄纸,进入另一个部落、宗教或伦理群体的道德领域。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全球性的伦理体系,都是竞争性的,它们不断争夺信徒,力求控制怀疑者,并且避开攻击。道德世界不是孤立的:每一个道德世界都在与另一个世界进行维护自身正当性的对话。
理解的重要之处在于,当彼此面对特定的道德原则问题时,来自不同文化和宗教体系的普通人到底会怎么做。宗教和世俗原则之间的冲突、环保和利润之间的冲突等,这些重大冲突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们的道德交易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如何互相理解?当他们产生分歧时,当冲突开始时,会发生什么?
换而言之,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我们所依赖的只是程序上的共性 —所有人类都有受尊重和被公平倾听的权利,任何人的观点都不应当因为他的种族、性别、宗教、教义、收入或国籍而凌驾于他人之上,那么,我们该如何就我们的差异展开协商?这是我们的全球伦理对话的初始问题。
我们的初始问题,不是道德全球化是否正在发生,而是它正在塑造谁的道德实践。其他学者的研究证实,人权仍然是一种“精英议程”,是一个有影响力但范围有限的群体的通用语,这个活动家、新闻记者以及技术官员,等等。事实上,他们就是我在哈佛开设的人权课堂上教过的学生。通过他们,我目睹了人权和全球伦理是如何塑造了他们的雄心、他们的道德凝聚力和他们的忠诚 —不再是单单对他们本国忠诚,而是忠诚于全球公民社会的伟大事业:解决战争、移民、全球不平等、贫穷和气候变化的问题。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但我想问的一些问题可能是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的世界主义者无法回答的。我的问题是,道德全球化是否已经触及那些被排除在特权社会阶层之外的社会群体?它如何形塑全世界平凡的人们的道德活动?我说的“平凡的人们”,在我的脑海中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或社会定位,当然我也不想赋予“平民百姓”任何道德特权 —那些民粹主义政治家在指责自由主义精英忽视普通人时通常会这样。我的意思是,任何人,既包括穷人也包括有钱人,没人付钱给他们去进行抽象的思考,他们不以竞选活动为生,他们的生意不涉及人权的经常运用或把道德哲学作为常规思考方式。这就是我们要付出特别努力,走出研究室和学院的休息室,走上街头的原因。我们的卡内基伦理对话带领我们去往四个大洲的社区中心、贫民窟、警察总局、修道院和其他宗教场所,还有贫穷街区。
我试图探索,对于按上述方式界定的普通人而言,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相互竞争的全球性和本土性主张做出归类整理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的研究成为亲密社会学(intimate sociology)和伦 有什么共同之处,而在于当人们在生活中面临伦理压力的时候,他们事实上会有什么共同之处。
结果表明,第一种压力是当代历史的发展势头本身。在我们这个后帝国的全球化时代,关键特征是爆炸性的、令人无所适从的、动荡不安的变化。变化总是令人类既恐惧又兴奋,但只有在现代国家的时代,人类才相信他们可以控制决定自己生活的历史力量。在欧洲扩张的帝国阶段,人们常相信是帝国 —其统治者、代理人、仆从 —掌控一切,至少在帝国首都如此。在 1989年以来的后帝国时代,新的焦虑在于无人掌控。与后帝国时代相伴的是对于如何理解国家的一种深刻的变化。到 1945年,归因于战争动员的经验,罗斯福的美国、艾德礼的英国以及斯大林治下完全处于另一脉络中的俄罗斯,都证明了一种全新国家理念的正确性,即将国家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安全保障和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以及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关键推动者。法语词组“ l’état providence”——幸运的国家——涵括了“二战”之后崛起的政府的全部雄心。到 2016年,很难找到仍然以这种方式看待国家的人。国家不再是变革的主引擎,它不再赋予自己保护公民免受全球化影响的权力。从 20世纪 70年代以来,这些雄心遭到了严重打击,部分是因为国家未能实现这些雄心,部分是因为国家自身被保守派的复辟剥夺了能力—我们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的结果是,部分最赞同“将国家从我们背上挪开”的想法的选民现在鼓噪着要求保护,希望免遭那些不受欢迎的全球竞争力量的影响。但国家既不再有能力,也不再有雄心去充当世俗的守护神。和其他任何一个社会角色一样,国家试图乘上技术、科学和社会变革的浪潮,平安上岸,确保自己的权威、收入和能力。对国家的信心、对帝国首都拥有远见卓识的信心、对接受来自远方的指令的信心,所有这些都已退潮、消逝,即使在完善的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中也是如此。现在,从某些人在某个地方掌管一切的幻觉或妄想中解脱出来之后,我们都面临改变。必须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的智慧来生活,也许只有那些特权阶层仍然相信全球化可以充当他们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在我们所有的对话中,问题的起点是如何应对改变:在巴西,是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和腐败;在洛杉矶和纽约,是过度多样化的移民;在日本福岛,是海啸与核事故的后果;在缅甸,是从军事统治走向民主的漫长过渡;在南非,纳尔逊 ·曼德拉的“彩虹之国”支离破碎;在波黑,种族冲突再度陷入恶性循环。
与我们交谈的那些个体,从未将他们的私人困境与他们所居住之地更为广泛的冲突环境割裂开来。关于人类责任和道德论证的泛泛而谈对于他们而言没什么意义:环境就是一切。在每一个地方,当我们的对话同伴受困于那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应对的问题时,我们听到了共同的伦理话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