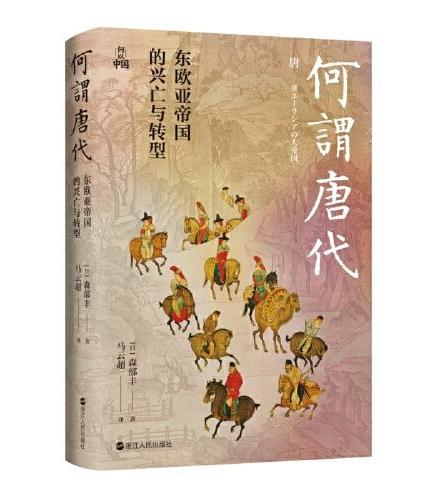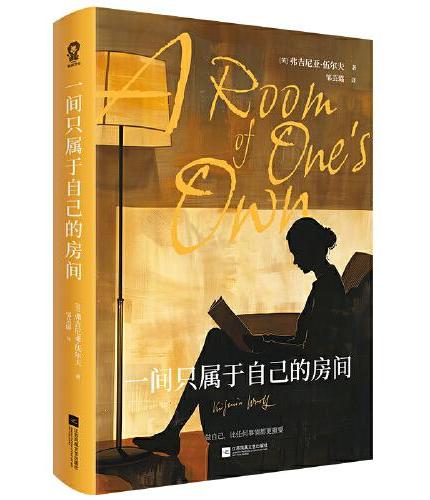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新时代硬道理 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
》 售價:NT$
352.0
《
6S精益管理实战(精装版)
》 售價:NT$
458.0
《
异域回声——晚近海外汉学之文史互动研究
》 售價:NT$
500.0
《
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聚焦亚洲、中东和南美洲被忽视的本土农业文明
》 售價:NT$
454.0
《
无端欢喜
》 售價:NT$
347.0
《
股票大作手操盘术
》 售價:NT$
245.0
《
何以中国·何谓唐代: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
》 售價:NT$
398.0
《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代表作 女性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的象征,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 售價:NT$
203.0
編輯推薦:
√记述了从1949年延续到21世纪、横跨60余年的乡村人生故事,聚焦三代、六类人,他们命运的沉浮、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种种样貌。
內容簡介:
所谓“双面人”,即指那些在“古今之变”中陷入悖论的农民。作者以粤西梧县“程村”为调查对象,通过书写三代人的人生史,呈现一个普通村庄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再到21世纪的发展历程,描绘了当地基层乡镇治理的转型、半工半农结构的形成,以及乡土人情、精神信仰等多个维度,进而直入中国文化的内在肌理。
關於作者:
谭同学
目錄
初版序言(吴飞)
內容試閱
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