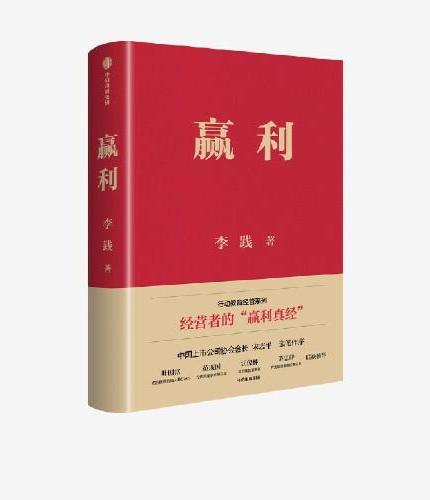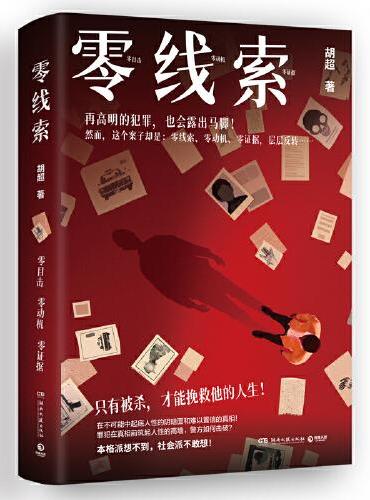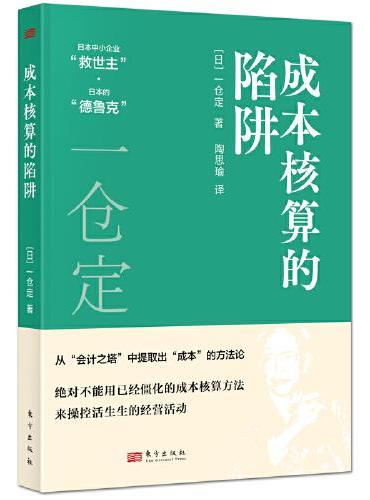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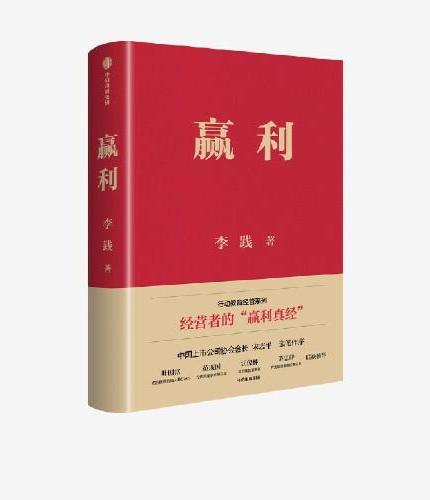
《
赢利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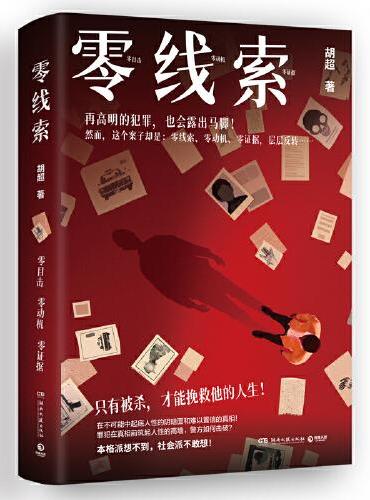
《
零线索(只有被杀,才能挽救他的人生!)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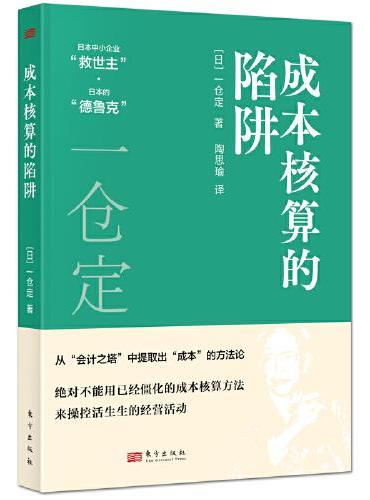
《
成本核算的陷阱
》
售價:NT$
214.0

《
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万有引力书系)
》
售價:NT$
484.0

《
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
》
售價:NT$
528.0

《
活力物质:“物”的政治生态学
》
售價:NT$
435.0

《
哪吒传漫画(1-4册)
》
售價:NT$
396.0

《
我是时代的孩童:陀思妥耶夫斯基随笔选
》
售價:NT$
484.0
|
| 編輯推薦: |
|
医学的服务对象是人,人不仅仅具有生物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人的心理、习俗、价值观念等因素无不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和疾病及其转归。但受近代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医学的人文内涵逐渐被剥离,医学日益成为技术、资本的附庸,对人文社会因素的关注越来越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兴起,强烈呼唤着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目前卫生事业与医学科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大多与人文因素密切相关。因此,从人文视野探讨医学问题,当下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和必要。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广州医科大学二级教授、博导刘俊荣教授团结带领一批学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直面医学之目的和服务对象之本身,立足现实的生命个体,回归医学应有的科学性和人文性,进行医学与人文的整合,出版了第二辑《人文视野中的医学》。
|
| 內容簡介: |
|
《人文视野中的医学》(第II辑)分别从哲学、伦理、管理等多个人文视角,对医疗决策、医疗责任、知情同意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分析了医学实践中的医德取向、知情同意、医患关系、资源配置等热点问题,并在强化医德建设、和谐医患关系、优化资源配置、改进医院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有益的方略对策。
|
| 關於作者: |
刘俊荣:男,哲学博士,二级教授,广州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广州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院长(2005.10-2019.04)、党总支书记(2010.03-2019.04),现任广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广东省医学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广州市医学伦理学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公共事业管理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带头人、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医学伦理学”负责人等。
先后荣获广东特支计划领军人才(特支计划教学名师)、广东省高校教学名师、南粤优秀教师、广州市优秀专家(A证)等荣誉称号。目前,兼任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伦理学试题开发专家组组长、教 育 部高校医学人文素养与全科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卫健委医学伦理学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副主编、《医学与哲学》编委会副主任等。先后出版《医患冲突的沟通与解决》《人文视野中的医学》等个人专著4部,主编《护理伦理学》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医学伦理学》《中华传统医德思想导读》等著作13部、副主编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医学伦理学》等14部;荣获省级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3项,厅级成果特等奖1项、二等奖2项;指导学生获得大学生“挑战杯”全省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教 育 部人文社科项目及省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等省级课题12项、厅级课题7项、横向课题9项,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
|
| 目錄:
|
目?录
1? 医学问题的哲学之辩 1
1.1?身体理论语境下当代生命伦理关涉的基本问题 1
1.2?基于身体理论的当代生命技术伦理研究现状之审视 13
1.3?身体理论视域下的医者德性之养成 24
1.4?身体伦理视域下现代医学模式的哲学反思与重构 34
1.5?自我、身体及其技术异化与认同 38
1.6?基于责任伦理的医疗决策主体之审视 52
1.7?健康的道德负载及其现实意义 62
2? 医学问题的伦理之思 73
2.1?医疗决策中利益冲突的伦理纷争 73
2.2?“家庭共决”保障脆弱人群的伦理限度及困境 85
2.3?艾滋病防治中的利益冲突及其伦理决策 90
2.4?医疗决策模式与决策主体的选择倾向 98
2.5?医师人格特征对伦理困境下医疗决策的影响 110
2.6?医疗决策中医务人员的价值期望及其影响因素 124
2.7?临床护士伦理决策能力研究现状 134
2.8?急诊科护士道德困境研究进展 145
2.9?艾滋病患者隐私保护中的伦理困境 156
2.10?厘清医学伦理难题,关注保护性医疗 164
2.11?医方也有“知情同意权” 168
2.12?放弃治疗知情同意书及授权委托书使用现状调查 175
2.13?“三亲婴儿”培育技术的伦理辩护及反思 184
3? 医学问题的管理之道 193
3.1?医疗机构防范医患冲突的差异性分析 193
3.2?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对医患冲突处理方式评价研究 203
3.3?不同类别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对处理医患冲突方式的认知与评价研究
209
3.4?医师职业倦怠与其医患关系的相关性研究 216
3.5?患方权利冲突境遇下的医疗决策及其矛盾之化解 225
3.6?基于患者视角的医疗决策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233
3.7?基于患者视角的共享决策参与现况及策略 246
3.8?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医患认知调查分析 255
3.9?医患双方对权利位阶的认知态度及其相关因素 268
3.10?住院医师人格特征对术前签字认知态度的影响及评价 280
3.11?医务社工介入医患冲突的感知性评价及其影响因素 292
3.12?广州市三甲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患者满意度之比较 303
3.13?国外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对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启示 310
4? 拾零 319
4.1?人人都应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 319
4.2?医疗决策还需考虑非技术因素 325
4.3?坚持德法并举,捍卫学术尊严 328
4.4?否定基因编辑婴儿不等于否定优生技术 330
4.5?伦理拷问:青年和老年,先救谁? 332
4.6?关于医学与人文整合的再思考 336
4.7?我国医学人文学科建设的现状调查及建议 343
|
| 內容試閱:
|
1?医学问题的哲学之辩
1.1?身体理论语境下当代生命伦理关涉的基本问题
人作为生命伦理的关怀主体,既不是纯粹思想的“心灵实体”,也不是纯粹广延的“机械身体”,而是具身的(embodied)存在。国内也有学者将“embodied”译为“涉身的、缘身的”等。笔者认为用“具身的”更能反映其本意,一方面“具身”强调人是具有身体的主体和存在,这与笛卡尔的心灵主体相区别;另一方面,强调身体是不同于肉体的主体,它具有与外部环境、物理客体等进行互动感知的能力,从而与拉美特里的机械身体相区别。只有认同人是“具身”的存在以及身体的属“我”性,才可能进一步探讨身体在认知中的意义等“涉身”问题,因此,与“涉身”相比,“具身”有着更基础、更广泛的适用性。人首先是肉体的、躯体的、生物性的存在,其次才是理性的、文化的、社会的存在。身体理论的兴起和哲学主体间性的建构,消解了近代西方哲学中祛身的自我,使自我返回到了世界和尘世,对我们反思当前生命伦理的基本问题,提供了别样的视角。身体作为自我构建的始基,既不是纯粹的肉体,也不是心灵的容器,它是人与人进行交往、对话的场所,是自在与自为的统一。生命不能脱离时空而存在,人的生命的界定既需要考虑时间因素,也需要考虑空间因素,人的生命与身体在时空上具有统一性。
一、人的生命与身体的共时性与历时性
“人的生命”与“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的生命只是人的一种属性,作为个体存在的人除此之外,还具有其他多方面的规定性,如充当特定的社会角色、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遵循社会道德和法律法规等。但是,二者又相互联系,人的生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失去了生命,人就不能称之为人。
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关于人的生命之起始有着不同的界说。其一,生物学标准从人的种生命出发,把受精卵作为人的生命的开始,如《阿根廷民法典》规定“人的生存自孕育于母腹之时开始”[1]。1962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声明中指出:“无论何时精神性的灵魂被创造以构成一个人(位格),生命从一开始就必须被小心地保护。”因为人为的干预要么阻碍了受精卵发育成为正常人的可能性,要么影响了胚胎作为一种“人”的正常发育,这种思想似乎能够从柏格森的时间观得到说明。按照柏格森的真正时间观,生命是无间断的、不可分隔的、非空间化的绵延,人的生命从精卵结合之时已经确定,此后的空间性变化如细胞的分裂、组织的分化、器官的形成等,只能就其空间时间而言,只是真正时间的空间化过程。这种观点,仅仅把人看作了纯粹的生物存在,看到了人的种生命,而忽视了人的类生命。显然,这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它与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所认可的人工流产、人工生殖及利用受精卵或胚胎进行合法研究的科学活动相背离。其二,授权标准从人的类生命出发,认为胎儿只有得到父母或社会的接受才算生命的开始。法国天主教道德神学家波希尔等认为,完人的生命或人化的生命必须在亲属这个名义之内才能算数[2]。这种标准固然考虑到了生命的社会性,但却否认了生命标准的客观性,把父母或社会的“接受”看作生命的标准,必然走向相对主义,最终导致标准的混乱,并可能成为某些弃婴行为的辩护借口。
笔者认为,人的生命的界定不能仅从种生命出发,但也离不开种生命,种生命是类生命的物质载体,只有依赖于种生命才能进一步说明人的类生命。所谓“种生命”就是“被给予的自然生命”,而“类生命”则是“自我创生的自为生命”[3]。种生命具有自在的性质,受自然法则所支配,而类生命是由人所创生的,为人所特有,受后天条件所影响,因个体创造能力的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对于人的种生命,不能仅从动物的种生命的意义上去理解,更不应将其视作构成生命基本单元的细胞层次(包括受精卵)上的生命,不能以“遗传学上的连续性”为由,强调受精卵已具有人类的种生命。人的种生命是社会化了的种生命,它不同于动物纯粹的种生命,受精卵只有一般生物的自然生命,人类的种生命并不是简单的基因序列,它的存在是以人的实体存在为基础的。就人的生物发育过程而言,人的身体雏形只是到胎儿阶段才得以形成,但是这一时期所谓的身体也只不过是肉体,只具有纯粹的生物学特征,而缺乏基本的文化体验和认知功能。直到分娩前,由于胎儿与其孕母仍然是一元的存在,尚隐藏于母体之中,完全依靠母体,不能扮演任何社会角色,还没有进入社会化程序,也称不上是人的种生命。只有分娩成功,新生儿诞生之后,新生命与孕母的关系才由一元存在变为二元存在。这时,虽然他仍然依赖母体的营养和照料,但新生儿与胎儿不同,他已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一员,可以扮演子女、病人等角色,其身体可以感触父母的抚摸与呵护,可以进行包装和修饰,并已开始与他人发生心身的交互,具备了基本的认知图式(这已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理论所揭示)。只有从此开始,它才实现了与外界的直接联系,才真正成为人类中的独立个体和道德意义上的具身主体。
当然,刚刚出生的婴儿并没有自我意识,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因为他已完全具备了人的直观表象,并已成为文化、制度、技术等规训的对象,已开始进入“自我意识”和“社会关系”的社会程序之中。尽管“自我意识”并非为人类的每一个体所具有,但就类的属性而言,它是人的生命与其他灵长类、受精卵、胚胎、胎儿的生命区分开来的本质性特征。正是由于自我意识,促成了个体发展的整个生命过程中的质变:即当个体发展到产生自我意识时,人的种生命开始发展出人的类生命,但种生命并未因此而消失,而是进入了社会化程序,成为社会化的种生命。而当人的自我意识不可逆转的丧失时,又复归为人的种生命或二者同时消失。但自我意识的丧失并不必然意味着类生命的完全丧失如植物人状态,就植物人来说,尽管其类生命的自我创生能力已不复存在,而其所承载的父亲、母亲、儿子等社会角色依然存在,只不过其类生命已处于次要的方面,屈从于种生命,成为种生命化的类生命。由于自我意识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实践,大脑仅仅是思维的外壳,只有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实践过程中,意识才能得到产生和发展。立足于社会关系,不但可以进一步区分人与胚胎、胎儿的生命,而且还有助于深入地认识人与其他灵长类生命的异同,如:在镜子中能辨认自己的黑猩猩,似乎也有自我意识,但不符合社会关系的标准。因此,我国学者邱仁宗认为:人是在社会关系中扮演一定角色的有自我意识的物质实体。这不仅说明了人的种生命,同时也强调了人的类生命,人的生命应该是种生命和类生命的有机统一,单纯的种生命或类生命都不能称为人的生命,缺少或失去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人都不应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或正常的人。[4]
因此,从发生学上说,人的种生命与类生命、人的身体与生命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也就是说,在时间坐标中无论从纵向上还是横向上看,人的生命的孕育过程与人的身体的形成过程都遵循着完全一致的时间生成轨迹,分娩前的生命至多是人的种生命,此时的身体也仅仅是肉体。只有胎儿娩出这一刻之后,人的类生命才得以形成,肉体也才转化为身体,胎儿才成为具身之人并进入社会化进程。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和我国《宪法》《国籍法》《刑法》《民法通则》《母婴保健法》等法律中,均将个人基本权利的时限界定为出生之后,尚未出生的胚胎不能成为法律关系中的法律主体,这就从法律上确认了人的生命之起始。
但是,人的生命与人毕竟不是一回事,人是有生命的存在,是生命的物质表象或载体,生命是一种流变、冲动、过程和存在方式,生命有生命质量与生命价值之分、有种生命与类生命之别。种生命与类生命的统一性关系是就人类的生命而言的,就某些生命个体来说,种生命和类生命并非总是统一的。也就是说,拥有高质量的种生命并不一定就拥有高质量的类生命,拥有高质量的类生命也未必就拥有高质量的种生命。例如,某些身强力壮、十恶不赦的罪犯,其类生命质量可能为零甚至负值;某些残疾人或病患虽然其种生命质量较低,但其类生命质量即生命价值并不小于某些正常人,霍金就是例证。因此,种生命与类生命、生命质量与生命价值并非总是正相关的。我们不能因为类生命质量的降低或消失而完全否定其种生命的存在和意义,也不能因为种生命质量的受损或降低而否定其类生命的质量和价值。更不能因为某些病患如植物人、无脑儿等没有自我意识,类生命质量低劣,而否定其种生命的尊严和神圣。
二、人的生命与人的空间性:关于胎儿生命的再定位
人的生命作为种生命与类生命的统一既然始于出生,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胎儿的生命?它是不是人的生命?是否具有生命的权利和尊严?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阐明胎儿是不是人?由此,又势必需要界定什么是人?
关于人是什么?“我是谁?”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无论古希腊的人学理论,还是基督教、文化人类学者等学派的人学理论,都没能够摆脱原有观念中关于人的灵魂、理性、情感、心智等认识的困扰,将思维者、行动者的特性类推到一切人类个体,并试图从思维抽象中揭示人的本质,忽视或漠视了感觉直观中的人,其结果不尽如人意,抽象的本质并不能适用于无限多样的个体。对人的界定应当从最简约的、最具普遍性的特征入手,考虑到人类的每一个特殊个体,包括正常的和异常的不同情形,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人,避免践踏个体及生命尊严的现象。现象学方法为我们达成这种目的提供了可能,现象学强调研究者从传统的观念、理论、思维、偏见中解脱出来,摆脱一切理论性的先入之见,从原初看到的“纯粹”现象中认识事物,从事物本身洞察事物,主张“只有回到直接的直观这个最初的来源,回到由最初的来源引出的对本质结构的洞察”[5]。这种方法通过“相似性统觉”揭示不同个体间的共性,发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把所研究体验的描述还原到它的基本要素或本质。就此而言,人首先是我们能够体验到的像你、我、他有着一般人所具有的头颅、躯干、四肢的动物。这是我们对人的类生命特征的直观体验,这种直观体验是我们进一步判断某物是否是人的基础。从外部直观来说,也许某一个体缺失了常人所具有的手、脚甚至四肢,但只要他具有人的头颅和躯干,有着人的基本生命体征如脉搏、呼吸、体温、进食、排泄等,他所呈现给我们的仍然是人的直观,我们决不会因为他缺少了手、脚或四肢而否定其作为人的事实,头颅和躯干的共同存在是人之生命活动的基本条件,也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解剖学要素。至少就目前的生命科技水平而言,没有头颅或躯干的人是无法存活的。脱离了躯干的头颅或与头颅分离了的躯干,都不能称其为人。因此,头颅和躯干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形态,这是我们基于对人类不同个体的“自然相似性”获得的最简约的直观体验和认识。尽管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个体在肤色、头发、眼睛颜色等方面存在的差别,但我们总能看到不同个体在头颅和躯干上的结构相似。基于这些自然相似性,我们便获得了他人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一种通过感知类比而获得的相似性。“只有在我的原初领域内,对作为另一个人的身体的躯体进行类比,才能从根本上说明如何得以把握那里的那个与我的躯体相似的躯体。”[6]而灵魂、理性、情感、心智等作为意义建构和意识抽象的结果,只是特定阶段的正常人才具有的特征,如果将其强加于人类的一切个体,必然会将该阶段之外的或非正常的个体排除在人的概念之外,如婴儿、无脑儿、植物人等可能均被排除在人类之外,这显然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事实上,婴儿、无脑儿、植物人等,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特殊个体。之所以是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人的理性、情感与心智,也不是出于对这些特殊个体的怜悯、同情与责任,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能给予人以人的感觉直观且拥有人的基本生命体征。不可否认,当言说他们能给予人以人的感觉直观时,我们并没有完全脱离意识中原有的关于人的整体表象,但我们并没有被原有的表现所桎梏,而是将一般常人的整体表象予以悬置,保留其最基本的要素。事实上,彻底的还原是不可能的,现象学“还原法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完全还原的不可能性”[7]。如果完全悬置了对人的一切认识、理念和习惯,人的概念就无从谈起,它至多是一个无以言表的客观存在。
事实上,将人作为如其所是的直观体验,并没有也不意味着漠视人的精神、意识与情感,相反,关注人的精神和意识正是现象学与实证主义方法的根本区别。从最基本、最简约的直观体验还原到一般的人,所需要给予的正是精神和意识,使其在被悬置之后得以再现。我们只有根据直观体验将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个体加以考察和审视,回归真实的生活世界,才能得到原初的生活体验,并对其加以无偏见的描述,达到生命的直观,看到形态异彩的世界,实现最基本、最简约的本质还原。也只有在最基本、最简约形态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揭示复杂的群体形态,归纳出类的不同层面的共性和特征。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从最简约的、直观的人的概念出发,再赋予其不同层次、不同属性的类的特征,就可以还原到现实中不同状态的人类群体,如包括正常人、残疾人、病患者、婴儿、儿童、青年人、成年人、老年人等。也可以再进一步将道德、法律、文化等属性赋予不同的群体,并进行更深一层次的分类。相反,如果对人的界定的起点太高,反而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而且会造成对人类个体生命的践踏。在部分学者如辛格等关于人的分析中,之所以出现否定无脑儿、植物人等作为人类之个体的归属,其根源就在于没有从最简约的直观体验观察和描述对象,用一般常人的标准去衡量非正常的人,违背了科学哲学中的经济思维原则。
综上所述,人的界定需要以身体为准绳,人就是如人所有的头颅、躯干及基本生命体征而独立存在的具身个体。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揭示复杂的群体形态,归纳出类的不同层面的共性和特征。
胎儿尤其是28周以后的胎儿已具备人的头颅和躯体,已符合人的最基本条件。但是,如果以自我意识、灵魂、理性为标准,无疑胎儿不是人。我们对此结论持肯定的态度,但并不赞同其否定的理由。因为自我意识作为人的正常状况下类的属性并非适于一切人类个体,并非所有的人类个体都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意识的个体未必就不是人。因此,我们不应以自我意识的缺失而将胎儿排除在人类个体之外。事实上,胎儿虽没有自我意识,但有发生自我意识的潜能,只不过胎儿还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仅具有人的基本雏形,与社会还未发生任何现实的联系,其生命是纯粹的种生命,其身体也还是纯粹的肉体,没有任何文化、技术、社会的印迹,尚没有进入社会化程序,也没有具身认知的能力。无论是古希腊的人学思想、现象学的人学视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人首先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具有自主认知能力的主体,要么是一种理性的实体、先验性存在,要么是一种经验性存在或对象性存在。作为主体其与周围世界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或者将世界视为自身的对象或者视为自身的有机整体。即使宗教神学,也只是要求尊重胚胎、胎儿的生命并没有明示胎儿是人。如在《生命福音》通谕的声明中虽强调“堕胎是故意杀害一个无辜的‘人’”,但其中的“人”的英文是“human being”而不是“person”,即指人类存有或生物的人而不是位格或社会的人。
笔者认为,关于胎儿的道德属性的界定,不能仅仅以时间来衡量,还必须考虑到空间上的差异。例如,一个孕35周的胎儿,如果存在于母体的子宫之中,就只能称之为胎儿,不是现实意义上的人。但是,如果早产或人为地将其从母体中取出并放在保温箱中,它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因为它已经进入了经验的世界和社会化程序,能够扮演特定的社会角色,形成了现实的对象性关系,实现了种生命的类化,具有类生命的特征。事实上,仅就其刚刚从母体娩出的瞬间而言,它在生物学组成、生理机能、意识状态等方面与娩出前并无显著的差异,只是存在空间和存在方式的不同。这表明,人的生命不仅具有时间性,也具有空间性,生命通过存在于时间、空间之中的身体等现象表现出来。正如兰赛(Paul Ramsay)所说:“作为一个有灵魂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具有身体的外形和轨迹。”[8]
因此,对胎儿的道德地位、胎儿是不是人的判断不能仅仅从时间上来考虑,空间判断有着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正是由于空间的变换,种生命才开启了类生命的社会化进程,肉体才获得了身体的意义,胎儿才成为婴儿并标志着新生命的诞生。
三、无心之身的生命:以植物人为例
种生命是类生命的实体依托,心灵、意识是类生命的策动之源。就类的属性而言,心灵、意识是类生命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之一。但面对多样化的、不同生命质量的个体,如何评判其地位和意义?仅有种生命而没有自我意识的个体是否为人?例如,植物人的大脑皮层功能严重受损,认知能力完全丧失,除具有一些本能性的神经反射和物质能量代谢外,无任何自主活动,处于不可逆的深度昏迷状态。这样的人是否还具有人的生命?如何判断其作为人的道德地位?
按照笛卡尔的二元论,植物人是一个没有理性、心灵和理智的不能思维的身体,更不用说拥有尼采所强调的权力意志。它仅仅是一个具有广延性的“机械结构”,是有生命的“尸体”,称不上能够“我思”的、具有生存意志或权力意志的人。辛格与此持一致的态度,并否定了植物人生命的内在价值,他在《实践伦理学》中指出:植物人“没有自我意识、理性和自主,因此,对生命权和尊重自主的考虑就不适用于他们。如果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再有任何经验,那他们的生命也就没有内在价值。他们生命的航程已经终结。他们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还活着,但在传记意义上已经死去”[9]。邱仁宗先生则从意识能力的角度否定了植物人作为人的生命的存在,他认为:“一个已经不可逆昏迷的人,或者脑死亡,或者处于永久性植物状态的人,他们也具有所有的人类基因组,并且有一个人体,但也不是‘人’。”[10]显然,以上观点均将理性、意识、自主当作了评判人的必要条件或生命内在价值的依归,而否定或淡化了躯体中本能性的神经反射如咳嗽、喷嚏、打哈欠以及呼吸、心跳、物质能量代谢等在对人进行道德判断中的价值,更没有兼顾到伊德、梅洛·庞蒂所强调的涉身主体的意义。在梅洛·庞蒂看来,笛卡尔二元论背景下的“身体”及其各组成部分与其对象之间只具有外在的机械因果关系,其实质是处在机械自然观的客观世界中的一种广延实体,它是建立在机械因果模型下的传统生理学基础之上的。在传统的生理学理论中,身体的“刺激—反应”行为只能用刺激、接收器和感觉之间的机械因果关系来描述,身体被构想为客观世界中的一个自在对象,并可以从第三人称视角对身体行为进行外在观察,此即“对象身体”。梅洛?庞蒂试图通过“幻肢现象”表明身体并不是纯粹客观意义上的认识对象,他提出了“现象身体”的概念。所谓“现象身体”就是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综合,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在世存在的载体”。现代生理学研究表明,身体并非单纯被动地接受外部刺激,也能排斥特定刺激。身体行为并非单纯的机械因果关系,还包含着某种主动性或目的性的成分,身体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主动地加工和选择刺激,表现出自组织的功能。作为“现象身体”的身体主体与意识主体的根本区别在于其自身不是纯粹和透明的,而是暧昧的、含混的。身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来自同一个“形体领域”,即活的肉体,它们不是彼此并列且外在联系起来的实存。相反,它们是彼此交叠和共存,相互纠缠并不可分割地互相连接。事实上,身体本身就是意义表达的能指,身体动作、身体姿势承载着一种比理性意识更本源的运动意识或知觉意识,这种知觉意识“是通过身体以物体方式的存在”,它不同于作为对象性、反思性意识的“我思”。正是身体提供了人类基本感知的条件,将人置身于世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并使之成为世界的中心。
植物人虽然已不具有人的意识和认知能力,但他仍具有人的直观表象,并且保有着人的基本生命体征如脉搏、呼吸、血压、体温等,并且具有人之为人的身体。我们可以否定他作为意识主体的存在,但却没有足够的理由否定他不再是一个身体主体。当一个陪伴植物人的人熟睡在植物人旁边,难道一个陌生人能区分出二者谁死谁活,或者能说出哪一个是沉睡的人,哪一个是植物人吗?然而,一个具有认知和分析能力的熟睡的机器人,无论他睡得再深,也无论机器人伪装得再像,你也不会说机器人是人,也能够区分出哪一个是人。而做出以上判断的依据绝不是认知能力和思维,而是其具有直观表象的身体和基本的生命体征。故而,在判断生与死的问题上,身体死亡与意识丧失同等重要,传统死亡标准之所以至今仍被不少人所固守,正是因为它能给人们更直观体验的东西。
因此,笔者认为,对人及其生命的理解,不能拘泥于二元论立场,仅仅将其看作活力、机能、功能、精神、思想等,而应从身体理论的视域,将身体作为生命的应有内容。人的生命是人的身体与意识、意志、冲动等精神形态的统一,即人本身,生命的结束也就意味着身体的死亡,身体变为尸体。梅洛?庞蒂认为:“身体自身的运动包含着自身进入所询问的那个世界……每一个世界都对另外一个世界保持开放。”[11]植物人虽因失去意识和认知能力而区别于常人,但也不同于没有思维、没有意识、没有认知能力的动物,更不同于具有思维和认知能力的机器,其身体是文化、权利、尊严等社会属性的载体,具有人的社会关系属性,是其与他人进行交流、对话的场所。植物人仍然具有人的种生命并扮演着病患、父子等现实的角色关系,不能因为其意识的消失而完全否定其作为人的存在。
意识与意识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无意识不能作为评判人的标准,否则刚出生的婴儿、处于全身麻醉状态的人等都将被列入非人的范畴。笔者认为,“自我意识能力”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概念。新生婴儿、处于全身麻醉状态的人等虽然此种状态下不具有自我意识,但他们有发生或恢复自我意识的能力。自我意识能力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范畴,一个人的能力包括自我意识能力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而且它与科技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无脑儿、植物人等就当下的科技水平而言,已不太可能再发生或恢复意识,不具有自我意识能力,但若有朝一日通过大脑移植或修复等技术,植物人能够恢复意识、无脑儿可以治愈,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正常”的人。就自我意识能力而言,胎儿具有发生自我意识的潜能与植物人具有恢复自我意识的潜能是不同的,前者要变成现实需要生殖科学的支撑,后者要变成现实需要临床医学的支撑。由于前者还不是独立的个体,在情感、价值等方面与后者曾经为人且已与社会发生过现实联系的事实是不同的。前者所具有的种生命与后者所具有的种生命是不等价的,后者是一种类化了的、社会化了的种生命。因此,人工流产与放弃对植物人、深度昏迷者的治疗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是不同的。但无论如何,不应当否认人类种生命的神圣性,只不过不同状态的个体的种生命的价值不同罢了。对不同状态的种生命的价值评估应当从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分析,植物人的种生命的价值并不因其已被社会化而必然大于胚胎的种生命的价值,但也未必小于胚胎的种生命的价值。一个胚胎既可能发育发展成一个健康的有用的人,也可能发育成一个如无脑儿的无用之人。
如果说植物人仍属人类个体意义上的人,其尊严、权利和价值等社会属性与常人何异?这些问题直接关涉着对植物人的临床治疗态度和治疗行为,关涉着植物人的治疗意义和治疗价值等问题。
按照“理性—尊严说”,人的尊严源自人的自主意志和选择能力。无论“自主—尊严说”“道德自主—尊严说”,还是“自我目的—尊严说”,尽管其主张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但都认为尊严是以自由意志、理性能力为前提的,奥古斯丁、斯多葛学派、康德等都持有此类观点。依此,无脑儿、植物人因没有或失去自由意志及选择能力,就无人的尊严。显然,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判断。自主意志、选择能力虽然影响尊严,但并不是人的尊严存在的必要条件。人的尊严可分为生命尊严、社会尊严和心理尊严,自主意志、选择能力所体现的仅仅是人的社会尊严或心理尊严,而生命尊严是人所固有的,是人的自然属性,只要是人类成员,就拥有超越于其他物种的生命尊严。德国宪法法院在一项判决中写道“有人的生命的地方,就有人的尊严;起决定作用的并不在于尊严的载体是否意识到这种尊严或者知道保护这种尊严。从开始便建构在人的存在中潜在的能力就足以对这种尊严做出论证。”[12]依此,只要是人的生命都享有生命的尊严,其生命都同样神圣不可侵犯,植物人作为人的生命的存在,与常人一样拥有生命的尊严。尊严与生命并不是直接同一的,生命尊严仅仅是人的尊严的最基本的方面。已逝者虽不再拥有生命和生命的尊严,但不等于无尊严,其荣誉、名誉等社会尊严依然存在。人的社会尊严、心理尊严会因人的社会地位、角色权利、心理感受而不同。同样,生命尊严也有大小、高低之别,受生命状态、生命质量、生命价值的因素的影响。“早期胚胎与胎儿、潜在的人与现实的人、健康的人与生命末期的人等,由于其扮演的角色及承载的义务不同,其生命权大小也不同。”早期胚胎与胎儿,虽然具有人的基因组甚至人的种生命,但还不是一个独立状态的人,尚不具有人的生命尊严。尊严作为一项权利,“这项权利的载体却又不像生命权利的载体那样广泛。如胚胎或胎儿,虽然享有生命权,但因感受不到侮辱,故无法享有尊严权……尊严这项权利并非为所有人类生命形式所享有,就像选举权的拥有必须是以一定的认知能力为前提条件那样”[13]。尊严是人维护自我的独特性、相互关怀、避免侮辱的权利,它源自人作为人所内存的规定性及其基本的情感和精神需求。一个罹患绝症生命垂危而又痛苦不堪的人,虽然其生命的尊严依然存在,但因痛苦的感受和对医疗器械的依赖,其心理尊严无疑会受到损害,植物人尽管感受不到自己尊严的损害,但其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即社会尊严可能会有所改变。我们虽然不能将人的生命价值与生命尊严画上等号,但人的生命价值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人对其生命尊严的道德判断。由于植物人已失去自我意志和意识,失去了对尊严的内心感受,已无其内在的目的和价值,更不可能再为家庭、他人或社会创造外在的价值,如果此时仍继续对其进行无意义的救治,在身体上插满胃管、尿管、氧气管等异物,不仅是对其身体主体的粗暴干预,也是对其社会尊严、形象的损害。因此,在现有的医学技术条件下,笔者赞同放弃对植物人的救治,但这并不意味着植物人不再是人或已经死亡,而是因为继续救治已不可能提升其生命尊严和心理尊严,放弃治疗更有助于留下其曾有的健康形象、声誉和价值,维护其社会尊严。同样,对于脑死亡患者,尽管其心跳、呼吸等生命体征可能会短暂地持续,但已经临床判定、神经脑电确认试验、自主呼吸激发试验等加以判定,其种生命就不可逆转,其类生命也将随着种生命的终止而消失。即使心跳、呼吸尚在进行的那一刻,其身体反射包括植物人所具有的膝跳反射等功能亦不复存在,作为身体主体业已死亡,身体已成为尸体,继续救治更无益于其生命尊严和社会尊严的捍卫。当然,作为人的社会尊严并不因种生命和类生命的消失而消失,其曾经的名誉、声望、贡献等仍应得到与生前一样的保护和尊重。
总之,人的生命是种生命与类生命的统一,需要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来界定,应当有身体的在场。意识与人并非直接统一的存在,对人及其生命的诠释关涉着生命伦理的本原性问题,影响着胚胎、无脑儿、植物人等生命个体道德地位的厘定及其处置方式,有待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1] 最新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M]. 徐涤宇,译注.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3.
[2] 何兆雄. 医学伦理学概论[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37.
[3] 高清海. “人”的双重生命观:种生命与类生命[J]. 江海学刊,2001(1):78-84.
[4] 邱仁宗. 生命伦理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90.
[5] 徐辉富. 现象学研究方法与步骤[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27,31.
[6] 胡塞尔. 笛卡尔沉思与巴黎演讲录[M]. 张宪,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47.
[7] 徐辉富.现象学研究方法与步骤[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8] 许志伟. 生命伦理对当代生命科技的道德评估[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62.
[9] 辛格. 实践伦理学[M]. 刘莘,译. 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192.
[10] 邱仁宗. 论“人”的概念:生命伦理学的视角[J]. 哲学研究,1998,17(9):26-35.
[11] MERLEAU-PONTYM.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M].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8:141.
[12] 甘绍平. 人权伦理学[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142,160.
[13] 甘绍平.人权伦理学[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