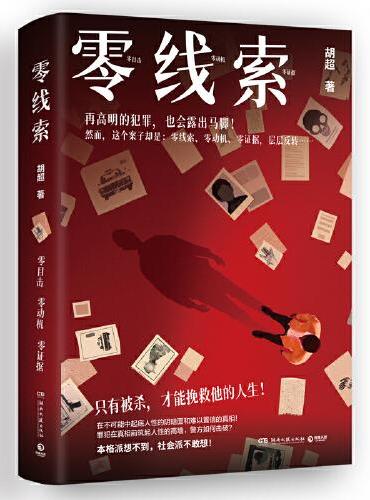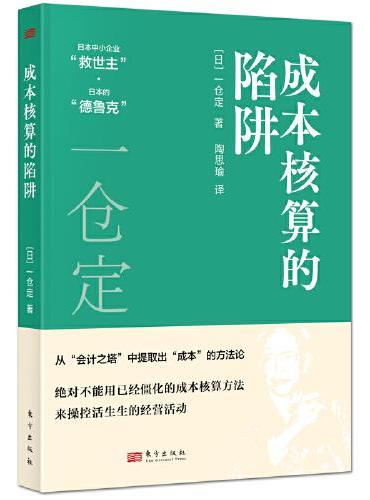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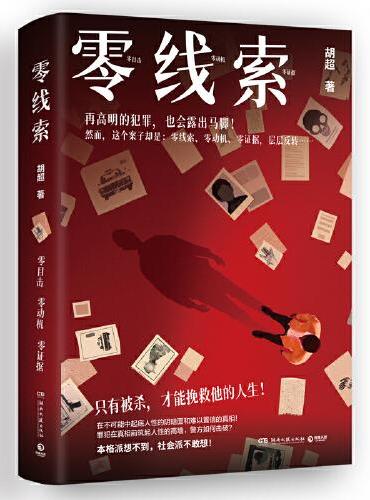
《
零线索(只有被杀,才能挽救他的人生!)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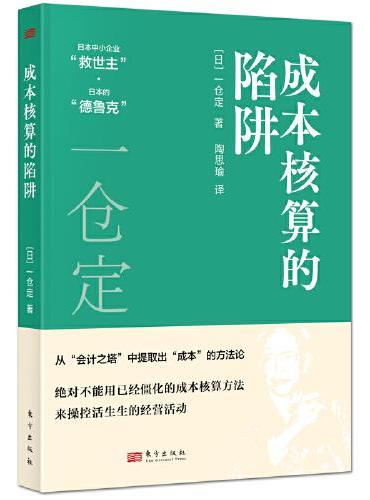
《
成本核算的陷阱
》
售價:NT$
214.0

《
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万有引力书系)
》
售價:NT$
484.0

《
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
》
售價:NT$
528.0

《
活力物质:“物”的政治生态学
》
售價:NT$
435.0

《
哪吒传漫画(1-4册)
》
售價:NT$
396.0

《
我是时代的孩童:陀思妥耶夫斯基随笔选
》
售價:NT$
484.0

《
捡来的瓷器史(2024年“最美的书”,从偶然捡到的古瓷碎片中发现中国瓷史的重要瞬间)
》
售價:NT$
869.0
|
| 編輯推薦: |
戏剧、 电影、行为艺术、音乐、脱口秀、法庭程序……
在数字化的当下,现场意味着什么?
美国教授奥斯兰德为您解读
|
| 內容簡介: |
《现场性:媒介化文化中的表演》 探讨的可能是当今各种表演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一个由大众媒介和数字技术主导的文化中,现场表演的地位如何?
菲利普·奥斯兰德的这本开创性著作自问世以来,已经推动了一个新研究领域的重新界定。通过探讨现场表演的具体实例,如戏剧、音乐、体育和法庭证言,《现场性》对媒介文化提出了深刻的见解,认为媒体技术已经侵入了现场活动,以至于许多活动根本就不是现场。在这个新版本中,作者彻底更新了他的挑衅性论点,将互联网的影响以及文化、社会和法律的发展纳入考察范围。在解开围绕着现场活动高雅文化地位的最后一些观念桎梏的过程中,这本经典著作将继续塑造公众观念,并就一个关键的艺术困境引发热烈辩论:什么是现场表演?它现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这本经过整体修订的新版《现场性》是所有学习表演课程的学生和学者的B读之作。
|
|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菲利普·奥斯兰德 (Philip Auslander)
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乔治亚理工学院文学、 媒体和传播学院表演研究和流行音乐学教授,其研究涉及戏剧、 电影表演、行为艺术、音乐、脱口秀、机器人表演和法庭程序等多个领域,代表著作包括《在音乐会上·:表演音乐人格》《重新激活:关于表演及其文献的论文》 《表演华丽摇滚:流行音乐中的性别与剧场性》等。
【译者简介】
陈恬,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教授。
|
| 目錄:
|
【目 录】
第三版序
第一章 导言
关于章节
第二章 媒介化文化中的现场表演
现场表演的文化经济:表现与重复
现场与媒介化表演的易逝与分发
反对本体论
电视戏院
现场表演的媒介化
互联网时代的现场性
生命的证明:疫情的表演(一则后记)
一则个人注释
第三章 音乐中的现场性与本真性话语
音乐的文化经济
现场音乐与媒介化
音乐的本真性
本真性的悖论
可信度
乐器性、本真性和电子音乐
技能 vs. 控制:音乐才能的新范式
第四童 法定现场:法律、表演、记忆
电视法庭,或录像带审判之可抵抗的崛起
疫情时期的诉讼
你不拥有我:表演与版权
作为版权的表演:习惯法版权、不正当竞争、形象权、商标
咕噜问题
法律与记忆
第五章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
| 內容試閱:
|
导言
在一次以“为什么是戏剧:新世纪的选择”为题的会议这次会议于1995年秋在多伦多举行,由多伦多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主办。上,会议章程提出了一个问题,直指我在本书所关切之事的核心:“戏剧和媒介:是对手还是伙伴?”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两者皆是。戏剧,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现场表演,以多种方式与媒介合作,首先,现场和媒介化的形式是相互界定的:如果没有两者,区分就毫无意义。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第三章中讨论的音乐会和录制音乐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在文化经济我用“文化经济”一词来描述一个考察领域,它既包括文化形式之间的实际经济关系,也包括不同文化形式所享有的文化声望和权力的相对程度。层面上,戏剧和现场表演与大众媒介往往是竞争对手。从历史上看,电视侵夺了剧场的文化地位和观众,而现场表演的普遍趋势则是通过技术融合而变得越来越像媒介化表演,这是一种竞争策略。
在一篇关于戏剧和电影的文章中,赫伯特·布劳(1982:121)引用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特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余的生产,它的关系因此为其他生产分配等级所影响。它是一种普照之光,一切其他颜色都沐浴其中,并改变它们的特殊性。它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决定了在其中具现的每一个存在的重量。虽然马克思描述的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之下的工业生产,但对布劳而言,“他倒不妨说是在描述电影”。我与马克思和布劳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认为马克思也可能是在描述数字屏幕,无论是电视、电脑还是智能手机。马克思提及普照之光和以太(在早期关于广播的讨论中,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电子波通过的介质),相比电影,它们更适用于这些无处不在的屏幕散发的光亮。
确实,广播电视现在是一种处境艰难的媒介,深陷在与各种流媒体的竞争中,并寻求向流媒体进军。尽管如此,电视仍然是目前在统计学上占主导地位的媒介。此外,电视早已超越了其作为一种特殊媒介的身份,而作为“电视性”(the televisual)充斥在文化中。电视性之名意味着……媒介在一个语境中的终结,而电视作为语境到来。显而易见,电视必须被认为是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它的传输不再由开关来控制。(Fry 1993:13)即使电视本身不再是曾经的文化核心机构,数字媒介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电视化的。因为现场表演是最直接受到电视媒介主导地位影响的文化生产类别,所以解决现场表演在我们的媒介化文化中的处境问题,就显得尤为紧迫。
在为写作本书而调查现场表演的文化价值时,我很快就对那些我认为是传统的、不加反思的假设感到不耐烦,它们在试图解释“现场性”的价值时,除了援引陈词滥调和故弄玄虚,诸如“现场戏剧的魔力”、据说存在于现场活动中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能量”,以及现场表演在表演者和观众之间创造“共同体”之类的说辞,此外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明白这些概念对于表演者和现场表演的拥护者来说确有价值。实际上,特别是对于表演者而言,他们甚至可能必须相信这些概念。但是,当这些概念被用来描述现场表演和它目前所处的媒介化环境之间的关系时,它们产生了现场与媒介化的归纳性二元对立。史蒂夫·沃兹勒(1992:89)沃兹勒(Wurtzler 1992:8990)挑战了这种二元对立,他断言“现场和录制这两种社会建构的类别,不能解释所有的表征实践”。他提供了一个图表,各种事件根据空间和时间向量被定位。其中出现了两类既非纯粹现场也非纯粹录制的表现形式:一类是表演和观众在空间上分离,但在时间上共存(如电视直播或广播直播);另一类是表演和观众在空间上共存,但表演的元素是预先录制的(如对口型演唱会,体育场视频显示器上的即时重播)。很好地总结了这种传统观点:作为社会和历史的产物,现场和录制这两种类别被定义为一种互斥的关系,因为现场的概念是以没有录制为前提的,而定义录制的事实则是没有现场。在这一传统中,“现场代表了一个完全处于表征之外的类别”(ibid.:88)。换言之,通行的假设是,现场事件是“真实的”,而媒介化的事件则是对真实的次要的、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复制。在第二章中,我将论证这种思维不仅在整个文化中持续存在,甚至在当代表演研究中也是如此。本章的论点旨在挑战关于现场性及其文化地位的传统思维方式,即采用其术语(传统的二元对立),然后对这些术语本身进行批判。本书整体上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现场性”不应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无差别的现象来研究,而应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与特定的文化形式相联系。
也许是因为我对传统看法的不耐烦,我有时会被误认为是一个不重视甚至仇视现场表演的人。事实远非如此:我对现场表演的文化地位的兴趣,直接来自我作为一个受过戏剧训练的演员的背景,以及我感到在我所生活的这种文化中,现场性的价值正在不断地被重新评估。尽管我自己钟爱戏剧和其他形式的现场表演,但在本书中,我试图采取一种相当冷静的、非感性的方法,去挑战广为接受的观点。
行为艺术家和演员埃里克·博戈西安(Eric Bogosian)将现场戏剧描述为:针对充满电子媒介精神污染的有毒环境的药物……戏剧使我的头脑清醒,因为它消除了媒介疯狂的潜台词洗脑,并把潜台词大声喊出来……戏剧是仪式。它每一次发生,都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戏剧是神圣的。我们不是被阴极射线管轰击,而是在对自己说话。人类的语言,不是电子噪音。(1994:xii)博戈西安对现场表演的价值的认识,显然来自它只存在于当下(“每一次发生”),以及假定它有在参与者(包括表演者和观众)中创造共同体(如果不是宗教团体的话)的能力。这两个问题我都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对于目前的讨论最重要的是,他将现场表演置于与媒介化对立的关系中,并将反对大众媒介强加给我们“电子噪音”这一压迫性制度的社会功能,甚至是政治功能,赋予了现场表演。这种对立关系,以及现场表演表面上的治疗能力,大概来自现场和媒介化文化形式之间重要的本体论区别。这种对现场和媒介化之间的对立关系的认识激发了我自己的论述,我希望在第二章讨论现场表演本体论时解构这种对立。
我对“媒介化”一词的使用隐含着几个重要前提。最初,我从让·鲍德里亚 (1981)那里借用了这个词,他不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描述媒介产物的中性术语。相反,他认为媒介是一个更大的社会政治过程中的工具,这个过程将所有的话语置于一个单一符码的支配之下。
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用这个词来表明某个特定的文化对象是大众媒介或媒介技术的产物。“媒介化表演”是指作为音频或视频记录,以及其他基于复制技术的形式,在电视上传播的表演。由于这个原因,我发现对于我的目标而言,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的定义比鲍德里亚的定义更有用。在夏瓦(2013:2)看来,媒介化理论的前提是当代文化和社会被媒介所渗透,以至于媒介可能不再被视为与文化和社会机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反而是要设法了解社会机构和文化进程是如何因媒介的无所不在而改变其特征、功能和结构的。夏瓦(ibid.:20)研究的两个核心文化机制是他所说的“直接”和“间接”媒介化。直接媒介化指的是以前的非媒介活动转换为媒介形式的情况,也就是说,活动是通过与媒介的交互进行的。直接媒介化的一个简单例子是国际象棋从实体棋盘到电脑游戏的连续转变。在表演艺术领域,观看《汉密尔顿》(Hamilton)的流媒体版本或聆听录制音乐是直接媒介化的例证。“间接媒介化是指一个特定的活动在形式、内容、组织或语境方面越来越受到媒介符号或机制的影响。”(ibid.)我在第三章讨论的一个间接媒介化的例子是YouTube交响乐团。尽管该乐团是一个传统的音乐团体,但它与YouTube的文化和经济关系,以及它通过在线面试建立组织,并通过在线追踪程序发展,由此导向在卡内基音乐厅的现场表演,而这场表演也以视频的形式呈现,这都标志着它是一个间接媒介化版本的乐团。在本书中,我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了夏瓦的语汇。
我将现场表演和媒介化表演视为参与同一文化经济的平行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媒介化”的使用遵循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对该术语的定义:“传统艺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媒介系统中多种媒介之一的进程。”(1991:162)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66:25)在其关于戏剧和电影的文章中,将这两种形式进行了对比,她说:“戏剧从来不是一种‘媒介’”,因为“人们可以把戏剧做成电影,但不能把电影做成戏剧”。我在第二章中的部分讨论旨在证明桑塔格是错误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做成”的戏剧由来已久,现场表演甚至可以作为某种大众媒介发挥作用。桑塔格的评论所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戏剧和现场表演艺术大体上属于一个独立于大众媒介的文化系统,而在詹姆逊的意义上,现场表演形式已经被媒介化了:它们迫于经济现实,承认自己在包括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在内的媒介系统中的地位。一些剧院含蓄地承认了这种情况,打出了类似于亚特兰大联盟剧院外的横幅,宣称其产品“不提供视频”,这表明在当前的文化氛围中,为现场表演的经验赋予特殊性的唯一方式,就是参照媒介化经验。
毫无疑问,现场表演和媒介化形式在文化市场上争夺观众,而且媒介化形式在这场竞争中获得了优势。百老汇制作人马戈·莱昂(Margo Lion)对戏剧在这种竞争性文化经济中的地位的观察,可以普遍适用于现场表演:“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都在争夺同一笔娱乐资金,而在这种环境下,戏剧并不总是排在首位的。”(引自里克·莱曼[Rick Lyman]:《台前幕后》,《纽约时报》1997年12月19日,B2版)。布劳(1992:76)阐述道:[戏剧的]地位不断受到阿多诺所说的文化产业和……媒介不断升级的主导地位的威胁。“你经常去看戏吗?”
许多人从未去过,而那些去过的人,即使是在拥有悠久戏剧传统的国家,他们也会去其他地方,或者留在家里看有线电视和录像,这也是戏剧的事实,实践的基准。正如布劳所认识到的,戏剧以及其他形式的现场表演,与在市场上更占优势的媒介化形式直接竞争。他把现场表演与媒介化竞争的压力称为“实践的基准”,认为表演实践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这种压力,体现在表演发生的物质条件、观众的构成及其期望的形成,以及表演本身的形式和内容上。
将现场表演和媒介化表演视为同属一个媒介系统,这种思考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现场表演被刻印在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64:158)所定义的媒介历史逻辑中:“一种新媒介从来不是对旧媒介的补充,也不会与旧媒介和平共处。它从未停止过对旧媒介的压迫,直到为它们找到新的形状和位置。”杰伊·博尔特(Jay Bolter)和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 1996:339)用他们的“补救”概念,即“一种媒介在另一种媒介中的表现”,完善了这一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新的表现技术是通过改革或补救先前的技术来展开的”(ibid.:352)。我在第二章中讨论戏剧和早期电视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电视对现场表演的取代,就是描述这种历史逻辑在该实例中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尝试。第三章在音乐的语境中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质言之,对于媒介化形式的压迫和经济优势,现场表演的一般反应是尽可能肖似它们。从装备即时重播屏幕的球赛,重现音乐视频图像的摇滚演唱会,到电视节目和电影的现场舞台版本,再到舞蹈和行为艺术与视频的结合,媒介化对现场活动的侵入在所有表演类型中都能找到证据。
这种情况给那些重视现场表演的人带来了焦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可能正是出于这种焦虑,他们才需要说明现场表演具有超越和抵制市场价值的重要性。在这种观点中,现场表演的价值在于它对市场和媒介、它们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以及支持它们的文化生产体系的抵抗。由于许多原因(将在下面的章节中阐述),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先前存在于现场和媒介化之间的区别逐渐缩小,现场活动变得越来越像媒介化活动,对我来说,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场形式和媒介化形式之间是否真的存在明确的本体论区别?尽管我最初的论点似乎是建立在有区别的假设之上,但最终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如果现场表演不能被证明在经济上独立于媒介化形式,不受其污染,并且在本体论上与之相区别,那么在何种意义上,现场性可以成为文化和意识形态抵抗的场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