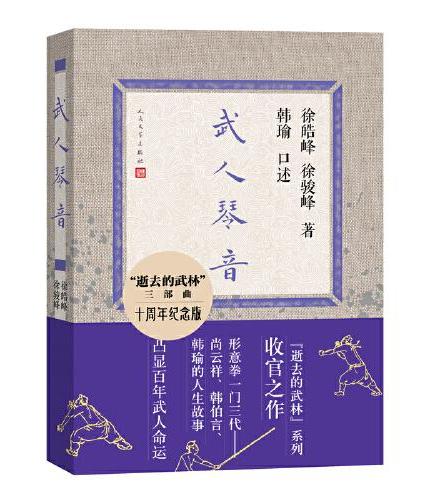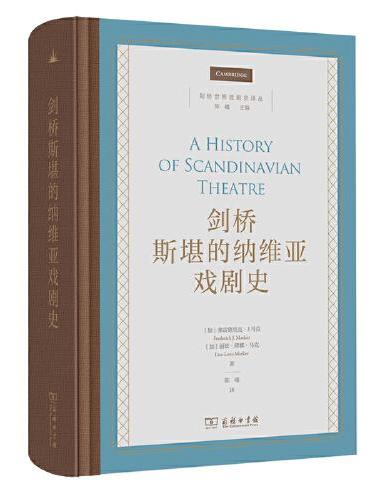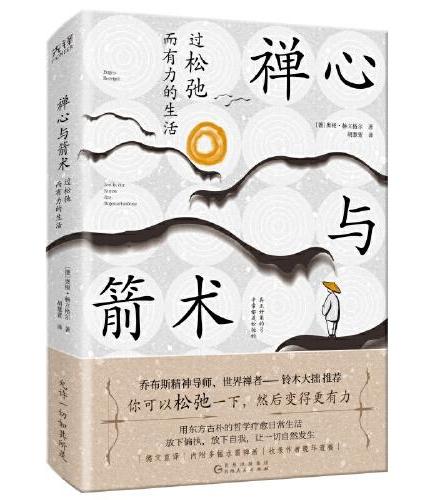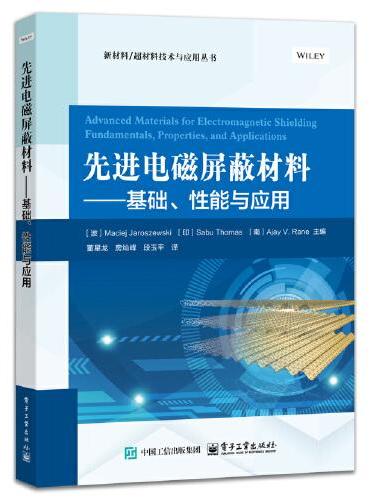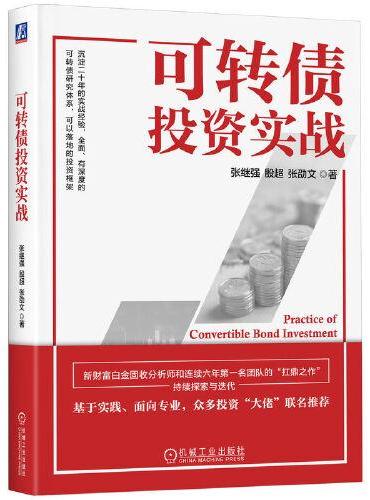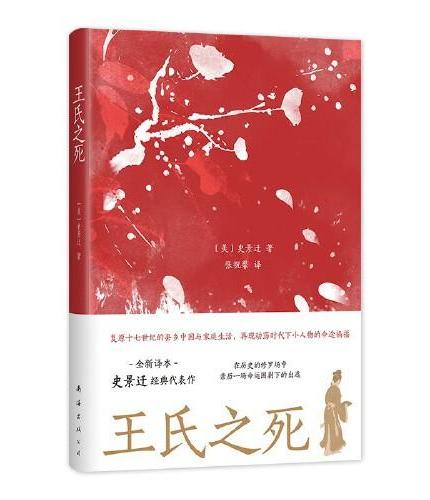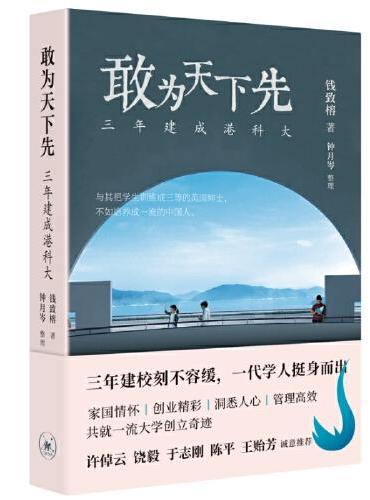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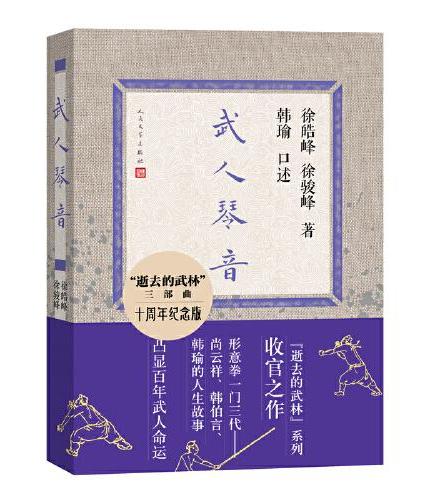
《
武人琴音(十周年纪念版 逝去的武林系列收官之作 形意拳一门三代:尚云祥、韩伯言、韩瑜的人生故事 凸显百年武人命运)
》
售價:NT$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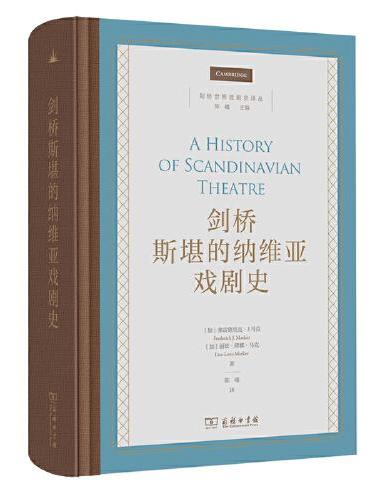
《
剑桥斯堪的纳维亚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NT$
7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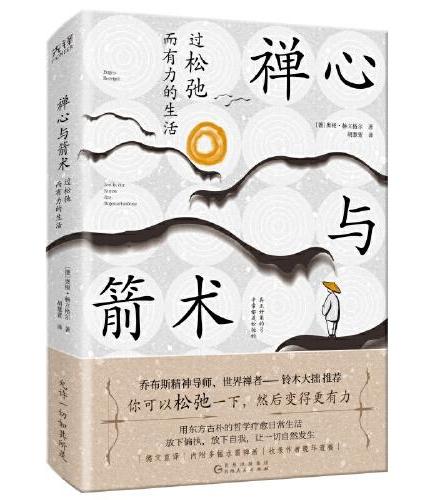
《
禅心与箭术:过松弛而有力的生活(乔布斯精神导师、世界禅者——铃木大拙荐)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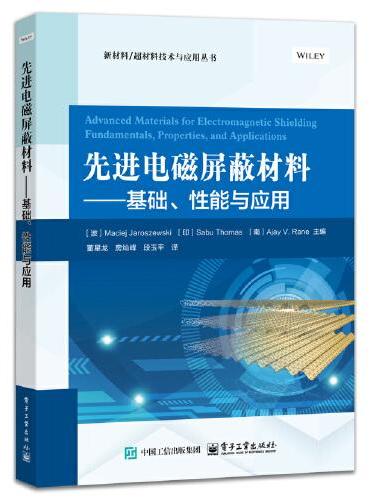
《
先进电磁屏蔽材料——基础、性能与应用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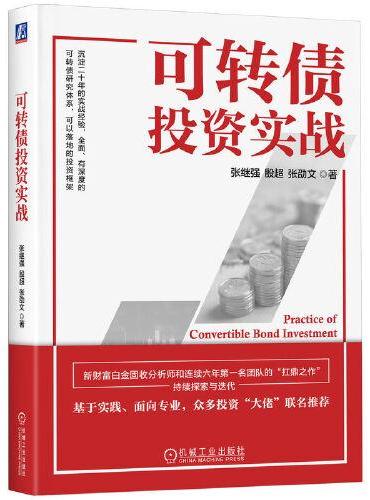
《
可转债投资实战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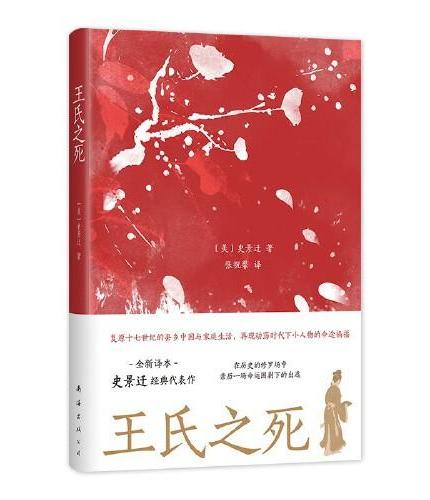
《
王氏之死(新版,史景迁成名作)
》
售價:NT$
2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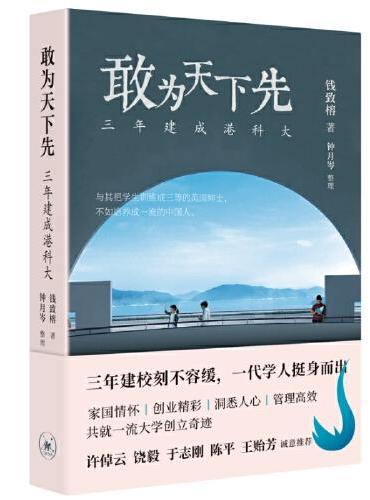
《
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
》
售價:NT$
352.0

《
直观的经营:哲学视野下的动态管理
》
售價:NT$
407.0
|
| 編輯推薦: |
在鲁迅同时代人的同类著作中首屈一指。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必需书。民国时期文化名人、鲁迅生前密友、知名高校教授所著,
最真实、最权威的《鲁迅传》。
|
| 內容簡介: |
|
许寿裳于日本留学期间与鲁迅相识,并结为终身挚友,1937年与周作人共同编撰《鲁迅年谱》。他撰写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这两部回忆录,时间跨度长,内容翔实,范围广博,感情深挚,文笔淳厚,在鲁迅同时代人的同类型著作中首屈一指,是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入门书。本书收录了《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等,许寿裳关于鲁迅的一系列文章,为读者了解鲁迅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
|
| 關於作者: |
|
许寿裳,早年就读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1902年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历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西北联大等校教授。1946年台湾行政长官陈仪邀请许寿裳主持台湾省编译馆,不久编译馆裁撤后并入教育厅管辖,转往台湾大学任教。
|
| 目錄:
|
目录
上篇亡友鲁迅印象记
小引/
1剪辫/
2屈原和鲁迅/
3杂谈名人/
4《浙江潮》撰文/
5仙台学医/
6办杂志、译小说/
7从章先生学/
8西片町住屋/
9归国在杭州教书/
10入京和北上/
11提倡美术/
12整理古籍和古碑/
13看佛经/
14笔名鲁迅/
15杂谈著作/
16杂谈翻译/
17西三条胡同住屋/
18女师大风潮/
19三一八惨案/
20广州同住/
21上海生活——前五年/
22上海生活——后五年/
23和我的交谊/
24日常生活/
25病死/
读后记/
下篇我所认识的鲁迅
1我所认识的鲁迅/
2怀亡友鲁迅/
3回忆鲁迅/
4怀旧/
5鲁迅的人格和思想/
6鲁迅的精神/
7鲁迅与民族性研究/
8鲁迅的避难生活/
9关于《弟兄》/
10鲁迅的游戏文章/
11《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
12《鲁迅旧体诗集》序/
13《鲁迅旧体诗集》跋/
附录一鲁迅古诗文的一斑/
附录二鲁迅书信?致许寿裳/
附录三鲁迅先生年谱/
|
| 內容試閱:
|
小引鲁迅逝世,转瞬快到十一周年了。那时候我在北平,当天上午便听到了噩音,不觉失声恸哭,这是我生平为朋友的副眼泪。鲁迅是我的畏友,有三十五年的交情,竟不幸而先殁,所谓“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因此陆续写了十多篇纪念的文字,如《怀亡友鲁迅》、《怀旧》、《鲁迅的生活》、《回忆鲁迅》、《关于〈兄弟〉》、《鲁迅和民族性研究》、《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鲁迅诗集序》、《鲁迅的几封信》等,都是“言之未尽,自视欿然”。近来,好几位朋友要我写这印象记,我也觉得还有些可以写的,只是碌碌少暇,未能握笔。近景宋通信也说及此事,有“回忆之文,非师莫属”之语;我便立意随时写出,每章只标明目次,不很计其时间之先后。可惜现在身边没有《鲁迅全集》,有时想找点引证,多不可得,这是无可奈何的!
剪辫
一九○二年初秋,我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东京留学,初入弘文学院预备日语,鲁迅已经在那里。他在江南班,共有十余人,也正在预备日语,比我早到半年。我这一班也有十余人,名为浙江班,两班的自修室和寝室虽均是毗邻,当初却极少往来。我们二人怎样初次相见,谈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大约隔了半年之后吧,鲁迅的剪辫,是我对他的印象中要算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
留学生初到,大抵留着辫子,把它散盘在囟门上,以便戴帽。尤其是那些速成班有大辫子的人,盘在头顶,使得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口里说着怪声怪气的日本话。小孩们见了,呼作“锵锵波子”。我不耐烦盘发,和同班韩强士,两个人就在到东京的头一天,把烦恼丝剪掉了。那时江南班还没有一个人剪辫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监督——官费生每省有监督一人,名为率领学生出国,其实在东毫无事情,连言语也不通,习俗也不晓,真是官样文章——不允许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监督姚某,因为和一位姓钱的女子有奸私,被邹容等五个人闯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我也兴奋地跑去看过的。姚某便只得狼狈地偷偷地回国去了。鲁迅剪辫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大约还在姚某偷偷回国之先,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阿,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此情此景,历久如新,所以我说这是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一个印象。
鲁迅对于辫子,受尽痛苦,真是深恶而痛绝之,他的著作里可以引证的地方很多,记得《呐喊》便有一篇《头发的故事》,说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晚年的《且介亭杂文》里有云: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病后杂谈之余》)
鲁迅回国之后,照例装假辫子,也受尽侮辱,同书里有云:“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同上)
鲁迅的那篇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有云:……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
看了上面所引,鲁迅在初剪辫子的时候,那种内心的喜悦,也就可以推测,无怪不知不觉地表现到脸上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