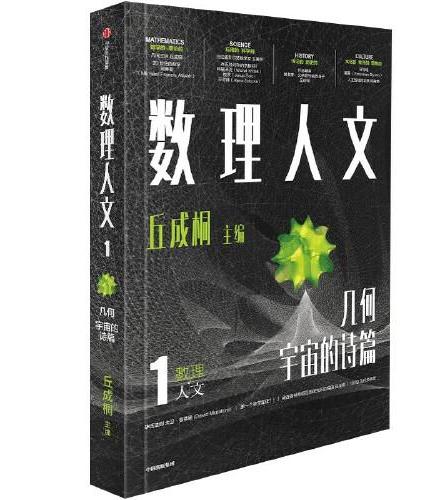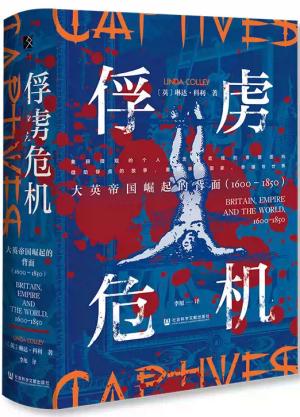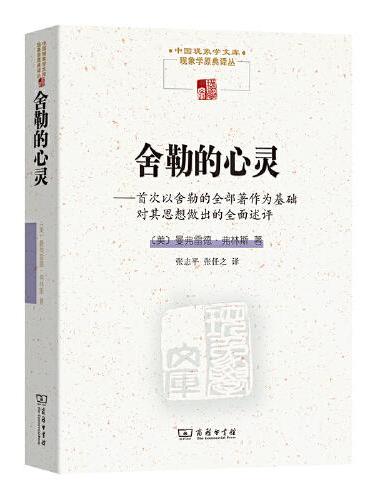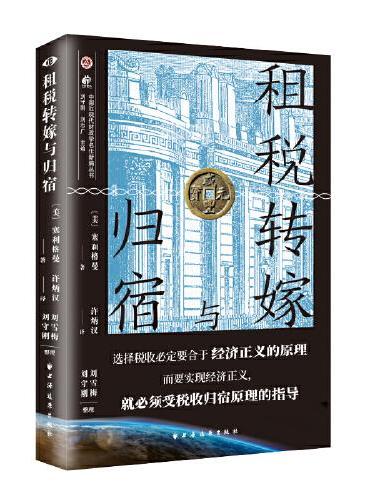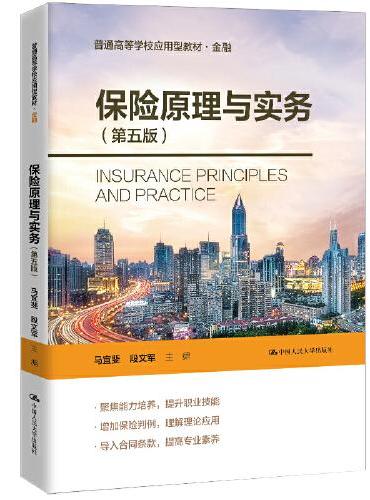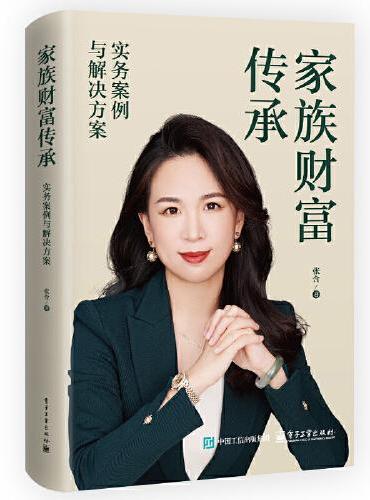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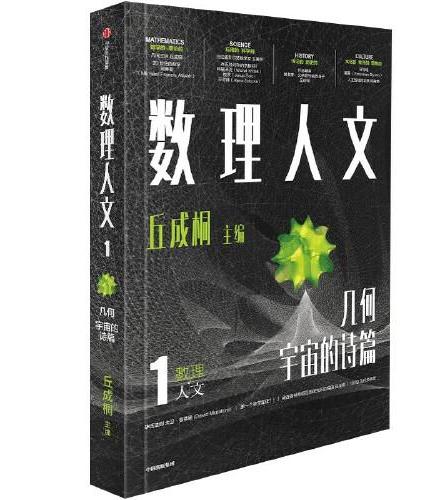
《
数理人文(第1辑)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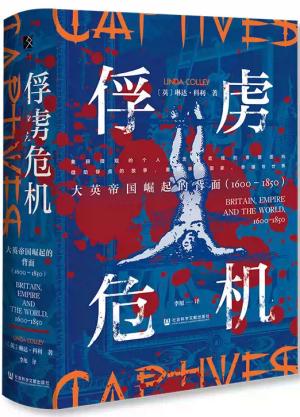
《
俘虏危机:大英帝国崛起的背面(1600~1850)
》
售價:NT$
607.0

《
家庭心理健康指南:孩子一生幸福的基石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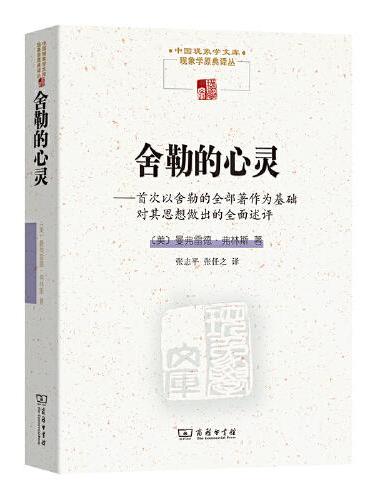
《
舍勒的心灵(中国现象学文库·现象学原典译丛)
》
售價:NT$
3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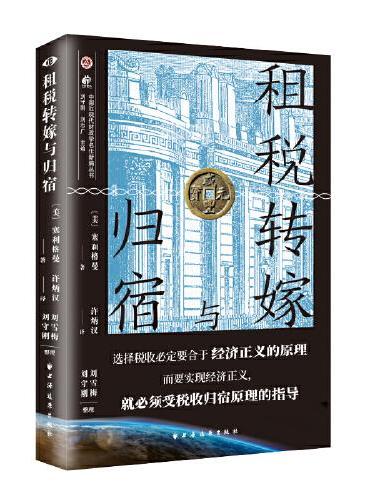
《
租税转嫁与归宿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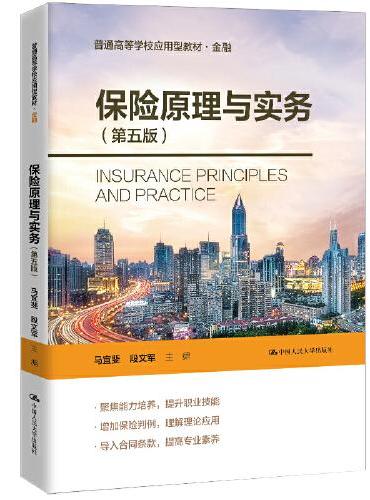
《
保险原理与实务(第五版)(普通高等学校应用型教材·金融)
》
售價:NT$
230.0

《
十三邀Ⅱ:行动即答案(全五册)
》
售價:NT$
14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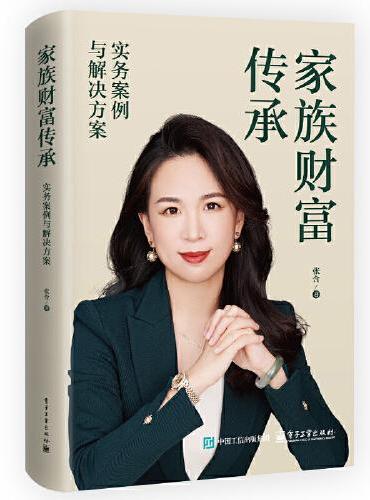
《
家族财富传承:实务案例与解决方案
》
售價:NT$
454.0
|
| 編輯推薦: |
一部讴歌新时代祖国山川之美、普罗大众多彩生活的散文精品
自然美景与精彩的生活交相辉映的美丽图景
|
| 內容簡介: |
|
散文随笔集《镜水秋月》收录作者精选作品58篇,共分两辑:“流光碎影”“行旅拾英”。“流光碎影”记录亲情、友情,描绘生活情趣;“行旅拾英”赞美山川名胜,讴歌时代春天。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示出当代社会人们的多彩生活,饱含对生活和自然的热爱。
|
| 關於作者: |
|
葛新,男,安徽省巢湖市人,先后供职于安徽省巢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现居合肥。喜好读书写作,在各级报纸杂志上发表新闻稿件1100余篇、思想政治工作和劳动保障工作方面的研究论文40余篇、散文随笔160余篇,出版有杂文集《樗下沉吟》。
|
| 目錄:
|
自序 / 001
上辑行旅拾英
走读郊野 / 00
城市二咏 / 0
少年的河流 / 0
花香六月藕 / 0
正是群芳烂漫时 / 0
平野菜花春 / 0
巢湖岸畔写意 / 0
一城幽香 / 0
读楮 / 0
花竹幽窗午梦长 / 0
霜晨不萧瑟 / 0
窗外的小精灵 / 0
夜宿大山村 / 0
参谒海子故居 / 0
姑苏访友 / 0
沧浪亭情思 / 0
怀想“十字街” / 0
陋室隐 /
半枝梅的味道 /
褒禅山寻踪 /
触目亚父山 /
秦川大地行 /
下辑流光碎影
葫芦记 /
摸秋 /
西望都江堰 /
人过五十 /
昨夜今朝间 /
迁于乔木 /
暮年学驾 /
惜秋花 /
盲从的代价 /
梦里浏阳踏歌来 /
我的偶像 /
惦记一个人 /
惜福 /
“漂亮”父亲 /
祭念岳父 /
父子连心 /
致孙儿 /
怀中的春天 /
家 /
窗外的阳光 /
别样的招待 /
旅途纪事 /
谚语里的美味 /
|
| 內容試閱:
|
走读郊野
一、引子
推开城市的门,从喧嚣嘈杂中分离出来,我听见自己敲击地面的脚步声,嚓、嚓、嚓……
此刻,日头西斜,我正恣意地行走在郊区的旷野。移动的身影,远处的人看去,以为是在赶路,或在散步,其实都不准确,我就是那么不紧不慢地走,时疾时徐地走,随心随意地走。间或,停顿下来,做一会儿漫无目标的瞭望。天空不再狭小与残缺,状若巨伞的穹顶下,地平线展露出它原有的开阔与邈远。我豁然感觉胸襟像天地一样的敞亮、空灵。一个人的郊野,真好,一路无语,心头却好似有鸟鸣欢唱,溪水潺潺。
这是我例行的健身走,每日的必修课。人离岗了,时间余裕贱如草。
我是一个乐生者,心理从众却又特立独行。最初是在大街小巷晃悠的,是和晨风暮雨同行的,可是走着走着,一个闪念,就走出了城郭,走向了郊野。城市是可喜的,繁华,热闹,动感而充满激情。不过相较这样的可喜,我更青睐另一种可爱。郊野就是可爱的,在扰攘与寂寥之间,它以中庸的姿态,把动与静、文与野恰到好处地糅合在一起,织成浓淡相宜的过渡带。带子上落着城市之光的余晖,却不失山水田园的本色。我置身其间,用心去看,去听,去嗅,以至情不自禁地去触摸,不觉在惬意之余,隐隐地有所发现。
二、山水
依我之见,一座城,依山,便增了英气;临水,则添了灵气。诚如明人徐继善、徐善述所言:“有山无水谓之孤,有水无山谓之寡。”二者缺了一方,都是不美的。欣慰的是,我所在的城邑,“登高四望皆奇绝,三面青山一面湖”,真是上苍的恩赐,难得的一座山水城市,永远地瞧不够、登不厌。
登山、观水,是我经常活动的项目之一。近距离的,以步当车,远点儿的,则先坐一段公交,然后步行。三面的青山——银屏山、旗山、鼓山、汤山、岠嶂山、紫薇山、凤凰山、龟山及望城岗、放王岗,无不留下我重重叠叠的足印。这些位于江淮过渡带的山,皆为低山,高峰不过三百来米,或呈集群式,或做脉条状,或为孤立形,它们从不同的高度、不同的角度,为我打开了一方方天地,启我心智,壮我豪气。
本土曾流传着一首民谣:“一塔撑天系卧牛,晚萃亭内话许由。十景以外又三山,鼓打旗摇凤点头。名扬天下人文胜,曾出九公十八侯。”其中的“鼓打旗摇凤点头”,即鼓山、旗山和凤凰山,顾名思义,山形像鼓、像旗帜、像凤凰展羽,它们环城而立,仿如冷峻而威严的卫兵。因了近,我成了它们的常客。山上,昔日的泥石小径被草木淹没,从山脚铺建的水泥路曲折地通向峰顶。
稍稍留意一下,觉得有趣,那鼓山、旗山、凤凰山的峰顶,分别矗立着佛塔、寺庙和电视发射塔,貌似不伦不类,却隔山呼应,同时把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举向自由的天空。我之所以常登这几座山,可不是欲想昔日公侯之梦,仅仅只是想居高俯瞰市容市貌,检阅小城一年一年的变化。在汲取了头回经验后,通常我上午登旗山或鼓山,下午爬凤凰山,这是因为鼓山、旗山居东,凤凰山居北,要想看得市容清朗,须得避开逆光,顺着太阳走。其实,登山无季节,四季皆有景,只是依着时序嬗变而已。登上山巅远眺,小城一览无余,仿佛伸手就可把它揽在怀里,好不亲切。
四时节气里,清明前后最宜上山望远,这时候,山下的圩田和岗地里,金黄的油菜花怒放,连片连片的,望不到边,仿佛上天的画师作画时不小心打翻了颜料桶,漫天泼洒下来,明晃晃地照亮世界。心下或会想,有人放着身边的宝贝,跟风跑到千百里外的西递、婺源看油菜花,舍近求远真的傻;或又会沉醉其中,就想变只蜜蜂飞入花海里,飞回梦一般青葱年华的时光里,牵着心爱的人儿在花丛里嬉戏疯跑。
只是现在,我有个明显的感觉,感觉老来看山与早年大不同。小时候仰望这些山,仰得帽子都掉下了,那是多么的巍峨高峻啊!而如今,山好像老了,犹如老人一样萎缩,视觉里变成了丘包,似乎几个箭步就可蹿上顶去。思其故,是不是人生旅途中见过太多有形的山,也征服过太多无形的山,从而使人的意识与感知有了异化?大自然是神奇的,人也是微妙的。
山水是一对姊妹花,珠璧契合才为上。看山不看水,半渴;看水不看山,半饥。菜单里山水交融,方可餍足。
多年前,为探察水蓼,我曾花了两日骑车寻遍城内外,目力所触,深为吾乡的水系发达而骄傲。有人不以为然,平平淡淡,有啥看头。我想他错了,犯了视觉上的审美疲劳——熟悉的地方没风景。美的东西,不只裸露在视线里,还藏在意念里。比如,这个“三面青山一面湖”的巢湖,这个“万顷湖光吞岸白”的胜境,小城的居民恐怕没有几人没去看过,有人看了也就看了,至多落下个白浪滔滔的印象,或笼统地赞美一句“湖光山色而已”。我当然去看过,而且年年去,常常去,从西坝口分道,或朝南岸走,或沿北岸行,南至盛湾,北抵温家套。
观湖觅景的次数多了,终于发现,若要领略到胜景奇观,须在方位与时段上讲究。比如,湖光夕照——薄暮时分,站在小湾子堤段朝西望去,夕阳浮在湖面,轮廓鲜明如一枚巨大的橘子,霞光满照,风吹浪涌,碎金万点,闪闪烁烁,间或有帆影幢幢,鸥鸟掠过。禁不住会联想起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又比如,青山白屋——无分季节,也不论晨昏正午,从海军圩湖堤向南岸望去,尖山、楚歌岭一线就像一堵背影的墙,色苍如黛,山岚氤氲,在此映衬下,岸畔碧桂园小区白色的群楼分外醒目,招人向往。再比如,烟雨城郭——此时换个视角,当然是在雨天,转足碧桂园湖岸,把目光投向临湖而筑的小城,高层建筑物及城区两旁的山峦,躲在雨丝或雨后岚气织成的面纱后面,若明若暗,若即若离,朦朦胧胧如一幅神造的水墨画儿。
这样的湖,怎能不叫人欢喜?欢喜的不只是它衍生的风光,还有它本身。它是滋养我们生命的饮用水源,是生长“湖三鲜”——大闸蟹、银鱼、凤尾鱼的天堂。
凡诸水,净不净,容不容生灵,鱼先知,鸟也知。一面湖、一条河、一口塘,里面有没有鱼,有多少鱼,多大的鱼,以及鱼品纯不纯,可作为检测水质的简易标志。在巢湖、柘皋河、下阁河、双桥河、裕溪河、清溪河、半汤河,乃至城区内的环城河、陆家河、丁岗河,我就常常见到大大小小各色的水鸟,看到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的钓者的身影。就说清溪河吧,它在远郊,是两个县域的分界线,我多次坐公交到沫桥或山口站下,步行到河堤上溜达,用散淡的目光,沿途欣赏着各种各样的野趣。这条发源于邻县山区的河流,曾因上游造纸和化工排放,一度河水污染严重,时过境迁,而今平水缓流,清清幽幽,几米深的水下,隐约可见水藻在随流晃动。倘是春天,还可以听见鲫鱼在漂浮的水藻上打籽的啪啪声。
圣人云,智者乐水。我够不上智者,却是善者。我的博客名字,就叫“善水游鱼”。
三、草木
我曾写过一篇文字,题为《看树去》,说自己喜欢看树,往广里说是喜欢看植物。为识得更多的植物,叫得出更多的名字来,我曾对《诗经》里135种植物和《红楼梦》里267种植物做了研究,至今熟稔在心。城里的草草木木固然也美,譬如公园,譬如绿化带和行道树,但它们的种类和数量毕竟不敌野外,且生存空间也有别,人为施加的意志太多,多为千人一面,少了个性,看了很少为之打动。而郊野的则不同,乔木、灌木、藤类、草类、蕨类、藻类等植物品种十分丰富,且高矮胖瘦,交杂相处,一副无规无矩、形态迥然的样子。
我的闲走似乎也一样,毫无章法,跟着心情遛,遛到哪儿是哪儿。若是秋冬季节,偶或捡一根树枝握在手里,盲人似的点点戳戳,而逢春夏之日,则常于路边采一朵蒲公英绒球、拔一茎狼尾草穗,把在手里耍玩,那样子,一个无事可做的闲客范儿。我就是在这种散漫的状态下,将视线发散开来,捕捉周边的一切。
记忆里好像20世纪90年代后,乡下日常的烧茶煮饭渐渐用上液化气和电能,告别了稻草麦秸和野草杂木那种传统燃料。这为生态的恢复带来了福音。草木的本性,厌恶干预,喜“无为”,借助鸟儿、风儿,把种子撒遍山山岭岭。它们有它们的繁衍成长之道。
以鼓山为例,40年前,为开垦山地扩大农作物种植,山上的树木荒草被砍伐殆尽,光秃秃的,无遮无掩,一副黄巴巴的病态样,而今退耕还林,浴火重生,仿佛打个盹的工夫,变得一头的乌发,一脸的浓须厚髯。除了一片片人工栽植的马尾松,还有大量的野生黄檀、楮树、刺槐、山槐、朴树、棠棣、枫香、白榆、臭椿、毛栗、野山楂、山胡椒、卫茅、花椒、六月雪、绣线菊等等。你上了山,若是避开现成的路径私下乱走,走不出三五步的,那些密密匝匝的杂树和荆棘,非在你身上留下刮痕不可,尤其是苍耳和鬼针草,歪厮缠样地缠着你。我老家的祖坟就在山的南麓,坟都被齐腰的杂草和没人的灌木给掩盖了,不得不每年挥镰清理一两次。
就在这座山,20多年前我曾率单位员工,在山的西麓和北坡植下不少外国松苗,现在都已长成合抱粗,有时念起它们,我会特意拐过去望一望、摸一摸,感受时光的成长与岁月的老去。
自然真的很神奇,树木也分落叶乔木与常绿乔木,隐隐地透着平衡法则,譬如:落叶乔木,夏日遮阴,冬日透阳,物候循环,阴阳协和;而常绿乔木,在萧瑟凋敝的冬日,傲然醒目于旷野,彰显勃勃的绿色,点缀着自然的美好,给人以生机与希望。这在乡下的村庄,感受尤为明显。
村里人家依然沿袭传统,热爱在房前屋后栽树。偶然间,一次细心观察,我发现,从前备受青睐的椿、槐、杨之类的常见绿化树种失宠了,消失了。农民们赶新潮,追逐城市的流行风,越来越多地把常绿的香樟和广玉兰请到了门前,同时又不忘在传统的杏树、柿树的果木旁,迁入枇杷这位新移民。这些时尚的植物投下的树荫,好像也成了城乡趋向融合的一个影子。
如果从鉴赏的角度,看树还是宜往山地旷野里走,宜往少有人迹的地方去。山地旷野的树,彻底的自由主义者,野性,肆意,散漫。你看那伸展俯仰、旁逸斜出的各式姿态,就像人关起门来在家里,或者把脚搁在茶几上,或者把身子横躺在床榻上,怎么样舒服就怎么样生长。树们落地为家,不拘肥壤瘠地,仿佛吃粗粮干粗活的汉子,面上粗陋些,身子却高高大大,健健壮壮。
我想它们应该感谢风。风是树的至亲,始终关怀它们的成长,老是摇啊摇,摇得树们一棵棵根深叶茂,遒劲有力,天塌下来也压不垮。不像城里的行道树,少了风摇,根基弱,又修修剪剪,宝宝似的惯着,一场大雪便扛不住,枝杈砉然断送掉脆弱的美丽。
不知出于敬畏还是怜惜,我对楮树别具只眼。在义成圩南北埂道沿线、郭家圩和蔡家圩靠近河流的坡面,以及凤凰山东边脚下废弃的铁路,楮树疯长得如墉如栉,气势惊人。每次路过,我都会投以专注的目光,缓步细察,试图从中发现什么。楮树又叫构树,是一种非常普通的树种,抗逆性强,耐旱耐瘠,生命力极旺盛,郊野里几乎随处可见。可我一直奇怪,为什么人们大多不喜欢这种树?苏东坡说它是“不材木”,朱熹说它是“恶木”。
归结起来,瞧不上它的原因,恐怕还是以貌取“树”,嫌它外表不好看,嫌它非栋梁之材,又出于物滥则贱的心理,厌它碍眼。其实楮树浑身都是宝:甜美果实可供人鸟共享,树叶树汁可制药物,而树皮则是造纸的上等原料。这些特质已足够成为我们爱它的理由。其实每一种树,每一株树,最终都是有用的,或为绿化,或为器用,或为薪炭,即使庄子笔下的樗,无用亦为大用。不管别人怎样看,楮树之于我,一如袁中道在《楮亭记》所言,“深有当于予心”。于我,它是耐看的树种之一。
观赏草木,晴朗的日子出行固然是好,但要是逢上雨天,也有着别样的意蕴。静静地,一个人,撑把伞,最好选择村村通的水泥道,悠悠地走。这时候人影几无,山色空蒙,四野一片岑寂,唯雨沙沙沙……路旁的河流或池塘,水面上雨滴激起密集的水泡,炒豆似的蹦跳着,蹦着跳着,腾起的薄雾渐渐漫溢开来,偶或有家养的鸭群、鹅群剪浪而行,嘎嘎有声,分外响亮。
一会儿雨停了,万物洗刷一新,此时俯看脚边的狼尾草、牛筋草、地肤草、益母草、车前草、狗牙根、泽漆、飞蓬、牛尾蒿、野燕麦、婆婆丁、拉拉藤、菟丝子、蛇床子、石灰菜、曼陀罗、南瓜、扁豆诸般植物,叶片上躺着一团团水珠,叶尖上吊着一枚枚水珠,透明透明,晶亮晶亮,有微风拂来,轻微地晃动着,仿佛可闻琤琤玉音。倘若心念繁忙,无心观景,那便散散淡淡地朝前晃去,一路聆听雨打阔叶的声音,或雨打伞棚的声音也好。或者干脆,既不看又不听,闷头想心思也无妨,一个人的王国,一人坐天下,无纷无扰,自在。
我倒不是矫情,郊野踏看草木,看是一面,另一面则是呼吸泥土的气息,草木的气息,草木和泥土交融的气息。这种难以描述的气息,微微的,淡淡的,唯在周遭贞静中,心神宁静时,你才可以感受到肺叶里的畅然浸润。于途中,兴之所至,我常常会寻一静处,甩甩胳膊,扩扩胸,做一做难得的有氧运动。
四、鸟兽
城邑周边的山,有野猪出没,已不是新闻。但新近风闻,鼓山有狼嗥,我有点奇。鼓山不是那种连绵的山,是孤立的一座山,四围皆是农田,面积不大,海拔也不高。犹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这座山的最后一匹狼,被农人烟熏后从岩洞里拽了出来,此后再无狼的踪影。许是生态改善了,现在野狼回来了,只是,它从哪儿回来的呢?我没亲耳听过狼嗥,更没亲眼见过狼影,无法验证这个消息确切与否。但我在鼓山丛林里见到过野猪、獾子和草兔觅食,它们可是狼的美食,从食物链推断,狼的存在是可能的。
我没见过狼,却看到过黄鼠狼。这个学名叫黄鼬的机灵鬼,真是胆大而机警。有次走在旗山脚下的埂道上,忽然有只黄黄的身影闪到埂头,停了停,朝我瞅瞅,瞬间又箭一般地射向坡下的草丛中。我立马认出是黄鼠狼。这个高灵性的家伙,身上附着民间赋予的诡异色彩,容易使人联想到“察见渊鱼者不祥”那句话。但是我不信,不信则不灵,就像听喜鹊叫,欢喜,听乌鸦叫,也一样欢喜。
郊外的旷野平川,乌鸦偶见,常见的是喜鹊,更多的是麻雀。喜鹊爱凑热闹,喜欢把巢筑在靠近人烟的地方,比如村庄、道旁。要想确切知道哪里有喜鹊,最好是在冬季探寻它的巢,彼时树上的叶子凋零尽了,抬眼即可看得清清楚楚。但也有例外,譬如在靠近湖光村的湖滨大道,跨湖的高压电线塔上端,便坐落着一个硕大的鹊巢,碰巧时,你还会见到喜鹊飞上飞下,姿态甚为高傲的样子。而在地面树上筑的巢,则要比它小得多,也多得多,几乎每个村庄都有。
据说这些鹊巢不一定都是喜鹊住的,有的可能过了户,易了主,新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斑鸠。斑鸠懒得做窝,好强占喜鹊的巢,所谓“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是也。
我对有些鸟儿混淆不清,比如大山雀与白头翁。山斑鸠、珠颈斑鸠也是,我常当它们是鸽子,有时以为是大杜鹃。因其警惕性非常高,一般难以接近。通常它们都隐藏在高枝上,诡秘得很。
杜鹃科的,在我们这儿,常见的有大杜鹃和四声杜鹃。大杜鹃叫声似“布谷、布谷”,所以又叫布谷鸟;四声杜鹃又称子规鸟,叫声似“割麦插禾”“割麦割谷”。每逢雨前或雨后,你在路上走着走着,冷不丁地,远远近近的,或有斑鸠的鸣叫声传来。相比子规鸟的“割麦插禾”的婉转歌喉,民歌风味,斑鸠的嗓音低沉浑厚,粗犷嘹亮,犹似西洋的美声唱法。我仔细辨听过,斑鸠以“咕”咬字开腔,有点类似杜鹃,唱法有二连音、三连音、四连音,其四连音在第三声停顿一刹那,然后再咕一声,吐口气似的。这种咕咕咕的语言,表达着什么,传递着什么,我不懂,只好奇。据说斑鸠早晚唱法有些区别,不过我还没厘清。
我注意到,鸟雀们白天基本上是分散的,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它们要觅食,要谈婚论嫁,要生儿育女。而当薄暮降临,它们便纷纷集结,各归其宗,俨然一个鸟雀的社会和家庭组织。有天黄昏,我正在放王岗南麓的村道上埋头行走,忽有叽叽喳喳的声浪朝我袭来,侧眼望去,原来是斜对面的灌木林上落满了麻雀,估摸有上千只,也不知为家事还是为公事,闹嚷嚷的,吵翻了天。要是小时候遇见,我肯定会捡块石头扔过去,恶作剧一回,但今天没有,我不想用荒唐的不恭,惊扰一个自由而祥和的欢乐世界。
絮絮叨叨的这些鸟,归属于山鸟种群,它们四处飞翔,有的在城区内也可见到。而水鸟则不然,它们有特定的水域。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沿着巢湖湖滨大道散步,常常可以看到大批候鸟和留鸟,在沼泽湿地觅食和嬉戏,东方白鹳、白琵鹭、鸿雁、鸬鹚、反嘴鹬、野鸭,还有一些不认识的水鸟,它们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北方飞来,有的在此越冬,来年再返回北方,有的则把巢湖视为驿站,在此补充能量,短暂休息后继续往南或往北飞去。平日,天气正常的情况下,在裸露的湖滩浅水处,可见活动着的大量水鸟,但种类不多,以环颈鸻、红嘴鸥为优势种,苍鹭、扇尾沙雉、白鹡鸰、银鸥为常见种,黄鹡鸰、凤头麦鸡为稀有种。
本地常见的水鸟中,我喜爱的有两种。一种是白鹭。我一直以为白鹭只在巢湖水岸湿地栖息,未承想,在远离巢湖十几里的义成圩稻田里,居然落下三十多只。大片的稻苗正在拔节抽穗,白鹭们涉足其间,分散开来,有的低头觅食,有的昂起脖颈做悠闲的瞭望,远远看去,绿毯上嵌着星星点点的白,分明而耀眼,给人以美妙的视觉冲击。
另一种是。,吾乡称水葫芦,以前我一直当它是野鸭,其实不是,它比野鸭身量小得多,称它为小精灵实在恰当不过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在城西坝口至巢湖闸的湖面,以及天河、环城河,我都能见到它们小巧灵敏的身影。令我意外的是,有天散步到北城郊的老鹤窝村子的山塘边,不经意间往塘口瞅了瞅,竟发现两只正在菱角丛中扎猛子捕食,不知这些惹人怜爱的小家伙,是如何越城到这里来的。可见动物们挣口饭吃,也是历经艰辛,多么不容易啊。
宋末元初文学家舒岳祥有诗曰:“春花不及寒花耐,山鸟何如水鸟清。”看来他是偏爱水鸟,至于为什么,我不清楚。
五、庄稼
阳光、空气、水,土地、庄稼、人,看似各自独立的单元,实为息息相关的生命的链。庄稼活在土地里,人类活在庄稼里,生命的永恒,以转换形态的方式得以传承和延续。
我对庄稼的膜拜,心存至尊。记忆里的大饥荒,一碗米汤就可把路旁的饥饿者救活过来的镜头,总令我颤抖。土地不语,庄稼不语,凡诸为人者无不明白。
农民的骨子里安放着土地,眼眸里看守着土地,土地曾是他们的命根子。如今粮食作物虽然不再是收入主要来源,但若要他们抛弃土地,离开土地,不惜拿汗水挣来的银两去买一日三餐的口粮,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至少是剜心割肺般的痛,尽管明白钱粮可以互换。他们对土地的深情,对粮食的宝爱,早已转化成了基因。曾有一户农民因故被罚款,因拖延软抗,罚方强行拉走一车粮食,家中老人扑上去,倒在地上拦阻,哭喊着“宁愿给钱,也不能拖走我的粮食”。可见粮食对农民,有着不可替代的生死情结。
粮食出于庄稼,庄稼系着生命。所以土地是不能荒的,也不会荒的——尽管外地有抛荒现象存在,那是忘乎根本的罪孽。我在郊野一路可见,大片的水田、大块的坡地,长年青青的、绿绿的,便是沟坎地角那些碎片的隙地,也都种上了粮食、油料、瓜果、菜蔬之类的作物,一季接着一季,一茬接着一茬。有的农民进城安居,甚至把这种对土地和作物的感情延伸到城里,在小区的隙地、阳台的花盆,也不忘种几许蔬菜,散发着浓浓的生活味。
只是如今,除了集约式的种粮大户,一般人家只在自有的责任田里栽种单季稻,标准是够吃就行。从前的那种抢收抢种的“双抢”场面,早已沉入历史的册页里。
时代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农民的传统观念开始松动摇摆,他们爱恋着故土家园,爱恋着庄稼,却又赞叹和向往城市的生活。而城里的人,也觉着隔山那边美,不时把欣羡和赞叹的目光投向乡村田园。曾有都市的居民兴起一股风,到郊区租用农户的土地,自己种菜种果,或者委托农户代耕代种,体验劳动之获,为了生态食品的安全和新鲜。这种时风也蔓延到了小城。
我的两个同学,就在半汤山岗租了50亩地,盖了房。开荒植下的果木间,季节性地种着玉米、大麦、芝麻、花生、紫薯和菜蔬,又掘了山塘,饲养了鸡、鸭、鹅,不了解的人还真以为是农户人家。我去观赏过,更多的是平日享受着他们馈赠的成果。
我不会种庄稼,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庄稼之美的激赏。我从田间地头走过,视线里的稻子、麦子、油菜,连片连块的,衣装整齐划一,面容清爽俊秀,排队似的端然立着,感觉就像是士兵的方阵,而我分明就是个检阅的将军,不由得自大起来,暗自欢喜。
我用目光抚摸它们,亲昵它们,想着秧苗从萌发、拔节到吐穗、结实,从绿油油的身姿到黄灿灿的靓影,一路跟着季节走,走向周而复始,走向时光深处。时光若是回到从前,年轻的时候遇见这样的景象,我定会激情澎湃,就像当年登青城山一样,唰唰唰,写上好几首诗。但现在很平静,于平静中,我只闻到了饭香,闻到了油香。
闻着,闻着,忽然有一天,我惊悚地闻到了一种“异味”。那是去年5月,下午五点钟光景,我走到义成圩杨陆村口,被眼前的场景震骇了:上百亩的圩田,凄凄惨惨戚戚,枯黄成一片褐色,就像是凋敝的冬季来临。时值初夏,大地有土的地方,无不翠翠绿绿,而这般景象到底何故?趋前问农人,答说,喷洒了除草剂,等草死光了,过些天泡泡水,再将稻种撒到田里就行了。我又问,田土不翻吗?村人笑了,说,犁田麻烦,谁还用牛呀,如今可省事了,洒洒农药、撒撒化肥,就坐在家里收粮食啦。我茫然。怪不得我没见到耕牛,原来农民是用这种方法种田呀!语云,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看来,这主粮安全,怎一个忧字了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