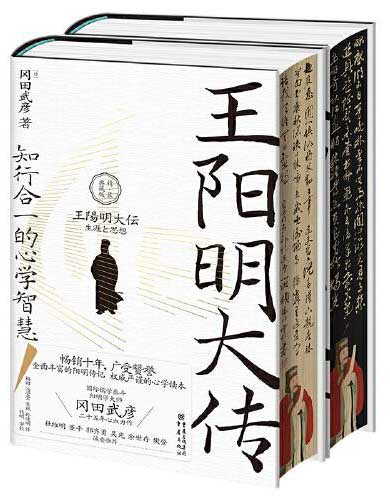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一个人·谁也不是·十万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反思自我的巅峰之作)
》
售價:NT$
250.0

《
重写晚明史(全5册 精装)
》
售價:NT$
3560.0

《
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
》
售價:NT$
602.0

《
强者破局:资治通鉴成事之道
》
售價:NT$
367.0

《
鸣沙丛书·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
售價:NT$
551.0

《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兼论宗教哲学(英国观念论名著译丛)
》
售價:NT$
275.0

《
突破不可能:用特工思维提升领导力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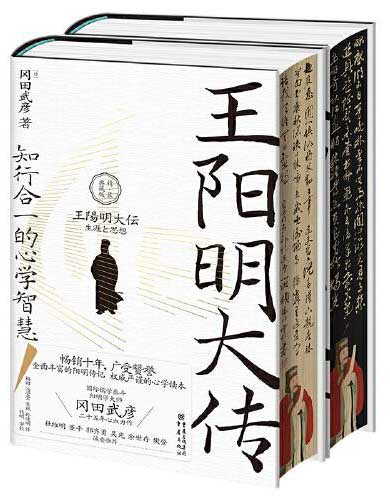
《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1010.0
|
| 編輯推薦: |
◎ 电影《天之坑》的原创作品
电影《天之坑》通过平凡人等在现实生活里的“神秘”交际,反映广大人民在脱贫攻坚中思想、道德、理想的变化和升华,凸现个体生命对现实生活的“发现”“热爱”和“回归”,表达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 小说好看,具有较强的戏剧冲突效果
写诗起家的尹马用诗歌的节奏成就小说叙事的律动、隐忍和通透,让作品具有阅读上的“感官性”。
作为钟情于讲故事的“段子手”,尹马一直注重构筑小说情节的视角现场感,其作品具有较强的戏剧冲突效果。
尹马的小说创作是让乡下还原为乡下、让生活承认生活、让计谋回避计谋的创作,集子中的7个中篇和2个短篇,都具有“故乡流传化”“故事喜剧化”“诗歌陌生化”的特点,具有感叹式的声响和启幕式的色彩,往往会使人在阅读中找到一种“眼前的下落”。
◎ 作者是个很会讲故事的诗人
作者在故事里说:我的人生全是大坑。故事里,他说,天坑是女娲炼石补天时在地上采石采出来的一个大坑。小说写的是爱情,是生死,是一个活跃着生命体征的荒僻之地,是你短暂的一生中必须去一趟的地方,它会告诉你,人世间,你得这样活着。
讲故事需要策略。有时候,故事完了,你还没走——那就
|
| 內容簡介: |
《天坑》是70后代表作家尹马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尹马近年来创作的7个中篇小说和2个短篇小说。
集子中,中篇小说《天坑》以一个被庸常生活束缚的工薪阶层去“世外”的荒诞奇遇为线索,将“无法过滤的爱情与生死”切入普通人物的命运,在不断反转的剧情中呈现平民道德的“因果”关系,该文被改编拍摄为电影《天之坑》于2022年“5.1”黄金档在全国院线上映.
中篇小说《到双马杆去》《四人制》《什么也没有》《明天见》《谈笑无期》《天籁》和短篇小说《燕子》《想飞的人》同样锁定“工薪人物”, 以“乡下”“县城”“工厂”为依托,借力一群人的处世“真相”呈现事实图景,是典型的“轻现实主义”力作。
|
| 關於作者: |
尹马
云南昭通镇雄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散文选刊》《大家》等杂志。
出版诗集《数羊》《我的女娲》,长篇小说《回乡时代》,中篇小说集《蓝波旺》《天坑》,散文集《在镇雄》。
曾获云南文学奖、滇池文学奖、诗刊征文奖等奖项。
|
| 目錄:
|
中篇小说:
到双马杆去
什么也没有
谈笑无期
四人制
天坑
明天见
天籁
短篇小说:
燕子
想飞的人
|
| 內容試閱:
|
到双马杆去
1
“以前羊多的时候,我想为每一只羊都起一个名字。每天想啊,想得头皮都抠破了,最后硬是一个字也没想出来。”那个坐在火堆旁边抽烟的男人,四十来岁。他说,“到后来,我只有一只羊,可我却想出了很多名字。”
这是在后河,黄连原始森林的宿营地。后半夜,他把唯一的一只羊杀了,吊在一棵香樟树上。他披一件开叉的蓝色旧西装,坐在火堆旁抽烟。他用一根木棍在火堆里搅动,说火不够旺,烧不开水,做那么多人的饭菜,是很费力的。
我在狭小的睡袋里躺了大半夜,几乎没有合过眼。尽管走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身心疲惫,但还是睡不着。地面太潮,睡袋又太小,身旁是一个胖子,只装了半截身子进去,但他躺下不到三分钟,就打起了呼噜。
后河宿营地的营房,两层,建于三十年前,是一座两层的水泥砖房。一个没有扶手的直直的楼梯,把两层楼房连在一起,像一根大头针穿过一片腐烂的落叶。二楼有两间房,楼梯左边的那一间住着四个女人,右边一间,是五个男子。房屋中间的隔墙没砌到顶,上面有一条巨大的缝隙,彼此能听到指甲在肉皮上挠痒的声音。
胖子的鼾声,先是在男人中招来一阵恶毒的咒骂,接着又引起隔壁女人“嗤嗤嗤”不停的笑声。那天晚上,我甚至在百无聊赖中计算一个人生命的长度,我想,以七十岁作为平均数的话,如果你的身边是一个打呼噜的胖子,你就可以活到一百四十岁。当然,一个把呼噜打得有声有色的人,他即便碌碌无为,也能让你记住他轰隆隆的一生。胖子的呼噜层次清晰,每一个步骤都那么铿锵,过门、间奏和高潮错落有致,节奏明显。在我还在抱怨睡袋太小翻不了身的时候,胖子先是“嘘”的一声,随即喉头里发出沉闷的咆哮。在胖子开始用四二拍的节奏打呼噜的时候,另一个睡袋里的人抛出谐谑的语言, “哇,这是鬼子进村的节奏嘛!”说话的人叫马航,人们都称他为“小蚂蝗”。小蚂蝗刚说完,隔壁女人就“嗤嗤嗤”地笑。胖子的鼾声愈发响亮,节拍从四二拍转为四四拍,又上升到重金属摇滚,原本松动的窗玻璃在木格子里发出“咣当咣当”的叫喊。躺在我左边的乡村诗人兀地从睡袋里弹起,月光下,他满目的狰狞瞬间化为惊慌失措,顿了几秒钟,他问,“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每哼一句,门外的山蛙都会叫一声。”几个男人都说:我们早就发现了。
有人下楼撒尿,一会儿又回来。他说:“那个护林员,把他的那只羊宰了。”
胖子的呼噜一阵紧似一阵,呈排山倒海之势。我自知入梦无望,干脆逃离睡袋,也下楼撒尿。在白天栓羊的那棵野桃树下,磨蹭了半天,勉强表示了一个意思。经过院坝时,护林员正把烫了皮的羊往树上吊,旁边的火堆里发出干柴噼里啪啦燃烧的声响。
我向他递了一支烟,他接过了,拿到眼前瞅了半天,说:“老板,这烟很贵吧!”
“不贵。”我说。
“你们抽一包烟,够我们买一袋肥料了。”他从火堆里抽出一朵火苗,点燃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一大块烟圈从嘴里钻出来。他说,“这烟真好。”说完话,居然还有烟圈从鼻孔里往外冒。他又狠狠地抽了一口,把烟拿到鼻子底下,仔细地看,说,“这烟真稀奇!”
“你为什么不睡觉?”他问我。
“睡不着。”我说。
“这荒郊野外,第一次来,睡不着也是正常的。”他吐了一个烟圈,说,“我以前刚进来的时候,也整晚整晚的睡不着,有一段时间,我头发都掉光了。”
“你后来想了什么办法,才让自己睡着的?”我问他。
“我数羊。”他说。
“你有很多羊吗?”
“之前有,不过后来没了。”声音里透露着一丝伤感。
“以前没进山的时候,我有很多羊,我每天都要把它们撵到黄连森林边上的黑熊坡上去放,那时候,我想为它们起一个名字。”他说。
“它们后来怎么没了?”我问他。
“卖了,给我母亲治病。那几年,我母亲天天吐血,瘦得皮包骨头。”
我不好再接续问下去,只好又递给他一支烟。
“老板,这么好的烟,你自己留着抽吧,别让我糟蹋完了。”他很羞涩地接过烟。“对了,老板,你喝不喝酒,我有酒。”他说。
“能喝一点。”我说。
他站起身,进了一楼左边那间用胶纸糊了窗子的房间。一会儿,他左手拎了一个胶桶,右手拿着两个碗出来。他递给我一个碗,倒了小半碗酒,说,“下半夜天凉,不想睡觉的话,喝点酒抵挡一下。”
我问他,“数羊真的能睡着吗?”
他笑了笑,说,“如果有羊,数一数,心头高兴,自然就睡着了。”他端了酒,对我说,“吃一大口!”
吞下一口酒,浓烈的液体瞬间浸透全身,我差点打了一个喷嚏。
“以前我数羊,是这样数的。”他右手指着火堆,“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三十七只,三十八只……”他吞了一口酒,喉头里发出“咕咚”的声音。“我说过,那时候,我有很多只羊。”他仿佛沉浸在他所描绘的富足之中,脸上堆满笑容。
“后来,我只剩一只羊了,一只小羊羔,难产留下的,我不忍心卖它,就把它带进山来了。”他又吞了一口酒。
“只有一只羊的时候,你得这样数。”他换了一只手,指着火堆,开始数羊:“一只,一只,一只,一只……”他说,“后来,我就睡着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