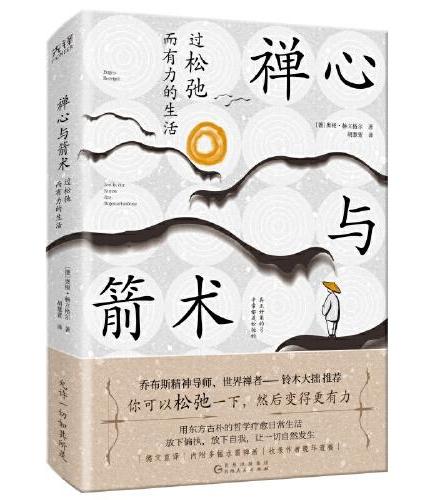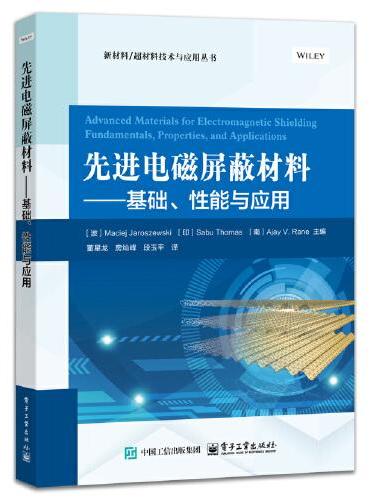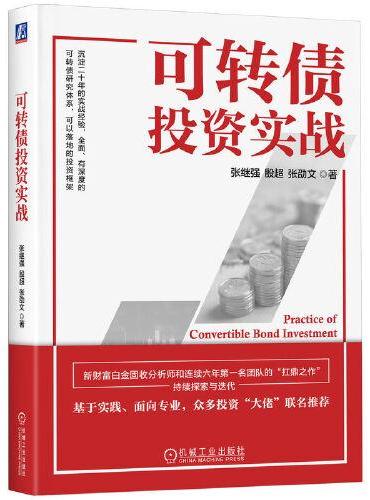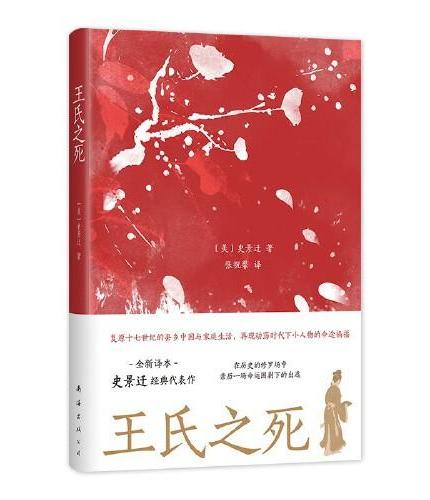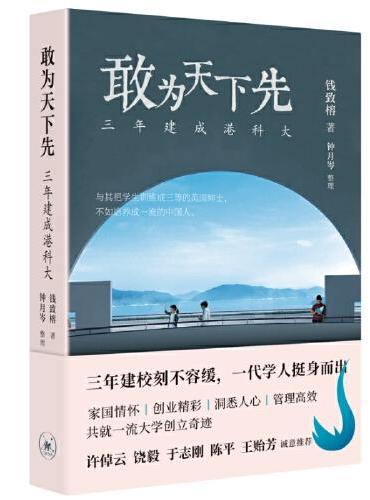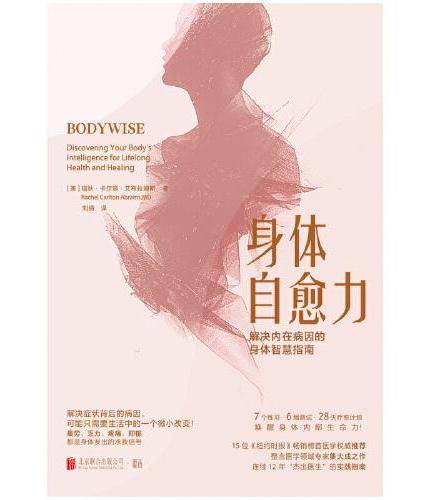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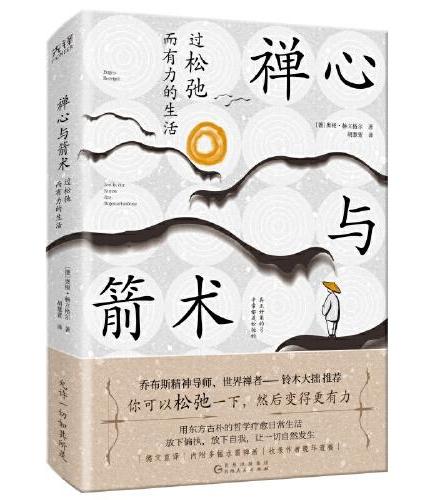
《
禅心与箭术:过松弛而有力的生活(乔布斯精神导师、世界禅者——铃木大拙荐)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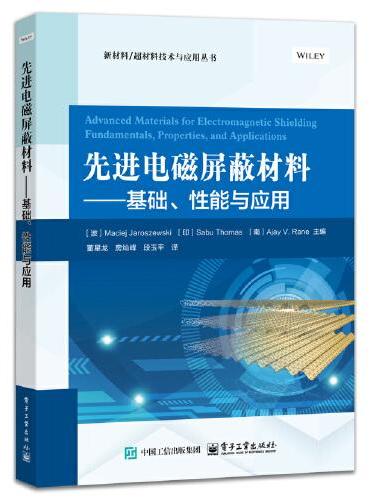
《
先进电磁屏蔽材料——基础、性能与应用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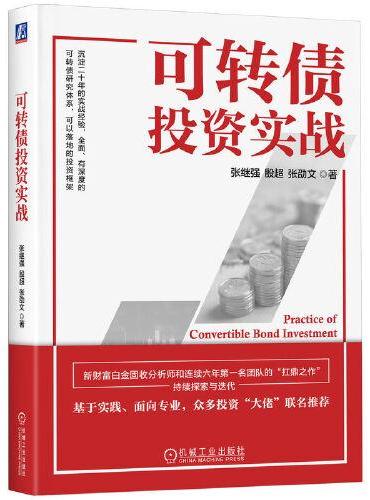
《
可转债投资实战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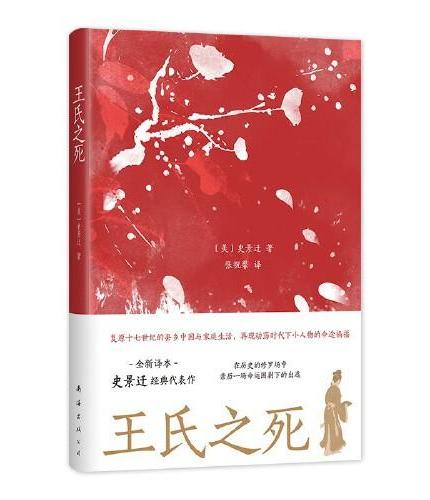
《
王氏之死(新版,史景迁成名作)
》
售價:NT$
2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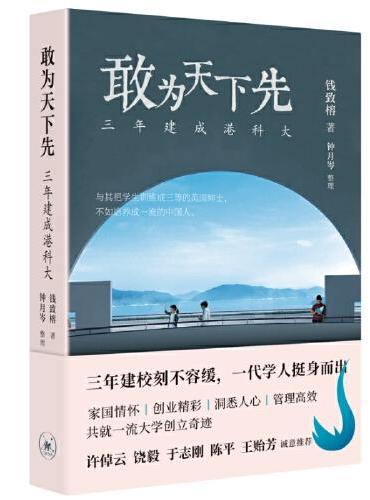
《
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
》
售價:NT$
352.0

《
直观的经营:哲学视野下的动态管理
》
售價:NT$
407.0

《
长高食谱 让孩子长高个的饮食方案 0-15周岁儿童调理脾胃食谱书籍宝宝辅食书 让孩子爱吃饭 6-9-12岁儿童营养健康食谱书大全 助力孩子身体棒胃口好长得高
》
售價:NT$
2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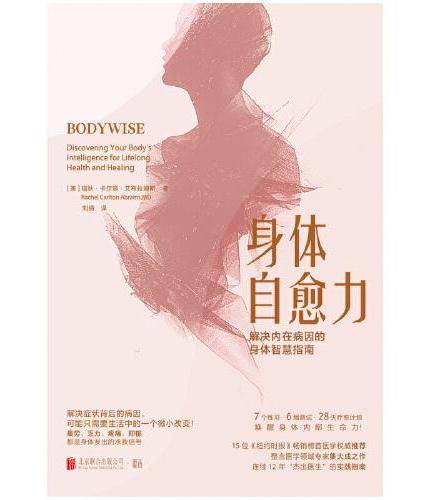
《
身体自愈力:解决内在病因的身体智慧指南
》
售價:NT$
449.0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主体部分收入了对北京大学十位哲学家的评述,他们均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后汇聚于北大哲学系的哲学大师。以年龄为序,分别是熊十力 (1885~1968)、梁漱溟(1893~1987)、汤用彤(1893~1964)、金岳霖(1895~1984)、冯友兰(1895~1990)、宗白华(1897~1986)、贺 麟(1902~1992)、张岱年(1909~2004)、任继愈(1916~2009)、张世英(1921~2020)。此外,还收入了对汪子嵩先生的访谈录《中西哲学交会的历史反思》。十位大师中有几位是作者当年北大求学时期的老师,作者在书中,忆述了当年与这些老师接触的情景,阐述这些老师的学术生涯与人生际遇。其中既有理性的分析与评论,也有感情的追忆与思念。崇敬之心,怀念之意,感恩之情,溢于笔端。书中所阐述的这些老师年龄不同,专业各异,但是他们在学术上共同的特点与优点是:融会古今、贯通中西。他们的学术生涯与学术成就,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过程的若干足迹,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中西哲学会通与融合的产物,是中国现代哲学对西方哲学的积极回应。本书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发展史,了解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提供了某些思考的视角,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
| 關於作者: |
|
林可济,男,汉族,1933年12月生,福建省福州市人。1950年4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其间,曾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身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4~1958年就读并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长期在高等学校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1987年起为福建师范大学哲学教授。校外曾担任的学术职务主要有: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福建省科协委员、福建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国立华侨大学兼职教授等。作者著述颇丰,主要学术著作有:《科技与文明》(1988)《信息社会理论辨析》(1992)《中西哲学源流》(1995)《〈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2013)《爱智篇——哲学学习探索40年》(1999)《张世英哲学思想研究》(2008)《“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中西哲学比较的重要视角》(2010)《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2012)《哲学:智慧与境界》(2013)《皓首沉思录——林可济哲学论文自选集(2003--2014)》(2013)《中西哲学散论》(2018)等。
|
| 目錄:
|
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北京大学历史上的若干重要史实(1898—1954)
蔡元培:北大人永远怀念与敬仰的校长
——为纪念蔡先生逝世80周年而作
略论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马寅初:学生心目中坚持真理的好校长
坚守独立思考的学术争鸣之道
——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回顾与反思
北京大学哲学系求学漫记
——1954—1958年的远事与近思
十位哲学名师的人生经历与学术生涯
独辟蹊径平章华梵融会佛儒兼采中西
——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思想的再认识
梁漱溟和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著作
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为往圣继绝学
——汤用彤的中国佛教史和魏晋玄学研究
西方逻辑分析方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完美结合
——金岳霖哲学著述与学术人生
世纪哲人冯友兰的学术贡献与人生际遇
漫步在美学和艺术的林间花径
——宗白华的《流云》《美学散步》《艺境》及其他
贺麟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与翻译的坎坷历程
融合古今学贯中西
——张岱年的学术著述与坎坷人生
任继愈《老子》研究中的方法论探索
张世英:百岁著名哲学家的睿智人生
——受教60余年的追思
毕业后与母校的交往
毕业后60多年所发生的与母校有关的若干人与事
2018年回到母校参加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
百年系庆,重听老师教诲
——读《守望智慧的记忆》
中西哲学交流会通的历史反思
——汪子嵩先生访谈漫记
跋:大师远行,其道不孤
附录:阐述十位哲学名家哲学思想相关的学术论著要目
|
| 內容試閱:
|
北京大学哲学系求学漫记
——1954—1958年的远事与近思
引言
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曾经做着毕业后考大学的打算,但在1950年4月参军之后,已经把读大学的想法抛在一边了。没有料到我在东北军区工作期间,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政务院(后来改称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动员地方和部队的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的青年报考大学。这就让我重新点燃了读大学的希望。但是,由于时间匆促,又缺乏思想准备,应该报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却十分茫然。
北京大学是国内最享有盛名的高等学校之一,如果从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她已有120多年的历史了。我是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了为期四年的求学生涯。那时是四年制,1955年起,改为五年制,所以,我那一届是北大四年制最后一届的毕业生。1958年我毕业离校,供职于东南一隅的福建师范学院(1976年后改名为福建师范大学),转眼之间已半个多世纪了。
在这60多年的岁月中,作为校友,我当然仍然关心着母校。她的每一个成就,都让我们高兴;同样,她的任何一点被人诟病的事情,也会让我们不爽。
我写这篇文字,以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记述了1954—1958年这一段我在北京大学,主要是哲学系所走过的道路。这一段路,应该说是很不平坦的,有起有伏,相当坎坷。有些事件与人物,也许是终生难忘的。由于许多人都能理解的原因,我是没有写日记的习惯的。这样,书中所说,容或有不够准确之处,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是在今天来追述昨天,免不了会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昨天的事物,也忍不住对已经成为历史的事件与人物,发些感慨,略作评论。因此,文章中既有“远事”,又有“近思”,既不是单纯的历史记载,也不是无事实的凭空议论。当然,这些感慨与议论,带有个人的印记与色调,不可能尽人皆同,但也不至于完全没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处。
即使也是北大的校友,如果就读的时间不同,对北大的感受与认知也会各有所异。因为北大随着时代的步伐,也在不断地变化与发展。我常常做这样的设想:如果时光倒流,我又变成一名北大的学生,再回到今天的北大去读书。肯定的,我对今天的北大,一定会有些不习惯、不理解,甚至有不以为然的地方。那么,当今的读者,即使也是北大的校友,由于他(她)们的经历与我们当年的经历不同,对我书中所见、所思之事件与人物,产生出惊愕,乃至于不理解,视之为天方夜谭,不也是非常自然的吗?
半个世纪以前,我有机会在北大读了四年书,这是我的幸运。我当时不是个好学生,后来也不是一个可以让母校引以为荣、惦记着的校友。学生也好,校友也罢,我都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良知来读书、来做事。古人云:不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反躬自省,庶几近之。
由于本文带有回忆录的某些特点,所以行文不求全面,不求系统。事实上不必全面、系统,以个人的阅历,也不可能做到全面、系统。特别是当时所参加的一些全体学生都必需的政治运动,限于篇幅,不作记述。总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兴之所至,笔当随之。
为什么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在中学时代虽然对文科和理科都有兴趣,但参军四年多,学业都荒疏了,报考什么专业,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时,部队宣传部门的一位老同志建议我报考哲学系,因为按照当时的权威说法,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而又偏重于文科的一个专业。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哲学这个名词,还谈不上对它有什么认识。
经过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当时全国高等学校中的所有哲学系,都合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1956年以后,又有几所综合大学恢复了哲学系)。因此,要报考哲学系,北京大学是唯一的选择。以我当时的实力,加上准备不足,要让北大录取,实在信心不足。好在高中时我的学习基础还比较扎实,虽然中断学业四年,想不到经过两个月左右的突击补习,居然以第一志愿,于1954年夏天,被北大哲学系录取。从此,我开始了四年终生难忘的大学学习生涯。
1954年8月的某一天,我告别了部队的领导和战友,登上了从沈阳去北京的火车。
在火车上想起了四年多的军旅生活,历历在目。既有对往昔岁月的怀念,也有对未来大学学习的憧憬,千头万绪不禁涌上心头。幸好后来在车厢里,遇到了几位像我一样考上大学也要去学校报到的部队战友。虽然并不认识,但聊着聊着就如同老朋友了。其中有两位是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的,他(她)们对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很是羡慕。但是,对于什么是哲学,和我一样,也是一头雾水。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入学后曾经想从哲学系转系到中文系,为了这件事,还专门找过当时任教务长的周培源先生。周先生是享誉世界的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学家,年轻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还在爱因斯坦领导下从事广义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他认真听了我的口头申请后,调阅了有关我的高考资料,耐心地说,我的要求虽不无道理,但中文系学生多,哲学系学生少,能够不转系尽量不转系。让我回去再考虑。后来我也就作罢,不再要求了。
四年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北京大学是我国一所享誉中外的著名高等学府。北大哲学系,始建于1912年,到了1914年正式招生,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最早成立的哲学系。历史上,著名学者蔡元培、马叙伦、章士钊、胡适、熊十力、梁漱溟、张申府等先后在这里执教。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曾在此开设过哲学课程,最早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在这里,我们不但能听到全国第一流学者的讲课和各种学术报告,而且还经常见到一些著名的领导人。他们或者来校参观,或者来做报告。我们听过陈毅、乔冠华、李富春、廖鲁言等领导人做的报告。
因为我是提前来校的,这就有了在开学前饱览校园的充足时间。早就有人说,“诗的北大,散文清华”。北大校园之美,果然名不虚传。
从北大西校门踏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对引人注目的华表。它与那些黄绿琉璃瓦的飞檐宫殿式建筑格局相谐趣,构成了校园古色古香的整体风格。
北大校园,名为燕园,原为燕京大学的校园。而燕园是司徒雷登当校长后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于1921年重新兴建,于1926年基本建成的。那一对华表原先是在圆明园,是当年修建燕园时移来的。那是真迹,绝非赝品。
北大校园,有人给予了“一塌糊涂”之戏称。“一塌”指的是水塔,“糊”指的是未名湖,“涂”是图书馆。这里说的图书馆,实际是指图书馆总馆的那座大楼。它位于办公楼的附近,很有欧洲建筑的风格。馆内一层是个大阅览厅,咖啡色的阅览桌上配有绿色的罩台灯。暗暗的大厅,桌上却有着明亮的灯光,别有一番韵味。校内的水塔具有实用的功能,但它的外形却是一座十三层的中国式宝塔,颇具特色。湖是未名湖,因久不得其名,索性就以“未名”而名之。早晨的阳光透过位于东侧的水塔,照射到湖面上,水塔在水中的影子还是晃动的。夕阳西下,阳光从办公楼方向透过那些小山上松树、杉树的缝隙,照在湖面上。北大校园,面积宽广,布局精致,散落着御花园式的山水,宫殿式的建筑,可谓美不胜收。
北京大学学生会下属有好几个自己组织的社团,课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诗歌、舞蹈、音乐欣赏、摄影、绘画、书法、演戏……应有尽有。我当时曾经先后参加过舞蹈、摄影、音乐欣赏等项活动。最后一项是不定期的,同学们看到海报后,踊跃走向指定教室,陶醉于各个名曲的优美旋律之中,使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升华。现代学子最欣赏的多为古典音乐,偌大的教室鸦雀无声,这与当今流行歌星的通俗唱法的音乐会所呈现的疯狂、喧嚷场面,形成巨大的反差。
当时,我们除了要上一些属于公共必修的课程(政治理论、俄语、体育等)以外,属于哲学类的基础课和专业课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形式逻辑、数理逻辑、伦理学、美学等。大学四年除了上课、考试之外,老师希望我们写些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文章。这既能对所学课程加深理解,也可以增强思维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四年学习期间,我所写的文章,除了发表于当时的《中国青年报》外,学术性稍强的几篇,也发表于当时《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和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到了高年级,系里要求我们加修一些选修课。选修课的选择,大体上根据每个同学所确定的专门化的方向。哲学专业所属的专门化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逻辑学、自然辩证法等。我选择的是“自然辩证法专门化”。
我们班的同学并不多,入学时有40多名,由于各种原因,毕业时还不足40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像我一样,是工作了几年之后又考进来读书的,叫做调干生。经过一段工作后,大家深知掌握知识的重要性,都十分珍惜这种读书的机会,学习都非常用功。
在北大四年,作为学生,我们还常常有机会参与一些外事方面的活动。当然,是以听众或观众的身份出现的。
记得在一年级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华访问。我们学生参加了在飞机场迎接的群众方阵,周恩来总理陪着他绕场走了一圈。我们不仅看到了尼赫鲁,而且是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周总理。大家非常高兴,返校后还一直谈论不休。
1956年10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问我国。有一天,他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来到清华大学的大操场,为清华、北大两校的学生做演讲。我们北大哲学系、中文系的学生也列队前往。那天,他身着民族服装,头戴黑帽,手中拿着一根闪闪发光的手杖。他的演讲声音洪亮,极富感情色彩与煽动性。年轻学子即使不经过翻译,都能从其声调、表情而受到强烈感染。同年11月,周恩来总理陪同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和夫人到北大参观,并在办公楼顶层的小礼堂向1000多名北大哲学系和中国佛学院师生以及佛学界人士,做关于佛学的讲演。
1957年5月5日,正在中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邓小平的陪同下,来北大参观。我们学生在西校门的入口处列队欢迎。以上几次活动,让参加的学生开阔了眼界,见到了这几个国家的政要,也有机会在近距离看到了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机会并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科学进军”影响下,
当时北大的学术自由气氛
在1954—1958年这段时间里,我感到在政治上、思想上最为宽松的是1956年。正是在这一年,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也正是在这一年,党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努力学习,向科学进军。
党的伟大号召让广大知识分子感到莫大的鼓舞和振奋,当时,国务院组织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国家十二年(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该规划包括数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后者之中,包括有自然辩证法这个领域,它是哲学这个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规划草案拟定了9类研究题目,50多位专家分别写了“说明书”,阐明该课题的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这个大背景对我在高年级时,在几个专门化之中,选择“自然辩证法专门化”作为我攻读的主要方向,有着直接的影响。
当时,北大曾请来著名科学家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到校,对学生进行科学演讲。演讲在大饭厅举行,现场坐满了听众。那时的大饭厅,名副其实的大,能够摆得下好几百张桌子。它的功能不仅供学生进膳之用,还是北大的政治中心、文化活动的中心。把饭桌拉到旁边,中间就是一片宽敞无比的开阔地,同学们自带凳子来,顷刻之间就变成了可供数千、近万人开会、听报告、看电影的大礼堂。在节假日,它也是举办舞会的大舞场。跳累了就坐到旁边自带的凳子上边休息,边欣赏其他同学欢快的舞姿。前些年,为了迎接百年华诞,北大在原址上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大会堂,还起了一个华丽的名字。但在老校友之间,仍然把它叫做大饭厅,它比任何其他称呼都温馨。
当时北大哲学系也是一派学术自由的气象。系主任郑昕教授在《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8日)上发表了题为《开放唯心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就非常另类,让人惊异。因为那时的唯心主义,已是过街老鼠,为何还敢“开放”?该文指出:“在人民内部开放唯心主义是解决我们思想中长期存在的学术与政治矛盾的钥匙……而正确地估价唯心主义,是对唯心主义展开斗争和最终战胜唯心主义的前提。”张岱年教授也认为:“既然唯心主义存在,与其让它以伪装的、隐蔽的形式存在,何如使其公开化,给它以宣传的自由呢?唯心主义公开化就更便利于哲学思想斗争的开展。”(张岱年:《如何对待唯心主义》,《人民日报》1957年1月13日)在这个时候,哲学系相继推出郑昕的康德哲学、贺麟的黑格尔哲学、洪谦的维也纳学派哲学和熊伟的存在主义哲学等西方唯心主义哲学课程,受到学生的欢迎。
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无论你在高年级时选择什么专门化,在低年级时都要上自然科学基础这门必修课。到我们那一届,又增设自然和自然发展史一课。它的内容除绪论外,还包括物理世界、生物世界和人三个部分。于光远同志亲自讲绪论,理科的几位著名专家,如周培源、王竹溪、黄昆、徐光宪、沈同等老师分段讲授后面三部分。这也是全系同学都要学习的必修课。作为自然辩证法专门化的学生,只学这些当然远远不够,系里安排我们到理科相关的系里,选修一些自然科学的课程。我是到数学系和物理系选修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学这两门基础课。因为是跟着数学系或物理系相关的学生班级一起上课,任课的老师对我们哲学系学生的要求,和对所在系学生的要求是一样的,既要听理论课,还要上习题课和实验课。这对于哲学系的学生来说,当然是很吃力的,但却受到了关于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严格训练,养成了按科学规范办事的习惯。课后,复习教材、做作业的任务很重,每天的自修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有时候吃晚饭走进饭厅,抓几个馒头,买一份菜,掉头就走,为的是能到图书馆或其他阅览室里占有一个自修的座位。这简直就是一场紧张的战斗啊!
毕业分配回福建,从教60年
1958年夏天,我们54级学生经过四年的学习,面临着毕业分配。那一年全国各省都在“大跃进”,都需要毕业生,所以,我们全班30多位同学要被分配到10多个省份去。哲学系党总支号召大家要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具体地说,就是要支持边疆,到新疆(3人)、云南(3人)、贵州(3人)去。我们班级并没有从这三个省份来的,原籍在这三个省份以外的同学想去就要自愿报名。一下子就有10多位同学报名了。我也在其中,第一志愿新疆,第二志愿云南,第三志愿贵州。但是,这三个省只要9个人就够了,而福建省有一个名额,福建籍的学生又刚好只有我。领导上动员我回原籍工作。当时我还不大乐意,认为我当年(1950年)是出来参军,是参加革命工作的。好男儿志在四方,干吗要回家?巧就巧在1958年发生了“金门炮战”的军事事件。总支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任宁芬同志对我说,炮声就是命令,你是转业军人,你不去,谁去?在这个前提下,我别无选择地分配回福建,到当时的福建师范学院人事处报到。从那时起,一直坚守在哲学教学与研究的岗位上,长达60年!这是后话。
人到老年就会喜欢怀旧,回忆往昔岁月中曾经出现的人与事。在我,也不例外。我出生于1933年,到今年(2021年)已经步入了第88个年头。中国的汉字很奇妙,人们通常把88岁称为米寿,以笔画造型论之也。又把108岁称为茶寿,也是从笔画而言。有好事者又把米寿视为形而下,茶寿视为形而上,所以,米寿者应向茶寿迈进,遂有“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之说。
古人有云: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的人,寿命长了,进入耄耋之年者,比比皆是,并不稀罕。近些年来,北大哲学系的学者曾撰文说,该系教师,80岁者众多,90岁以上者也不少,去年9月逝世的张世英先生已是百岁寿星了,所以,可以把北大哲学系称为长寿系。说者、听者都开怀一笑。我今年虽已88岁,但与高寿的老师相比较,实不足道。
在过去的88年中,如果把童年、少年抛开不算,从教的时间也有60余年。2018年的教师节,我所在的单位曾因我从教60年,而有庆贺之活动。但我自身而言,这60年的从教经历,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遑论庆贺了。倒是在担任高校教师之前的青年时代,有两件深深留在记忆中的经历。一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一为求学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近年来,总是想把后一件事比较详细地记载下来,但因惰性而久拖至今,未能实现。现在,总算完成了,了却宿愿,心里轻松了不少。
北大的四年学习生涯,最令人遗憾的是,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占用了好些本可以进行学习的时间。而那些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学有专长的老师,很多人为政治运动所累,没有更多的时间也不大方便对学生进行学术上的指导。
北大的四年学习生涯,使我终生难忘。这并不是因为我在那里学到了多少知识,而在于北京大学那个特有的氛围,给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于学术品格、治学作风方面所受到的熏陶;在于学术视野的开拓和人的全面素质的培育。那都是书本以外的东西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