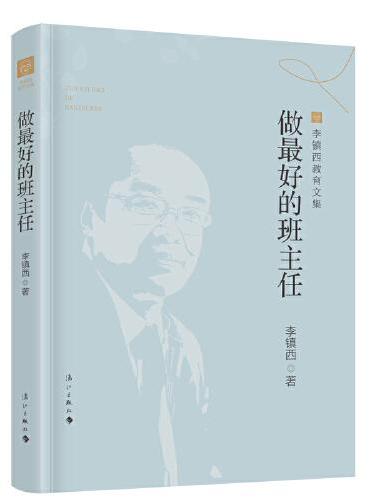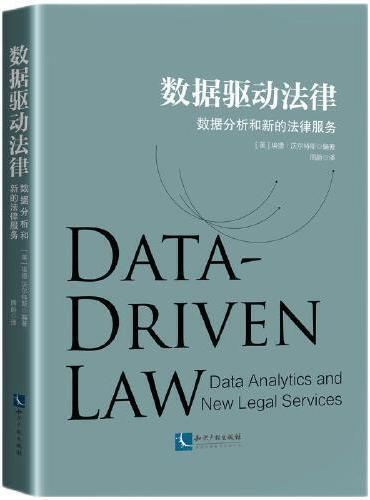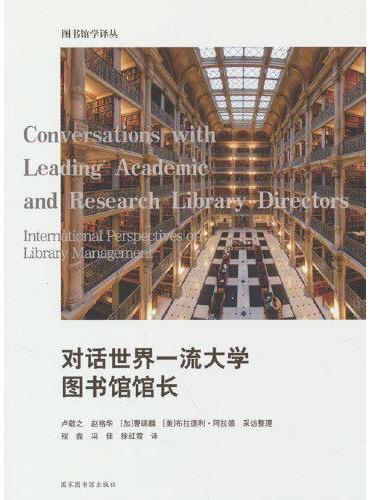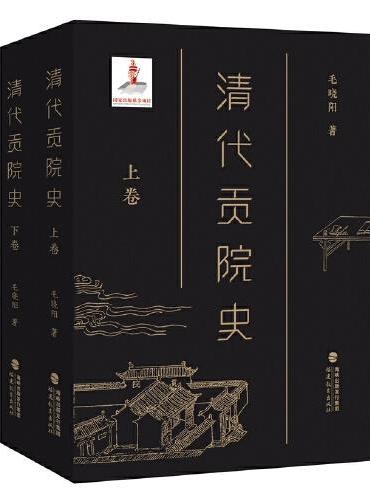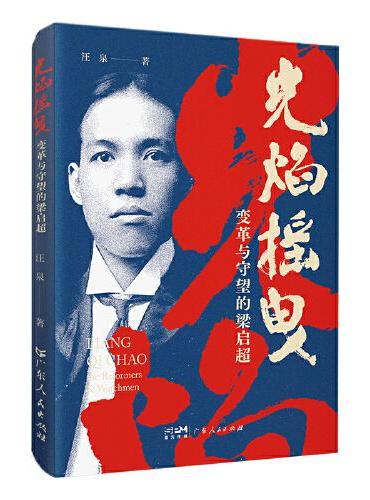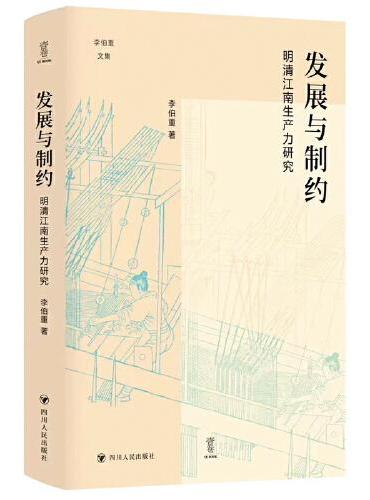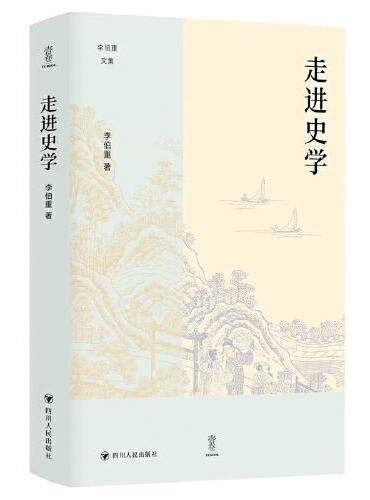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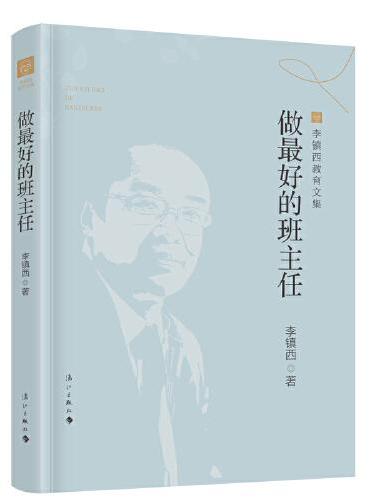
《
做最好的班主任(李镇西教育文集版)
》
售價:NT$
2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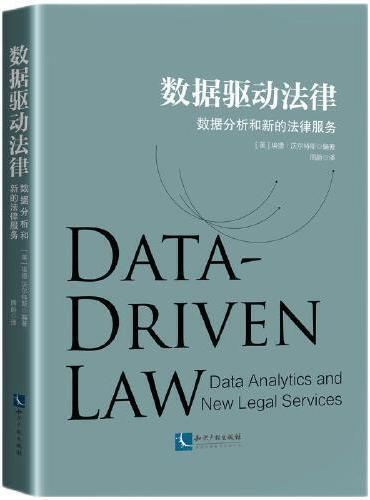
《
数据驱动法律
》
售價:NT$
3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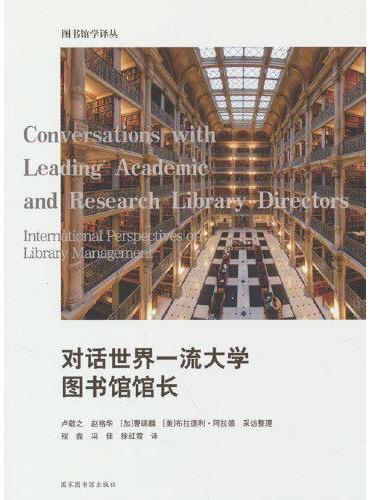
《
对话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馆长
》
售價:NT$
995.0

《
揭秘立体翻翻书--我们的国宝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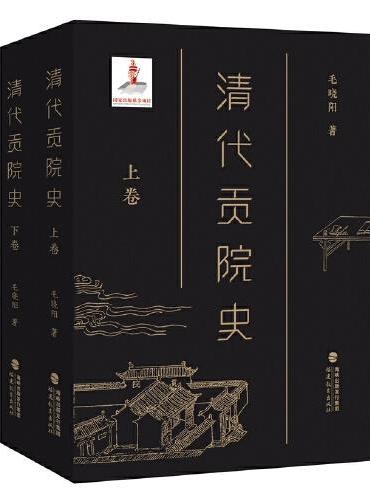
《
清代贡院史
》
售價:NT$
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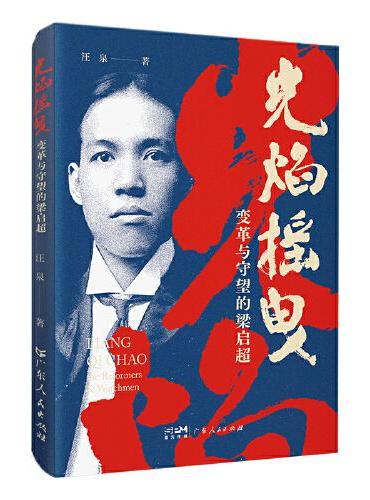
《
光焰摇曳——变革与守望的梁启超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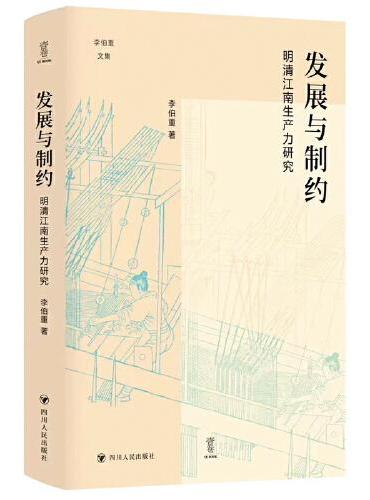
《
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壹卷李伯重文集:江南水乡,经济兴衰,一本书带你穿越历史的迷雾)
》
售價:NT$
4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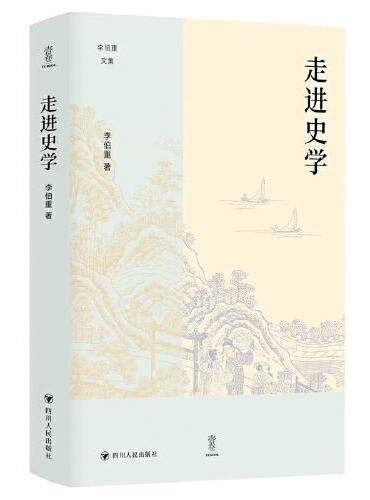
《
走进史学(壹卷李伯重文集:李伯重先生的学术印记与时代见证)
》
售價:NT$
360.0
|
| 內容簡介: |
|
作品收入了七篇散文《沈焕江》《一个温暖的雪夜》《烈火》《生活的波澜》《草原夜话》《张翠霞》《风雨黎明》,生动细致地刻画了沈焕江、林礼克、张志永、田成富、张方、张翠霞、武星文等人物形象,描写了他们在生产生活一线的感人故事。这些作品均写于1958年。“除了最后一篇,是一九五八年冬天,从福建前线回来写的,其它六篇,都是一九五八年春天在黑龙江写的。”作品饱含深情地记录了当时人物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着作家的写作风格。
|
| 關於作者: |
|
刘白羽(1916—2005),北京人。1937年到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曾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及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总政文化部部长,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等。全国第一届政协代表,全国第一、二、三、五、六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七届政协委员,中共八大代表。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风风雨雨太平洋》《第二个太阳》《大海——记朱德同志》《心灵的历程》,散文集《红玛瑙集》《海天集》《秋阳集》《腊叶集》等,短篇小说集《草原上》《兰河上》《五台山下》《太阳》《幸福》《扬着灰尘的道路上》等,报告文学集《刘白羽东北通讯集》《环行东北》《为祖国而战》等,短篇小说《无敌三勇士》《战火纷飞》《政治委员》等,散文《长江三日》《日出》等。电影文学剧本《中国人民的胜利》获1950年斯大林文艺奖一等奖,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
| 目錄:
|
目录
沈焕江/ 001
一个温暖的雪夜/ 011
烈火/ 024
生活的波澜/ 034
草原夜话/ 047
张翠霞/ 065
风雨黎明/ 078
|
| 內容試閱:
|
序
这个小小的集子,如若说有什么值得纪念的,是它收集了我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年代写的七篇速写。除了最后一篇,是一九五八年冬天,从福建前线回来写的,其他六篇,都是一九五八年春天在黑龙江写的。前几年,曾收集在短篇小说集《踏着晨光前进的人们》之中,现在把它们单独出版。
是那年的二月,万里冰封,千里雪飘,我从北京奔向黑龙江。
在我的日记中有二月二十七日一则可查:
“在车厢里,初睡时闷热不堪,黎明时却又冷气袭人。天明一看,窗外茫茫无际的风雪,雪的岗岭上耸立着光秃秃的树丛,冰道上有几匹马热气腾腾地拉着大板车奔跑,若不是火车奔驶呼啸,我该能聆听到那随风雪而旋转的马项铃的叮当声响吧?映入眼帘的这一切都多么亲切呀!原来车已驶至松花江上,前面就是陶赖沼。可是到处是冰是雪,不辨何处为江身,何处为江岸。我记得:那是第三次下江南,大踏步前进之后,忽然来了一个大踏步后撤,我和一位纵队的政治部主任,连宵风雪,马踏坚冰,天明一看,竟不知已经过到江北。现在当我把脸贴在冰冷的窗玻璃上,这一切又都恍然如在目前了。……”
不错,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战争中,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不知从松花江上出入多少次。事隔十年,而今是震撼世界的“大跃进”年代了。透过风声雪影,一九五八年,这一红色世界的黎明,将在人们生活之中,永远留下其无比鲜明的姿态。我常常想:在人类历史巨册中有那么一些珍贵的,如同洪亮钟声一样震响的日子。这六亿人民踏动地球,奔腾前进的大跃进的日子便是其中的一个。革命战争的暴风雪和革命建设的大跃进,当我在我所熟谙的黑龙江土地上行走时,是多么像一支交响诗一样交织到我的心灵中啊!我先到了肇源县,农村中那一股火热的热情冲破冰天雪地,也冲激着我的创作激情。我真无法叙说我的喜悦,如同一颗种子投入土壤之中,我回到了我热爱的人们中间。当年在炮火下抢救伤员的人们,正是今天在原野上创造建设奇迹的人,一股历史的暖流,从他们的身上流注我的心里,种子得到水分与阳光,这几篇速写便开始诞生了。
还在动身之前,由于报纸上发表了一批作家到各个地方去的消息,很快,我就收到了黑龙江一些不相识的朋友的来信。当我从肇源到富拉尔基、齐齐哈尔又回到哈尔滨松花江边的临时寓所时,我忍不住写了一封《复几位朋友的信》,发表在《北方》上面,那里面十分真实地记录了我的心情,现在我把它抄录于下:
“还在北京时,就收到了你们写去的信。现在,我已经到了我所怀念的黑龙江来了。虽然和你们都不曾见过面,但你们那些热情的信,更加吸引我到这亲爱的北方来了。
“不过,你们想得到,对于一个在战争的岁月中曾经与这块土地共过命运的人来说,十年阔别,是有多少话想讲啊!今天,在这里,每走一步路,都使我有着许多新颖的感觉和深沉的思索。人们常说: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当然,谁真有扭转乾坤的本领,让日月来一个倒流?生活可不能像放映机上的胶片,您随时可以重装,重演。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有些历史生活却永远永远地留在心中。不论是工作到深夜或黎明,只要你细细思量一下,战争的风暴就又响了起来,那进军途中的冰雪,那宿营地的温暖,想起来都是何等的亲切。
“十几天前,我在肇源,十分意外地和二十年前相识的一位同志相逢了。当我们一道离开肇源,乘着汽车在公路上奔驰时,无数的回忆,自然地流露出来。在他的谈话中,我记下这样非常感人的一个片断:抗日时期,在敌后战争最残酷的日子,一个往日的同学,当时的战友,在勇敢作战中,给敌人一颗子弹射中头部。他是一个爱写诗的人,当他从昏迷状态中醒转时,他说:‘我只觉得我脑子里血像小溪一样流……’但沉重的伤势终于要夺走他的生命了。最后,他要求:‘你们摘一朵花给我看看。’他沉默地、安静地看了看那朵花。他说:‘你们代替我看看将来的胜利吧!……’
“是的,在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漫长的道路上,革命,斗争,怎么能没有血与泪?我们能是那么健忘的人吗!就在东北,我可以举出一大串我们部队激战过的地方——农安、城子街、其塔木、德惠、四平、塔山、锦州……我还记得哪一个同志,把他的鲜血流在哪一片土地上。但这是不是就使我们的回忆只是一丝淡淡的血痕呢?不,绝对不。我们所以想到这些,是为了使我们知道我们的道路是怎样踏出来的,想到这些,只能更加深对这块土地的爱,想到这些,我们就要坚决地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记忆中的战争时代,是一个英雄的飞跃的大时代,我常常说:那一段生活是我最幸福的一段生活。也许您问:为什么?现在我就讲一点吧。第一次上前线,我就把腰摔坏了,同志们用担架抬着我。那天夜晚,我寄宿在松花江边一个贫苦农民的小草房里。天将明,我睡梦蒙眬之中听到两个人在轻轻地谈话。我睁开眼,灶火洞里的火光照红了两个农民的面孔。我没动弹,他们也以为我还在熟睡。那正是革命处于艰苦的关头,是‘天空似乎还黑暗’的时候。他们抽着烟对着火光说着心里的话,但他们叙说的是对人民军队的热爱,对革命斗争的誓言。赤诚的人民,在最困难时,伸出手支持革命。当时我听着,十分感动。松花江边这一夜,成为我永生永世不能遗忘的一夜。它如同一扇门,打开了我通往人民之路。您想一想,当人民的情感流入你的心灵,它就像血与乳一样哺养了你,你才懂得那是什么样的幸福。我也许是一个幻想家,一个浪漫主义者,但我绝不是仅仅为北方的大风雪和大森林所吸引,而是由于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养育过我,我在这儿曾经默默地留下我的感情与生命的一部分,这些年,这种情感在加深着,而成为真正的怀念。
“战争的风暴早已吹过去了。今天,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大时代,展开在我们面前。从抵达哈尔滨那天算起,到现在还只一个月时间。但我如同早晨起来,推开窗户,面对着春天的原野,一种无比新鲜的感觉回荡在我的心里。这时没有一句最恰当的歌词,也没有一句最适合的诗句,能表达我的心情。语言、文字与人民精力所创造的灿烂生活对比,是如何的逊色啊!当然,这也说明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在这时,我特别喜爱一位朋友从绥化来的一封信上的这段话:‘……春天已经降临到黑龙江省。在松花江畔,在各种树干上远远地都可望见了。虽然树枝上还结着晶莹的树挂,构成一片银装,但这美丽富饶的好地方,很快就会变成一片浩瀚的绿色的海洋。到夏天,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牧放着牛羊群,水草茂盛,鲜花芬芳盛开,像一个美丽的大花园……’我感谢您,不只是因为您在信中提到十年前的那回通信,我特别要感谢的是您对祖国这遥远北方的热爱,是您用这种热爱对我的启发、督促和勉励。
“可是,有多少人对这地方确实还不够了解,他们把‘北大荒’当作一片荒寒之地。从前的‘诗人’‘墨客’对于北地的严寒更不惜借题发挥,夸大其词,比如我手边这本西清的《黑龙江外记》里就说:‘冬日唾抵地辄如凌节节断。’可是,人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怎么还能按照老黄历办事呢?不错,这儿是冷,但冷得那样可爱,它不是那样阴凄凄,寒瑟瑟,它冷得清新,冷得爽朗。事实上,黑龙江是最肥沃也是最美丽的地方。你不能不喜爱那一望无边的黑色土地。这土地上密布着田野和森林,你听那耸天的白杨,发出多么欣快的絮语,人们说:‘杨叶在拍巴掌啊!’至于那嫩弱的小白桦,在太阳光下就像银色蜡烛一样闪闪发亮。这儿的江流如此澄碧。这儿的草原万紫千红。鸟在海蓝的高空中鸣啭,高到你看不见它的影子。成群的狍子在森林密处奔跑。我永远记得大森林里,像撞碎玻璃一样清脆的伐木声,我永远记得那伐木者木棚里的熊熊火光。想想看,这是如何彩色绚烂的生活图画啊!你看这一片洁白的冰雪,你可别给它吓倒,它是不喜欢胆怯的人的,对于胆怯的人,它也许要发怒,但对于真正勇敢的人,它却那样情深意密。要知道,正是暴风雪,把这儿的人锻炼得如此刚强、豪爽,像纯钢一样铮铮地发响。你说这儿冷吗?这儿人的心比火还要炽热,还要明亮。如果有人甘心一生一世做暖室里的花草,那咱们就不必跟他说了,如果他要做一个真正社会主义时代的主人,那他就应该在战胜大自然中经受大自然的陶冶。
“现在,让我跟你们谈谈这短期旅行的印象吧!由于时间关系,我只到肇源、富拉尔基、齐齐哈尔一行。但我觉得一切就像早晨的阳光一样鲜红明亮,在十年间,人们在这儿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几千年,几万年,谁能够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这样能干。十年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我到过富拉尔基,但现在,那荒凉的车站、简陋的小屋、破烂的街道都到哪儿去了?一个在整个地球上都称得起是最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平地升起了。这次到富拉尔基,头一晚,我怎样也睡不着,一直到夜深,还站在窗前瞭望着工厂区的上空。那辉煌的灯火,那闪闪的蓝光,是多么美啊!落过雪的早晨,我访问了齐齐哈尔园艺试验站。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内,诚朴的站长同志说出米丘林的豪迈的语言:‘植物学家不应该等待自然恩赐,而应该向自然索取。’他们打破了日本植物学家渡边认为北纬四二度以北不能结苹果的说法。就是这样不愿墨守成规的人在北纬四七度二〇的齐齐哈尔,移植苹果成功。一九五二年第一次结了三颗金黄色的苹果,但这是寒带地方的星星之火,现在金黄色的苹果已经大量种植,结实累累。让我们再展眼望一望吧!是谁在杳无人迹的草原上燃起一片金色朝霞,是梅里斯区的青年们,他们像鹰一样在这大时代的高空中振翅飞翔,他们亲手垦荒,建立农庄。多么自由的时代,多么壮阔的生活,只有这个时代,才能使每一个有雄心、有志气的青年人的理想变为现实。在那儿,我不但看见当地青年,我还和从广西、湖南、湖北、四川、南京、海南岛来的青年交谈。是什么支使着他们从暖和的南方来到这寒冷的北方?我知道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他们懂得什么生活是真正可爱的生活,他们懂得什么道路是最光荣的道路。这道路从遥远的南方铺到遥远的北方,这道路还要从灿烂的今天铺向更灿烂的未来。
“您看,河一解冻就奔流起来了,话一说开就止不住了。这信写得太长了。这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的上午,我刚刚从旅行中回到哈尔滨。但是马上我还要到小兴安岭林区去。现在我的窗外土地湿润得发黑发亮了,那么松花江开江的日子就要来到了,丁香花开花的季节也就要到来了。我非常愉快,在这样的星期天能在精神上和你们一起度过,不过请你们原谅,我就不再一一给你们写回信了。工作与学习在等待着我们,在这一切都是速度、一切都是飞跃的突飞猛进的大时代里,让我们把所有情感、所有思想都奉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奉献给祖国的土地吧!那么,最后让我总括起来再说一句,你们的信深深地鼓舞了我,我也希望你们把自己的心交给这丰饶的土地,如你们信上所说那样,把祖国的北方变成一个比这更美的花园。”
我舍不得让“大跃进”的每一寸可贵的时间从我身边飞去,写了上面这封信之后,我又上了火车,向更遥远的北方——小兴安岭大森林中去。至今,那森林的芳香还回环于我的记忆之中,这在我四月八日的日记中有着记述:
“清晨,睁眼一看,已过铁骊,车窗外就是一列一列满载原木的火车,再向前进,我们就进入林区了。森林郁郁苍苍,春天已透过冰雪。一些黑色的水泊还镶着一点冰凌的花边。阳光很暖和。一道河流一会儿在铁路这边一会儿在铁路那边,流急之处,白湍飞溅。桃花水的季节来到了,泛滥的河水淹没了道旁的小树林。在还是金黄色的山谷中,白桦树像一条条银晃晃的链条,鲜艳的红柳枝上结着银灰色嫩苞,草地从远处望去有点绿意了,只有那经冬不落的梖椤树的枯叶像火焰一样燃烧,可是愈往北走愈冷,山上的积雪也更多了。九点四十二分,到了南岔。十几年前我来过这里,那时这里是一个荒凉的小站,满地泥泞,由破旧的茅草屋拼凑成一条小街,有几家挑着幌子的饭铺,这是进入小兴安岭的一站。我只记得那时森林那面一片黑雾迷蒙。现在,全变了,一排一排房屋,远远望去像是一片工厂,烟囱上冒出黑色白色的烟团。我和车厢里的同行者谈起来,一个四川人,是一九五二年从军队上转业来的,现在到外面去招考工人,刚刚回来。他告诉我:‘伊春,这森林中的城市,早先就是一片山沟洼塘,脚踩到路上,地面像橡皮样稀软,只有几家住户,过着打皮子、采木耳的生活。就是我们的一个五年计划,把伊春变了样了。那时候,四匹马拉的空车一陷到泥洼里就拉不出来呀!’车窗外,树林愈来愈密,大山上盖着积雪,小河里覆着坚冰,连我这在车厢里的人也觉得冷森森呢!出着太阳,空中却飘下一阵茸茸的雪花……下午到了伊春,我多么渴望立刻看到这个森林中的新城市呀,但是车站上到处矗立着装载木材的列车,拦着我的视线。这时,却有一股木材的芳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肺。到了住处一看,周围大街小巷,山坡平地,到处木材堆积如山。趁着太阳还没落下,我爬上南面山坡,这个热闹而繁忙的城市一下出现在我的眼底,烟雾与霞光交织在一起,展开绚烂而多彩的小兴安岭大森林的序曲。”
我所以描叙当时的情景,是为了提供这样一个背景。在这背景上,人们万马奔腾,勇往前进。不用说,这是朝气蓬勃、明丽动人的时代景象。当我从人们的身上,看到我们革命的宏伟的理想实现时,我心中无限振奋。我们冲破无数封锁,战胜一切困难,牺牲流血,不正是为了劳动人民能按照革命的理想,自由地飞跃前进吗?当我深入到乌马河森林深处,看见拖拉机拽着巨木从山上轰鸣着奔来,我觉得森林中每一株树都在欣然欢笑。……
如若说还有什么值得回忆的,那就是从二月到四月我在哈尔滨寓所中写作的情景了。当时,我是不分日夜,奋笔直书,但这还远不是我所想完成的,我计划写的要比这多。现在让我再记下我写作时的若干零星的情景,来结束对于这个小册子来说似乎太长了的序文吧!
“从窗玻璃上望出去,见空中有极其细小的东西在簌簌动,我当是第一场春雨呢!谁知却是小雪花儿。这北国的春天来得真迟呀!雪下大了,雪很快染白了地面和树枝。”
“写着,写着,我把目光停留在庭院中一株老树上,忽然之间满屋通明,天完全晴了,隔了细纱窗帘望出去,由云层中拥出来的太阳像一团火。我继续写下去。不久,西面剩下一片红霞,不久,天完全漆黑了,只有透过疏林的一点灯光像星一样亮着。”
“松花江开江了。虽然整个江身还盖满白雪,但雪上已出现两道黑色的冰流。仔细看时,从许多冰涧中,已露出快活的春水了。”
“风很大——窗外的树木在摇摆,呼啸,阳光将摇荡的树影落在桌上。”
“江身大半边都是汹涌的流水了,水冲激到未融化的冰块上汩汩作响,原来江上的雪白颜色已不见,就是尚没融化干净的冰也已变成黑色,江的上空飞翔着一群活泼可爱的野鸭。”
“中午,过呼兰,见松花江完全解冻了,偶然,在波浪中还漂荡着一点冰凌。落雨,春雨的雨珠细蒙蒙地布满火车窗上,而风又将机车上的浓烟拂下地面,常常遮着我伸向窗外的视线,我静静地坐着,我在构思,我多想立即动手写作呀!”
“今天黄昏,在工作一天之后,我久久站在江边上。江上的风景如此迷人:西面有一抹红霞,而南边整个宽阔的江面上凝聚着漆黑的雨云,江天一色,显得那样雄伟。我前面江上有一只木船,扬着红白两色三角帆,在平滑的江面上垂下倒影,清晰得像画的一样,江对岸丛林中开始闪出钻石般一点灯光。江流,春天的江流,你是流在‘大跃进’的春天的江流啊!”
1964年3月10日,北京
沈焕江
北风呼啸了一夜,天蒙蒙亮的时候,乡人民委员会办公室里来了一批客人。
我在办公室里间屋过的夜,刚从热炕上爬起。乡党委书记老高就哐啷一声拉开屋门,笑呵呵地告诉我:
“老刘啊!黎明社的支部书记来了。”
我一愣。他见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就连忙解释说:“你忘了,就是昨晚上我跟你谈的沈焕江那个社的,……”
他一提沈焕江,我可就想起来了。昨天夜里,大风在这郭尔罗斯后旗草原上翻滚奔腾,将这办公室的玻璃窗摇撼得“格朗——格朗”紧响。屋里却很暖和。红砖砌的火炉上,铁叶子水壶沙沙——沙沙地将要滚沸。墙壁上那只大挂钟滴答——滴答地摇着钟摆。那盏低低垂到桌面上空的白玻璃罩煤油灯射出一个淡黄色的光圈。就在那时候,老高跟我谈起沈焕江,在这茫茫的松花江冰雪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老高那浓黑的帚眉下,放出赞叹的目光,点着头说:“是个厚道的同志!党给他什么任务,他干得可真踏实呀!这一点我了解,我在他们乡担任过书记。比方他到党委会来办事,三十里地一片冰雪,他夜晚晌一个人什么也不拿,带根电筒就来了。结果呢?弄得从脚底板到脑瓜顶都是泥是水。我说:‘老沈呀!你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爱惜自己呀,这样远的道,为什么不白天来?’他慢吞吞地看了我一眼说:‘白天不误工?’你看!这样一个好同志,一个好庄稼人。去年松花江差点决了堤,这新闻你是知道的,在那场斗争中,他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真感动人!在大江大浪里,昏过去三次,抬下来三次,又上去三次,……”我立刻请他详细讲讲,他却吸上口纸烟摇了摇头:“哎呀,真可惜,去年我调县民政科去了,我谈不大清楚,——反正沈焕江是完全干得出来的,我早就看到他干得出来!……”到底干出了什么?却谁也没作出具体的回答。我当然感到一阵轻轻的失望。老高一定是看出我的心情来了,所以现在他急忙忙地把这意外的消息传来给我。
黎明社支部书记陈荣,是个精干的三十岁上下的壮年,黑黑的圆脸盘,一双活灵灵的大眼睛,讲起话跟连发卡宾枪一样咔咔的。他们原来是到县里去参加除四害的会议的。想赶个大早,趁天亮到县,夜里三点钟就搭一辆拉砂子的胶皮轮大车上路了。谁想到风愈刮愈大,天愈亮愈冷,已经开化了的冰泡子冻得钢板一般硬。顶着风,眼瞧几匹马干蹦跶腿却走不出道来。顶了这么几十里地,现在只好在吉祥乡打个尖再说了。跟他来的一伙人到后面伙房里去找暖和地方去了。只剩下个头戴皮帽,足蹬“踏踏马儿”(一种软底高靿皮靴)的十三四岁的少年,独自个儿坐在红砖火炉旁低着头烤黄米面豆包吃呢。经老高一介绍,我们就围炉坐下,听陈荣谈沈焕江。他沉吟了半晌。火苗在火炉口上忽悠——忽悠地摇晃着。他忽然问老高和刚进来坐在一旁条凳上的女乡长王月娥:
“高书记!王乡长!我估摸去年夏天那大风比这冬天的还大是不是?”
“当然比这大,足有九级。”
“对,本来是西南风,风平浪静的,半夜三点钟转了东北风,风向一转,涌浪就一直朝着我们江堤冲了。天亮,雨瓢泼般下,连风带雨,把谷穗子啪啪地往地下摔。我跟沈焕江在防汛指挥部往总指挥部打电话报告情况。七天七夜,电话机子没离耳根,嗓子早就喊劈了,大伙都靠打手势讲话。这工夫,一个民工一头冲进来,瞪着两眼,脸吓得白纸一样,抖擞着嘴唇,搞了半天才冒出一句:‘可,可,不得了了,……江堤决了,水哗哗……往里倒,……’这还得了!他话一出口,我的脑袋就嗡的一声。我们这儿要是决了口子,七县六十二洼就全要淹掉呀!沈焕江一听,忽地站起身就往大堤上跑。大堤那样滑,跟小孩溜的滑板一样,沈焕江不知跌了多少跤,才爬上去,人已经变成个泥人了。他一看,堤倒还没决口,可是江面上那白花花的浪头,往江堤一冲就跳起两节楼那么高,再趁着风势一吹,就泰山压顶一样往江堤上猛压下来。前面的浪往后一退,后面的浪又一涌,呼的一下就从堤顶上空飞扑过来了。那个民工见那样大水直扑,就当是决了口子了。不过形势可确实严重极了!城墙厚的堤坝,给江水刷得堤坝顶上只剩下刀刃那么厚一片了。这还经得住大风旋上几旋,大江摇上几摇?站在堤顶上,你往前一看,哈!乌云滚滚,雷电齐鸣,雨点砸到脸上就跟刀尖子剜一块肉一样疼。眼看洪峰一峰接一峰往这刀刃厚的堤坝顶上猛扑。咳!就这刀刃般厚的堤坝顶在这儿抵住七县六十二洼上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呀!怎么办?!麻袋草袋都堵上了,手里可什么都没有了。这时节,老沈猛喊了声:‘共产党员跟着我来呀!’他就扑通跳进江水里,江水冰冷透骨,人怎么撑得住。可是他跳下去了,党员同志就一个跟一个跳了下去。人们就手拉着手紧紧地拉成一道线,脊背朝外,把胸脯贴在那刀刃般薄的堤坝顶上,就这样用自己的脊梁加厚江堤,顶着洪峰猛浪。一浪扑过来,大伙就一低头。风雨波浪绞在一道那力量该多么大?就那样一个劲啪啪——啪啪地往身上拍,谁能顶得住?可是沈焕江就那样在冰冷的江水里挺住。挺住,挺住,可渐渐支持不住了。只见他的嘴上直冒白沫子,眼睛慢慢走了神,他还挣扎着,从风浪里扬起脖颈喊叫:‘坚决,坚决呀!同志们!……’喊着,喊着,把脸栽到泥水里,人就昏迷不醒了。民工们去拉他,他还挣扎着怎么也不肯上来,拉上来之后,他还两腿跪在江堤上,——还一把一把抓住堤上的泥土往江水里放,……”
我听得出了神,连屋墙外的大风也听不见了。那戴皮帽的少年两眼更是亮晶晶的,看着陈荣,听他讲。
“又过了一会,他完完全全失去知觉了,我们把他抬回江堤下面的防汛指挥所里。卫生员给打上一针强心针,又在身上给压了几条厚棉被。这样,他才慢慢慢慢地苏醒过来。一苏醒过来,沈焕江同志他可又上来了。”
女乡长王月娥惊叹地睁大眼睛说:“怎么能又上来!”
“是又上来了。那九级大风一点也不给人留情啊!眼瞧着一浪比一浪大,一浪比一浪高,一浪比一浪猛。人就算钢筋铁骨,又哪能顶得住这狂风猛浪呢!可是沈焕江上来一看这情景,一句话没说,就又跳下去了,又把胸脯贴在江堤上。这一回,不要说共产党员,就是所有民工都受了他的感动,都跟着他跳下去了。下面浪打,上面雨浇,乌云滚滚,天空简直就压到江面上来了。沈焕江在江水里又搏斗了三十分钟。人们发现他嘴唇黑紫,两眼火红,大伙正要拉他,风浪就把他打昏了,人们一动他,他又清醒过来。恰好咱们县委王书记带着抢险队赶到堤上来,由他下命令,才算是把他抬下去了。谁知道风浪愈来愈大,报警的枪声顺着大堤上到处砰——砰响,到处响起了最紧急的抢险的信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