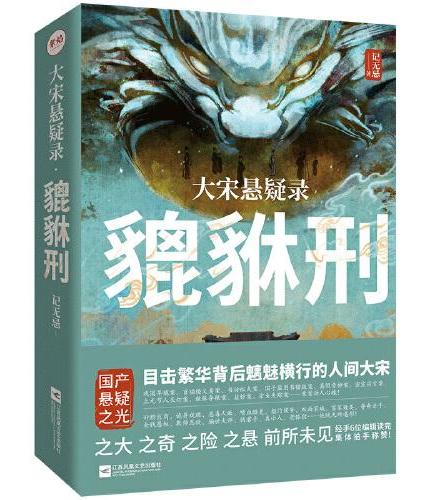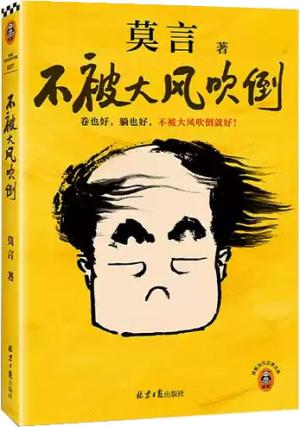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爱丁堡古罗马史-罗马城的起源和共和国的崛起
》 售價:NT$
349.0
《
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
》 售價:NT$
240.0
《
大宋悬疑录:貔貅刑
》 售價:NT$
340.0
《
不被大风吹倒
》 售價:NT$
300.0
《
人生解忧:佛学入门四十讲
》 售價:NT$
490.0
《
东野圭吾:分身(东野圭吾无法再现的双女主之作 奇绝瑰丽、残忍又温情)
》 售價:NT$
295.0
《
浪潮将至
》 售價:NT$
395.0
《
在虚无时代:与马克斯·韦伯共同思考
》 售價:NT$
260.0
編輯推薦:
在中国历史中,元代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期,异族统治、科举废弛、经济凋敝,给文人的精神世界蒙上了一层灰色,然而当他们转借书山画水以寄托生命时,却掀起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绘画革命”。
內容簡介:
在宋朝之前的数百年间,绘画有许多母题皆出自前图绘时期及纹饰的传统,而且毫不避讳装饰的效果。到了宋代,装饰价值虽然仍在,但是已经退居写实之后了;绘画成为洞察自然界的具体展现。到了元代,这样子的绘画是再也不可能了。此时,一些比较积极的画家奋力朝罗樾所谓的“超再现艺术”迈进。他们撇开早期所关心的课题,致力创新各种个人的、表现性的及思辨性的风格,这种风格隐含古意,却不至于牵强。就元代的知识分子而言,绘画成了一种修身养性和彼此沟通的工具,用罗樾的名言来说是一种人文锻炼。
關於作者:
高居翰(1926—2014),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教授,1997年获该校终身成就奖;亦曾长期担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书画部顾问。2010年,史密森尼尔学会授予其查尔斯?朗?弗利尔奖章(Charles Lang Freer Medal),表彰他在亚洲和近东艺术史研究中的杰出贡献。高居翰教授的作品融会了广博深厚的学识与细腻敏感的阅画经验,皆是通过风格分析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典范。重要作品有《图说中国绘画史》《隔江山色:元代绘画》《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山外山:晚明绘画》《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致用与娱情:大清盛世的世俗画》等。
目錄
三联简体版新序
內容試閱
元代画坛的变革与业余文人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