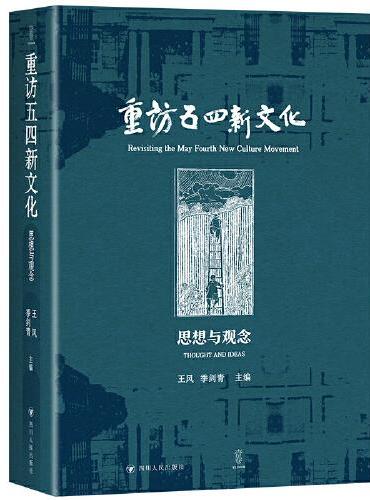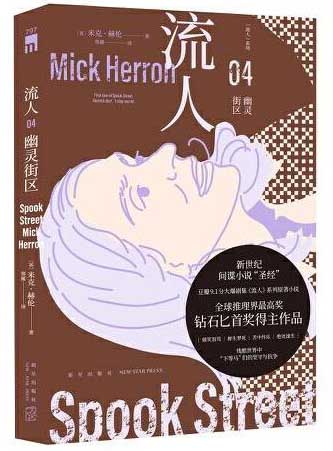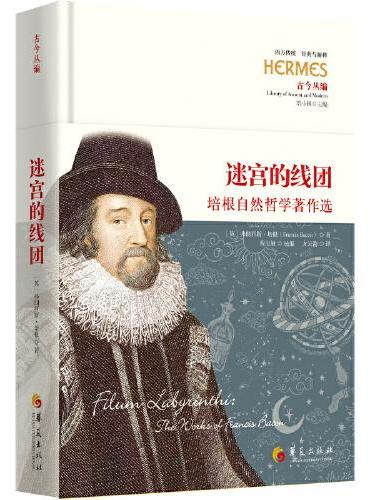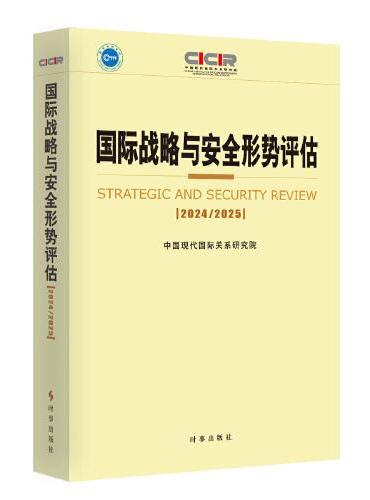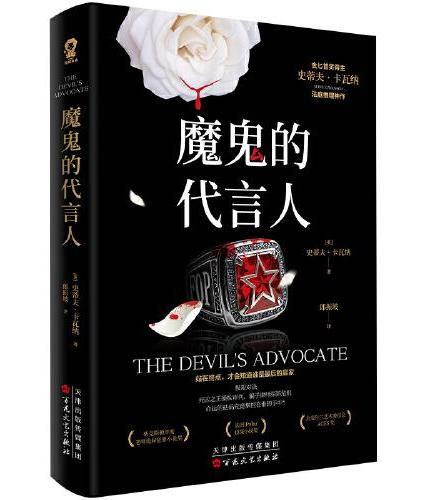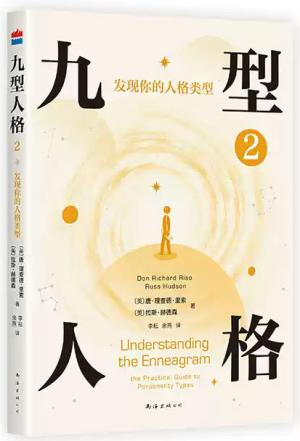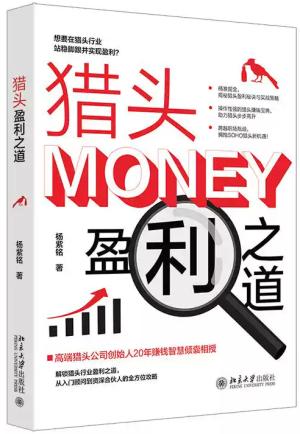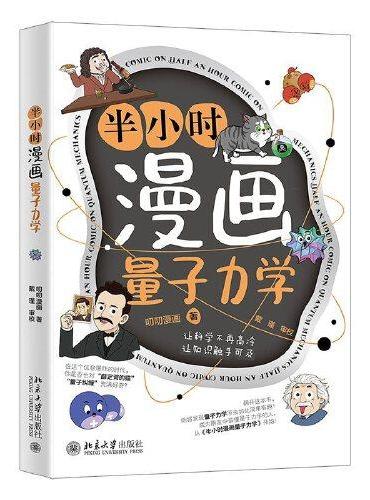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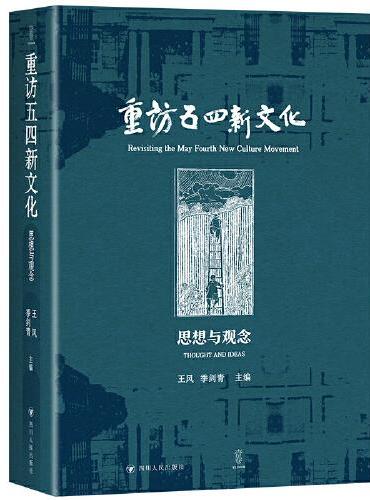
《
重访五四新文化:思想与观念(跟随杰出学者的脚步,走进五四思想的丰富世界)
》
售價:NT$
4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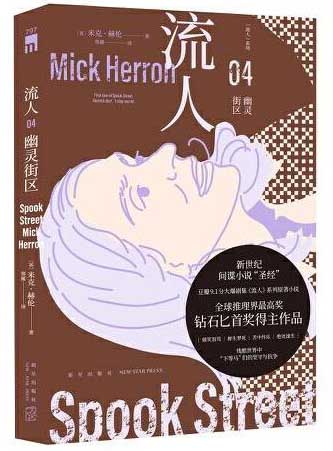
《
流人系列04:幽灵街区 午夜文库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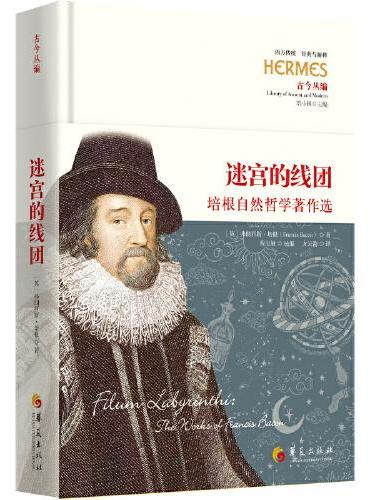
《
迷宫的线团:培根自然哲学著作选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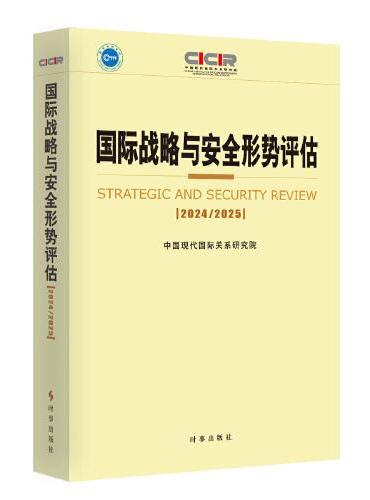
《
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24-2025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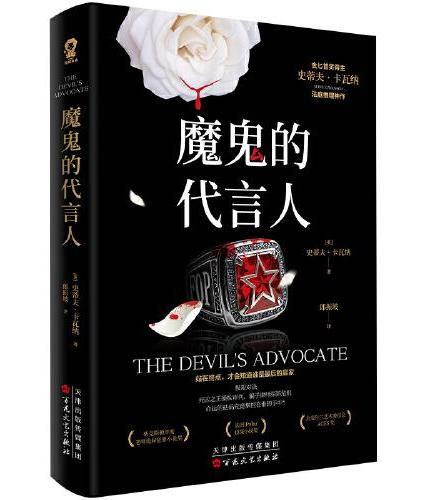
《
魔鬼的代言人
》
售價:NT$
2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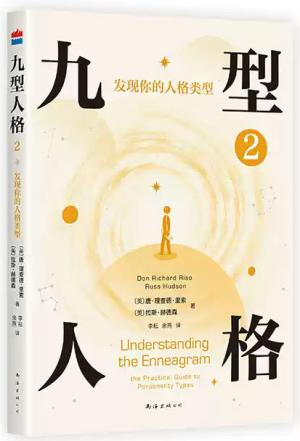
《
九型人格2:发现你的人格类型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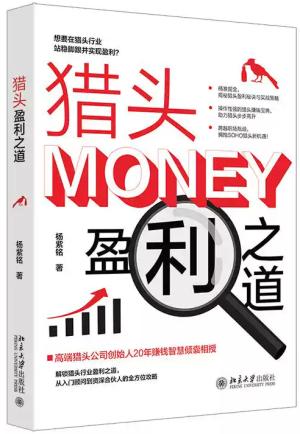
《
猎头盈利之道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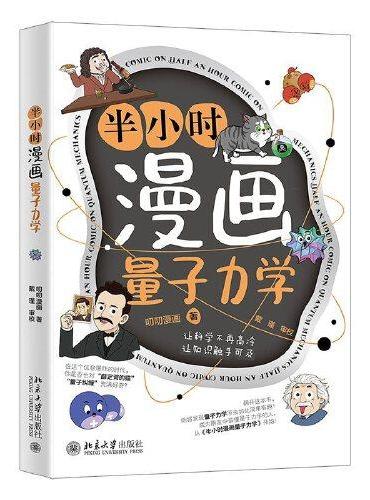
《
半小时漫画量子力学(让科学不再高冷,让知识触手可及,叨叨漫画著、戴瑾审校)
》
售價:NT$
250.0
|
| 編輯推薦: |
| 编辑推荐
【成年人的崩溃从父母生病开始】
◇照护父母如同载着他们开夜车,漫长崎岖的夜路,驶向他们的死亡。
——每天晚上,我都要 伴着父母被病痛折磨的呻吟声艰难入睡,但是只要家里一安静下来,我就会条件反射般从睡梦中惊醒,翻身下床冲去查看他们是否还活着。
——在日常生活的不堪与琐碎中,疲惫与绝望交替登场。而最安慰人心的话就是:“这种日子过不了多久了。”“照护父母”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爱化为灾难,正如它轻而易举地将灾难化为爱。
【我们该如何在守护父母的同时,安放好自己的焦虑】
◇一本细腻鲜活的照护日记,一段暗中有光的自救之旅。
——关于衰老、和解与珍惜。
——无比真实的记录,难以启齿的情绪:谁都无法坦然地承认,自己既怕照顾不好父母,又怕要一直照顾父母。
——作者选择匿名写作,以保护父母的隐私。
【了解之后,会释然】
◇每个家庭都需要的“处方书”、“安慰剂”。
◇灰暗的日子仍有温暖的爱意流淌,我们都可以好好地生活。
|
| 內容簡介: |
我们该怎样在守护好父母的同时,安放好自己的焦虑?
《不情愿的照护》开始于《卫报》的一篇文章,在2019年1月走红,讲的是一个匿名的中年男子搬回他年迈患病的父母家住,讲述了他在个人和职业生活分崩离析的同时,回到童年的家照顾日益虚弱的父母的经历。本书以日记的形式展开,共有四个部分,记录了2017年11月到2019年7月近两年间照护父母的日常。
故事从一个电话开始,87岁的父亲因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留下89岁的母亲独自在家。所以作者收拾了一个小袋子,回家帮忙。但是,他的生活就像父母的健康一样迅速崩溃了……作者被困在你长大的房子里,重新和与养育他的人一起生活,所有事情都在考验着他的理智和耐心。为了排解内心的苦闷,作者通过写日记自我舒缓,他的日记充满了对自我坦诚到残忍地剖析、对生活真实的记录、令人又哭又笑的英式幽默。了解之后,会释然。
|
| 關於作者: |
作者 | 不情愿的照护者
2019年,一篇讲述中年男子回家照护父母的文章在英国《卫报》走红。故事从一个电话开始,没错,就是我们都害怕的那种电话。父亲因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留下母亲独自在家。所以作者回到了童年时期的房子,开始了照护父母的生活。但是,他的生活就像父母的健康一样迅速崩溃了。
为了保护父母的隐私,他以匿名方式写作,现实生活中他的职业是作家、记者、编剧。
译者 | 万洁
自由译者。毕业于吉林外国语大学,曾任《科幻世界》杂志社外文编辑,代表译作《时间足够你爱》。三十岁前,天马行空,眼里只有书中的豪侠与巨龙;三十岁后,责任渐重,才看到生活的琐碎与无奈,遂发愿要译兔子洞和魔衣橱的异界奇景,也要译火车站和急诊室的人世悲欢。
|
| 目錄:
|
倒行上山 i
第一部分 001
2017 年 1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8 日
每个人都受伤 / 用餐与方向盘 / 沉睡者小队 / 肃静 /亚马逊会员 / 电话骗子 / 爹地是谁? /我们少数派 / 翻版阿拉莫 / 身份欺诈 / 黑色星期五 /园艺用品店里的人间乐事 / 一切终将成为过往 /树 / 解脱 / 成为贴身男仆 / 书架人生
第二部分 099
2017 年 12 月 9 日—2018 年 1 月 19 日
无望成功的计划 / 参与义务 / 生命重负 / 喝麦芽酒的风险 /厨房重地 / 赤身裸体者和爸爸 / 甜蜜的情绪 /朽坏与爆发 / 煎熬暂缓 / 快乐绅士过圣诞 /一个重量级拳手的安魂曲 / 狼狈的老人 / 压力下的体面 /手术刀下 / 等候 / 边际收益 / 城市画卷
第三部分 191
2018 年 1 月 20 日—2018 年 9 月 5 日
回家 / 恐惧的泪 / 重重倒下 / 求仁得仁 / 大妈群体 /内心世界 / 理想世界 / 阴影与尘埃 / 上楼 /这才是我们自己 / 儿子照常起床 / 管道又坏了 /光明的未来 / 通信不畅 / 假期,庆祝 / 继续尖叫 /复古商店 / 热天午后 / 轻伤员
第四部分 293
2018 年 9 月 10 日—
如何死得其所? / 水下逆流 /充满同情心的“法外之徒”/ 迷失在超市 /所谓高尚情操 /“如果病情恶化”/ 必败的绝望 /悲伤的故事最好留给冬天 / 使命宣言 /弗洛伊德与拉金之外 / 承诺和失信 / 夺回掌控 /苦尽甘来 / 可爱的伤口
|
| 內容試閱:
|
倒行上山
忘记是谁打来的电话了,但我记得那通电话的内容。到底是父亲身上的哪一种病突然发作,让人无法忽视,是心脏、肾,还是被低焦油层层包裹的肺?谁都说不准。其实,明智的选择是先解决他呼吸系统的问题,可我们已经在别的方向上耗费了太多时间,就算现在明智起来也为时已晚。
这类电话迟早会来,才不会管你的“旅途”(这是他们的说法)正行至何处。一个你爱的人,或者应该爱的人,他的倒下就会把你绑架到另一重现实里。
问题在于,你有多心甘情愿接受这件事。
每次母亲、姐姐或哥哥向我详细讲述父亲最近的住院情况时,我都会在我家楼上踱步。我们总是在楼上接重要的电话,因为那里信号好。
“我来想想该怎么办。”说完我挂了电话。
胃部的痉挛其实已经充分说明了我的真实想法——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到父母生活的地方,我度过大部分童年时光的地方,和我目前的住所相隔七十英里的地方。
我昨天刚刚从那儿回来。爸爸八十六岁了,妈妈八十八岁,比父亲身体康健些,但也同样虚弱。他们那里总有活儿需要人帮忙,所以就算只是陪在他们身边也是好的。其实我一次次去看他们,不过是为了再次离开时心里好受些,但这样做总好过袖手旁观。说来说去,我还是喜欢那里的。在某种程度上,那里的生活像是童年再现,除了演员的年纪都大了不少,本质上戏码还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这种参与程度可以让我进退自如。
父母过了四十岁才生下我,姐姐比我大十二岁,哥哥比我大九岁。节假日时,别的孩子偶尔会误以为他们是我的祖父母,这一点曾让我颇为烦恼。不过,我还有别的烦心事。自从我意识到活着的代价是死亡后,我就在为他们的死亡和一切死亡做心理准备。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我七岁。当时,我就在我现在写这本日记的房间里,看一本关于鸟的故事书。书中有只鸟死了,其他的鸟无法将它
复活,也无法接受它的亡故。我慌慌张张地跑下楼,问母亲我们是不是都会死。
“是的,”她告诉我,“但我们还会活很久。”
这两点都让她说中了。愿望如石沉大海并不算什么,若祈祷真的灵验,你才该小心。而我祈祷的是,愿他们长命百岁。
爸爸随着商船船队在海上漂了四十载,近些年,我眼看着他的健康跟他们的一艘船一样,缓慢且无可挽回地走着下坡路。他的工作性质,意味着我在成长阶段不怎么能见到他。等到他退休时,我已经离开了家。如今,他频繁陷入危急状态,每每发生状况我便回家探望,与早年的情形构成一种古怪的对称。这就像我们一直都在朝着对方的方向返航。更确切地说,是他埋伏在水下某处,浮浮沉沉……像一颗水雷。可这通电话不同寻常。我有预感,而且心下明白得很,因为我宁愿自己不明白。尽管我数十年来都在为此事盘算、发愁、反复劝慰自己,我仍然发现,就扛起这副担子而言,四十七岁的我并不比七岁的我更够格。
我下楼告诉妻子此事。“爸又住院了。我觉得我去与不去也没什么区别,毕竟我刚刚才从他那儿回来。也许我该等等,看情况如何……”
妻子的母亲患癌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为了照顾母亲,她曾无数次飞越大西洋。听见我这样说,正在做饭的她转过身,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快去。”
哥哥开车接上我,九十分钟后,我们就到了父母家。我们在 1976 年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夏天搬进这栋房子,路边的花草被晒得耷拉着脑袋,朋克摇滚在全国掀起热潮。我敢说,当时大家一定都觉得门前那铺着光滑地砖的五级高台阶很不错,就像吸烟和无保护措施的性爱一样。
日久年深,台阶上的地砖裂了。尽管后来加了栏杆,但在雨天或冬天,对踏上这些台阶才能进门的人来说,它们始终是一种可怕的存在,宛若登山者心目中的乔戈里峰和艾格峰。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年迈或滴酒未进的人从这些台阶上摔下来过,可是,那天我拖着行李包进门,感觉就像沿着台阶向上跌落,从一种生活跌进了另一种生活。在一英里之外的医院里,爸爸正挣扎在生死边缘,可真正改变的却是我的世界。死神还没开门,爸爸却早早在门口扎好了帐篷,就像在尚未营业的酒馆外焦急等待的酒蒙子,或是在还没开门的商场外徘徊的购物狂;总而言之,他为接下来
要发生的事做好了准备,我却被这件事打了个措手不及。
——————
在那九个月里,爸爸的病情有了一些好转,医生便允许他带着那像回转自助餐一样的并存疾病回家调养了。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自己的家。我的婚姻就像父亲的健康状况一样,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稳定,我和妻子已经走到了离婚的边缘。无法回头。
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的工作没了,与此同时,转向自由职业的机会也被我平白弄丢了。要想回到事情被搞砸之前的原点,恐怕要花上许多年,还得是运气好才行。于是,我那好歹在恢复中的父亲开始接受一个默默崩溃的儿子的照顾。侍奉在他床前的是一个深陷错误泥潭、缺钱、缺爱、霉运缠身且无家可归的人。随着难挨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发现自己似乎会时不时地被父母的房子和惯常生活所吞没。在他们能做的、不能做的和不该做的事之间,好似有一条条裂隙,而我不停地掉进了这些裂隙中。
渐渐地,我成了一个照护者。我的姐姐和哥哥都有孩子和各自背负的“债”。他们还要上班。而我现在没有孩子,没有工作,没钱,也没什么人需要操心。就这样,我回到了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离开的小城和卧室,开始照料站在八十岁尾巴上的两位老人。
我自然是关心他们的,可同时也觉得自己像个俘虏。“关心”听起来总好过“失败”。毕竟,除了父母家,我已经无处可去了。
“不关心也得关心!”母亲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这句劝诫来自一首古老的儿歌。结果一语成谶。
他的名字叫“不关心”,
肆意妄为无顾忌。
偷完李子偷梨子,
就像乞丐的野孩子。
他的名字叫“不关心”,
再不关心也得关心。
不关心就树上吊,
不关心就锅里煮,
煮熟煮透算拉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