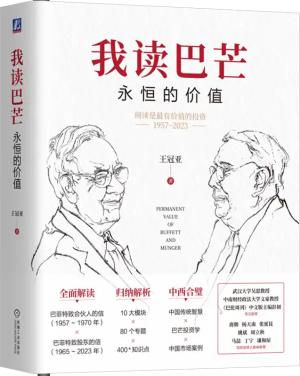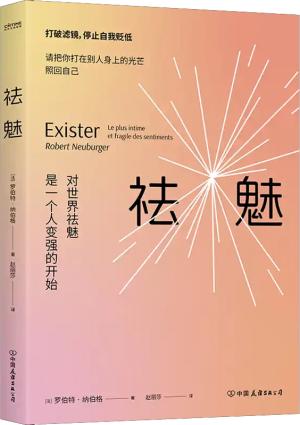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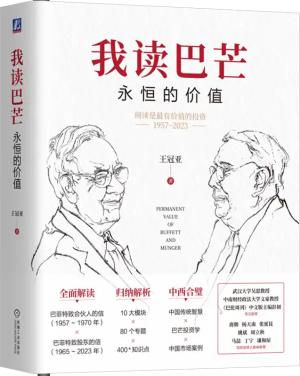
《
我读巴芒:永恒的价值
》
售價:NT$
602.0

《
你漏财了:9种逆向思维算清人生这本账
》
售價:NT$
254.0

《
我们终将老去:认识生命的第二阶段
》
售價:NT$
4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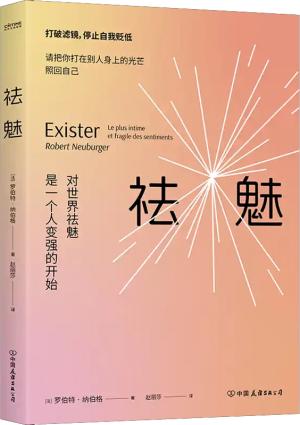
《
祛魅:对世界祛魅是一个人变强的开始
》
售價:NT$
286.0

《
家族财富传承
》
售價:NT$
704.0

《
谁是窃书之人 日本文坛新锐作家深绿野分著 无限流×悬疑×幻想小说
》
售價:NT$
254.0

《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第3版
》
售價:NT$
505.0

《
8秒按压告别疼痛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1.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获奖作品《另一个女孩》,中文版shou次引进
2.献给另一个女孩、一个素未谋面的姐姐的镇魂曲,你虽然缺席,却一直在我身边
3.傅雷翻译奖、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得主胡小跃倾情翻译
4.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 埃尔诺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出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她始终如一地从不同角度审视在性别、语言和阶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
|
| 內容簡介: |
我来扫墓25年了,从来没有跟你说过一句话。
但你不是我姐姐,从来不是。
我们没有一起玩耍过,吃过饭,睡过觉。
我从来没有碰过你,拥抱过你。
我不知道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你没有身体,没有声音,
只是若干张黑白照片上的一个平面图像。
我出生的时候,你已经死了两年半。
你是上天的孩子,是看不见的小女孩,
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你,大家谈话都避开你。
你是一个秘密,死着进入了我的生活。
|
| 關於作者: |
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
法国当代作家,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940年出生于法国滨海塞纳省的利勒博纳,在诺曼底的小城伊沃托度过童年。她起初在中学任教,后来在法国远程教育中心工作,退休后继续写作。
埃尔诺从1974年开始创作,至今已出版了二十余部作品,她的全部作品被授予“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奖”(2017年)、西班牙“福门托尔文学奖”(2019年)、“伍尔特欧洲文学奖”(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2022年)。
|
| 內容試閱:
|
这是一张乌黑色的照片,椭圆形的,贴在一个发黄的硬本子上。照片上有个婴儿,身体的大部分都坐在带齿形花边的坐垫上。坐垫有好几个,重叠在一起。她穿着一件绣花衬衣,只有一条系带,很宽,上面打了一个大大的结,几乎挂在肩后,像一朵硕大的鲜花,又像一只巨大的蝴蝶翅膀。婴儿瘦瘦的,脸被照片拉得很长,分开的双腿向前伸,一直碰到了桌边,高高的前额垂着褐色的鬈发。她圆睁双眼,死盯着你,仿佛要吃了你似的。这个婴儿像玩具娃娃般张开双臂,似乎在动。简直要跳起来。照片的下方,有摄影师的签名—“里代尔先生,摄于利勒博纳”—小本子的封面左上角也有签名,姓名首字母龙飞凤舞。本子已经裂开一半,封面脏极了。
小时候,我还以为—别人一定这样对我说过—那就是我。可那并不是我,而是你。
不过,我也有一张同一个摄影师拍的照片。我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褐色的头发也是鬈鬈的。但我看起来很胖,眼睛深陷在圆圆的脸中,一只手放在双腿间。我已经记不清当时看到这两张迥异的照片是否感到震惊。
快到万圣节的时候,我去伊夫托的公墓给两座坟墓献菊花,父母的坟墓和你的坟墓。一年年过去,我忘了坟墓在什么地方,但我以那个高高的十字架为参照物,它很白很白,从中央小道一眼就能看到。它矗立在你的坟墓上,就在他们的坟墓旁边。我在每座坟墓上放一束颜色不同的菊花,有时在你的坟墓上放一盆欧石楠。我把花盆埋在石板下方专门挖出来的花坛里。
我不知道人们在坟墓前是否会浮想联翩。我在父母的坟前逗留了一会儿,好像在对他们说:“我来了。”告诉他们这1年我的经历,我做了什么,写了什么,想写什么。然后,我走到右边你的墓前,看着墓碑,每次都会读一读上面的金色大字。那些字亮晶晶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粗糙地覆盖在原先的字上面的。原来的字没这么大,现在已经看不清了。做墓碑的石工擅作主张,把碑上原有的字铲去一半,姓名底下只留下这句话,当然是因为他觉得这句话最重要:“1938年圣周四去世”。第一次去给你扫墓时,让我吃惊的也是这句话。好像刻在墓碑上的这行字证明,你是上帝的宠儿,你是神圣的。我来扫墓25年了,从来没有跟你说过一句话。
根据身份登记信息,你是我姐姐。我们同姓,我“婚前”姓迪歇纳。在父母那破烂得不成样子的户口本上,我们俩一上一下地出现在“婚生子女出生与死亡”一栏上。你在上面,有利勒博纳(滨海塞纳省)市政厅的两个印章;我只有一个—我的死亡情况将填写到另一个官方户籍簿上,它证明我出生在某个家庭,姓改了。
但你不是我姐姐,从来不是。我们没有一起玩耍过,吃过饭,睡过觉。我从来没有碰过你,拥抱过你。我不知道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你没有身体,没有声音,只是若干张黑白照片上的一个平面图像。我想不起有你这么一个人。我出生的时候,你已经死了两年半。你是上天的孩子,是看不见的小女孩,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你,大家谈话都避开你。你是一个秘密。
你已经永远死了,在我10岁那年的夏天,你死着进入了我的生活。你在一个故事中出生和死亡,就像《飘》中斯嘉丽和白瑞德的小女儿邦妮。
那一幕发生在1950年的暑假。那是表姐妹们从早到晚一起疯玩的最后一个夏天,邻居的几个女孩和一些来伊沃托度假的城里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扮演商人和成年人,在父母的商店后院,在院子里搭建的许多小屋里用瓶架、纸板和旧衣物给自己造房子。我们站在跷跷板上轮流唱歌:“皮埃尔老师你们家那边天气很好”“我的紧身带和我的长裙”,就像在参加电台听众评选赛。我们逃出去摘桑葚。家长们禁止男孩跟我们玩,理由是他们老是玩粗鲁的游戏。到了晚上分手时,我们个个都脏得像泥猴。我洗洗胳膊和大腿,很高兴第二天又能重来。一年后,女孩们全都将四散而去,或者生了气。我感到很烦闷,只好看书。
我想继续写那年暑假,让它慢些离去。把那个故事写出来,就是与模糊的过去一刀两断,就像动手冲洗在柜子里保存了60年、从未冲洗过的照相底片一样。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故事始于一条狭窄的小路,那条路沿父母的杂货店兼咖啡店的后院延伸,叫作学校路。之所以这样叫,是因20世纪初,种着玫瑰花和大丽花的小花园旁,曾有一家私人幼儿园。墙边安装了高高的铁栅栏,墙脚杂草丛生。墙对面,是一道又高又密的篱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就常跟一个来自勒阿弗尔的年轻女人聊个没完。那个女人是带着她4岁的小女儿来公公婆婆家,也就是S.夫妇家度假的。S.夫妇的家离学校路十来米远。母亲也许是从商店里走出来继续跟这个女顾客聊天的。在那个季节,商店是永远不关门的。我在她们旁边跟那个小女孩玩,她叫米瑞伊。我们跑啊,追啊,想抓住对方。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警觉起来的,也许是因为母亲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我开始听她说话,听着听着好像都喘不过气来了。
我无法重述她讲的故事,只是,故事的内容和她说的话穿越了那么多年,直到今天仍好像在我耳边回响。它们瞬间影响了我的整个童年生活,就像一团没有声音也不热的火,但我继续在她旁边跳来跳去,围着她转,低着头,免得引起任何怀疑。
(现在,我觉得她的那些话撕破了一个朦胧地带,一下子攫住了我。结束了!)
她说,除了我之外,她和丈夫还有一个女儿,战前在利勒博纳死于白喉,当时才6岁。她描述了那个女儿喉部的皮肤及窒息状况,说:“她像个小仙女一样死了。”
她复述你临死之前对她说的话:“我要去看望圣母玛利亚和仁慈的耶稣了。”
她说她丈夫从热罗姆港的石油提炼厂下班回来时,发现你死了,“他都快疯了”。
她说“这跟失去伴侣不一样”。
她说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们不想让她伤心”。
最后,她说你“比那个人更可爱”。
那个人,指的是我。
当时那一幕,跟照片一样留在我心里,都没有变。我还看见那两个女人在马路上分别所站的准确位置。我母亲穿着白色的罩衫,不时地用手帕擦眼泪。那年轻女人的身材比一般顾客要漂亮,她穿着浅色的裙子,头发往后梳,绾成一个低矮的发髻,椭圆形的脸非常温柔(记忆在所遇到的众多人群中随机抓取,然后像打牌那样把同样的花牌配成对子,但我现在把她与鲁昂附近伊玛尔夏令营的一个女校长混淆了。1959年,我曾在那里当辅导员。她的图腾是蚂蚁,老穿着白色和米色的衣服)。
首先,一种有形的幻觉向我证实了那个情景的真实性,我“感到”自己紧紧地围绕着那两个女人跑来跑去,“看到”学校路上80年代才用来铺沥青马路的燧石,“看到”了斜坡、栅栏和逐渐减弱的光线,好像必须吞掉世界上所有的背景才能支撑即将来临的东西。
我无法准确地说出那个夏日的星期天具体是几
号,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在8月。25年前,我在读帕韦泽的《日记》时,发现他已经于1950年8月27日在都灵的一家旅馆房间内自杀。我赶紧核实,发现那天刚好是星期天。从此,我就认为是同一天。
我一年年远离它,但这是一个幻觉。在你我之间没有时间相隔。有些词永远没有变化。
“可爱”。我好像已经知道这个词不会用在我的身上。根据我的行为,父母平时是用这些词来形容我的:“胆大妄为”“臭美”“贪吃”“无所不知小姐”“令人讨厌”“你着魔了”。但他们的指责对我影响不大,反而让我确信他们是爱我的,他们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不时地送我礼物,这些都是证明。独女,被宠坏了,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总是在班上轻而易举地拿第一。总之,我感到自己有权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可爱”。在上帝眼里,我也并不可爱,正如7岁那年,我第一次忏悔时,B神父向我断然指出的那样。当时,我承认了“独自和与他人一道有过不良行为”,等于今天正常的性觉醒。他说,那些行为正让我走向地狱。后来有一天,寄宿学校的女校长也向我证明了这一点。她用明亮的眼睛斜睨了我一眼,说:“哪怕在班上门门功课都满分,也不一定能让上帝高兴。”我对宗教那套东西不怎么感兴趣。我不信教,但没有人觉察到—当我在教堂里跪在红色的亮光前,女校长对我耳语要我“向仁慈的上帝祈祷”时,我顽固地保持沉默。那种命令我觉得很幼稚,与大权在握的母亲身份不符。
“可爱”,也意味着亲热,爱抚,“亲切”。在诺曼底,人们就常常用这些词来形容孩子和狗。我跟成年人保持距离,喜欢观察他们,听他们说话,而不是拥抱他们,所以他们认为我不可爱。但对他们两人来说,我敢肯定我是可爱的,甚至比别的孩子更可爱。
60年后,我还不断地遇到这个词,不停地想弄清它于你、于他们而言是什么意思。那时,它的意思马上就跳出来了,瞬间改变了我的地位。在他们和我之间,现在有了你,别人虽然看不见你,但你被挚爱,而我被排斥,被推开了,以便让位给你。我被推到阴影里,你则在永恒的光芒中高高地翱翔;我一直认为自己是独生女,不存在相互比较的兄弟姐妹,而你出现了。如此情况,如何用词语表达,如何区分、排除?更多/更少,或者/和,之前/之后,存在或者不存在,生或者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