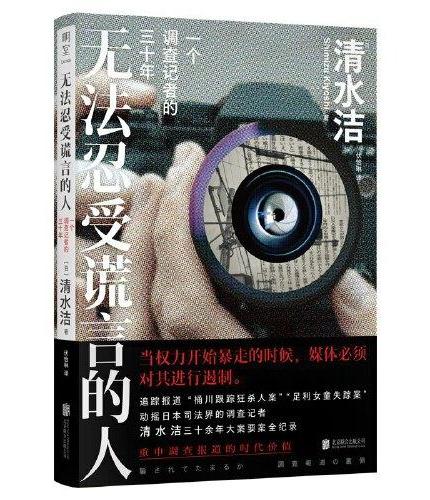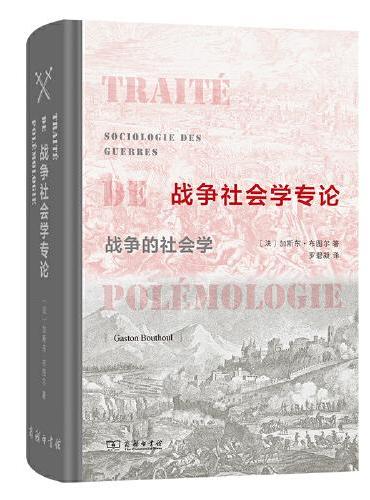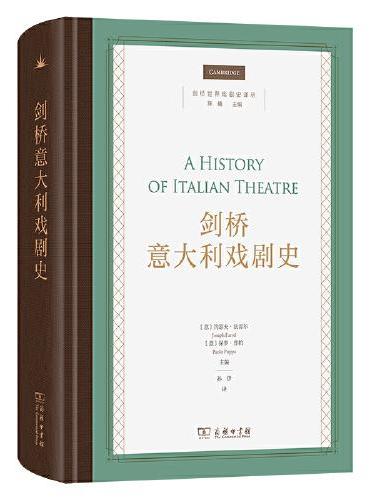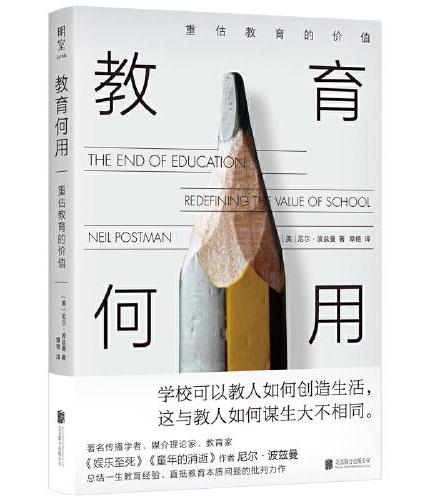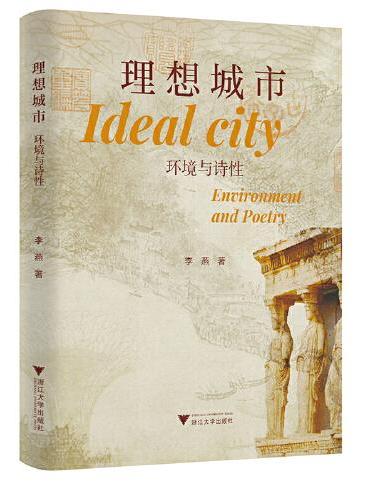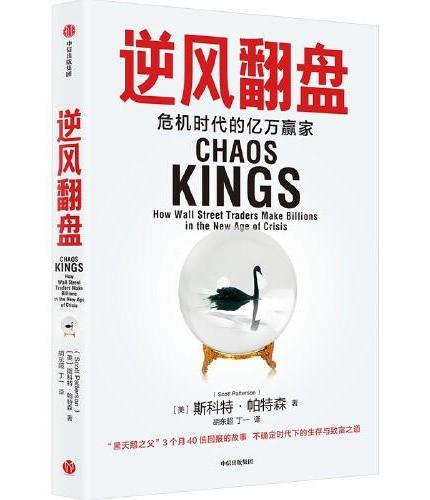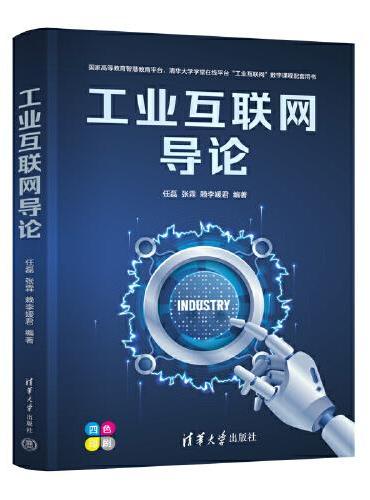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悬壶杂记全集:老中医多年临证经验总结(套装3册) 中医医案诊疗思路和处方药应用
》
售價:NT$
6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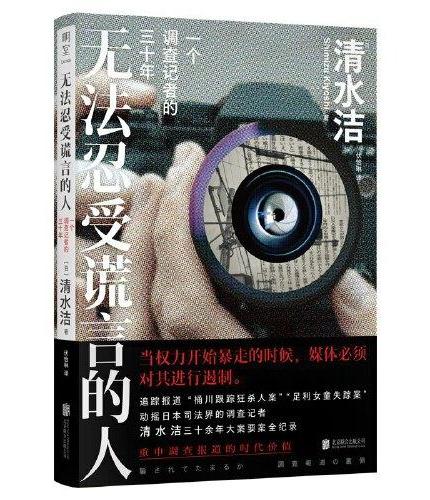
《
无法忍受谎言的人:一个调查记者的三十年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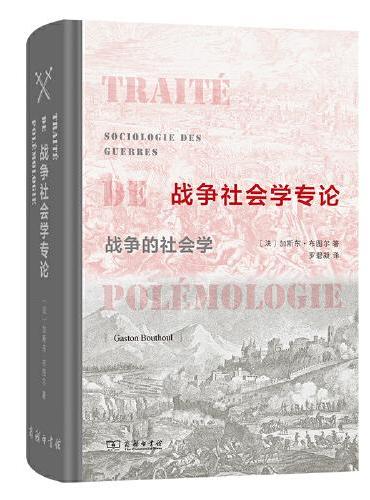
《
战争社会学专论
》
售價:NT$
5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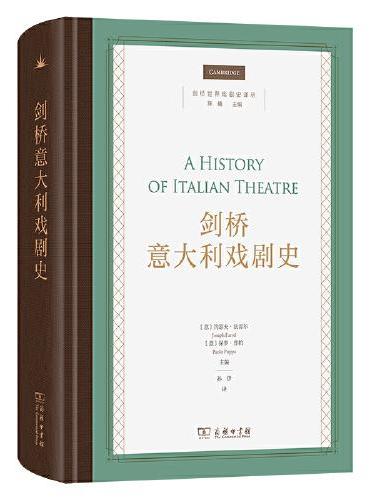
《
剑桥意大利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NT$
7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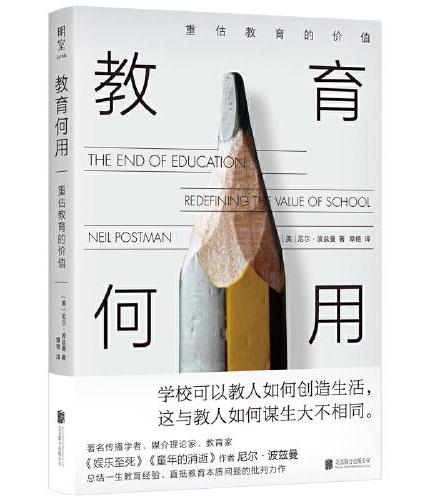
《
教育何用:重估教育的价值
》
售價:NT$
2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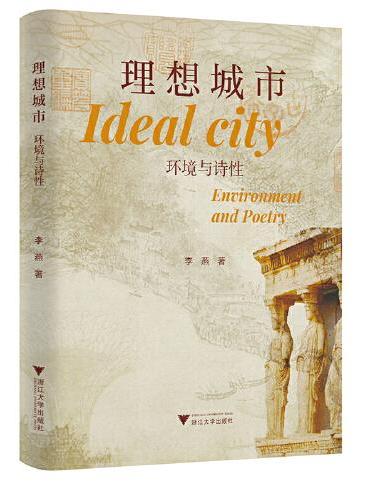
《
理想城市:环境与诗性
》
售價:NT$
3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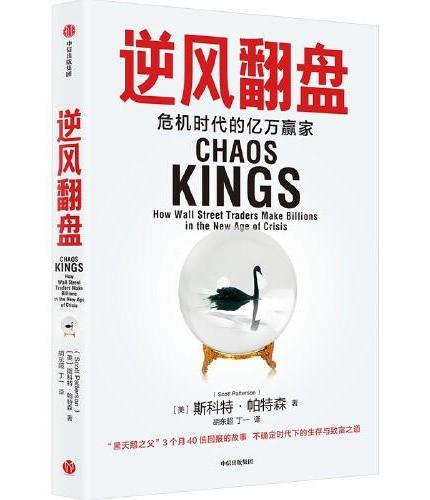
《
逆风翻盘 危机时代的亿万赢家 在充满危机与风险的世界里,学会与之共舞并找到致富与生存之道
》
售價:NT$
6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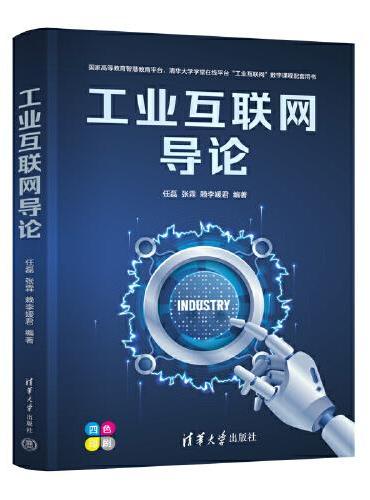
《
工业互联网导论
》
售價:NT$
445.0
|
| 編輯推薦: |
这条路离悬崖很近,崎岖不平,但它是我心之所向,妈妈。
献给所有从未屈服的女性
新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年度最佳图书
维多利亚州总理文学奖
|
| 內容簡介: |
|
1893年,澳大利亚南部雪山山脉荒凉的山坡上,莫利·约翰逊,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及一名普通农妇,她独自艰难地抚养着孩子们,同时在无望中等候着她那赶牲口的丈夫。在他们生活的荒无人烟的山间高地上,新上任的白人镇议员克林托夫一家,与一名被通缉的土著人几乎同时抵达了莫利的简陋棚屋。随着莫利和克林托夫两条主线故事的徐徐展开,人类对抗自然、母性、生存,以及原住民身份认同等主题逐渐凸显,扣人心弦。
|
| 關於作者: |
利亚·珀塞尔 Leah Purcell
澳大利亚原住民后裔,作家、导演、演员、编剧。《莫利》及其改编的同名电影曾获Nick Enright剧本奖、新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最佳图书奖和最佳戏剧奖、维多利亚州总理文学奖、澳大利亚影视艺术学院奖(AACTA)及赫普曼(Helpmann)最佳戏剧及最佳新澳大利亚作品奖。利亚·珀塞尔所创造的角色,是充满强大生命力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女性的代表。
译者简介:
段满福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泰国西瓦那大学导师。
刘小虾
本名刘志芳,1972年生人,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法律系,热爱文学与翻译。
|
| 內容試閱:
|
一轮满月终于从山顶上探出头来,照亮了大地。莫利站在自家露台上,直直地凝视着前方,说不出话来。
亚达卡站在莫利面前,穿着她丈夫的裤子、衬衫和背心,就是她前一天晚上在火坑周围修补的那件背心。亚达卡的头发湿了,向后梳着。“不要紧吧?”他问道。
莫利仍然不能说话。
“你的丈夫,看见我穿着他的衣服了?”
“穿上一双靴子,你就能被看成一个正派的人。”莫利终于说话了。亚达卡看着他的光脚。莫利说得有道理。也许丹尼说得对,正派的人脚上会穿一双靴子。从亚达卡现在的穿着来看,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儿像是真的。
莫利继续说:“你为我工作,我给你衣服作为报酬。他的衣服。旧衣服。那是你说的。这是事实。”
亚达卡点点头,转身要离开。
“等等。”
亚达卡转过身来面对着莫利。看到莫利站在月光下,他叹了口气,满怀渴望。
“我要给你的头发打蜡,让你的头发保持直立。湿头发会干的。干了以后,你的头发就卷起来了。坐下。”莫利指了指砧板。亚达卡知道他应该走了。离开,现在就离开!但他的心却让他留下。他取下斧头,把它放在一边,坐了下来。他盯着远处那个大大的银色月亮升到山顶上。它像一盏聚光灯一样,照进前院。
莫利回到屋里取蜡。回来时,她手里拿着一个小锡罐。她打开锡罐,挖出一块来,在指尖揉搓着。她看向亚达卡正在看的地方,用嘶哑的声音低声说:“满月。”
“对走夜路有帮助。”亚达卡回答说。两人都知道,月亮出来意味着亚达卡要离开了。
莫利慢慢地走向亚达卡,看着他的身形,把蜡油揉到手上。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女人的头脑是一团乱麻。”
莫利走近亚达卡,一边让自己镇静,当她探出身子,手指从亚达卡头发中划过时,她终于坚定了信心。莫利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内心也从来没有涌动过这样的感觉。她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涌动。一定是月亮。
莫利的手在轻轻地触摸着亚达卡的头发,感受着莫利的触摸,亚达卡呼吸变得急促。这种感觉是如此简单,却又如此有效。一种温柔的女性的触摸——一种他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的感觉。
莫利深深地叹了口气。一种无法控制的冲动侵袭而来。他们离得太近了,她也受到了影响。莫利摇摇头,努力地驱散月亮的魔力和此时此刻的诱惑。她必须找到一个分散注意力的东西,她必须隐藏这些冲动。把蜡抹到亚达卡头发里的时候,莫利看到了他的侧面。“你长得很好看。”
“我有一个白人爸爸。”
“你认识他吗?”
“我想甚至我母亲都不认识他。”
莫利对自己点了点头。“我不认识我妈妈。”
莫利有点儿对自己恼火了。她从来没把这件事告诉过任何人。她的丈夫知道,但仅仅是因为她的父亲警告过他,莫利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女性的影响,可能需要一些“学习”才能让她表现得像个女人。他指的是性。乔·约翰逊很好地保证了莫利的学习。不幸的是,对莫利来说,这种学习是通过残酷暴力的方式完成的。
亚达卡打断了她的思绪:“你有家人吗?”
“只有我的孩子们。有孩子之前,只有我爸爸。只有爸爸和我。他总会说:‘我们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家庭’。”
现在,他们之间你一言我一语,轻松地聊着。莫利把发蜡揉擦到亚达卡的头发后面。这对拉直卷发并不会真正起作用,但她在努力。莫利暗自希望亚达卡能回家。她不愿伤害他。“她生我的时候死了,我的妈妈。”
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让亚达卡震惊。自从他来到这里,莫利生活中的细节,让他亲切熟悉,而现在她说的这一件事……慢慢地,莫利的故事中支离破碎的片断在他的脑海中被联系在了一起。
亚达卡看着莫利。谜底终于揭开。他笑了。“是你。”现在,各种事实都吻合上了,亚达卡把这些线索从头捋了一遍。“莫利,玛丽的昵称。玛丽难产而死。金妮·梅数次来探望。”他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
“你说什么?”莫利看着他,满脸疑惑。给亚达卡的头发打好蜡后,莫利转过身来,站在亚达卡面前。
亚达卡想告诉莫利他所知道的一切。难道他注定要偶遇这个女人,并来到她家门口?“那个帮助你的女人,金妮·梅。她是我的养母。”
这对莫利没有任何意义。“世界真小——”她开口说,但亚达卡打断了她。
“你出生的那天晚上,她把你抱在怀里,你父亲趴在你死去的妈妈尸体上哭泣。”
“黑人妇女一直帮助白人妇女分娩。”
“金妮·梅一直在讲她妹妹深爱着一个白人男人的故事,要把这个故事传递下去。”
这句话触动了莫利。莫利不敢相信她所听到的内容。
亚达卡继续说,他有些激动地分享着他所知道的一切,金妮·梅告诉他的一切。这一直是她的计划。“黑玛丽,‘附近最白的黑人女人’——当地人都这么叫她。金妮·梅说她红头发,皮肤白皙,但她的恩加里戈人特征很明显。黑玛丽给一些赶牲口的人当厨师,你爸爸就是其中之一。”
莫利看着亚达卡,目瞪口呆。亚达卡趁机尽可能清楚地说出这个信息:“你的母亲。她是黑人。”
莫利狠狠地扇了亚达卡一巴掌。“你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我尊重你,你却得寸进尺。你在这里已经待够了!”
亚达卡知道,他必须把他故事讲下去,这是他的责任,尽管莫利很生气。如果他不这么做,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尽管他知道莫利现在可能会感到不安和不受尊重,他还是继续讲下去。他必须这样做。金妮·梅知道黑玛丽对那个苏格兰人的爱是真的,而对方对她的爱也是真的。因为没有人会接受他们,所以他们彼此保守着这个秘密。
“闭上你的嘴!”
“他们的爱就像最高峰对最低的山谷那样深沉,就像雪河那样狂野。”
“停!”莫利朝着她的猎枪走去,猎枪就放在露台的柱子上。
“恩加里戈人,他们是你的家人。这没什么可羞耻的。”
莫利转过身,把猎枪对准了亚达卡。“管好你那张说脏话的臭嘴,从我的土地上滚出去,滚开!”
亚达卡看着莫利,一脸绝望。他央求莫利让他把话说完。“莫利,求你了,我讲这个故事并没有恶意。这是真相,有关你的真相。一位伟大的女人讲给我的。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的生命——就是去分享这些故事,这样我们才能活得更长,活过明天,甚至活得更久。没讲出来的人生经历就是没活过的人生,而你的母亲,黑玛丽,瓦拉甘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在她短暂的一生中活得很自由。”
“我现在讲下一个故事,我无意冒犯你或你的妈妈,但我也从一个白人老农民那里听过一个版本。他雇我帮忙,作为报酬,在一段时间之内,他每天给我一顿饭,提供一个休息的地方。那个农民给我讲了那个白皮肤、红头发的年轻黑人妇女的事。从远处看,你会完全认为她是白人,但近距离看,她的黑人特征就很明显。他讲的故事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地区的白人给你妈妈取了个名字叫‘黑玛丽’,这样所有人都知道她确实是一个黑人女人,如果他们抓住了她……”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如果他们逮到她,就可以对她为所欲为了。”
老农民引用了别人说的话,对亚达卡说:
“一匹尚未驯服的小牝马。”
“她像野马一样狂奔。”
“像男人一样打架。”
“不过,她像黑人一样狡猾。”
亚达卡感受到了莫利的怀疑和困惑,后悔说出了这样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说了下去。“这些只是人们对她的一些评价。那个农民说他依稀记得有传言说黑玛丽被一个苏格兰人抓住了。农民的妻子说过黑玛丽和那个苏格兰人的事,但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我到那个农民家的时候,他的妻子早已不在了。‘娶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是合适的,’老农民说。‘与她发生关系是一回事。对一些人来说,这是常事。但要结婚,他们就得保密,不让别人看见。’”
亚达卡站在莫利面前。听到这些,莫利的情绪特别激动。亚达卡做最后一次努力,他想让莫利明白:“金妮·梅让那些故事流传了下来,她的妹妹对一个白人男人的伟大的爱的故事。她把这个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她最小的儿子巴尔布莱听,但他丝毫不感兴趣。巴尔布莱知道这是被吉米国王禁止的事情。我确实问过金妮·梅,为什么她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讲她妹妹的故事,她只是说,‘人们需要知道’。”
亚达卡盯着莫利。莫利接受了吗?
莫利在几秒钟内拼命想弄明白脑子里闪过的许多问题,那几秒钟对莫利来说就像一辈子一样。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她的故事——她就是不能彻底厘清,至少现在不能。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她怎么能够厘清呢?厘清了又有什么好处呢?被人知道有黑人血统。那她的孩子们怎么办?他们将不得不面对的?她必须把孩子放在第一位。
莫利终于开口说话了:“我需要你离开。现在。滚!听到了吗!滚!”
亚达卡终于沉默了,他转身离开。但就在这时,莱斯利骑警骑着马穿过灌木丛跑了过来。他的马口里吐着白沫——莱斯利骑得太快了。斯宾塞·莱斯利从马上一跃而下,既不优雅,也不气派,脚底还绊了一下,一只手里笨拙地握着手枪。他的马高高跃起。莱斯利看起来很累,显得很慌乱。“我听到了叫喊声。这里一切都好吧?”
莫利迅速镇定下来,心想,今晚还会发生什么事呢?这该死的满月!天啊,现在她必须处理这一切。像一个熟练的女演员一样,她眨眼间改变了自己的举止,说道:“没事的,谢谢你。”
亚达卡没有注意到莫利的变化,他迅速转过身去,系上衬衫最上面的扣子,掩盖他的伤疤和第一次和莫利见面时所带的铁项圈留下的红色印记。正是莫利使他摆脱了那个项圈。莫利此时此刻祈祷,亚达卡能把这件事情深埋心底。亚达卡转头面向骑警,低着头站在那里,像一个顺从的仆人。他也可以配合着演戏。多年来他一直这样做。他就是这样活下来的。
斯宾塞在他最上面的口袋里摸索着他的小笔记本,说:“这是——”他找到了他需要的信息。也许他只是在为了表达效果而假装犹豫。或者由于此时肾上腺素激增,使他一时糊涂,忘记了这些事实。“这是乔·约翰逊先生的房子吗?”
莫利,没有丝毫迟疑,表现得温暖而又热情好客。“我是乔·约翰逊太太。”
斯宾塞继续盘问:“约翰逊先生在哪里?”
“他到城里去买给养去了。明天早上就回来了,如果你愿意那时再来的话。”莫利回答道。
亚达卡一直低着头,保持沉默,努力去找到一个摆脱这种局面的方法。但就在他想出一个主意,抬头面向莫利的时候,那轮满月爬到了树顶,把一束光洒在他的脸上。“太太?”
斯宾塞转过身去面对这个黑人,一看到他的脸,马上意识到这就是海报上的通缉犯。此人因谋杀爱德华兹一家、他们家的中国用人、一名骑兵和一名当地警察而被通缉。我的上帝!
看到骑警的反应,亚达卡知道他被认出来了。他告诉自己要保持冷静,希望莫利能配合他。“我到外面去办事吧,太太?”
斯宾塞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如果他抓捕了这个黑人,他就会得到某种信任,这正是他所急需的。“不许动!”斯宾塞命令道。他的手颤抖着,努力地稳住手枪,把它对准了埃弗顿的头号通缉犯:一个逃跑的凶残野蛮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