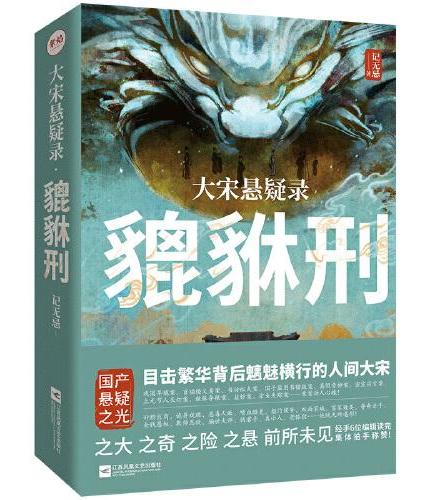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爱丁堡古罗马史-罗马城的起源和共和国的崛起
》
售價:NT$
3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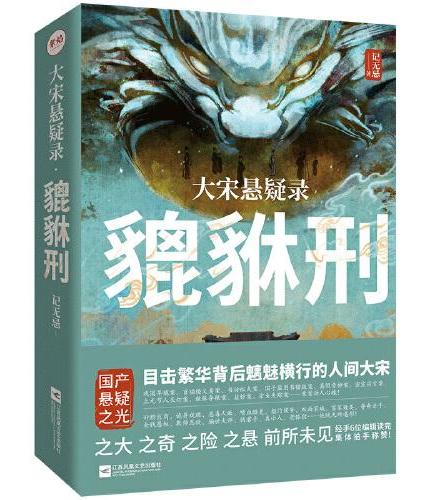
《
大宋悬疑录:貔貅刑
》
售價:NT$
340.0

《
人生解忧:佛学入门四十讲
》
售價:NT$
490.0

《
东野圭吾:分身(东野圭吾无法再现的双女主之作 奇绝瑰丽、残忍又温情)
》
售價:NT$
295.0

《
浪潮将至
》
售價:NT$
395.0

《
在虚无时代:与马克斯·韦伯共同思考
》
售價:NT$
260.0

《
日内交易与波段交易的资金风险管理
》
售價:NT$
390.0

《
自然信息图:一目了然的万物奇观
》
售價:NT$
640.0
|
| 編輯推薦: |
自19世纪30年代起,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脱离西方,建立属于自己本民族——斯拉夫民族的哲学思想,学界称之为斯拉夫主义。20世纪初期,俄罗斯社会经历了几次巨大的社会动荡,外来思潮蜂拥而至,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继承了先辈的事业,将斯拉夫主义推到了新的高度,其中七位杰出的学者共同编写了《路标:论俄国知识分子文集》。
《路标:论俄国知识分子文集》于1909年4月首次在莫斯科出版。该文集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把强烈的社会现实关切建立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基础上,主张知识分子的真正责任与使命在于社会精神与道德建设。在此基础上,文集从哲学、宗教、政治、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对俄国知识分子世界观进行了深刻反思。
文集包括7篇论文。尼·亚·别尔嘉耶夫的《哲学真理与知识分子的真理》批评俄国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谢·尼·布尔加科夫的《英雄主义和苦修主义——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宗教本性的思考》批评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粗俗无神论是在西方近代哲学的影响下形成的,脱离了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哲学精神;米·奥·格尔申宗的《创造性的自我意识》批评俄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思考的健全理智,只阅读、
|
| 內容簡介: |
|
1909年4月,七位俄国著名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文章合集《路标》在莫斯科出版,包括《哲学真理与知识分子的真理》《英雄主义和苦修主义》《创造性的自我意识》《知识分子与革命》等论文。这部文集鲜明地表达出一部分俄国学者对俄国激进知识分子的革命思想及其实践的反思与批评,旨在引导俄罗斯民族关注精神世界,构建属于俄罗斯民族的内在价值和民族精神。《路标》文集的出版在当时俄国思想界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
| 關於作者: |
米·奥·格尔申宗(1869—1925),俄国著名文学史家、政论家。
尼·亚·别尔嘉耶夫(1874—1948),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俄国哲学家,被誉为“二十世纪的黑格尔”“现代伟大的哲学家和预言家之一”。
徐凤林,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及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
张百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
| 目錄:
|
001 前言
米·奥·格尔申宗 / 著,徐凤林 / 译
004 哲学真理与知识分子的真理
尼·亚·别尔嘉耶夫 / 著,张百春 / 译
044 英雄主义和苦修主义——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宗教本性的思考
谢·尼·布尔加科夫 / 著,张百春 / 译
120 创造性的自我意识
米·奥·格尔申宗 / 著,张变革 / 译
160 维护法律——知识分子与法律意识
博·亚·基斯嘉科夫斯基 / 著,徐凤林 / 译
208 知识分子与革命
彼·别·司徒卢威 / 著,郭小丽 / 译
244 虚无主义的伦理学——评俄国知识分子的道德世界观
谢·柳·弗兰克 / 著,徐凤林 / 译
296 关于知识分子青年——日常生活与情绪侧记
亚·索·伊兹果耶夫 / 著,静纳 / 译
|
| 內容試閱:
|
中译本导言
2009年3月,当代俄罗斯著名哲学家霍鲁日(С.С.Хоружий,1941—2020)在纪念《路标》文集出版 100 周年的讲话中说:“《路标》是一部诊断的书,它谈论的是早已过去的危机,那是俄罗斯社会和意识的危机,俄罗斯生活原则的危机。看看《路标》之后的一个世纪,我们发现,那时的危机根本没有结束。” 这就意味着,这部文集的思想对于认识当今的俄罗斯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那么,《路标》文集是一部怎样的著作?
《路标》是由七位俄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共同参与撰写的论文集。其核心内容在于反思和批判俄国激进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活动及其背后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观念,这些分析广泛涉及俄罗斯的历史与文化、政治思想、法律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文集于 1909 年 3 月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效应。到1910年2月,一年内四次再版,出现了219篇回应文章, 5 本评论文集,国内外举办多次研讨会。回应者包括各种政治思想派别的著名代表,有文化保守派、民主派、自由主义者和革命者,包括哲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等。
这本文集为什么能够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我们认为大致有三个原因。首先,文集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俄国革命派知识分子主导的、通过民众暴动所造成的政治变革,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1905 年虽然实现了君主立宪制,但此后几年民主机制并未建立,政治动荡不安,无政府主义状况频现。因此,《路标》文集对这些迫切的现实问题的反思引起了俄国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其次,那个时代是俄罗斯思想和文化繁荣的时代,学术争鸣异常活跃,加之文集作者大多是当时的著名学者,甚至是某些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在学界有广泛影响。这种情况也使得该文集备受关注。后,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该文集的深刻思想性。文集提出了一系列尖锐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揭露不仅限于俄国知识分子这一对象,而且触及了俄罗斯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
那么,《路标》文集的宗旨是什么?提出了
哪些问题?俄国哲学家帕· 伊·诺夫戈罗采夫(П.И.Новгoродцев,1866—1924)在 1918 年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任务与道路》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概括,他指出,文集参加者想要号召俄国知识分子重新检查他们迄今为止赖以为生的那些信念,那些信念给他们带来了 1905 年的巨大失望,并且,未来必将给他们带来更沉痛的失望。文集参加者本身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著名代表,他们没有号召知识分子拒绝思想创造,也没有号召他们弃自己切身使命的信仰,而是只想指出,俄国主流知识分子迄今为止所走的道路,是一条错误的和毁灭的道路,他们可以也应当走另一条道路,这是很久以前俄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代表恰达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号召他们走的道路。如果他们不走这条道路,而是选择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拉夫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作为自己的领路人,那么,这既是俄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巨大不幸,也是俄国的巨大不幸。因为这是一条堕落的道路,是背离积极的生活原则的道路。抛弃这个走向深渊和毁灭的传统,回归历史的客观基础——这是俄国知识分子应当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这是展现在俄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两条道路,一条是生路,一条是死路。应当做出选择,这个选择也关系到国家的命运。这就是文集的
结论。
具体来说,文集的前言和七篇文章的大致思想观点可以概述如下。
文集的主要组织者和作者之一,历史学家米·奥·格尔申宗(М. О. Гершензон, 1869—1925)在文集的前言中指出了两种对立的原则立场,一种是文集参与者共同具有的立场,认为精神生活在理论和实践上优先于人类社会的外部制度。他们确信,“个人的内心生活是人类存在的创造力量,只有它,而不是政治制度的某些独立自在的原则,才是一切社会建设的牢固的基础”。而俄国激进派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则是建立在相反原则基础上的,他们否定精神生活,为社会生活牺牲精神生活,这是与人的精神本性相矛盾的,也是在实践上无成果的,不能达到他们给自己提出的目标,即解放人民。
哲学家尼· 亚· 别尔嘉耶夫 (Н. А. Бердяев, 1874—1948)在《哲学真理与知识分子的真理》一文中,从对待哲学的态度上揭露了俄国激进知识分子的功利主义。这些特殊的、“小圈子的”知识分子缺乏哲学修养,否定哲学的真理意义,使哲学服从于功利主义的道德准则。对“人民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崇拜,
成为这些知识分子的价值与“真理”(правда),压倒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真理(истина)。他们之所以不重视哲学创造乃至一切精神价值创造,是因为他们具有这样一种深层的“内心结构”和“精神本原”:“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和情感中,对分配和平等的需求总是高于对生产和创造的需求。”俄国历史在俄国知识分子身上塑造了一种与客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相对立的心理结构。因此,俄国知识分子只热衷于根据政治和功利主义标准来评价哲学真理,没有兴趣和能力从价值的观点来研究哲学和文化创造。俄国知识分子感兴趣的不是“形而上学是不是可能的”、“形而上学真理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形而上学是否会对人民的利益有害、是否会使人偏离同专制制度的斗争和为无产阶级的服务”的问题。俄国知识分子愿意相信任何哲学,只要它有利于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同时也可以抛弃任何深刻的和真正的哲学,如果这种哲学被怀疑是不利于这些理想的,或者仅仅是对这些理想持批判态度的。他们不能无私地对待哲学,他们要求真理成为社会变革的工具和实现所谓人民幸福的工具。
哲学家谢·尼·布尔加科夫(С. Н. Булгаков, 1871—1944)在《英雄主义与苦修主义》一文中深刻分析了俄国知识分子在国内政治环境与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革命性和非道德性。一方面,俄国政府始终对知识分子进行警察式的监督,他们经常遭到来自政府方面的打击和迫害,这使得他们在心理上有一种受难意识。因此,在俄国知识分子身上带有一种狂热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冒险精神,他们仇恨沙皇政府,时刻准备着推翻它,这种仇恨和破坏的情绪,构成了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的基础。另一方面,俄国知识分子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把无神论置于自己世界观的核心。无神论终成为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新“信仰”。丧失了原本的宗教信仰后,知识分子摆脱了罪的观念的束缚,陷入自我麻醉和幻想之中,把自己的阶层神化,立志为解放俄国人民和整个人类而奋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使用各种的手段。这一目的成为他们的无原则性和非道德性的有力辩护。在实践上,他们没有个人责任的观念,道德意识薄弱,为了“崇高的目的”,“一切都是允许的”。
历史学家米·奥·格尔申宗在《创造性的自我意识》一文中揭示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即知识分子的生活完全被社会舆论所捆绑,认为只有关心社会公益才是真正的人,这实际上是以关心社会问题的名义放弃对自我个体精神发展即个体意识的关注,必然导致其精神无力。格尔申宗认为,一切生命存在都是个体性的,而人又具有自我意识,所以人应关注个体的精神状况。他分析了人的精神结构,认为在意识与意志的关系中,意识应该摆脱外界强加的指令,服从内心意志,通过思考使自己成为完整而正常的人,而不是处于分裂状态。俄国知识分子忽视个体的发展,违反内心天性,热衷于社会公众生活,成为激进盲目的力量;他们与人民脱节,更无力反抗专制暴政。格尔申宗认为革命的失败暴露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同时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转机,可以使知识分子有选择和思考的自由,从而肯定自我个体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指向创造性的自我意识,帮助其摆脱精神危机。
法学家博·亚·基斯嘉科夫斯基(Б. А. Кистяковский, 1868—1920)在《维护法律——知识分子与法律意识》一文中揭露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法律意识水平的低下。作者指出,俄国激进知识分子从外部和形式上理解法,把法看作是法规大全,不明白法的本质。然而,一切文明民族走向政治和社会的进步,都是以对法的兴趣和法的发展,以及社会各基层法律意识的形成为基础的。在俄国,法从来没有引起过深刻兴趣。问题不在于没有杰出人物,而在于没有对法律观念的兴趣,这是因为“在俄罗斯人民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法律秩序”。“法律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内涵是自由。当然,这是外在的、相对的、受社会环境制约的自由。但内在的、更加的、精神的自由,只有在有外在自由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外在自由是内在自由的好训练班。”“俄国知识分子不具有那种使他们内心守纪律的法律信念。我们之所以需要外部纪律,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内心纪律。”俄国知识分子排斥法律,诉诸伦理道德,认为人们可以绕过法律规范,法律是形式现象、外部现象,伦理道德才是内在的真正的现象。他们忘记了,仅仅以道德为基础不可能建立具体的社会制度。作者认为,法律观念不可能从别处照搬并直接嫁接在本国土地上,社会需要对法律观念有所体验,而俄国没有这样的体验。若要把国家政权从“强权变成法治”,必须对社会进行法律意识上的重建。
经济学家、哲学家彼·别·司徒卢威(П. Б. Струве, 1870—1944)在《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中认为, 1905—1907 年革命是激进知识分子鼓动民众暴动给国家带来的政治危机。他认为造成这一危机的思想根源潜藏于激进知识分子的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中。从他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俄国激进知识分子犯了五个错误(甚至罪过)。,对国家的背叛。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形式是对国家的疏远和敌视。背叛的形式表现为无政府主义,相对形式是形形色色的革命激进主义。第二,在对待人民大众的态度上犯了道德的错误。知识分子虽然具有苦修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但是缺乏作为支配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之原则的个人责任思想,当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不认为人民也应当有自己的义务。因此他们的为人民服务精神也就“失去了根本的道德意义和教育的力量”。第三,知识分子否定对人民大众的教育。“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提出激进的要求并为此号召人民付诸行动的时候,完全否定了政治中的教育,并用唤起亢奋情绪的方式取代教育。”结果是“民粹派的说教在历史现实中变成了为所欲为和道德败坏”,而“在没有教育思想的政治中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专制制度,一种是暴民政治”。第四,对政治变革与进步的理解。激进知识分子认为“社会进步可以不是对人的改进所得到的成果,而是这样一种赌注,用激发民众的方法就能在历史的游戏中强行得到这个赌注”。第五,对政治与教育的关系的错误理解。激进知识分子把政治归结为社会生活的外部安置,归结为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竞争,使精神生活服从于外部含义上的政治。作者指出,这种错误理解应当加以改变,政治不是外部斗争,而是提高人民精神生活(道德水平)的手段,政治是为教育的理念服务的;教育的理念不是建立外部社会环境并依靠它发挥对个人的教育功能,而是人的精神创造,“是人对自身的积极改进,是为了创造的任务而在内心深处展开的自我斗争”。
哲学家谢·柳·弗兰克(С. Л. Франк,1877—1950)在《虚无主义的伦理学》一文中深刻挖掘了俄国革命知识分子道德世界观的根源,主要包括三种根源。一是虚无主义的功利主义,它否定一切价值,把为人民的物质利益服务看作是道德目标;二是道德主义,它要求个人自我牺牲,服从社会利益;三是反文化倾向,它力图把所有人变成“劳动者”,为实现普遍平等而压缩高级需要。20 世纪初的俄国知识分子不同于 19 世纪 70 年代“到民间去”的民粹主义实践者,而是成为革命者,这些革命者的存在是“现代俄罗斯文化的不幸”。因为他们只想着未来人们的幸福,为此与现有的恶作斗争,为了未来而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他们的爱未来实际上是爱神话,确切地说,爱的是自己关于未来的观念和自己为未来所进行的斗争,而把现实的他人要么作为世界之恶的源头,要么作为这种恶的牺牲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需要对现有世界进行破坏,因此,他们的基本道德命令是恨。这种对人民敌人的恨成为他们生活的心理基础。
政论家亚·索·伊兹果耶夫(А. С. Изгоев,1872—1935)的《关于知识分子青年》一文与其他作者取材不同,他把注意力放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成长阶段——童年和青年时期。作者在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基础上,追踪考察了俄国青年知识分子从家庭到学校、再从学校到社会的发展变化,并与英法德等国的学生进行了横向比较。作者一方面指出,俄国专制制度对青年精神面貌的负面影响——学校作为政治工具、小组活动被打入地下、进步界对学生一味逢迎;另一方面更强调指出,青年因缺乏正常的家庭学校教育和社会接纳而陷入隔绝状态,在伙伴关系中养成妄自尊大、打击异己和盲目服从等心态,打着社会活动的幌子荒废学业、肆意妄为,用高尚的精神目标掩盖卑劣的行为和无所作为,后,不甘平庸者甚至自寻毁灭以求得证明。作者对俄国知识分子以往的斗争方式和结果做出反省和检讨,呼吁青年学生走出狭隘圈子,努力学习知识和技能,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针对《路标》作者们的这些分析与号召,俄国当
时的主流知识分子是怎样回答的呢?他们是否认同《路标》的观点?根据诺夫戈罗采夫的见证,当时的主流知识分子方面的反应几乎是一致地反对和谴责!他们说,俄国知识分子没什么可重新检查的,也没什么可改变的。他们应当继续自己的工作,不需要拒绝任何东西,而是要坚决地指出自己的目标。他们指责“路标派”思想是反动的产物,是疲劳和沮丧的结果。其代表人物维佩尔教授在 1912 年写道:“我们伟大的国家在许多方面是不幸的,但有一种东西是健康的和强大的,并且能够许诺出路和解放——这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激情。”
的确,俄国激进派知识分子继续了《路标》作者
所力图阻止的道路。几年之后,俄国发生了更大的革命。又几十年之后,国家发生了剧变。许多历史事件和思想观念得到了重新评价。《路标》文集再次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自 1990 年至今,《路标》文集在俄罗斯出版发行总数达到 30 多万册。在文集出版 90周年和 100 周年的纪念日,俄罗斯学界都组织了专题研讨会。这证明,《路标》文集对那个时代症结的分析和揭露,其意义不仅限于那个时代。
俄罗斯历经百年风云变幻,但正如霍鲁日教授所说,“俄罗斯生活原则的危机”并未结束,甚至更加显著。透过《路标》文集的分析批判,我们能够隐约看到这一危机背后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根源。
当然,像任何观点都具有时代特殊性一样,《路标》思想也具有其历史局限性,我们译介这部著作,不意味着完全认同其中的理论观点,相信读者也能够有自己的鉴别。但由于这些理论是针对俄国知识分子及其精神文化的,而且这些观点也反映了俄罗斯精神的某些特性,因此,《路标》的思想观点对于我们研究俄罗斯历史文化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本书翻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寅卯研
究员召集组织,多位俄罗斯哲学与文化研究专家合作完成。文集前言及七篇论文依次由北京大学徐凤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百春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张变革教授、河北师范大学郭小丽教授等负责翻译。
感谢西苑出版社领导和各位编辑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工作。
译 者
2022 年11 月8
前 言
米·奥·格尔申宗 著
徐凤林 译
这本文集的论文不是为了像教条主义者那样,站在已知真理的高度审判俄国知识分子,也不是为了对俄国知识分子的那段过往进行高傲的鄙视,这些论文是带着对那段过往的痛心、带着对祖国未来的强烈忧虑写成的。1905—1906年革命及其后继事件的出现,仿佛是对俄国社会思想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将之奉为圣物来遵守的那些价值进行的一次全民测验。一方面,个别有思想的人从某些先验的设想出发,早在革命很久之前就已经明确看到了这些精神原则的错误;另一方面,社会运动本身的外部失败,当然还不能证明引发这一运动的那些思想是具有内在不正确性的。这样,就本质而言,俄国知识分子的失败并未暴露出任何新东西。但这个失败在另一种意义上具有重大意义:,这个失败令广大俄国知识分子深受震动,使他们觉得需要自觉地检验知识分子的传统世界观的那些基础,这些基础在此之前一直是被盲目信仰的;第二,事件的细节,也就是革命及其镇压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使那些大致意识到这种世界观之错误的人,能够更清楚地了解那段历史的罪过,并更加令人信服 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就产生了这本书:它的参与者们不能不说出对他们而言已经显明为真理的东西,同时他们都怀有这样的信念,即他们是在以自己对俄国知识分子之精神基础的批判,去迎合大家普遍意识到的对这种检验的需要。
在此为了一个共同事业而联合在一起的几个人,有的彼此之间无论在“信仰”的基本问题上,还是在自己的实践愿望上,都远不一致,但他们在这一共同事业上没有分歧。他们的共同立场是,精神生活在理论和实践上优先于社会生活的外部形式,其含义是,个人的内心生活是人类存在的创造力量,只有它,而不是政治制度的某些独立自在的原则,才是一 切社会建设的牢固的基础。从这一观点看,俄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这种完全建立在相反原则基础上,即建立在认定社会形式的优先地位这一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对于文集参与者来说,是具有内在不正确性的,也就是与人的精神本性相矛盾的;同时,这种意识形态也是在实践上无成果的,也就是没有能力实现俄国知识分子为自己提出的目标,即解放人民。 在这一共同思想界限内,文集参与者之间没有分歧。从这一思想出发,他们从不同侧面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如果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知识分子的“宗教”本质问题上,似乎显得有些矛盾,那么,这个矛盾也不是来自上述共同原则中的思想差异,而是由于不同的作者是在不同层面上研究这个问题的。
我们不是审判过往,因为我们清楚,过往的历史是必然发生的,但我们要指出,社会迄今为止走过的道路,已经把社会带入绝境。我们的警告并不新鲜:从恰达耶夫到索洛维约夫和托尔斯泰,我们全部的深刻思想家所反复强调的也正是这一点。他们的话没人听,俄国知识分子与他们擦肩而过。也许,现在已被巨大的震动唤醒了的俄国知识分子,将会听见那更加微弱的声音。
1909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