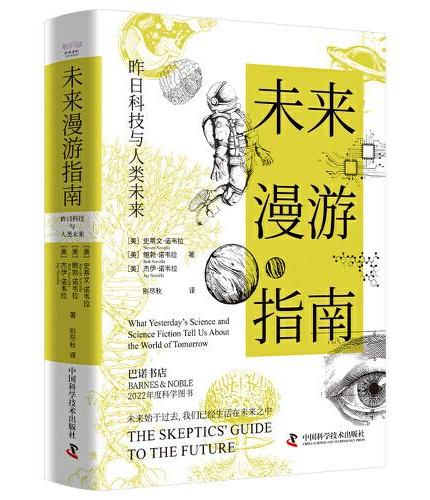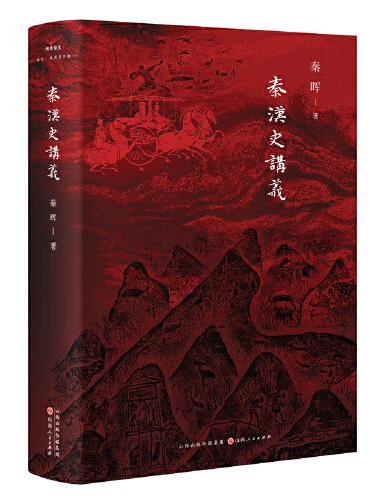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采煤机智能制造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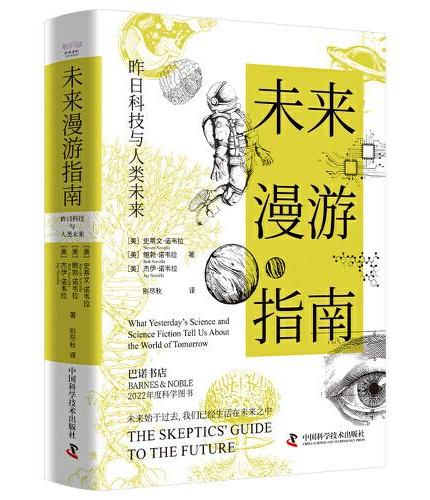
《
未来漫游指南:昨日科技与人类未来
》
售價:NT$
445.0

《
新民说·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上下册)
》
售價:NT$
790.0

《
我从何来:自我的心理学探问
》
售價:NT$
545.0

《
失败:1891—1900 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
》
售價:NT$
390.0

《
送你一匹马(“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看三毛如何拒绝内耗,为自己而活)
》
售價:NT$
2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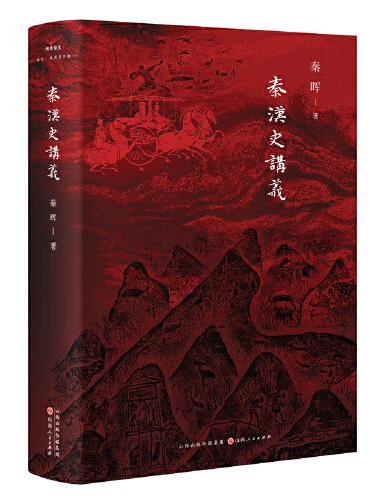
《
秦汉史讲义
》
售價:NT$
690.0

《
万千心理·我的精神分析之道:复杂的俄狄浦斯及其他议题
》
售價:NT$
475.0
|
| 編輯推薦: |
|
从“异域之眼”到少数民族本位的视野,从花鸟历法到交错的时间观,从语言神话到晚生的文字……本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以历史对照当下的视角,呈现碧罗雪山傈僳族生活图景,展演并探讨了傈僳族文化历史源流,尽显西南边陲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历史底蕴,体现了人类学者的学术洞见与理论素养。本书将以人类学的方法与理论为指引,展示碧罗雪山傈僳族的过去与当下。
|
| 內容簡介: |
|
生长于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向来是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早在古代就已和中原民族相互“观察”和“审视”。本书从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的傈僳族研究为起点,援引从《云南志》到《滇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的大量史料,向前回顾三江并流区域傈僳族走过的漫长岁月,向后则延伸了学科发展及傈僳族研究逐步深入的路径,着重分析了傈僳族的生计方式、时间制度、祖先崇拜与丧葬仪式等习俗,以小见大、深入浅出地呈现了碧罗雪山傈僳族的社会生活图景,由此揭示出傈僳族独特的时空观乃至哲学观。
|
| 關於作者: |
高志英,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专门史(中国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博士后,民族学、宗教学硕士导师,主要致力于云南“藏彝走廊”多民族、怒江流域跨境民族的族群源流、族群关系、族群文化互动与变迁研究。
杨晓龙,纳西族,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南边疆民族及中缅跨境民族研究。
|
| 目錄:
|
导论 相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一一重访碧罗雪山傈僳族
一、陶云逵与碧罗雪山傈僳族
二、从“山国”“族国”异文化的陌生人到“云南通”
三、陶云逵面对的傈僳族多重时空叙事
章 时空交集视野下的碧罗雪山腹地同乐傈僳古寨
节 空间:自然与文化空间叠合的同乐古寨
第二节 时间:山林到村寨的同乐建寨历史
第三节 靠山吃山:同乐山地生计中的时间、空间及其转换
第二章 多民族共生空间的生成与傈僳族时空观演变
节 历法:区域族际关系与多套时间制度的并行
第二节 村民生计方式变迁与时空观演变
第三节 神圣空间里的现实社会地位等级呈现
第四节 神圣仪式中的时空观与国家化呈现
第三章 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中的时空认知与仪式实践
节 依赖自然、亲近自然的山民
第二节 山神:靠山吃山民族亲近的自然神
第三节 敬畏自然而产生的氏族图腾崇拜
第四章 祖先崇拜中的时空观认知与仪式实践
节 祖先神话里的异族同祖异域观念
第二节 氏族祖灵的善恶分类与时空联隔
第三节 葬俗中的生、死时空转换
结论与讨论
参考文献
后记
|
| 內容試閱:
|
探寻发现社会文化新知识的另一条路径
《重访民族志从书》总序 何 明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主要的知识生产方式。受实验科学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1898年至1899年剑桥大学教授哈登率领考察队赴托雷斯海峡调查,开启了人类社会文化研究的新时代。后经由英国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归纳、完善与倡导,田野工作成为人类学认知与解释人类社会文化、生产新知识的必经之路。田野工作的地方,即所谓“田野点”,往往被视为人类学知识生产的起点和源头。
有些田野点在某项调查研究完成之后,仍然被该项调查研究者或其他研究者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即进行所谓“再研究”,继续着社会文化的知识生产。再研究的一种模式为追踪研究,即研究者对自己的田野点“回访”。许多人类学家会在某一个田野点完成调查研究并出版民族志成果之后,或连续或间断地返回该田野点进行调查研究,如林德夫妇(Robert Lynd and Helen Lynd)对于中镇(Middle-town)的回访、雷蒙德·弗思( Raymond Firth)对于提科皮亚(Tikopia)的回访、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对于南太平洋的美纳斯人(Manus)的回访、费孝通对于开弦弓村和大瑶山的回访、林耀华对于黄村和凉山的回访等。在这一模式中,人类学家与其田野点在一定时间内持续着研究与被研究的关系。另外的一种模式为接续研究,即其他研究者对他人调查的田野点的“重访”。一些人类学家曾经调查研究过的田野点受到其他人类学家的关注和调查研究,如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对玛格丽特·米德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田野点的研究、庄孔韶对林耀华《金翼》田野点的研究、周大鸣对葛学薄(Daniel HarrisonKulp)《华南的乡村生活》田野点的研究、褚建芳对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田野点的研究、梁永佳等人对许娘光《祖荫下》田野点的研究等等关于再研究的知识生产意义已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做了比较深入的论述D,在此不再赘述,仅引他人的论说以明之:“在社会人类学形成时期所做的许多研究,其资料犹如分散的岛屿一般,彼此是孤立的。这些研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人类社会的各种实例,人们可以把这些实例作为基础来研究社会的一般理论。但是,如果研究都是孤立的,那么,对社会过程的了解无论是从实际知识的角度或从科学分析的角度来说,其作用都是有限的。有关具体地区的一些资料很快会过时,它们只能提供关于变迁的可能性和原因方面的一些推测,因为每一具体地区的资料只能描述某一个时期的情况。然而,如果后来,同一个作者或其他作者,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能继续以同样的精确性对同一个社会进行描述,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从不同阶段的比较就能得出关于社会过程的有效成果,其价值也就超过各个孤立的研究。”
云南大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一直乘持“从实求知”的学术传统,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的“魁阁时代”,到21世纪初的“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中国少数民族农村调查”及近些年开展的西南民族志、边疆民族志、东南亚及其他区域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始终把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和民族学知识生产的基础和人才培养的重点,并努力探索推动从田野工作激发知识创新的新路径。
探索之一是“村民日志”及其后出版的《新民族志实验从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辑,学苑出版社出版第二辑)。从2003年至今,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在云南少数民族农村建设了14个调查研究基地,该项目的内容之一是请当地村民从“我者”的视角记录本村发生的事情,目的是释放被遮蔽或压抑的文化持有者的话语权,使其拥有自主的文化叙述与解释权利,形成独特的文化持有者的文化撰写模式。
探索之二是《反思民族志从书》(人民出版社出版)。负责各调查基地的老师撰写反思民族志,就村寨的社会文化与村民进行“对话”。如果说“村民日志”是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的“独唱”,那么《反思民族志从书》则力求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搭建起共同的“多音位”的“对唱”与“合唱”的舞台。通过来自异文化的学者与文化持有者村民分别对村寨的社会文化的解释并形成讨论或互文,呈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交互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及其所达成的程度,反思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民族志知识生产
探索之三是田野调查基地的回访。我们早的田野调查基地建于2003年,交由相关教师负责管理并开展持续的跟踪调查研究,以改变国内许多田野调查“一次性”的状况。在这一过程中,有的教师因工作变动或其他原因中途退出,但多数田野点负责人一直坚持下来,他们与其负责的田野调查基地村民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并经常返回田野调查基地调查。迄今,有的学者对田野调查基地已进行了持续近二十年的跟踪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成果,产出了一些具有原创性的知识和思想。我认为,这一探索对于推动田野调查和社会文化解释的细化和深化,促进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知识创新,成效非常显著。
探案之四是重返前辈学者田野点的再研究,成果即本套从书。我们鼓励与支持一批学者重返前辈学者的田野点进行再调查和再研究接续人类学和民族学中国研究的学术脉络,呈现与解释社会文化变迁与先贤们进行学术交流与对话,以期能够对中国社会文化研究提供新见解、新知识和新方法。
是以为序。
2021年3月20日于白沙河窝所
第二章第四节 神圣仪式中的时空观与国家观呈现
傈僳族认为,一个完整或正常的人是由肉体与灵魂构成的。而且,人死后其灵魂却不灭,需要通过丧葬仪式、念《指路经》将其灵魂送到遥远东方(在地方性空间认识里是东方)的祖灵所在地。这类祖灵就成为保佑后人的好鬼,汉语中常翻译为“神”。其他的非寿终正寝、凶死者,或者没有享“尼帕”念《指路经》的丧葬仪式的死者,其死魂就变为作祟于人的恶鬼。在这样的灵魂观下,有了不同的丧葬仪式,也有了过年期间的接祖、祭祖仪式。因时间、空间固化的“阔时节”,也使生者与祖灵交集的时间、空间随之固化了。其前提,一是祭祖主体的定居、半定居;二是被祭祀对象——祖神、祖灵(皆称“尼”)有其所处空间;三是祭祖主体有了时空固化的宗教性节日。因此,我们不得不回到碧罗雪山区域傈僳族的生产生活发展史来探讨这个问题。
前文已述,据同乐村民的口述史与区域历史事件互相印证,当地傈僳族大约在雍正年间(1722—1735)从“迁徙无常”转向定居、半定居的时代。定居,是在某一地驻扎下来,世代繁衍,并逐渐形成以村寨为中心,其下开辟水田,其中与其上开辟山地,再其上作为牧场、猎场、采集场的传统生产格局。差不多一个村子就占据一座山坡,其上下左右皆为其村寨空间范围。半定居,则是发现此地不适合居住,如没有水源,发生泥石流、塌方,或族人莫名病多、死亡多、先天残疾人多,就搬迁原村址不远之处建新村。另外就是因为垂直海拔田地、牧场导致的季节性迁徙。如在远离村落的山地季节性居住、耕种、放牧、狩猎、采集。而从外部动因来看,到雍正年间,维西之地被诸多纳西族、藏族土司分而治之。作为土司领地的属民,有服役、交租、从征等义务,土司以村落、氏族、家户为单位派役、收租,也就不可能“迁徙无常”,而是以氏族为单位寻找村址,建村立寨。于是,傈僳族从山民变成了村民,也有了固定的生产生活空间。
宗教观念的变迁,往往与其主体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同步。或者说,宗教观念变迁,是其主体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镜子。既然生者已经安居下来,那么对死者就从“丧则弃尸”转向以固定空间埋葬死者,于是有了死者灵魂的栖息地——坟地。又因其灵魂观念中,首先认为人死而灵魂不灭,而且死者灵魂仍然会与生者有关联;其次对于寿终正寝(正常死亡)者与非寿终正寝(意外死亡)者的灵魂属性有善恶之分,虽同用“尼”一词,但前者被认为是善魂,可翻译为“祖先”“祖灵”;后者可翻译为“恶鬼”“孤魂野鬼”。所以,“祖先”与“孤魂野鬼”被赋予“佑人”与“祟人”两种不同的功能。这就为两种死者(死魂)安排了不同的空间:寿终正寝者有氏族、村寨的固定坟地,非正常死亡者则埋尸野外。其空间分布与其善灵、恶鬼属性相对应,生者对前者的祖坟会在三年内维修,对后者的荒坟野冢则唯恐避之不及。但总的来看,伴随该区域傈僳族的定居、半定居,祖坟、野冢的空间已被固化了,并与生者保持着一种既有关联又有区隔的微妙关系,这就为在固定的时间祭祀祖灵提供了时空条件。
其次,就是如何固化祭拜祖灵的时空的问题。傈僳族村民认为生者与祖灵各有生存空间,应该各安其所。然而,寿终正寝者虽以经过“家—坟地—祖居地”的正常顺序列入“祖先神灵”之列,也仍需要生者定时供奉安抚;非正常死亡者却不可能从荒坟野冢到达祖居地,更不可能列入“祖先”之列,而不过是缺吃少穿的孤魂野鬼,就需要生者在其索取时提供祭品。因此,无论是“祖灵”或“孤魂野鬼”都依赖生者的供奉而“生存”,只不过前者只需定时——年节时由生者接祖、祭祖、送祖即可,所以祭拜“祖灵”的时空是固化的;而后者因为饥寒交迫,时时跟生者索要祭品,所以不仅需要年节时空固化的祭拜,平日里它们还会以作祟于人的方式索要祭品,因而祭拜的时空并不固定。祭拜祖先亡魂(善灵、祖先与恶鬼、孤魂野鬼)的传统中,由此出现了时空固化与随机两种模式。
再一方面,生老病死,为人生常态。面对不可回避的死亡问题,傈僳族村民也会思考: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尽管因为没有民族文字,他们并无远祖、中祖的线性历史记忆,却世世代代相传存在着一个祖居地,死者的灵魂终都要回归祖居地,与祖先们团聚。于是,对于祖灵,特别是寿终正寝者,傈僳族设置了一个遥远、模糊而虚拟的生存空间。这样看来,尽管村民乃至“尼帕”也不太讲得清楚坟地的性质,即其为死者灵魂永远的栖息地?或是生者在死者故去后上坟的前三年为死者灵魂、尸体的所在地?或者只是尸体埋葬地,而其灵魂在生者到坟地为其喂水三天后已经远达祖居地与远祖、中祖与近祖们相聚?但是,在村民的认知里,“孤魂野鬼”是到不了也不能去祖居地的,所以这个想象出来的虚拟空间对非正常死者是不存在的,只有一个物化的荒坟野冢,或泛化的荒郊野外,总之离村寨(生者)是不远的,其荒坟野家是实在的;而“祖灵”却有两个空间,一个是离村寨不远的坟地,一个是遥远的祖居地。前者也是实在的,有死者坟茔为中心的氏族、村寨坟地边界;后者却是个浩渺、模糊的想象空间。可见傈僳族村民的“祖灵”栖息地是实在兼虚拟的。但这并不影响村民在固定或场景性的时空祭拜“祖灵”与“孤魂野鬼”。至于“场景性”的问题,亦即生者在非年非节之时被后者“作祟”时,就不得不随机性加以祭拜。由此可见,我们说祭祖仪式伴随其主体的定居、半定居而日渐固化,也是相对而言的。
另外,死者是否能够埋入祖坟,以及之后能否被列入祖先神灵行列,除了需要是寿终正寝者之外,还需要重要角色“尼帕”介入,为其主持一环扣一环的丧葬仪式程序。而非正常死亡者,则不可能有此待遇,只能在“地狱”“阴间”受苦挨饿,不得已在年节生者祭拜“祖先”时蹭吃蹭喝,还在日常以作祟于人的方式与生者产生时空交集。那么可见,“尼帕”在死者灵魂分类中也充当了重要角色,或者说以其对不同方式死亡的人所采取的态度、行为,代表了村民的祖先崇拜与灵魂崇拜观念。在此意义上,“尼帕”成为祭祖仪式时空固化的关键人物。因此,作为祭祖仪式时空固化的先决条件之一的“尼帕”的产生和活跃,也与定居、半定居生计方式的形成有密切关联。而其中祭祖仪式时间固化、细化,还与本土的“十月花鸟历法”“哇忍波十二月历法”以及汉族农历、西洋公历的传入有重要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