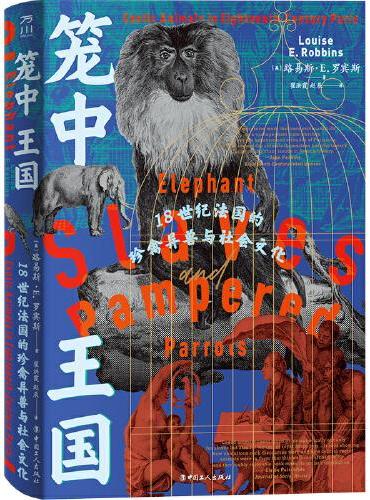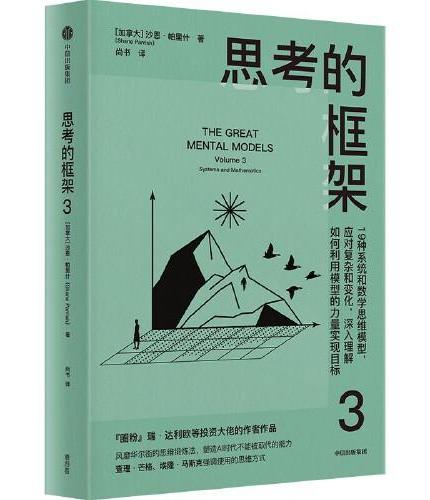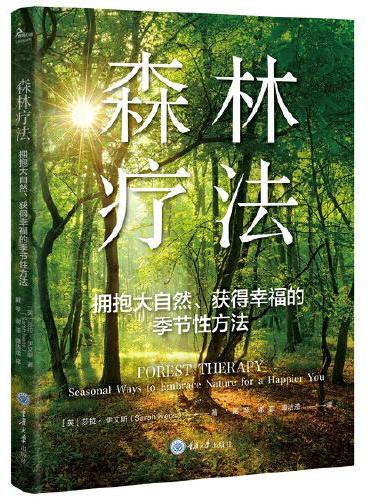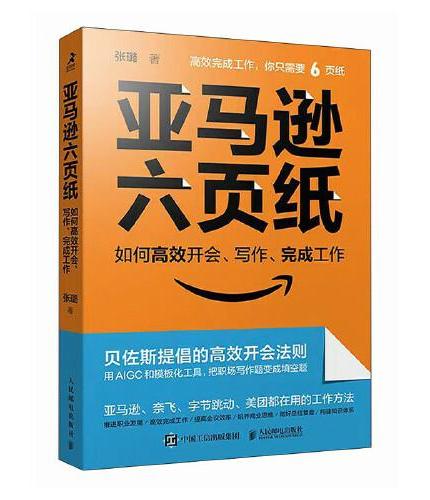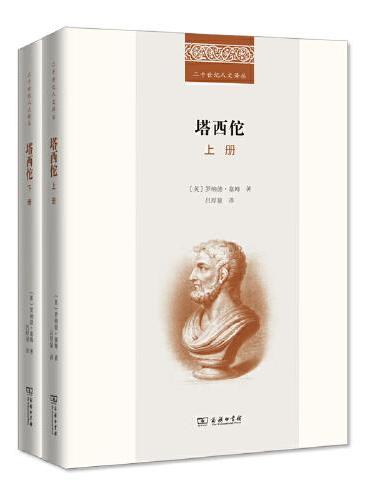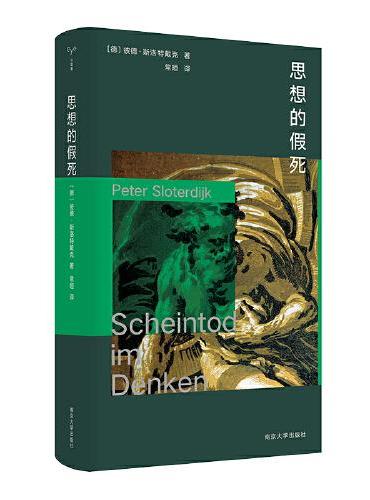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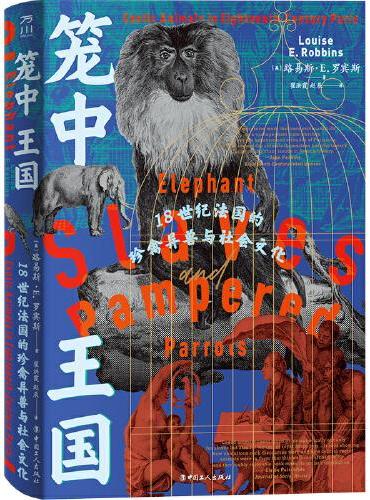
《
笼中王国 : 18世纪法国的珍禽异兽与社会文化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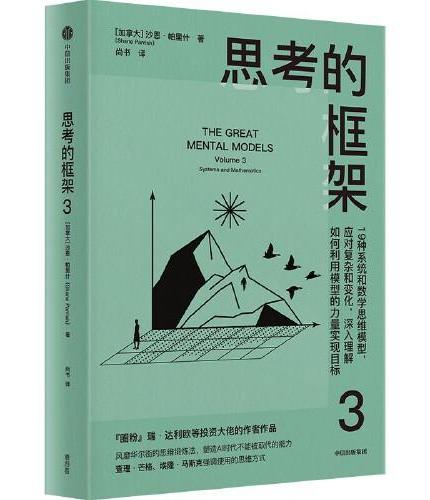
《
思考的框架3 巴菲特芒格马斯克推崇的思维方式 风靡华尔街的思维训练法 沙恩·帕里什 著
》
售價:NT$
2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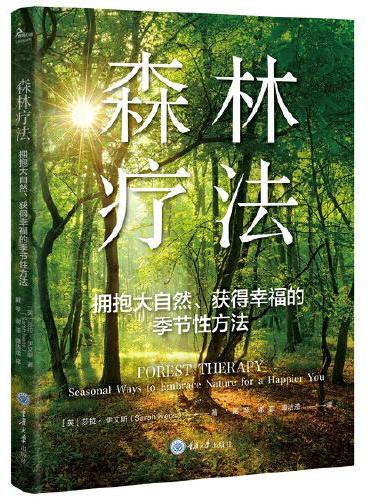
《
森林疗法:拥抱大自然、获得幸福的季节性方法
》
售價:NT$
340.0

《
希腊人(伊恩·莫里斯文明史系列)
》
售價:NT$
8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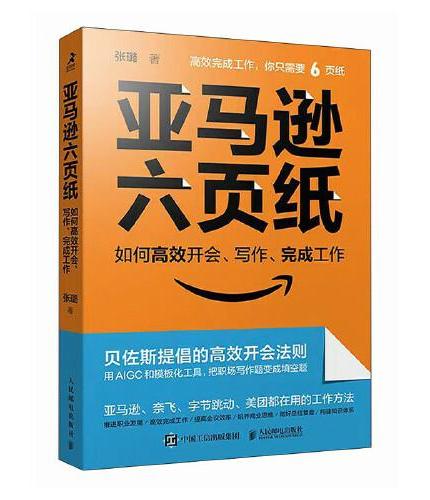
《
亚马逊六页纸 如何高效开会、写作、完成工作
》
售價:NT$
349.0

《
世界巨变:严复的角色(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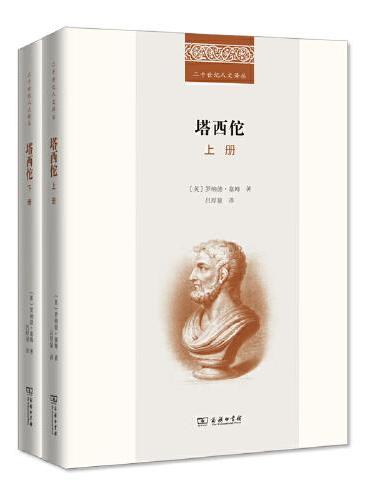
《
塔西佗(全二册)(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
售價:NT$
1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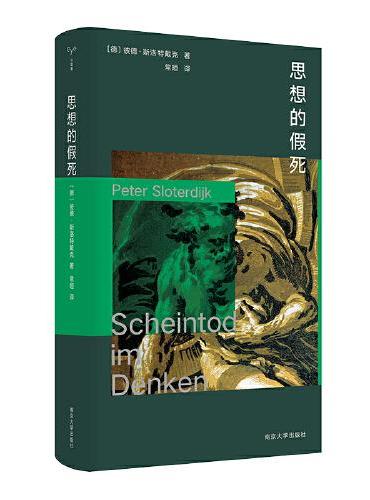
《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思想的假死
》
售價:NT$
290.0
|
| 編輯推薦: |
★收录《雪国》《千鹤》,一本书读两部诺奖作品
★读爱情小说,就读川端康成;读川端康成,不可错过高慧勤经典译本
★学者型译者高慧勤,海量读者心中的“白月光”
★精心页下注,扫除文化差异下的阅读障碍
★川端康成入门读,这一本就够了
|
| 內容簡介: |
1968年,川端康成凭借《雪国》《古都》《千鹤》三部代表作获诺贝尔文学奖。本书收录《雪国》与《千鹤》。
《雪国》是川端康成倾注心力最多的一部作品,也是最能体现他文学风范的作品,被称作“近代文学史上抒情文学的顶峰”。在其所有作品中,《雪国》被海外翻译得最多,字里行间的虚无之美、洁净之美与悲哀之美达到极致,令人怦然心动又惆怅不已。
在川端的作品中,《千鹤》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它展现了爱与道德的冲突,从多方面反映了川端创作的独特风格,是一部较复杂、较有争议的作品。如川端所言,小说家“要敢于写无道背德的作品,做不到这一步,小说家就只有灭亡”。
|
| 關於作者: |
作者 [日] 川端康成(1899—1972)
日本新感觉派作家,著名小说家。1968年凭借《雪国》《古都》《千鹤》三部代表作获诺贝尔文学奖,亦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日本作家。
译者 高慧勤(1934—2008)
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日文专业,曾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副会长、会长,在日本文学研究、翻译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她的译著文体风格贴近原著,译文典雅优美,选词炼句精益求精,在国内外译坛享有很高声誉。主要译著有《罗生门》《日本短篇小说选》《舞姬》《蜘蛛之丝》《雪国?千鹤?古都》《川端康成作品精粹》《地狱变》等。
|
| 目錄:
|
雪国???001
ゆきぐに
千鹤???141
せんばづる
|
| 內容試閱:
|
雪?国
ゆきぐに
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大地赫然一片莹白。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姑娘从对面的座位上起身走来,放下岛村面前的车窗。顿时卷进一股冰雪的寒气。姑娘探身窗外,朝远处喊道:
“站长先生!站长先生
一个男人提着灯,慢腾腾地踏雪走来。围巾把他的鼻子都包住了,帽子的皮护耳垂在两边。
岛村眺望窗外,心想:竟这么冷了吗?只见疏疏落落的几间木板房,像是铁路员工的宿舍,瑟缩在山脚下。不等火车开到那里,雪色就被黑暗吞没了。
“站长先生,是我。您好。”
“哦,是叶子姑娘呀!回家吗?天儿可又冷起来啦。”
“听说我弟弟这次派到这儿来工作,承您照顾啦。”
“这种地方,恐怕待不了多久就会闷得慌了。年纪轻轻的,也怪可怜的。”
“他还完全是个孩子,请您多加指点,拜托您了。”
“好说好说,他干活很卖力。这往后就要忙起来了。去年雪可大哩,常常闹雪崩,火车进退不得,村里送茶送饭的也忙得很呢。”
“站长先生,看您穿得真厚实呀。弟弟来信说,他连背心还都没穿呢。”
“我穿了四件衣服。那些年轻后生,一冷便光是喝酒。现在着了凉,一个个横七竖八全躺在那儿了。”
站长朝宿舍方向扬了扬手上的灯。
“我弟弟他也喝酒吗
“他倒不。”
“您这就回去
“我受了点儿伤,要去看医生。”
“噢,这可真是的。”
站长的和服上罩着外套,他似乎想赶紧结束站在雪地里的对话,转过身子说:
“那么,路上多保重吧。”
“站长先生,我弟弟这会儿没出来吗叶子的目光在雪地上搜寻着。
“站长先生,我弟弟就请您多照应,一切拜托了。”
她的声音,美得几近悲凉,那么激扬清越,仿佛雪夜里会传来回声似的。
火车开动了,她仍旧没从窗口缩回身子。等火车渐渐赶上在轨道旁行走的站长时,她喊道:
“站长先生,请转告我弟弟,叫他下次休息时,回家一趟。”
“好吧——”站长高声答应着。
叶子关上窗子,双手捂着冻红的脸颊。
这是县境上的山。三辆扫雪车时刻准备着,以供下雪天之用。隧道的南北两端,已架好雪崩警报电线,还配备了五千名清雪民夫,再加上两千名青年消防员,随时可以出动。
岛村听说这位叶子姑娘的弟弟打冬天起,便在这行将被大雪掩埋的信号所干活,对她就越发感兴趣了。
然而,称她“姑娘”,不过是岛村自己忖度的罢了。同行的那个男子是她什么人,岛村自然无从知道。两人的举止虽然形同夫妻,但是,男的显然是个病人。同生病的人相处,男女间的拘谨便易于消除,照料得越是周到,看着便越像夫妻。事实上,一个女人照顾比自己年长的男子,俨然一副小母亲的样子,别人看着不免会把他们当成夫妻。
岛村只是就她本人而论,凭她外表给人的印象,便擅自认为她是姑娘而已。或许是因为自己用异样的目光观察得太久,结果把自己的伤感也掺杂了进去。
三个小时之前,岛村为了解闷,端详着自己左手的食指,摆弄来摆弄去。结果,从这根手指上,他竟能鲜活地感知即将前去相会的那个女人。关于她,他越是想回忆得清楚些,便越是无从捉摸,反更觉得模糊不清了。在依稀的记忆中,恍如只有这个指头还残留对女人的触感,此刻好似仍有那么一丝湿润,把他带向那个遥远的女人身边。他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时时把手指凑近鼻子闻闻。无意之中,这个指头在玻璃窗上画了一条线,上面分明浮现出了女人的一只眼睛,他惊讶得差点儿失声叫出来,因为他魂牵梦萦正想着远方。等他定神一看,不是别的,原来是对面座位上那位姑娘映在玻璃上的影子。窗外天色垂暮,车中灯光明亮,窗上玻璃便成了一面镜子。但是暖气的温度使玻璃蒙上了一层水汽,手指没有擦拭之前,便不成其为镜子。
单单映出星眸一点,反而显得那姑娘格外迷人。岛村把脸靠近车窗,赶紧摆出一副旅愁模样,装作要看薄暮景色,用手掌抹着玻璃。
姑娘上身微微前倾,聚精会神地守视着躺在面前的男人。她肩膀使劲的样子、眨也不眨的眼睛和带点儿严肃的目光,都显出她的认真来。男人的头靠窗枕着,蜷着腿,放在姑娘身旁。这是三等车厢。他和岛村不是并排,而是在对面一排的另一侧。男人侧卧着,窗玻璃只照到他耳朵那里。
姑娘恰好坐在岛村的斜对面,本来劈面便瞧得见,但是他俩刚上车时,岛村看到姑娘那种冷艳的美,暗自吃了一惊,不由得低头垂目;蓦地瞥见那男人一只青黄的手,紧紧攥着姑娘的手,岛村便觉得不好再去多看。
映在玻璃窗上的男人,目光只及姑娘的胸部,神情安详而宁静。虽然身疲力弱,但疲弱之中流露出一种怡然的情致。他把围巾垫在脑下,再绕到鼻子下面,遮住嘴巴,接着向上包住脸颊,好像一个面罩似的。围巾的一头不时落下来,盖住鼻子。不等他以目示意,姑娘便温存地给他掖好。两人无心地一遍遍重复,岛村在一旁看着都替他们不耐烦。还有,裹着男人两脚的大衣下摆,也不时松开掉下来。姑娘会随即发现,重新给他裹好。这些都显得很自然。此情此景,使人觉得他俩似乎忘却了距离,仿佛要到什么地角天涯去似的。这凄凉的情景,岛村看着倒也不觉得酸楚,宛如在迷梦中看西洋镜似的。这或许因为他所看到的景象,是从奇妙的玻璃上映现出来的缘故。
镜子的衬底,是流动着的黄昏景色,就是说,镜面的映像同镜底的景物,恰似电影上的叠印一般,不断地变换。出场人物与背景之间毫无关联。人物是透明的幻影,背景则是朦胧逝去的日暮野景,两者融合在一起,构成一幅不似人间的象征世界。尤其是姑娘的脸庞上,叠现出寒山灯火的一刹那顷,真是美得无可形容,岛村的心灵都为之震颤。
远山的天空还残留一抹淡淡的晚霞。隔窗眺望,远处的风物依旧轮廓分明,只是色调已经消失殆尽。车过之处,原是一带平淡无趣的寒山,越发显得平淡无趣了。正因为没有什么尚堪寓目的东西,不知怎的,茫然中反倒激起他感情的巨大波澜。无疑是因为姑娘的面庞浮现在窗上的缘故。映出她身姿的那方镜面,虽然挡住了窗外的景物,可是在她轮廓周围,接连不断地闪过黄昏的景色,所以姑娘的面影好似透明一般。那果真是透明的吗?其实是一种错觉。不停地从她面容后疾逝的垂暮景色,仿佛是从前面飞掠过去,快得令人无从辨认。
车厢里灯光昏暗,因为没有反光,窗玻璃自然不及镜子明亮。所以,岛村看着看着,便渐渐忘却玻璃之存在,竟以为姑娘是浮现在流动的暮景之中。
这时,在姑娘脸盘的位置上,亮起一星灯火。镜里的映像亮得不足以盖过窗外这星灯火,窗外的灯火也暗得抹杀不了镜中的映像。灯火从她脸上闪烁而过,却没能将她的面孔照亮。那是远远的一点寒光,在她小小的眸子周围若明若暗地闪亮。当姑娘的星眸同灯火重合叠印的一刹那顷,她的眼珠儿便像美丽撩人的萤火虫,飞舞在向晚的波浪之间。
叶子当然不会知道,自己被别人这么打量。她的心思全放在病人身上。即便她转过头来朝着岛村,也不可能望见自己映在窗玻璃上的身影,恐怕更不会去留意一个眺望窗外的男人。
岛村暗中盯着叶子看了好一会儿,忘了自己的失礼,想必是镜中的暮景有股超乎现实的力量,把他给吸引住了。
刚才叶子喊住站长,真挚的情义盎然有余,也许岛村早在那时就出于好奇,对她产生了兴趣。
车过信号所后,窗外一片漆黑。移动的风景一旦隐没,镜子的魅力也随即消失。尽管叶子那姣好的面庞依然映在窗上,举止仍旧那么温婉,岛村却在她身上发现一种凛然的冷漠,哪怕镜子模糊起来他也懒得去擦了。
然而,事隔半小时之后,出乎意料的是,叶子他们竟和岛村在同一站下了车,他觉得好像要发生什么跟自己有点儿关系的事似的,回过头去看了一眼。但是,一接触到月台上凛冽的寒气,他便顿时为自己方才在火车上的失礼行为而感到羞愧起来,于是头也不回地绕过火车头径自走了。
男人把手搭在叶子肩上,正要走下轨道,这边的站务员急忙举手制止。
不一会儿,从黑暗中驶来长长一列货车,将两人的身影遮住了。
旅馆派来接客人的茶房,身上是全副防寒装束,穿得跟救火的消防员似的,包着耳朵,穿着长筒胶鞋。有个女人也披着蓝斗篷,戴着风帽,从候车室的窗户向铁道那边张望。
火车里的暖气还没从身上完全散掉,岛村尚未真正感到外面的寒意,但他这是初次领略雪国之冬,所以,一见到当地人这副打扮,先自被唬住了。
“难道真冷得非穿成这样子不可吗
“是啊,完全是一身冬装了。雪后放晴的头天晚上,冷得尤其厉害。今晚怕是要到零下了。”
“这就算是零下了吗岛村望着屋檐下怪好玩的冰柱,随着茶房上了汽车。一家家低矮的屋檐,在雪色中显得越发低矮。村里一片岑寂,如同沉在深渊中一般。
“果然如此,不论碰到什么东西,都冷得特别。”
“去年最冷的那天,到零下二十几度呢。”
“雪呢
“雪嘛,一般有七八尺深,下大的时候,怕要超过一丈二三尺吧。”
“哦,这还是刚开头哪
“可不是,刚开头。这场雪是前几天刚下的,积了一尺来厚,已经化掉了不少。”
“竟还能化掉吗
“说不定几时就要下大雪。”
现在是十二月初。
岛村感冒始终不见好,这时塞住的鼻子顿时通了,一直通到脑门,清鼻涕直流,好像要把什么脏东西都冲个干净似的。
“师傅家的姑娘还在不在
“在,在。她也到车站来了,您没瞧见吗?那个披深蓝斗篷的。”
“原来是她?——等会儿能叫到她吧
“今儿晚上吗
“今儿晚上。”
“说是师傅家的少爷今儿晚上就搭这趟末班车回来,她来接他了。”
原来,暮色中,从镜子里看到的那个姑娘照料的病人,竟是岛村前来相会的那个女人家的少爷。
岛村知道这事后,心里不觉一动,可是,对这一因缘时会却并不感到怎么奇怪。他奇怪的,倒是自己居然不觉得奇怪。
凭手指忆念所及的女人和眼睛里亮着灯火的女人,这两者之间,不知怎的,岛村在内心深处总预感到会有点儿什么事,或是要发生点儿什么事似的。难道是自己还没有从暮色苍茫的镜中幻境里清醒过来?那暮景流光,岂不是时光流逝的象征吗?——他无意中这么喃喃自语。
滑雪季节之前,温泉旅馆里客人最少,岛村从室内温泉出来时,整个旅馆已睡得静悄悄的。在陈旧的走廊上,每走一步,便震得玻璃门轻轻作响。在长长的走廊那头,账房的拐角处,一个女人长身玉立,和服的下摆拖在冰冷黑亮的地板上。
一见那衣服下摆,岛村不由得一怔,心想,毕竟还是当了艺伎了。女人既没朝这边走过来,也没屈身表示迎候,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但是远远看去,仍能感到她的一番真情。岛村急忙走过去,默默无言地站在她身旁。她脸上搽了很厚一层白粉,想要向他微笑,反而弄成一副哭相。结果两人谁都没说什么,只是向房间走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