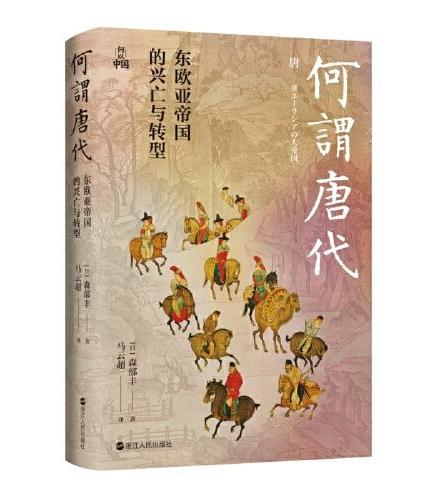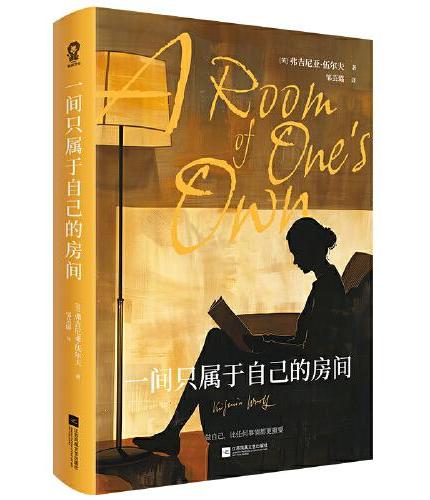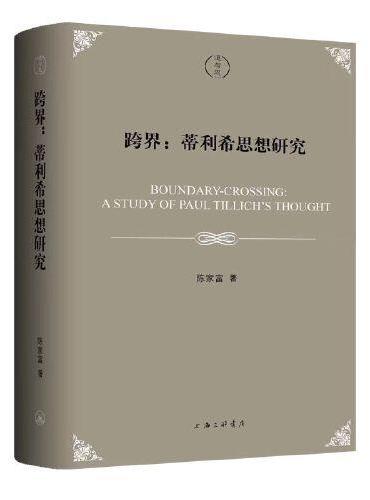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无端欢喜
》
售價:NT$
347.0

《
股票大作手操盘术
》
售價:NT$
2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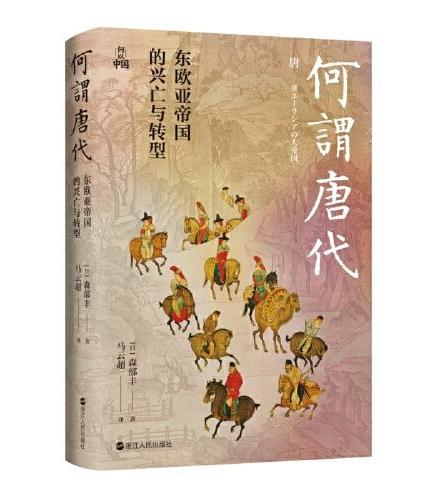
《
何以中国·何谓唐代: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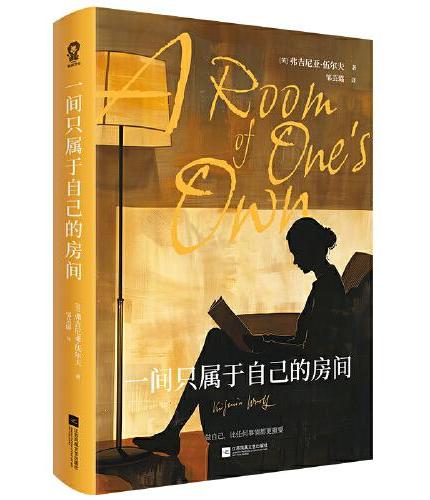
《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代表作 女性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的象征,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
售價:NT$
203.0

《
泉舆日志 幻想世界宝石生物图鉴
》
售價:NT$
611.0

《
养育女孩 : 官方升级版
》
售價:NT$
2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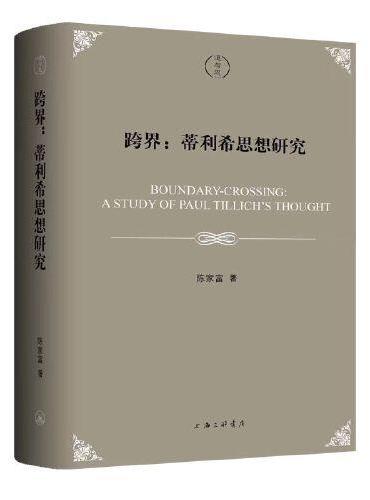
《
跨界:蒂利希思想研究
》
售價:NT$
500.0

《
千万别喝南瓜汤(遵守规则绘本)
》
售價:NT$
203.0
|
| 編輯推薦: |
|
邓一光新作,近八十万言,叩问人性渊薮之力作!一部记叙帝王时代结束后国人成长密码的史诗作品,一部勘探国民精神萌芽时民族凝聚原点的鸿篇巨制!邓一光的写作重新审视了人类与生俱来的荣耀和弱点,捍卫了人类的恐惧权利,捍卫了弥足珍贵的个人立场,尊严地活着,也要知道为什么而活!展现出一位小说家深厚的人文关怀。邓一光考据史料,非虚构与虚构笔法相结合,勾陈史实,宏大磅礴,既可以看见张爱玲、萧红等人的香港生活印迹,又可以看到主人公的内心挣扎、犹疑,我们对他多了解一分,我们对自己,对人的状况、限度与可能就多了解一分。小说出版后,入选《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佳作、“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奖、阅文 ? 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2019 十大好书”等十数种文学专业榜单,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
|
| 內容簡介: |
在这本小说中,邓一光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讲叙了中国现代史中早期知识分子与民族、国家和世界命运同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主人公郁漱石在国民觉醒时期以少年之身赴日本和美国留学,在民族危亡时刻以青年之身归国抗战,在全球反法西斯战场的香港保卫战中,率小组与敌寇作战,因被俘身陷囹圄,经历了三年数个月的非人折磨,又以直面恐惧与软弱的勇敢逃出战俘营,寻找同样陷入战争囚笼的恋人,参加了香港战后重建工作,由此度过了短暂的一生……
邓一光说:“恐惧是值得被捍卫的,正因为有人类原生的恐惧,人才不会沦为野蛮的杀戮机器,希望才能够得以留存。”邓一光的写作重新审视了人类与生俱来的荣耀和弱点,捍卫了人类的恐惧权利,捍卫了弥足珍贵的个人立场,展现出一位小说家深厚的人文关怀。
小说出版后,入选《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佳作、“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奖、阅文 ? 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2019 十大好书”等十数种文学专业榜单,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
|
| 關於作者: |
邓一光,男,1956年生于重庆,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文学院院长,2009年以高级人才身份引入深圳,从事专业创作。著有长篇小说《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家在三峡》等10部,中短篇小说集《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深圳蓝》等20多部,影视剧本若干,有长、中、短篇小说以英、法、德、俄、日、蒙、韩等多种文字译介到海外。
小说作品曾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冯牧文学奖、首届郭沫若散文奖、首届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作家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三届郁达夫文学奖等数十项重要文学奖项;作品两度入选当代文学年度长篇小说榜、两度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小说榜、两度入选全国城市文学排行榜、两度入选收获文学年度小说榜、两度获得十月文学奖、三度获得人民文学奖、三度获得《小说选刊》奖、三度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优秀作品奖,并获得《当代》年度长篇奖、《作家》金短篇小说奖、《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长江文艺》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上海市长中篇小说大奖,入选《亞洲週刊》全球华人十大中文小说榜、《扬子江评论》年度长篇榜、《长篇小说选刊》年度金奖等重要文学榜单。
|
| 目錄:
|
目录
第一部/00
一法庭陈述:我应该活着/00
二法庭调查及其他:被告没有在内地任何战场上作过战/0
第二部/0
三法庭陈述及其他:他和同伴充满幸福的聚集地/0
四法庭外调查:没有过去和未来,只有地狱般的现在/
五法庭外供述及其他:我愿意接受诅咒,永世不再变成人/
六法庭举证及其他:哔啵,一个气泡破裂了/
第三部/
七法庭外调查及其他:陆军省俘虏情报局的冈崎小姬/
八法庭外调查:他们向英国人和美国人宣战了!/
九法庭调查及其他:我有足够的理由退出战争/
十法庭外调查:我身边那些尸首,他们会不会突然坐起来/
第四部/
十一法庭外调查:摆脱麻木的最好办法就是找死/
十二法庭外调查:炖猪肉、烤鱼和青菜酱汤,超过四盎司
大麦饭/
十三法庭外陈述:我唯一的喜悦和幸福,就是我的男人/
十四法庭外调查:我身处两座战俘营中/
第五部/
十五法庭外调查:卑鄙是会传染的,而且它会上瘾/
十六法庭外调查及其他:我被自己出卖了/
十七法庭外调查:死亡有很多方法,活下去只有一种/
十八法庭外调查:影子武士后代,影子武士后代/
十九法庭外调查:不管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人们总要结婚/
第六部/
二十法庭外调查:我只选择一种方式活下去/
二十一法庭外调查:君不见樱花明日落尘埃,倾尽全力
瞬间开/
二十二法庭外调查:那一刻我相信,我们如同至亲骨肉,可以在
彼此的眸子中看到自己过去的样子/
第七部/
二十三法庭外调查:如露之临,如露之逝/
二十四法庭陈述及其他:“抬头,看上面!”/
二十五结案报告和遗书:妈妈,我坚持不下去了/
本书参考资料/
|
| 內容試閱:
|
张英:您是如何想到写《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作品的?
邓一光:写完《我是我的神》后就想写一个角度小点的故事,关注人性中另外一些侧面,比如一些脆弱和隐秘的内容,想知道它们在故事中会呈现出怎样的光芒,当时特别质疑之前那种恣意汪洋的写作。我自己总结,想写人的小,而不是大。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中的一些在失去,一些潜流是重要的,却因生命在高峰期的轻谩而忽略了,一些微微的生命内容,也被我忽略了,想找回来。后来慢慢地,发现失去的不是真失去,是被限制住了,囚禁住了,想写一个限制者或囚禁者的故事。
张英:为什么是囚禁?这个题材不多见。
邓一光:作为个体生命,特别微弱无力,在他一生中,很多愿景和行动力被囚禁住了。比如我是农民,或是工人,一生在田里干活,在工厂工作,其实我有很多和稼穑、和机器不一样的念头,但我被生计和职业囚禁住了,我的行动不属于我自己,我被囚禁在一个地方。再比如,我有很多愿望想去做,想把自己敞开,去拥抱世界,我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想要改变,成为另外的样子。可我不可能那样做,我被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更主要是主体的格式化,被思想和精神限制住,被无知、文明、秩序……囚禁住,那样的我是分裂的。我为这个题材着迷,我认为人最终是要从人性中找到和自我对话的窗口,当时就想写这么一个故事。
张英:您选择这个题材,写作之前都做了哪些工作,如何落实您的想法?
邓一光:首先要找形式上的囚禁,比如从原始部落开始,一直到现代社会的各种秩序,比如限制和剥夺人自由、尊严,甚至生命的手段,比如监狱。这个故事的场景也可以放到现代或未来,以日常生活为背景,写进一个大企业,写在一个自由人身上,写现实中不存在的世界,都可以,但我后来觉得,把故事放在非常态环境中,可能更有表现力。
张英:这个非常态环境就是太平洋战争中的香港。
邓一光:故事酝酿阶段,选择过几个历史环境,也考虑过当下,但特别不好找落地点。此前也知道香港在1941年到1945年被日本侵占时的一些情况,那会儿没引起注意,移居深圳后,和香港一河之隔,有时过去走一走,逛逛书店,看几场戏,接触了一些人,很多气息扑面而来,于是开始收集资料,做些田野考察,它们让我渐渐产生出兴趣。
张英:能具体说说是什么让您选择这个写作背景?
邓一光:首先,香港战役在太平洋战争中几乎没什么战略价值,唯一说得上的价值,是日本知识界复兴派鼓吹亚洲论和世界强国论,让日本陆海军出奇地达成一致,选择在占领香港的方式上,用武力打败老牌帝国英国,这让香港成为太平洋战争中第一座被攻打下来的城市。每座城市都有它的光荣史和屈辱史,香港1842年起被英军占领,1941年又成为日本占领地,1945年英国人再回到香港,重新夺得殖民权益,换言之,香港是三度被殖民,而殖民是一种文明改造和囚禁。那个年代香港人口最多时有160万华人,1946年时是60多万华人,这么多华人,在香港却没身份,他们的身份被囚禁在殖民管理机制和占领地文化的浸润中了。而香港战役造成了日后亚太地区政治态势的改变,也在香港的城市屈辱史上抹上了一道战争血痕,形成了香港人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文化记忆,甚至形成了部分香港的城格和香港人的文化人格。
其次,我去查这段历史资料时,发现可以接触到的非常少,英国政府没对这场战役做出整体交代,日本也没。日本直到1975年,才由防卫厅出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重点在长沙作战,战略上要打通大陆线,从部署上能看出,打香港只用了一个师团的部分兵力、一支舰队和少量的空军,和长沙作战完全不一样。至于国民政府,留下的只是些行文模糊的总结,我看到了第七战区战役总结,只有几千字,连史料条件都不具备。我很吃惊,太平洋战争第一个被攻下的城市,这么重要的政治意味、战略价值和战争标志,记录怎么会这么少?参战国各方为什么不总结,却都采取了沉默方式?即使在战前和战争中,基于战略考虑撒了很多的谎,战后为什么不反省?这个选择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意识形态考量的。比如为什么日本陆海军高层坚决要先打下香港,而不是先打下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后,香港不攻自破。攻打香港的日军三十八师团也伤了元气,再战瓜达尔卡纳尔岛,被盟军打废了,以后再没参战能力,最后连建制也被解除了。我问了很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军事学家,日本陆海军高层为什么要选择攻打香港?没人能清晰地回答。我当时就觉得,这场战争的理由没出处,不是没人知道,是知道的人不说,它被囚禁在什么地方了。
张英:当时有个“文化大营救”,茅盾、邹韬奋、夏衍、梁漱溟、蔡楚生、张友渔、胡绳、戈宝权等文化名人,以及上千名进步学生被营救出香港。其中有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部长级官员,很多人成为了文化、文学艺术、教育、新闻等领域的栋梁。
邓一光:如果这些人没被营救出来,他们的命运会完全不一样,很可能中华文明的进程都会换个面目。这场战争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对香港还是对内地都非常大。如今一说张爱玲、萧红大家都知道,她们最好的作品或是在香港写下的,或记录了香港战时生活,可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这段历史?这样一步一步走进这段历史,我决定用它做背景写这个故事。
张英:看到《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名字时,我在想,这本书是否把您的文学理念做了个全面总结:首先是人,其次是所有的士兵?
邓一光:说到底,正是因为人对自己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确定性困惑、不满足和不放弃的执念,才有了虚构化的文学性表达。书定稿时,有人给我提建议,说书名拗口,应改个容易辨识的,就叫《士兵或所有的人》。我没同意,写这本书时,名字只有一个:人。我要从符号化回到生命本体。先不说主人公,说张爱玲、萧红,这些在故事中出现的人物,当时中国刚刚摆脱帝王统治走向共和,军阀混战,国运坎坷,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个体生命在其间不断挣扎,他们都是永恒少年。所以,一定要从个体生命开始,至于他是不是士兵不重要,叫《人,或所有的平民》《人,或所有的工人》《人,或所有的农民》都可以,人不能易位。
邓一光:故事中写到200多位历史人物,主要人物是虚构的。
张英:你把整个故事放在法庭庭审和庭外调查这样一个闭环结构中讲述,为什么?
邓一光:法庭结构是一种限制形式,让故事在“囚禁”中讲述。
张英:你又写了一个从开放社会到战俘营的多国人相处的结构,好几个讲述者他们背景不同,什么样的人都有,为什么这样设置?
邓一光:个体与群体既有交互也有冲突,这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状况,战争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总和的冲突,在不可调和时导致的结果,囚禁是其中一个环节。太平洋战争前,香港已是重要的东亚港口城市,160万人口主要是两广和福建籍为主的华人,但权力在数千到上万名欧洲和美洲人手上,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由他们体现,冲突的主导也是,后来一些上海和重庆的华人去了,声音多了一些,不过华人仍是利益边缘体。更大范围的冲突,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冲突和交互换了一个场合,换到一个肉身的日常生活被囚禁,尊严、精神和自由被剥夺的战俘营里,主导者成了东亚国家,这个东亚国家不但对西方有复杂的情感和利益诉求,对亚洲,包括同在东亚的中国也有复杂情感和利益诉求,那么多文化观、民族观、历史观在被充分限制的体系里共存。这种异质性的存在,需要一个适合讲述的结构。
张英:布局挺有意思,您把香港战役的外部空间扩充了。
邓一光:题材决定的。
张英:这种结构意识落实在写作上,有难度吗?
邓一光:技术上没有,历史现场上有。当事各方都选择沉默,资料获取非常困难。我在处理资料时也有障碍,不懂英语和日语,只能支付翻译费,找学生和儿子帮忙,这个工作用了几年时间,最后还是觉得这一块的历史是坍塌的,很难把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拼接起来,更别说还原故事的现场真相。
张英:您说战争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总和的冲撞,在不可调和后导致的结果,能更详细地谈谈吗?
邓一光:意识形态是人类现有手段的最终目的,不同民族、国家、团体都可能引发意识形态对立,不管哪种目的,政治的、经济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到最后,冲突到不可协调时,作为终极手段,只能用战争来解决。而战争也随科技进步不断发生战争介质的改变,到两次世界战争,杀伤性和破坏性越来越大,当然战争也有另外的观察视角,比如战争推动历史进步,但不是这本书要讨论的。
张英:从开阔的角度讲,战争仅仅出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吗?暴力手段在个体之间有没有?
邓一光:暴力是人的本性之一,战争条件在人性中自然存在,天生就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战争满足于人的高级欲望,而初级形态的暴力满足于人的初级愿望,一方面,人们想遏制战争,制止战争,另一方面人们做不到这点,更大的需求不断滋生出对战争动因、权力和结果的欲望。这是个巨大的悲哀。
张英:这个看法很有意思,近一两百年发生的战争似乎都与人性中对战争的欲望有关。
邓一光:比这个更早,2300年前苏美尔地区的城邦国家,他们实行的是公民兵制,《吉尔伽美什与阿伽》中记载,基什国王要打埃勒克国,埃勒克国长老会说我们投降,民众说谁要投降,我们打,结果全国的人都自愿跑去打仗,国王和长老会并没强迫他们。早期人类使用的工具是石头和棍棒,比较奢侈的是兽骨,它们的作用是不加区分的,寻找和种植食物、建立栖身地、争夺配偶、征服其他人。古希腊文学大量故事讲的是人性暴力源头,哲学家早看到人性的这一逆根性产生的机制,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找到一种方式,能真正遏制自己心中的暴力欲望和冲动。
张英:包括甘地、曼德拉,还有哈维尔,他们知道生命的价值,不赞成用暴力对暴力,用黑暗对黑暗。
邓一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看到自己天性中的黑暗、内心的阴影,主动加以约束。哈维尔在《公民自由权运动宣言》和公民论坛中,从公共场合批评该怎么谈话入手,建立公共冲突的准则,用以约束暴力在无序交流中的升级。暴力则不同,升级为战争更不同,战争是恶性发展自己的能力,推动野心和愿望,无视人类良性竞争原则的行为。
张英:就像甘地,提出最普遍的要求,反抗,但不是和军队对抗,不是进行战争,而是从每个人开始,说真话,用和平的方式抗议,形成一种洪流,显示你力量的存在,慢慢地推进。
邓一光:和平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是伟大的,作为一种力量则非常微弱,但它的精神是了不起的。这样的文明精神在种族中一代代积累,力量会越来越大,会将抑制暴力的愿望转化为人类共识。我的主人公对战争有质疑,他没有理论依据,困惑于生命遗传中的两难,同时被生命史中的审美感动,甚至战俘营管理者在要杀死他时,被毒蛇咬伤了,他也去救施害者,用最后一点力量把毒液吸出来。有位批评者说,他不能接受这样的行为。我回答他,从道德层面我也不能接受,但你没看到他那样做也是反抗,比你我更接近人应当有的尊严。
张英:是的,虽然很少。
邓一光:太少了,所以才要写。
一
法庭陈述:我应该活着(GYB006—B—191)被告郁漱石法庭自辩记录:
谢谢法庭给我辩护的机会。
我猜,在法庭最终决定我命运之前,或者说,在你们把绞索套上我的脖子之前,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
我要说,我没有什么可辩护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辩护,为什么站在这儿接受审判。
你们指控我在中日战争期间犯下通敌叛国罪,请告诉我,你们怎么界定中日两国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从哪里开始算?同治十三年1874年5月,日本入侵台湾,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专条》,承认琉球为日本保护国,赔偿白银50万两。?光绪二十年1894年7月至次年2月,日本进攻驻朝鲜清军,攻占辽东半岛,消灭清朝北洋舰队,迫使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和《中日辽南条约》,史称“甲午战争”或“清日战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日军攻陷天津、旅顺、奉天,携11国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并单独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北四省事宜条约》,获得在中国东北南部特权。?民国三年1914年8月,日军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全线,携英军攻占青岛,迫使袁世凯政府接受《日华条约》。?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至次年10月,日军进攻青岛,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制造“五三”惨案。?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在随后3个月内占领东北全境。?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被迫签署《上海停战协定》,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3月9日,日本挟持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成立“满洲国”,并先后攻占济南、热河、察哈尔及河北大部,进逼平、津,迫使国民政府签署《塘沽协定》。?还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攻打中国守军,随后攻占平、津,11月攻占上海,12月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宣布全国抗战。?不,你们从来没有说清楚过,害怕说清楚。你们说不清楚中日间的战争自何时起,说不清楚近百年来中日间的冲突哪些算战争,哪些行为应该被计入战争罪,哪些罪行应该由国家承担,由担任政府决策者和最高领袖的人来负责,你们在这些事情上语焉不详,在国家责任上闪烁其词,又怎么能够合法地执行生杀予夺大权,指控我这个低级军官对中日间的战争负责?我若不明白这个,怎么交代“罪行”?
战争的发动者宣布终战了,施加者交出了佩刀,你们不在乎终战与投降的关系,只在乎终于熬过了“这一场”战争。“很好”,你们说。你们想尽早结束眼前的一切,去忙别的。那是另一场战争,对手换成了中国人,对吗?
一个国家经历了七十一年战争,有多少肮脏的内幕,多少人的死亡和耻辱,还不够?
总之,你们是“这一场”战争的胜利者,有足够的理由利用审判这种合法方式好好享用战胜者的权利,以缓解七十一年财殚力痡的国家间战争留下的创痛,消解七十一年佛头着粪的耻辱,为下一场战争歃血以誓。看起来这很合理。可是,上百万渡过中国海登上中国大陆烧杀掠抢的战争施加者,他们呢?你们为什么要把他们匆匆送走,你们害怕什么?
我不属于胜利者一方。
我只想活着,不要被人蒙上脑袋,拉上绞刑架,脖颈套上发硬的绳索,启动暗仓,像一枚风干的果子坠落进长长的暗道。
就是说,我们都不希望结束得太快。
好吧,我愿意配合你们,至少我可以学学山鲁佐德,而尊敬的法官和军法官先生们,你们就是山努亚和萨曼,我们来玩一个讲故事的游戏,看看我能在死神面前做些什么,熬过多长时间。
现在,让我们从头开始。
你们说,你们有确凿“证据”,证明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燊岛丛林中发生过一场激烈攻击,致使中国派遣军1939年,日军大本营发布“大陆令”362号,向中国派出遣华军,首任司令官西尾寿造,末任司令官冈村宁次。D战俘营毁于爆炸和大火,那是美国人的轰炸造成的——日治期间,英国政府支持盟军轰炸日占区香港,国民政府也支持轰炸日占区华南,美国人的“米切尔”“解放者”“入侵者”和“复仇者”反复向情报提供的目标俯冲投弹,空袭导致了大量误炸伤亡,比如红磡小学事件,正在上课的学生来不及躲避开呼啸而来的航空炸弹,一百多名孩子当场被炸死。既然如此,当第14陆军航空队的纳尔·克尔中尉率领的10架B—25轰炸机在万米高空发现了隐藏在燊岛原始丛林中的D战俘营,并且把战俘营操场上用石灰画出的矩线当作日军隐藏在丛林中的零式飞机跑道,克尔中尉下令“消灭小鬼子的苍蝇”,4架B—25轰炸机打开投弹仓,投下5吨炸弹,几百名战俘连同D战俘营消失在火海中,就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件了。
你们告诉我,美国陆军情报局A.莫斯特上尉奉命调查民国三十四年在香港大轰炸中因坠机被俘的13名美军机师的下落,他是战后最早进入华南的美国军官,他向上司提供了一份D战俘营毁于盟军误炸的报告,报告根据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作战日志、日军香港防卫司令部空袭预警日志和日军荒木胜利支队战俘审讯记录,证明造成D战俘营被炸结果是空中观察误判引起。莫斯特上尉从香港战俘总营的文件中查到了由D战俘营第131号战俘设计的《战俘体育运动项目报告》,莫斯特上尉的助手在D战俘营废墟中找到残存的贝壳石灰和一些简易体育用具,以上证据证明误炸这一说法是可信的。而这一切,应该由造成这场可悲事件的相关人员负责,就是说,由那个设计了D战俘营《战俘体育运动项目报告》并亲自用贝壳石灰在战俘营中画出21道白色矩线的第131号战俘负责。
看上去,这个推断很合理。
我就是D战俘营第131号战俘,那个似乎应该对这场造成数百名战俘死亡事件负责的人。
我能说什么?你们想听到什么?你们希望我为什么做证?
我不知道你们为何拒绝接受D战俘营毁于日方“消灭痕迹”预谋的事实,为什么不承认那是一场计划中的屠杀,为什么要在日本宣布终战10个月之后,把D战俘营日方管理者匆匆送回日本。他们是屠杀事件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他们应该告诉你们,在燊岛原始森林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们怕什么?有什么事情会被揭穿,需要遮掩?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什么是事实。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燊岛上的大屠杀开始了,它从下午5点09分开始,整整持续了3小时。屠杀者用去的时间比这个更长,如果算上刽子手们离开燊岛之前对奄奄一息濒死者的补杀,以及焚烧小山般的战俘尸体用去的时间,屠杀应该超过72小时。
126名英国战俘,133名加拿大战俘,17名印度战俘、4名荷兰战俘、3名意大利战俘和1名菲律宾战俘在大屠杀中被日本人处心积虑的预谋和盟军趾高气扬的航空炸弹合谋杀害。死者中部分人遭到航空炸弹的弹片和烈焰的攻击,因为营养不良和窒息失去所剩无几的逃生机会,剩下的大多数人在冲向铁丝网的逃亡途中被藏匿在丛林中的机枪子弹击中。死亡群体中人数最多的来自中国,总共有682名中国战俘在屠杀中死去,包括几名年仅十几岁,在D战俘营关满三年的未成年战俘。
重复我刚才的话,凶手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和美国陆军空军。
大屠杀开始的时候,我在离现场1公里远的海边坡地上。D战俘营就在我脚下。我亲眼目睹了屠杀。
那真是一个奇怪的场景。太阳正在落入林梢,盟军空军编队从东北方向飞来,它们的目标是燊岛西南的香港。我听见95式重型机枪的声音,它们从D战俘营西北方向的森林中传来,短促的连发,大约三次。子弹射向空中,目标是从天空中飞过的盟军轰炸机编队。这是以指挠沸的公然冒犯,对吗?已经飞过头顶的轰炸机编队中,4架B—25米切尔轰炸机从西北方向折返回来,向燊岛俯冲。至少20枚200公斤重量的航空炸弹落下,数枚炸弹准确落在营区中,大火立刻燃烧起来,营房快速坍塌,到处都是抽搐和扭动的战俘。我看见一些战俘从一排排倒下的营房中惊慌地窜出,在弹片和硝烟中爬动,他们不甘地翘起消瘦的肩膀和佝偻的背,挣扎着被火焰吞噬掉。米切尔轰炸机上的05英寸机枪响了,战俘们的胸膛和颌骨像夏天最后晚霞中的花卉一样争相绽开,成片倒下,任由随后追上来的大火烧成焦炭。我还是看到了愤怒,大量的愤怒。那些国民政府第7战区的士兵和英联邦军队的士兵们,他们即使在中弹之后也骂骂咧咧,顽强地从地上爬起来,手里攥着一块发臭的布片或者被机枪子弹切断的同伴的手掌,试图躲开从森林中不断飞来咝咝喷涌着黄烟的瓦斯罐以及伏击者发射出的榴弹和机枪子弹,徒劳无功地跌落回地上。
这不是我的错。
我在屠杀现场,但我活下来了,看上去比那些大汗淋漓的屠杀者还要完整,这不是我的错。
我不是唯一侥幸存活下来的D战俘营战俘。还有一支游击队——他们曾经是D战俘营的战俘,一共63人,在屠杀日的前20天,他们从东区21号宿舍下那条奇迹般的地道中成功地逃出战俘营。请原谅,是61人,有两人在逃亡前留了下来。逃出D战俘营的61人中,1名掉进海中溺死,1名在路上病死,1名因不明原因在海上被同伴杀死,剩下58人。他们在登上惠州海岸时,慎重地做出将会返回燊岛拯救留在D战俘营的兄弟的决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兑现了承诺,是否返回过燊岛,但显然,就算他们返回燊岛也来不及了。
先生们,你们知道这些事情,对吗?你们中间的每个人都知道,燊岛上的大屠杀它真实地发生过,你们手中有一份秘密档案,证实它的确存在。与其说第14航空队的轰炸帮助了日本人,不如说它就是日本人“消灭痕迹”计划中的一部分。多么有趣的配合啊,一支耀武扬威的轰炸机队,规模庞大的杀人武器库,它们飞抵头顶,只需要按照计划向机群轻轻扣动机枪扳机,三次,或者再多一次,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D战俘营被大火烧成灰烬,在几场大雨之后恢复成更早时期的清代兵营废墟,人们无法辨认南方茂密的雨林植被中曾经存在的D战俘营,它消失了,不见了。但你们知道,那场屠杀,它的确存在。
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你们帮助真正的刽子手销声匿迹,是害怕仇恨无休止地蔓延下去,还是对战争的认真清理将耽搁你们去进行另一场战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关于这场大屠杀,你们指认的被告不是犯下战争罪和杀人罪的组织和集团,不是中国派遣军和第14航空队中的任何人,而是一名中国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