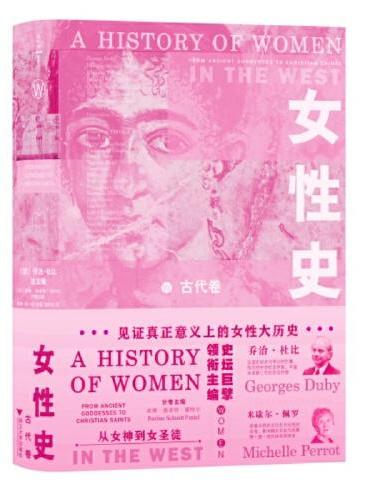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成吉思汗传:看历代帝王将相谋略 修炼安身成事之根本
》
售價:NT$
280.0

《
爱丁堡古罗马史-罗马城的起源和共和国的崛起
》
售價:NT$
349.0

《
人生解忧:佛学入门四十讲
》
售價:NT$
490.0

《
浪潮将至
》
售價:NT$
395.0

《
在虚无时代:与马克斯·韦伯共同思考
》
售價:NT$
260.0

《
日内交易与波段交易的资金风险管理
》
售價:NT$
390.0

《
自然信息图:一目了然的万物奇观
》
售價:NT$
6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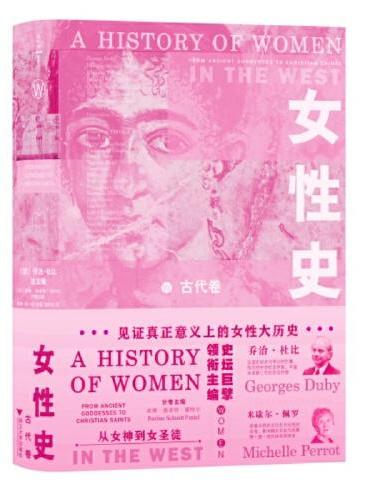
《
女性史:古代卷(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大历史)
》
售價:NT$
560.0
|
| 編輯推薦: |
|
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得主,知名翻译家、作家、评论家黄昱宁全新文学评论集,一名专业读者的倾心之作,彰显了其在文学评论上的智识与野心。如她所说:“在我个人的写作生涯中,还从来没有哪一次结集耗时如此之长,改写幅度如此之大,但是过程又是如此之快乐的。”细节是一道光,照亮文学的密林。如作者所说,本书这些文字,由始至终,都从细节中来,往细节中去。若干年后,故事会淡忘,人物关系会误植,文本意图会模糊,唯有那些无法磨灭的细节——伊丽莎白的马车或者基督山伯爵的小刀——在记忆的暗处,熠熠闪光。以文本细读为方法,精彩解读从简·奥斯丁到石黑一雄的二十多位世界文学大家的作品,深度挖掘小说家讲好故事的秘诀。二十六篇文章,上百个小说细节以及被这些细节激发的文字,就构成了这本四百多页的文集。作者对小说的细致分析和深入解读,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引领和指导,能帮助读者更深刻地领悟小说的魅力。黄昱宁集小说家、翻译家、评论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为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和可能性。她以译者的天然优势(翻译过阿加莎·克里斯蒂、麦克尤恩、亨利·詹姆斯、菲茨杰拉德、库切等),兼以写作者的亲身体悟和评论家的敏锐透彻,以无厚入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部文学评论集,聚焦二十余位世界级知名作家,其中既有简·奥斯丁、大仲马、福楼拜、狄更斯这样的经典作家,也有加缪、菲茨杰拉德、纳博科夫、菲利普·罗斯、多丽丝·莱辛、艾丽丝·门罗、石黑一雄、托卡尔丘克、麦克尤恩这样的现当代文学大家。
黄昱宁正是这些小说家所期待的理想读者,她秉持传统的细读方法,却不落窠臼,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别具一格的审美发掘小说细节的灵光闪耀之处,向读者揭示小说艺术的魅力。她的这些文字,自始至终,都从细节中来,往细节中去。
同时,在本书中,她又是一位极好的文学阅读领路人,以译者的天然优势、写作者的亲身体悟和评论家的敏锐透彻,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文学与现实、小说与评论之间。其细腻的感知、独到的见解、切中肯綮的分析,如一个个通往文学密林的路标,引领读者进入深幽的文学世界。
|
| 關於作者: |
|
黄昱宁,生于上海,横跨翻译、出版、创作三界的全能型作者。翻译过F.S.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阿加莎·克里斯蒂、伊恩·麦克尤恩等多位知名作家的作品。著有小说集《八部半》,随笔评论集《一个人的城堡》《梦见舒伯特的狗》《阴性阅读,阳性写作》《变形记》《假作真时》等。2019年,其首部小说集《八部半》获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
|
| 目錄:
|
i 序言
001 简·奥斯丁:预祝天气变坏
017 艾米莉·勃朗特:纳莉的眼睛
037 大仲马:纸团,小刀与坟场
052 福楼拜:两难
065 欧·亨利:故事从圣诞节开始
081 亨利·詹姆斯:地毯上的花纹
100 伍尔夫:一个女人想买花
117 菲茨杰拉德:度量盖茨比
129 纳博科夫:杀人犯总能写出好文章
144 多丽丝·莱辛:南非的爱玛
164 艾丽丝·门罗:人造丝与白孔雀
180 阿特伍德:走过岔路口
195 加缪:第二遍铃声,以及黄昏的囚车
211 库切:逆行的鲁滨孙
224 莫拉维亚:自我的碎片
240 达里奥·福:闹剧的古典光泽
255 菲利普·罗斯:野蛮的玩笑
271 伊恩·麦克尤恩:十三个细节
290 希拉里·曼特尔:猎鹰的眼睛
306 托卡尔丘克:时间无所不能
321 石黑一雄:迷雾与微光
339 查尔斯·狄更斯 vs.萨莉·鲁尼:从上等人到正常人
355 麦克尤恩 vs.石黑一雄:克拉拉这样的机器
367 歇斯底里简史
391 戴维·洛奇访谈:“我似乎听说过《围城》”
409 麦克尤恩讲述麦克尤恩
427 附录
|
| 內容試閱:
|
《小说的细节·序言》
那些随手在小说里夹入的书签,在手机备忘录上做的笔记,在电脑中摘录的片段,那些在一篇书评谋篇布局时先用来“定位”的关键词,那些限于篇幅无法见诸正文的“边角料”,是这本书真正的起点。当这些碎片集中在一起,呈现出一定的规模时,方法本身也呈现出某种趣味。很多情况下,它们就像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有意无意撒下的路标。沿着这些标记逆向而行,当时的思考路径渐渐在回忆中重现。顺着这条路,我最终回到文本,回到那些曾经刺激我动笔的段落和句子里。
这其实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文本细读似乎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方法,因而我们现在常常读到的是另一种:有趣,游离甚至独立于文本之外,弦外之音远比题中之义用了更多力气——或许我自己也写过。有时候,把评论与评论的对象放在一起看,我们读到的是奇特的落差、动人的误解,以及方向偏转时产生的类似于折射的奇妙效果。只不过,我能确定的是,在这一本集子里,我想暂时排除这样的作品。
收入这本小书的篇目,大多与我近年写过的外国小说评论有关,但几乎全都经过了重新编排和改写。我选择其中与小说细节有关的内容加以扩充,再把那些原本只留在笔记中的词语一个个打捞出来,归拢,黏合,抛光。然后,我在小说中寻找相应的段落,摘几句出来,与评论放置在一起,形成对照。我希望这样的对照有实在的意义。如果说,评论是对原文的咀嚼与反刍,那么原文对评论也构成了某种无声的审视与追问。阅读的多重意义,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得以延伸。
另有少量篇目,在结构上与前者略有差别。比如写《包法利夫人》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旧文,再比如那篇名叫《歇斯底里简史》的新作,以及与两位英国文学大师的对谈,都没有偏离“文本细读”的主旨。这些文字,由始至终,都从细节中来,往细节中去。
如是,二十六篇文章,上百个小说细节以及被这些细节激发的文字,就构成了这本四百多页的文集。在我个人的写作生涯中,还从来没有哪一次结集耗时如此之长,改写幅度如此之大,但是过程又是如此之快乐的。没有什么深邃的命题(文学之奥义,小说技术之演进,写作之于人生)——即便有,也隐没在昏暗背景中,等待被细节的光芒照亮。这就像我们对于小说的记忆:若干年后,故事会淡忘,人物关系会误植,文本意图会模糊,唯有那些无法磨灭的细节——伊丽莎白的马车或者基督山伯爵的小刀——在记忆的暗处,熠熠闪光。
黄昱宁
二〇二二年二月
《简·奥斯丁:预祝天气变坏》(节选)
黄昱宁
他放低了声音,“我已经说过,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永远也不会一致。也许,任何男人和女人也都不会的。不过,请允许我指出,种种史实都说女人不好;所有的故事、散文和诗歌都是如此。要是我有本威克那样的记忆力,我马上就可以引出五十条论据来证明我的观点。我觉得,我一生中很少看过有哪一本书不讲到女人是反复无常的。歌词和谚语都说女人水性杨花。不过,你也许会说,这些都是男人写的”。
“也许我会这样说的。是的,是的,请你不要从书本中找例子了。男人在叙述他们的奇闻轶事方面比我们强多了。他们受的教育比我们多,笔杆子握在他们手里。我认为书本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劝导》第十一章
“哦!就一本小说!”年轻的小姐一面答话,一面放下手中的书,装作没事儿似的,或者一时表现出不好意思的样子。“不过是《塞西丽亚》,或《卡米拉》或《比琳达》罢了”;或者简而言之,只不过是一部表现了思想的巨大力量的作品,一部用最贴切的语言,向世人传达对人性的最彻底的认识、并对人性的种种表现作最恰当的刻画,传达洋溢着最生动的才智与幽默的作品。相反,假如同一个年轻小姐是在阅读一卷《旁观者》,而不是在看一部这样的作品,她便会非常自豪地展示这本杂志,说出它的名称!尽管她肯定不可能被那本大部头刊物里的什么文章所吸引,但这刊物无论内容还是风格亦都不会使一个具有高尚情趣的年轻人感到厌恶:这个刊物上的文章常常是陈述荒谬的事情、别扭的人物以及活人不再关心的话题;而语言也常常粗糙得使人对容忍这种语言的那个年代不会有很好的看法。
——《诺桑觉寺》第五章
重读奥斯丁,记下了这两段与情节主线并没有多大关系的闲笔。就像是写累了,突然借着人物的口吐个槽,浇胸中郁积已久的块垒——小说家都有这样难得的放飞自我的时刻。无论是叙事权的性别之争——“笔杆子握在男人手里”(请注意上文,这里指的是“歌词或谚语”,而不是小说),还是年轻小姐对于小说的矛盾态度,都需要做一点时代注解才能领会奥斯丁的深意。
那时的英国,“小说”这种题材还处于青春期,虽然前面有斯威夫特、笛福和菲尔丁开道,但是它还登不上大雅之堂,在文学的整个生态系统里还处在相对底层的地位。后人一般把那一段称为浪漫主义时期,可是当时台面上主打的基本上都是华兹华斯那样的诗人。那时的小说家有点像我们这个时代网络小说草创时期的样子,海量的作品,强大的流传度,作者虽然能获得一些实际收益,但作家地位基本上处在“妾身未分明”的状态。更有尊严更有追求的男作家、男读者往往羞于混迹其中,这就促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读小说的是女人,写小说的也往往是女人。引文中提“《塞西丽亚》,或《卡米拉》或《比琳达》”全都是这一类作品。
奥斯丁时代最流行的小说通常比较狗血,简小姐肯定在很多哥特小说里读到闹鬼的城堡,或者在感伤小说里遭遇千篇一律的脆弱女性的形象,她们总是眼泪汪汪,动不动就要昏过去。日常生活里是不是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有没有可能比古墓荒野、比传奇故事更有趣?这样的问题,简小姐也许在昏暗的烛光下翻来覆去想过很多回。实际上,当奥斯丁决定要突破套路、写点不一样的东西时,她就真正地改变了文学史。因为后来的评论家发现,如果没有她的推陈出新,那段时间就拿不出一个像样的名字、一部像样的作品可以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深藏在闺阁之中的老姑娘简·奥斯丁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个案。这种情况跟后来集群式轰炸的19世纪大不相同。奥斯丁所有的作品都是匿名发表,所有的文坛声誉都来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的追认。她几乎是单枪匹马、悄无声息地填上了这个空白。
* * *
“我可以乘着车子去吗?”吉英问。“不行,亲爱的,你最好骑着马去。天好像要下
雨的样子,下了雨你就可以在那儿过夜。”
“这倒是个好办法,”伊丽莎白说,“只要你拿得准他们不会送她回来。”
“噢,彬格莱先生的马车要送他的朋友们到麦里屯去,赫斯脱夫妇又是有车无马。”
“我倒还是愿意乘着马车去。”
“可是,乖孩子,我包管你爸爸匀不出几匹马来拖车——农庄上正要马用,我的好老爷,是不是?”
“农庄上常常要马用,可惜到我手里的时候并不多。”
伊丽莎白说:“可是,如果今天到得你的手里,就如了妈妈的愿了。”
她终于逼得父亲不得不承认——那几匹拉车子的马已经有了别的用处。于是吉英只得骑着另外一匹马去,母亲送她到门口,高高兴兴地说了许多预祝天气会变坏的话。她果真如愿了;吉英走了不久,就下起大雨来。妹妹们都替她担忧,只有她老人家反而高兴。大雨整个黄昏没有住点。吉英当然无法回来了。
——《傲慢与偏见》第七章
一段不到四百字的对话,调遣四个人物,四种情绪,实现情节的转折。文本前提是这个姓班内特的英格兰乡绅家庭膝下无子,一共有五个待字闺中的女儿,而隔壁庄园刚搬来的新住户正好有个阔少爷。班太太一收到他们家发给大女儿吉英的请柬,算盘就开始打起来。天眼看着要下雨,吉英只有单人骑马去才有可能被留在彬格莱家里过夜。我们不得不感叹班太太的细密心思,她甚至考虑到此时彬格莱家的马车正好也有别的用处,没有可能及时送吉英回来。所以班太太只需要做两件事:第一,阻止丈夫把马车给女儿。第二,祈祷下雨。前一件在她的控制范围内,后一件只能看天意。因此,班太太对大女儿说,预祝天气变坏。
这一计果然奏效,并且替班太太超额完成了任务。吉英非但留在那里过夜,而且因为骑马淋雨生了病。伊丽莎白不放心,可她不会骑马,只能步行三英里去富家庄园探望姐姐,路上溅了一身泥,于是她们都给留在那里过了不止一夜。经此一病,青年男女们得以近距离相处,傲慢与偏见得以互相碰撞。
如此具有功能性的段落,同时还能用最简洁的笔触为四个人物塑形,这正是奥斯丁在象牙上微雕的绝技。班太太的迫不及待和精于算计,班先生顺水推舟之余的暗含揶揄,伊丽莎白的“看热闹不嫌事大”和吉英虽然不无羞怯却终究掩藏不住的憧憬,全都跃然纸上。
* * *
古典小说的情节线,往往构成一个完美的闭环。不过,一旦隔了上百年的时光,离开当年的时空环境太远,就不太容易体会人物的逻辑。早已习惯现代交通工具的我们,在阅读奥斯丁之前,需要先想象一个速度更慢的世界。那时,农村里的圈地运动已经发展了好几轮,向海外开辟新航路的事业方兴未艾;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但离高潮尚远,还要再过十几年蒸汽机才能被搬上铁路。所以我们看奥斯丁小说里所有的交通方式都得通过马和马车,各位女士的活动范围、出行规划都得受制于马匹的速度。奥斯丁在这些问题上非常精确,以至于你读完小说之后差不多能在脑子里勾勒出那几个郡县、村庄的线路图,标出在它们之间往返的时间。你还能发现,奥斯丁很善于利用这种精确的时间概念推动小说的情节。一辆看似无心、实则有意顺路捎上女主角的马车,一场拥挤的、被人流冲撞得忽而遭遇忽而分开的音乐会,那些欲说还休的片言只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眼神和心跳,如同吉光片羽,常常出现在奥斯丁的故事里。
比马和马车更难理解的,也许是英国18世纪的财产继承法。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个法相当奇葩,既复杂又不近情理,它造成的大量纠纷正是过渡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几乎出现在奥斯丁的每一部小说中。
18世纪的英国采用复式继承制,动产和不动产的继承奉行的是不同的规则。动产相对合理一点,通常分为三份,妻子、儿女和教会各得一份。按照这个规则,班先生如果去世,则班太太和她的五个女儿一共可以在动产部分得到五千英镑,另外班太太自己也有一笔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共计四千英镑。然而,和我们今天一样,家庭的主要财产是不动产。我们从奥斯丁小说的很多细节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房地产交易和租赁市场相当活跃,房价总体上涨势喜人。在《傲慢与偏见》中,班家的小日子之所以过得凑合,就是因为他们家有一处地产,每年可以给他们带来两千英镑的稳定收入。然而,根据不动产继承的游戏规则,这笔钱只能领到班先生去世为止,因为当时英国的土地承袭中世纪的封建宗法传统,把长子继承制作为第一原则。长子继承制的好处是保持土地和房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国家管理,长子在继承基业的同时也得承担教养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但这种从政府角度看一劳永逸的办法,在实行起来常常碰到问题。好比班太太,一直生到第五个女孩之后,才发现不动产没有长子可以继承。她早年从未担心过这一点,吃穿用度从不省俭,如今却为此日夜焦虑。丈夫只能这样安慰她:过一天算一天吧,没准你还有幸死得比我早呢。
比长子继承制更糟心的是限定继承权。英国的土地权属错综复杂,很多地产在相当长时间里都附带着古老的封地义务。这种义务来源于距今一千年前的诺曼王朝,非常复杂,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这种土地是国王的,一层层往下分封,但是你不能白拿这块地,得有男人服役。从小说的情节看,班家的地正是这一种。尽管让男丁到军队服役的行为实际上早就被废除了,但由此产生的限定继承制度却没有被废除。限定继承地产不能空置,必须有形式上的男性服役者,如果你家里没有男性,那对不起,有关部门就会按照亲缘关系指定男性继承人。如果班太太不幸比班先生死得晚,班先生的表侄柯林斯就随时能把她和五个女儿赶出门。
这样不公平的继承法延续了很多年,让大大小小的班太太们气火攻心,引发了不少伦理公案,直到1925年才彻底废除。所以我们在英剧《唐顿庄园》的第一集里就能看到,20世纪初的贵族庄园仍然要面对和《傲慢与偏见》一模一样的问题——爵爷同样膝下无子,同样只能把家业传给表亲,同样为这事搞得鸡飞狗跳。可想而知,从《傲慢与偏见》到《唐顿庄园》,这块骨头在英国人喉咙口鲠了一百多年还没有消停。
因此,班太太虽然性格不那么讨人喜欢,但她的焦虑是实实在在的,也是情有可原的。那个时代的女性没有工作,婚姻非但是头等大事,而且,用奥斯丁的说法,是“唯一的大事”,关乎生计甚至生存。她们通过社交手段求爱、相亲,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女性把高考、求职和恋爱结婚打包在一起,一战定生死,以后基本没有翻盘的可能。这样的命运其实颇为凄凉,这里头的明争暗斗也肯定十分激烈,但是奥斯丁并不打算凄凉地写凄凉,激烈地写激烈,她更愿意把整个事件当成一个笑话。所以从一开始,她就坚定地为她所有的小说都铺上喜剧的基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