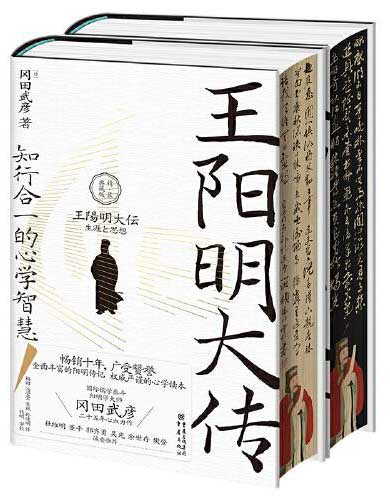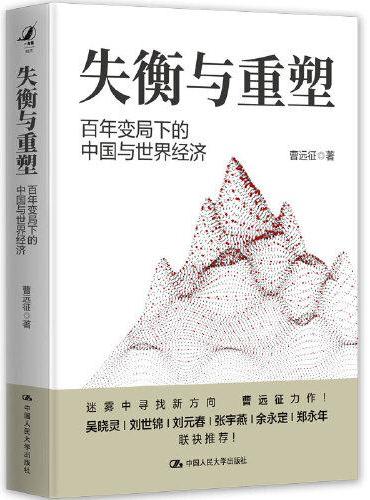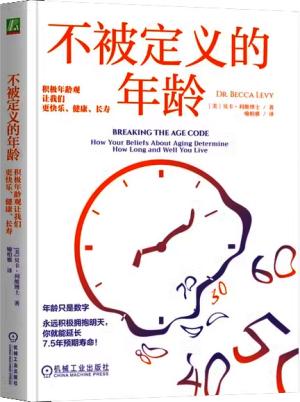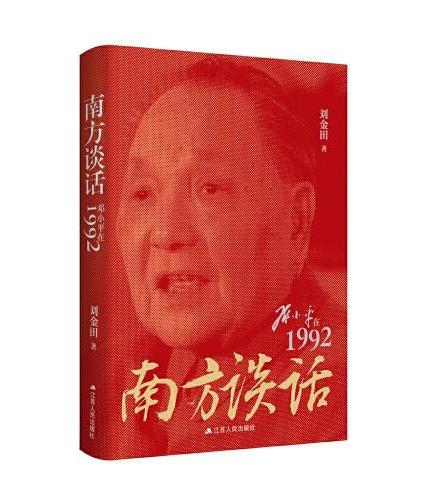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强者破局:资治通鉴成事之道
》
售價:NT$
367.0

《
鸣沙丛书·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
售價:NT$
551.0

《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兼论宗教哲学(英国观念论名著译丛)
》
售價:NT$
275.0

《
突破不可能:用特工思维提升领导力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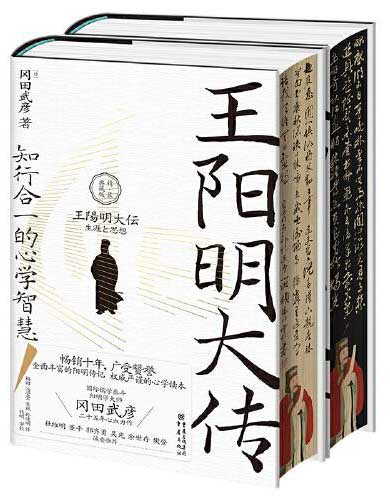
《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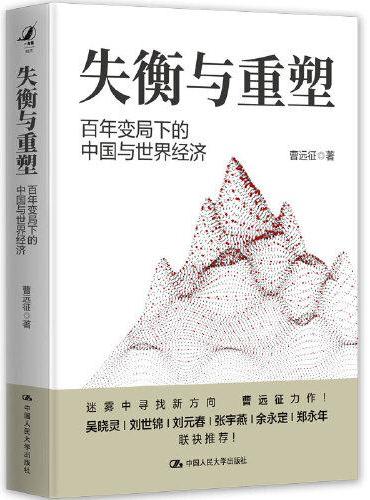
《
失衡与重塑——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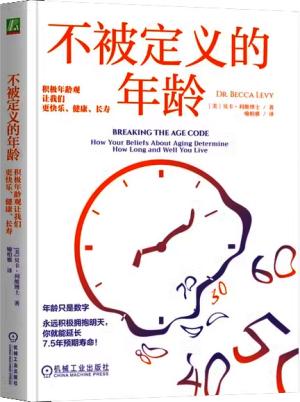
《
不被定义的年龄:积极年龄观让我们更快乐、健康、长寿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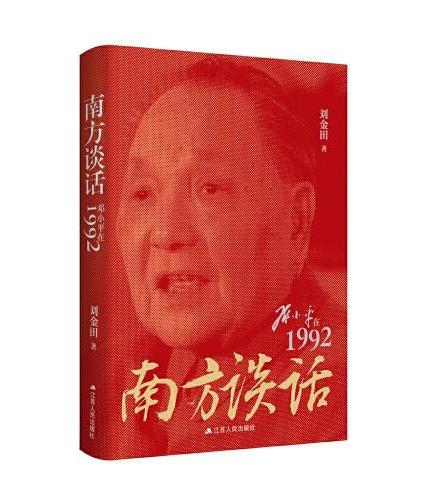
《
南方谈话:邓小平在1992
》
售價:NT$
367.0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针对农民工家庭的传播研究,重点考察家庭的流动与变迁,既有理论张力,也有充分的经验材料为证据。作者从家庭的策略传播、代际传播、仪式传播、时空传播、媒介传播等分别进行论述,并将落脚点放在农民工家庭的阶层再生产或者循环上。作者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呈现出伸缩性与延展性的特征;家庭团结与家庭个人主义的内在冲突与妥协构成了家庭传播的核心;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改变了家庭原有的权力结构;媒介承诺成为重塑新的家庭文化的形式之一;家庭出身与教育获得之间逐渐形成了阶层再生产的逆循环模式。
|
| 關於作者: |
|
李红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媒体传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所,获得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曾经于1994—1999年在媒体工作,先后在香港城市大学、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做访问学者。 自2005年以来,持续从事农民工、农民群体的研究,集中于该群体信息传播系统与总体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关乡村传播、城乡互动传播、三农传播的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关于乡村传播学的论文,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乡村传播学的教材和专著,并在高校开设了分别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乡村传播学”课程。
|
| 目錄:
|
绪论
一、家庭研究的历史脉络
二、研究框架与研究工具
上篇 陌生的希望:家庭迁移VS.策略选择
第一章 生存导向:家庭策略
一、自发流动与两地长期分居模式的形成
二、血缘地缘流动中的“临时家庭”
第二章 职业导向:家庭生产
一、农村与城市临时分居模式
二、城市分居模式
三、城市团聚模式
第三章 文化选择:家庭养育
一、被托管的童年:时空距离和情感距离
二、教育:作为救赎的形式
三、打工:另一种轮回
四、代际关系与个体化
中篇 挪用的技术:家庭迁移VS.媒介选择
第四章 仪式选择:农业时间与城乡勾连
一、春节仪式与春运潮:返乡还是留守
二、农忙时节的返乡仪式:农民还是工人
小结
第五章 媒介“内外”:家庭场域VS.信息传播
一、家庭内外:工作时空还是家庭时空
二、家庭领域:家庭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边界的重新设立
小结
第六章 媒介流变:家庭迁移VS.代际更替
一、“媒介挪用”中的流变史
二、虚拟与非虚拟关系场景中的媒介生活方式
三、媒介中的代际勾连
小结
下篇 移动的尺度:家庭单位VS.阶层选择
第七章 农民工家庭的阶层传播
一、阶层的自我认知
二、阶层的互斥性
三、阶层的同质性
四、阶层变动与社会再生产
小结
终篇 流动的边界:个人主义VS.家庭主义
第八章 媒介承诺:流动中的家庭生命周期
一、家庭生命周期呈现出“伸缩性”与“延展性”的特征
二、家庭团结和家庭个人主义的内在冲突与妥协构成了家庭传播的核心
三、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改变了家庭原有的权力结构
四、媒介承诺成为重塑家庭文化的形式之一
五、家庭出身与教育获得之间逐渐形成了阶层再生产的逆循环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仪式传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九章 余论
一、个体生命历程的重构与家庭生命周期的转折之间是什么关系
二、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政治抑或文化
三、家庭“危机”:个人主义还是家庭主义
参考文献
后记
|
| 內容試閱:
|
绪论
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曾经、依旧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尽管家庭常被看作是一个激起人们感情的社会单位,但是它却是一个为更大的社会结构服务的一种功能性结构,许多其他机构都取决于家庭所作的贡献。”(古德,1986:8-9)
在全球化过程中,人口流动加速,技术带来的信息传播迅疾地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家庭内外的传播模式,这些因素合力,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家庭观念、家庭的信息传播结构和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成员之间的传播关系也在不断调整:尽管每个家庭成员在社会上有了新的角色,他们依然希望通过相互交往为其他的家庭成员提供有形和无形的帮助,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Koerner & Fitzpatrick,2010)。一方面,家庭作为一个领域,是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另一方面,家庭作为组织、家庭成员作为个体,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都自然而然地与家庭之外的领域发生关系。
就中国的家庭而言,其变迁过程与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一样,也在不断调整中。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社会变化几乎渗透在各个层面。这些变化的动因,部分来自外力的迫使,部分来自中国人自身的努力。1949年之后,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确立,家庭的变化在各个层面铺开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则以另一种新的变革形式,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D?D家庭,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其中,农民工家庭应该是承受这种冲击力度较大的单位之一,对其进行关注和研究,可以为中国社会变迁趋势提供一个层面的社会明证。
从劳动力角度而言,相比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司和个人,一个家庭生产单位对劳动力的态度很不相同。首先,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不会在边际劳动报酬低于市场工资的时候继续投入劳动,而一个家庭农场,如果没有其他就业机会,依然会继续投入劳动以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求,在经济逻辑上一直到其边际报酬为零。其次,家庭农场中的辅助劳动力不能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理解,因为这样的劳动力在市场上不能出售,但在副业生产上却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黄宗智,2011:96)。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压力与家庭经济组织结合,形成庞大的“非正规”底层社会和其家庭经济单位,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认识并想象真正的中国。这是与现代西方不同的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不同不仅仅在于它的经济原理不同,也包括它的社会结构不同(黄宗智,2012)。因此,从家庭单位出发,而不仅仅是从西方现代“个人”的建构出发,才可以认识到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层历史动因。
从变迁而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农民工群体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首先,尽管改革开放的政策一开始是从农村到城市,但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需要的是多方位的配合,在农村集市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市场、由城市改革所引发的乡镇企业的出现,以及这个过程本身对农民观念的触动所导致的行为变化,都使得人口的流动在市场的自发运作中、在城市社会的“边缘”职业需求中渐渐成为一种不得不面对的现象。其次,从城市管理的政策而言,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的工作意见》中,首次涉及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进城务工的问题的议题,2003年出台了两个标志性的文件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3〕1号)和第381号国务院令《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2003年8月1日正式施行)。前者的出台所隐含的信息指向依然是以城市管理稳定为中心的行政导向,因此在执行层面上文字意义更大于现实运作。后者的出台导致1982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其标志性意义在于外来者进入城市流动的行动自由权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保证。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将进城务工人员列为产业工人。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这个建议可以说将城乡之间的就业市场直接纳入了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中,与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相呼应,就业和服务管理成为农民工进城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2005年12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专门提到了农民工问题:“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如何对待农民工,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全局和长远的大事。”
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撰写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对“农民工”的概念做了明确的界定:“‘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