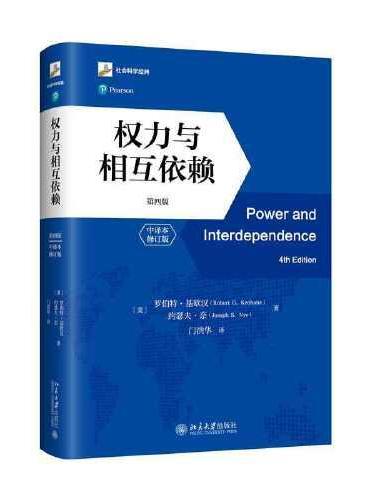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民法典1000问
》
售價:NT$
454.0

《
国术健身 易筋经
》
售價:NT$
152.0

《
古罗马800年
》
售價:NT$
8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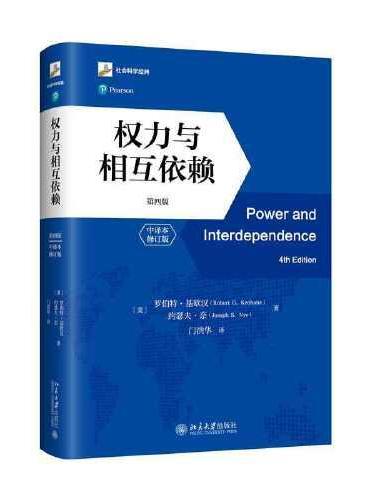
《
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中译本修订版)
》
售價:NT$
658.0

《
写出心灵深处的故事:踏上疗愈之旅(修订版)(创意写作书系)
》
售價:NT$
301.0

《
控制权视角下的家族企业管理与传承
》
售價:NT$
398.0

《
冯友兰和青年谈心系列
》
售價:NT$
762.0

《
利他主义的生意:偏爱“非理性”的市场(英国《金融时报》推荐读物!)
》
售價:NT$
352.0
|
| 編輯推薦: |
本书所涉及的李大钊、章士钊、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物与《新青年》杂志、五四运动等事件,均在中国近代史上意义不凡。其杨琥先生系李大钊等方面的研究专家。
本书主要使用新近公布的史料,尤其注重历史细节的爬梳与疏证。所提出的新认识既在学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对大众历史爱好者有较强吸引力,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民国史感兴趣的读者。
|
| 內容簡介: |
|
这是一本关于清末民初zhong要思想人物研究的学术论集。晚清中国,中西交冲,新旧消长。时势逼迫下,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得风气之先的人士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数十年强毅力行,行走在中国人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蹒跚路程上。全书共收入十余篇文章,涉及当时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本书尽可能多地使用新近公布的档案、书信、日记乃至国内外报刊,解决了许多史学界关注却未作深入研究的问题。长篇考证发掘出大量沉睡的历史秘辛,从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丰富了今人对晚清的认识,具有zhong要的学术价值。
|
| 關於作者: |
|
杨琥,甘肃通渭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李大钊生平与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史、北京大学校史。著有《李大钊年谱》,编撰《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1919-1949)》《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李大钊卷》《夏曾佑集》《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等近代人物文集和史料集多部;参编“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李大钊全集》(注释本)和《孙中山全集》。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党的文献》《北京大学学报》等权威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
| 目錄:
|
【目录】
上 篇
戊戌时期章太炎尊荀思想及其中西学术渊源
一、问题的提出
二、章太炎尊荀与乾嘉荀学复兴
三、章太炎尊荀与西方进化论、社会学
四、章太炎尊荀的核心:“合群明分”
五、余论
转型时代的观察与思考:夏曾佑晚清政论试析
一、“荀学”与“秦人之教宗”乃中国近代落后之源
二、“孔教改良”与“改革政体”
三、“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
四、以历史的眼光分析和预测时局演变
五、针砭政府之弊 批评新党之病 力求发表“公论”
六、余论
民初严复与章士钊关于“民约论”的论争
一、清末民初“民约论”在中国的传播
二、严复、章士钊关于“民约论”的论争
三、结语
章士钊与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的创设
——以《甲寅》杂志为核心
一、章士钊与“通信”栏的设置及其演变
二、《甲寅》“通信”栏与民初社会、文化的互动
三、余论:《甲寅》“通信”栏的先导作用
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的前前后后
一、蔡元培出长北大并非孙中山“支持”和“指派”
二、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外在之因
三、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内在之因
下 篇
《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
——《新青年》创刊史研究之一
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
——《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
一、《新青年》撰稿人的构成与特征
二、《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聚合途径
三、结论
《新青年》“通信”栏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互动
一、《新青年》“通信”栏的设置及其演变
二、“通信”栏的讨论话题与编者、读者之间的思想互动
三、“通信”栏编、读之间的人际互动与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的汇聚
四、“通信”栏与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的互动
五、结语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兼谈《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的编辑和印行
一、《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与《新青年》第6卷第5号的交付印行和出版时间
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的定稿与“明生通讯”、《新青年》第6卷延期问题
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撰写时间与《新青年》第6卷第5号的编辑与策划
四、余论
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
——《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与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二、李大钊是《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动人物
三、几点结论与愿望
《每周评论》等报刊若干撰稿人笔名索解
——“明生”“去闇”“CZY生”及其他
一、《每周评论》:“明生”即陶孟和
二、《晨报副刊》:“去闇”即李大钊
三、《甲寅》月刊:“CZY生”“渐生”“运甓”及“重民”之真实身份
四、余论
附 录
乾嘉荀学复兴概述
“五四运动”名称溯源
民国宪政先驱——张耀曾生平略传
一、主持《云南》杂志 鼓吹革命思潮
二、参与制宪 草拟《天坛宪法草案》
三、再次东渡 投身反袁
四、出任司法总长 组织政学会
五、任职法权讨论委员会 主持司法考察
六、退隐上海 执律师业
七、为抗日奔走
后记:求学与治学经历的简要回顾
|
| 內容試閱:
|
学问·生命·时代
我与杨琥相识,最初是在导师刘桂生先生为清华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中西文化与中国革命》课上。从此以后,我们便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至今已有30多年。杨琥在清华读研期间留给我的最大印象是:为人诚实耿直,酷爱学术,嗜书如命,研究中敢碰难题。随着后来交往的不断增加,我又进一步发现,杨琥不仅爱读书,而且会找书,会读书。刘桂生先生教给我们的目录学、文献学等方面的一些方法,他都能够很好地付诸学术实践,不时从清华、北大等图书馆的馆藏中发现一些前人所未曾发现的新材料,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新的文献支撑。这让我钦佩不已。
收入《清末民初的思想与人物》中的论文,绝大多数我都曾经认真拜读学习过,有的甚至是在其正式发表前就阅读过。但是,汇编成集后,与过去单篇阅读时的感受完全不同,从中更能看出杨琥治学的一些突出特点。
一是治学专精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这一历史阶段是中国近代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中西文化加速碰撞、交流,新旧思想激烈争鸣、交锋,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古今中外交汇、不古不今不中不外”的特殊现象。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对于深入理解和认识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理清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由旧趋新、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机理,十分重要。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特殊性,研究起来难度很大,研究者不仅需要对“旧学”有一定基础准备,而且还要对“新学”“西学”有相当了解。收录在此文集中的论文,内容上涵盖了从甲午到“五四”的整个历史时期,主题涉及章太炎、夏曾佑、严复、章士钊、蔡元培、李大钊等重要思想家的思想学术主张,《甲寅》《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新舆论工具的兴起及其作者队伍的聚合,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承续因缘等。对于这些重要领域,作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考察,得出了新认识,尤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源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等问题,更是取得较大进展,深化了对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认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二是治学风格上“小题大做”。在一般人看来,似乎题目越“大”,价值也越大,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常常是“大”而无当,越大的题目往往越空,越难以在学术上有所突破。与此相反的是“小题大做”,即在学术史上一些看似“小”,但却极其关键极为重要的问题上下功夫,才会在学术上实现真正的创新和突破。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导师刘桂生先生从我们入学起就耳提面命、反复强调的。收录在文集中的《〈每周评论〉等报刊若干撰稿人笔名索解》,就很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这篇论文表面上看只不过是对《每周评论》几个撰稿人笔名的考证,看似很细小,因此一般人可能意识不到它有什么重要价值。但实际上,论文所考证的这几位人物笔名,均牵涉到《每周评论》等报刊的一些关键问题的枢纽,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报刊史研究中需要解决而又长期未能解决的难题。这篇论文的重要价值在于:(一)文内的考证,确认解决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性历史人物的身份问题。“渐生”这个笔名,研究清末民初报刊史的人都会经常碰到,尤其研究章士钊或《甲寅》月刊的学者都知道,“渐生”是《甲寅》月刊的重要撰稿人,与章士钊长期合作,但是这位先生究竟是谁,长期以来却没有人知道。杨琥从多种材料、多种角度查证,终于确定“渐生”是《帝国日报》主编、《甲寅》月刊撰稿人、《甲寅日刊》经理兼发行人陆鸿逵。这个考证,说明杨琥的这篇文章所解决的是长期需要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学术问题,是一个真学术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加深了我们对《甲寅》杂志及新文化运动兴起史的认识。(二)在研究方法上,这篇论文显示了社会关系在考察相关笔名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历来重视人际关系,该文在解决“明生”“去闇”“运甓”这些人物笔名时,首先从每个人物的社会关系与生平活动入手,详细地考察其朋友、同事等相关人物的活动与行事,层层推进,终于解决了需要解决的笔名的真实身份。(三)这篇论文还显示了训诂学方法在考证近现代文献中的笔名、化名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人,在取名时有一定的寓意和习惯,杨琥在考察“去闇”“渐生”“CZY生”等笔名时,充分地运用了语言训诂方面的知识,将史料考证与语言训诂互相印证,对这些人物笔名一经考定,就如同铁证,无法推翻。这篇论文总字数1.6万字,正文不过8千多字,而为正文所作注释却多达7千多字,几乎与正文的字数相等,真可谓无一语无出处,字字有来历。
三是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注重从现实的社会交往中,而不是仅仅从抽象、孤立的文本文献中,探讨思想文化现象。思想文化都是时代性、社会性的,离开了时代和社会,就无法理解思想文化。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真正做起来却很难,要做得好,就更难,非长期花大气力,下细功夫不可。收在文集中的《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一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它考察了《新青年》杂志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揭示了新文化运动研究中以往被忽视的一个侧面。《章士钊与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的创设》《〈新青年〉“通信”栏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互动》二文,从鲜为人注意的《新青年》的通信栏入手,澄清了以往不为人知的众多通信作者的身份,及其与《新青年》编辑部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传播提出了新的见解。此外,《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若干问题的再探讨》等文,通过对《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晨报副刊》改版的考察,从社会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等问题,做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究,纠正了国内外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误或错误观点,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业师刘桂生先生在指导我们时,多次指出:学问、学术、思想都是从一定时代具体的活的社会关系脉络中生长发育起来的,它们不是外在于时代和社会的抽象的存在,不是“死”的知识,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对其所处时代、社会、境遇的应对与思考,以及他们的人格、精神、心灵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生动呈现。历史研究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特点,才能真正认识并揭示思想文化的内涵及其意义;也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特点,才能够做出原创性的研究。换言之,历史性的问题,只有在历史的过程中,用历史的方法才能得到解决,而这些历史性的问题一旦这样地得到解决,我们对此历史性问题的认识,也往往就会得到极大提高;历史研究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也因此而得到彰显。杨琥的这些研究,充分说明和体现了这个道理。
杨琥的论文集即将出版,我很为他高兴,相信这本论文集的出版,一定也会像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他花20年时间所著《李大钊年谱》(上下卷)的出版一样,受到学界同行和普通读者的欢迎。
王宪明
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的前前后后
“蔡元培与北大”是人们常常谈论的老话题,也是蔡元培与北大校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这样一个课题,以往的学术界已进行了很多研究工作,以致人们觉得“蔡元培与北大”似乎已是无可探究,早有定论的问题。然而,事情往往是相反相成的,唯其“无可探究”,其中也许反倒隐藏着值得探究之处。比如,蔡元培出长北大“是孙中山支持”的,以及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工作,是革命党隐伏在北方文化教育方面的一着棋”之类的说法,就长期在学术界流传,而这类说法,与历史的实际是否相符,换言之,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历史事实究竟如何,正是本文所要考察探究的问题。
一、蔡元培出长北大并非孙中山“支持”和“指派”
以往关于蔡元培或北京大学校史的代表性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认为,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是得到孙中山支持的,有些甚而提出蔡同意出长北大是受孙中山指示的。可见这种说法由来已久,流传甚广。但考察此一说法的来源,其持论根据不外乎罗家伦和黄季陆的回忆,换言之,罗、黄二位是此一说法的造其端者。现将罗、黄二人的说法照录于此,再做分析:
民国五年底,蔡元培先生自己被任为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党内同志有两种意见,一种赞成他北上就职,一种不赞成。国父孙中山先生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先生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所以主张他去。蔡先生自己又不承认做大学校长是做官,于是决定前往。
黄季陆在《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一文中,也说:蔡元培在考虑接受当时北京政府的任命时,在上海曾遭受旧日同志的反对。而孙中山对蔡元培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却予以赞成。他进一步指出:“蔡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工作,是革命党隐伏在北方文化教育方面的一着棋。民国八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如果说北京大学是当时思想策动的中心,那末其中心人物无疑也就是蔡元培先生。五四运动的真实意义是国民革命的的发生与继续,是固蔽的思想、文化的突破,亦即是另一种形式的首都革命。”
罗、黄二位先生言之凿凿,但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一)原始材料不能印证此一说法
1.翻检有关蔡元培的原始材料,蔡本人关于他出长北大之事,曾在若干文章中述及,最早的一篇是《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而据蔡元培回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jiaoyu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蔡之回忆,只提“友人”,并未直接提指“孙中山”,更未说他愿去北大是接受“孙中山”的“着意安排”。后来,蔡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1938年)中又回忆及长北大事,文字与上引文字略有不同,但所述情形与上文是一致的。
除蔡本人的回忆外,蔡之“日记”“自述”中皆无直接材料印证此一说法。
2.具体考察1916年底到1917年初蔡元培任职北大时孙、蔡二人现有的交往材料,孙、李二人之间,也无关于蔡长北大的相关讨论、协商之议。其间二人交往的具体情况是:
①蔡元培于1916年9月1日接到教育总长范源廉邀请其出任北大校长的电报,10月2日离法归国,11月8日到达上海。在上海,11月9日,孙中山、蔡元培等同在黄兴灵堂吊祭。
②11月12日,蔡就离开上海回杭州、绍兴。11月29日,以主丧友人的名义,与孙中山等联名向全国发出通告电,并在各报登出关于黄兴的“讣告”(蔡仍在杭州),直到12月12日左右返回上海。
③12月13日再赴杭州,然后由杭州直接北上。于21日到北京,26日,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蔡为校长”。
④蔡任北大校长后,孙、蔡的交往是:
1917年4月14日,在再次公祭黄兴时,孙中山向蔡元培电索黄公碑文,蔡即日复孙一函b。在此之后,一直到1918年11月14日,蔡、孙二人之间在一年多时间中再无通信。而从1918年11月14日到1919年1月21日,蔡又致孙中山函共四通,除第一、二通是向孙中山鼓吹和平主义、敦促开展南北和谈之事外,三、四通所谈论的都是无关实际政治活动的其他事务。
由此可见,孙中山“支持”蔡元培出长北大的说法尽管流传甚广,但至今尚无确切的、充分的原始材料证明此一说法。
(二)从当时孙中山蔡元培二人的政治活动、思想倾向分析,二人正处于分歧状态之中
1.政治上,二人分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两位领袖孙中山、黄兴在如何“讨袁”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导致革命党分裂,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主张“武力讨袁”;而支持黄兴的人士则组成“欧事研究会”,主张积聚力量,联合其他政党,以温和渐进的方式共同反袁,蔡元培则属于此一系统,在反袁问题上,与孙中山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
2.思想上,二人的主张也不同。反袁结束后,如何建国?孙中山认为北洋政府腐败,政治上无法取得进步,故主张“实业救国”,准备从事实业。而蔡元培尽管也认为北洋政府腐败,但却力图从教育入手,以改造学校教育而提高人民素质。
3.在具体的政治事件上,二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也不同乃至大相径庭。1917年2月,在蔡元培就职北京大学不久,北洋政府即因对德宣战问题而发生府、院之争。在对德宣战问题上,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国民党人及其议员,大多数持坚决反对“参战”的态度,而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作者群(新文化派)则赞成、支持北洋政府段祺瑞“对德宣战”,而且,陈独秀还撰文批评孙中山的态度。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重大的政治、思想问题上,孙、蔡二人处于相当分歧、不一致的状态之中,在这种状况下,孙中山不可能支持、赞同乃至指示蔡元培出长北大校长一职,而蔡元培也未必接受孙中山的主张。蔡之所以出长北大校长一职,客观上有一定的大环境支持,而更为关键的,则在于他自己的思想、主张、理想促使他接受此一职务,外人的劝告实际作用并不大(关于蔡就职北大时的心路历程,详后文)。
(三)罗、黄等人的说法之误
众所周知,孙中山对“五四运动”是支持的,赞同的,但对于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以及此一运动所反映出来的民族虚无主义,则持严厉的批评态度。然而,问题在于,时过境迁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却以文学革命、反孔斗争等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对于这样一场伟大的思想运动,其领导权究归于何人、何阶层呢?此一问题,在五四运动发生后几年不久,即成为各个政治派别争论的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一运动的评价越来越高,而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及国民党,却同这场运动关系不大。于是,论证孙中山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成为国民党党内部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史家的努力目标。罗家伦、黄季陆等就是这部分史家的代表。他们说孙中山支持蔡元培出长北大的说法,于史无证,于理不合,但为什么这样呢?其目的就在于争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权。
尽管孙中山本人和国民党与这场运动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但蔡元培却是新文化运动发生中心的北京大学的校长。他们如果将蔡进北大论证为受孙支持或“指派”,那么,孙中山领导了或指导了五四运动,就成为顺理成章的结论了。罗家伦、黄季陆等人作为国民党的史家,做出这样的论证或说法,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大陆的史学家也承袭此说,不加省察,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马克思说,意识形态的造作不等于学术研究,在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校史的研究中,我们不能只为一时的宣传而神化、美化蔡元培或其他历史人物,而只能从原始的材料出发,去确实地说明每位历史人物的真实事迹。
二、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外在之因
(一)北洋系、进步党(研究系)、国民党三派的合作,是蔡出长北大的大环境
蔡元培出长北大,有特定的时间、条件、环境和背景,即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调整,段祺瑞上台,北洋系、进步党(以梁启超为首)、国民党三派人士大合作,当时的政局气象为之一新。原来的国民党、进步党两大党高唱“不党主义”,主张“容纳异己”,因之政府由北洋、进步、国民三派人士合作组成,议院中最初也无党派对峙的局面。而北洋政府jiaoyu部长由进步党人范源廉担任,范与蔡元培在民元jiaoyu部曾共事(蔡长部长、范任次长),为蔡出长北大提供了政府方面的支持。
(二)北洋政府jiaoyu部,江浙人士的人际网络,为蔡出长北大提供又一便利条件
北洋政府的jiaoyu部,由晚清学部与民国初年jiaoyu部二者合流演变而来。晚清学部是清政府在“新政”中设立的一个新部门,其中不乏维新人士;而民初的jiaoyu部,在蔡元培主持下,更是大力引进了革命党人,尤其是浙江、江苏人士,著名的如袁希涛(普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社会教育司司长)、蒋维乔(参事)、许寿裳(参事)、鲁迅(佥事),此外还有钟观光、董鸿祎、汤中等人(其中袁、蒋、汤为江苏人,余均为浙江人)。临时政府北迁后,jiaoyu部与学部合流,是北洋政府中思想、作风、气度等均较新的一个政府部门。而在这一部门中,同乡、同门的互相援引,使得浙江籍人士占有相当大的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北京的教育界。当时的状况是,jiaoyu部长及次长因受政治斗争、政局变动的影响,经常发生变更,而司长、参事则相对稳定(如夏曾佑,连任四年司长,许寿裳、蒋维乔任参事达五六年之久),至于下级官员和部员就更为稳定了(如鲁迅任佥事,直到1926年南下广州为止,长达十多年)。
在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之时,jiaoyu部的次长是袁希涛,参事是许寿裳、蒋维乔,专门教育司司长是沈步洲,均为江、浙人,而且或为蔡元培早年的友人,或为其革命同道。
(三)北大内部的人事变动也为蔡出长北大创造了条件
具体到北京大学内部,在民国建立以后,临时政府北迁,大批议员随之北迁,倾向革命的文化人也纷纷到北京教育界谋职。北京大学在清末民初,是桐城派的天下,严复、马其昶、林纾、姚永朴、姚永概主导着北大文科。但在严复去职,何燏时、胡仁源长校,夏锡琪、夏元瑮分别主持文科和理科学长之后,却援引了大批留学归国的同乡及友人进入北大,他们是:沈兼士、沈尹默、沈士远、马裕藻、朱希祖、朱宗莱、钱玄同、黄侃、马叙伦、陈大齐、沈步洲、康宝忠等,这些人除黄、沈、康三人外,均为浙江人,其中大多是章太炎的弟子,部分则是章太炎清末革命时的师友。他们因同乡、同门的关系,在北大也自成一股势力(此派势力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这股势力与jiaoyu部及北京教育界的其他浙江籍人士(如汤尔和)相结合,基本上左右着当时北京教育界的人事安排(沈步洲即由北大预科学长而入jiaoyu部,任专门教育司司长;后来马叙伦又任jiaoyu部次长)。
这种同门、同乡结成的人际网络关系,为蔡元培出长北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天时、地利、人和”,基本上都具备了,蔡元培只要愿意接受北洋政府的任命,即能有条件在北大进行改革。而蔡是否愿就北大之职,则需要考察蔡此一时期的思想主旨。
三、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内在之因
根据上文所引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所述,蔡元培在上海滞留期间,在考虑是否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时,多数友人反对,少数友人赞成。而蔡元培本人,最终还是做出接任校长的决定,也即是服从少数的说法而进了北京。
由此可见,蔡元培如此选择,是力排众议的。而蔡氏为何做出这个选择呢?这要结合蔡氏一生的经历、思想、人格来探索。本文仅略举大端如下:
(一)早年的追求与行事:从参与革命到疏离政治斗争
蔡元培出身翰林,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同情维新派,但并未积极参与。戊戌维新失败后,蔡元培做了深刻的反思,其反思,一是针对清政府,“知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已,乃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发民智”;另一方面,则是针对维新派,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于是,他在1898年冬由北京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由此可见,蔡氏早年在登上政治舞台后,最初所萌发的思想是:改革政治必先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是教育。后来,尽管蔡氏也曾参与革命,宣传反清,并曾一度热心暗杀活动,但主要从事的仍是教育活动。而且,随着革命工作屡遭挫折,蔡元培“意颇倦”,转而去德国留学了(1907—1911年),直到武昌起义爆发后才回国。
可以说,从戊戌到辛亥,蔡元培是一身兼二任,既是革命家,又是教育家。但从其人生道路发展的轨迹看,他经历了一场由投身革命到疏离政治活动的转变。
(二)教育救国:从倡导留法勤工俭学到主持本土国立大学
民国成立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此一时期,据其自述,他的关注对象主要在于高等教育:“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但由于民初政争的影响,蔡不久即辞职,总长任内并未实现其改革整顿高等教育的理想。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以孙、黄为代表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大多流亡日本,而主要从事文化、宣传、教育工作的人士,如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等则赴法国。在法国期间,蔡元培与李、吴等人的一项重要工作,即是组织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提倡留法勤工俭学等教育活动。
而接受教育总长范源廉邀请,决定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乃是蔡元培倡导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力图从教育入手救国的逻辑延伸,这在他出任北大校长后致汪精卫的信函中讲得较明确。他写道:“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昔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为数次爱国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学校教育,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育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发端于此。”而在他与另一友人吴稚晖的通信中,更将他本人的心思表露无遗:“弟到京后,与静生、步洲等讨论数次,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由此可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真正原因,是本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而做出的抉择。换言之,他是怀抱着“革新北大”,从改革大学教育入手而塑造和培养新的人才,从而提高人民素质,以实现祖国“转危为安”的目的而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的。
正因为蔡元培怀抱这样的理想和胸怀,因之,他上任伊始,一方面即聘请宣传新思潮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另一方面也积极邀请其在法国从事勤工俭学活动的同志和友人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等来北任教。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以近代民主主义思想改革北大,在北京大学养成新的风气。由此可预知,随着蔡元培的出长北大,一场新的思想革新运动即将在北大上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