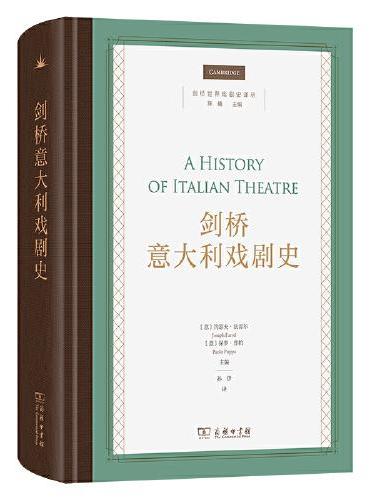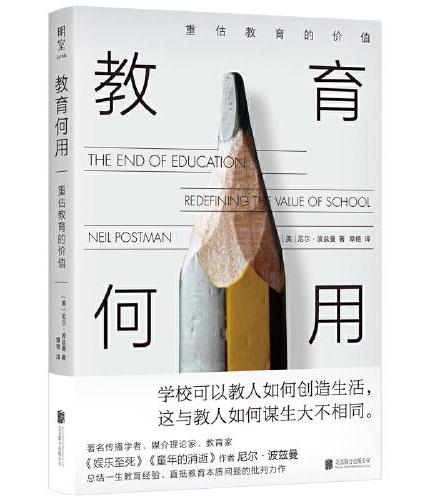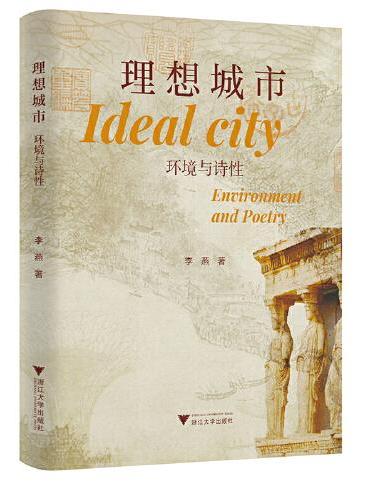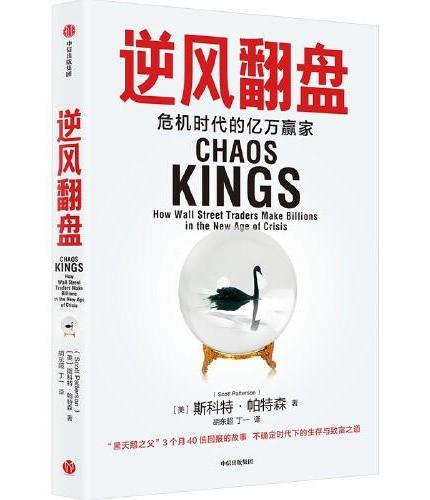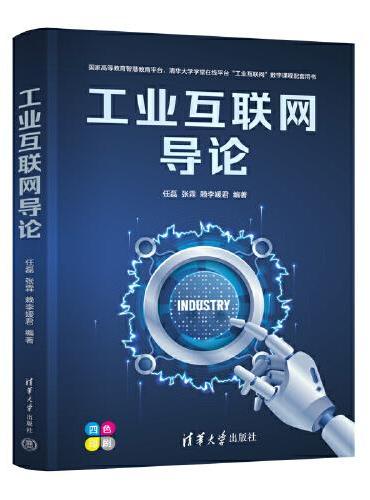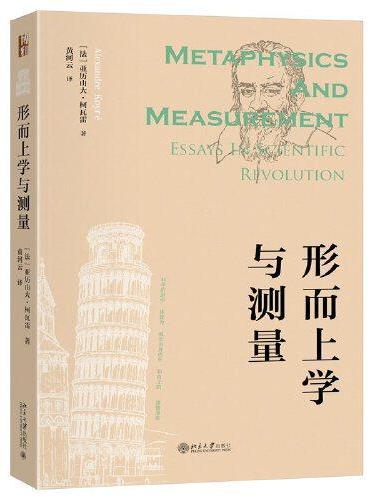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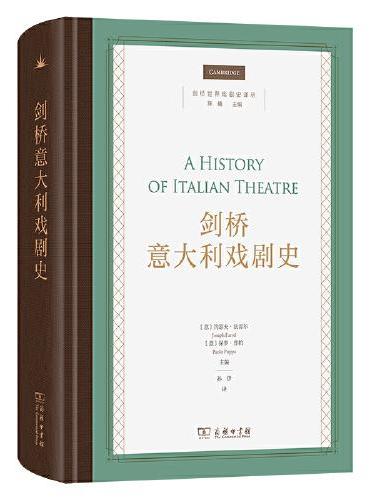
《
剑桥意大利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NT$
7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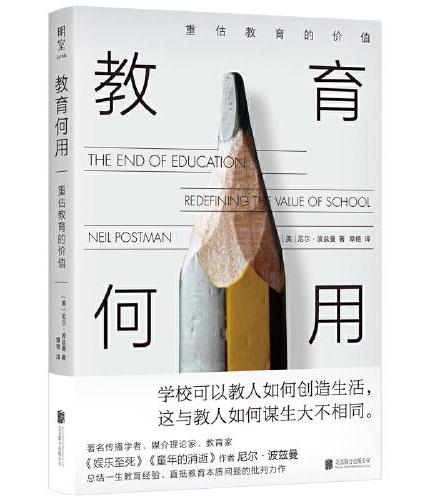
《
教育何用:重估教育的价值
》
售價:NT$
2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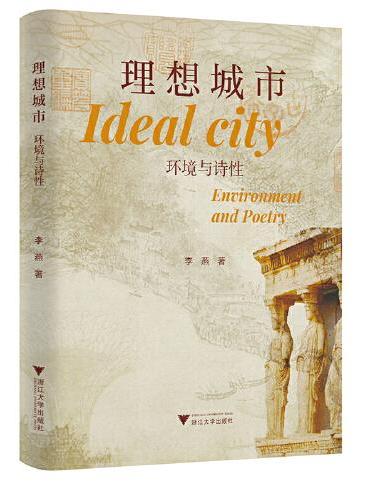
《
理想城市:环境与诗性
》
售價:NT$
3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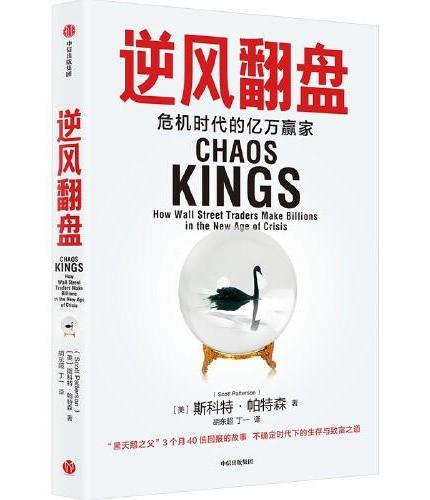
《
逆风翻盘 危机时代的亿万赢家 在充满危机与风险的世界里,学会与之共舞并找到致富与生存之道
》
售價:NT$
6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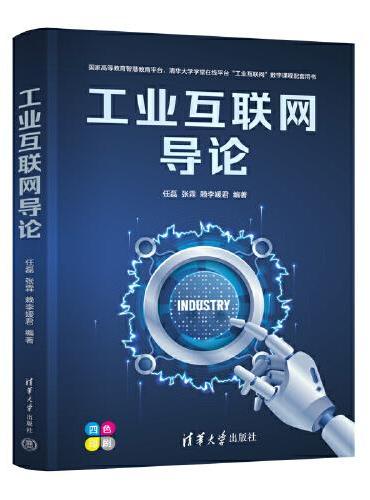
《
工业互联网导论
》
售價:NT$
445.0

《
孤独传:一种现代情感的历史
》
售價:NT$
390.0

《
家、金钱和孩子
》
售價:NT$
2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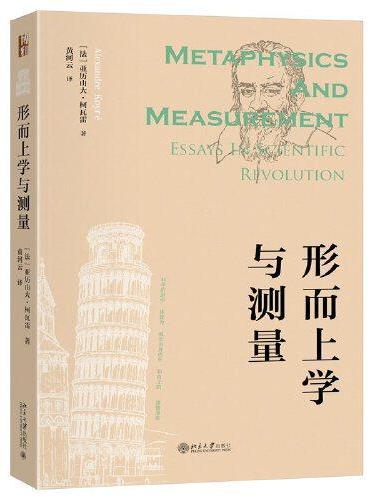
《
形而上学与测量
》
售價:NT$
340.0
|
| 編輯推薦: |
|
在《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在校勘、注释、表述上的补正,将杨先生晚年的两大专著融于一编,是杨先生七十年龙学研究的总成果。
|
| 內容簡介: |
|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一部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巨著,是研究文学、美学与文艺学等必读的经典作品。《文心雕龙》的古注,学界向来都认为清代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较好,后经李详补注,征事数典,又有了新的补充。杨明照先生素称“龙学泰斗”,其《文心雕龙校注》先全录清人黄叔琳的辑注和李详的补注;后为杨先生自己的校注,广泛校勘传世诸本,判定是非,并补前修注释不到之处,终集大成。杨先生取得了许多凌越前贤的成就,是当代学人研治《文心雕龙》的杰出代表。本书对【黄叔琳辑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分别施加注码,以便读者阅读查检。
|
| 關於作者: |
|
杨明照(1909~2003),字韬甫,四川大足(今重庆大足区)人。著名的文献学家,《文心雕龙》研究专家,现代“龙学”的开创者之一,被誉为“龙学泰斗”。杨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及古代文献研究,尤其对《文心雕龙》一书的研究,几乎从未中断,因此也取得了许多凌越前贤的成就。他是当代学人研治《文心雕龙》的杰出代表,其研究成果更被公认为划时代的著作。其主要著作有《文心雕龙校注》《学不已斋杂著》《抱朴子外篇校笺》等。
|
| 目錄:
|
前言
梁书刘勰传笺注
文心雕龙校注卷一
原道第一
徵圣第二
宗经第三
正纬第四
辨骚第五
文心雕龙校注卷二
明诗第六
乐府第七
诠赋第八
颂赞第九
祝盟第十
文心雕龙校注卷三
铭箴第十一
诔碑第十二
哀吊第十三
杂文第十四
谐隐第十五
文心雕龙校注卷四
史传第十六
诸子第十七
论说第十八
诏策第十九
檄移第二十
文心雕龙校注卷五
封禅第二十一
章表第二十二
奏启第二十三
议对第二十四
书记第二十五
文心雕龙校注卷六
神思第二十六
体性第二十七
风骨第二十八
通变第二十九
定势第三十
文心雕龙校注卷七
情采第三十一
镕裁第三十二
声律第三十三
章句第三十四
丽辞第三十五
文心雕龙校注卷八
比兴第三十六
夸饰第三十七
事类第三十八
练字第三十九
隐秀第四十
文心雕龙校注卷九
指瑕第四十一
养气第四十二
附会第四十三
总术第四十四
时序第四十五
文心雕龙校注卷十
物色第四十六
才略第四十七
知音第四十八
程器第四十九
序志第五十
文心雕龙校注附录
《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质疑
引用书目
|
| 內容試閱:
|
前言(节选)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从先秦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部杰作。全书由五十篇组成,分为上下两编,约三万七千余字。上编论述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下编则为创作论、批评论和统摄全书的序。结构严密,体大虑周,构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论体系。列宁曾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的东西。”我们按照列宁的教导来衡量刘勰,那他在《文心雕龙》中的确比他的前辈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不愧是我国最优秀的古代文学理论遗产之一,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探讨。
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刘勰认为文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也浸透了作家的主观感情。
《物色篇》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明诗篇》也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学创作的对象是“物”,丰富多采的客观事物引起了人们感情的波动,纔发而为文辞。这种物——情——文的公式,是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刘勰要求这种反映尽可能地真实:“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就是要求文学创作要宛转入微地刻画客观事物的面貌,委曲细致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他说:“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把表达作者情志放在第一位,而把刻画事物形貌放在第二位,因而不满于“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物色》)的倾向。但这并不是反对文学创作不应该“形似”,而是反对片面追求“形似”的形式主义文风。
以上是就描写自然景物而言。当然,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对象还是描写人们的社会生活。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乐府》)。这就是说文学的发展变化是由社会情况、时代面貌决定的,因为文学就是社会和时代的反映。所以他分析建安文学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这一段论述,是从建安文学和那个动乱时代的关系着眼,所以能精辟地总结出建安文学的特征。刘勰的这些观点,继承了自《礼记·乐记》和《毛诗序》以来我国文论的优秀传统。
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刘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要求文学为封建制度服务。
《征圣篇》发挥了儒家论文的传统主张,把文学的社会作用归纳为三点:“政化贵文”、“事迹贵文”和“修身贵文”。他把文学的社会功能提到了极高的地位,《序志篇》对“文章之用”说是“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程器篇》也说:“摛文必在纬军国。”这种对政事教化的强调,也贯穿在文体论各篇中,如《议对篇》要求对策能“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书记篇》指出“书记所总”的二十四种“艺文末品”,为“政事先务”。正因为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在所评论的作品中,除了一些应用文外,还有学术著作。这是由于他的广义的文学观念使然。比起萧统“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的选文标准,就显得瞠乎其后了。
刘勰的这些观点,表现了儒家思想封建保守的一面。不过,当时文坛上占主流的形式主义文学,完全抹煞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堕入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泥坑。刘勰反对“近代辞人,务华弃实”(《程器》),也并非没有积极的意义。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刘勰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要求作品达到二者的统一。
《情采篇》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这是比喻一定的形式(“文”)是由一定的内容(“质”)所决定的;“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是比喻一定的内容要求一定的形式来表现。在文、质并重的前提下,他并不把二者同等看待:“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归根到底,文章的美好(“辩丽”)不是取决于它的形式(“文采”),而是取决于它的内容(“情性”)。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他主张由“经正”导致“纬成”,由“理定”达到“辞畅”,要求内容和形式象经线和纬线一样有机地组织成一个整体,这种辩证的观点贯彻在《文心雕龙》全书中。
根据这个原则,刘勰对比了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这虽然是总结历史经验,实际是针对当时文坛而发,因为“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疎,逐文之篇愈盛”。因此,他着重批判了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这表明《文心雕龙》对当时的浮艳文风是一种挑战。
在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刘勰主张既尊重历史形成的文学规律,又根据现实的情况加以创新。
《通变篇》说:“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这是就继承而言,各种文体有一定的写作规格,需要通过借鉴前人的作品来掌握;“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这是就创新而言,临文时的变化无穷,要依靠作者的独创性来实现。只要正确处理“通”(继承)和“变”(创新)的关系,“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在规律中求变化,在继承中求创新,就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使创作的路子越走越宽。所以他说:“变则可久,通则不乏。”把“通”和“变”看作是保证文学发展“日新其业”的重要规律,这是一种辩证的观点。
刘勰的文学史观不是停滞的,而是发展的。他提倡“趋时必果,乘机无怯”的变革精神,称赞“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的实践。他看到了文学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可是这种“踵事增华”的演变却引起了他的忧虑:“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疎古,风末气衰也。”这种忧虑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表现了刘勰对当时形式主义文风的不满:“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疎矣。”另一方面,也流露出某种复古的倾向。这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所以他开出矫正时弊的药方,却是“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这当然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在作家与风格的关系上,他认为作品风格是作家个性的外现,要求作家通过加强学习来培养高尚的风格。
《体性篇》从纷纭繁多的文学作品中,归纳出八种基本的文章风格,即“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为什么会呈现这缤纷多采的种种风格呢?他认为来源于作家不同的个性:“故辞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一句话,风格即人。这是我国古代第一篇风格论,对后代风格论起过开源导流的作用。
刘勰把作家个性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其中既有先天的禀赋,也有后天的习染:“然才有庸儁,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才和气是情性所铄,属于先天的禀赋;学和习是陶染所凝,属于后天的习染。刘勰虽然也强调作家的天赋,但并不认为天赋决定一切,而是把后天的学习提到重要的地位:“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斵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因此从一开始就沿着正确的方向学习,对形成高尚的风格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强调学习的踏实学风,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事类篇》说:“才自内发,学以外成。”“将赡才力,务在博见。”这对初学者来说,乃是一种有益的教诲。
在创作与技巧的关系上,刘勰强调作家必须通晓写作规律,反对忽视技巧的倾向。《总术篇》说:“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这是借博弈为喻,说明掌握艺术技巧,便能稳操胜算;鄙弃艺术技巧,即或偶有所得,终究难竟全功。他提出了写作的极高境界:“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这似乎已经出神入化,并非仅仅是技巧问题。不过倘若没有辞采、宫商、事义、情志等方面的修养,也是断难达到这种创作的化境的。因此,他把通晓各种写作规律作为“通才”的必要条件:“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最后还要求能“乘一总万,举要治繁”。可见刘勰对“研术”何等地重视!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还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分析,总结了许多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方面的规律。例如《镕裁篇》和《附会篇》,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文章的主题思想和行文修辞的关系。前者归纳了提炼思想、精炼文句的一套办法,后者提出了集中主题、敷陈辞采的种种措施。《比兴篇》阐述了“比”、“兴”这两种传统表现方法的作用,《夸饰篇》探讨了夸张与真实的关系,特别是冠下编之首的《神思篇》,对艺术思维分析,更深入到创作过程中精深微妙的境地,说明了刘勰理论所达到的深度。像这一类精到的分析和论断在全书中不胜枚举,构成了《文心雕龙》充实而富有启发性的内容。
正因为刘勰重视艺术技巧的作用,所以他虽然反对当时的形式主义的文风,却批判地吸取了其中的许多艺术经验。例如,片面地追求声律、对仗、用典本是当时唯美主义骈体文在语言上的特色,不过这些表现手段本身却自有其合理的价值。刘勰写了《声律》、《丽辞》、《事类》等篇来探讨这些表现手法,《文心雕龙》本身也是骈体文的典范,超过了古代的好些骈文著作。难怪范文澜有“全书用骈文来表达致密繁富的论点,宛转自如,意无不达,似乎比散文还要流畅,骈文高妙至此,可谓登峰造极”的好评了。但一般读者阅读起来有困难,却也是事实。
关于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刘勰要求文学批评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并提出了正确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
《知音篇》劈头就发出“知音其难哉”的浩叹,致慨于公正的文学批评之难逢。这是有感而发的。后来《文心雕龙》成书之初,也曾遭到人们的轻视。刘勰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批评者的三种偏见,即“贵古贱今”、“崇己抑人”和“信伪迷真”。因此,他要求文学批评客观地反映作品的实际,“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他反对以主观的偏爱代替公正的批评:“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这在今天也是批评者应引以为戒的。
文学作品不是作者思想的图解,而是生活的形象反映;作者的思想倾向是隐藏在形象之中的,文学创作的这一艺术规律,也是批评不易公正的客观原因。刘勰说:“文情难鉴,谁曰易分?”他固然认识到准确领会作品内容并非易事,但也认为作品毕竟是能够认识的:“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学批评的途径和文学创作正好相反,不是由内容(“情”)到形式(“辞”),而是由形式(“文”)到内容(“情”),这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作为“沿波讨源”的具体方法,他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六个方面:“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这似乎偏重在文学的形式方面,不过刘勰提出“六观”是为了考阅“文情”,并没有脱离文学的内容。而要真正掌握“六观”的方法,还要以批评者的丰富实践经验为前提:“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也就是实践出真知的意思。
《文心雕龙》本身就包含了大量的文学批评实践:《指瑕篇》批评作品,《才略》、《程器》两篇批评作家,《时序篇》是“十代”的简明文学史,上编文体论各篇实际上是分体文学史,也包括了丰富的文学批评内容。这些批评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不乏精到见解,达到那个时代的先进水平。
总之,《文心雕龙》是对齐代以前文学理论批评的一次大型总结,同时也是对齐代以前文学创作实践经验的一次系统探讨,成就是巨大的。当然,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刘勰不可能不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因而书中也必然存在一些偏颇的甚至错误的见解。但是,从总的成就看,那毕竟是次要的。对于这样一部杰作,我们应该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进一步研究它,发掘它,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提供更多的借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