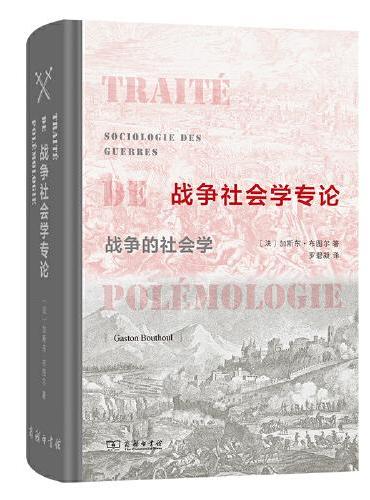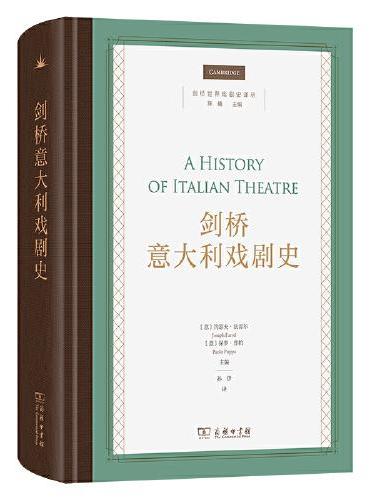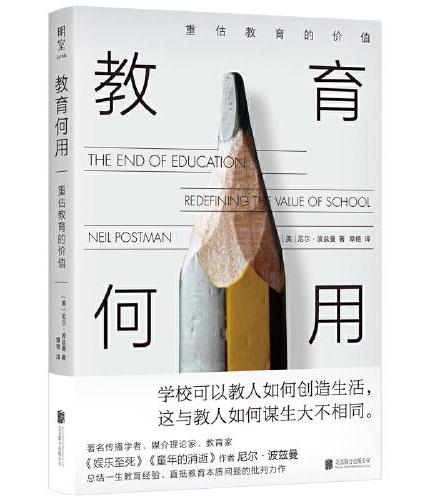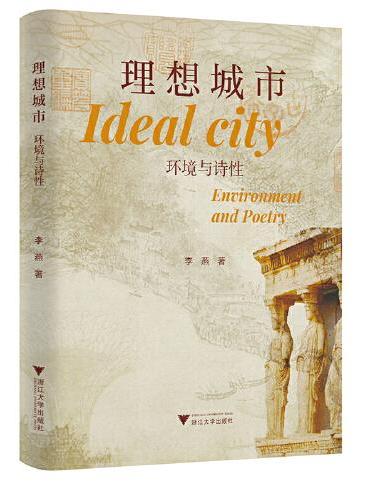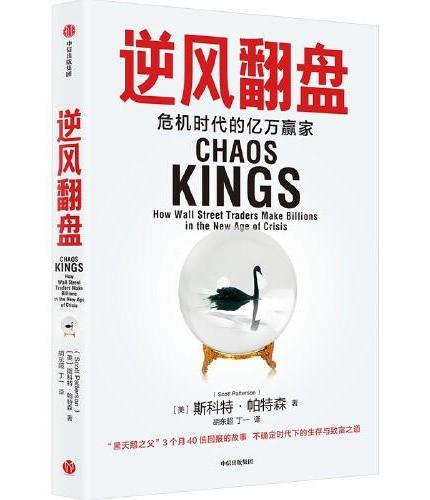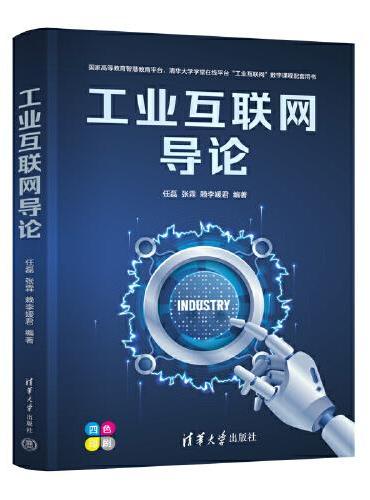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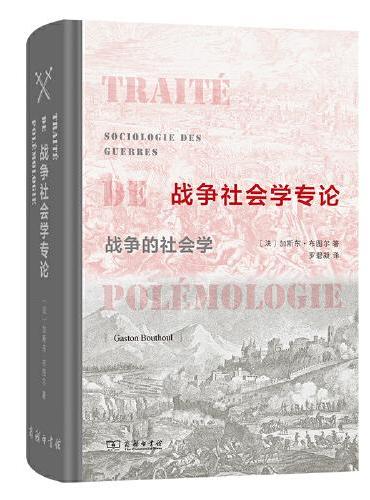
《
战争社会学专论
》
售價:NT$
5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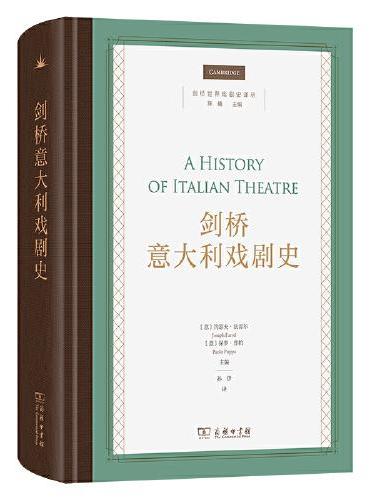
《
剑桥意大利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NT$
7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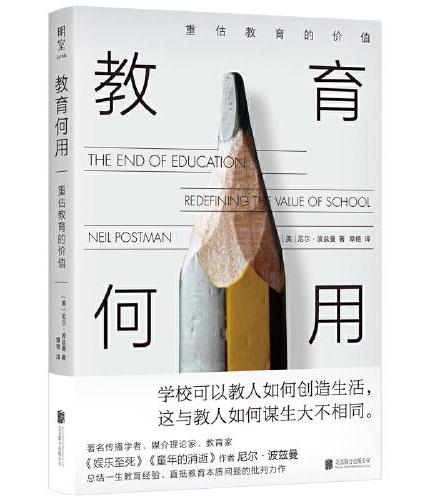
《
教育何用:重估教育的价值
》
售價:NT$
2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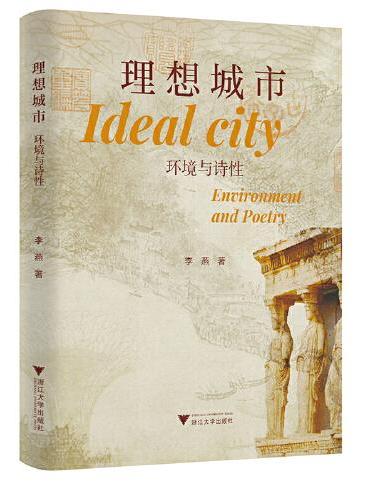
《
理想城市:环境与诗性
》
售價:NT$
3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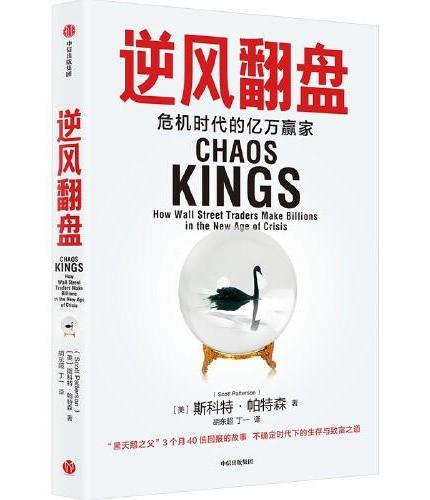
《
逆风翻盘 危机时代的亿万赢家 在充满危机与风险的世界里,学会与之共舞并找到致富与生存之道
》
售價:NT$
6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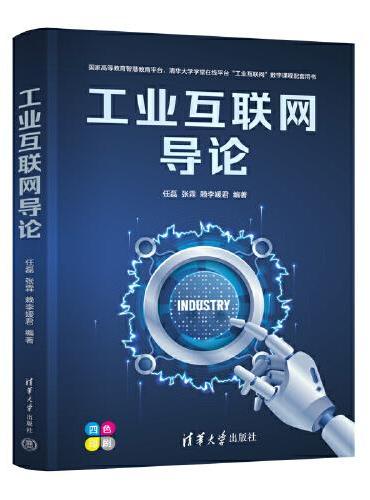
《
工业互联网导论
》
售價:NT$
445.0

《
孤独传:一种现代情感的历史
》
售價:NT$
390.0

《
家、金钱和孩子
》
售價:NT$
295.0
|
| 編輯推薦: |
|
张光直先生娓娓道来回忆其早年生活。一位考古人类学家的早年经历如何引发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关注。
|
| 內容簡介: |
|
作者回忆早年生活的自述作品。因祖籍台湾,台湾岛的形状像个番薯,岛上两三千万汉人自称“番薯人”,故以此名书。书中记述其家世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度过的孩提时代,重点追忆了18岁作为“政治犯”被捕入狱一年的特殊经历。这段经历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一生的志向,也由此引发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科学兴趣。
|
| 關於作者: |
张光直(1931—2001) 当代华裔考古人类学家。祖籍台湾,自称“番薯人”。50年代在台湾大学读人类学,师从李济先生。后负笈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院毕业。先后担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美国科学院及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
张光直一生致力于中国考古学与考古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通过一系列有影响的专著和大量学术论文,把自己祖国古代文明的丰富考古材料介绍给英语世界,更倡导以世界性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力求通过中国文明进程和发展模式的建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内涵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
| 目錄:
|
前言
父亲、母亲和他们的朋友们
北京的生活
师大第二附小和男附中
回台
40年代的板桥
建国中学
二·二八事件
建国中学(又一章)
四六事件
监狱生活
回到情报处
内湖
回家
后记
附录一 老兵的佛像
附录二 伐檀
附录三 小人物的速写
|
| 內容試閱:
|
拉丁语lpomea batatas,英语sweet potato,汉语“番薯”,是一种块茎类的植物,植物学家都说它起源自南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把它带到全世界去。它到明代末年才传到中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水手们把它传到了中国。这种作物非常适合中国山区干地,所以在中国长得十分茂盛。
拉丁语Colocasia esculenta,英语taro,汉语“青芋”或“芋仔”,也是一种块茎类作物,植物学家说它起源于东南亚,包括中国南部和马来西亚。它的年代与东南亚的栽培植物(例如稻米)一样地早,大约一万年以前。
1895年,大清帝国与日本打了一个大海仗,输得一败涂地,被迫将台湾岛给予日本。从此,台湾岛上的居民便成为“亚细亚的孤儿”。因为台湾岛的形状很像一个白薯,所以岛上两三千万的汉人常常叫他们自己为“番薯人”。我父亲就是一个“番薯人”,他在1924年从台湾到北京念大学;本来念的是中国大学,后来承吴承仕先生介绍,转到北京师大,在那里碰到我母亲。我母亲是湖北黄陂人,那年只有18岁。我父亲23岁,两人相恋,母亲家里不同意,两人便私奔台湾。在台湾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婚礼。证婚人林献堂先生,介绍人洪楢、王敏川二位先生,地点是在台北江山楼。从1926年到1941年,一共生了四个儿子一一光正、光直、光诚、光朴。
我们四个兄弟都生在北京,我们都是说标准的京片子,但是因为我们祖母不会说北京话,而且我家常常是台湾人在北京歇脚的地方,有很多台湾人来往,所以我们兄弟也会说台湾话,不过都程度不一地有点北京腔。我们从小学就不喜欢日本人,虽然学了六年日文,但是日文只能看,不能说,也不能写。我们自己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台湾人,是番薯人;但也是闽南人、中国人。
现在的台湾人也自称为“番薯人”,但是有一个新名词加入了族群语汇,那就是“芋仔”,指1945年以后来的外省人。胡台丽说“芋仔”这个词是1949年以后,从大陆来了六十万大军之后开始出现的。这些阿兵哥再加上之前来的外省人,被台湾人称为芋仔,或老芋仔。芋仔和番薯人现在被人为地界定为两个刻板印象:芋仔人不说台语,不与台湾认同,也痛恨日本人;番薯人说台语,本土性强,对日本人有亲切感。
我们一家人用新的语汇就无法分类。事实上,三四十年代的台湾人,都不能清清楚楚地分出番薯人和芋仔。在北京的台湾人,除了我们一家以外,且举几个例子:徐木生、张深切、黄烈火、柯政和、江文也、林焕文(林海音的父亲)、连震东、苏芗雨、赵炼、苏新、苏子蘅、谢文达、蓝荫鼎、郭柏川、杨开华(杨英风的父亲),这些人都可以说是以中国人自认的。但是今天认同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我相信他们都会很乐意地被叫做番薯人。但是别的称呼呢?我们无法知道。
我弄不明白的是:青芋在台湾已经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当代的政论家却用它来象征来到台湾只有半世纪的大陆人。而番薯这个植物在台湾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但却用它来象征台湾本土人。也许是因为我们台湾汉人的祖先抵达台湾和番薯来台湾的时间差不多同时,反而芋仔到达台湾的时间已经不能在人的记忆中回想得到。芋、番薯,都是象征性的言语,而象征是流动的。老芋仔本来指来台军人而言,现在芋仔又包括非军人。第二三代更没有一定的规矩来说了。妈妈也许是云林人,爹爹是上海人。自己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也许会说点闽南语,也许会几句家话,也许只会台湾国语。这种人,有时被父亲强迫说是上海人,有时随自己的意思说是台湾人,多数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人。
我知道我是哪里人。在三四十年代,只听见人说番薯人,与其相对的就是日本人、四脚(Sika)。将其包围的观念是唐山人或阿山。我和父亲都是唐山人或番薯人,这都是特殊的唐山人。40年代以后,族群的观念有连续的改变。但是,那是在这本书的故事发生以后的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