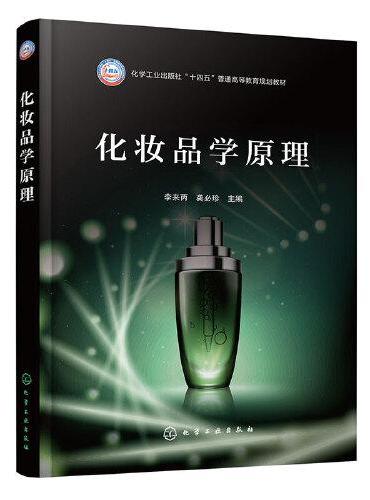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收尸人
》
售價:NT$
332.0

《
大模型应用开发:RAG入门与实战
》
售價:NT$
407.0

《
不挨饿快速瘦的减脂餐
》
售價:NT$
305.0

《
形而上学与存在论之间:费希特知识学研究(守望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译丛)
》
售價:NT$
504.0

《
卫宫家今天的饭9 附画集特装版(含漫画1本+画集1本+卫宫士郎购物清单2张+特制相卡1张)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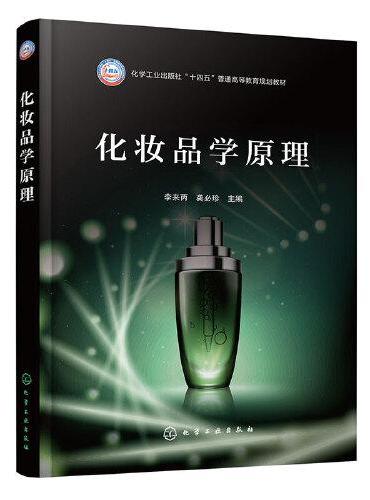
《
化妆品学原理
》
售價:NT$
254.0

《
万千教育学前·与幼儿一起解决问题:捕捉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教育契机
》
售價:NT$
214.0

《
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
》
售價:NT$
254.0
|
| 編輯推薦: |
|
恐怕没有比“魔都”更适合的词汇来概括1920年代的上海了。这里是国际大都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枢纽,拥有中西方文明冲突融合所造就的“魔性”,堪称近代中国的高度浓缩和真实写照。1924年,日本文人村松梢风*次使用了“魔都”来指称这座城市,描绘了黑白交织的城市面貌,新潮的社会风尚和市民生活,田汉、郭沫若等中国新文学家的风采……将近一百年过去了,具有标识性意义的“魔都”已经悄然成为了上海的代名词,拥有全新和丰富的内涵,但有一点承接了从前:象征着挑战与机遇并存、容纳多种文化的上海,拥有着令人向往的魅力。《魔都》是一部见证也是一个引子,可以启发对“魔都”意象追根溯源的思考,以及对中国、上海近代以来发展变化的感悟。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一部编译作品,从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所著的多部作品中选择与上海有关的文章汇编而成,主要为作者于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游历见闻。在本书中,村松梢风深入感受了上海的繁华街区、娱乐场所,参观了中国的新式教育机构,与中国进步文人进行了密切来往,游览了杭州、苏州等地的园林风景,其惊讶于国际大都市上海包罗万象的特质,使用了直观、生动的文字来描绘自己在上海的见闻,*次使用了“魔都”这一意象指称上海,体现了旧上海复杂多样的历史面貌。全书分为四辑,配有插图多幅。
|
| 關於作者: |
|
村松梢风(1889—1961),日本作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多次到中国游历,撰写了近十部有关中国的著作,与中国渊源颇深。代表作有被著名导演沟口健二翻拍成电影的小说《残菊物语》等。《魔都》是其在中国的部旅行记,也由此创造了上海的“魔都”意象,如今这一词语几乎已成为上海的代名词。
|
| 目錄:
|
译者前记
辑 一
3 扬子江
7 明亮的上海 黑暗的上海
22 夜上海
33 绿牡丹
44 田汉先生
51 新世界、大世界
56 参观学校
69 移居俄国人的公寓、友人来
78 《创造》同人
89 跑马
100 西湖之旅
114 归国之日
辑 二
119 乞丐与剩饭
127 梦寐之乡
129 中国的色彩
131 黄包车
142 欢乐之都
148 大世界 新世界—上海的民众娱乐场
156 赏钱
辑 三
161 车站一景
165 我观上海
170 跑狗
175 北四川路
177 俄国女郎
182 黑猫跳舞场
186 赌博馆
辑 四
193 风景的印象
196 建筑
200 中国的庭园
205 都市的风景
207 茶馆
211 中国菜肴
219 苏州游记
238 西湖游览记
|
| 內容試閱:
|
村松梢风(1889—1961)的作家地位在20世纪的日本文坛大概连二流也排不上,尽管他生前发表过几十部小说和人物传记,曾经有过不少的读者,他撰写的六卷本《本朝画人传》被数家出版社争相出版,一时好评如潮,1960年中央公论社在建社100周年时又以精美的装帧将其作品作为该社的纪念出版物推出,在日本出版的各种文学辞典和百科全书中,对他也有颇为详尽的介绍。不过对于梢风的小说,评论界一直很少给予关注,他撰写的作品,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故事,人文的内涵比较浅薄,除了作为大众文学作品集出过寥寥两种选集外,在文集、全集汗牛充栋的日本出版界,迄今尚未见到有梢风的著作集问世。这大概可以映照出梢风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指数。之所以要翻译出版这本《魔都》,主要是因为1924年梢风早创造出了“魔都”这一词语以及“魔都”这一意象。当年也许只是不经意间创造的这一词语,由于内含了太多难以言说的复杂的元素,或者说是较为准确地概括了混沌叠合、明暗相交的上海的各种因子,时隔将近一世纪之后,突然在如今的中国爆热起来,在说到上海时,差不多是一个使用频率的词语。事实上,“魔都”一词及其意象被创制出来的当时,在中日两国都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在日本,由于梢风的文学影响力有限,并未得到广泛的传播(间或有人提及),而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梢风的文学作品,他的《魔都》以及记述他在上海经历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上海》都没有被译介到中国来,因此这一词语差不多一直沉寂了几十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开始新的腾飞,上海的近现代发展历程又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瞩目。1995年,日本放送协会(NHK)派出了一批记者来到上海作专题采访,从历史的演绎来考察日中关系的未来,在当年的5月出版了一部《魔都上海 十万日本人》。2000年,来自中国的刘建辉经由讲谈社出版了一部日文著作《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介绍了20世纪初叶日本人与上海的关联。在此前后,日本一些报道或研究论文对上海使用了“魔都”一词,尤其是在日本的上海史研究界。梢风以自己的中国游历为素材所撰写的两部长篇小说《上海》和《男装的丽人》,近被东京的大空社作为“重刊‘外地’文学选集”的两种分别按原版本影印出版,标志着日本出版界重新注意到了梢风在这方面的影响。但在中国本土,“魔都”一词似乎仍然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我在2001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村松梢风的中国游历与中国观研究》(《日本学论坛》2001年第2期,后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选刊《外国文学研究》当年第12期全文转载),这或许是在中国早论及梢风与“魔都”的文章。也不知因何缘由,两三年前开始,“魔都”一词突然在中国蹿红起来,且往往与时尚和流行交织在了一起,染上了些许魔幻的色彩。但人们依然不怎么知晓这一词语乃是出自近一个世纪前的日本人梢风的笔下。其实,与同时代的谷崎润一郎[1]、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等相比,村松梢风在中国文史上的学养以及原本对中国的兴趣,都要弱得多。梢风于1889年9月出生于静冈县的一户地主家庭。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笔者未能找到青少年时代的梢风曾对中国或中国文史有兴趣的记录,他后来提到的孩童时代跟中国相关的记忆是,当年风行一时的所谓“壮士剧”中经常会出现作恶多端的中国人的形象,小孩要是不听话的话,大人就会用“小心被中国人拐骗了去”的话来镇住孩子。梢风在家乡的中学毕业后,来到东京进入了庆应义塾理财科预科学习,此时他才接触到日本的新文学,并由此萌发了对文学的兴趣。不久因父亲的猝然去世,作为长子的他只得返回家乡看守田产。其间在家乡的小学和农林学校担任过教员,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颇为倾倒的作家有永井荷风[2]和谷崎润一郎等,而卢梭的《忏悔录》更是他的不释之卷。从个人习性上来说,梢风不是一个安分稳静的人,他不顾自己已娶妻生子,常常一人跋山涉水,四出游行。“什么目的也没有,只是想到陌生的土地上去行走。喜爱漂泊,喜爱孤独。”[3]这一习性,与他后来的中国游历很有关系。他忍受不了乡村的沉闷,1912年又来到东京入庆应义塾的文科学习。这一时期他陷入了东京的花街柳巷,家中的田产也被他变卖得所剩无几,他一时感到前途困顿。恰在此时,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出兵,于1914年11月占领了原属德国势力范围的青岛。前途迷茫的梢风不觉将目光移向了中国。他想到这一陌生的土地去闯荡一下。这时他的一位师长辈的人物洼田空穗劝阻了他。洼田劝他不必急着到中国去,在这之前不如先锻炼一下文笔,在文学上辟出一条路来。于是梢风暂时打消了去中国的念头,一边写稿,一边帮朋友编杂志,以后又进入日本电通社做记者。1917年,他将写成的小说《琴姬物语》投到了当时影响的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得到了主编泷田樨阴的赏识,在8月号上刊登了出来。由此梢风在文坛上正式崭露了头角,作品频频刊发,知名度也日趋上升。梢风写的大都是传奇故事类的大众文学,渐渐他感到可写的素材已捉襟见肘,于是想到在人生中另辟一条生路,这就是使他35岁以后的人生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中国之行。梢风后来在以第三人称撰写的自传《梢风物语—番外作家传》中这样写道,1923年的上海之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受了芥川中国之行的刺激,但主要是他自己想去上海寻求自己人生的新的生路。从这意义上来说,他的意图可谓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而其结果是梢风将35岁以后人生中的十几年生涯沉入到了中国之中。”[1]这里所说的芥川的刺激,是指芥川龙之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的特派员于1921年到中国作了近四个月的旅行,回国后在报上陆续发表了《上海游记》等多种游记,后来集成《中国游记》一书出版。芥川那稍稍有些夸张的、多少有些寻奇猎异的文字无疑打动了梢风的心。梢风为此曾专程去访问芥川,芥川告诉他,写旅行记的要领是,仔细观察,随时在笔记本上详记所有的见闻。从梢风日后所写的游历记来看,可以说是深得个中三昧。1923年3月22日清晨,梢风从长崎坐船来到了上海,“说起我上海之行的目的,是想看一下不同的世界。我企求一种富于变化和刺激的生活。要实现这一目的,上海是理想的地方了。”据对各种文献的梳理考证,可知在1923年至1932年间,梢风总共到上海来过6次。次是1923年3月22日至5月中旬,约两个月,初抵时寄宿在西华德路上的日本旅馆“丰阳馆”,大约在4月10日左右,他移居到老靶子路[4]95号一处房东为俄国人的公寓(此建筑今日仍然留存)内。其间认识了在上海教授交谊舞(实际上是在西洋人开的舞厅内当舞女)的日本女子赤城阳子,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同居在一起。回国之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五万字左右的《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翌年以《魔都》为书名出版。第二次来上海,是在1925年4月初至5月10日左右,主要下榻在“一品香”旅馆。第三次来上海,是1925年6月10日左右至6月底,主要住在日本旅馆“常盘舍”。第四次来上海是1925年11月初,大约于11月底或12月初归国,长篇小说《上海》是对以上几次经历的自传体叙述。第五次是在1928年的秋天,访问的目的地主要是新近成了中华民国首都的南京,但登陆地是在上海,且也在上海盘桓了数日。第六次是1932年2月初,由日军挑起的中日武装冲突已在上海爆发,梢风为了要撰写一本记述事变的书籍,来到上海采访,待了半个多月。此后他又到中国来了好几次,除了上海和江南一带之外,足迹北及东北、热河,南涉台湾、广东、香港,有关中国的文字,仅结集出版的即有十本之多。此次将他有关上海的文字编选翻译出来,其意义大概有两个。其一是展现了梢风当年视野中的魔都上海,即1920年代的上海,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当年的上海,虽然总体社会环境动荡不安,然而因处于西方列强势力的卵翼之下,局部出现了畸形的发展和繁荣,差不多拥有远东繁华的商业和娱乐业,这就是梢风笔下魔都的所谓“明亮”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整个中国尚处于战乱状态,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各自为政,法律与行政都局限在自己的管辖区,因而上海也往往成了藏污纳垢的混沌之地,且由于战乱和部分农村破产,周边区域的贫民纷纷涌入上海,因而也就有了众多犄角旮旯的存在。梢风文章对有些历史实状的描述,在中国的文献中未必有详细的记载,或已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漶漫不清。他的文字,并非事后的回忆,而是即时的实录,且文字亦颇为生动,可权当一部黑白纪录片来观看。其二是反映了当时日本人中国观的一个侧面。来中国之前,梢风对于中国并无太多的学养和知识,相对成见和偏见也较为淡薄,在他的文字中所体现的,多为直观感受,鲜活生动,也不免有些肤浅低俗,当年日本人对中国的歧视,多少也有些流露。在文人中,他算是一个游荡儿,吃喝嫖赌都不会缺位,在这方面,与井上红梅有些相近,也因为如此,笔墨所涉,就相当广泛。开始的几年,他对中国相当痴迷,他也写苏州旧城的逼仄,古迹的颓败,写南京城区出奇的黑暗,写南京城门口人声鼎沸的杂乱和壅堵,写广州珠江上船民生活的诸种实相,写黄包车夫谋生的艰难。日本大正、昭和时期出版的日本文人的中国游历记,多达上百种,相比较而言,梢风这一时期对中国的描述不管是怎样的五色杂陈,却始终带着一种温情,没有芥川那样的冷眼。这种笔下的温情,构成了上海事变前梢风中国观的基本色调。需要指出的是,1932年1月28日爆发的一?二八事变(日本人称为次“上海事变”),成了梢风中国认识或者说对中国态度的一个分水岭。梢风从此前的中国赞美者,骤然变成了日本当局的同调者。严格地说,一?二八事变以后梢风到中国来已不是纯粹的游历了。这一时期他有关中国的著述结集出版的有《话说上海事变》(1932年)、《热河风景》(1933年)、《男装的丽人》(1933年)和重新编定的《中国漫谈》(1937年)、《续中国漫谈》(1938年),在战后有将以前的长篇小说《上海》和《男装的丽人》稍作修改后重新出版的《回忆中的上海》和《燃烧的上海》。虽然他对中国的情感依然无法割舍,但狭隘的日本人的立场却严重扭曲了他观察中国的视角,对此,我在《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1923—1946》一书中曾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这部译稿,一半多完成于1998年我在日本长野大学的任教期间,原本是应北京的一家出版社之约,将颇费苦心搜集来的梢风的文字选择一部分进行了翻译(当年还是手写稿),不意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又加上版权问题,译稿就一直被束之高阁,长期蒙尘。这次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肖峰编辑的鼓励,将梢风有关上海的文字编选了一部分,主要来自《魔都》《中国漫谈》《新中国访问记》《话说上海事变》。在原来译稿的基础上,又增加翻译了十余篇,其中重要的,就是《魔都》。另外,又加入了几篇有关苏州、杭州的旅行记,这几篇另收录在《中国的色彩》一书中,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另行出版,这是要对读者说明的,但《魔都》的文字是次在中国问世。对于本书中出现的一些旧地名和一般不广为人知的人物、事件以及有关日本的词语,译者做了适当的注释。
徐静波2017年9月24日,一个秋雨淅沥的周日中午
|
|